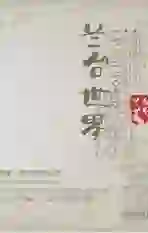近代边疆民族地区妇女就业
2020-04-22张丽虹
张丽虹
摘要 近代云南妇女参与就业的历史进程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近代云南敬节堂解散、提倡妇女就业自立;禁止缠足为妇女参与社会劳动扫除障碍;近代云南妇女参与农业、工业及服务业劳动。这一历程既具有中华民族一体化特征,又具有民族特色。
关键词 近代 边疆民族地区 妇女 就业 云南
选择从云南看近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妇女参与社会劳动这一论题进行研究,是因为在广泛阅读近代云南史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不少有关女性的档案文献,在之前所阅读的论文书刊中都没有刊载过。“对档案价值的研究要将档案与人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去阐释价值本质,这样或可对档案价值有更为全面、准确的认识”[1]27。
一、云南敬节堂解散,提倡妇女就业自立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面临帝国主义侵略,在与外部势力的矛盾、冲突中凸显中华民族的整体存在感,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认识逐渐形成。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95中华民国成立后,云南一地整个政治氛围中都弥漫着浓厚的民本思想。如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云南紧接着发生“重九起义”,云南都督府一成立即对各属声明:云南起义“其宗旨在铲除专制政体,建设善良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护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3]34。
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贞操观、提倡婚姻中的男女平等,对中国广大妇女、包括云南妇女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胡适在《贞操问题》中说,“因为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爱情,心思专一,不肯再爱别人,这就是贞操。贞操是一个‘人对别一个‘人的一种态度。因为如此,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4]30他的看法将贞操问题转变为男女平等、对妇女本身的关照问题。据档案记载,1948年国民政府依法作出撤销云南敬节堂的决定:“查敬节堂之设置,现行法无此规定,应予撤销。惟育幼养老系属社会救济事业,该堂取消后,其有合于法定应行救济者,由省会示范救济院接收;其年力强壮不合救济者,应即一律遣散,饬其自力谋生,以免养成依赖恶习,沦为惰民。”[5]国民政府不仅仅是不再褒扬节烈之风,而提倡就业自立是鼓励妇女与男性平齐、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二、禁止缠足,为妇女参与社会劳动扫除障碍
从当时大量官方文书看,云南解放妇女缠足运动早于全国。民国二年(1913),辛亥革命刚刚成功,云南地方政府军都督府民政长官罗佩金便颁布《云南通省妇女缠足惩禁令》11条,规定滇省妇女15岁以下者未缠足者不准再缠,已缠足者立即解放。直到1928年,南京中央政府才向全国颁发《禁止妇女缠足条例》,比云南晚了15年[6]96-98。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致使该民族地区反缠足运动领先于其他地区。如福貢设治局“夷民向无神祠朝宇,亦无神权迷信观念,妇女均跣足不履,向无缠足陋习……性爱平等,尚无蓄婢风气”;宁江设治局“地处边陲,居民多为夷、阿卡、猡黑等族,其妇女素无缠足习俗,以故全属天足”;河西县蒙古族“喜劳动善勤俭,女子全是天足”;平河设治局汉人妇女“染夷习,虽有穿鞋者,多系天足。偶有少数私自缠裹,严令解放,并布告各县,以期家喻户晓、并勒令以后不准再染缠足恶习。夷人妇女概系天足惟少数汉人妇女缠足者已勒令解放由”[7]。
到1946年,民国云南佛海、澜沧、丽江、五福、宾川、昆阳、昆明、车里、广通、江川、元谋、沾益、安宁、文山等近百县对政府提倡禁缠足作出回应,报告禁缠足工作完成得很好[8]。这一方面是近代云南政府30多年持之以恒提倡、督促禁止妇女缠足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少数民族妇女崇尚天足的风俗使然。正因为少数民族妇女参与社会劳动,所以经济和社会地位并不低下。这也是我们在看到一体化的同时不应忽视的民族性。
三、近代云南妇女响应政府提倡、参与农业劳动
据档案载,武定直隶州禄劝县知县童益泰编写《蚕桑弹词》,童益泰原籍江南水乡,“夙谙蚕事”;因云南气候温和适宜植桑养蚕,童益泰因地制宜,把江南经验介绍到云南。他编写的弹词采用对比的说明方法,说明云南人喜欢种烟或养鸟,都不如种桑养蚕好,因为种烟违禁、养鸟没有收益;并且针对云南妇女参与农事较少的现实,特别强调妇女在养蚕中的作用,引导云南妇女用自己的双手建立富裕的生活[6]59-63。而民国政府也提倡以种粮食等取代种烟,云南妇女响应号召禁烟种粮。以一份档案文献为例,“云南省政府主席卢钧鉴,案据镇雄县县长罗人吉签称为签请事。窃查属县陇确佐陇余太夫人,深明大义热心公益,举凡地方桥路学校无不慨捐巨款极力与办,早已口碑载道。尤是本区人民多偷种烟苗、憨不畏法,惟该陇余太夫人能守国法、恪尊禁令,对于其所属之佃户数千家,均事先告诫不准偷种,并常亲身督查其佃户皆听教训,故其辖境之内并无一株一叶、皆种粮食。如此贤能殊堪示范,为推行禁政起见,应请特予奖许,以昭激励。”[9]分析档案可知,镇雄县长罗人吉特请示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希望嘉奖陇余太夫人,以作示范。
由档案文献还可以看到,“清末云南在传统的封建农业生产关系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已经形成近代的股份制公司和民族资产阶级。”近代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妇女群体受其影响变化很大。传统农业劳动多为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所以农业劳动中男性一般较女性占优势;而近代农业劳动中增加了机械化成分、体力劳动强度逐渐降低,所以较之过去,女性可以更多地参与农业劳动。在《股份制农业公司的出现》一文中,有题为《昆明近郊,农村踩水车的农妇》的插图,结合文图,可以推断出在清末云南股份制农业公司的出现过程中,农妇参与了农业生产劳动[6]40-42。以植桑养蚕、种粮食替代种烟的生态化以及机械化的近代农业发展趋势首先出现在东南沿海和内地,而渐慕华风的边疆民族地区云南妇女不甘其后,在政府倡导下积极参与农业劳动。
四、近代云南妇女参加工业及服务业劳动
以云南纺织厂为例,分析工友类别、人数、工作时间及薪酬,“工人计分男女工友两种:男工一八零人,内技工纺纱运转部十八人,保全部十五人……女工六二零人,内技工三十人(包括纱布厂副教师及实验工),余为艺工和杂工。本厂工作时间采用三八制,每班工作二十四小时。男女技工最高工资贰元九角,最低贰元六角。艺工最高工资贰元贰角,最低壹元贰角。杂工统照论工计算,每日工资亦为壹元贰角,男女一律。”[10]这份档案表明:首先,云南纺织厂工作时间采用每班工作24小时、每8小时轮换制。一方面,采用机械作业,最高效经济的方法就是“歇人不歇马”,让机器24小时昼夜不停运转,以减少开机关机损耗,以及机器停工期的产出损失;另一方面,工人虽然每8小时轮换,但是夜班工人需要昼夜颠倒地工作,工作仍然非常辛苦。其次,虽然不同工种人数有差别,但是档案资料反映出男女同工同酬,这对于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相比起云南敬节堂的节妇,民国时期有不少云南妇女就业。她们不仅响应政府提倡积极参与农业、工业生产,而且在接受“边民教育”[11]117、专业教育训练后,在教师、医生、会计[12]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专业岗位就业。例如,据载1937—1943年云南省培训的卫生人员共426名,其中女性144名,占到33.8%[13]258-259。抗战时期,由于战争需要,云南妇女积极参与医疗、宣传等社会劳动,推动了云南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近代云南妇女的就业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中华民族一体化影响近代云南婦女的就业,这一变化具有不同于封建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内地化经营”[14]的人与人平等和关照妇女本身的本质特征。
近代中国妇女反对贞操观念、反缠足,参与就业。在这一过程中,地处边疆民族地区的云南妇女不甘落后,云南政府解散敬节堂、提倡妇女就业自立;近代云南妇女响应政府提倡,参与农业、工业及服务业劳动,在就业方面发生本质的变化,渐趋近于全国妇女的发展。这一历史进程具有近代中华民族一体化的特征。同时云南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其妇女参与社会劳动具有不同于沿海及内地妇女的民族特色。如民国时期在政府和组织开展大规模禁缠足的过程中,对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妇女而言她们不仅不是劝禁的对象,还不自觉地扮演了新风尚的引领者[15]182。说明近代云南妇女的变化具有民族多样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