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我与地坛》讲“宿命”
2020-04-20李广良
李广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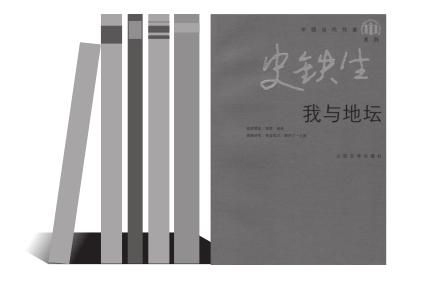
壹
《我与地坛》是一部动人心魄的杰作,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题材、它的写作手法、它的结构和它的文笔,而且是因为它的诗意、它的历史感和它的存在深度。
文章从“一座废弃的古园”开端。“古园”处于“废弃”状态,“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这个“废弃的古园”就是地坛,“地坛”是古园的名称,“废弃”是古园的存在状态。“废弃”并不是说古园不存在了,它还在那里,但古园在帝制时代所具有的祭祀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没有了,在旅游业兴起之前它也不是作为“旅游景点”而存在,它只作为“一座废弃的古园”而存在于世。然而,即使作为“废弃的古园”,地坛也没有退出現实的“生活世界”,它沉默而固执地挺立在那里,坚守着自己,并且在“因缘际会”之下成为史铁生文学创作和思想的源泉。
地坛与史铁生“有缘”,他之所以曾在好几篇小说中“提到过”地坛,因为他与地坛之间“缘分”“有着宿命的味道”,带有某种命定论的必然性。史铁生写道: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撤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记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
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
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在这里,“缘分”“宿命的味道”“上帝的苦心安排”等语词,似乎显示着在古园与史铁生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隐秘的关联,正是这种关联决定了史铁生的生命方向,决定了史铁生的感知、想象、思考和书写,决定了《我与地坛》奇迹般地“现身”于文学史上。
贰
一切文学都是存在者的存在的开显,是存在的保存,而保存存在,也就是保存历史、生活和思想。文学的力量就来自于其所保存的存在。存在包括物的存在和人的存在,前者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之存在,后者如贾宝玉、林黛玉等之存在,在二者之间,乃人和物之存在论关系。文学通过纯粹的文字保留物的存在、人的存在和人物之间的存在论关系,以此把真实的存在和存在的真实开显出来。
文学作品之成败得失,须在此存在论的视域中去观看。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之反映论,似乎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认识理论,其实质在我看来却是存在论,所谓“客观现实”其实就是“客观存在”“真实存在”之意,现实主义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最高典范正是基于其对存在的真实揭示。和所有伟大的作家一样,史铁生用他的文字书写了现实的故事,书写了真实的存在。
在存在论的视域中,《我与地坛》有三重书写:物的存在书写、人的存在书写和人物间性的书写。三种书写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缠绕的、内在贯通的,但我们仍然可以对其做分立的考察。
物的存在书写,是对“古园”及其中的物的存在的书写。“古园”是一个独立而开放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喧闹与静止、“活跃”与“沉寂”都有其存在论的隐秘。“园墙”、“金晃晃的空气”、“寂寞如一间空屋”的“蝉蜕”、露水在草叶上轰然坠地摔开的万道金光、草木竟相生长弄出的响动、满地上亮起的月光、车轮留在地上的印迹,以及那“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对蝉歌的取笑”“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耀眼而灼人的石凳”“爬满了青苔的石阶”“半张被坐皱的报纸”“一只孤零的烟斗”等,这一切都是一个世界及所有物的生机充满的展开。尽管经历了人的“肆意雕琢”,地坛的世界还有一些“谁也不能改变的东西”:
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
人的存在书写,是史铁生对自己的个体命运的书写,对母亲的“在”与“不在”的书写,还有对令人羡慕的情侣、热爱歌唱的小伙子、“一个真正的饮者”、“中年女工程师”、“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以及那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和他的哥哥的书写。一个“在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的、“被命运击昏了头”的“失魂落魄的人”,在古园里观察万物和众生,思考生死大事,看书和写作,“发脾气”或者“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沉郁”“哀怨”和思念,为了让母亲骄傲而发表小说,这是史铁生自己的存在。“她有一个长到20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这是史铁生母亲的存在。而文中所书写的其他人,每一个也都以独一无二的形象在古园中“出现”并“退场”,他们与古园的“缘分”有深有浅,但他们的存在却都是深不可测的。
人物间性的书写,是对在“我”与“物”、“我”与“他人”之间的原发经验的书写。在15年的时间里,除去几座殿堂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作者去过地坛的每一棵树下,在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留下了他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他都在这园子里待过。他在这园子里观万物荣枯,观历史盛衰,观众生生灭,观自身苦乐。他在看到了“时间”,看见了四百多年的沧桑;他看见了“茂盛得自在坦荡”的“野草荒藤”,看见了“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他看见了“自己的身影”,看见了“味道”中的“全部情感和意蕴”;他看见了母亲的“苦难与伟大”,看见了上帝和命运。他书写的不仅是“物”和“我”,而是在“物”和“我”的交感中所生成的“气机”“气韵”。
叁
文学不仅以描写、叙事和抒情的方式保留存在,而且以“思想”的方式保留存在。这思想可以在文论中“现身”,也可以在诗歌、小说和散文中“现身”。真实的思想可以以各种形式显现自己的存在。《我与地坛》之所以被人看作是“长篇哲思抒情散文”,就是因为其中充满了“哲思”,以文学的形式保留了“思想”,以“思想”的方式保留了存在和存在的问题。
史铁生思想的中心问题是生死问题,他从自己的“残缺状态”出发,直面生命的痛苦,深入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其实就是致力于存在问题的个性解答。他写道:
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
这是贯穿史铁生一生的根本问题,也是贯穿《我与地坛》全篇的主旋律。史铁生之所以反复思考生死问题,一是基于个体的遭遇,基于自身的困顿和母亲的英年早逝,二是基于80年代的时代和社会氛围,基于改革开放年代的思想状况。有人认为,《我与地坛》中有一种存在主义的意味,有萨特小说的味道,这与80年代的存在主义热有关。另外,史铁生反复提到“上帝”,这说明他很可能受到了基督教神学的影响。
然而,史铁生并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基督徒。他的作品中并没有萨特小说中的那种“荒诞”“恶心”“呕吐”等的经验描写,相反倒是充满了抗争的勇气、爱的激情、奋斗的精神意志和达观向上的生命态度。他反复提到的“上帝”,其实和“命运”“缘分”“宿命”“必然性”等是同一个系列的概念,具有差不多的内涵,指的不过是“整个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那些限制我们的外在必然性。这些外在的必然性,可以制约我们,但从不能真正打败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史铁生是一个“存在的英雄”,他的母亲和那些在艰难困苦中奋斗的人们也都是“存在的英雄”,他们深刻地体现了“存在的英雄主义”精神,即处身“艰难的命运”却仍然存有“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的精神。
史铁生深刻地发问: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
他的结论是:如果在人间彻底消灭了残疾,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样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即使算我们将丑陋、愚昧和卑鄙等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都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味健康、漂亮、聪慧、高尚,人间的戏剧也就将就全要收场。“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難,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
何谓“存在的本身”?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存在之为存在”?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实际生活经验”或“在世”?还是佛家所说的“真如实相”?或者是辩证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客观实在”?史铁生是否想过这些,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在《我与地坛》中,他说的就是人的“生活世界”的“存在”。这个“存在”不仅需要“统一”和“幸福”,也需要“差别”和“苦难”,没有“差别”和“苦难”,这世界的“存在”就将轰然崩塌,失去意义。故所谓“存在的本身”不过就是由对立的“差别相”构成的存在整体,一方面是“幸福”“机智”“漂亮”“善良”“高尚”“健康”等,另一方面是“苦难”“愚钝”“丑陋”“恶劣”“卑下”“残疾”等。相对于世人对前一方面的执着,史铁生更关注后一方面,这是“存在的本身”特地对他开显出来的。
“存在的本身”是无可逃避的,我们只能像史铁生一样地去担负起它。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