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闪的红星》为什么这样“红”
2020-04-20陈涛
陈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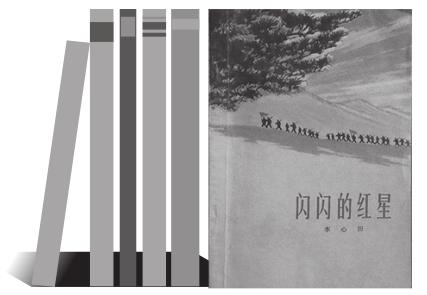
《闪闪的红星》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一部儿童题材的红色影片,于1974年10月1日上映。该片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集体改编,王愿坚、陆柱国执笔,李昂、李俊执导,祝新运、赵汝平、刘继忠等主演。电影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少年潘冬子在党和前辈的教育、帮助下逐渐成长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
对于这样一部经典的红色电影,我们在“重读”时,除却主题和叙事等层面的内容,更应当关注其形式和美学方面的特征,重读这一经典影片所包含的丰富美学意蕴。“红色经典”之所以经典,不仅在于内容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引导性价值,而且同其艺术语言和美学风格密不可分。
·“红色”的意蕴·
作为一种极富表现力的视觉语言,色彩在电影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革”故事片中的色彩往往兼具现实与象征的双重作用:一方面,这些影片通过色彩来表现秀丽竹林、苍茫群山、辽阔大漠、丰收盛景,以一种真实性的方式呈现人民生活;另一方面,电影也会用一种形式主义的方式来运用色彩,有选择性地采取不同色彩、光影甚至色调,来彰显特定造型、传达象征意义,甚至构成影片整体视觉风格。《闪闪的红星》也不例外。在影片中,江西竹林青翠的绿色、当地民居砖瓦的青色、土豪胡汉三衣衫的黑色等鲜明的色彩都令观众留下了印象,然而支撑起整部电影灵魂的还是红色。影片中众多红色的衣饰与道具(例如红领巾、红袖章、红衣衫、红领徽、红色的党旗以及漫山遍野的映山红等),具有强烈的造型和表现作用。尤其是片名中突出强调的“红星”,作为影片的核心意象,成为感召和引领主人公不断进步的动力和目标——而电影主题曲《红星歌》的歌词也清晰地点明了这一核心意象的象征意义。
除却造型和象征作用,“红色”在影片中也表达了强烈的抒情意味。电影借由色彩的运用,将画面点染出深远的意境,并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例如,核心意象“闪闪的红星”不仅隐喻了革命、正义和希望,而且寄托了少年主人公对红军父亲的思念和追随革命的信念。尤其在“小小竹排江中游”这一经典场景中,坐在竹排上的潘东子小心翼翼地取出用油纸包着的红星,阳光下的红星闪着璀璨的光芒,同波光粼粼的江面相互辉映,表达出画外音歌曲中“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的歌词意境。碧波、青山、翠竹、红星构成了诗意的画面,与优美的旋律和歌声相配合,共同表现出强烈的抒情色彩。
此外,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不仅彰显了春天的季节(及其所隐喻的革命胜利之意涵),而且作为红军归来的场景发生地,配合主题曲共同营造和烘托出一种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气氛和精神——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中前后两次出现的“映山红”场景在视听表现上具有差异性:前一次是潘东子想象中的画面,作为画外音的歌声来自于童声齐唱,音乐节奏较为欢快,画面则以东子的脸部特写为主;后一次是现实中的画面,已经加入红军的东子身着军装,同父亲和其他战士走在一起,歌声则由童声引入,继而以男女声合唱为主,音乐风格也从节奏感变为抒情性,配合交响乐器传达出一种壮阔宏伟的史诗感。
作为“文革”时期的一部“样板”式影片,《闪闪的红星》在“抒情性”和“三突出”之间进行了很好的平衡。根据导演李俊的回忆,影片一方面“不可能不受到‘三突出的影响”,大量情节(包括小小竹排、米店、母亲牺牲等)都是为了突出潘东子这一主要英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影片试图将“好的镜头、好的光线、好的色彩”同人物塑造相结合,因此“画面尽量拍得美一些”。正是这样一种在“抒情性”風格和“三突出”情节之间平衡的做法,为这部影片赋予了一种独特而崇高的美感,也令其具有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力。
·“全红”的奇观·
在这部影片中,“红色”不仅具有表现、抒情和象征的作用,而且在几个重要场景中构成了视觉上的整体色调,有意识地突显了一种“全红”奇观。这样一种“全红”视觉效果的达成,不仅源于色彩和光影的配合,而且需要借助红色滤镜完成。
在东子妈妈入党的影片段落中,整个房间都充盈着暖红色的光辉:一方面,导演将墙上悬挂的红色党旗作为画面中最重要的色彩构成,传达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另一方面,这一场景设置了两个重要的红色光源——一个是党旗背后窗口照射进来的主光源,另一个是从侧面窗户照射进来的红色线性光。在这里,电影大胆地借鉴了黑色电影中“百叶窗”式的线性侧光,并创造性地将其转化为红色,令场景中三个人物的脸呈现出一种立体感。红色布景、道具和灯光的配合,令场景中的一切都“沐浴在党的红色光辉下”。而演员的位置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三人中只有潘东子的脸是朝向主光源的,因此红色照亮了他全部的面庞,也符合“三突出”的人物塑造原则。
紧接着,当吴修竹开始讲述“从今以后,又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时,伴随着画外音《东方红》旋律的悠然响起,窗外透入的红色光芒变得更强,东子和妈妈也在红光之中深情而充满希望地呼唤:“毛主席!”此时,在下一个镜头中,伴着画外音旋律的渐强与激昂,画面中出现了一轮盈盈升起的红日,呼应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词内容。这一镜头加入了鲜明饱和的红色滤镜,令画面成为一种“全红”的奇观。这一“全红”的画面,并非再现该场景窗外的现实景象,而是具有强烈的象征意涵——或者说,从前一镜头中的红光到后一镜头的红日,任何自然的光源都无法提供如此纯正和完全的“红色”。
这一“全红”奇观在上世纪70年代的其他一些电影中也有类似的体现,例如1975的《海霞》在开头和结尾处的沙滩都加了红色滤镜,令其具有了强烈的情感色彩和象征意味;而1979年的《小花》在片尾出现了长达4分钟的“全红”画面,整个战斗场景都用以红色滤镜进行渲染。这些场景不仅将红色作为基本色调和光调,而且运用滤镜将整个画面处理为“全红”,彰显了这些影片强烈的形式主义风格,也从某种程度上呼应了“祖国山河一片红”这一“文革”时期的经典话语。
这样一种“全红”奇观的塑造,同新中国成立后胶片和染印技术的更新与突破密不可分。自从1953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制作完成,我国的彩色胶片经历了从国外引进到自主研发的过程,而彩色电影生产技术的突破同其他工业、军事领域的技术革新一样,被纳入“自力更生”的语境中,成为民族自豪感的源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同影片《第二个春天》中早出“争气船”、《火红的年代》炼出“争气钢”一样,新中国影片中色彩(尤其是红色)所体现出的“自力更生”的民族自豪感,是彩色片本身所具有的重要象征意义。然而事实上,正如新中国成立后的其他一些影片如《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青松岭》等,《闪闪的红星》并未采用国产胶片,而是使用了进口的美国柯达公司的伊斯曼胶片,这主要是考虑到其更好的显色能力。正因如此,观众不仅能够看到“全红”的奇观,而且发现影片在色彩上具有高饱和性和高对比度的特征——于是绿水、青山、红星、蓝天等意象变得更加鲜明突出,电影镜头也处处表现处出一种“如画”的视觉效果。这样一种使用进口胶片的做法,似乎脱离了民族主义的诉求,却体现出当时审美主义或美学追求的重要性,从侧面说明了色彩对于当时艺术创作和文化宣传的作用。
·“火红”的情状·
影片中另一处重要的段落是“火海献身”:东子妈妈为了掩护乡亲们转移,不幸被白匪放火烧死。电影并未正面表现东子妈妈在火海中的形象,而是以全景和远景拍摄了着火的小屋,同时东子和乡亲们的脸庞被火光照射得通红,“火紅”的愤怒从火海传递到人们的脸上,再传递给银幕前的观众。这一场景的画外音是影片中另一首经典的插曲《映山红》。与第一次出现(潘东子和妈妈在冬日山里盼望红军)时的抒情性不同,此次的歌曲在风格上昂扬激愤,歌词“映山红哟映山红,英雄儿女哟血染成;火映红星哟星更亮,血染红旗哟旗更红”不仅直接塑造了“英雄儿女”的形象并填补了画面中未出现主体的空白,而且将多种不同的“火红”意象(红星、红火、映山红、鲜血、红旗等)熔于一炉,突出了“革命鲜花代代红”的主题。

在这一场景中,“火”的意象成为一种“情感”的动力,将诸多“红色”的激情通过蔓延(火焰、火光、火红)的方式进行了传递。在《闪闪的红星》“火海献身”这一经典段落中,高强度的“红色”同燃烧的“火焰”一起,配合激昂的歌曲,共同推动了银幕内外“同仇敌忾”的情绪与情感——“红色”的火焰不仅激发了影片中人物(东子和其他群众)的革命情绪,而且唤醒了观众热血沸腾的情感,于是也“点燃”了观众的“怒火”。这样一种从银幕内“感染”到银幕外的情感,彰显了“火红”影像(色彩、特写、声音、道具等)的“情状”特质。而电影也在此为这种情绪和情感提供了行动指南:这一段落在结尾处,画面从火焰的意象叠化为飘扬的红旗,清晰地点明了“复仇”与“革命”的路径——只有共产党和红色政权,才能打倒反动派和土豪劣绅,建立幸福美好的新中国。
从红星到红旗,从红灯到红花,从红霞到红歌,我们对于“文革”电影的记忆,似乎沉浸在一片红色之中——正所谓“祖国山河一片红”。而《闪闪的红星》作为“红色”经典的代表性影片之一,在这一片红色记忆中尤为闪耀。由此可见,“红色”不仅仅是内容、主题或意识形态的表达,更是形式、风格和视觉美学的建构:从造型到象征,从抒情到奇观,从动力到情状,“红色”的意蕴不仅是复杂和多元的,而且同材质与传播密不可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