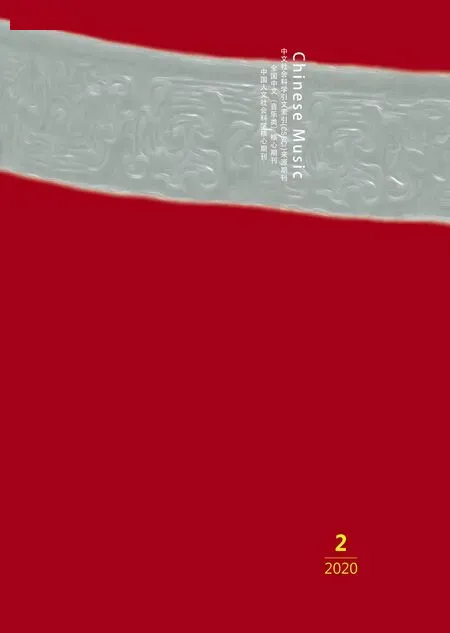“中国史学家的学术视野—礼观乐史”系列讲座思想述要
2020-04-18
引言
自2019年3月21日至6月20日,我校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研究基地成功主办了“中国史学家的学术视野—礼观乐史”系列讲座。“礼观乐史”的立题目的,就是求索儒家“礼乐”思想体系历经历史流变之后,在中国史学家不同的学术视角中,是如何聚焦和成为各自学问的。此系列讲座的应用目的和现实意义,是为师生提供一个学术平台,学习、了解和借鉴中国史学家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及学术精神,并以此拓宽我们的音乐历史研究视野,同时,鞭策、激励我们每位同仁,及各位今方少年同学,为实现学校部署的“承国学、扬国韵、育国器、强国音”的办学理念,砥砺奋进。现将讲座所涉及到的思想内容述要如下:
一、探赜篇:“礼乐”文明的特征研究
“礼乐”文明,彰显着中华民族文明的特质和文化心理的价值取向。究其学术本质而言,“礼乐”就是求索天、地、人的和谐关系,求索社会秩序中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学问。可以说,“礼乐”作为文明象征而历古续今,乃是国内外历史学家们十分关注的学问。
宫长为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讲演“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理论与实践”(2019年4月25日)中,介绍了国际通行的三个文明判断标准,即城市遗址、文字和礼仪建筑。结合中国文明的特点来看,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将冶金术作为文明的判断标准之一,这有助于我们对中华文明历史的探索。他认为,就文明的特征而言,可将中华文明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就文明的历程而言,亦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前5000年是中华文明的奠基阶段,中间的3000年是中华文明的开创阶段,后2000年则是中华文明的发展阶段,距今100年是中华文明的转折阶段。随着考古事业的发达以及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意义会逐渐显现,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深刻。
宫长为先生的讲演“国学与国学新思考”(2019年5月9日)在阐述学习“国学”重要性的同时,一方面强调“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另一方面,主张既要重视“国学”,也要尊重佛教、道教等其他文化。“国学”代表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谓近现代的“国学”“国学热”等概念,是不同时期的学人应对“西学东渐”的文化潮流提出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
对于以“承国学、扬国韵、育国器、强国音”为办学理念的中国音乐学院师生来说,继承与传播中国“礼乐”文化乃是源自薪火传递的历史责任。“国学”的核心内容,正是“礼乐”文明生生不息的存在体现。的确,如果我们没有对“礼乐”给予足够理解,就不能够真正或全面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现在正处在面对世界文化、接受世界文化、影响世界文化的重要时间点上,如何看待“礼乐”文明,即“礼乐”文明到底是我们向世界讲述中国音乐文化的优势,还是趑趄不前的负担,解答这一问题,亟待需要一个或多个学派的担当。这是中国音乐的根本问题,正如宋代儒家程颐所云:“推本而言,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
常怀颖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在讲演“考古学视野中的古代中国乐制和礼乐起源”(2019年3月21日)中,以考古学的视野,阐述了他对中国古代乐制和礼乐起源问题的理解和思考。其中,他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晚商墓葬中的编列小铙、鼓、埙、磬等乐器,据此,他认为:“殷墟时期已经开始把乐器纳入礼制器用体系之中,用以规范社会秩序,标识身份等级。‘礼乐’制度的雏形,在殷墟时期已开始构建并出现。”常怀颖先生对晚商时期“礼乐”制度雏形的判断,是基于考古学的视野而提出的。对于夏、商时期的“礼乐”探索,学界往往借用《论语》所载的一段话作为史料的支撑,即孔子云:“(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段话的大意是:“殷代袭用了夏代的礼制,其内容的增减是能够知道的;周代袭用了殷代的礼制,其内容的增减是能够知道的。”
据此而言,随着学界对商代“礼乐”研究的深入,以及相关文献和文物的出土或发现,必将使这些历史久远的规范等级、秩序的“礼乐”制度之用,清晰于今。
常怀颖先生在讲演“周代乐钟使用的等级、性别与使用目的”(2019年3月28日)中,从西周时期北方地区的葬乐、东周时期北方地区的葬乐、西周至春秋时期楚地的葬乐、西周至春秋的“窖藏”乐钟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其中,讲演涉及到了不同时期随葬制度和习俗,以及随葬制度规律化,因地域不同所形成的差异,且因镈钟配合编组所反映出的不同等级特征等问题。常怀颖先生认为,周时期的北方地区乐钟性别差异较为明显,与西周时期相比,东周贵族女性用钟更加普遍,东周大部分国君与其夫人虽然都用钟,但编组与埋藏方式都有差别。不仅如此,除了丧葬,在生用、祭祀方面,东周女性贵族也较西周时期更为普遍地使用乐钟。值得注意的是,常怀颖先生认为,在随葬的编列乐钟之外,楚地的“窖藏”中少有其他器物伴出,往往是以钟镈单独瘗埋。即便多钟共瘗埋的现象,也多不能成列,这应该是由楚地早期土著人群的信仰所致,它很可能属于山川祭祷或其他祭祷活动的遗存,应属于“祭坎”或“瘗坎”性质。其存续时间,与楚乐制的形成几乎同步。
由此可以看出,两周时期的钟镈使用制度从逐渐规律化、规范化,到出现“僭越”的使用情况,实际反映出的是社会之变,以及由百家争鸣而激荡出思想之讴,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学术思想史。
刘国忠先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曾国之谜的提出与破解”(2019年4月4日)讲演中,从文献学和考古学的角度,向师生们介绍了提出探索曾国(即随国)之谜与破解曾国之谜的全过程。
刘国忠先生指出,北宋时期,在湖北省安陆县一带曾经发现过两件曾侯钟,且记载于宋代金石学家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之中。需要说明的是,薛尚功借鉴了赵明诚《古器物铭》的说法,认为铭文中的楚王章即楚惠王,器作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然而,薛尚功对曾国的属性没有给予具体的阐明。直至清代,又有学者阮元提出“曾当为鄫,夏之后”(参见《积古》)之说,指出铜器铭文中的“曾”就是文献所记载的山东之“鄫”。这个说法一直影响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学界的大多数研究者都认同此说。20世纪30年代,在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出土了楚幽王墓中的一对曾姬壶,其中的铭文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即:“唯王廿又六年,圣桓之夫人曾姬无卹。虞宅兹漾陵蒿间之无匹,用作宗彝尊壶。后嗣用之,职在王室。”刘节先生判断,其中的“曾”不是以往古书所提到的姒姓缯国(在山东旧峄县东),乃是姬姓之国。需要提示的是,在我国古代历史中,被称为曾国的地方可不止一个,除山东的鄫国之外,还有河南郑地的曾国,继而断定“曾人之足迹北起郑郊,南及光州,西起南阳,东抵睢州”。之后,湖北、河南等地相继出现了反映春秋时期的曾国青铜器。特别是1978年,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出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礼器、乐器、金器、玉器、漆器、兵器和竹简等,共计15000余件。其中,曾侯乙编钟引起国内外的广泛重视,但是,索遍先秦史料,则不见这个姬姓曾国的任何史料。1978年10月4日,李学勤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曾国之谜》一文中,一方面肯定了刘节的说法,即曾国是姬姓诸侯国;另一方面,李先生认为曾国人的活动范围并非刘节所判断的曾国位于河南中南部一带,而是在湖北北部的汉水以东范围。李先生认为,曾国已在《左传》(譬如,在《左传》中载:“汉东之国,随为大。”)等先秦典籍中有所记载,只是这个国家的名字不叫作“曾”,而是叫“随”,且“曾”“随”之称,乃为一国两名。由是,李先生判断曾侯乙编钟其中有一枚是楚惠王铸赠送曾侯的镈,所以给予曾侯这种礼遇,乃是因为公元前506年,吴国攻入楚国郢都,楚昭王(楚惠王的父亲)仓皇出逃,在这危难的时候,随国保护了楚昭王。最终,楚昭王在秦军帮助下,恢复了楚国,楚惠王为了报答救父之恩,故而赠镈,亦即李先生所判断:“就是保护了楚昭王的随君的后裔,楚惠王铸编钟来祭享他,正是报德之意。”李学勤先生陆续发表了《论汉淮间的春秋青铜器》《续论曾国之谜》《新见楚王鼎与“曾国之谜”》等文,阐发思想。伴之与2010年底至2013年,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葬群的发现,有关“曾国之迷”的探讨逐渐趋向高潮。其中,叶家山M111(曾侯犺)中的五件套编钟(四个甬钟和一个镈钟)的出土,比曾侯乙编钟早了500多年。2009年,湖北随州文峰塔发现的曾侯與编钟,对于解开曾国之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中,在一号钟铭有:“伯括上庸,左右文武,挞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君此淮夷,临有江夏。”(伯括,即南宫)“吴恃有众庶,行乱,西征南伐,乃加于楚。……有严曾侯,业业厥圣,亲搏武功,楚命是靖,复定楚王。”铭记了先祖“南宫括”受命于周王所赋予的嘱托“西征南伐”至楚的事迹,从而为最终破解曾国之谜,提供了直接的文献依据。
历史是问题的提出者,也是问题的解答者。历史之谜的破解,缘于对历史的审视、发现和求索。“曾国之谜的提出和破解”,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解读和判断曾侯体系的“礼乐”文化,乃至由此对曾侯级别“礼乐”系统谱序的探索,所衍生出的两周时期音乐历史、音乐生活、音乐风俗流变的特征,提供了富于建设性的学术视野。
二、索隐篇:“礼乐”文明的释义研究
王志平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在“出土文献中与先秦诗、乐有关的几个问题”(2019年5月30日)的讲演中,从“出土文献与先秦诗、乐”和“先秦诗、乐中的几个问题”两大方面,阐发了他对先秦诗、乐的研究心得。
首先,王志平先生谈及“出土文献与先秦诗、乐”这一问题时认为,所谓出土文献,其实是包括了金石、简帛等文字资料的概念。其优势是,这些文献未曾经过篡改,是难得的第一手研究素材。近些年来,由于简帛文献层出不穷,比如,阜阳汉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清华楚简、安大楚简(即安徽大学楚简)等这些新发现,为我们认识先秦时期诗歌与音乐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场景和细节。其中,有一些与先秦诗、乐相关的内容前所未见,令人耳目一新。特别是很多出土资料亟待学术界重新思考先秦诗、乐的关系定位。王志平先生在这一部分中,涉及到了他对“甲骨文、金文、石刻中的诗、乐因素”的理解。其中,在“甲骨文中的诗、乐因素”部分,提及到了在甲骨文中乐舞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和著述,譬如,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释和言》、裘锡圭的《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丰”“鞀”》(附录《释“万”》)等,对于古文字中的“龠”“箫”“笙”“镛”“丰”“鞀”等几种乐器以及“万”舞作了考释;在“金文中的诗、乐因素”部分指出,在发现甲骨文之前,金文的重要性是其他形式的文献无法比拟的,即便是现在,研究西周或东周时期的出土文献依然需要以金文为主。西周金文除了文体多变之外,文学色彩也很浓厚,文中大量押韵,显得声调铿锵。春秋时期的青铜器更重视工艺,轻视文字,铭文开始出现衰微。但是,在一些乐器中,也保存了难得的字数较多的铭文,譬如,在《齐侯镈》中有174字;在《洹子孟姜壶》中有143字;在《秦公钟》中有135字等。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叔夷钟》(又名《叔弓钟》)由七个编钟组成,总计有铭文501字,是春秋金文中最长的,等等,兹不赘述。王志平先生在“石刻中的诗、乐因素”部分认为,所谓石器题铭,是指铭刻或者书写在石器上的文字,并非仅指石器题名形式,而石器题铭形式的出现与甲骨文几乎同时。在殷墟遗址中,曾出土过石器题名的商代石簋、石磬等,其最著名的有《小臣系石簋》,铭文共有12字,还有《妊竹石磬》,铭文共有四字。王志平先生认为,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战国之际秦国的“石鼓文”。据说原物共有十个石鼓,每鼓环刻四言诗一首,文体模仿《诗经》,现仅存300余字,据推测原文应有600余字。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重印弁言》中指出:“石鼓文是诗,两千六七百年前古人所写所刻的诗遗留到现在,这样的例子在别的国家并不多见……故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石鼓文不仅直接提供了一部分古代文学作品的宝贵资料,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民族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诗经》的真实性。”由此而言,“石鼓文”在音乐文学方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简牍帛书中的诗、乐文献”部分中,王志平先生指出:“出土简帛也分两种基本类型:即文书和文献两种。文书近于档案,文献才近于典籍。不过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些都是史料。”在此,王志平先生强调了“出土简帛(即简牍帛书)”的重要性,他认为其中包含了传世古书、新出佚籍。对于传世本的古书而言,简帛本的重要性在于为其提供了最早的原始祖本;对于未传世本的佚籍而言,简帛本的重要性则在于为学人提供了前所未闻的新知。譬如,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了楚简805支。其中,包括《老子》甲乙丙本、《太一生水》《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尊德义》《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六德》《性自命出》《缁衣》《五行》《语丛》(一至四)等。对此,李学勤先生指出,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前半部分,对“礼”与“乐”的关系,“礼乐”与“性情”的关系,以及“性”与“天命”的关系,给予了精练的阐述,其思想对探讨早期的儒家文艺学说具有特殊的价值。
其次,王志平先生论及“先秦诗、乐中的几个问题”时认为,出土文献为我们研究先秦时期诗歌与音乐遗留了诸多问题,比如,“诗”“乐”“舞”之间的关系,《诗经》与《楚辞》之间的关系,先秦礼、乐之间的关系,以及《乐经》与《乐记》之间的关系等等,都在新的材料下获得了新的认识。王志平先生在阐发对“诗、乐中的‘终’与‘章’”的认识时,以为它们是关系非常密切的同义词。”以“清华简”中乐诗为例,他认为:“从清华简中我们知道,简诗《乐乐旨酒》《輶乘》《赑赑》《明明上帝》只有一章,也只有一终;从单一篇章来说,所谓‘一终犹言一章’并没有错。可是简诗《蟋蟀》分为三章,却也仅有一终,说明‘一终犹言一章’仅适用于单一篇章,而对于重奏复沓的多篇章来说,则不适用。”由是:“从乐诗角度来看,每一篇乐诗都有相应的‘曲折’,即使有重奏复沓的许多章,其‘曲折’(乐谱)仍然是贯穿始终的那个首章的旋律。所以无论是单一篇章还是重奏复沓的多篇章,其‘曲折’(乐谱)都只有一篇。也就是说,无论篇章多寡,一首诗对应的都是一套大曲。从诗乐对应的角度来说,诗的一篇就是乐的一终。即使诗分三章,乐奏三次,仍然只能算作一终。”继而“‘每曲一终,必变更奏’,如果一首乐曲翻来覆去地演奏,其实还是同一个旋律,并没有产生变奏。只有改换乐曲,才能说‘曲终变奏’。因此,一章一终的说法显见不能成立。”值得注意的是,王志平先生还以“清华简”中《周公之琴舞》为例,即:“周公作《多士敬(儆)怭(毖)》,琴舞九絉。……成王作《敬(儆)怭(毖)》,琴舞九絉。”对此,他认为:“而我们读‘絉’为‘肆’,即用于乐舞之‘佾’字。所谓‘琴舞九肆(佾)’,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出土向我们展示了古代诗乐‘弦之舞之’的本来面貌,为两千年后深入探讨古代乐制打开了历史之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目前,我们对甲骨卜辞、金石、简帛等文字资料中的音乐现象,以及音乐与人的关系等问题的探索,尚未形成体系性的研究。不论是郭店楚简研究,还是清华简研究,对中国音乐的学术未来如何在传世文献基础上,且结合20世纪与21世纪的“新发现”来挖掘、拓展和激发今后的研究与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促进意义。
宋镇豪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殷墟甲骨文中的乐器与音乐歌舞”(2019年6月6日)的讲演中指出,殷墟甲骨文中记有齐备的乐器品类,且有许多的乐歌名和不同的舞蹈形式,以及乐师“多万”和“舞臣”的专门分工,体现了殷商时期的“礼乐”制度在生活实践方面的应用。
在讲演“甲骨文中的乐器”研究时,宋镇豪先生例举了殷墟甲骨文及石器刻铭中的鼓、庸、丰、鞉、竽、熹、磬、龢、言等20多种乐器。他以鼓为例,认为,“壴”与“鼓”通。所谓“玉壴”者,乃是特喻其鼓有精致的玉饰品。鼓是商代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礼乐器之一,通常在祭祀活动,或在宴飨等重大活动中应用。古人以鼓声来引导祭祀仪式或宴飨活动的节奏和速度,使其有序。在甲骨文中所记的那些形制不同、大小不一、用途各异的鼓,基本能够与商代鼓乐器的考古得到印证。譬如,1977年,在湖北崇阳汪家咀出土了一件商代的铜鼓,通高75.5厘米,鼓面直径39.5厘米,重达42.5公斤,遍饰云雷纹,鼓身上有带系孔的钮饰,下有托座。再譬如,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收藏了一件晚商时期的铜鼓,通高82厘米,鼓径44.5厘米,且上有双鸟钮饰,下有四足,鼓身饰以夔纹,鼓面铸成鳄鱼皮纹。值得注意的是,两鼓的共同之处,都是既可以置奏,也可以悬而奏之。宋镇豪先生还介绍了在河南安阳西北岗第1217号殷王陵出土的鳄鱼皮鼓,其鼓长68厘米,鼓面直径60厘米,以及在山西灵石旌介遗址的商代一号墓葬中出土的朱漆鼍鼓,其鼓面直径约30厘米,且残留有鳄鱼鳞片。
在讲演“甲骨文中的音乐歌曲”时,宋镇豪先生例举了在殷墟甲骨卜辞中所记载的有关音乐歌舞之名的文献。譬如,
叀商奏。
叀美奏。(《合集》33128)
[贞]其奏商。(《屯南》4338)
[甲]申卜,舞,叀戚。(《屯南》2842)
万舞,其……(《屯南》825)
叀林舞,又正。
叀万乎舞(《合集》30028)
等等,兹不赘述。其中,宋镇豪先生认为,“林舞”与“万舞”对贞,应是指不同形式的两种祭祀舞名。“万舞”亦即《诗·商颂·那》中说的“庸鼓有斁,万舞有奕”之“万舞”。这些均体现了不同的祭祀音乐或舞蹈活动。
殷商王朝的乐舞,每有其人负责教授。譬如,有卜辞云:
丙戌……多万……入教,若。(《英藏》1999)
宋镇豪先生认为,“多万”即是从事舞乐工作的“万”人之群称,他们有时充当执教者的角色,即所谓的“乐师”。
总而言之,在殷商贵族社会生活中乐舞的应用性很强,它集合了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思想,彰显了以占天卜地、威仪序政为特质的商代“礼乐”体系。其甲骨文中诸多祭祀乐舞形式,不同类别的乐器形态,加之乐师“多万”和舞者“舞臣”的专门分工,印证了商代音乐、歌舞与器乐的繁盛。
三、钩深篇:“礼乐”文明的兴衰研究
彭林先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从正史《礼乐志》看儒家礼乐思想的边缘化”(2019年4月11日)中开宗明义:“中华是礼仪之邦,儒家是礼治主义者,礼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而在秦汉以后,儒家礼乐思想经历了来自外力的两种位移,一是被边缘化,二是被妖魔化。前者主要是执政阶层对礼乐的理解似是而非,因而日益远离礼乐的本义;后者主要来自近现代思想界和某些政治人物对礼的过度批判以及恶意诋毁。”
在彭林先生看来,由于夏代的传世文献不足,故而难于征考,因此,论述夏代的礼乐文化是有难度的。商代崇尚鬼神,人们的礼仪活动大多以祭祀鬼神为主,也可称之为“器以藏礼”的时期。周武王克商之后,加之周公“制礼作乐”,彰显人文之德,此为西周人本主义思潮之兴起。对此,王静安先生说,周公“制礼作乐”之举,乃是“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代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自春秋以来,社会因“礼崩乐坏”而出现道德凌迟的局面,直至孔子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倡导“克己复礼”,以求重返西周“礼乐”,拾缀西周人文之精神。基于此,子思学派,求索以人心明道救世,修德守善,树立了以天、道、性、命、情为主的心性之学,主张以性情为本,将“礼乐”为修身之用,且注重以礼节性、以乐化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乃是子思学派对儒家“礼乐”思想的凝练,体现了儒家对人的情感与和谐社会的关系而进行的理论探索,儒家礼乐思想由此开始走向成熟。在子思学派看来,“情”是“性”的现实具体体现,由是,提倡以“始者近情,终者近义”,强化了儒家现实性格和实践精神。儒家“礼乐”思想内涵在历史中不断地丰富,并逐渐走向成熟。儒家深谙“礼乐”对人的道德和精神的“化性”作用,正如《乐记》所云:“禽兽知声而不知音”“众庶知音而不知乐”“惟君子能知乐”。彭林先生认为,除《史记》《南齐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中礼乐排名一、二之外,其余排序皆有后移,而且《隋书》《旧唐书》直接以“音乐”二字连用命名,把声、音、乐三分(禽兽知声,众庶知音,唯君子为能知乐)的界限打破,降低了“乐”的地位。彭林先生对于正史中所出现的《礼志》《乐志》之名被改的现象是这样认为的:“《后汉书》将《礼志》改名为《礼仪志》,可谓缺乏礼学常识,由此而开一恶劣的先例,《隋书》《旧唐书》也随之将《礼志》改称《礼仪志》,令人失笑。”且:“无独有偶,《旧唐书》在将《礼志》改为《礼仪志》的同时,也将《乐志》改为《音乐志》!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似乎并无实质变化。但从儒家礼乐思想的角度来看,却是一种颠覆性的窜改。”
儒家“礼乐”之论,意在寻求人之性情得其正,社会秩序得其正,道德理义得其正。彭林先生通过正史《礼乐志》排序变化的整理,以求对儒家“礼乐”流脉的梳理,印证了儒家“礼乐”边缘化的历史过程。此举,具有端本察变的学术意义。
彭林先生在“《周官》‘六代大舞’说考辩”(2019年4月18日)中,立足于儒家经典文献,以及历代儒家对经典文献的注疏,介绍了他对“六代之乐”的考证心得和对“六代之乐”是否为后世学家附会之说的思考。
首先,彭林先生从历史学研究的动态导入,强调要时刻关注考古的新发现,才能站在学术的最前沿。他认为,“六代大舞”的说法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从考古学上说,研究夏代的考古学家目前还不敢确认,更何况黄帝、颛顼、尧的时代,因此,黄帝时期、帝尧时期的乐舞就很成问题了;其二,史料的年代存在真伪的情况,彭先生对此作了考证,认为“六代大舞”说源于《乐纬》,而《纬书》本身就不可靠。
其次,《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有《云门大卷》《大咸》《大》《大夏》《大濩》《大武》等乐舞名,而未提及其所属年代。其年代是郑玄以之与黄帝以下六代之王对应,为《周官》作注时加进去的,经后世经师孔颖达、贾公彦等附会,殆成定说。《云门大卷》《大咸》所处的时代,本身就是东周百家为高远其说而编造,创出“三皇五帝”之说。
最后,彭先生说:“《周官》所列《云门大卷》等乐舞名,乃是采缀《乐纬》《元命包》而成,不可置信。周代庙堂乐舞,不过《韶》《夏》《赉》《武》;而以文舞(籥舞)、武舞(干舞)为主体。所谓六代之王有六代之乐,乃后世学者据《乐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铺衍而成。《周官》以《云门》等祭祀天地四方百神,乃至特祭先妣,均违背史实,不可采信。”
彭林先生研机析理的推究,乃是缘于他在礼学领域长年累月的学术积累而阐发的思考。儒家的学问,体现究本溯源功夫的学风有崇尚“义理之学”“考据之学”“会通之学”等,虽各有侧重,但最终都要用“文以载道”精神来实现“以文化人”之目的。
四、致远篇:文献与文物的保护
田率(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先生和刘国忠先生分别于“虎鎣说略”(2019年5月16日)、“汉代第一刀剑”(2019年5月23日)、“清华简”的保护与整理(2019年6月13日)讲座中,向各位师生介绍了在具体的文献与文物保护工作中获得的体会。
在“虎鎣说略”讲座中,田率先生向我校师生介绍了西周晚期的“虎鎣”入藏国家博物馆的缘起,以及“虎鎣”在经历了圆明园于1860年被英国军官哈利·埃文斯劫掠的辗转过程。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派出专家,田率亲历了赴英对虎鎣进行鉴定的全过程。他从“虎鎣的器形、纹饰特征和时代断定”“虎鎣的类型学价值”“虎鎣的铭文释义”“盉(鎣)的功用”“虎鎣的流传及归国经历”等方面,讲解了国家对流失海外文物的重视和保护力度。
在“熠彩生辉的‘汉代第一刀剑’”讲座中,田率从“永寿二年钢刀的历史价值和科技价值”“永寿元年钢剑的历史价值和科技价值”“刀剑比较及铭文所反映的东汉末年政局”三方面,介绍了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入藏的东汉永寿二年错金钢刀。经专家鉴定,此刀是目前所见使用者等级最高,且铭文字数最多的汉代刀剑。此刀剑与另一柄现存的东汉永寿元年错金银钢剑,皆属中国古代灌钢法最早的实物例证,亦是改写中国冶金史的珍贵资料。
刘国忠先生在“‘清华简’的保护与整理”讲座中,从“什么是清华简?”“书于竹帛”“清华简的入藏与保护”“清华简的整理”四个方面,介绍了“清华简”的来龙去脉,在整理“清华简”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在保护“清华简”的工作中,所采取“拼接”与“编联”的具体技术和方法。
田率、刘国忠所亲历的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都与一种载体和符号密切地相关联,即文字。不论是青铜器铭文,还是竹简,都是人类的智慧和创造。“礼乐”,就是依托于文字,跨越时空,传播于今。由是,我们理解了儒家钟情于“说文解字”式的人文叙述方式,乃是以专注的情怀,在儒家经典的字里行间,注疏、正义着“礼乐”思想的变迁。
刘国忠先生在“清华简的专题研究”(2019年6月20日)的讲演中,介绍了“清华简”的整体特点,即“清华简”属于古书,其中,保存了先秦时期的古籍原貌,总数约2500枚,经过序排,总共约有70篇,文献抄写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05年左右,是目前所发现的战国竹简中数量最大的一批,且内容丰富。“清华简”避过了“秦火”而现于今,实属中国文化的一大幸事。
就“清华简”内容而言,大家感兴趣的是与音乐相关的内容。对此,刘国忠先生向在座的师生介绍了在整理“清华简”中所发现的未曾见过的周代诗篇(也可称之为乐诗)。譬如,在“清华简”《耆夜》篇中,记载了周武王八年征伐耆国(即黎国)得胜后举行“饮至”典礼的史事。该篇涉及到了典礼仪式中的饮酒赋诗场面,其《乐乐旨酒》之段的韵律极富音乐性:
乐乐旨酒,宴以二公。
任仁兄弟,庶民和同。
方壮方武,穆穆克邦。
嘉爵速饮,后爵乃从。
从该段乐诗的韵脚来看,属于中东辙。需要说明的是,《耆夜》篇共有十四枚简(有四枚折断),文字残缺。由于参加此次凯旋典礼的不仅有武王,还有毕公、召公、周公等臣僚,《乐乐旨酒》体现的是,周武王在典礼中的饮酒仪式,致毕公而作的乐诗。值得关注的是,《耆夜》中还涉及到了周武王致周公的《輶乘》,以及周公致周武王的《明明上帝》和周公致毕公的《英英》,且《乐乐旨酒》《輶乘》《明明上帝》《英英》四篇,皆属未曾见之文献的乐诗。其后,刘国忠先生还提到了与《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有关的重要学术信息,以及在“清华简”中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十进制数学算具实物—《算表》,这对于今天的音乐学者探索先秦时期的乐律工作者是如何利用《算表》来进行乐律计算的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且难得的文献和实物依据。刘国忠先生指出:“在尚未整理的清华简中,有先秦的礼书和与音乐有关的文献,还有当时众多的诗歌。”
可以说,在未来的“清华简”整理中,依然充满了值得我们期待的学术信息。在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的史学家们看来,“清华简”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过我们过去所能想象的程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清华简”出土于我们以往所认为的蛮夷之地的楚国,由此看来,这种认知已成为学术偏见。“清华简”的发现,恰恰说明楚国文化所具有的学术高度。
结语
中华文明乃是由各民族各地区共同缔造的。史学家们提醒我们,走近夏商周“礼乐”的遗绪中,我们不仅可以对探索依稀其旨的夏代“礼乐”充满神秘遐想,还可以发现殷商时期“礼乐”祀于神鬼之用的特征,同时,我们也可以知晓,是“礼乐”铸就了西周人本主义的灵魂,推动了西周重视“道德”对陶冶和铸范人格作用的建设,也影响和成为了中国历代圣贤君子自我约束和“教化”社会的行为规范。伴以“承国学、扬国韵、育国器、强国音”的办学理念,在“礼乐”体系中寻找和接续圣贤的足迹和思想,对于中国音乐学院的学术建设,以及在“礼乐”的历史回顾与不断求索中的思想者来说,正当其时!21世纪的学问“新发现”,如同20世纪的学问“新发现”一样,必将启蒙、拓展出21世纪“礼乐”学术的新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