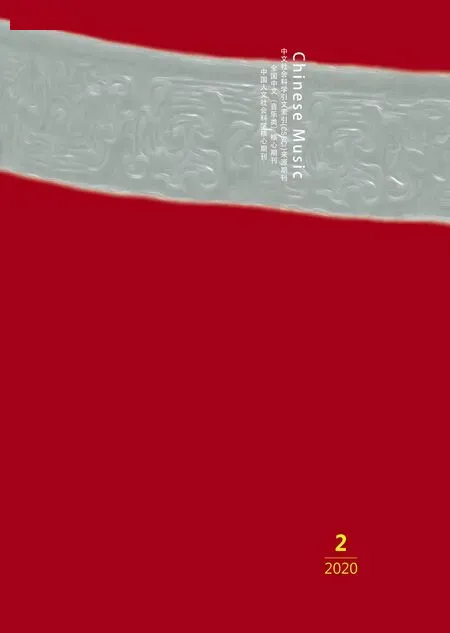“多元文化”与“返本开新”之辨— 管建华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研究
2020-04-18
引言
音乐教育哲学是管建华音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管建华的三大研究领域(即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哲学、音乐教育哲学)之一,而且成为了管建华的学路历程与心路历程的落脚点与归宿。管建华是国内研究音乐教育哲学最早的一批学者之一,他基于中西方乃至东西方音乐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逐步渗透至音乐教育哲学在思想与实践两大层面的思考,既有对音乐教育哲学存在的历时性与共时性问题的反思,又有对音乐教育哲学的方向性及前沿性问题的预见。尽管管建华已经离开我们,但是其音乐教育哲学的价值在音乐教育的实践中开始显现。今天,我们重读管建华音乐教育哲学的论著,并对其音乐教育哲学思想进一步认识,仍具有现实意义。
一、管建华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索源
一位学者能够在一片学术领域有所建树,其学术研究的理路应如南宋著名理学家陆九渊所言的那般—“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种人与学术之间的双向呼应,促使学者对先贤智慧理解的通达,同时,在理解与解释先贤智慧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融会其他领域的知识,破除思想研究与价值研究的层层壁垒,对先贤智慧加以引申与发挥,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学术观点,从而构建新的思想体系。管建华先生的学术思路正是契合了如此的学术规律,其扎实的学术积累,敏锐的问题意识与前沿意识,对古今、中西关系细致入微的洞见,使其在音乐领域的学术理念独树一帜,然而,这一切与管建华的学术理想与学术旨趣是不可分的,甚至,与其个人经历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管建华于1953年9月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医生家庭,出于子承父业的传统观念影响,管建华有过短期的学医经历,然而,正是因为这样一段经历,使其发现了中西医两种知识体系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背后隐藏着两种文化的不同内蕴,它为管建华在中西音乐比较研究上提供了思想层面的借鉴意义。20世纪70年代末期,管建华考入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四年本科阶段学习作曲的经历,使他能够较为系统地掌握西方音乐体系,八年京剧团乐队的小提琴经历以及乐团配器的经历,使他既有中国民族音乐的理论功底,又有西方作曲理论体系的整体认知。然而,管建华在从事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教学时,却出现了阐释的“焦虑”—“似乎没有一个现成的与西方专业音乐创作体系架构相类似的中国民族音乐创作体系的架构。”①管建华:《中西音乐文化比较的心路历程》,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3、224页。显然,管建华发现,中国民族音乐创作体系的建构,实质是中国民族音乐的创作方式对西方音乐创作体系的“复制”,这是中国其自身音乐定位及其音乐创作体系的“硬伤”。20世纪80年代初,以比较音乐学作为开端的民族音乐学学科开始盛行于中国,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的重新兴起,使管建华找到了其学术研究的基点—比较音乐学。由此,管建华意识到,从纵向上,他需要梳理中西音乐比较的历史脉络,把握比较的历史背景,如在他发表的《试评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观点》②管建华:《中西音乐文化比较的心路历程》,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3、224页。一文中,印证了他的想法;从横向上,他认为,“必须把握中西哲学、文学、艺术、美学、宗教、历史及文化的一些研究成果才能进行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③管建华:《中国音乐审美的文化视野》,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1985年,管建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攻读民族音乐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期间,音乐人类学对其学术理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了拓宽其学术视野,他聆听了大量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领域专家与学者的演讲,如杜维明、梁漱溟、汤一介、乐黛云、季羡林、傅伟勋等,这使他清楚地意识到,“中西音乐体系的差异应建立在对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认识和比较之上”。④管建华:《中西音乐文化比较的心路历程》,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3、224页。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开始影响中国的学术及理论研究,同时,后殖民批评理论也悄然地影响中国的各个学术领域,它们既为管建华提供了独辟的思维模式之契机,也为其思考中西音乐关系之文化研究赋予新的理论思考。此外,文化研究一直贯穿于管建华学术思想及理念之中,而研究文化的目的在于传承,管建华曾说,“音乐教育首先应该担负起自身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建构任务”。⑤管建华:《中西音乐文化比较的心路历程》,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3、224页。因此,基于国际视野,他坚称,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是世界音乐教育未来发展的趋势;立足于本土行动,他呼吁,构建中国音乐教育理论话语体系,二者形成管建华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体现在生活世界之实践活动中的意义。
二、从“中心”到“多元”:音乐教育哲学的新视野
1.“审美”的解构与“文化”的兴起
管建华认为,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的认识论哲学基础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有必要对其进行批判。首先,他指明:“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的认识论哲学基础是普遍主义,它将‘审美’作为人类理解音乐的最重要的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凡是人类的音乐都必然是通过‘审美’而感受音乐,或者对于所有文化只有‘审美’才是最有价值的。”⑥管建华:《“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批评与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建构》,《中国音乐》,2005年,第4期,第13页。显然,以“最”“凡是”“必然”“只有”等犀利的字眼辅以绝对的表述口吻,管建华内心对“审美”的音乐教育范式之态度溢于言表,他将“审美”在音乐教育中的价值推向制高点,众目睽睽之下,他又将问题化为一支支利剑,直击“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之要害,即音乐是由“审美”来界定的,然而,普遍的“审美”范式能界定所有音乐吗?所有音乐有共同的“审美”标准吗?其实,管建华指出“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不足之处时,已经给出问题的答案—普遍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普遍真理,其与音乐教育内涵的多种可能性是相悖的,其作为“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的认识论基础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不同的音乐文化由不同的“审美”来界定,所以不存在用一种共同的音乐标准来衡量全部人类音乐经验的“泛人类”标准。其次,管建华认为:“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的认识论哲学基础是反历史主义的,从笛卡尔开始,哲学一直在构建一个认识论框架,或者说寻找一种永恒有效的、可以超越历史的真理知识或认识世界的框架。”⑦同注⑥,第13、14页。“审美”自其概念诞生之时,近代西方的哲学家们均在为是否存在着亘古不变的“审美”定律而“上下求索”,然而,接受当代哲学思想洗礼的管建华,在重新厘定“审美”概念之时,他给予了一种历史性的判断,在他看来,“审美”是历史的产物,它经受着历史的检验,并且历史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历史,是一种不断被解释的历史,而相反的是,反历史主义是在寻求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其赋予“审美”的意义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实为一般理念下的“审美”,因此,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中,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是一种倒退的史观,它沉浸在19世纪西方的客观性与理性所建筑的“乌托邦”中。更进一步说,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是逆向历史而非“效果”历史的。再次,管建华认为:“‘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的认识论哲学基础是反哲学语言学转向的。”⑧同注⑥,第13、14页。近代以来,自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观点提出,对于哲学关系的探讨,由本体论转变为认识论,而后者建固于主客体对立的思维模式之上,同时,语言学的转向也开始初露端倪,即语言学转向现象学与哲学解释学,目的是形成主体间的交流与理解。因此,管建华漫步于西方哲学史的“长廊”,在与西方哲学的先贤们“促膝长谈”中,通过时空转换的对接,心灵之间的“暗物质”感应,形成思想上的“量子纠缠”,其学术思路的“通达感”之创获,使其俯视“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之合法性,揭露了其瑕疵所在:这种音乐教育观与语言学的转向是背道而驰的,它并不是体现主体间交互所生成的意义创生,其哲学的根基依旧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二元论”,它强调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以主体为中心,将音乐作品作为客体的存在,以审美聆听的方式,停留在音乐形式的感受和体验之上,音乐“内心”的文化意蕴无法向主体敞开。
由此可见,语言学的转向推动传统的西方哲学由自然科学领域过渡至人文科学领域,并且思维范式的转型对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这也预示着新的音乐教育哲学理念的“问世”。因此,涌现了一批倡导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学者,如戴维·埃利奥特、韦恩·鲍曼等,并且他们都倡导音乐教育对实践的关注,如埃利奥特认为,“音乐是一个多样化的人类实践活动”。⑨戴维·埃里奥特著:《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齐雪、赖达富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年,第41页。鲍曼认为,“音乐审美只能是音乐和音乐活动中的一种形式,而不能是全部……它把许多不能通过传统学校音乐教育来实现的音乐活动排除在音乐实践之外”。⑩黄琼瑶:《鲍曼及其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中国音乐》,2007年,第3期,第91页。因此,管建华在与他们思想进行碰撞的过程中,清晰地意识到,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提出,实质是解构了“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在音乐教育思想中的绝对话语以及“审美”作为主体音乐观念的绝对地位。与此同时,管建华发现,“实践被纳入文化的考量,任何实践都是文化的实践。”⑪管建华:《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交响》,2012年,第1期,第7页。这是他将“实践哲学”结合了音乐人类学“音乐作为文化”这一命题的思考,并提出了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在与伽达默尔、胡塞尔、罗蒂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进行“非线性”的互动过程中,管建华发觉,语言学的转向所赋予实践的意义已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思考,实践的所指应当是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实践。不难发现,音乐教育的实践哲学与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存在紧密的联系,甚至,实践哲学的兴盛离不开文化哲学的兴起,由此,管建华认为,只有真正“了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才能形成音乐教育文化哲学的转向”。⑫同注⑥,第14页。显然,音乐教育文化哲学的内在理路已“跃然纸上”,文化哲学并非是一种思辨哲学、科学主义,而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彰显,也由此证明,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需要具备人文学科的视野,脱离二元对立的主体性哲学之窠臼,注重主体间性的交流问题与理解问题,并且对于文化的释义应当广采博纳,尝试多元领域的“跨界组合”,同时,秉持开放的态度面对生活世界中的音乐文化。
2.“一元”的消解与“多元”的架构
音乐教育的“一元论”思维模式实质是一种“现代性”表征,它趋同于隐伏在音乐教育体系中的“西方音乐中心论”。触摸历史的脉搏,自近代以来,随着欧洲音乐文化的传入,“西方音乐中心论”在实现“现代化”的大众之心性诉求中应运而生,它的出现所带来的是中西音乐文化之间的“错位”以及在后工业时代所引发的“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性危机”,因此,管建华认为:“建立中国(东方)‘自性’或‘主体性’的跨文化音乐的比较研究,即站在中国(东方)音乐文化的立场与西方音乐对话(比较),在世界音乐文化的发展和对话中从被动的‘他性’‘客体性’转向主动的‘自性’‘主体性’的参与。这是历史赋予中国音乐的使命。”⑬同注①,第210-211页。按照他的看法,之所以必须改变中国音乐发展的路径,重新促使中国音乐在多元文化的场域中找到自身的定位,是因为中国音乐依附于西方音乐体系下发展了近百年,而音乐的直线进化论之进步史观奉西方音乐体系为先进的、科学的典范,“我者”必以其为范式置换自身之话语,从而丢失了中国音乐的“本真”,形成了向西方“乞灵”的文化心理。因此,改变“西式”语境中的中西音乐关系之不平等地位,需要立足于自身的文化背景以及文化价值的认同,使中国音乐在中西关系中,转换主体性的文化身份,在中西双重主体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同时,促使音乐教育由科学语境走向人文语境。故,人文语境中的管建华,在反思音乐文化中的“西方中心”的同时,提出了“消解西方音乐教育的一元论和音乐话语的霸权,批判工业化音乐教育体系中西方工具理性所支配的课程理念和课程体系”⑭管建华:《后现代音乐教育学》,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这一观点。在他看来,中国音乐教育的课程体系是“植入的西方文明”,这种“西式体制”是工业文明的“现代性”产物,它强调“中心”地位与“话语”权威,同时,它象征音乐教育内在音乐文化的“独断论”,排除其他音乐文化共生的可能性,然而,音乐教育是音乐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之基础,音乐文化的多元也重新定义了音乐教育的人文属性,因此,只有消解音乐教育中的“一元论”,才能建构音乐教育的多元文化性质,才能构建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所孕育的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
如何建构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呢?21世纪是一个由工业技术文明走向信息技术文明的时代,亦有学者称其为“太空时代”,信息繁荣与文化交流,促使世界愈来愈趋向一个整体,世界各国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往来越来越密切,从而形成了频繁的跨文化交流,然而,在跨文化的语境中,任何自身以外的音乐文化都极有可能被视为“异文化音乐”或者“陌生音乐”,然而,“对‘陌生音乐’的跨文化理解往往是用自身文化价值标准对‘陌生’文化进行评价,并得出与‘陌生’文化价值标准相反的结论”。⑮管建华:《音乐的跨文化交流与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国音乐》,2003年,第1期,第23、24页。因此,管建华认为:“理解不同音乐,必须通过文化界定或文化认知体系的交流来沟通,缺少对音乐在文化意义层面理解的沟通,各持各自文化视界的‘音乐’便无法交流。”⑯管建华:《音乐的跨文化交流与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国音乐》,2003年,第1期,第23、24页。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是管建华为“5G时代”的“地球村”所编织的音乐教育“太空梦”。信息频繁交织,文化语境多元,音乐的多元之魅力在于其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与文化评判标准的非同一性,因此,文化是不同的音乐进行交流以及理解音乐的多样性之基础,理解不同文化语境的音乐为跨文化的共融提供可能性,更进一步说,跨文化交流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平等的对话,才能对音乐的文化性质有更深厚的理解与认识,从而促使不同音乐文化之间的“视域融合”,同时,这也成为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思想形成的前提。那么何为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学科的基础呢?管建华认为:“音乐人类学是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学科基础,所以,它不但重要,而且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与教学直接有赖于对音乐人类学的理解,因为,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学不是世界音乐知识的堆砌,更重要的是学会用音乐人类学的理念及多元文化的世界观看待世界各种文化的音乐。”⑰管建华:《21世纪初: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与音乐人类学在中国》,《音乐艺术》,2009年,第1期,第132页。音乐人类学是由早期的比较音乐学演化而来,其研究视野由初期非西方音乐文化领域拓宽至世界音乐文化范畴,并且音乐作为文化来界定是音乐人类学的立论依据,而文化价值相对论是音乐人类学的理念,因此,音乐人类学作为管建华“开宗派”“立门户”之学术,其更像是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参考书”,只有认真地“参悟”,才能为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实施提供有效“指南”,并且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传承世界音乐文化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承音乐文化本身,而是通过传承方式形成多元的文化观与相对的文化价值观。面向未来,管建华认为,“音乐教育学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其未来的学科理论和学术研究也必将是建立在全新的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基础上”,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音乐教育学才能形成该学科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新的转向”。⑱管建华:《德国音乐教育学的后现代转向》,《音乐探索》,2005年,第4期,第96页。未来的音乐教育学科的丰富性并非是基于西方传统音乐知识的活生生在场的多样性,而是内在跨文化的差异性以及外在跨学科的综合性,即人文科学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这是管建华为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提供的人文性展望。
由此可见,管建华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是基于音乐人类学所提供的理论支持,以及后现代主义对于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通过消解“审美”作为音乐教育的中心地位,解构音乐教育中“西方音乐中心论”的话语霸权,立足于跨文化与跨学科之基础,构建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以及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
三、回归与重塑:中国音乐教育理论话语体系的构想
1.“母语”的重拾
在“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组委会的倡议下,于1995年10月8日举办了“中华文化作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研讨会,各路专家、学者以及记者围绕“中华文化作为母语音乐教育的意义与界定”与“母语音乐教育的困境及建构、规划、实施等问题”,各抒己见,为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之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首先,管建华将“母语”定义为:“一个民族将自己的文化、历史以及对环境做出的反应的各种体验都凝聚在自己的语言里,也包含在音乐语言里,并经有代代相传,维系着整个民族群体生命的延续。”⑲管建华:《中华文化作为母语音乐教育的性质和意义》,《人民音乐》,1996年,第1期,第31页。“母语”实质是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甚至,它是一个民族文化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彰显,在管建华看来,“母语”是比语言更大的概念,前者是流淌在民族“血液”里的“DNA”,并且“母语”在音乐中的体现,包含了历史积淀、人文环境等元素,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血脉”传承。其次,从中华文化作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课程设置角度,管建华认为:“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课程设置,它需要有明确自身母语音乐体系结构的概念表达系统。这种概念表达系统需要不断与其他音乐文化系统相比较加以明确,使这种音乐概念表达系统与其他音乐文化系统获得一种共时性与现代性,即获取平等的价值地位。”⑳管建华:《21世纪中国音乐教育面临的挑战:课程改革与文化》,《天津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第12页。中华文化作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独特性之基础在于其自身文化的哲学观,即有机宇宙观,而西方的哲学观是机械宇宙观,由此决定了西方音乐的本体形式是“乐音运动形式”,中国音乐的本体形式是整体形式,它包含了说唱、戏曲、民歌、器乐、方言、音色、音感等元素,然而,中国的高等音乐教育以西方音乐语汇去规约“母语”音乐,甚至其课程设置仍是以西方音乐体系为主线,因此,管建华毫不避讳地揭示了这种教育的弊端—“阿炳考不上民乐系,刘天华考不上作曲系,梅兰芳考不上歌剧系,王光祈考不上音乐学系”㉑管建华:《21世纪的抉择—从中国高校音乐教育的三个“缺失”问题谈起》,《人民音乐》,2015年,第1期,第74页。,故,从他的话语中隐约地能察觉到,母语音乐体系是中华文化作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课程设置之根基,前者的价值体现在母语音乐文化与其他音乐文化之间的非同一性之中,并且通过“母语”与“他者”的不断比较,避免中华母语音乐文化受到其他音乐文化同化的趋势,而丧失“自性”的特征,形成“我者”与“他者”平等对话的关系。最后,如何以“母语”彰显中国音乐教育的理论话语呢?“母语”是彰显民族文化“自性”或“主体性”的符号“烙印”,也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标识,因此,管建华认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是关系到国家民族音乐文化的传递及文化内聚力的问题。”㉒同注⑲,第32页。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母语”是民族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当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彰显“我者”文化身份的话语。基于此,管建华意识到,以中华文化为母语所构成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与世界多元音乐文化是互动同构的关系,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离不开中国元素,中国音乐教育体系需要在世界范围内体现自身的文化价值。因此,“母语”音乐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中国音乐教育需要构建自身的话语,只有这样,中华文化作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才能“丰富世界文化的音教体系”,“使我们主体的音乐教育体系成为世界中的一元”。㉓同注⑲,第32页。
2.“返本开新”的重绘
“当一个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前夜,它必须回顾自己的历史文化,从中汲取力量,‘返本开新’。”国学大师汤一介如是说。中国正处于民族文化复兴的“前夜”,民族的复兴必须依靠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予以支撑,才能在“新的轴心文明时代”,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实现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为此,中国音乐教育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其理论话语体系也应当重塑。首先,管建华认为:“礼乐文明是一种伦理精神和信仰体系,它是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灵魂所在。失去她,就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中国社会当今出现的信仰危机正是与中国音乐教育所失去自己的‘灵魂’相关。”㉔管建华:《生态社会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文明归复—礼乐文明实践哲学与希腊文明实践哲学的返本开新》,《中国音乐学》,2015年,第1期,第41页。如若一个民族舍弃其自身的历史文化而去论复兴,那么其文明的缔造将是无本之木、无根之水,因此,在管建华看来,礼乐文明就是铸就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根”与“魂”,它代表了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化精髓以及先辈们智慧的结晶,故,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内在寻“根”必须努力实现礼乐文明的归复,只有接受和推动文明的归复,才能凸显中国音乐教育体系中独有的理论话语。其次,管建华认为:“作为实践的范式,中西伦理学的差异也影响到音乐行为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国及东方演创合一的实践行为其本身更多是体现集体精神的行为……但是,工业化社会的音乐教育体系以及重视理论智慧的西方音乐学和音乐审美哲学研究也覆盖到中国的音乐教育实践。”㉕同注㉔,第32、38页。显而易见,中西方音乐文化的实践差异是由中西哲学观的互异性所造成的,中国的实践注重“精神行为”,西方的实践注重“理论智慧”,但在管建华看来,在不同的中西实践范式中能够透视出中西文化比较的文明抉择,这种文明抉择所造成的正是中国音乐教育实践的“错位”。因此,中国音乐教育体系亟待重新“正骨”,从文明抉择转向文明自觉,通过文化心态的转变,重构中国音乐教育的理论话语体系。最后,管建华认为:“在新的轴心文明时代,我们并非要排斥西方,但要回归自己立于文明音乐教育主题的实践,转向中西差异并存形成差异性的张力,进行对话。”㉖同注㉔,第32、38页。从他思想的理路中,能体会到的是,在“新的轴心文明时代”,构建中国音乐教育的理论话语体系,并非走向一种“单极主义”,既非固守本土文化,对西方文化推行“排他主义”,也非全盘西化,视本土文化的回归为“守旧主义”,而是建立一种“多边主义”的机制,即“本土行动,国际视野”,因此,中国音乐教育理论话语体系的“返本开新”,不再是音乐文化的“权力”与“话语”之间的规训,它是一条深深地根植于中华礼乐文明与多元音乐文化平等对话的新路径,这亦是管建华未尽的毕生之志。
可以看到,管建华基于中华文化作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来传承的角度,以世界多元音乐文化为参照,从思想与实践两大层面建构中华文化作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理论话语,并指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建构应当扎根于中华礼乐文明,在新的轴心文明中建立自身的立足点,以中华礼乐文明的归复以及文化身份的构建,实现“返本开新”。
结语
总之,音乐人类学提倡的文化价值相对论与后现代主义倡导的文化多元“无缝衔接”,二者为管建华倡导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之发展提供理论性支撑。与此同时,以“母语”作为中国音乐教育话语之基础,促进中国音乐教育在实践层面实现文化身份之认同。通过礼乐文明归复的“返本开新”,构建中国音乐教育理论话语体系,是其一生所愿。不得不承认,管建华是音乐教育学界的一盏“明灯”,其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照亮了音乐教育由现代性转向后现代性的方向,为音乐教育在理论及实践层面注入了一股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