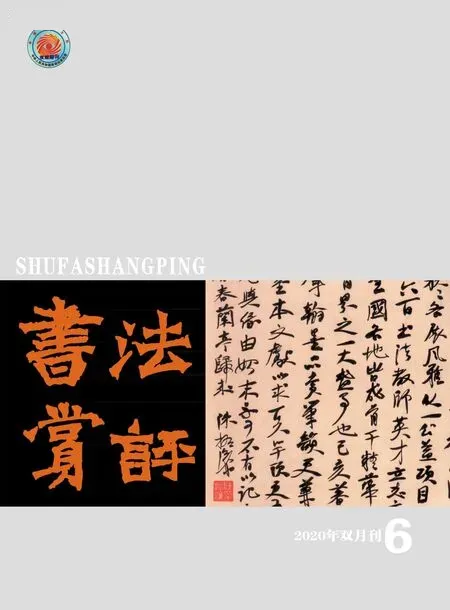北朝造像碑中“书工”与“匠刻”关系以及字体杂糅现象
2020-04-17曾勇
曾 勇
一、造像碑中的书工、匠刻关系
陈振濂在洛阳进行龙门书风的美学嬗变讲座中提到:“龙门造像题记有三大特点,第一是以佛教造像(雕塑)为主体的书法配属形式,第二是以雕塑意识、刻凿意立场的文字观和书法观,第三是作为雕塑衬托之配角式的文字记录以及随机成形的书法格式与外形能力。”[1]所言之意为造像题记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文字表现,其功能是为了记录。且多位于洞窟之内,别说书丹难以进行,就连刊刻也未必能达到尽善尽美,观之龙门造像题记,多为粗糙露弊之作,就连造像二十品也存在诸多败笔,且多有布局不均和错字漏字现象。因此在造像题记的刊刻上多半是工匠在造像刊刻之后随手进行文字刊就,也没有进行字数考究和书丹,这一观点也是能站得住脚的。
而造像碑是一种宗教性质的石刻艺术,和其他刻石不同之处在于造像碑艺术必须满足宗教信仰的表现、传统石刻制度和中原文化体制等内在需要。造像碑的形成不仅是对佛教美术、雕塑的形象刻画,还对中国石碑文化的延续和中国书法艺术的再现有着重要参考价值,故而造像碑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多重意义的艺术表现。造像碑上的文字是在平面石板上刊刻,对于排版布局上更为讲究和细致(如图1 所示)。从河南地区分布的造像碑来看,尽管风格各异,不过它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就是造像碑上的文字布局是以一个整体形式存在的,或刻在侧旁,或在佛龛下方,也或在石碑之阴面刊刻。对布局上更为讲究且刻工精细,诸多碑石还绘格规制,看来造像碑书法在刊刻之前是有着系列整体排版规划和书丹的,以至于造像碑书法在风格上来说更为清晰和多样化。

图1 河南地区《刘根造像碑》原石,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院,系笔者拍摄
对于宗教类书法的刊刻,如造像就有专门从事造像工作的“造像家”,且在北朝十分兴盛。因此民间造像碑书法的刊刻,也存在选用特供的“造像家”参与在其中的可能。中国历来十分重视石刻艺术,因此古代石匠也是比较多的。随着佛教的不断兴盛,具有宗教符号的石刻艺术门类兴盛起来,原来的石匠转换为造像家也不是没有可能,且他们这一类人是具备最高技艺的专业写手和刻手。当外来佛教造像新题逐渐上升为社会大量需求的石刻题材时,他们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的需要,不自觉地会被并入到造像家以及从事造像刊刻的行业之内,故而在造像方面拥有专业的造像刻手也成为了普遍接受的一个结论。
北朝佛教盛行,故而从业造像的匠人更是数不胜数,也不乏技艺非常高超且名气大的造像名家。不过就当时造像家而言,大体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的石刻工匠,这一类多者出现在民间,可以雕造陵园、修缮建筑、以及一些普通工艺摆件的雕刻,还可以兼顾刊造一些大型的宗教题材的石刻雕像,这一类人显然不是虔诚的教徒,更偏向于是一种社会地位的需要以及靠手艺换取钱财以维持生活的方式。还有一类造像家是外来入境的寺庙僧人,因此叫做“僧匠”,他们有许多身怀雕塑技艺,推动了佛教造像的普及和艺术的发展,这一类人在当时社会中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是属于专供的造像家。
造像碑多出自民间,不少普通发愿俗家也会参与造像发愿文的刊刻,结合造像碑上发愿文对造像碑书者身份的认定,也有一部分学者提出是“工匠和民间书手”这一说法。[2]古代是社会等级森严的社会,能接触到文化的学习的必定是家族地位比较高的。社会工样百种,大部分民间石刻匠人等一类人是没有机会接受正统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更别说是对古代文化、文字的辨识和风格展现。因此在民间流行的造像碑书法是否均出自所谓的工匠和民间书家之手呢?民间在挑选造像碑的工匠的同时是否有一定的选择标准呢?可以说,在偏僻的乡村山野之地,可能存在民间刻工直接参与在造像碑的刊刻中,而在都城附近,对于造像碑的刻工和书艺终归是有考究的,对于造像碑风格水平的呈现也是一种严谨和体系化的结果。逢成华认为:
造像碑记等同于普通的碑刻,施作者既可以将其放倒书刻,同时又有足够的空间进行章法布局。另外,造像碑刊刻完毕,一般置于佛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施作者的书刻水平也受到重视。[3]
这一观点和笔者的立意是一样的,北朝佛教的盛行让很多人都具备造像刻书的能力,甚至出现了专门刊佛造像的买卖经营活动。另一方面恰恰说明,有利可图的买卖行为,让民间的石碑刊刻技艺变得更为讲究,而对于造像碑发愿人来说,筹资造碑自然会选择技艺良好的刻工进行刊刻。造像碑多为私人发愿修造碑石,尽管是私人发愿,不过由于要立于广宇之中,对于写手和刻手等工匠的水平和层次也是甄别和筛选的。前面提到,造像碑大部分出自民间“石匠”“石工”和刻手所为,这些石匠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文化水平低下。[4]不过因为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在当时一些造像家以及工匠是可以自身手艺来体现他社会地位的高低,尤其在民间,这一类人往往也是通过刊刻的造像作品来展现他们各自的水准。作为工匠,不仅会雕像,对于造像碑上文字的刊刻也需具备很强的把控能力,由于民间团体的广泛和区域性,造像工匠尽管在艺术水平有高有低,不过他们都是根据客人等大众审美来进行造像碑的样式打造。王朝闻等人认为他们:
通过长期训练出来的理解力和艺术眼界,使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浓厚的民族气息。即使是皇家微调的工匠也不例外,其作品除了财势的原因而雕造得壮伟高大、更有贵族气外,与民间所作一样与大众审美息息相关。[5]
造像碑是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石刻造型形式,是在刻有供养发愿内容文字的基础上雕刻佛像的碑。关于造像碑刊刻的样式和布局也比较多样,综合河南地区集中的造像碑来看,有的雕像占一龛,采用佛传故事、供养人系列等内容而布满正、背面和侧面,例如《四面造像碑》,全碑以佛像雕塑形象来展示,无文字刊刻。有的雕像在碑石的上方或者下方,在下方或者一侧进行文字布局刊刻,如《平等寺之韩永义等人造像碑》。还有一类是图像刻于一面,其他一面为文字刊刻,如《姜篡造像碑》的样式等(如图2 所示)。虽然总体所刊刻的题材和方向是一致的,不过也存在这样大的风格差异,不得不提及到的很大原因,是由于当时工匠的刊刻风格和所处区域的不同所造成的。首先,不同区域和不同师承的造像工匠,他们所惯用的手法不同以及工具有差异,其次就是他们民间生成的刻工和造像工匠,没有经过统一的刊刻技术和理念培养,他们各自的处理方式就造成了样式的不同,也存在着他们自我发挥的成分。他们刊刻时,不论佛教人物雕刻还是文字特征把握上,都是工匠技术层次水平的体现。


图2 《姜纂造像碑》拓片,现藏于偃师商城博物馆,系笔者拍摄
二、字体杂糅、及别字情况
黄惇提及造像的书丹和刊刻,认为北魏洛阳地区的铭石工匠用刀的方式是延续师门或者家传的定式方法。有一句话记载道:
从造像中可以看到,最重要的下刀方法,都是从右至左的。这种顺手的用刀动作,恰恰与书写者从左至右用笔顺序相反……至于被后人看作稚拙之美的缺笔少画、移动部位、部首支离,显然许多成分也来自刻工。[6]
可以看出,受到造像碑商品化的影响,产业化的石刻公工序是将书丹和造像碑文字刊刻区分开的,完成这两个过程也并非是同一个人,而不同的人处理方式不同,理解不同,自然就和原始的书迹存在差别,也是造成了缺笔少画、移动部位、部首支离等情况原因之一(如图3)。不过对于造像碑书法中存在的别字,以及字体杂糅的情况还得归之于整体书风的把握,更多地从时代书风上去理解会清晰得多。北朝政局长期动荡,已经失去了用字的规范和标准,对于汉字书写上也会加剧字体杂乱和出现别字、错字。
其实这一类问题应该统一归置于大的时代环境下去讨论,有一种有可能性是在北朝当时的文化体制和现在我们的文化体制不同造成的,因此,出现着一些问题,从根源上说不只是文字学上的问题,也是复杂的社会文化意识问题。
有两种情况,第一是别字和错字现象,在笔者看来只是今天行内的专家、学者把诸多不能辨识的字范作为别字和错字去对待,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别字和错字。张羽翔就“碑别字”也曾提到:“今人断定的别字、误字在北魏可能不是错字、误字,还有可能是当时的正字,即北魏碑别字中存在着较多的古正今别的字以及现在极少使用或被他字取代了的生僻字。”[7]只是由于北朝那个时代离我们当下过于久远,文化的差异性过于悬殊,以及较少的存世文献资料去记录这类史实,这些字已经变得模糊和陌生起来。

图3 《高显达造像碑》原石,现存河南省博物院,系笔者拍摄
由此,我们在区分和对待这些现象时,还是得从多方面去全面把握,如果根据我们的主观笼统判断未免过于局限性和武断了。另外,造像刻石时主要突出对造像的宗教人物的敬仰和表达,而对于文字,往往作为一种辅助题材去体现,因此也不排除由于工匠们的疏忽的原因,从而造成刊错或者多缺笔画的情况存在。
第二是在造像碑中还存在字体杂糅的情况,这和第一种情况存在明显区别,首先这是字体的问题,不是字形错误与否以及用字的规范性问题。虽然也有刻工的形成因素,不过在字体的选择上,多半是书丹者的行为。前面论述到,造像碑书法和普通的石碑刊刻原理是一样的,先是书工字经过眼睛的布局安排之后,把文字书丹在碑身上,继而进行刊刻,这两个过程是独立存在的。而刊刻工序只能影响到文字刊刻的精细和表达程度,不会改变原始字体。魏晋南北朝是隶书向楷书交替变换的时期,隶、行、楷、草各种书体相互交融和错落发展。所以在北朝各个区域和具体时间上的造像碑形式和书法风格都存在差异,当然就涵盖了这里提到的字体杂糅的问题,从大的角度来看,这也是这个时期刻石书法的生态表现。
有一段话记载:“皇魏承百代之季,绍五运之绪,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巧。”[8]可以说明这个时代的文字的使用没有完全定型,因而会出现在北朝碑石书法中有一些字形运用篆书的字形,又存在隶书的笔法,还参杂着不成形楷书元素和定式的书法意态。例如河南地区《平等寺之韩永义造像碑》《北齐造像碑》可以看出,造像碑不同于造像题记书法的刊刻,从布局到内容发的书丹,以及造像碑的刊刻终成于考究,也多会受于时代书写特征的影响,故而造像碑书法体现的是一种刻石艺术的时代性书写符号。
王朝闻提到造像碑是在结合了宗教题材后,又进一步吸收了汉代石刻画和浮雕的美感,然而未放弃书法美的一面。认为“它又是一种综合性审美表现形式。庄正的碑形、厚重的体态、精美的造像、灵动的书法构成了造像碑的综合审美品格”。[9]因此就造像碑中存在的相关问题除了其本身的宗教意愿之外,其书法刊刻以及书风方面和北朝盛行的书法风格更是息息相关。
总之,自宗教传入中国,最开始为了扩大宗教的影响力,采用和结合了立碑的形式。北朝时期造像盛行,在制碑和造像心理上来看,一是追求旌表供养者心愿与虔诚,二是寻求造佛像立功德的供养报应。而汉代以降,石碑作为审美对象十分强调其表现书法美的功能,书法的艺术和形式美感甚至超过碑的造型,也自然就超过文字文本的涵义本身而被普遍瞩目,北朝时期造像碑自当如此。这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方面之一,也是本文去深入探讨造像碑中存在的相关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