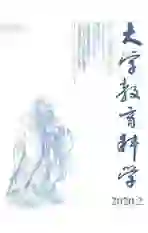大学之道的比较与发展
2020-04-06王义遒
摘要: 大学的宗旨和目标代表着大学的内涵。对比中西方大学的宗旨与目标可以发现,其共同点是通过教育使自然人成为能与他人和睦共处、服务于社会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无论《大学》中所言“新民”,还是《学记》中的“化民易俗”,都强调“爱国”“为国”的观念,作为维持宗法亲情社会秩序的“礼”也就成为了大学的核心理念。中国近代大学虽然是“舶来品”,但坚持了中国的人文传统,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而西方大学更看重知识与科学,强调纯粹理性的观念,尤其是大学被移植到美国后,又发展出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三项职能,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学之道”在“中西合璧”的基础上有了两点新的重大发展: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强调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此两点与传统大学之道之间具有包容性与逻辑合理性,也是当下我国必须坚持的“大学之道”的新常态。
关键词:大学之道;大学宗旨;大学目标;大学文化;中西方差异;发展与前瞻
中图分类号:G40;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0)02-0046-07
一、大学之道的内涵
什么是大学之道?也许有人会说,两千多年前的我国典籍《大学》里已经说清楚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确,这个“大学之道”经过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的阐释与弘扬,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几乎是尽人皆知了。它指明了大学的宗旨与目标,即所谓“三纲领”:明德、新民和止于至善。同时,《大学》也规定了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及其基本内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共八个环节,常称之为“八条目”。它特别强调“治国”的义利关系,“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也就是要求通过个人接受教育、修养成为服务于社会、国家和人类的人。
上述诸点只是道出了中国古典“大学之道”的要旨或核心,还不能概括它的全部内涵。《大学》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其实,《礼记》中还有一篇《学记》,它不但将《大学》里的“三纲领”具体化为“化民易俗”“近悦远怀”的作用,宣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而且对教育体系做了明确的阐述,提出“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等不同层次教育机构的概念。它还规定了“入学”后要隔年考核,使教学内容循序渐进。如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实际上将“小学”与“大学”区分开来,甚至大致规定了学习的年限。入“大学”大体上与孔子所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相当,就是说小孩子大概十五岁开始可以上“大学”了。它还制订了施教的七条规矩,对礼仪、学习态度、时序甚至惩戒工具都做出了规定。
《学记》还明确了教学中教与学的关系,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思想,并对教学原则和方法、教学活动的安排以及教师的作用做了比较细致的论述。譬如,教学活动有“藏脩息游”四种方式,即:课内要努力吸取知识;课外要做作业进修所学的;休息时要学习各种技艺;还要广交学友、互相砥砺。在教学方法上提出了“豫时孙摩”四条原则,这就是说:要防患于未然;要及时地进行施教;要根据学生的年龄、个性、天赋实施教育,就是“因材施教”;还要互相研讨观摩实习。同时,它又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当时存在的“教”的六种弊端和“学”的四种失误,强调“教”要启发诱导,促进学生主动学,切忌强制包办;“学”要掌握分寸,不能贪多偏狭、浅尝辄止。它还进而描述了对教师的要求与作用、为师要严,要有渊博的知识,要以身作则,要让学生能主动跟着自己学。这样,它也就指明了理想的师生关系。这可能就是梅贻琦“从游论”的雏形[1]。由此,它说明了尊师重道的道理,而“择师”应当是非常慎重的。对教学手段,《学记》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在“结论”中,它还着重论述了做人做事的一些基本原则,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学记》所讲的是要培养“治国平天下”“化民易俗”的“君子”和官吏,他们是管理国家的人。这与《大学》的观点一致。
《学记》可说是世界上第一篇完整的“教育学”古论文。它阐释“大学之道”不仅包括大学的宗旨与目标,而且给出了办学的整体理念,包括:对“大学”的界定,大学体系、制度,大学教学的原则、具体内容、方法和手段,还有大学师生关系和对教师的要求,等等。总之,《学记》道出了大学之道的文化内涵。
然而,《学记》毕竟是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先贤(尤其是儒家)对教育(特别是对大学教育)的一些看法的结晶。而近代中国大学却是“舶来品”,深受西方大学理念和工业化的影响。这给“大学之道”带来了不少变化,并增加了更为丰富的内容。比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教育使人成为人”(两个“人”分别表示作为动物的自然人和社会人)鲜明地拓展了《大学》的纲领。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举办大学的宗旨定位,其内部治理与管理规章,处理各种内外关系的原则等,也应该是大学之道或大学理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职业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国际化,大学的职能不断扩充,其结构已经非常复杂化了,举办大学的动机与大学的运行机制也更为多样化,大学里教和学的方式、学科与学习内容的编设又发生了新的变更,因而“大学之道”的内涵也会随之更新或扩充。因此,探索“大学之道”的命题应该是十分宽泛、细致切实,又是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充满前瞻的。本文主要围绕大学的宗旨与目标,即其要旨或核心来展开较为详细的讨论。
二、东西方大学宗旨的同异及其影响
用上面康德的话来说明西方对教育(包括大学教育)的目标与作用,总体上似乎与我国传统的观念大致相同,都是通过教育使自然人成为能与他人和睦共处、服务于社会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社会人。然而,细想起来,它们还是有所区别的。
在我国,由于两千年前已经形成了民族国家,知识分子通过个人的修身养性要成为具有治理国家、乃至“平天下”的知识和能力的“君子”,塑造了中國知识分子强烈的人文传统、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从春秋战国开始,特别是汉以后“独尊儒术”,这种精神持续发扬,到宋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家国情怀的至理名言。这里所谓的“心”只是指日月运行、宇宙万物存在的“规则”,而并非是它们运行的内在规律与本源动力;而“命”则是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即所谓“安身立命”。这当然是崇高的人文关怀与担当精神,体现经国济世的崇高气节。
华夏民族自从管仲以来的历朝历代虽也产生过不少经济管理人才,为国家治理与天下太平推出过许多改革举措,然而,他们所重视的主要在于调和生产关系,使百姓和睦相处,“和为贵”,天下太平,而真正关注从根本上提高生产力,特别是改进生产工具的不多。“不患寡而患不均”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所以,中国大学的传统教育目标,说“新民”也好,“化民易俗”也好,都是基于社会与国家治理的,强调的是“仁”。在华夏农耕亲情社会里,“国”只是“家”的放大,“天子”“国君”是大“家长”。大学培养“君子”,协助国君来推行这一套宗法伦理,以治理社会与国家。这反映宗法皇权社会对大学教育目标的尊重。所以“天地君亲师”,师长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作为教育者,就是这套宗法伦理关系的推行者与传承者。后来王朝渐衰乃至覆灭,“君”为“国”所取代。而将这套教育目标体现在对学生的要求上,则是京师大学堂成为单纯教育机构之后首任总监督(相当于校长)张亨嘉于1904年上任时对学生的训词“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八个字[2]。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强调的是“规则”或“秩序”,且认为它是客观实在的事物存在与变化之“道”。在人际交往中,它体现社会等级划分的伦理关系,即“礼”。中国的大学之道脱离不了这个“礼”。这种文化传统偏重于保守和包容。但是,这套观念很少想到,天下太平了,人口就会不断增长。如果生产力维持在原有水平不变,受自然资源的限制,一定时段之后,社会就会出现物资供给不敷人口繁殖的现象;而阶级的存在,“不均”是必然的,于是就会有造反,致使天下大乱。所以,在华夏社会,虽然先贤创造了理想的教育目标,却从未真正持续实现过。社会总是先治而后乱,乱而后治,如此往复,循环不已。
以古希腊和希伯来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则不同。根据科学史家吴国盛的观点,由于他们以航海和游牧为生,接触的以陌生人为多,形成了以独立自主的个人为主体的契约文化[3]。这种文化强调个体自由,拷问对“自己”的认识。这种拷问就在于追求事物“存在”(“自己”是其一)的永恒本质与规律的知识,养成了万事问个“为什么”的理性。这是西方文化追求科学推理与探索真理的源头。起源于中世纪的西方近代大学,无论是博洛尼亚大学(学生管理为主),还是巴黎大学(教师为主)模式,都继承了这个传统;其基本价值观念就是:大学是教学与研究科学真理的学者共同体,大学虽然并不完全排斥功利目标,但却是很次要的[4]。欧洲的民族国家形成较晚,像上述两所大学的师生都来自许多城邦国家,因此大学根本就没有什么“爱国”“为国”的观念。这种大学之道的核心理念持续到19世纪工业化时代。这时,英国教育家纽曼(1801-1890)提倡“自由教育”,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知识本身”[5]。他所指的“知识”包含了人类所拥有的全部知识体系,但却不包括为谋职所需要的专门技艺。他排斥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任务,说“探索与教学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功能”;他要培养的是具有智慧理性的“绅士(君子)”。与此同时,德国教育家洪堡(1767-1836)则提出了与其不同的一系列大学理念,其中主要的有:大学具有探求科学和修养个性与道德的双重任务。这里的“科学”也不包括实用技艺,是“纯科学”。他认为唯有通过科学探求才能达到“修养”的目的,主张在探求和创造中完善人格。所以,大学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创造知识。为了能够创造,“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于是,修身、科学、自由、寂寞成为德国古典大学的四个核心观念[6]。
然而,中国文化典籍中除了屈原因受极大冤屈而发出过悲天悯人的《天问》之外,少有拷问事物本质和原由的探索,而多是作“应什么”或“要怎样”的论述的。因此,中国古代文化缺乏近代理性科学的基因。这正如陈省身先生所说,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知道了“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却无法找到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的平面几何的推论[7]。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难以用来进行数学演算这个偶然因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正是由于缺乏近代理性科学,依赖于经验规则的创造发明而提高了生产力、并通过人多势众而积累了巨大财富的中国,被在近代工业化机器生产中制造出大量先进商品器物和坚船利炮的西方国家打败了,失地赔款,丧权辱国。到这时,中国人才猛然醒悟:自己受侵略、挨宰割,是因为缺少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工艺技术,生产力薄弱,武器不精良,从而出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科技的“洋务派”,开启了“变法维新”的举措。于是,“西学东渐”,原有的国子监(太学)和民间书院被废弃、改造,模仿欧洲(或通过学习日本)的新式学校兴起了。
中国文化是包容的,这种来自异族的“舶来品”迅速在中国安身。然而华夏文化又是保守的,它坚信自己的“正统”。这样就出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外来的科学技术只能作为发展经济与军事的工具而加以利用。1902年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了办学纲领是“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还要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这里的“开通智慧”,就包容了纽曼与洪堡的基本理念——追求知识和科学,但“忠爱”与“实业”,“趋向”与“通才”,却完全反映了要服务于满清王朝和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宗旨。所以,中国现代大学从开办以来,就充满了西方大学所没有的家国情怀,它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斗转星移,西方出了个美国。它将欧洲的“大学之道”移植了过去,却并未照单办理。他们吸取了纽曼和洪堡的大学理念,根据美国发展各州经济与社会的需要,开办了不少更适应自己需要的大学,有重要创新。他们不但继承了“自由教育”理念,还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强调大学创造与扩增知识的功能,并且还要直接进行社会服务,以促進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过,这时大学的社会关系也比此前复杂得多,不仅学科众多,附设的专业研究机构不少,而且各类研究生人数也大大扩展,出现了“多元化巨型大学”[8]。这样,大学行政管理也变得非常繁杂,在管理机制上产生了“学院型”与“经营型”之争[9]。这种“大学之道”的新元素带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却是符合美国实际的,对美国后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
可是,满清时期创办的几所大学并没有改变中国贫困落后挨打的局面。美国的进步使中国人觉醒,没有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让昏庸无度的专制王朝继续当政,中国没有出路。于是发生革命,成立民国。不久,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又发现,没有思想文化上的大转变,即使政体变了,社会依然照旧,民族不得复兴。这样,新文化运动乘势而起,竖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汹涌澎湃。“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也获得一时风光,“中体西用”成为落水狗。此时“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访华两年,到处宣扬“民主主义教育”;原来靠美国返还的部分庚子赔款支持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升格为大学,并获得迅速发展。这些影响使中国高等教育界以学习美国的“大学之道”为主流,大学以知识为中心,形成了传播、扩增(创造)和应用知识的三大功能,或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三大职能。独立、自由的学术风气和评议会等大学民主管理制度也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各类大学兴建起来。这使中国现代大学体制逐渐完备,走上正轨。
即使如此,我们也可看到中国大学体制中固有文化的“大学之道”的影子。这就是大学教育归根结底是作为“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工具,它始终缺乏西方大学那种“知识就是目的”的“自由教育”(“为知识而知识”“为科学而科学”)的独立性。这种功利主义倾向成为中国大学发展的一块短板,阻碍有才能的学者取得长期稳定的支持以收获重大基础研究成果。它一直依附于某种权力,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这样,在新的共和国中也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科学”这两面大旗也不过是作为国家救亡和民族复兴的工具而已。因此可以说,中国大学一直是在“中体西用”的体制内建设与运行的,这体现了华夏文化的保守性。然而,恰好就是这种保守性成为了我们今日得以“文化自信”的根基。
三、大学之道在中国的发展与前瞻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高等教育发展巨大。1949年全国仅有高校221所,学生约12万人。到2018年,全国有普通高校2 663所(其中高职院校1 418所),在校学生总规模达3 833万人,毛入学率为48.1%。在学研究生则有273.13万人,其中博士生38.95万。近年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年增长数在2%以上,估计目前它已接近或超过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标准。无疑,中国已是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那么,从“大学之道”角度,中国大学有哪些发展变化呢?从根本上来说,大学服务于国家发展这一基本原则没有变。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学发生了两点重大变化: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尊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二是大大提高了高等教育入学率,促进了高等教育普及化。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这两点中前者体现了“中国特色”;后者反映了时代特征(所有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都已普及高等教育了)。
那么,为什么将这两点作为“大学之道”的发展呢?这两点是否与之前的大学之道有矛盾呢?下面作简要分析。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大学之道”的根本宗旨
1.教育必须坚持科学与人文相结合,并将人文置于科学之上,这是“大学之道”的基本逻辑遵循
从欧洲发祥的现代大学,其首要精神是科学。科学的追求是无边际的,什么事情,什么问题,都可以进行拷问:有什么?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首要的前提是自由和独立,它不能依附于任何利益和权力,否则就会受到限制,设置了邊界与禁区,从而就会妨碍对客观真理的探寻。因此,1988年在意大利庆祝博洛尼亚大学成立900周年的时候,由世界各地主要大学校长所共同签字的《欧洲大学宪章》,将“基本原则”的第一条规定为“处于社会中心的大学是一独立机构”,“应独立于一切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之外”(笔者有幸参与此盛典,并代替当时北京大学丁石孙校长在其上签了名)。
然而事实上,这只是人们的一种良好愿望。任何当代大学想完全摆脱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的影响,取得真正彻底的“独立”是不可能的。其原因在于:一是由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快,科技已成为最重要的“第一生产力”,它关乎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与未来命运。因此,政府与社会势力会千方百计地干预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学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运作与行为难免带有功利色彩。二是由于进入20世纪以后,科技发展迅猛,即使是做基础研究,个人单枪匹马难以取得重大成就,许多课题往往需要有巨额投资的设备装置和大批人员组成的团队齐心合力才能完成。因此,借助国家和社会力量的支持成为必需。国家与社会也须从全局考虑,权衡得失利弊,以决定对某项科研活动是否给予资助或否决。三是由于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给社会与人类带来福祉,也可能造成贻害、甚至灭顶的灾难。目前全球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生态破坏就是一例。这样,任何一个科研项目或技术课题是否可以启动与运作,必须仔细考察其社会影响和后续效应。而这些也必然涉及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利益。四是由于当下科学技术发展还萌发出众多的科学伦理问题。科技进步一日千里,人们或许会问,漫无边际的科学研究是否能解决人间的一切问题?无所不能的技术可否制造出某些人所要的任何东西?答案是否定的。而且,当下机器人、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大数据、云计算、脑科学、基因技术的发展,既能大大改善人类的生产能力与生存状态,也会造成灾难性的伦理质疑:生命过程能否计算出来、人可否长生不老、人可否知晓与控制他人的思维过程与内容、人可否随心所欲地繁殖出理想的后代?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要是这些都能实现,对人类究竟是祸还是福?难以预测。
正因为这样,科学实际上是受限的,技术不是无所不能的。试以曾经标榜实行“3A原则”(Academic freedom, Academic autonomy, Academic independence,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独立)的哈佛大学为例,我们只要读一下《哈佛规则——捍卫大学之魂》一书[10],就可发现它跟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的结合是何等紧密的了。我们看到,现在“3A原则”在哈佛大学几乎已偃旗息鼓了。
上述对科学技术的限制,用一句话说,就是不能将科学研究及其作用过分地、不恰当地、片面地强调和发展到“科学主义”的地步,特别是不能将它充斥到教育领域。这已引起教育界有识之士的深刻忧虑,他们认为“科学主义”将冲击完备的、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美国克龙曼的《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就是反映这种忧虑的著作之一[11]。
笔者翻阅了本世纪出版的我国关于教育学的著作,一个明显的印象是,不少作者都试图将教育学视为一个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在实验基础上严密论证的“科学”,因而他们将重点都放在从脑与神经科学及认知科学中获取结果与方法,进而单纯从“认知”上去论述教育目标与方法,这样就会迷失教育的方向,放弃对人生意义的拷问,缺乏对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教育终极目标的追求。
不错,“认知”、追求知识是大学之道特别是“自由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不过,我们要仔细辨认,这种“知识”是指人类拥有的全部知识体系,其中也包括人生意义、价值观和世界观等人文内涵。而认知确是大脑与神经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因此也完全可以从生理心理机制上将人类智能的产生与运行作为自然科学进行实验研究。美国学者加德纳就将人类智能分门别类地从生理心理上进行分析论证[12],提出了“多元智能結构”概念,对教育有很大帮助和启示。不过,我们不要忘了加德纳自己所说的:“‘多元智能不应该是也决不是教育的目标。教育目标必须反映人类自身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决不可能简单地来自科学理论”。
因此,教育学的“科学化”倾向可能并不是正面的,它将销蚀教育的真谛。教育必须坚持科学与人文相融合,而且将人文置于科学之上。这才是符合逻辑的,因为科学本来就是人的活动的一部分,是人对客观真理的探讨活动及对其结果的表述。所以,它是“人文”的一种内容。这样,意识形态在这里就起着重要作用。
2.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科学的独立自由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实现理想的“大学之道”的必然要求
从中国的情况来说,传统的“大学之道”本来就带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与人文关怀,“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曾经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所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大批知识分子正是凭着这种精神投身于火热的革命与建设大潮,使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并富起来了。当下我们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正要“强起来”,但内忧外患仍然严重存在,还有许多艰难困苦的任务要解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万众一心地攻坚克难。因此,在现阶段,大学要取得完全独立只是一种幻想,大学还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
不过,大学原则上仍应追求不受功利和权力影响的目标。科学史表明,将科学变成为生产力必须以技术为媒介,而从科学原理和规律到能满足人们需求与福利的物质或精神产品,或与其相应的服务,是一个十分艰难曲折复杂的长期过程。许多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果是“无用”的,只能满足少数人的好奇心理,所以,从事基础研究者往往需要有一种狂热的兴趣和闲适的心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竺可桢),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我国当下要求经济转型,一个重要障碍是技术上的原始创新不足。原始创新来源于基础研究,由于它浩渺无际,因而不可能按计划出成果。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在高精尖技术上还留有不少空白,还有一些关键技术被人家“卡脖子”,因此,目前我国的科学研究还偏重于有定向目标的应用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国力的增强,“无用”的漫无边际的基础研究将会逐步增加。到那时候,就可实现“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愿景,诺贝尔科学奖自然会不断涌现。预期这种时刻的到来也许不会等待太久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历史表明,如何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科学的独立自由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关乎高等教育与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面,这甚至会影响国家民族的兴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尊重知识、尊重科学技术人才的基础上才能确保党的领导。涉及科技文化事务决策,党和政府要倾听内行的意见,遵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处理,不做过多干预。在科学技术问题上绝不能“瞎指挥”,以致造成像“大炼钢铁”“超声波热”一类的荒唐事。只有这样,中国大学和科技事业才会走上康庄大道。因此,大学不断追求这种科学的独立自由精神将和党的领导形成一种合理的张力,成为实现理想的“大学之道”中的常态。
(二)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具有适应于当代社会文明程度的信仰和智能的普通劳动者或公民,是当代中国“大学之道”的时代特征
大学之道应该体现时代特征。整个人类进步了,财富总体上在增长,全球的文明程度在提高,人们受教育程度也相应提高。就我国而言,高等教育已经接近普及了。就是说,不久之后中国社会大多数人都受过高等教育了,这是社会或世界进步的结果,也是社会趋于公平的表现。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是中国传统的,还是西方近代的,“大学之道”都是以精英教育为出发点的产物,培养的不是治理国家和天下的“君子”,就是有闲暇时间可用来从事科学文艺活动的“绅士”或“某某家”之类的“英才”。因此,他们是社会的高阶人士,是少数。这种“大学之道”难道能适用于普及高等教育的现况吗?显然不能。
当下,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我们提出了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也就是说,大学所培养的应该是“人”,是能在社会立足并做出贡献的人,是普通劳动者或公民,而不仅仅是居于平民百姓之上的社会国家、乃至“天下”的治理者或“人上人”。当然,我们必须在前面加一定语,即培养具有适应于当代社会文明程度的信仰和智能的普通劳动者或公民。而这个信仰就应该是以24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特别要尊奉与践行对于公民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八个字,培养具有责任感、创新和担当精神的“公民”。这就是“德”。至于人必要的“智能”,则应是科学与人文融合,能够理性认识自己、认识周遭、认识世界大势,能够与他者对话、反思自我、进行批判性思维,从而能自如地应对错综复杂迅速变幻的世界的智慧与能力。所以,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核心内容应该是清晰的。
不过,“大学之道”也并非千校一面,它应当体现学校的特色定位。大学还有多种多样的,也有服务于特定地域与人群的。在普及化高等教育背景下,也应当允许有不同类型精英教育的存在。这使大学园地显得万紫千红、五彩缤纷。
科技在迅猛发展,信息在快速流通,人们的体力劳动乃至多数脑力劳动,将逐步被机器所代替。瞻望前程,世界在不断进步,但人类是否能走向更加文明,能否构成和谐的命运共同体,教育负有重大责任,“大学之道”起着关键作用。然而,当下我们看到,世界上乱象丛生。在这里,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少数操纵着当代尖端科技手段的人控制了世界绝大多数的财富。对此,有的人怪罪于高等教育的普及:认为当下社会是“过教育”了。这当然并不符合实际,是不对的。但这也不得不引人深思:大学到底怎么了?
归根结底,“大学之道”的根基在于“文化”。“文化”即“人化”,“人文化成”;也就是“育人”“立德树人”。《易经》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学作为文化机构,应该以继承和创新文化为使命,成为国家文化科学的标志,并以此来解决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乃至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人类更加“文明”。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简明确切地来表述“大学之道”呢?有待大家进一步思考讨论。
参考文献
[1] 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学报,1941(01):1-9.
[2] 王义遒.论自爱[J].高校教育管理,2015(03):30-46.
[3] 吴国盛.什么是科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27-35.
[4] [瑞士]瓦尔特·吕埃格,[比]里德-西蒙斯.歐洲大学史(第1卷):中世纪大学[M].张斌贤,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458-188.
[5] [英]约·亨·纽曼.大学的理想[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0-15.
[6]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62-84.
[7] 陈省身.陈省身文选[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244.
[8] [美]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3,12.
[9] 王义遒.探索新型综合大学——王义遒教育文选[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513.
[10] [美]理查德·布瑞德利.哈佛规则——捍卫大学之魂[M].梁志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5.
[11] [美]安东尼·克龙曼.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M].诸惠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0-89.
[12] [美]霍华德·加德纳.智能的结构——多元智能理论诞生20周年纪念版[M].沈致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6.
The Comparis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Ideology
WANG Yi-qiou
Abstract: The purpose and goal of university represent the connotation of university. Comparing the aims and objec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ir common point is to make natural people through education who can live in harmony with others and serve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country. China is a multi-ethnic country. The concepts of "patriotism" and "for the country" are emphasized in both the "make intimate association with people" in “The Way of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changing the people and changing the customs" in “Xue-Ji”. As a "rite" to maintain th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of family love and social order, it has become the core concept of universities. As a result, although the modern universities in China are an "imported products", they adhere to China's humanistic tradition and have a solid character in creating strong feelings of home country. Western universit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knowledge and science, and emphasize the concept of pure rationality. Especially after the concept of university was transplan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t has developed three functions of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erving the society, which has obvious utilitarian color.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university ideology" has two new and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first, it adheres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direction of running a school; second, it emphasizes on improving the cultural quality of the whole people and promot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goal of running a school. These two points are inclusive, logical and reasonable with the traditional university ideology that must be adhered to new standards of university ideology.
Key words: university ideology; university purpose; university goal; university cultur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责任编辑 李震声)
收稿日期:2019-11-12
作者简介:王义遒(1932-),男,浙江宁波人,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大学文化研究;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