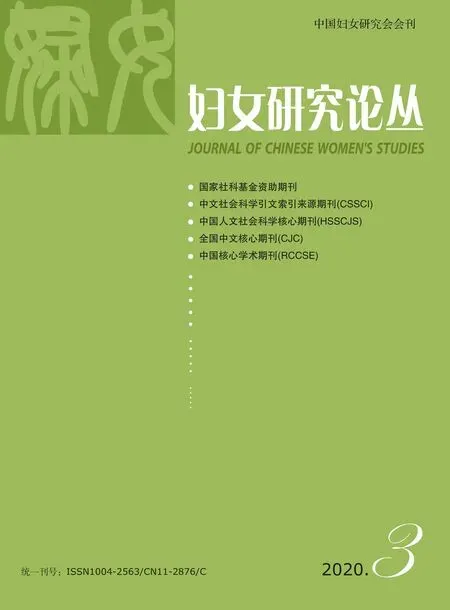延安妇女劳动英雄与新中国妇女的诞生
2020-03-22NicolaSpakowski著单佳慧译
Nicola Spakowski著 单佳慧译
(1.弗莱堡大学 汉学研究所,弗莱堡 79095;2.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政治学系,布鲁塞尔 1050)
1943年2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17岁女劳动英雄马杏儿的300字的报道[1]。文章讲述了马杏儿如何通过田间工作,逐渐摆脱贫困,获得周围环境的认可,并形成独立的意识。该文最后总结道:“新中国的女儿诞生了。”[1]马杏儿是1943年3月8日妇女节庆祝活动的焦点以及妇女通过劳动获得解放这一新模式的早期范例。此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被誉为“劳动英雄”或“劳动模范”(劳模)(1)“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这两个术语可以互换使用,但在早期,“英雄”一词占主导地位。,彰显了新中国在妇女经济参与、获得社会认同和自尊方面的潜质。而且,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文学、艺术和对外宣传的作品里的女性大多为劳动妇女。因此,作为重要的社会参与者和“新中国”的代表,妇女劳动英雄理应受到关注(2)有关女劳动英雄现象的介绍,可参见Patricia Stranahan,“Labor Heroines of Yan’an”,Modern China,1983,9(2),PP.228-252。西方学术界并不重视对劳动英雄的研究,这篇文章得益于中国学者关于延安劳动英雄的丰富研究成果。特别是张伟、王莹:《华北及陕甘宁根据地女性英模的生活》,《安徽史学》2016年第5期,第90-99页;隋立新:《陕甘宁边区时期文艺界对劳模的宣传》,《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7期,第66-79页;王彩霞:《延安时期“英雄”角色的置换——陕甘宁边区的文艺与劳模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121-125页。。
新中国妇女的隐喻性诞生是在战争和革命的背景下发生的。除了关于马杏儿的文章外,《解放日报》当天还报道了陕甘宁边区和生产领域的各种现象,如中国的战局、希特勒和欧洲的战争、红军的进展、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的演讲、印度的罢工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和当时政策的一面镜子[2],该报显然发现,马杏儿及其体现的新的妇女政策与当前的地方、国家和全球形势密切相关,足以被放置其中进行讨论。这也体现了国防、生产和新社会关系建设之间相互依存的战略。
我在其他地方论述过妇女问题如何与战争和革命问题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我也反对脱离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具体语境抽象地看待妇女问题[3]。我提出“变革”这一概念,它是一个全方位、多维度、复杂而又矛盾的过程,形塑了妇女的现实和中国共产党的妇女政策[4](PP 1-16)。从“变革”的角度理解这些妇女的现实和妇女政策,有助于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理解妇女解放的具体路径,也有助于保留复杂的历史时刻,避免线性“妇女史”。这些历史时刻有保护,也有介入。对某一群体和个人来说,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获益,有人受损。
在本文中,我将讨论延安的妇女劳动英雄,特别是其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文化再现。首先,我将论述在新民主主义背景下对国家和民族建设的考量如何刺激了当时妇女劳动英雄现象的形成。不少与这一社会主义形成阶段有关的新概念,比如劳动、社会、社会主义新人、女权主义、家庭、文化等,影响了妇女劳动英雄的再现和她们的体验,也促成了她们的多维度性(3)有关之后妇女参与生产的多维度研究,可参见董丽敏:《组织起来:“新妇女”与“新社会”的构建——以延安时期的纺织生产运动为中心的考察》,《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6期,第10-22页。。其中,劳动的概念最为重要,因为它已成为社会的根本准则和塑造社会关系的机制。因此,无论是作为妇女通过生产获得解放这一新宣言的范例,还是作为重新理解以劳动为核心的社会的切入点,妇女劳动英雄的故事都很重要。妇女劳动英雄被置于一个以劳动为基础的初级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劳动促成新的社会关系,人人参与劳动形成新的社会互动和新的共同体,例如家庭、邻里/村庄和跨地区的政治共同体,即使是“旧”社会最边缘的人群也能享有物质幸福和社会认可。当然,无论从国际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语境来看,这种以劳动为基础、由生产者组成的社会主义社会都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4)关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参见杨宏雨、吴昀潇:《建党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劳动观——以〈劳动界〉为中心的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204-212页;刘宪阁:《现代中国“劳动”观念的形成:以1890-1924年为中心》,《现代传播》2017年第3期,第22-31页;Xiang Cai,“Narratives of Labor or Labor Utopias”,in Xiang Cai,Revolution and its Narratives,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ebecca E.Karl and Xueping Zhong,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16,PP.251-306;Aminda Smith,Thought Reform and China’s Dangerous Classes:Reeducation,Resistance,and the People,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2013;Grewal,Anup,A Revolutionary Women’s Culture:Rewriting Femininity and Women’s Experience in China,1926-1949,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2012;Nicola Spakowski,“Dreaming a Future for China:Visions of Socialism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1930s”,Modern China, 2019,45(1),PP.91-122。。然而,它的基本特质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尤其是比较了阶级斗争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以及消费作为共和时期“上海现代性”和当下中国的调节机制而言。
其次,我将指出,不同于线性叙述,在革命进程中对妇女劳动英雄的再现和她们被赋予的理想角色存在断裂、矛盾和多重解读。确实,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了政策上的决定性转变和意识形态上的确定性转变[5]。但是,对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式的争论、矛盾和不断的探索仍然是共产主义运动从开始就展现出的基本特征,即动态的和多元主义的。共产主义史很多方向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其中一支是政治史,研究认为政策制定过程的实验传统是中共的一个显著特征,并贯穿于其整个历史之中[6](PP 1-30)。对中共来说,用暂时的模式解决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是非常有效的,劳动模范可以看作中国共产主义实验主义和地方主义策略的体现(5)[德]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也提到了劳动英雄,并加入了儒家传统和苏联劳动英雄运动对中国实践的启发,参见Sebastian Heilmann,“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The China Journal,2008,(59),P.20;关于毛主义使用劳模作为儒家“人”的观念的延续,参见Donald J.Munro,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具体到延安时期,对根据地的研究已证明,在不同根据地之间甚至同一根据地内部政策的异质性[7]。此外,对延安妇女的最新研究证实了妇女再现和妇女经验具有动态性和异质性。例如,文学学者董丽敏的研究展现了革命作家如何通过对新妇女政策的批判性反思,探索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式,以便妇女能够在脱离家庭压迫的同时不会陷入经常性的冲突或社会孤立状态之中[8](PP 16-28)[9](PP 10-22)。通过对不同作家乃至同一作家就具体妇女问题提出的动态解决方案的梳理,董丽敏的研究促使我们将延安时期看作一个探索的时期,而非巩固规范性话语模式的时期。同样地,历史学家丛小平在其对婚姻法的研究中,也强调了法律案件的复杂性以及革命的国家在不放弃妇女在婚姻问题上的利益的前提下,寻求调和革命意图和地方习俗的解决方案[10]。这些不同学术领域所勾勒的动态、近乎多元的情形,也解释了不同妇女劳动英雄形象的出现。
再次,我要重点强调在妇女参与生产方面同时存在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路径,并将之归因于当时中国共产党自我定位的双重时间性。这种双重时间性,一方面来自于以短期生存为必需的抗日战争,另一方面是具有长期视野的新民主主义和像妇女劳动英雄这样长期现象的形成或“诞生”。抗日战争及其带来的短缺是所有政策领域和对所有社会群体采取实用主义方针的出发点。因此,在大生产运动中,劳动英雄和妇女劳动英雄确实被当作模范,来提高生产率[11](P 229),但是,并不能把对劳动英雄和女劳动英雄的宣传简化成纯粹是为了提高生产率。另外,新民主主义使得共产主义运动的侧重点从权力斗争转向了国家和民族建设,或者,用当下的说法,就是从斗争转向建设。新民主主义被认为是初级社会主义,介于“尚未”但“已经”之间,是正在开始的阶段(6)参见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623-670页。。在革命叙事中,这一特定时刻体现在它调动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从“记忆”到“预言”的转变。整风运动(7)对劳动的强调,并不是否定阶级斗争在延安时期以及其后阶段的重要性,而是首先关注延安时期的“建设”转向,其次了解新的劳动概念如何成为全面社会转型的工具。正如我曾经论证过的[Nicola Spakowski,“Moving Labor Heroes Center Stage:(Labor)Heroism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Yan’an Period”,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2021,5(1),2020年3月20日网络发布:https://doi.org/10.1017/jch.2020.4],整风和生产运动是相互联系的,劳动英雄和女劳动英雄是权力格局的核心要素,包括毛泽东与人民群众、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另见阿米达·史密斯(Aminda Smith)2013年关于劳教的研究(Aminda Smith,Thought Reform and China’s Dangerous Classes:Reeducation,Resistance,and the People,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2013)。表明,“斗争”并没有从延安的话语和政治实践中消失,但是,长期的目标是“建设”。“建设”意味着新的权力结构已经形成,阶级斗争要让步于建立一个和平的社会。短期的实用主义和长期的理想主义视角间的矛盾,呈现出不同的妇女劳动英雄形象,她们或是作为“劳动力”,或是作为创建“新中国”的代表甚至是推动者。
本文由六部分组成,介绍了塑造妇女劳动英雄形成的政策和理念,并指出了女劳动英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同时存在的多种解读。第一部分,论述劳动英雄运动的理论基础——新的劳动观念以及对劳动作为社会基础的新认知。第二部分,介绍1943年中共妇女政策的转向以及新发布的妇女参与生产实现解放的决定。这里,我会反驳中国共产党的妇女政策转向保守的说法,并解释妇女参与生产实现解放的理念如何与全新的家庭和共同体形式联系起来(8)许多学者关注中共在延安时期妇女政策中的不同内容,将之看作对早期进步路径的偏离。其中一项是将1943年修订的婚姻法理解为维持父权制家庭结构的手段,参见Judith Stacey,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Kay Ann Johnson,Women,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Chicago/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另一项是1943年党动员妇女进行生产的决定,并伴随着对早期“女权主义”路线的批评,参见Kay Ann Johnson,Women,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Chicago/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PP.69-75;贺桂梅:《“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历史思想》,《南开学报》2006年第6期,第16-22页。。第三部分,讨论劳动英雄和女劳动英雄文化生产中的主要要素,尤其是作家和“群众”之间新的关系、以再现劳动英雄作为首选的报告文学以及乌托邦主义作为时间上的方向。第四、五部分,将分析有关20世纪40年代早期两位杰出的女劳动英雄马杏儿和韩凤龄的文本。一方面,展示妇女劳动英雄的整体形象如何反映了劳动、妇女解放和文化这些新理念;另一方面,指出这些文本中所描绘的女劳动英雄具体形象的差异。我将特别说明,通过不同的能动性和时间性范式,她们如何在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两条时间线上,在党的领导对象和变革的独立推动者、党的解放对象和自我解放者、过去受压迫的象征和未来新中国的先驱之间转换。最后一部分,我将总结研究发现。
一、“劳动是光荣的”——新的劳动理念及其通过劳动英雄的体现
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语境之中,劳动和工人都是共产主义理论关注的核心。在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背景下,劳动自然得到了新的关注[12](PP 30-35)。然而,延安大生产运动所提倡的劳动理念,不能仅仅从这场运动以及生产力的观念来理解。《解放日报》于1943年4月8日发布了一篇题为《建立新的劳动观念》的社论。作为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核心文本,从中可以看出,劳动对提高生产力和变革社会关系都至关重要,劳动英雄在这两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3]。这篇社论以劳动英雄新现象开篇,并将其与中国历史上对英雄主义的新理解、新理念联系起来:“从来只有战争中或政治舞台上的英雄,而现在劳动者也可以成为英雄了。”[13]这种角色的逆转,显然反映了生产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性,反映了参加生产的群众作为社会主义社会骨干力量的重要性。这篇社论以大篇幅分析了新旧劳动观念的区别,即劳动果实归属于谁——是劳动者自身(满足其短期和长期利益)还是剥削阶级。这篇社论指出,劳动英雄已经内化了这个新观念:“这些劳动英雄,他们本身也是一种新的人物。他们是解放了的人,他们懂得自己的劳动的意义,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劳动。”[13]显然,劳动被视为建立新的社会主义主体性的基础。
“建立新的劳动观念”在为构筑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劳动者的社会奠定了基础的同时,也反映了延安当时的形势和政策,包括大生产运动和对知识分子、干部的整风。文章指出,根据地残存的旧的劳动观念依然发挥着作用,影响了大生产运动的推进。一些劳动者依旧把劳动看成“受苦”;一些知识分子和干部,以妇女干部为例,也残存着轻视劳动的观念(9)《建立新的劳动观念》,《解放日报》1943年4月8日第1版。这段文字直接引自1943年2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轻视劳动的知识分子和干部被描述为“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根据唯物史观,劳动意味着体力劳动。因此,劳动被认为不仅可以提高生产,而且有助于培养热爱劳动的社会主义意识。因此,所有没有参加生产的人,包括女人、干部和知识分子、移民和“二流子”都成了当时运动动员的对象(10)这些运动压迫性的一面以及劳动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关系在动员“二流子”运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参见周海燕:《乡村改造中的游民规训与社会治理策略考察——以“改造二流子”运动为例》,《江海学刊》2012年第5期,第124-129页。有关1949年后体力劳动与社会主义意识之间关系更为详尽的理念,参见Aminda Smith,Thought Reform and China’s Dangerous Classes.Reeducation:Resistance,and the People,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2013,PP.38-51。。
接着,文章指出了大生产运动狭义的目的,即提高生产力和劳动效率:“几月来生产运动的经验已经证明,劳动者的积极性的提高[…],和劳动力的有效的组织[…]对于我们的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说起着主要作用。”[13]因此,劳动者需要被教育,以便理解和获得新的劳动观念。正是劳动英雄运动为大众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为了回应1939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实施的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大生产运动,劳动英雄运动正是这一生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直到1942年,中共才系统地以劳动英雄为榜样,动员边区所有人加入生产,以便提高生产力(11)有关延安时期甚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苏维埃时期的生产竞赛或者劳动者被授予荣誉、其事迹和生平被传播的例子,参见高玉娇:《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研究》,《延安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46-125页;齐燕庆:《中国劳模现象的历史及其沿革》,《理论前沿》1996年第9期,第31-32页;田松林:《模范文化与延安文学中的英雄叙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68-77页。有关大生产运动的研究,参见Mark Selden,China in Revolution:The Yenan Way Revisited,Armonk,London:Routledge,1995。有关选择和授予妇女劳动英雄荣誉的实用性一面,参见Patricia Stranahan,“Labor Heroines of Yan’an”,Modern China,1983,9 (2),PP.228-252。。在接下来的3年里,劳动英雄成为边区随处可见的现象。至1945年1月,有12000人获得了劳动英雄的称号[11](P 230),劳动英雄也成为延安时期改善物质状况、改造社会结构的起点(12)有关后一方面,参见Nicola Spakowski,“Moving Labor Heroes Center Stage:(Labor) Heroism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Yan’an Period”,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2021,5 (1),2020年3月20日网络发布:https://doi.org/10.1017/jch.2020.4.。
从1942年5月《解放日报》报道劳动英雄吴满有开始,《解放日报》以及其他出版物开始大篇幅报道劳动英雄[14](P 128)。通过劳动英雄集会和生产展示,干部和普通百姓可以接触到这些劳动模范,进而了解新的生产方式,看到近来生产运动的成果。并且,劳动英雄成为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起的新文化政策的核心主题。在讲话中,毛泽东呼吁知识分子服务和投身人民群众之中。鼓励知识分子深入乡村、深入工厂,与劳动英雄同住,用通俗的文艺形式再现他们的生活(13)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 by Bonnie S.Mcdougall(Michigan Monographs in Chinese Studies 39.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80).See also Chang-tai Hung,War and Popular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David Holm,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Brian James DeMare,Mao’s Cultural Army:Drama Troupes in China’s Rural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商昌宝、邱晟楠:《由报告文学创作看延安文艺转型》,《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26-130页。。
劳动英雄的宣传并没有遵循一套统一的概念。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它被划分为两种基本的视角。这两种视角在《建立新的劳动观念》中已有体现:一种是历史哲学视角,强调颠覆传统的权力关系,为想象社会主义新人和新的社会关系做铺垫;另一种是经济视角,强调经济理性,首先将劳动者看作劳动力。这两种视角在《解放日报》中以相当矛盾的方式并存。一方面,对大生产的报道是从经济视角出发的,强调扩大劳动力,督促每个人加大产量,来提高生产率。这类报道里充斥着数字:劳动者或劳动力(也可以被算作半劳动力)的数量、个体和集体产出、耕地面积等。个人生产计划被用来教导劳动者以理性的方式生产(14)有关生产计划的研究,参见王建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户计划》,《中国农史》2010年第1期,第66-74页。《解放日报》1943年6月16日的一篇文章很好地解释了生产计划如何运作,该文章对比了按照生产计划进行生产的儿子和有待被理性计划的生产方式说服的父亲,参见伊苇:《生产计划》,《解放日报》1943年6月16日第4版。。在这类报道里,尽管劳动英雄很重要,但只是罗列了他/她们的名字,将其作为有效动员的范例。另一方面,正如下文会讲到的,关于个别劳动英雄和女劳动英雄的长篇报道,能够远远地超越这些狭隘的生产率和生产理性,而是将这些英雄人物作为生产者和具有社会性的人,放在他们的切身环境中进行描述。此外,劳动英雄的形象根据诸如经济部门、性别等变量而有所不同,每个变量又与特定的政策有关(具体政策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在当时还未实行集体化的农业领域,吴满有代表了一种允许农民追求自身利益、积累个人财富的政策。相比之下,在工业领域,赵占魁被宣传为一个无私的楷模,代表集体工厂工人正确的价值观。妇女劳动英雄的形象并没有偏离上述这些领域劳动英雄的模式。但是,有关她们的报道被扩展到妇女解放和女劳动英雄的家庭生活层面。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在三八妇女节前后大力宣传女劳动英雄事迹的原因。女性劳动英雄肯定没有男性劳动英雄数量多(15)这个结论基于《解放日报》。1943年11月到12月,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被授予荣誉的180人中,有6位女性;1943年11月27日,《解放日报》头版报道插图里的11位劳动英雄木刻肖像画,其中有2位是女性;1943年12月19日,《解放日报》头版报道插图里的25位劳动英雄木刻肖像画,没有一人是女性。遗憾的是,我并没收集到整个时期和所有地区劳动英雄的数目。关于劳动英雄大会的意义,参见Nicola Spakowski,“Moving Labor Heroes Center Stage:(Labor)Heroism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Yan’an Period”,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2021,5 (1),2020年3月20日网络发布:https://doi.org/10.1017/jch.2020.4.,但她们并不是这些报纸的边缘人物。正如下文第四、五部分所论述的,诸如年龄、地区和特殊经历等更多的变量会起到作用,并有助于劳动英雄和女劳动英雄形象的多元化(而非个性化)。总之,我们必须将劳动英雄理解为作家提出的构想,而不是对现实的直接反映。在动机和政治态度问题上尤其如此(16)我与帕特里夏·斯特拉纳汉(Patricia Stranahan)在其“Labor Heroines of Yan’an”一文中的观点不同。斯特拉纳汉把《解放日报》文章当成客观报道,并强调劳动英雄的自我利益以及缺乏革命决心。我的观点会在有关劳动英雄韩凤龄报道的解读(第五部分)中得到更清晰的阐释。报纸对同一个人的动机和革命决心的报道会发生变化。我还发现斯特拉纳汉对于纺织运动(以妇女劳动英雄刘桂英为代表)的解读有误导性。即使缺乏统计数据,《解放日报》关于劳动英雄运动的报道也已经清楚地说明各个领域都有妇女劳动英雄。斯特拉纳汉为了弄清刘桂英是不是典型,其所选择的15个样本中,有9个样本来自农业领域。。
二、1943年妇女政策的转向:通过劳动获得解放
20世纪40年代早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妇女政策的一个转折点。1943年2月26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15](以下简称《决定》),宣称妇女参加劳动是她们获得解放的关键。根据《决定》,“经济丰裕”和“经济独立”是“提高妇女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的起点。中央委员会在《决定》的最后一段,号召妇女组织在即将到来的三八妇女节重点动员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
将妇女解放与她们的经济独立联系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早期中国妇女运动中并不新鲜[16][17]。在中国历史中,妇女参加生产也不新奇(17)参见Patricia Ebrey,The Inner Quarters: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解放日报》1944年8月25日。。该《决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以一种权威的框架阐述了妇女问题,远离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妇女解放的多元理解[17],标志着对妇女劳动英雄全面传播的开始。由于《决定》所体现的矛盾影响了妇女劳动英雄的再现,“1943年的转向”也是之后一些女权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妇女政策成败争论的关键,因此,必须在此加以论述。事实上,一些学者认为,延安时期中共妇女解放的立场转向了“父权制社会主义”(或相似观点)。他们的负面评价基于《决定》及其解释性文本对女权主义的批评和/或婚姻法的修订使军婚离婚变得困难这些事实(18)根据1944年的法律,与军人结婚的妇女可以在军人最后一次与家人接触的5年后申请离婚。对于这条和其他被视为妇女权利受挫的规定,参见Judith Stacey,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166-173;秦燕:《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家庭变革》,《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第196-197页;Xiaoping Cong,Marriage,Law and Gender in Revolutionary China,1940-196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然而,将其解读成保守转向则过于简单了,对此需要更为细致和透彻的论证。
首先,不能孤立地评价婚姻法的修订,而应将其置于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宣传新式家庭的一整套措施中加以理解。现实证明,延安当时的婚姻法不足以作为妇女解放和动员的手段,其浪漫爱情和自由意志精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出身和五四传统,并与乡村社会的婚姻传统相冲突。相比于城市,婚姻在乡村具有很强的经济色彩。在法律实践中,现存婚姻法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因为它仅使部分妇女群体受益,也往往被一些妇女利用而违背其精神,引起社会冲突并危害社会稳定(19)具体可参见董丽敏:《“劳动”:妇女解放及其限度——以赵树理小说为个案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3期,第16-28页;董丽敏:《组织起来:“新妇女”与“新社会”的构建——以延安时期的纺织生产运动为中心的考察》,《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6期,第10-22页;董丽敏:《延安经验:从“妇女主义”到“家庭统一战线”——兼论“革命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的生成问题》,《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6期,第19-27页;Xiaoping Cong,Marriage,Law and Gender in Revolutionary China,1940-196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周蕾:《冲突与融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家庭政策的变革》,《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第40-48页。。的确,提倡和谐家庭的理念是为了平定社会关系,但这一举动并不一定就是保守的。妇女并没有被要求回到过去的封建家庭,而是被置于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之中(20)具体可参见董丽敏:《延安经验:从“妇女主义”到“家庭统一战线”——兼论“革命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的生成问题》,《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6期,第19-27页;周蕾:《冲突与融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家庭政策的变革》,《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第40-48页。。
这些新的社会关系的核心是“新式家庭”,1944年8月《解放日报》的一篇文章描绘了理想的新式家庭(21)《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解放日报》1944年8月25日。关于新的家庭政策和家庭生活的新民主形式,参见周蕾:《冲突与融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家庭政策的变革》,《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第40-48页;王建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户计划》,《中国农史》2010年第1期,第66-74页;张孝芳:《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第137-140页。。这个新式家庭,既是一个经济单位,也是一个社会单位。它产生于一种理性和民主的方式之中,采用生产计划,合理分配任务,实行物资激励、红利和奖金制度,以及通过所谓的家庭会议的方式来决定生产和收入的分配,并且每位家庭成员都有发言权。显然,理论家们将家庭构想为一个理性生产者的单位,这些生产者既是劳动力,也是新的社会存在。至于解放的问题,新式家庭会议有一种均衡效果,所有家庭成员,无论年龄和性别,都以生产者的身份参加会议,平等地分担繁重的劳动,分享劳动成果,为家庭带来可计算的收入,并因此获得家庭和家庭之外的认可。生产被视为解决家庭冲突的关键因素,作为妻子和儿媳,农村妇女通过对家庭收入的贡献,获得了丈夫和婆婆的尊重。此外,鼓励妇女自愿参加的生产合作社可以被看作家庭和公共利益之间的一种调节方式[9](PP 10-22)。因此,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照搬,也不完全是剥削作为劳动力的妇女的手段,而是摆脱具体压迫形式的一种更为现实的对策。
其次,《决定》及其相应文件对妇女干部和女权主义的批评,反映了更为普遍的时代关切。即,当时对知识分子相对于人民群众的地位以及群众运动的路径和组织结构的普遍性忧虑。一方面,无论男女,所有干部都被鼓励为提高生产力做贡献,融入群众,了解群众的“真实”生活[18]。而且,所有群众运动开始放弃相对独立发展的传统和“斗争”精神,而倾向于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建设”的语境中形成新的身份和认同(22)有关整风运动时期工会的情况,可参见周海燕有关赵占奎运动的论述。周海燕:《记忆的政治》,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有关妇女、工人和青年少组织同样被批评的研究可参见《西北中央局对边区群众工作的指示》(1943年5月5日),载山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第二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61-65页。。在女劳动英雄的文章里,这个问题体现为能动性的问题。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妇女组织和妇女劳动英雄是潜在的变革源。另一方面,对妇女干部的批评确实较为严厉。《决定》批评她们“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15],《解放日报》在《建立新的劳动观念》一文中引述了这段话,其他文章对妇女干部也有类似批评(23)例如,刘少奇批评女干部“冒充英雄”,高岗指出村民称她们为“二流子”。参见《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妇委同志的讲话》(1945年4月),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772-780页;高岗:《从生产战线上开展妇女运动》,《解放日报》1944年3月10日。。同时,在个别党的男性领导人中,还残留着对妇女的偏见,影响了他们对妇女解放的承诺(24)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论述了延安时期男女平等的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参见丁玲《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第4版。据说贺龙将军提到这篇文章,称丁玲为“臭婊子”,直接引自商昌宝:《〈讲话〉的接受与“暴露派”的转向——以刘白羽,艾青为考察中心》,《湘潭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第96页。。
三、报告文学对劳动英雄和妇女劳动英雄的再现及其文学类型的乌托邦潜质
妇女劳动英雄的再现既受劳动话语的影响,也受妇女解放话语的影响。从经济的视角看,妇女劳动英雄表明了妇女可以作为劳动力;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她们体现了新的劳动观念和新的妇女解放理念。这两种视角在延安时期都是有效的,也同时存在于《解放日报》和根据地的其他报纸当中。妇女在新闻报道中的地位表明,社会把妇女当成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性的存在,是共产主义运动赖以生存的重要角色,也是未来新中国的正式成员。在某些情况下,她们被视为社会变革的驱动力,同时,作为妇女,她们展现了彻底打破封建社会结构的潜能。
妇女劳动英雄被纳入新闻报道中,这一事实构成了对过去甚至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一个根本性突破。在此之前,农村妇女只是作为动员的对象,作为一个集体被讨论。有名字的个体是例外,且仅作为这场或那场运动中的杰出代表被简单地提及(25)此观察基于对早期《解放日报》和《晋察冀日报》的粗略浏览,另可参见田松林对1933年劳动英雄最早报道的罗列。田松林:《模范文化与延安文学中的英雄叙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69页,报道的标题并不涉及具体劳动英雄的名字。。随着向劳动英雄学习运动的开展,个体的农民和工人——无论男女——他/她们的名字、生平、成就、某种人格和特定的社会环境被写入了报纸。以经济视角撰写的报道,只是简短地提及他/她们的名字和可计算的劳动成果;而报告文学叙事则侧重新的劳动观念、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义人格。的确,以报告文学作为体裁、以劳动英雄为主题和以乌托邦主义为时间上的方向,形成了一个整体范式,形塑了劳动英雄和女劳动英雄的具体形象。
1930年,中国文学学者开始使用“报告文学”这一术语。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报告文学就成为中国左翼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是,正如查尔斯·劳夫林(Charles Laughlin)等学者所描述的,报告文学根植于具有更为悠久传统的文学类型,也受到了国外报告文学的影响(26)Charles A.Laughlin,Chinese Reportage:The Aesthetic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Peiqin Chen,“Social Movements and Chinese Literary Reportage”,in John S.Bak and Bill Reynolds,eds.,Literary Journalism across the Globe:Journalistic Traditions and Transnational Influences,Amherst and Boston: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11,PP.148-161。有关中国报告文学的历史、它的国际面向、共和国时期工人阶级和妇女作为报告文学的主题等内容,可参见Grewal,Anup,A Revolutionary Women’s Culture:Rewriting Femininity and Women’s Experience in China,1926-1949,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2012,P.228,作者认为延安时期的农民妇女劳动英雄是早期报告文学中女工人形象的延续。。广义的报告文学指“对当下事件、个人和社会现象的任何非虚构写作”[19](P 2),在劳夫林看来,其文学潜力在于“对社会空间的文化建构”,包括“所描述的社会情境的具体轮廓、结构、气氛和独特事态变化”[19](P 29)。报告文学通常将劳动英雄置于其生活的物质和社会空间中,通过描写他们所居住的物质和社会空间来刻画劳动英雄。换句话说,劳动英雄是通过文学手段构建社会空间的首选对象。在延安的背景下,毛泽东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促进了报告文学数量的激增。随着毛泽东号召作家融入群众,更好地反映群众的现实,作家们走访了边区的村庄,会见了劳动英雄,并通过其周围环境来刻画他们(27)具体可参见商昌宝、邱晟楠:《由报告文学创作看延安文艺转型》,《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26-130页;胡玉伟:《历史的转折与文体的演进——论解放区的报告文学》,《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02-107页;隋立新:《陕甘宁边区时期文艺界对劳模的宣传》,《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7期,第66-79页;Charles A.Laughlin,Chinese Reportage:The Aesthetic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PP.227-230。关于作家与群众之间关系的讨论,可参见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Nicola Spakowski,“Moving Labor Heroes Center Stage:(Labor)Heroism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Yan’an Period”,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2021,5(1),2020年3月20日网络发布:https://doi.org/10.1017/jch.2020.4。有关作家应如何表现劳动英雄的当代例子,请参见萧三:《第一步——从参加边区参议会及劳模大会归来》,《解放日报》1945年2月20日。。通过描述他们的工作、容貌、空间环境(住房内部、市场等)、工作场所(田间、工厂)、他们的劳动产品以及通过直接引述群众间的互动,报告文学高度还原了群众生活,并使用了贴近群众的语言。同时,作家利用这些细节和场景构建着中国新农村这一特定的社会空间。
乌托邦作为时间上的指向并不是延安报告文学的必然特征,而是受到了当时文化政策的鼓励。这里需要对“乌托邦主义”作一个具体的定义,以便用来分析延安妇女劳动英雄文本的未来指向(28)有关乌托邦概念及其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应用更全面的介绍,可参见Nicola Spakowski,“Dreaming a Future for China:Visions of Socialism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1930s”,Modern China,2019,45(1),PP.91-122;Charles A.Laughlin,Chinese Reportage:The Aesthetic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第223页提到中国社会主义报告文学的“乌托邦修辞”,但列出的特征不一定都是“乌托邦式”的。另外,此文缺少对乌托邦主义的理论讨论。。研究乌托邦主义的学者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乌托邦主义,即“终极状态”和“过程导向”[20](P 174)。“终极状态”的乌托邦主义(也叫“蓝图”或“古典”乌托邦主义)指把乌托邦作为构想的理想政体[21](P 49),以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为原型。它的主要特点是,从整体结构上描述了一个更美好的社会[22](PP 4-5)。此类型乌托邦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它对理想新社会的描绘是静态的,同时,也是高度规制、完善和统一的[20](P 174)[22](PP 1-21)。相比之下,“过程导向”的乌托邦文本,“拒绝把乌托邦看成蓝图,同时保有此梦想。此外,这类[乌托邦]小说用大量笔墨讨论原始世界和与之相对的乌托邦社会之间的冲突,从而更直接地阐述社会变革的过程”[23](P 10)。我曾经论述过,共产主义思想包括(也需要)这两种乌托邦,既受到更美好社会的具体愿景也受到通向更美好未来的过程理论的启发[24](PP 91-122)。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中国共产党)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反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理由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试图把完美的计划强加给现实,而不是在现实中寻求社会变革的手段”[25](P 59)。
如下文所示,延安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类型是具有未来指向的,但是个体的文本对终极状态和过程导向的乌托邦主义有着不同的应用。前者受政治鼓励,当时政治要求作家聚焦根据地光明的一面(29)很多作家都讨论过“赞美光明”和“揭露黑暗”的关系,包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参见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光明指向“新中国”“新型的人”或“新时代”以及理想化的农村生活场景,这些场景通常缺乏时间深度或未超出农耕周期。在这些文本中,社会主义已经存在,就体现在劳动英雄和女劳动英雄的成就和观念中。
其他文本较为灵活,并以劳动英雄为例阐述社会变革的过程和动力。在这些文本中,能动性是最重要的因素,不同的时间模式导向不同的能动性。劳动英雄成为主体时,能动性就从中国共产党转到了普通群众的身上。正如作家萧三所言,劳动英雄是“新时代新社会的建设者、创造者、带头的和骨干”[26]。这类文本通过明确提及“新中国”以及彰显物质福祉、力量和富饶的场景和符号,视当前为光明未来的起点,这是自我意识觉醒和赋权的过程。在一些极端例子里,劳动英雄被描绘成村庄通往未来的领袖。相比之下,以党为主导角色的文本将这场革命看成是政治干预,回到了翻身叙事,着重刻画有关过去不公的记忆,并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运动将会修正这些不公(30)“翻身”作为叙事模式尚未成为学术研究焦点,但是对诉苦的研究提及了“翻身”,诉苦是公开呈现翻身叙事。例如参见Lifeng Li,“From Bitter Memories to Revolutionary Memory:On Suku in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Land Reform of the 1940s”,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2013,(47),PP.71-94。大体上,我将“翻身”理解为阶级解放叙事。与本文讨论的大部分文本不同,在“翻身”和“诉苦”的叙事框架下,阶级仇恨是建立新社会的关键因素。。在这种范式下,中国共产党对劳动英雄和女劳动英雄的领导和规范是叙事的重点。
显然,报告文学文本在情节构架和不同风格元素的使用上是多样化的,下文的例子也会说明这一点。对同一个妇女劳动英雄,不同的报告文学文本可以传递截然不同的形象以及不同的社会理念和革命历程。在延安时期,报告文学仍然具有实验性质,因此成为探索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的媒介(31)有关此体裁的杂糅、实验本质、风格选择以及“再现实践”,参见Grewal,Anup,A Revolutionary Women’s Culture:Rewriting Femininity and Women’s Experience in China,1926-1949,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2012,P.202。。
在接下来的两个部分,将介绍有关劳动女英雄马杏儿和韩凤龄的文本,这些文本反映了革命叙事从党到人民、从过去/现在到现在/未来的转向(不是绝对的转向)以及从“记忆”到“预言”的过渡(32)对于这两个术语,可参见Ruth Levitas,“Pragmatism,Utopia and Anti-Utopia”,Critical Horizons,2008,9(1),P.56.。的确,在有关这两个人的文本中,(横向的,即当代的)人在社会和自然环境中的场景比(纵向的)解放的历史多。前者表现为和谐、协作的后革命中国农村,人们幸福安康,甚至最贫穷的成员都能得到社会认可。两种类型的共存源于不同的合法性模式,以及新民主主义作为“已经”但“尚未”的时态,这是从(需要记忆的)“斗争”到(需要预言的)“建设”的转变阶段。露丝·列维塔斯(Ruth Levitas)在其关于乌托邦主义的著作中,将这种从记忆到预言的转变与能力的变化联系起来:“对能力的强调意味着,应从个人和集体会成为什么,而不是来自哪里的角度来表达人类身份。”(33)参见Ruth Levitas,“Pragmatism,Utopia and Anti-Utopia”,Critical Horizons,2008,9(1),第56页提及罗伯托·昂格(Roberto Unger)的著作Democracy Realized:The Progressive Alternative。
四、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妇女解放新模式和主体性的诞生
1943年2月2日,马杏儿被提为劳动英雄[27](P 738),她是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女劳动英雄[28],也是1943年三八妇女节庆祝活动的中心,是众多通俗文艺作品表现的对象[29](PP 122-123)[27](P 738)。马杏儿成名时才17岁(20岁去世,具体情形不详)(34)《解放日报》没有报道马杏儿的死亡。根据延安当地编史,马杏儿20岁结婚并收养了一个孩子。孩子的死亡造成了她精神分裂,无法救治。具体死亡原因不详。参见延安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延安市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38页。。本文选择马杏儿,源自她是第一个妇女劳动英雄,而且她的事迹接近1943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决定》动员妇女参与经济生产的时间。一方面,马杏儿是农业领域女劳动英雄的典型;另一方面,她极其年轻,是年轻女孩的榜样,也许还为新中国妇女的隐喻性“诞生”提供了灵感。马杏儿的故事被《解放日报》表现为两种成就的典范:一种是贫民迁移到延安的成功故事,她与父亲马丕恩,被叫做马氏父女(35)马丕恩也是劳动英雄,并且是“马丕恩运动”效仿的对象。参见Pauline B.Keating,Two Revolutions: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 1934-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关于安置的问题参见第90-129页,关于运动的内容参见第121-122页。马丕恩和他的女儿出现在多篇《解放日报》报道中。1943年2月11日的《解放日报》在头版介绍了马氏父女的故事,还刊登了一篇题为《劳动家庭》的报告文学。分别参见《马氏父女生产卓著一年劳动两年余粮移民生活迅速改善的榜样》,《解放日报》1943年2月11日第1版;莫艾:《劳动家庭:难民马丕恩翻身的故事》,《解放日报》1943年2月11日第4版。,一起出现在报道中。另一种是妇女解放的故事。两个故事交织在一起,表明了政策领域以及男女个人和家庭命运的不可分割(36)有关马家历史可参见莫艾:《劳动家庭:难民马丕恩翻身的故事》,《解放日报》1943年2月11日第4版。。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既将劳动英雄和女劳动英雄看作劳动力,也把他/她们看作社会主义变革的象征甚至推动者,存在多种对马杏儿的解读就不足为奇了。一方面,马杏儿是妇女节活动和演讲的重要人物,党的代表们通过她的例子,从经济的角度歌颂通过劳动获得解放的新政策;另一方面,马杏儿的例子激发了报告文学作者们,在妇女解放的漫长叙事中探索新解放逻辑社会性的一面,这种新解放逻辑指向的是未来的理想社会。
1943年妇女节庆祝期间,马杏儿是党宣传的重点。《解放日报》做了大量报道,甚至在头版刊登了马杏儿的事迹,连同一幅她的木刻肖像[30][31]。当天的口号使她成为妇女解放新逻辑的典范:“学习马杏儿”,或者“纪念三八妇女节要努力生产”[31]。根据《解放日报》,庆祝活动分为群众活动和政治活动两部分。群众活动部分针对农民展开,农民可以直接接触马氏父女。这部分报道的焦点是欢乐的气氛和马杏儿如何受欢迎,人们来看她,指着她,围着她,跟她握手[32]。父亲和丈夫们告诉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学习马杏儿,为咱家也争点光吧。”大人们叮嘱小女孩:“你看,人家多光荣,你也得好好劳动。”[32]显然,农民渴望拥抱新政策,并把马杏儿当作学习的榜样。政治活动部分是针对干部的,由党内领导的讲话组成。所有讲话都专注于生产以及妇女对生产的贡献。朱德称生产是建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基础。高岗明确表达了妇女劳动的经济价值。根据他的测算,如果边区妇女每人养一头猪和一只羊,边区全年即可增加10亿元财富。高岗认为,提高产量将“自然”地解决妇女和女孩的所有问题。另一位领导人建议用“马杏儿自己动手,建立经济基础,因而为众人所崇敬的故事”,来鼓励妇女参加生产。同样,妇联会(37)妇联会是共产党边区妇女组织的名称。副主任建议用马杏儿的“例子”证明,“只要好好生产,财神爷自然就上门了”[30]。这些报告表明,马杏儿被作为了传递政治信息和宣传的范例。在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中,党内一些领导人把农民妇女看作潜在劳动力,其平均产出总和是一笔巨额的年收入,或者将其看作家庭荣誉的贡献者。
相比之下,1943年2月13日刊登的《新中国的女儿诞生了——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1]则开启了新的文学探索,把妇女解放的新逻辑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要素。这篇文章不是典型的报告文学,它仅仅再现了马杏儿、她的母亲以及作者三个角色的密切互动,并聚焦在马杏儿的想法和情感,而不是她作为劳动英雄的日常活动和以此建立的社会关系。聚焦马杏儿的内在生命使得“新中国女儿的诞生”成为自我觉醒和主体性的问题。读者可以从文中了解到,新民主主义旨在认识新的现在和其蕴含的未来潜力,而拒绝沉迷于过去。
马杏儿的故事是由她的母亲讲述的。作者似乎在场,描述着当时的场景和马杏儿的反应,有时候会插入,提出问题和做出解释;马杏儿本人是被动的,在母亲的怀里哭泣。除了抽泣,她只大声说了两次话。从她和母亲的亲密和自怜看,马杏儿就像个孩子。在蜕变成为新中国隐喻性女儿的过程中,她的形象的确就是一个女儿。文章没有过多刻画马杏儿的母亲,她似乎介于因过去的苦难陷入痛苦的女儿和理性的作者之间。作者是介入者,对马杏儿的悲痛提出疑问,并帮助她意识到其崭新的“现在”。此外,作者还确认了新中国的“女儿”诞生的时刻,打开了新中国的时空视野。
这篇故事讲述了马杏儿过去在富人家里当仆人,嫁到跟自己家一样穷的人家的依附经历和所受的屈辱,以及她不得不和娘家人一起生活,并和父亲一起参加田间劳作。田间的劳作非常艰辛,比她想象得更具有挑战性。另外,这些都是违背父母意愿的。但是,马杏儿适应了劳动的艰辛,最终承担起了一个“全劳力”的工作。因此,她获得了物质独立和社会认可:“但是,劳动产生了幸福:凭着自己的辛苦,吃的穿的都有着落了,按照自己的需要,要吃多少是多少,谁也不敢再来限制了。”她的外观也改变了,“有着自己的健康的英姿”,村民都很尊重她。来自“上级”的某个“同志”就她的工作成绩采访了她。“她的劳动没有白费,而且获得出乎意外的‘社会报偿’了。”社会甚至让她成为劳动英雄,这意味着她成为“处在社会高层级的人”。
这是一个自我解放的故事,马杏儿通过艰苦劳动实现了从依附到独立的转变。她的故事与之前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打破阶级剥削的典型故事形成对照。党在这篇文章里几乎不在场,文章里提到的“同志”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角色。此外,这篇文章虽然深入探讨了马杏儿的过去,但其真正的作用——体现在记者的声音中——是质疑她对过去苦难的悲痛。记者反复询问她为什么哭泣,鉴于她过去的生活非常艰难,记者对她表示了同情,但一直引导她关注当下。马杏儿自己是矛盾的,她会哭,也会难以置信地承认:“妈!想不到还有今天!”在文章前几段对她外貌的刻画中,马杏儿潜在的自我意识已有所体现,她对着新买的镜子在观察自己。她的外表变得坚强、健康甚至迷人(38)参见Grewal,Anup,A Revolutionary Women’s Culture:Rewriting Femininity and Women’s Experience in China,1926-1949,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2012,第202页关于报告文学对“表达、姿态、做法、外观”描写的偏好,并把这些描写看作“一套揭示社会主体性的实践和新型主体出现”的内容。。但是,仅在最后一段,她才意识到新的自我:“熬过来了,自己可以吃苦了,我也可以不靠人家了。”正是记者权威的声音最终将马杏儿的矛盾情绪转化为明确的信息:过去的记忆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在的认知和对未来的信心。记者告诫马杏儿:“不要再想了!不要再想了!还是说说现在吧。”在马杏儿谈到自己的独立时,记者插入总结道,马杏儿“不再是俯首从人的妇女”,而是能养活自己、自信、通过自己的劳动给自己创造经济基础的人了。“从她坚定的面容上,我看出了一点:新中国的女儿诞生了!”这个“新中国的女儿”不是一个满足经济运动需要的劳动力,她的个人价值也并不止体现在经济方面。相反,她是以一个获得独立(这种独立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社会认可和自我意识的人的形象出现的。
1943年10月5日刊登的《访马杏儿》(39)具体可参见式微(笔名):《访马杏儿》,《解放日报》1943年10月5日第4版;Judith Stacey,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是典型的报告文学,它充分运用了报告文学的手法描绘理想的外在社会空间。文章最惊人的是报道的时效性(采访日期是9月19日)、场景的呈现以及作家和村民的互动(40)参见Grewal,Anup,A Revolutionary Women’s Culture:Rewriting Femininity and Women’s Experience in China,1926-1949,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2012,第202页关于“发现、启示、调查、相遇和交谈”作为报告文学的典型修辞策略的内容。:记者们到了马杏儿所在的村子,却需要等到马杏儿从市场回来才能见到她。他们利用等待的时间挨家挨户地走访,采访了马杏儿的亲戚和邻居,吸引了新近到来的移民,最后是马杏儿加入交流。因此,这个故事在记者(作为知识分子)与群众、村民之间有着丰富的社会互动。此外,文章充满了直接引语,使用着这些非常大众的语言。前文提到的三八妇女节政治报告直言不讳地传达了参加劳动的妇女会赢得丈夫和婆婆的尊重,但在这篇文章中,记者在解释时相当克制,而是通过村民的话来表达马杏儿获得了认可和尊重。
与《新中国的女儿诞生了——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一文不同,在《访马杏儿》这个故事中,马杏儿是和生活在移民定居点的公婆家一起接受的采访(41)在《新中国的女儿诞生了——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中,婆家只出现在描述马杏儿的过去的篇幅里,来说明她为何悲情。她是典型的儿媳妇,总是最后一个领到食物,丈夫是陌生人,离开了她,迫使她与自己的娘家人住在一起。参见育涵(笔名):《新中国的女儿诞生了——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解放日报》1943年2月13日第4版。从对马杏儿访谈得知,由于丈夫在城市工作,这对夫妇只是暂时分开。马杏儿的公婆对她评价很高,透露了这个似乎是幸福的婚姻的一些细节。参见式微(笔名):《访马杏儿》,《解放日报》1943年10月5日第4版。。选择这个环境可能是记者故意为之,以便展开论述那些效仿马家的新近移民案例以及描绘儿媳与婆家的新型关系。故事是这样说的:记者来到村子,遇到了马杏儿的婆婆,得知马杏儿去了市场。跟马杏儿一样,婆家高家也来自米脂,最近才追随马家搬到了延安。记者来到高家的窑洞,跟邻居聊了聊。高家没有马家富裕,窑洞和家里装饰都很简陋,但非常干净,给人一种“愉悦的感觉,就好像在说,这个家庭对生活的态度是幸福而严肃的”。因此,他们也是成功的。而且,马杏儿的婆婆和邻里的妇女们(丈夫不在延安工作)还“带着一些骄傲和满意”地聊起了安顿情况、农活、家务、孩子和日常生活。所有人对马杏儿的评价都非常正面且怀有敬意:她的婆婆知道记者要来采访马杏儿,在记者到达时带着愉快的微笑,“显然她分得了杏儿的光荣了”。邻居承认马杏儿喜欢劳动。她的公公估计她还没回来是因为回家路上遇到太多熟人。据记者所言,这是因为她是劳动英雄的缘故。终于,马杏儿和她9岁的叔叔一起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双没做完的布鞋。与上篇文章一样,记者详细描写了她的外表,并用“结实、健康、快乐”来形容。对马杏儿的访谈聚焦在她的农业生产经验和冬季的计划。文章倒数第二段总结到,马杏儿的原生家庭和婆家都很看重她,这是因为劳动的妇女提升了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她们已经摆脱了“封建樊笼”,并有机会参与社会生活。“这就是说,在新民主主义政治之下,我们的妇女是开始得到真正解放了。”文章最后一段回到直接对话:被问到冬天的计划,马杏儿回答了一个词“纺纱”。记者鼓励她努力工作,以便成为来年的劳动英雄。最后,马杏儿邀请记者一起参观了秋收成果。
《访马杏儿》一文所构建的社会空间是中国新农村,在这里,农民受到关注,包括知识分子和农民在内所有社会关系都是相互尊重和协作的关系。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是妇女通过劳动走向解放的缩影,是这个新型农村社会中受尊重的一员。在这篇文章中,时间性主要体现为农民的视野:农业年(去年的收成、明年的生产计划)以及最近的移徙经验。而变革的过程是通过作者之口(尽管很微弱)表达的。妇女通过参与生产,“封建束缚”被打破了。在新民主主义背景下,妇女“开始”解放。在这篇文章中,马杏儿同样是初期社会主义的典范。
五、妇女劳动英雄韩凤龄和妇女作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
妇女劳动英雄韩凤龄家住中国东北部晋察冀边区涞源县银坊村。晋察冀边区与陕甘宁边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靠近前线,因此经常受到日军袭击,自然灾害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艰辛(42)具体可参见《新型的妇女——韩凤龄》,《晋察冀日报》1943年6月27日,载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编:《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第613-617页;《边抗联邀请戎冠秀等开座谈会制订一九四四年生产计划》,《晋察冀日报》1944年2月22日,载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编:《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第618-622页。。在这种背景下,韩凤龄的形象包含了她克服困难、遭受各种挫折后恢复工作的能力。1940年,韩凤龄被提为妇女劳动英雄,时龄39岁(43)仓夷:《韩凤龄》,《晋察冀日报》(1944年2月25日)和《解放日报》(1944年3月27日),载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91页。关于韩凤龄年龄的确定,参见罗宗藩、高振德:《涞源妇女劳动英雄韩凤龄》,《晋察冀日报》1945年1月24日,载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1945年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130页。。《晋察冀日报》和《解放日报》报道了她的成就[33],当时不同的画报和插图书籍共发布了十张她的照片[34]。关于她的文本相对较多以及这些文本提供的她的故事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和冲突(44)在韩凤龄的例子中,劳动英雄是为家庭财富还是为集体工作的动机,以及日益富裕的劳动英雄的阶级地位的问题非常突出。有两个文本根据韩凤龄明智的经济决定,认为她的动机是增加财富,参见《新型的妇女——韩凤龄》,《晋察冀日报》1943年6月27日,载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编:《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第613-617页;《政府奖给韩凤龄一条黑牛——涞源妇女劳动英雄受奖记》,《晋察冀日报》1944年2月4日,载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编:《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第611-612页。相比之下,另外两个文本强调了她的无私和她对“发财思想”的自我批评,参见仓夷:《韩凤龄》,《晋察冀日报》(1944年2月25日)和《解放日报》(1944年3月27日),载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89-295页;罗宗藩、高振德:《涞源妇女劳动英雄韩凤龄》,《晋察冀日报》1945年1月24日,载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1945年卷,第1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130-134页。,这是本文选择她的案例的原因。作为一个在组织工作方面很有经验的中年妇女,韩凤龄的榜样生活比马杏儿更为丰富。
从经济或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对韩凤龄的报道和马杏儿一样。1943年的妇女节庆祝活动报告提到了“韩凤龄运动”。报道简短甚至有些公式化地介绍了韩凤龄的生平和成就,提到了妇女的解放,但仍聚焦在生产(45)《北岳区举行盛大纪念会》,《晋察冀日报》1943年3月14日,载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编:《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第317页。1943年至1945年晋察冀妇女运动文件多次提到韩凤龄,参见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编:《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第324页。次年的文献也有重点提及韩凤龄形象,参见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编:《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第435页。有关《解放日报》中的韩凤龄形象,参见“中共晋察冀分局登记馆”。。不难发现,《晋察冀日报》也把妇女节与大生产运动的宗旨联系在了一起。
在分析有关韩凤龄的最典型报道之前,我想借助一组文本来说明劳动妇女不同形象所展现的不同能动性如何引发对革命历程不同的概念化和理论化。其中一个版本,可以称为“党领导的动员”,其中,韩凤龄的生活和成就被写成政治传记,聚焦在作为干部、热衷践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她及其丈夫的工作(46)具体可参见仓夷:《韩凤龄》,《晋察冀日报》(1944年2月25日)和《解放日报》(1944年3月27日),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89-295页;罗宗藩、高振德:《涞源妇女劳动英雄韩凤龄》,《晋察冀日报》1945年1月24日,载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1945年卷,第1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130-134页。。这类文本也属于报告文学,不过没有对农民生活场景的直接描绘。这类文本语言比较抽象,会根据不同的活动和政治态度,系统地组织被报道者的生命历程,并且充满政治性色彩。其中一个文本,就叫《韩凤龄》,是一个典型的翻身叙事。在这篇文章中,韩凤龄必须从封建的过去中解放出来,经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后,养成了模范行为。时间线从过去一直延伸到现在,但并没有实现面向未来的超越。文章的最后一段问道:“要是没有共产党和八路军,老韩怎会有出头的今天?今天也怎会有一个人人拥护的韩凤龄?”[35](PP 289-295)韩凤龄的忠诚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他们是“中国的救星”。这种局限于对党及其在转型中的领导作用的关注,显然影响了作者对新社会的进一步理解。
相比之下,《晋察冀日报》于1943年6月27日刊发的《新型的妇女——韩凤龄》一文[36](PP 613-617),体现了格外强烈的妇女能动色彩,可以称为“妇女主导的变革”。与《韩凤龄》一文相似,《新型的妇女——韩凤龄》读起来也像政治传记,只有最后一部分转为描写韩凤龄和作者当时的互动。这篇文章不是写妇女解放过程,而是写通过解放的妇女,也就是“新型的妇女”的行动促使村庄变革(47)关于韩凤龄的过去,只有从她本人讲话中总结的寥寥几行字,接着是对解放逻辑的直接引述:“可是说妇女解放,要解放,就要做活。”参见《新型的妇女——韩凤龄》,《晋察冀日报》1943年6月27日,载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编:《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第614页。。在这篇文章中,时间导向体现在关键词“变”上。因为没有具体涉及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韩凤龄的变革性角色得到了进一步体现。韩凤龄完全具有能动性以及在家里和村里的道德权威。在家庭生活方面,韩凤龄是积极活跃的,文章甚至都没提她当村长的丈夫的名字。她的丈夫显得悲情而胆怯,容易屈服于不利环境。韩凤龄需要说服她的丈夫到田间工作。在村民方面,韩凤龄影响了她同村的男男女女。她鼓励妇女加入生产,以她的成功为榜样,妇女们一个接一个都加入了田间劳动。村民评论说:“女人变了。”[36](P 614)韩凤龄给整个村子都树立了标准,并在同村的男性身上确立了自己的道德权威,这在她和一群男性干部之间冲突的长段描写中可以看出来。年长的妇女嘱咐她们的儿媳向韩凤龄学习,说道:“孩子!学学老韩吧!不会像咱们那时受罪。”[36](P 615)在经济方面,韩凤龄被描绘成一个有远见的人,她投入并逐步拓展事业,使家里成为中农[36](P 615)。成为劳动英雄,韩凤龄感到开心,并感恩她通过劳动获得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的认可和物质福祉:“还是劳动好,又落名声又过好日子!”[36](P 614)这句引述证实了妇女解放的新逻辑。然而,整篇文章意在刻画基于新型妇女的权威带来的深远的社会变化。文章最后一段解释了我们能从韩凤龄身上学到什么,也体现了韩凤龄的个人特质和精神的未来潜力。韩凤龄和记者们聊起了她来年的计划,包括组织妇女参加工作以及农业生产计划。记者总结道:“从她那刚强的性格可以克服一切困难的毅力和决心、高度的政治热情和积极劳动的精神看来,你会知道时代已为我们国家创造了新型的妇女。”[36](P 617)以韩凤龄为榜样,未来已经存在。
最后要谈的是《晋察冀日报》于1944年2月4日刊登的文章《政府奖给韩凤龄一条黑牛》[37](PP 611-612)。这篇文章回到了通过对初期社会主义社会的详细描述,极其优美地呈现事件及其意义,达到时间和地点的统一这种叙事。此外,这篇文章也是报告文学具有典型农民关怀的又一范例。如标题所示,这篇文章是关于颁奖典礼的,同时描绘了典礼之前的市场情况。通过描写韩凤龄在市场卖煎饼,文章从一个有经济头脑的人的角度介绍了韩凤龄,颁奖典礼则聚焦她社会性的一面。颁奖典礼是政治聚会的一部分,这种聚会包含多种政治议题。最终,在大生产运动的议题下,韩凤龄发表了讲话、接受了奖品。韩凤龄的出现吸引了群众:“无论谁一看到她,就有一种可敬可亲近的感觉。她是一个新型的女性。”而且,“她的话老乡们欢喜听”[37](P 612)。领奖部分的描写非常有趣,因为它直接细致地描写了韩凤龄、牛、韩凤龄和牛的互动以及农民观众的反应。作为稀有珍贵的农业工具以及力量和财富的象征,牛被当成了核心角色,对其描写跟对韩凤龄的描写一样细致。它还是头小牛,但是,正如文章所言:“将来一定是一头肥大的黑牛。”村民好奇韩凤龄将怎样牵牛,有些人甚至跟着她。一个观察者反复说:“好牛!好牛!”一个老头羡慕地说:“老韩要用牛耕地了!”文章以“韩凤龄牵着牛沿着集上的大路走去了”这句话结束了全文[37](P 612)。
文章的最后,政府并不是完全不在场,但是核心人物韩凤龄的行为是自主的,她成为村里每个人包括男性农民的榜样。韩凤龄的奖品——牛具有高度象征性,调和了妇女解放的新逻辑(劳动得到报酬)和典型的农民观(牛作为农业工具和地位象征)。中国的未来孕育在坚强、乐观、具有前瞻性的[37](P 612)“新型妇女”的宣言和承诺以及一头年轻而强壮的公牛的成长潜力中。
六、结论
在本文中,我解读了在延安复杂的形势下对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和韩凤龄的报道,并重点解读了劳动作为社会转型的机制以及当时党的意识形态的双重时间性。一方面,当时的革命理论家称抗战是暂时而紧迫的,需要动员群众解决紧急需求,尤其是提高生产率。从这个角度看,女人和男人都是劳动力,妇女参加生产获得了合法性,并与妇女解放联系在一起。这类文本可能超越对经济活动纯粹量化的解读,但仍然把社会变革看成自上而下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和规范的。另一方面,通过对“建设”的长期关注以及对社会主义初期的理论主张,新民主主义打开了通往未来的时空视野。对于作家而言,出现了一个创作空间,来想象一种和平的、具有社会主义视野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创作中,以报告文学作为体裁、以劳动英雄作为主题、以乌托邦主义作为时间上的方向,共同形成了妇女通过劳动获得解放的新理念,重新确立了她们的能动性,并将她们置于新的社会关系之中。不同于翻身叙事和革命叙事中中国共产党是把妇女从过去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最终执行者,这些故事则“从记忆转化到预言”,这是妇女展示能动性以及发挥其作为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存在的全部潜能的前提。在报告文学中,普通百姓包括妇女进入了历史舞台,有了名字和生平传记,在家庭、邻里、村庄和跨地区政治共同体里被视为社会的正式成员。基于劳动,他们得到了认可,并获得了尊严。“劳动力”和乌托邦式的“新型妇女”两种观念共同塑造了延安妇女劳动英雄的经验。这两种视角的冲突,反映出社会变革过程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无法用单一维度的“解放”或“压迫”叙事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