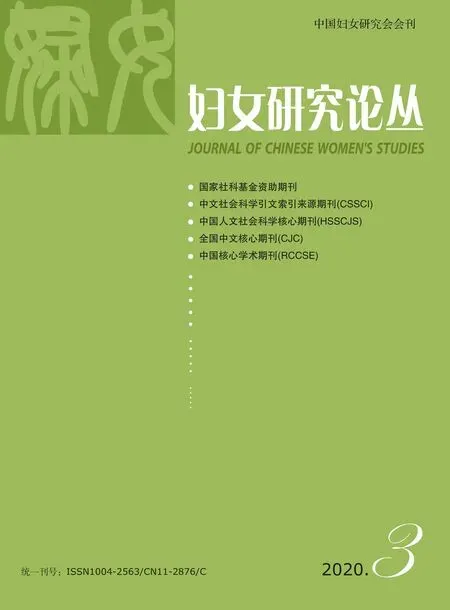明清时期男性关系网络主导下的女性择医
2020-03-22顾玥
顾 玥
(香港大学 中文学院,香港 999077)
象征着文明和礼教的内外空间意识在明末清初得到空前强化,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性别界限。身处内闱的女性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相关的事务时,不得不仰仗于关系亲密的男性家属(如父亲、丈夫),这也成为一种日趋固化的社交模式。在此背景之下,明清社会中女性对于家中男性的依赖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从社会现实的角度出发,女性对于男性亲属的依赖程度并非恒定,而是随社会阶层的不同而变化。与此同时,社会上层的女性病患也通过女科大夫、女医等医疗救治者探寻出游离于男性关系网络之外的就诊渠道。本文选取社会医疗史这一研究棱镜,以女性择医问题作为切入点进行进一步阐释。在研究明清女性就诊生态的过程中,女性病患的择医渠道也被生动地展现出来,女性择医主要是在男性关系网络的主导下进行的。社会上层的女性病患对于这种关系网络的依赖,不仅体现在择医过程中,更展现在问诊时与医者的互动上。女性病患的缄默可以理解为择医问题的延伸。通过对不同阶层女性求医渠道的对比可以发现,她们在求医问诊过程中对于男性关系网络的依赖程度有很大差异,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病患对这种关系网络的依赖相对较弱。
在中国古代女性医疗史研究中,文献资料的匮乏一直是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里的匮乏并非指中医学语境下对于女性身体的认知、妇科医学理论历时性的发展与演变(1)如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在《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中所展现出的古代妇科医学从宋代到明代理论和实践上的转变以及性别隔离对医疗领域的影响。或者是近年来备受重视的女性作为医疗救治者的研究(2)如李贞德的《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妇女与社会》以及吴一立的Transmitted Secrets:The Doctors of the Lower Yanzi Region and Popular Gynecolog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等著作都将女医、稳婆、医婆等女性照顾者作为研究对象。不够,而是指对女性作为被救治者时在患病、诊疗过程中所面临问题的深入探讨不足。在妇女和医疗史的跨领域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受到医学著作写作目的和受众的影响,对于女性病患的记载十分有限。与此同时,她们在诊疗过程中的缄默更是为需要通过“四诊”(望、闻、问、切)而综合判断病情的医者带来了极大不便[1](P 223)。为了诊疗能够顺利进行,男性家属会选择代替患者回答医者的问题。此外,还存在某些更为极端的情况,女性病患全程出现在其男性家属和医者的对话当中。出于种种原因她们并不愿意与医者发生直接的接触,因而其男性亲属不得不将她们的病史、症状以及潜在的发病原因进行转述。
值得强调的是,性别隔离意识的确为医者对女性病患的诊疗带来不小的挑战,这不只是明清时期医者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一个历史颇为悠久的问题。北宋寇宗奭在《草本衍义》中就曾探讨过在对女性病患进行诊疗时面临的困难:“妇人虽有别科,然多有不能尽圣人之法者,今富贵之家,居奥室之中,处帷幔之内,复以帛蒙手臂,既不能行望色之神,又不能殚切脉之巧,四者有二缺焉。”[2](P 17)这段论述强调了被层层幔帐所包围而无法观察患者的病容,以及受帛巾所覆盖而无法准确感知患者的脉象。程茂先在为吴鹭客嫡妻治疗时需要确认病人的面色方可下药,他因此征求了患者丈夫的意见,最终被允许入帐观察。甚至在患者拒绝交流的问题尚未被考虑在内的情况下,医者在为女性病患诊疗的过程中就已面临诸多挑战。
然而,医学著作中所显示出的男性医者与女性病患在沟通和交流过程中存在的客观障碍并不代表女性病患在此类文本中的缺失。自汉代起,医者就开始有意识地将妇科儿科作为重要的分支与其他疾病区分开来,在唐代妇产科已然成为独立的专科。明清时期不少极富盛名的医者如冯兆张、万全、王孟英等都曾撰写过女科著作(3)如明末清初著名医学家冯兆张编写的《冯氏锦囊秘录杂症大小合参》中就包括了《女科精要》。明代医者万全所著的《万氏女科》(又称《万氏妇人科》)记载了妇科常见的90多种病症,对后世的女科治疗影响广泛。清代王孟英对《女科辑要》医书进行了参订,其本人对于女科疾病也有不少独特见解。。当然,这些著作主要在医疗语境下以病因、病理、证候等论述为主,女性患者的形象依然面目模糊。然而医案却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它生动地呈现出女性患者的个体差异。医案作为中国古代医者对于患者病例、辨症、治疗、预后连续性的记录,是记述中医诊疗活动的载体。虽然,医案在撰写过程中受到医者个人风格的影响,形式多样,侧重也不尽相同,但其中的一些医案不仅重点阐发病因病理和治疗方法,更注重对患者本身的叙述——此类医案中强调了患者身份、背景、患病缘由和过程,甚至涵盖了医患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没有局限于医者和患者之间,还包括医者与病患家属乃至患者与其家属之间针对疾病的讨论。从明代开始,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个人医案专著大量增加,万历年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医案类书《名医类案》。清代更是医案发展的鼎盛时期,不同风格和形式的医案在这一时期井喷式地出现,成为研究前人医学理论、传递自身医学心得的重要文本。
医者并不排斥对于女性病患诊疗经历的记载,事实上,许多医者花在女性患者上的笔墨并不比男性患者少,在《洄溪医案》《程吉轩医案》《遯园医案》等书目中均有对于女性患者的记载。如在孙一奎所著的《医案》第1卷所记载的57件病案中,涉及女性病患的案例有27件,几乎达到一半,且年龄跨度从十几岁到八十几岁不等,身份地位也很悬殊,从官宦内眷、仆妇到妓女均有记载。在《程茂先医案》第1卷的22件病案中,为女性病人问诊的有8例,关于女性的记载有1例。因而,明清医案可以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一时期女性的就诊生态(4)当然,同一时期的笔记小说和世情小说也能反映女性的疾病历程,如《客座赘语》《里乘》《留青日札》中均有妇女特别是社会下层女性身患奇症被治愈的记载。其中不少与胎产相关,如在“人生夜叉”“产怪”等故事中,救治者从男性医者转换成了女医、稳婆、方士等社会下层更容易接触到的求助对象。与此同时,这些故事也多少会带有巫系色彩。。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病案中的很大一部分为直接问诊。不可否认的是,患者家属转述的情况时有存在,但是从医案中相对完整的情形来看,转述行为并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一种受到礼教意识影响而形成的强制性问诊模式。其中一些病患在性别隔离意识的影响下选择在就诊过程中沉默,另一些来自不同年龄、拥有不同社会身份的女性则选择对于自己的疾病和身体状况进行表达,这在一些医者的论述和实践中均有体现。相较于男性家属的转述,女性病患在与医者直接交流其病况的过程中,更侧重于自身感受、病程演化以及生活处境的叙述。
一、社会中上层女性的择医
虽然明清时期医案的风格各不相同,但倾向于记载患者年龄、身份、患病历程的叙述型医案对于患者背景资料的记录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对于男性病患身份的描述方式有很多:官职、亲缘关系、社交网络乃至与医者的直接联系都有可能作为身份介绍出现在医案中。相比之下,对于女性患者身份的说明就简单得多,她们毫无意外地被置于家庭网络当中,其中一些典型的叙述如“大司马潘印川第三令子室,尚书蒋公孙女”[3](P 624),“李君思澄之姪女懿娟”[4](P 1),“宁波石碶周子章先生室人吴氏”[4](P 20)。在中国古代对于性别的传统认知中,女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以家庭亲属的角色被人们认知的[6](P 6),因而这些医案中的表述并不能表明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这只是以父系家族制为主导的男性关系网络下,通过叙述女性病患的家庭身份来表明其社会身份的方式。
当然,在探讨中国古代女性的生命历程时,将其笼统地视作一个整体而忽略其客观存在的阶层差异,会让她们所呈现出的形象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在明清时期女性择医及其诊疗生态这一问题上也毫不例外。她们所处的阶层会为她们提供截然不同的医疗资源,这在医疗资源整体匮乏的年代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女性的择医乃至就诊过程。阶层的差异不仅直接导致女性病患天差地别的结局,更使得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男性关系网络呈现出控制力的差异。故此,在讨论女性病患求医渠道的时候,我们简单将其分为中上阶层和社会下层的女性,而妓女将被作为游离于“家庭关系”之外的特殊群体单独讨论。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谓的中上阶层不仅包括贵族、学者、官员家中的女眷,有时也包括商人和富庶之家的家眷。需要说明的是,因宫廷内部的诊疗秉承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故明清时期统治者的女性亲属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在中上阶层女性患病寻求救治的过程中,男性之间的交往和社会联结显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当女性患者身染难以医治的重症或久病不愈需要医术高明的大夫来挽救生命的时候。这些男性关系网络主要可分为以医者为核心和以病患为核心两种。
在以男性医者为核心的关系网络中,他们个人的生活和旅行经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可能接触到的病患范围。医者可能会受宗族、好友、同行的儒医以及借宿家庭所托,为他们身患疾病久治不愈的女眷进行诊疗。这是一种以医者为中心发散的网络,其中或许会出现多重的人际关系转换,但无一例外都在男性的社交圈中进行。如在“张思轩妇人心痺”一案中,进贤三尹张思轩公家的施夫人出现了心痺的症状,请了城中的医生来看诊,病情却并没有好转,甚至出现了五天都无法进食的情况,全家人手足无措。所幸,潘少保印川公与张思轩是连襟关系。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著名的中医学家孙一奎与潘家的公子交好,因而到潘家做客拜访。潘公子转述了施夫人的病情,恳请孙一奎前去问诊,最终施夫人在孙一奎的救治下得以痊愈[3](P 585)。类似的交际网络在《王孟英医案》中也有涉及:
高鲁川三令爱,为外科姚仰余令郎杏村之室,年三十五岁,自去年仲夏患痢……杏村之僚婿蒋礼园、黄上水交荐孟英图之[7](P 379)。
在这一案例中,作者先是明确了患者姚高氏的母族,同时指出其家翁与自己一样拥有医者的身份。后提到姚高氏久病不愈,到了时年冬天每况愈下,家中甚至已经开始准备棺椁,其丈夫姚杏村的两位连襟向他推荐了王孟英,并做最后的尝试。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男性为家中女眷寻找更好的医疗资源的过程中,其家庭身份和社会身份在非常频繁地进行转换。
另外,亲友家的医生以及一众病患纽带也是男性关系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以病患为核心向外发散的择医渠道。医者高超的技术成为患者之间传递的重要信息,并最终被寻求救治的家庭获知。在“温巽桥子妇滞下”一案中,医者曾为温巽桥子妇、吴车驾涌澜公长女治疗发热恶心、小腹胀痛等病症。从医案的表述中可知,作为全科大夫的孙一奎并未在施夫人发病的第一时间被请至家中诊治,事实上,温巽桥是在专科大夫治疗30余日无效且主动请辞的情况下找到了孙一奎,最终保住了其长媳的性命[3](P 601)。不久以后,温巽桥的二儿媳产后出现胁胀痛的症状,不同于前一次的大费周折,温家人直接找到了孙一奎为之诊治[3](P 602)。病患之间的口耳相传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想要理解男性关系网络在择医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就不得不明确中国古代性别意识中“内”与“外”的区分。这并非是要强调“男外女内”这种静态且森严的社会结构导致女性患者由于无法接触到医者所处的公共空间,故而不得不依赖男性亲属以及他们的社交网络。在儒家文化的引导下,“内”与“外”的概念除了空间意识,更象征着文明化和礼仪化[6](P 83)。在此背景下,性别隔离意识逐渐发展为有助于维系稳定的社会体制的象征。对于社会上层而言,不让内闱的女性进入她们并不熟悉的“外部”领域,也体现了家族礼教的完备。在维系制度稳定的前提下,为迫切需要救治的家人寻找医疗资源的工作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常年游走于外部空间的男性身上。这也解释了身处于中上阶层的女性病患在择医过程中对于男性关系网络的依赖。女性自身的人际关系网络除了家人外多以女性为主,这样的社交网络使她们很难接触到身为男性的医者。更重要的是,一些医者与内宅女眷之间有违人伦的想象使得医患双方在一定程度上会尽可能地避免直接接触,如清代著名医学家冯兆张在“良医格言”中指出:“凡诊视妇女,及孀妇、尼姑,必俟侍者在旁,然后入房观看,既可杜绝自己邪念,复可明白外人嫌疑,习久成自然,品性永勿坏矣。”[8](P 13)因此,女性病患择医特别是聘请名医会愈发困难。
以翻转课堂为基础的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不仅能够在第一时间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能够更好的突破应试教育的桎梏,英语老师需要结合翻译教学的现实条件,积极地将翻转课堂与现有的英语教学活动相结合,不断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
当然,社会上层的女性在择医过程中也摸索到一些脱离男性关系网络主导的可能。家族中的女性亲属对于病患的治疗非常有主见,她们热衷于将偏方、巫术引入治疗过程。我们无法否认此类行为在明清时期的内闱之中确有存在,虽然与稳婆、药婆、师婆的频繁接触是被明令禁止的,但是在一些医者看来,已然脱离传统医学范畴的偏方,对女性患者却有着特殊的吸引力。此外,一些女科大夫的良好名声也在女眷之间迅速传播,他们在获得女性病患信任的同时,也取得了跨越闺门诊治的机会。这种病患之间的信任纽带一旦建立便很难被打破,特别是对于选择余地本就不大的女性病患而言更是如此。全科医生在医案中不乏对女科、专科医生的抨击,认为后者学艺不精。而令事态更为复杂的是,由于平日频繁的接触,内宅中的女眷往往更加信赖专科医生的说辞。一位医者在为后溪大兄孺人戴氏诊疗血痢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困境:
适后溪兄在浙,侄女辈素信医博黄氏为女科专门,延而治之……侄孙尔嘉持药见予曰:“家姑酷信黄医为专门,今已任事五日,较前精神大瘁,叔翁为祖父至交,宁无一语启愚乎?”子曰∶“吾非不言,欲诋黄,恐为妒妇之口,今子来,予可诊之。”[3](PP 711-712)
家中女眷对于这位黄氏女科专门可谓信任有加,从不允许他人诋毁中可见一斑。后来医者不得不与病人的男性家属一同蒙骗,在其他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让患者停止使用黄氏所开之药,并由医者开药调理,最终才使病人转危为安。与此同时,明代盛行的女医似乎也从某种程度上将女性择医从对男性社交网络的依赖中解救了出来。从谭允贤《女医杂言》中与患者的交流几乎看不到男性亲属的影子,他们仅存在于诊疗的对话当中。女性病患主导着这场求医,甚至一些幸运的病人可以在出游的客船上与女医攀谈并得到治疗[9]——这是向男性医者求医问诊时无法想象的。但是,无论是稳婆、医婆、女科大夫抑或是女医,他们在主流医学界、名医的著作中往往备受医疗和道德层面的驳斥。这也可以看作男性主导的择医制度对于女性试图游离于其关系网之外的回应。
二、中上层女性病患的缄默
女性病患在诊疗过程中的缄默问题在既往研究中时常被提及。女性在被问诊过程中的沉默为医者的诊断带来极大的阻碍[1](P 251),尤其是一些女性病患由于性别隔离意识而导致的沉默寡言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医者获取信息。有研究指出,明代医者为女性病患看诊时不仅需要其家属的陪同和准许,更有通过“往来之人言语传说”来了解病人症状的极端情况[10](P 25)。由此,女性病患在这一过程中似乎成为被排除在中心话语权之外的他者。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从明清时期的医案中可以看出,女性病患的缄默确有存在,一些女性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全权由家中男性代为回答医者的问题,如在“张氏妇心神不足肺经有痰”医案中便是这种典型的对答形式,医者在诊完张氏脉之后,直接转而向其丈夫询问病史和病因:
诊毕问予曰:“脉何如?”予曰:“心神脾志皆大不足,肺经有痰。”夫曰:“不然,乃有身也。”予曰:“左寸短弱如此,安得有孕?”夫曰:“已七十日矣。”予俯思久之,问渠曰:“曾经孕育否?”夫曰:“已经二次,今乃三也。”予问:“二产皆足月否?男耶女也?”夫曰:“实不敢讳,始产仅九个月,手足面目完全,而水火不分,脔肉一片,生下亦无啼声,抱起已身冷矣。”[3](P 626)
还有一种情形是由男性亲属拜访医者并转述女性病患的症状,医者甚至无法对病患进行切脉、观色或者听闻其气息,他们做出专业判断的依据主要是男性亲属的描述。这样的求医过程看似草率,却是一种相对成熟的就诊模式。这种就诊模式往往伴随着女性病患难以启齿的隐疾。中国古代女性本就不擅长对于自己的身体进行客观地认知和表达,面对陌生的男性医者,她们对于自身症状特别是私密部位病症的描述更加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女性病患会寻求女性亲友的建议和帮助,而此时年长及富有经验的女性亲友会将自己的患病经历与之分享。流传于内闱之间的偏方便是在这种情形下传递的。当然,一些女性亲友也会将自己相熟的专科(女科)医生介绍给向其求助的女性病患。女性亲友的经验和陪伴会令患者更容易接受专科医生的治疗,同时也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隐疾带来的窘迫。另一些女性病患则会和她们的丈夫商议。她们在陈述了自身病症以后便退出求医的过程。她们不愿意向大夫亲口叙述自身的隐疾。这种私密而又敏感的疾病甚至导致其不愿意与陌生的男性大夫面对面探讨病症。求诊的工作便全部落到了与女性病患最亲密的男性——她们的丈夫身上。譬如一位吴氏妇人的丈夫多番拜访医者寻求救治,即便身为男性,其对于隐疾也是态度扭捏,难以启齿:
一吴氏妇,有隐疾,其夫访于予,三造门而三不言,忸怩而去。后又至,未言而面先赭。予因诘之曰:“诸来诣余者,皆谓予能为人决疑疗急也。今子来者四,必有疑于中,疑而不露一语,虽百来而疑终不可决,疾终不可去矣……山妇子户中突生一物,初长可三寸,今则五寸许矣。”[3](PP 639-640)
另一则案例是马迪庵公之子马凤林内子的隐疾。医者先前治愈了马迪庵公内伤腹胀、大小便不利的病症,其子见状便将其夫人的症状转述于医者:“乘间语曰,内子包有隐疾,每月洵行,子户傍辍,生一肿毒,胀而不痛……外科历治不效,且致不孕。”[3](P 587)有趣的是,医者对于这样的诊疗模式似乎并不排斥,对于无法见到患者本人、无法切脉的情况也没有在医案中表现出过多的不满。在能够通过转述症状治疗病症的前提下,他们并不会要求面见患者。这也是对于女性病患的一种体谅。口述病症的求医模式在明清时期的医疗实践中并不少见,而在医案当中则表现为女性病患的缄默。
一些女性病患面对陌生男性自我表达的能力欠缺,且不擅长应对象征着“私密”的内在领域被他人入侵的情形,从而选择让男性亲友代劳。她们并没有被要求沉默以展现出其良好的修养以及高贵的品性,说明这并非一种行为规范。清代医者程杏轩在其医案中曾记录过一段应邀为菶翁儿媳诊治的经历:
菶翁邀视媳病,云日前因热贪凉,起初头痛呕恶,旋即怯风发热。至今热犹未退,似属外感,烦为解散,免致成疟。导予入室。诊际问其头痛乎,病者不答。转令使女询之,亦复默然。予曰:“殆证也。”辞不治[12](P 17)。
在诊治之初,医者虽然已经通过菶翁了解了病因和发病过程,但是在进一步诊疗的过程中,医者依然试图与患者(菶翁的儿媳)进行直接的交流,并询问其是否头痛。由其自然的语气可见,在日常为女性诊疗的过程中,直接的对话和问诊是被允许且不会被视作冒犯的。然而,在患者未做回答后,他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患者或许是主观地不愿意与其直接对答,因而让侍女再次转述。女性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拒绝直接回答问题的情况,对于经验丰富的医者而言偶有发生,他非常清楚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原由,从“转令使女询之”的行为中可以看出其对女性患者的谅解和尊重。事实上,在是否与男性医者进行直接对答的问题上,女性病患自身意愿似乎比人们想象中的更加重要,而社会对于女性患者与男性医者直接交流的行为也比人们想象中的更加宽容。
当然,缄默绝不是女性病患诊疗生态中的唯一姿态,我们也应当注意同一时期勇于对自己的身体和病症进行表达的女性病患。事实上,从数量来看她们并不在少数,且覆盖的年龄和阶层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一些不畏惧甚至擅于自我表达的女性在医案中占有一席之地。如在为方绣文的夫人治疗吐清水的病症时,作为方绣文好友的医者在了解表征以后,向病人询问强行咽下清水后的感受:
语其妇曰:“古有咽华池真水之法,咽之不吐何如。”妇曰:“若强咽下,即愦愦欲呕。”诊手少阴脉微动,问经事两月未行,告绣兄曰:“脉象似属妊娠,不卜昔年怀孕有此证否。”曰:“拙荆往年受孕,原有吐证,但所吐者食耳,此番证绝不类。”[11](P 22)
患者的回答流畅,相较于男性家属对于病况的叙述,她的回答更侧重于对自身感知的表达,包括生病的体验、身体的感觉和内心的想法。医者在与患者及其丈夫对话转换的过程中并未遇到太多阻碍。事实上,女性病患对于自身病症的阐发在医案当中并不少见。她们所用的语言因其身份、年龄的不同也各有特点,这些特征被医者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如医者在为胡某的儿媳诊治外感之症时,她的语气直爽且大胆,并无半点扭捏,患者的门第、性格在这样的对话中真实地展现了出来:
予曰:“冷水即是妙药,饮之无伤。”盖欲观其饮水多寡,察其热势之轻重耳。其姑取水至,虽闻予言,心尚犹豫,勉倾半盅与饮。妇恚曰:“何少乃尔。”予令尽碗与之,一饮而罄。问曰:“饮此何如。”妇曰:“其甘如饴,心地顿快,吾日来原欲饮水,奈诸人坚禁不与,致焦烦如此。”予曰:“毋忧,今令与汝饮,但勿纵耳。”[11](P 40)
明清时期处于社会上层的女性,在求医过程中对于家中男性亲属及其所拥有的关系网络的依赖进一步延展到了诊疗的过程中。其中一部分女性由于长期安于内宅,对于与陌生男性医者的交流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因而选择由男性家属代为回答医者问题甚至口述病症的诊疗模式,在医案中表现为病患的缄默。事实上,无论女性病患是否作答,以及如何对自己的病情和身体进行阐发及描述,只要不以打破内外秩序和规则为出发点,就不会受到过于严厉的抨击。在此背景下,一些女性病患与医者充满个人特性的对话在医案中被清晰地记录下来。
三、社会下层女性病患的求医渠道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女性所面对的诊疗生态与社会上层女性大不相同。通过对比女性择医过程和结果的差异可以发现,相较于中上阶层的女性病患,社会下层的女性在求医时对于男性关系网络的依赖相对较弱,她们身上表现出中上阶层女性病患没有的主动性。与此同时,中上阶层女性固守的内外界限在社会下层产生了明显的松动。社会下层女性可能是农民之妻、家仆或劳动妇女。在许多明清时期著名医者的医案中详细记载了他们为当时的达官显贵诊疗的过程,当然并不是说社会下层的平民百姓完全没有被声名显赫的医者救治的机会,只是医案中这样的案例并不多。与此同时,医者似乎并不重视平民百姓的身份背景,她们往往会被一个姓氏或者其丈夫所从事的职业一笔带过。在这种背景下,僧人、尼姑和游医道士成为女性患者主要的求助对象。他们在民间想象中被赋予一种“拥有可以治愈神秘疾病的偏方”的形象,如《一得集》中曾提道:“静修庵一老尼,年五十许。患腹痛,自作痧治。”[5](P 30)他们通晓一定的医理,能够对自己乃至身边的病患进行简单的治疗,无疑是无法享受充沛医疗资源的平民阶层优先选择的求助对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下层的女性尤其欢迎民间救治者如稳婆、药婆、巫医道士、僧人老尼的偏方。
更重要的是,民间救治者的药方多为便宜且容易寻到的药材,在这一阶层的经济承受能力范围内。孙一奎曾在医案中记载一仆妇难产需要喝上两斤共计一百帖的人参进行治疗的案例,然而其丈夫的回答则展现出了这一阶层真实的困境:“彼家朝佣暮食,无隔宿之储,甑生蛛网者半越月矣,安有人参二斤可服也,惟命是俟耳。”[3](P 725)医者虽然最后用锻石和芹菜等制作了廉价的代替方,但还是可以看出,对于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而言,即便延请医者诊治,昂贵的药材依然会令他们望而却步。事实上,在不少名医所著的医案中确有提及,部分女性患者求助于真正意义上的医者之前大都有被僧人、尼姑救治或者自医自救的经历。“翁嘉顺室,娩后发热,竹林寺僧治之不应,温、龚二医皆主生化汤加减,病益剧,请孟英诊之。”[7](P 290)他们所开的药方更接近偏方,不会超出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因而备受欢迎。然而当这些偏方治疗无效时,很多患者只能面临死亡。秀水董君枯匏夫人求医不得的病案就真实地反映了女性在医疗资源缺失的情况下的反应和心态:
至冬令证类三疟,余以病未能往视。来信云:“桐乡传一妙方,治三疟效验如神……”余即函复云:“此乃劫剂,仅可以治寒湿饮邪为患之实证,设虚证、热证,服之虽愈,必有后患。”[12](PP 451-452)
在医者因为生病而缺席的情况下,秀水董君枯匏夫人的疾病无人可治,她不得不转而依赖当地坊间流传的药方,但医者指出这一药方并非针对个体差异而开,甚至会对病人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秀水董君枯匏夫人的幸运之处在于,她与医者存在书信往来,因而得以及时规避偏方带来的负面作用,然而对于与名医并无交集的社会下层女性而言,偏方是她们可及的医疗资源,其中的很多人对偏方深信不疑,也因此而丧命。社会下层女性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是,寻求名医看病诊治很多时候只能依赖于偶遇:
去予舍二里许,地名曰前坑口。一妇人清明前十日发热、头痛……适予扫祖墓而近其家。其子闻之,即告急于予,恳为一诊[3](PP 716-717)。
与现代社会的医疗体系不同,中国古代的名医有时会四处游历,其至交或亲朋可能知道其去向,如遇难解的病症可以通过信件向其请教,但是对于与医者毫无关系的平民百姓或是慕名求医者而言,他们的就诊则多凭运气。当然对于社会下层的女性而言,择医过程也并非全然负面,她们不必受到男性关系网络的限制,邻人、好友都可以直接成为她们寻医看病的重要资源。《一得集》中曾记录了一位居住在定海东山的妇人,通过其邻人寻得此医者,并在罹患血痢时向其寻求救治的案例:“定海东山甲下某妪,前翁姓之邻居也。年四十余岁,患血痢日数十行,里急后重。腹如绞痛,粒米不入者十余日矣。身大热,口大渴,症在垂危,呻吟欲绝。余因治翁姓子之症,乘便邀余诊脉。”[5](P 29)
明清时期不同阶层女性的求医案例显示,患者社会地位决定其对于男性关系网络依赖程度,地位越低,这种依赖关系相对越弱。中国古代男外女内的性别隔离意识在社会下层出现了松动和弱化,因为仅凭家中男性在外的劳作并不能维持基本生活需求。放在社会医疗史的棱镜下,在面对本就匮乏的医疗资源时,家庭中的所有成员包括妇女本身,不得不动用所有潜在的人际关系,以寻求被诊治的机会。此时,性别隔离意识与传统的礼教观念不再作为优先级考量因素。
最后单独讨论的妓女这一群体,虽也处于社会下层,但是其特殊的社会圈子使其求医特征具有多元性。从其择医行为可以看出,她们对于男性关系网络的依赖并不比中上阶层的女性弱。妓女看似脱离了内外空间的限制,但是当需要寻求更好的医疗资源时,求助于男性社交网络是她们最有可能获得有效救治的择医渠道。一位医者曾详细地描述他为一位李姓妓女诊疗的过程:
壬申秋仲,予东游檇李,而王松泉吴小峰偕行,小峰语予,中秋至矣,此间一妓李姓者,行第七,殊可人意,须访之。晚令佐酒至,则见其态度果澹雅风致,坐少顷,连咳两声,小峰究其病曰,偶耳。小峰谓毋诳,孙公知人生死,不啻扁鹊,可求一诊[3](PP 593-594)。
得益于恩客吴小峰是医者的好友,这位李姓妓女才有获得被名医诊疗的机会。与此相似,这位医者还记录了为一位金姓老妓的嫂嫂辗转看病的经过:“有老妓金姓者,其嫂三月患头痛……予适吴江归,便道过檇李,访南溪吉泉二兄,吉泉兄以是症见询,且言诸医有以补中益气汤进者。”[3](P 594)无独有偶,明代著名医学家也曾有过深夜被友人带去医治妓女的经历:
予向同数友游寓榆关,客邸内一友,素耽风月,忽于仲冬一日,谯鼓初闻,其友急叩予户,启而问之,则张皇求救。云:“所狎之妓,忽得急证,势在垂危,倘遭其厄,祸不可解。”予随往视之[13](P 1305)。
这种妓女与恩客的关系成为两性各自封闭的社交网络中一个特殊的突破口,使得社会下层的妓女获得被名医救治的机会。当然,并非所有妓女都能够通过其恩客获得医疗资源。绝大多数时候,她们都和其他社会下层的女性一样,不得不仰仗流传于坊间的偏方或巫医僧人,如一位患杨梅结毒30多年的妓女,服用道人的偏方女贞条后,毒疮得以愈合,颜色也有所转淡。
四、结语
明清时期女性患者的诊疗生态可以展现出这一时期性别意识对女性社会生活的现实影响。从社会医疗史的角度看,在女性病患择医过程中,不同阶层女性病患对于男性关系网络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受到内外空间意识的影响,以医者和患者为核心的男性关系网络在中上阶层女性择医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这些女性病患在求医过程中对于家中男性亲属及其所拥有关系网络的依赖进一步延展到了诊疗过程,其所展现出的是部分久居于私人空间的女性患者的自我约束,以及她们对于与陌生男性医者交流的恐惧。问诊过程中女性患者的缄默大都源于自身的礼教意识及其相对较弱的社交能力。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明清时期一些女性病患寻找到了游离于男性关系网络之外的求诊模式。稳婆、药婆、女科大夫以及女医的存在为女性病患越过男性权力获得直接诊治提供了可能。作为对于这种尝试的回应,在主流医学界和名医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于三姑六婆、女科专科大夫以及女医从医疗技术层面到道德层面的驳斥。
中国古代两性关系中所呈现出的依附性和依赖性在社会实践中并未渗透至各个阶层。从不同阶层女性求医渠道的对比可以看出,相较于中上阶层的女性病患,社会下层的女性在求医时对于男性关系网络的依赖性相对较弱。明清时期医疗资源的匮乏使得社会下层的女性不得不走出私人的家庭内部空间,寻求一切被医治的可能。这一时期的妓女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虽然属于社会下层,但在一些案例中展现出对于男性的深度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