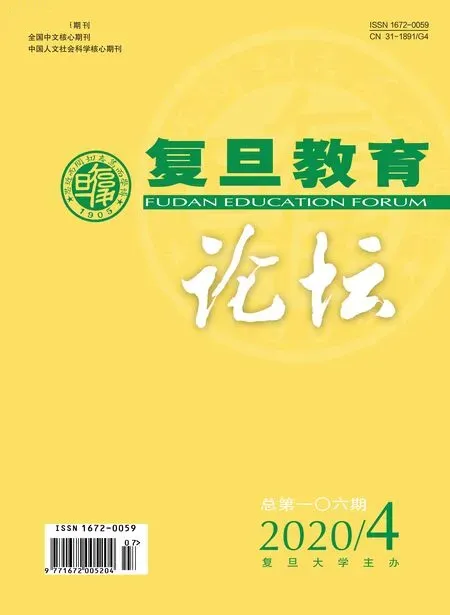程序与实体之间:美国公立大学录取纠纷司法审查标准研究
2020-03-22王俊
王 俊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北京100089)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高等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依学界通说,公立大学录取行为的权力来源表明其具有明显的行政权力特征,为充分保护学生受教育权,应将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1]那么,在司法实务中,法院介入公立大学录取纠纷的程度与边界为何?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中,以“招生录取”为全文检索关键词,检索2009年以来我国各级法院做出的行政诉讼裁判文书。经过筛选无关数据和合并重复数据,统计发现:过去十年来,在本科和研究生录取中因质疑公立大学不予录取决定,学生共计提起14起行政诉讼案件(含共同被告)。依据新《行政诉讼法》,法院总体上认为公立大学依据法律授权行使录取行为,应当接受外部监督,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少数案件中,一审法院认为学生录取属于办学自主权范畴,不是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行为,拒绝将其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二审法院及时予以纠正并发回重审(如“周卓然诉暨南大学案”①)。不过,仍有3 起案件的审理法院以诉讼请求为由,认为此类纠纷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如“王玉红诉新疆大学案”②)。
在其余11起案件中,法院对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表示尊重,重点审查录取行为的程序正当性。即使学校在录取程序中出现了工作不严谨、管理失序的问题,法院亦认为未对原告的权利造成实际影响(如“项骏诉武汉大学案”③)。程序审查对于从法律角度解释招生章程及简章的条款内涵与操作规则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本科录取纠纷案件中尤为明显,如“苏骏伟诉西南财经大学案”④中的志愿录取顺序规则和“刘沁诉中央美术学院案”⑤中的高考综合成绩评分规则。即使是在研究生录取纠纷案件中,程序审查亦能厘清纠纷焦点背后的规则适用,如“吕晓春诉北京师范大学案”⑥中不同类别复试考生的录取先后规则和“辛晶诉上海海事大学案”⑦中大学生士兵的资格标准。但是,在“肖虹诉中国科学院大学案”⑧中,原告质疑面试官恶意评分、以行政干预方式压低其复试成绩。法院认为,面试评分行为属于学术评判范畴,而原告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未予采纳支持。在这一案件中,原告认为复试环节中具有程序资格和行为能力的面试官未能正当合理地行使学术评判中的自由裁量权,而判决论理却苛以原告难以承担的举证责任。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认为司法机关不应对学校办学自主权范畴内的行为进行实体审查,应保持尊重谦抑。然而,随着录取纠纷越来越多地被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程序审查为边界的司法审查能否真正救济权利受到侵害的学生,司法审查是否应当进一步介入程序与实体之间的缝隙?
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法院在公立大学录取纠纷司法审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与我国相似,美国法院传统上尊重大学自治,避免对大学造成过度的司法监督。[2]即使依诉讼请求介入大学内部事务,法院也表现出谨慎与克制的态度,在相关司法审查中亦形成了“学术遵从”(academic deference)的理念和原则。美国高等教育在二战后走出精英教育的传统轨迹,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急剧提升,经济变革与政治运动也让个人对自由和财产的权利意识日渐增强。法院不得不受理越来越多以录取纠纷为由的诉讼案件,其中多以公立大学为被告。作为“州行为人”(state actor),公立大学受到联邦和州法律的规制。尽管学校以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作为排斥审查的辩护理由,但法院的立场并非一概而论,而是以行政法和宪法条款为基础,逐步构造了宽严相济的司法审查标准。本研究通过典型判例对其分别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在这一问题上对我国有所借鉴。
二、基于行政法的审查标准:解决录取评价中的程序纠纷
在美国,学生录取属于大学自治范畴,政府管控相对较弱,但公立大学因接受州政府资助而与之形成共生关系,在行使公权力实施录取政策时也被视为“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州政府机构”[3]。学校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并做出是否录取的决定,亦是在学术自由范畴内行使学术评判的裁量权。因此,当学生对录取结果提出质疑时,法院首先会考虑采用《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第706 节所规定的“任意和不正规”(arbitrary and capricious)标准予以审视,判断学校是否滥用自由裁量权。在法理上,自由裁量权应当依据具体情况明辨是非、辨别真伪,符合理智与正义,以最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4]509但是,“任意和不正规”是一项高度宽松的审查标准。[5]除非学校的录取决定没有任何合理的基础,超出了一个理性人对事实看法的不同,或者任何理性人都不会做出这样的评判,法院才会推翻录取结果。一般而言,法院在适用这一标准时会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否存在主客观评价标准之间的冲突
在审查学校以何种程序和标准做出录取决定时,法院一般出于遵从而推定学校在选拔合格学生时会秉持“善意”(good faith)。联邦上诉法院在1975 年审理“加斯帕案”⑨时曾指出,学校依据标准评价学生并确定其是否具备入学资格时,行使“准司法”(quasijudicial)职责。只要秉持善意且非任意,其在职责范围之内做出的决定应是结论性的。学校在录取程序中普遍同时采用主客观标准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但仍有学生质疑主观评价会导致滥用裁量权。如果主观评价中未见不当动机与目的,并且和客观评价标准之间没有冲突,那么法院一般支持学校的决定。在同年的“威尔逊案”⑩中,原告称亚利桑那大学艺术学院在评价申请人的艺术作品时,完全依据教师委员会成员的主观标准与评判做出决定,未使用任何“标准清单”(check list)或书面标准。州上诉法院表示,不能因为没有标准清单就判定录取结果是任意、不正规或者不合理的。在1976 年的“格罗夫案”⑪中,原告称俄亥俄州立大学兽医学院在录取程序中使用面试打分评价,存在任意和不正规的主观因素。联邦地区法院对于面试分数在录取决定中的权重问题表示遵从,并认为学院在引入主观评价因素时,已经为原告提供了充分的正当程序保障。
(二)是否合理考虑与学业表现相关的因素
公立大学依据入学要求对标学生学业表现并对其进行评价,应当合理考虑与学业表现相关的因素,否则会被质疑是任意和不正规的。在1963年的“莱塞案”⑫中,布鲁克林学院依据州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要求,在录取政策中执行两项与学业表现相关的标准——申请人在高中阶段完成固定数量课程单元并且平均成绩达到最低要求。原告的平均成绩略低于录取分数线,但是在高中阶段参加了课程内容更丰富、学业要求更高的特殊类课程,因此质疑学院未考虑课程难度。州初审法院判决支持原告,认为布鲁克林学院忽视特殊类课程的特征、质量以及学生入选该类课程的竞争程度等因素,而且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辩护理由。而州上诉法院推翻了该判决,认为学校依据授权在事务管理过程中行使自由裁量权,除非有证据表明在司法审查之下没有行使该裁量权的余地,否则法院不应干涉。州上诉法院同时也指出,除非能够证明学校明显地滥用法定权力、存在歧视行为或严重错误,否则法院应当克制,避免在评判学生是否符合入学资格这样微妙精细的问题上强加司法见解。
(三)是否遵循过往录取先例或事前承诺
在行政程序上,遵循先例或承诺是指对于相同的问题必须做出相同的处理。公立大学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应当遵循其事先公布的录取标准,尊重录取结果。在1971 年的“巴利特案”⑬中,蒙大拿大学法学院的录取委员会告知原告,获得录取的前提是完成一门财务会计课程。原告如约完成该课程,但成绩仅为“可接受”,之后法学院以成绩未达到“满意”为理由拒绝录取。州最高法院表示,学院未曾公开两项标准之间存在技术性区分,确属滥用自由裁量权。在1975 年的“伊登案”⑭中,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计划成立足病医学院并录取了15名学生,后因州政府财政压力暂停了新学院的开学计划。州上诉法院称,学校的确能以缓和财政危机、维护公共利益作为该决定的辩护理由。而经查明事实后发现,暂停开学计划会导致学校损失数量庞大的联邦经费和学费资金,而且学校仍需支付新学院已招聘教师的薪酬,所以即使暂停开学也不会减少经费支出。法院据此判决学校的决定是任意和不正规的,并要求学校如期接受学生入学。
三、基于宪法的审查标准:解决录取评价中的分类纠纷
一般而言,美国公立大学除学业成绩和测试分数外,在录取程序中会综合评价学生的多方面因素。有的因素不直接反映学业表现,但与综合素质关系密切,如志愿服务、课外活动等。有的因素看似无关,但学校认为从办学定位和教育目标的角度应当予以考虑,如种族、性别、身心障碍、居住地和家庭背景等。一旦在录取评价中引入这些因素,学生很可能质疑此举背离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违反联邦宪法“平等保护条款”。特别是当未被录取的学生发现学校最终录取了分数更低的学生时,往往会引发涉嫌歧视对待的诉讼。对此,法院会基于宪法条款启动司法审查,但会根据案情适用宽严相济的三级审查标准。
(一)在录取评价中考虑身心障碍因素:适用合理审查标准
合理审查标准是指,只要立法或行政行为与“正当的”(legitimate)政府目的“合理相关”(rationally related),法院即予以支持。[6]565该标准在司法审查强度上近似于前述“任意和不正规”标准,除非原告能够证明引发纠纷的行为并非服务于任何可以想象的正当目的,或者其并非实现该正当目的的合理方式,法院一般会做出“极大的司法遵从”。[7]联邦法律明确保护身心障碍学生的受教育权,1973 年《康复法》(Rehabilitation Act)第504 节规定,“具有身心障碍但其他方面符合资格的个人”在接受联邦资助的项目中不得受到歧视对待。在1979 年的“戴维斯案”⑮中,原告有严重的听力障碍,她在申请北卡罗来纳州东南社区学院的护理专业时被拒绝,原因是学校认为这一障碍会导致她无法安全地参加常规临床实习及照顾病人。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中并未明确审查标准,但在解释第504节条款时对学校的评判表示了遵从。法院认为,“其他方面符合资格”是指尽管有身心障碍但是仍然能够满足课程计划的所有要求,因此并不要求学校为了录取身心障碍学生而降低标准或者对标准进行实质性修改。这说明,当学校以特定专业的学业要求评判身心障碍学生是否具备入学资格时,法院应尊重评判结果。不过,在后续两个案件中,联邦上诉法院却在审查标准中出现了分歧。
在1981 年的“普什金案”⑯中,科罗拉多大学一名依靠轮椅活动的医学博士在申请附属医院精神科住院医师项目时被拒绝,原因是学校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可能会干扰精神科病人的治疗。联邦上诉法院在审理时拒绝适用合理审查标准,认为如果据此遵从学校的评判,无疑会让保护身心障碍者平等权利的法律沦为一纸空文。在同年的“多伊案”⑰中,纽约大学医学院在发现原告隐瞒精神紊乱和自残行为病史后要求其退学。联邦上诉法院则采用了合理审查标准,认为如果在学校确立和使用学术标准时,缺乏证据表明其“唯一的目的就是拒绝为身心障碍学生提供教育机会”,那么法院必须对其评判表示遵从。纽约大学作为私立大学,其法律地位有别于公立大学。[8]但两案不同的判决结果表明,联邦上诉法院在审查标准上意见相左。之后,在1985年涉及身心障碍者居住安置纠纷的“克利本市案”⑱中,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明确了此类诉讼适用合理审查标准,不过法学界也有学者担忧该标准不能充分保障身心障碍学生的受教育权。[9]
(二)在录取评价中考虑性别因素:适用中度审查标准
以合理审查标准为基础,联邦最高法院在基于宪法条款主张权利保护的案件中,逐步适用不同强度的审查标准,甚至根据不同案情事实采用更为严苛的立场。[10]中度审查标准是指,立法或行政行为是为了实现某一“重要的”(important)政府目的并且与该目的“实质相关”(substantially related)。[6]566美国法院认为,以性别因素对公民进行分类属于“准可疑分类”(quasi-suspect class)。[11]所以,当公立大学因在录取评价中考虑性别因素而引发诉讼时,法院会审视相比学校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选择的手段,是否存在对平等权利限制“较少”(less)的替代方案。相应地,举证责任也从学生转移至学校。在1982 年的“霍根案”⑲中,原告是一名已经获得执业资格的男护士,他向密西西比女子大学护理学院提出入学申请。该校自创建之初就仅录取女生,尽管原告其他方面符合录取条件,最终仍因性别因素被拒绝。学校允许他旁听课程,但拒绝其以正式学生身份注册入学并获得学分。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时,首先确认适用中度审查标准,并强调即使该录取政策歧视的是男性而非女性,也不能降低审查标准。学校辩称,考虑性别因素的目的是补救女性遭遇的歧视,并认为男生出现在学校教育环境中会对女生造成不良影响。法院则认为,作为该录取政策的实际受益者,女性从未在护理行业遭遇性别歧视,反而是该录取政策固化了护理工作就是女性专属工作的性别成见。而且,学校允许原告旁听,明显与学校主张男性对教学效果会造成潜在风险的辩护理由相矛盾。最终,法院判决学校未能给出“极具说服力的辩护理由”,录取政策与所辩称的目的之间并非“实质且直接相关”。
在1996 年的“弗吉尼亚案”⑳中,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因仅录取男生而被提起诉讼。联邦最高法院依据判例适用中度审查标准,并称其为“怀疑式审查”(skeptical scrutiny)。法院强调,若要证明在录取中以性别因素对学生给予区别对待,那么学校的辩护“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是假定的理由,更不能是为了应对诉讼而事后编造的理由”。申言之,学校在承担更多举证责任时,必须解释其在录取程序中秉持善意旨在达成的实际目的,而不是将事实上基于其他理由的行为合理化。学院提出两点辩护理由:一是单一性别教育能够产生重要的教育利益,而这种教育选择也能促进教育方法多元化;二是学校在人才培养中使用被称为“逆境磨炼”的教育方法,如果录取女生就必须大幅度修改甚至推翻培养计划。法院认为,单一性别录取政策仅为男生提供了特殊的教育利益,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教育选择,更不能证明只有通过排斥女生的方式才能合理地促进该州教育机会多元化。至于学校辩称录取女生就会降低教学质量、破坏培养模式甚至阻碍学校发展,法院则特别指出,应对这种观点予以“从严检视”(hard look),因为这与美国历史上用以拒绝平等权利保护的歧视主张别无二致。
(三)在录取评价中考虑种族因素:适用严格审查标准
严格审查是最为严苛的审查标准,它要求立法或行政行为是为了实现某一“迫切”(compelling)目标所“必需的”(necessary)。[6]567在适用该标准时,法院必须查明为实现该目标所选择的手段是否存在对权利限制“最少”(least)的替代方案。在司法实务中,受教育权并非联邦宪法予以明确或隐含保障的基本权利,但以种族因素对学生给予区别对待则被视为“可疑分类”(suspect classification)。这种分类“建立在一种自身似乎与既定宪法原则相悖的特征之上,以至于有意使用该分类因素都可被视作值得怀疑”[11],所以应当适用严格审查标准。不过,针对公立大学因实施“积极差别待遇”(affirmative action)录取政策而引发的诉讼,法院也曾在审查标准适用问题上产生分歧。在1978年的“巴基案”㉑中,联邦最高法院中的自由派大法官认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在录取程序中考虑种族因素,目的是对少数族裔学生给予一定优先对待,这种善意分类明显不同于历史上因种族歧视而拒绝录取的恶意分类,因此适用中度审查标准即可。毕竟,一旦触发“理论上严格、事实上致命”[12]的严格审查,其彻底、苛刻的审查强度将使公立大学在能否考虑种族因素这一问题上毫无自治与自由可言。投下关键票的鲍威尔(L.Powell)大法官在坚持适用严格审查标准的同时,也立足高等教育情境的特殊性,认为大学在严格审查之下仍有源于学术自由的遵从空间。[13]
在2003年涉及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格鲁特案”㉒中,联邦最高法院明确了对积极差别待遇录取政策适用严格审查标准,同时认可公立大学可以学术自由为基础,将学生群体多元化作为迫切目标。学院辩称,这一目标对于实现高等教育使命而言至关重要。法院认为,应当对这一教育评判予以遵从,并指出不应以“致命”的严格审查标准在法理上否定积极差别待遇录取政策。同时,法院也强调手段与目的之间契合的准确性,提出“紧密缩限”(narrowly tailored)原则,要求“对同样能实现学校所追求的多元化目标之可行的种族中立替代方案,予以认真、善意的考虑”。不过,随着美国国内政治力量与种族关系的变化,联邦最高法院对积极差别待遇录取政策的遵从立场也渐趋保守。在2016 年的“费希尔II 案”㉓中,因德克萨斯大学实施积极差别待遇录取政策引发的诉讼在历时八年后终于落锤。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严格审查不应是“理论上严格、事实上软弱”,强调法院对大学的司法遵从在目标判断与政策实施之间应有清晰边界。易言之,对大学如何界定其教育目标的遵从,应有别于对大学如何实现该教育目标的遵从。因此,法院进一步要求学校“证明其在采用种族分类之前,可用且可行的种族中立替代方案均不足以(实现该目标)”。这意味着,公立大学在解释为何实施此类录取政策时,须以推理或证据的方式展现其价值或优点,无疑要承担更多举证责任。[14]
四、美国公立大学录取纠纷司法审查标准之镜观
在我国,当学生质疑公立大学录取结果并提起行政诉讼时,学校多以办学自主权为名主张法院应予尊重,而法院在运用司法审查技术时亦多有犹豫,普遍止步于程序审查。正如开篇所提出的问题:在此类诉讼中应如何把握司法审查强度和举证责任配置,才能切实保障学生受教育权利,维护录取工作的公平正义?在美国,公立大学作为州行为人,同样依公权力授权实施录取政策,相对而言在学术自由范畴内具有更多裁量权空间。从其司法实务来看,法院在认可大学自治的基础上,在此类案件中采用了更为灵活和复杂的审查标准。予以镜观,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正当程序:程序性与实体性相结合
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美国公立大学录取纠纷全面进入司法审查视野。一方面,法院以行政法和宪法条款为基础,分别构造了两种类型化的司法审查标准。另一方面,除《行政程序法》对程序性正当程序的规制不言自明外,《联邦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条从“平等保护”和“正当程序”对权利予以一体两面的保障,而其中“正当程序”本身又涵摄程序性正当程序与实体性正当程序两层原则。[15]这成为法院构造宽严相济体系化司法审查标准的法理基础。纵横兼顾的审查标准为法院审理不同案件提供了查明事实和分析判断的指导基准,能够恰当地配置审查要件与举证责任。学校在何种程度上遵循录取评价的正当程序,是法院适用审查标准时所关注的重点。同时,法院进一步在程序性正当程序与实体性正当程序基础上,依据纠纷争议焦点延展出可以“滑动”的司法审查强度[16],以在给予学校司法遵从的同时,亦能合理把握司法介入的程度与范围。在适用宽松的“任意和不正规”标准与合理审查标准时,法院仅审视录取评价的程序性正当程序,从边缘介入对录取纠纷的审查。即使在适用更为严苛的中度审查和严格审查标准时,法院也要求学校解释在做出决定时是否存在“充足目的以证明其正当性”[17],仍然为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留有空间。正因为“即使对个人适用最公平的程序,也足以摧毁(生命、自由或财产)三种权利”[18],所以法院没有完全止步于对程序性正当程序的审查边界,而是将其与实体性正当程序相结合。
(二)过程探索:录取评价的逻辑推理
在行政诉讼制度中,实体性正当程序一方面在实体方面要求行政行为应当具有合目的性,另一方面在程序方面要求行政行为程序本身不仅具有形式上符合法定程序的合法性,还应当具有实质上不存在程序滥用情形的正当性。[19]美国法院在20 世纪30 年代曾对行政分支确立了“不探索决定者的思维过程”原则,后在司法能动主义推动下,逐渐要求行政行为的决定者说明理由。[4]377-379行政法学者劳森(G. Lawson)认为,司法审查在特定情形中需关注为何做出某一决定,即对做出决定的“推理”(reasoning)过程予以审查。他认为这是有别于传统程序审查或者实体审查的“过程性审查”(process review)。[20]在录取评价中,公立大学以个人或集体方式由专业人员对学生是否具备入学资格做出学术评判,自然需要主观评价和自由裁量。尽管法院认为专业人员在学术评判这类微妙事务上显然具备更佳的“制度能力”[21],但在适用中度和严格审查标准时,法院明确要求学校承担举证责任,就录取评价中考虑争议因素及做出评判结果的步骤与理由进行说明,这本身也是在探索决定者的思维过程。美国公立大学录取程序总是处于“黑匣子”之中,多数也是经过较高强度司法审查,通过证词陈述和庭审质辩才为民众所知。在形式上,过程探索偏向实体但不触及实体,仍然尊重专业人员的制度能力。但在技术上,它在特定情形中可以帮助法院在查明事实时,寻找司法审查的突破口。毕竟,看似形式完美的程序也不能掩饰推理过程中存在的逻辑缺失与证据冲突。只有明确呈堂应诉所提供的理由是学校做出录取决定时的真实理由,法院才能裁定学术评判的真实性和正当性。
(三)以法为矩:权力制约与权利保护
司法审查介入公立大学录取纠纷,本质上是对学术自由范畴内的裁量权予以制约,保护学生平等受教育权利。应当指出,美国法院以宪法条款为基础构造宽严相济的审查标准,其强度差异并非始于不同受保护权利的重要性差异,而是源于种族、性别、身心障碍等不同分类因素曾经被公权力用于排斥特定群体获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因此法院将其视为与“受保护阶层”(protected class)[22]密切相关。但仍然可以认为,美国法院在对公立大学录取纠纷进行司法审查时,适时运用实体性正当程序原则,将权力制约与权利保护纳入法治框架予以动态平衡,能够更好地弥合司法审查在程序与实体之间的缝隙。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教育法治进程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在教育管理实践中重视和引入正当程序。2019 年2 月,教育部要求在研究生考试招生中,统一制定复试小组工作基本规范,复试全程要录音录像,复试小组成员须现场独立评分,任何人不得改动。程序性正当程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它并不能充分规避学术评价中的滥权行为。作为受教育者,学生有权利要求公立大学在录取评价中,就自身是否具备入学资格做出公平的评判,也会在察觉可能存在不当行使裁量权之行为时,诉求法院介入及对录取行为进行审查。可以预见,随着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围绕录取纠纷会出现更多诉讼案件。假设学生因为初试成绩与复试成绩排名的明显变化而未被录取,质疑复试小组成员未能合理行使评判裁量权,法院可以要求学校举证说明做出评判结果的步骤、标准与理由。实体性正当程序不仅是一种权力制约机制,也是一种权利保护机制。[19]我国法院应理性借鉴域外经验,考虑在涉及是否合理行使学术评判裁量权的案件中,依案情事实和诉讼主张适度提高审查强度,恰当配置举证责任,切实保障学生受教育权利。
注释
①参见广东省广州市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6)粤71 行终1402 号行政裁定书。
③参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 行终242 号行政判决书。
④参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09)天法行初字第90 号行政判决书。
⑤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 行终362 号行政判决书。
⑥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 行终232 号行政判决书。
⑦参见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3 行终270 号行政判决书。
⑧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 行终261 号行政判决书。
⑨Gaspar v.Bruton,513 F.2d 843(10th Cir.1975).
学生阅读课文,体会罗丹修改塑像时的动作、语言、神态。仿照课文,对照插图,想象罗丹全神贯注工作的状态并写下来。之后对照原文进行修改。学习课文中的联想部分,感受联想的妙用。试着运用联想,再次修改。
⑩Arizona Board of Regents v. Wilson,539 P.2d 943(Ariz. Ct. App.1975).
⑪Grove v.Ohio State University,424 F.Supp.377(S.D.Ohio 1976).
⑫Lesser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New York,239 N.Y.S.2d 776(N.Y.App.Div.1963).
⑬State ex rel.Bartlett v.Pantzer,489 P.2d 375(Mont.1971).
⑭Eden v.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State University,374 N.Y.S.2d 686(N.Y.App.Div.1975).
⑮Southeastern Community College v.Davis,442 U.S.397(1979).
⑯Pushkin v.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658 F.2d 1372(10th Cir.1981).
⑰Doe v.New York University,666 F.2d 761(2d Cir.1981).
⑱City of Cleburne v. Cleburne Living Center,Inc.,473 U.S. 432(1985).
⑲Mississippi University for Women v.Hogan,458 U.S.718(1982).
⑳United States v.Virginia,518 U.S.515(1996).
㉑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438 U. S. 265(1978).
㉒Grutter v.Bollinger,539 U.S.306(2003).
㉓Fisher v.University of Texas,136 S.Ct.2198(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