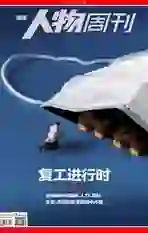阿斯哈·法哈蒂:我的电影不是秘密,但也不是答案
2020-03-18孟依依
孟依依

阿斯哈·法哈蒂。伊朗导演、编剧,1972年出生于伊朗伊斯法罕省,已有八部长篇电影问世,作品 《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 和 《推销员》 分别获得第84届和第8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无意识
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坐在舞台上的左侧,背后的大屏幕上,他的名字底下还有一行稍小的字:伊朗现代启示录。2019年底,海南电影节的这堂大师课引来了不少中国青年导演,人们真想从这个蓄着大胡子、说着波斯语的脑袋中挖掘出一些秘密。
他们讨论起了“无意识”的创作。
“我觉得我们所有人在内心里面都有一个非常大的、相当于一个银行的库存,我们从小就慢慢吸收很多信息到里面。所有的人都有这个‘银行,但是并不一定所有人都有银行的密码或者钥匙。所谓的艺术家,就是找到了自己的钥匙的一些人。”法哈蒂说。
从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2011)开始,法哈蒂这位伊朗导演被更多观众熟知。2012年,这部电影获得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打败了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
故事讲的是一对伊朗新中产阶级夫妇,为了带着女儿移民,他们办妥了所有手续,但丈夫纳德无法抛弃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在最后时刻决定留在伊朗,妻子西敏一气之下搬回父母家住。因此,纳德不得不雇佣一位保姆,在他白天上班不在家的时间里照看他的父亲。
有一天,纳德回家发现保姆瑞茨不在,而父亲的一只手被绑在床沿,整个人摔倒在地不省人事。纳德生气,冲着终于出现的瑞茨发脾气,并把她推搡出门——门外便是楼梯。瑞茨意外流产了。在伊朗,致使孕妇流产会被指控谋杀罪,之后两个家庭的冲突接二连三爆发。
法哈蒂讲过,《纳德和西敏》的“无意识创作”来自和爷爷有关的故事,“他是个非常诚实勇敢的人,小的时候,我希望长大以后像他这样就可以。”后来爷爷得了抑郁症,容易忘记很多东西,法哈蒂也有很长时间没去看他。一次,弟弟突然给法哈蒂打来电话,说,他们给爷爷洗澡,但是爷爷不让他们把自己的衣服脱下來洗干净。“洗澡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我弟弟就靠在爷爷的膝盖上哭了,这个场景一直在我的脑子中。”——类似的场景也出现在了这部电影里。
他的另一部影片《关于伊丽》(2009)的“无意识”线索则是时常浮现在他脑海中的一个画面:一个男生穿着大风衣面对大海,他的衣服是湿的,时间是下午。
圆脸的年轻导演杨子站起来问:“您刚才说的‘无意识这个词儿,我太好奇了,如果英文的话,这个词儿怎么翻译呢?”
“Unconscious.” 法哈蒂解释,“事实上,无意识在本质上每个人都有,但是没有人去用它。”这个单词还可以被解释为潜意识或者未发觉的,往往和人的感知相关。他有时候觉得奇怪,以前的电影质量比现在好多了,在法国、意大利、日本、中国、伊朗都是如此。他翻来覆去想,“现在我们什么都知道,拥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各种各样的设备,但是‘无意识已经没有人去用。”
“确实我自己也非常奇怪,由无意识开端而创作的作品,非常容易连接或者触到他人的无意识,因此观众会有感触。我们波斯语有一句俗话,‘从心出发的那一句话也可以进到面对面的人的心里去,意思是说无意识上出来的东西完全可以触到对方的无意识感觉上。”法哈蒂说。

《 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 剧照
反省
法哈蒂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父母虽然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但鼓励他追求艺术。13岁时,他加入了伊斯法罕青年电影协会,并用8毫米摄影机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短片。之后,他进入德黑兰大学主修戏剧,硕士则到塔比阿特莫达勒斯大学继续舞台导演的学习。成长过程中,法哈蒂已经完成了六部短片和两部电视剧的创作。
而与他的成长同时进行的是伊朗的战争和动荡。1979年,法哈蒂7岁的时候,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领导的君主立宪被推翻,在自由民主的理念被短暂接收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共和国。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掌权,对教育部门和公共部门推行伊斯兰化,学校加强宗教教育,剔除不符合伊斯兰政治要求的教师,充满了偏执和压抑。
共和国成立之后,此前一度全面停止的伊朗电影得到了扶持,但同时面临严格的审查,那是一道没有公开标准的工序,从剧本创作到最后的剪辑,任何环节都有可能无法过审,伊朗电影的创作也因此被看作是“戴着镣铐跳舞”。

《 推销员》 剧照
宗教便成了法哈蒂电影中的一大主题,这不仅仅体现在女性总是裹着头巾的外表上,更在于它对每个个体行为准则的影响上。
在《美丽城》(2004)中被害人父亲阿普哈桑为了给女儿报仇,决定以牙还牙杀死对方,但他还需要因此支付给对方一条女性生命的“血钱(blood money)”。因为《宪法》虽然规定男女同权,但《古兰经》仍是最高法律,在《古兰经》中,女性生命的价值是男性生命价值的一半。虽然不甘心,最终阿普哈桑也只能因贫困放弃复仇。
《推销员》(2016)中,丈夫伊玛德发现自己的妻子可能在公寓被闯入者性侵,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制裁对方,最终导致对方心脏病发。在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前,他是一个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一个风度翩翩的话剧演员,这些在宗教的传统面前荡然无存。
即使新作《人尽皆知》(2019)的故事以西班牙为背景,导演仍然放置了一个戒酒、虔信上帝的父亲,这导致他在女儿被绑架时选择了不作为,却和妻子及其旧情人产生冲突。
和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伊朗导演相似,法哈蒂继承了意大利新浪潮电影的血统,镜头对准的是真实生活,起用非职业演员。与伊朗的前辈导演们一脉相承的还有,他不自觉地将女性拍成主角,“或许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
但他有自己的另一种视角。《美丽城》之后,法哈蒂不仅仅只注意到无产阶级的生活、底层人物的困苦,他的电影中还出现了此后占据其作品主要篇幅的群体——中产阶级。角色们开始直面他们遇到的问题,而他们遇到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我电影中的人物开始自我反省,他们的行为到底是好是坏?”
法哈蒂和他的许多朋友都属于这个群体。20世纪初,恺加王朝后期,伊朗第一代知识分子出现,由此衍生而来的现代中产阶级如今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逐渐遭到抛弃:他们接受的西方教育和西方思想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困境,甚至有些人因此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能负担一位保姆的费用、供养两辆汽车,但支付不起四千万里亚尔的保释金(按照《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上映的2011年的汇率换算,约合25000元人民币);他们难见容于本国文化却也无法在异国文化中寻得慰藉,异国婚姻总以悲剧收场。
表象之下
苦难天然成为故事土壤,而法哈蒂关心日常,“日常生活的细节才是造成争议的关键所在。”他并不总是随手把一些细节记录下来,如果忘记了,那就证明是不重要的。到了写剧本的时候,“好像内心放了一块磁铁,它会自己找到我要的东西。”
2012年他拍《过往》,讲述的是一位伊朗男人前往法国与分居的妻子办理离婚手续的故事。拍摄时法哈蒂去法国住了两年——“当你拍摄的故事主题是过去的事情,除了巴黎你还能想到更理想的城市吗?巴黎处处都让人嗅到过往的气息。”
最后,他非常肯定地告诉摄影师他想要温暖的颜色,“我想让黄色(有时候染上一层褐色)随处可见,浸透在空间里的黄色让人想起过去。我知道在法语中,我们用‘发黄来形容陈旧的纸页。在波斯语中,黄色代表怀疑、不确定。”他在一次采访中说。

2017年2月26日,伦敦,电影《 推销员》 在特拉法尔加广场露天免费公映
如果需要一条有规可循的经验,法哈蒂会讲到他工作中的一个既定流程,那就是每一次拍摄前,他会把演员叫到一起,开始排练电影中不会出现的场景。
他的女儿曾出演《納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中的特梅,男主角的女儿。因此,法哈蒂让女儿把与自己的感情放在一边,“有一个新的爸爸,让他去接她、送她,跟她一起去餐厅,一起吃饭,一起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花很多时间跟她一起度过。”
然后,“就像我的前几部影片一样”,他们找到一个大厅,在那里排练剧本中没有的场景。像排练戏剧一样,每次用开始的半个小时做一些运动,中途如果有谁进去,一定会以为一场戏剧正要上演,“一会儿之后,我就再也感觉不到什么语言障碍了,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进入情绪。”
这些排练可以让法哈蒂大胆地在电影中设置停顿和空白。也许是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影响了他,他的硕士论文是写哈罗德·品特的。为此他研究了品特的作品语言,戏剧中的“静默(silence)”使他着迷,“角色们会说很多,但似乎张口是为了沉默,万物都在表象之下。”
不可否认的是,他非常擅长使用停顿,镜头转换之间存在叙事空缺,但同时留下足够多的蛛丝马迹,然后是由观众的参与填补起来的:让他们去思考一个老年痴呆的老人站在川流的马路边这一幕会对之后的故事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位女教师为什么消失在大海里,一只打火机是不是意味着出轨——“电影工作者可以对观众的想象力抱有乐观的态度。”
镜子
品特同样也影响了法哈蒂将故事聚焦在家庭中,宗教的冲突和文化的冲击被内化为一场场充满矛盾的婚姻。但和从小经历逃亡而缺乏安全感、认为家庭充满背叛和谎言的品特不同,法哈蒂把家庭视作社会的镜子。
《一次别离》中,西敏为了给女儿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而出国,纳德为了照顾老年痴呆父亲而决定留在伊朗,女儿特梅为了维护父亲打破伊斯兰教之大忌而撒谎,每个角色都被放置于必须做出选择的情境中,除了纳德的父亲,因为他得了老年痴呆症。
“这是人类的悲剧。无论你是否身在伊朗,当你必须做出艰难选择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同样的困惑。大多数人认为,只要你拥有了自由,你就是快乐和充实的。事实上,自由只是让你有能力做出选择,而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人能够禁止你选择的。所以,正是有了自由的存在才形成了许多个人和社会的困难。”法哈蒂希望讨论那些与我们相关的复杂问题,而这些复杂问题最终会细化为日常生活的细节。

《 人尽皆知》 剧照
选择产生差异,差异演变成对抗。传统悲剧讲述的是善与恶的战争,我们热衷于看待善战胜恶。而法哈蒂的电影讲述的是“善与善的战争,无论哪一方获胜,都令我们心碎”。
但他不会给出答案,“其实这些在我的电影里面有,但是最后不会有任何答案,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我不会说,比如传统和现代,或者家庭矛盾,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这完全不是我该去做的事情,如果我去判断的话,完全是侮辱观众的看法,结果要让观众自己去感受。”
他许多次被问到第一次接触电影的契机,许多次回答可以整理出一个大概完整的故事开头:
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作品第一次在奥斯卡金像奖获得最佳外语片的时候,距离他和其他兄弟姐妹逃跑去看电影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
法哈蒂出生在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省霍尔梅尼市,电影院在另一个城市,因此父母不许他们去看电影。他们于是偷偷溜走,坐上了从霍尔梅尼开出的长途巴士。
孩子们还是来晚了,电影已经放映了一半。因为和伊拉克的长期冲突,伊朗电影院偶尔会放映盟军关于二战的老宣传片,那天放映的正是这样一部电影。主人公是一个十多岁的东欧抵抗组织的成员,最后,他刺杀了纳粹恶棍。
故事的不完整导致之后好多天,法哈蒂都在试图构建他错过的那些场景和情节。这次经历在他后来的导演生涯中持续发挥着作用——法哈蒂的电影总是没有明确的结局,“我不想让这部电影为观众而结束,我想让观众在离开电影院的时候,脑子里还想着它,还在问问题。”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这么说,而在另一次采访中他说,相比于答案,我们更需要提问。
(参考资料:《伊朗的另一扇窗户——阿斯哈·法哈蒂电影研究》《Freedom and Its Discontents》《How Irans Greatest Director Makes Art of Moral Ambiguity》)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