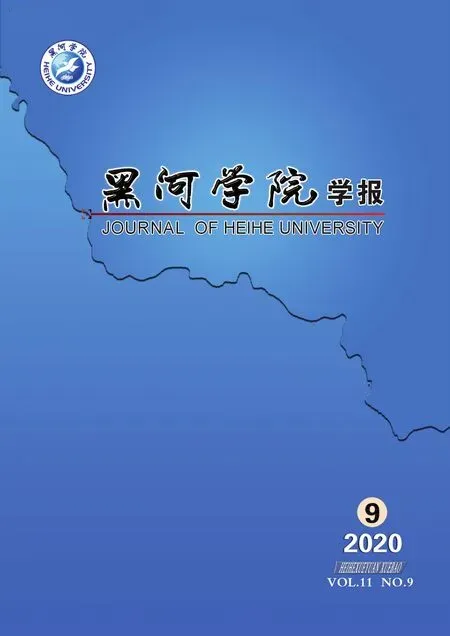旗帜的符号类型与符指过程研究
2020-03-17
(巢湖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旗帜对于全人类来说是普遍之存在,或多或少的参与到各民族的发展历程。作为一枚特别符号,与语言有许多共性:都人类所独有,都有交际与沟通之功能。孙子云:“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1]。”在言语不畅并视线受阻之时,旗帜所产生的符号效应能替代甚至超越语言。同时,是群体的象征,携带强烈的集体意识与强大的向心力与神圣感。正如涂尔干曾言:“一个士兵为保护他的旗帜倒下,肯定不会认为他仅是为一块布而牺牲性命[2]。”符号学视域下的旗帜,可以观照其类型与表意中的各种现象。
一、旗帜图案
旗帜包含三要素:图案、样式与材质。现如今,样式与材质大体相同,多通过图案与颜色搭配表意并区别彼此。依图案类型大体可分为三大类:自然型、人文型与条纹型。
自然型是指以自然界中某物作为旗帜图案原型,比如日月星辰、动植物、地图轮廓等,或因原始图腾,或为当地具有代表性的景致,此为当今旗帜主要类型之一。世界上有地区以太阳为旗帜图案,日本国旗来自大和民族对太阳的崇拜;新月旗帜代表伊斯兰起源于奥斯曼帝国,诸见于今天的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塞拜疆、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巴西的国旗是为纪念独立那晚天空景象,圆周内五角星的布局为首都里约热内卢的星空,加拿大的枫叶旗取自境内常见树木,象征广大国民与物产之丰盈,香港的紫荆花区旗,澳门的莲花区旗及西方常见的以狮子或鹰为图案的军旗样式皆为此类。
人文型指以自然景观以外的,来自宗教或其他人文图饰为旗帜图案,常见的基督教国家十字架搭配不同颜色,今天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英国、瑞士、希腊、格鲁吉亚、国际红十字会(在伊斯兰国家为星月)等旗帜都是此形。以色列的六角星旗,又称大卫之星或大卫王盾,是犹太教与犹太民族的标志;韩国的太极旗取自《周易》的阴阳之说。还有一些国家沿袭了封建王朝时期王室徽章图案,先前王权标识转而成为国家主权象征,比如,西班牙国旗上的王冠,葡萄牙国旗中央盾牌图样,五个点代表耶稣受难时的五个伤口,列支敦士登的神圣罗马帝国王冠等。人文型还包括以人们使用的某种工具或物品为图案,比如,镰刀与锤子代表农民工人;天平象征公正;沙特国旗上的白色宝刀轮廓与可兰经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橄榄枝设计虽是以自然物为图,但鸽子与橄榄枝代表和平来自《旧约》也属此型。
条纹旗传统起源于美法,常见的有两色、三色、四色与五色条纹,有水平排列、垂直排列与对角斜纹三种,为当今常见的国旗样式。美国国旗上五角星的数量代表联邦各州,而13道红白相间条纹代表独立之初的13个州,法国国旗起源于大革命时期,红白蓝三色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解释意义。这种旗帜类型最大的优点是一目了然,易于辨识,结构简单且易于记忆。
二、旗帜的符号类型
每面旗帜有其指称对象,其设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为旗帜符号学的研究首要内容。以索绪尔为代表的以语言为中心的结构符号学(semiology)学派认为:“语言是一套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与书写系统、盲文字母表、象征仪式、礼仪客套、军事信号等相当。”[3]此处的“军事信号”多依靠旗语实现。结构符号学将符号分两层:能指与所指,即符号与意义,认为二者主要是任意性的。
另一位符号学之父美国人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的符号学(semiotics)理论突破了笛卡尔的二元哲学观与康德的范畴论,将实用主义与数理逻辑应用于符号学研究,将对象纳入符指过程中,并就符号与对象关系进一步将符号分为:像似符(icon)、指示符(index)与象征符(symbol)。像似符与对象之间是建立在某种相似性基础上;指示符与对象之间没有像似性,而是通过某种隐蔽的强制力将关注点指向对象,毗邻是其联系所在。像似符与指示符、对象之间有理据相连,而象征符与对象之间是建立在某种社会习惯(convention)上,与对象之间的联系是任意性的,可视为任意性符号。需注意像似符与像似性(iconicity),指示符与指示性(indexicality),象征符与象征性(symbolicity)的区别,在皮尔士看来,并不存在纯粹的像似符[4],推而广之,也就不存在纯粹的指示符或象征符,但符号的像似性、指示性或象征性可能普遍存在。像似性、指示性与象征性指的是符号的三种特性(three properties),是就符号的功能而言。一枚符号可以兼具像似性、指示性与象征性。
绘画大多是像似性的,路标具有指示性,语言文字多属于象征符,旗帜有别于这些符号,一面旗帜可以三功能兼而有之。因为旗帜符号类型取决于其图形与色彩。但符号对象在图案之外,可以是代指某个人,如古代战场的帅旗;某个群体或组织,如国旗;标识某现象,如风向旗。因此,旗帜的符号分类需要兼顾其图案、色彩与符号对象的关系。就图案而言,上文的归类中,以自然景观为图案的旗帜,大部分为像似符,但像似性有差异。西方常见的军旗以鹰与狮为形,可以理解为图形与对象之间的某种品格像似;联合国旗帜上的以北极为中心世界地图可以理解为轮廓像似;有些旗帜以所在地的某一典型地貌为图案(如马来西亚的沙巴州以当地的名山为旗帜重要图案),这种以部分像似代替整体,在修辞学上属于提喻(synecdoche),属于部分像似。旗帜与对象无论是形似、品格像似或部分像似,都可以理解为像似型旗帜。
加拿大国旗中的枫叶与香港区旗的紫荆花虽然也是以自然物为标识,但是旗帜与对象之间不是建立在像似性的基础上,而是某种毗邻。从符号修辞学的角度看,枫叶并非像似加拿大,也不存在整体与部分的关联,而是一种转喻(metonymy):以常见自然物代指整个国家,按照雅各布森的说法,其关系的建立是种毗邻关系(congruity)[5]。红色枫叶是加拿大秋天常见景象,代表这个国家,同理,红花羊蹄甲最早在香港发现,以此代表这座城市也是一种邻接关系,皆可归为具有像似性的指示符类型。
镰刀与锤子代表无产阶级也可归此类。而以日月星辰为主要图案的旗帜,多为表达集体崇拜,太阳崇拜因为其孕育了生命,象征自由。伊斯兰国家的星月旗,因沙漠地区的月亮与点点星光代表了凉爽与驱散黑暗,以崇拜的自然物代指整个国家或地区则可以理解为指示符。人文型旗帜与之类似,以宗教或某种文化符号为旗帜图案代表国家或地区,比如,上文提及的十字型国旗、大卫六角星旗帜、韩国国旗等,图形与对象没有像似,可以理解为以信仰代地区,也是指示符类型。
其他的图案类型,比如皇冠以前指代君主,如今指代主权,皆为指示符;某些国家国旗能指涉某段历史,最为常见的是英联邦的一些成员国依然保留了宗主国国旗的某些特征,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此类图案也属指示符。像似型与指示型旗帜,在符号与对象之间都是存在一定理据的,或为某种相似性将对象与符号相连,或为某种毗邻关系将人们的注意力强制性指向对象,因为这种理据性的存在,解释起来其旗帜的意义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改,旗帜图案也相对固定,在当今旗帜系统中也易于辨识。
其实旗帜的象征性设计还是更加普遍,常见的有颜色表意,不同角数的星星表意(常见的有三角星、四角星、五角星、六角星等)与条纹表意等。旗帜的颜色表意或为约定俗成,或为设计者的人为解释并被官方接受,这种设计与所表达的意义之间并没有理据。当今国旗中常见的三色条纹旗,常见的颜色有红、白、绿、深蓝、黄、淡蓝与黑几种搭配,只在色度、条纹方向、比例做区分,如法国与荷兰,同样是蓝白红三色,主要是水平与垂直排列之别。符号与符号之间存在样式相近,存在辨识度不足的问题,甚至出现几乎完全相同的设计,比如,罗马尼亚与乍得两国国旗,都是蓝黄红三色,只是色度上有略微差异。对这类旗帜的意义解释时存在理据性不足,如出现同色不同义与同义不同色的现象。如法国国旗的蓝色象征自由,美国的蓝象征坚韧与正义,而欧盟的蓝象征真理与智慧;再如红色在中国有忠诚之意,比如“丹心”“赤忱”;在欧洲其代表色为蓝色,但在西方古代的纹章中为黄色。
旗帜是为了运用,为了表意,以上分析都是共时视角看待旗帜符号,从历时看其符号类型与意义之间存在关联。作为标识的旗帜有两种,一为等级标识,如中国古代的卤簿制度,每一级官员的旗号服饰都有所不同,再如欧洲中世纪华美的纹章,旗帜为身份与家族的象征。二为族群标识,如国旗或球队队旗。这让旗帜设计走向两端,一端走向复杂精巧,精美甚至浮夸型,以中世纪的欧洲为代表,“当贵族阶层形成,血统观念大行其道,一种稳定、古老而又排他的血统意识不断被强化,盾形纹章的发展正好为这种贵族血统的世袭提供了理想的符号[6]。”在当时,只有上层人员才能拥有为彰显身份地位,也为区别于一般图案的旗号。在中国古代身份旗帜系统里,多通过斿的数目、图案(多为像似图形)、旗杆高度来彰显地位。另外一端恰恰相反,其设计避繁就简,颜色搭配一般不超过五色,图形更是简洁明了,因为这类旗帜与身份地位无关,无需过多标识,且其代表的多是普通民众,过于繁复的设计不利于集体记忆。
当旗帜主要用来传递信号时,也就是所说的指示符,如中国古代数目众多的战旗,不同颜色、样式与图案含带不同战场指令;再如18世纪前后的海上信号旗亦是如此。旗帜的设计也会趋于简单化,这样其意图一目了然。试想如果设计过于复杂繁琐,受众精力就会分散,影响其实际用途;其次,信号讲究准确与及时,繁复的设计会延长受众的理解时长,影响交际效率。摇晃一面白色的旗帜表示投降,甚至无需任何图案。《墨子》记载“守城之法,木为苍旗,火为赤旗,薪樵为黄旗,石为白旗,水为黑旗[7]”。这里旗帜的颜色就是一种信号,传递的是城中需要的物资与援助。古代中国战场与近代海上的旗语将信息传递功能发挥到了极致:简单且易识别的颜色搭配,一目了然的形状设计,相应的操作手势,三者加以组合,其易见性确保了信号的传递。
总之,实际功能与设计是密不可分的,当其作为贵族标识时,图案多精美,结构繁复且材质贵重;当其用做信号传递时,设计简洁明了但数目种类繁多,据记载在古代中国战场上各种军旗多达88种[8],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科技的发展,封建等级观念被打破,旗帜的标识功能转向群体,这使得旗帜的设计舍弃了繁复的旗杆造型,复杂的图案与数目不等的斿等附属设计,其次,更为先进的通讯技术取代了旗语,应用的改变也让旗帜的设计趋向简单。
三、符用视角下的符指过程
符号的指称过程(semiosis),简称符指过程,皮尔士定义为:“我之所谓符指过程,(非指)发生在两主体之间所有身体的或心理的动态行为,或蛮力(brute force)行为,(无论他们是相互作用,或为完全或部分地施动与手受动关系)或者至少是二者行动的结果。与之相反,而是诸如符号、对象与解释项三者之间相互协作所产生的行为或影响,此三元影响绝非能简化为二元行为[9]。”此处的“蛮力”指的是与无视规则与理性之力。早期皮尔士受到康德的影响很大,此处可以明显看出他挣脱了传统的精神与物质二元哲学,也区别于欧陆结构符号学派能指与所指、表达层与内容层等二元法,将符指过程置于更加动态的三元之中。
著名的行为符号学家莫里斯进一步定义为:“符号过程,即某物对于有机体来说成为符号的过程[10]。”在莫里斯看来,符号的阐释者(interpreter)就是有机体,扩大了符号主体的范围,并进一步根据符号与人的关系,符号与符号的关系及符号与对象的关系将符号学分为三个维度:符用学(pragmatics)、符构学(syntactics)与符义学(semantics)。在语言研究方面,此三个维度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硕果累累。但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非语言符号,特别是视觉符号研究并不多见。事实上,符指过程可以在符义学与符用学的两个维度加以探讨,旗帜亦是如此。
艾柯借助叶姆思维列夫的表达层与内容层理论将符号表意(sign signification)定义为“一枚符号经常是一种由它的一个表达层惯例性地关联到一个(或几个)内容层的元素。……符号载体(即符号本身或表达层)的意义或者说符号功能的内容层是它在符义系统内所占有的确切空间。依此看来,符号载体的内容层就是《dog》的既定义素,它是与既定符义子系统内其他义素相对而言[11]48。”艾柯的符义分析的前提是文化场,在场内的每一个符号载体(sign vehicle)对应一个文化单位,都有其内容层——艾柯称之为义素(sememes)。艾柯是较早发现KF model在符义分析中的局限,因为就/dog/来说,绝不止只有字典上的“一种会叫的犬科哺乳动物”的意义。为了分析符号载体在不同文化系统里,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艾柯提出了“百科全书模式”的符义分析。
旗帜的意义符义层面即艾柯的字典意义,此层面意义较为固定,不受语境左右,也就排除了情感、语境、接受者等因素的影响,实为旗帜的一般意义与用途。从符义学的角度,旗帜的意义也就是旗帜的一般功能。此外,具体语境下符号所产生的字典之外的意义,即符用层面意义,在符用学的视角下研究符号的指称过程也甚为必要,即艾柯的百科全书意义,指在交际实践中符号传递的超出字典部分的含义。在特定语境(context)中,符号发出者、阐释者、时空和交际渠道等因素所引起的符号的改变。在皮尔士的体系中,将此称作符指过程。符指过程对语境的敏感度高,意义在皮尔士的眼中是动态性的,“符号活动依赖于时间与解释者,包含符号、符号对象、行为事件及相关的实施者等等[12]”。如在语言文字中,牺牲与死亡,Hesperus与phosphorus,符号对象相同,但意义天差地别。在不同的符境下,相同的符号意义也会千差万别。笔者认为主要受到符指过程中的三个因素的影响:所处的符号域,符号行为和符号主体。
符号域来自于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奠基人尤里·洛特曼(1984)的概念,“所谓符号域,指的是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13]”,“在符号域之外,符指过程无法存在[14]”符号域具有孤立性,存在中心与边界之分,边界是符号域与外界互动的前沿,通过“过滤层(filters)”将外界文本输送置内部,这是域类系统动态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符号域即具备空间的延展性,也具有时间的延续性。旗帜的符指过程首先是在一定的符号域内进行,脱离相应的时空,符指过程无法进行,也就不具备表意功能了,艾柯以红旗为例的语义分析中,认识到空间不同所引起的意义差别,“在公路边意为小心;铁路边意为停下;在政治话语中意指共产主义[11]114”。从符号域的角度,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域是一切符指过程的前提条件,即使是面对同一符号,其所在符号时空的不同也会直接影响到符用意义以及随之而来的情感效应。试比较如下两面日本国旗对于中国人来说的差异。

图1 日本侵华时期留下的日本国旗

图2 新冠疫情期间,两国相互援助物资上常见的并排国旗
图1的文字、旗帜构建了一幅二战期间掠夺者的符号域,让人憎恨厌恶,恰恰相反,图2虽然看不到箱内物品,但清晰的两国国旗,相互打气的诗句构建了一幅灾难面前唇齿相依友邻符号域,让人感动。此两域为时间层面,两幅画面展示的虽为同一符号,但情感效应恰恰相反乃因为所在的域的不同。
其二,与旗帜相关的符号行为是符指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不同的行为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符号意义。行为主义符号学派认为,“行为总是贯穿任何生命体始终的,没有谁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频繁地行动着[15]”。而每一项行为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由某种内在驱动所决定。莫里斯将行为结构分为先后三个阶段:定位、操纵与完成,进行定位是为了下一步操纵行为做准备,以最终达到满足这一目的。因此,一切行为都具有目的性,而符号可视为实现目的的工具或载体。在此三阶段分别扮演着指向性、规定性与评价性的功能。旗帜的实际运用,也是符号主体为实现个人目的而进行的某种符号行为。因此,作为工具与载体,旗帜的符用研究,应观照到符指过程中相关的操纵行为。常见的有:摇旗、升旗、下半旗、披国旗、燃旗、将旗帜倒挂、旗帜交接等。其中的一些已发展成为仪式。这些可理解为,为了一定的目的,借助旗帜这个特别的符号载体,形成的具有规定性的操控行为,表达了某种特殊的意义。比如,旗帜的展开与否会影响到旗帜的情感效应,一面耷拉的旗帜比不了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一面因自然力而飘扬的旗帜又比不了以人力摇晃的旗帜带来的符号效应,这些行为使旗帜在情感共鸣方面的效应差异巨大,虽然目的都只在展开旗身。升旗仪式中,为了表达忠诚与尊重之意,需要行注目礼、队礼或军礼,一切与升旗无关的其他举止会被视为冒犯。为哀悼要人逝世或某重大不幸事件而下半旗。烈士或领导人国葬时灵柩上覆盖的国旗以示为国捐躯或尽忠;运动员赢得某项国际赛事胜利身披国旗绕场而行的荣耀时刻。燃烧某面旗帜的行为有两种情况,一为表达对旗帜对象的愤怒;二为一些国家规定可以通过焚毁形式处理废旧或破损国旗。将旗帜倒挂起源于北欧,这种行为多是在游行示威中民众对本地区或本国政府表达不满。将一面有特殊意义的旗帜如奥运五环旗现场交于另一方表示举办方与举办地点的变更。这些行为已成为符指过程的一部分,行为的缺场或变更必定会影响旗帜的符号效应甚至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
以上仅为旗帜的常规行为,其实与旗帜相关的符号行为还有很多,如将国旗印制在车身;常常见到英美国旗图案的靠枕、坐垫、杯垫;甚至将其作为时尚图案穿戴在身。这些行为分析起来也较为复杂,很少是为了彰显符号主体的政治立场与观点,虽然在许多国家此类并不被提倡甚至明令禁止,但大部分与价值观、道德品质无关,更多的仅作为大众图案而已,对象没有多大关系。
旗帜的符指过程必然关系到符号的发出者与接受者,在此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三种决然不同的意义:意图意义、文本意义与解释意义。这三种意义的产生过程,也就是符号的表意过程。“这个过程从发出到接收会有一个时空跨度,符号信息是作为意义的载体,他是发送者与接收者交流的纽带……[16]”。可见,旗帜的符用意义,与符号主体即符号的发出者与接收者都有关系。从皮尔士的符号理论看,意图意义相当于皮尔士的意图解释项(intentional interpretant),解释意义相当于效应解释项(effectual interpretant),文本意义即共同解释项(cominterpretant)。在解释交际(communication)过程中应突出了参与者的角色,更加人性化,也更为贴近符号指称过程实际。
旗帜在符指过程中就常有意图意义与解释意义不一致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因为符号主体的不同,试看以下两则案例:2017年11月11日,在华沙举办旨在纪念波兰独立99周年的庆祝活动中,有超过6万名有“白人至上”主义的民族主义分子,手持波兰国旗,高唱“我们需要上帝”“欧洲是白人的欧洲”“纯粹波兰,白人波兰”“难民滚开”等口号。另一则发生在2018年2月3日,在意大利的中部马切拉塔市,一名28岁意大利白人男青年驾驶一辆汽车,在市区朝非裔路人开枪,6人受伤,重伤1人。在被警方控制时肩披一面意大利国旗,其后的问询中袒露因另一起刑事案件报复非裔移民,那起案件为一名19岁白人女青年惨遭一名29岁尼日利亚非法移民分尸。
此两件案例的共同点为旗帜成为其表意的工具,对于本人来说,所作所为是一种爱国行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不受外来人群的侵扰,国旗为所作所为披上正义的外衣。但符号接受者对此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阐释:在一部分人的眼中对此给予了一定的理解,甚至同情。比如,波兰外交部网站发文,这是“成千上万的群众以和平地方式表达他们的爱国之情”,甚至当时的内政部长夸赞道:“一道美丽的风景线”[17]。在另一些人的眼中,其所作所为与爱国有本质的不同,爱国行为表达的是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个体对祖国的依存关系,对祖国的归属感、荣誉感与自豪感。与对他国、他民族的偏见与歧视无关。而这些手持国旗的种族主义者,大多是存在极为严重的偏见,坚持白人至上,并长期敌视外来移民,甚至蔑视世界上其他一切文明。美国的3k党、欧洲的光头党、新纳粹主义者等也常常高举国旗,可掩盖不了其犯罪事实,爱国只是这些流氓的最后遮羞布而已。因此,旗帜的符指过程也受到了符号主体的影响,同一面旗帜可以画在球迷的脸上为本国球队呐喊助威,也可以攥在西方极端民族主义的手里成为其排外的利器。
四、结语
旗帜学(vexillology)以它的历史、演变、设计、象征意义为研究对象[18],从正式获名以来,旗帜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内容越发丰富,跨越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心理学、绘画设计等众多学科。其发展隶属专门史或人类学的范畴;象征意义与功能涉及社会学与心理学;图形与样式多是美学与设计内容。旗帜学研究在经历了初期热烈之后,现如今出现乏力之势头,原因有二:一是关注点的不同使研究内容彼此隔阂,很难形成串联达成统一理论;二是虽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但研究目的不清晰,方法不统一。旗帜研究之重点应为旗帜之表意,也就是旗帜的符指过程,也唯有符号学解开旗帜在实际运用中的种种迷局。因此,从符号学的角度研究旗帜甚为必要,也有待进一步深入。
当今世界旗帜的使用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广泛,其设计、使用及意义表达越来越全球化,作为一项工具,既可以用来增进集体的凝聚力与荣誉感,也可以被用来宣泄仇恨与排外。在天灾来临时可以振奋人心,鼓励人类前行;在动荡时期也可成为部分人施暴作恶,掩饰罪行的外衣。因此,有必要关注这一符号现象,研究其在符指过程中的一般规律,规范相应符号行为,发挥其积极的符号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