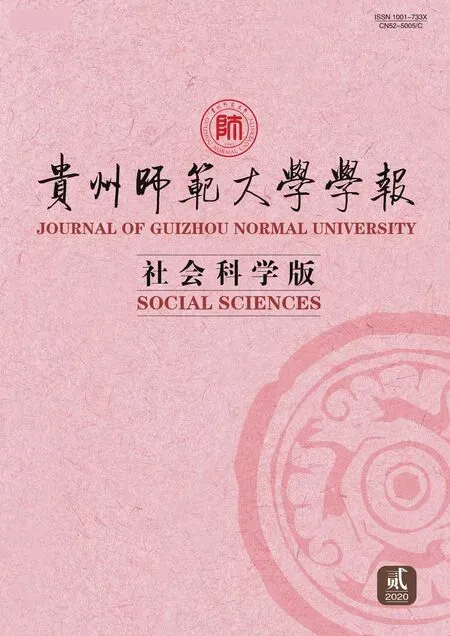借鉴、改写与加工:变异学视野下布莱希特作品中的“中国书写与想象”研究
2020-03-16菅娜娜
菅娜娜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1756)
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又译为贝托尔德·布莱希特,1898-1956),作为德国知名的剧作家,他与同时代驰骋于东方王国的伟大作家黑塞一样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古典哲学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在布莱希特的作品里大量浮现中国形象、中国主题和中国元素,这种有关中国的书写与表达,既包括有现实依据的对中国文化与智慧的主动借鉴与改写,又必然包含某种没有事实联系的异域想象与创造性加工的成分,笔者把布莱希特的这种书写界定为“中国书写与想象”。不可否认,无论是基于现实书写还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布莱希特笔下有关中国元素与题材的文学创作必然会因为中德两种异质文化在碰撞交流融合而产生诸多变异现象。正如曹顺庆提出:“当我们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投向不同的文明体系中的文学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除了一些基本的文学原则大致相同外,更多的是异质性的文学表现和面对同一文学对象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学表达形式或观念的变异[1]。因而,这种变异性才是应该关注的问题所在。
变异学是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作为一种专业术语,理论层面的真正提出是在2005年曹顺庆的《比较文学学》一书中:“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将变异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探究文学现象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2]此后,曹顺庆通过一系列学术论文和著作不断推广和丰富“变异学”概念。而2014年3月英文版《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f World Literature)则标志着曹顺庆变异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总结。此书除了指出跨国、跨语际、跨文学文本、跨文化、跨文明变异这几个层面之外还进一步修订完善变异学的定义:比较文学变异学是以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文学现象在交流中呈现出的变异状态、没有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的变异研究,以及对同一个主题范畴在文学表达上存在的异质性和变异性展开的比较研究,以探究文学现象内在的差异和变异的规律。”[3]这一定义强调无论有无事实联系,在文学交流传播与接受的过程都会发生变异,从而进一步为变异学研究扩大领域,提供更可靠的合法性。
通过对布莱希特作品的梳理和创作思想的把握,变异具体可分为三个维度:一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借鉴与运用;二是中国传统戏剧理论与戏剧题材的挪用与改写;三是中国经典老子形象的创造性想象与加工。从这三个维度可以对这位“说德语的中国人”[4]有关中国文化的接受情况进行一番更为细致的研究和评价,同时从变异学角度考量出“文化接触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问题,它们日益呈现为复杂的认识论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 。”[5]
一、 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借鉴与挪用
在布莱希特的青年时代,恰逢德国卫礼贤(原名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1873-1930)以及弗朗兹库恩(Franz Kuhn,1884-1961)等德国汉学家大量译著中国典籍,《易经》《道德经》《论语》《庄子》《孟子》《墨子》等纷纷翻译成德文出版,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在德国知识分子阶层引起广泛兴趣。而在其中年以及创作时代,同时代的克拉邦德(Alfred Henschke Klabund,1890-1928)、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德布林(Alfred Doeblin,1878-1957)以及埃伦施泰因(Albert Ehrenstein,1886-1950)均在翻译、变异或者创作中融入中国古典思想等中国元素,同为德国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布莱希特不可能不关注。有关考证指出,布莱希特最早接触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是道家,早在1920年他就阅读过深受道家无为思想浸润的德布林小说《王伦三跳》。同年,他又在友人瓦尔绍尔(Frank Warschauer)处见识了德译本《德道经》,并且留下“‘他向我介绍了老子。他同我如此相似。这使他惊讶不已。’这表明此时的布莱希特已感到自己与老子思想的亲和之处。”[6]154对于庄子,布莱希特也较为熟悉卫礼贤翻译的《庄子》与《南华经》并且还留下过一篇短评。布莱希特“不仅就其中的个别母题进行处理,还对庄子清净无为的哲学做过深入的探讨。”[7]281除此以外,墨子的倡导变革的主张及其学说的平民色彩也得到布莱希特的赏识,所以他才会托“墨子”之名写出《成语录》一书。就是对于孔子,布莱希特也有所关注。
当然,这些人之中,真正进入布莱希特的创作层面发生影响的主要是老庄。众所周知,老庄之学的核心也是对中国影响最深的是“心斋坐忘”“冥思玄想”“清静无为”的出世隐逸道家思想,但这些并没有进入布莱希特的中国想象与创作之中,相反,布莱希特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入世倾向,并且在创作的后期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就决定了布莱希特在接受中国传统的古典哲学思想时必然会有所选择、过滤、加工再创造。正如顾彬指出,在异质文化与文明的语境下,“异”首先是本质性的差异展现,是彰显自我与他者之间区分的一种方式,其次也表示“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衡量自己所不了解的人、事、地点等。”[8]所以,对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布莱希特倾向于对老子“柔弱刚强”之辩证法进行借鉴吸收,对庄子“招木近伐”“无用之用”等寓言与典故进行创造性挪用。
布莱希特对老子思想最突出的借鉴与吸收表现在他对“强弱之辩”这一辩证思想的灵活运用上。在他那篇1938年流亡途中所写的的长诗《老子西出关着道德经的传奇》中特别强调道:“弱水经久的运动,终会使强大的石头屈从。强者驯服,这点你懂。”[7]284“弱水”这一意象实际上在表述老子“柔弱胜刚强”的道理,这种思想可以在《老子》第78章指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以及第76章也明确指出“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的辩证处世哲学思想可以窥见一二。在同一年,布莱希特写下了《伽利略传》,书中借伽利略之口也表露了“我弱的时候,正是我强的时候。”[9]120布莱希特希望通过对老子“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的处世哲学来最终实现个体的欲望追求以及命运转变,这种强烈的入世意识,是布莱希特只选择摘取老子“柔弱刚强”之辩证法的根本分歧所在。这种分歧,也使得布莱希特后期逐渐流露出对庄子哲学的怀疑:“我也很想把智者做,古书中将智慧如此说,世间纷争莫纠缠,此生短暂应安过。不恃强权,以德报怨。无所谋求,一无烦忧。这是何等的睿智,我却不能将它拥有。真的,我生活的年代实在腐朽!”[7]291故此,乐黛云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借鉴与挪用“都是为了寻找一个外在于与自己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审视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但要真正的‘外在于自己’并不容易。人,几乎不可能完全脱离自身的处境和文化框架,关于‘异域’和‘他者’的研究也往往决定于研究者自身所在国的处境和条件。”[10]
对于庄子,布莱希特则通过创造性挪用“招木近伐”这一典故来表达他对庄子思想的理解和借鉴。《庄子外篇·山木》中记载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而伐木者却因“无所可用”放弃砍伐,故而庄子指出:“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同时,在《庄子·人间世》中也提及有用的木材最终“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1)经考证,“招木近伐”这一成语实际源于《墨子·亲士》:“甘井近竭,招木近伐。”即越甜的井水,人们越喜欢喝,所以越容易枯竭,太高大的树木,因为用处多自然容易被砍伐掉。布莱希特对于“招木近伐”这一故事的吸收应该并没有考证实际出处,而是在德译本《庄子》中有所了解并直接进行“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布莱希特对这种典型的中国传统的“材之患”、“无用之用”辩证法思想情有独钟,并且在创作中把这种处世哲学穿插于他所创造的戏剧文本《四川好人》以及《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之中。《四川好人》故事背景设于中国四川,布莱希特并没有来过此处,很显然这一地点的选择更多的是他对中国的想象性异域描写。剧中烟花女子沈德虽然因为其“材”——善良得到神仙的资助逐渐摆脱贫穷,但是沈黛的人生际遇转变却招来了邻居以及亲戚贪婪的垂涎,因而也为沈德招来了无尽的烦恼,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沈黛只好每个月扮演一次坏人出现。最后,神仙发现太过善良就会招来恶人的嫉妒和贪婪,就像有用的木材最终会被砍去,流露出“材之患”的思想痕迹。同时,本剧还流露出一种哲思层面的辩证性——道德的“两重性”以及悖论“好人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而不受腐蚀是不可能的。”[11]244
最后,“无用之用”这一辩证思想的灵活化用则体现了布莱希特对老庄思想的综合借鉴与吸收。布莱希特所创作的另一剧本《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也同样是发生在民不聊生的战争时代,剧中的大胆妈妈的几个孩子个个健全有力,但是大胆妈妈却担心他们会因此招来祸患:“那些长得笔直挺秀的树木,它们常常被砍去当屋梁用,那些长得曲曲扭扭的树反而可以安安稳稳地欢度年华。有用的木材会被砍掉,有伤疤的脸反而会在战争年代活下来。”[12]349
庄子这种“材之患”“无用之用”的辩证思想在剧中随处可见:“不要太锋芒锋芒要遭殃”“越是在一个有道德的国家越是不需要有道德的人”[12]303等等。甚至在剧中结尾处还流露出一股庄子的消极避世的思想的暗流:“世界上所有的道德都是危险的,就像这支歌所证明的那样,人最好不要有什么道德,只要舒舒服服地过活。作为一个士兵,勇敢也一点用处也没有,还挨着饿,不如在家里做个胆小鬼。”[12]370
总之,通过这两部剧可以看出布莱希特对老庄哲学思想的借鉴与挪用真正用意是为了借中国智慧阐释本国焦虑,意即指出身处民不聊生、艰难疾苦、战火纷纷的乱世,沈德绝对的善是不可能实现的,大胆妈妈想要自己的孩子获得现世安稳的愿望也不可能成真,从而把此剧引入现实层面,以此展开对道德悖论的思考和现实生活的批判,这种现实性思考使得布莱希特多了些人道主义色彩而少了庄子的形而上的辩证哲学意味。当然,这种书写策略既是布莱希特对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创造性挪用,又是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有意选择。
二、中国传统戏剧题材的改写与移植
余匡复认为20世纪有三个对中国话剧界影响最大的人物:“20世纪是易卜生,20世纪40-50年代是斯坦尼拉夫斯基,20世纪70-90年代则是布莱希特。”[13]据此,韩国学者宋云耀指出:“布莱希特作为剧作家和诗人,简直可以称他为‘中国的布莱希特’。”[14]《高加索灰阑记》写成于美国,是布莱希特流亡期间所写的最后一部剧作,也是他所有戏剧创作中和中国关联最为紧密的一部作品。个中原因除了“在于把故事的核心赋予历史的色彩并使之成了戏中戏的;它还为重述“智戡灰阑记”这个中国古代民间传说提供了理由。”[11]245他本人还在剧本的楔子《山谷的争执》中明确指出故事来源于“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它叫《灰阑记》,从中国来的。”[9]257长久以来学术界多从故事的情节、母题、人物形象设定等和中国元杂剧家李行道的《包待智赚灰阑》以及同时代的戏剧家克拉邦德的《灰阑记》来进行对比研究,得出三者的异同以及彼此影响渊源,这实际仍属于影响研究的范畴,而很少从变异学的角度考察布莱希特所进行的创造性移植与改写。以知网为例,输入“变异学”和“布莱希特”进行检索,得出的相关研究论文为零,这无疑是学术界的一种盲视。
《高加索灰阑记》剧情发生在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高加索地区的两个农庄。牧羊农庄和苹果农庄就一个山谷的归属问题发生了争执。后经协商山谷一直以来的所有人将山谷让给苹果农庄经营。于是,苹果农庄的庄主请专门的歌手和演员演了一出五幕剧《灰阑记》来表达谢意。布莱希特却极其巧妙地采撷元杂剧的“灰阑断案”和“两母争一子”这一基本情节的戏剧化情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胆地挪用与改写,使得此剧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均展现出和原剧的迥然不同的异质性成分。在形式上,正如布莱希特自己在原文中指出的在“演出的形式方面也做了更动”[9]257,这主要是指布莱希特抛开原剧的简单呈现而采取剧中剧的戏剧结构,戏剧表演者在表演灰阑一剧的同时又镶嵌一个法官“灰阑断案”的剧情,这样既点名戏剧的主题,又使得戏剧结构浑然一体。内容上的移植与改写则主要通过陌生化的情节和人物形象,打破中国传统的思维定式和人物类型化设置。这些主要通过剧中的两个母亲形象及结局的陌生化处理、养母的戏剧化人生际遇、判官性格的复杂性及结局的出人意外得以体现。
李行道元杂剧是一部典型的道德教化剧,剧中的人物被分为善恶两类,生母张海棠代表弱势善良的化身,养母马大嫂代表凶悍恶毒的化身,判官包待制是公平正义的象征,最后的结局是善良战胜恶毒,生母最终获得孩子,这些都具有典型的类型化倾向。同时,这种结局也符合普遍的传统宗族伦理观:血浓于水,这种血缘关系更为真挚感人,生母是永恒的善的化身,所以最后孩子判给生母也符合中国人千年来的阅读期待与审美接受。但是布莱希特却一反常态,运用他最擅长的“陌生化”手法,把剧中的生母(总督夫人)塑造为一个阴险狡诈、嗜钱如命的恶毒夫人,而养母(格鲁雪)却是一个性情柔顺、具有同情心的善良母亲,“两个剧本中, 生母与生母、养母与养母,在身份和人格上, 都作了对称性置换。”[15]这一对称性置换既使得本剧取得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引起观众的惊叹和思考,同时又彰显了布莱希特的生命价值观与哲学思考:单纯的生物血缘关系不足以衡量母性,而真正的道德和质量才是更强大的纽带。由此得出:天赋的权利并不是绝对的,如果孩子的母亲没有对一个孩子该有的照顾和爱心,如果土地所有者没有能力耕种好自己的土地,那么,为了真正的公平,孩子和土地最终的归属应该重新分配:
但是《灰阑记》的听众,请记住古人的教训,一切善于对待的, 比如说孩子归慈爱的母亲, 为了成材成器,车辆归好车夫, 开起来顺利,山谷归灌溉人, 好让它开花结果[9]359。
布莱希特将孩子判给抚养孩子长大的善良养母而不是生母,将土地判给灌溉人而不是土地所有者,这一结局安排打破了我们的惯有的以血缘定亲伦的思维定式,也使得我们重新思考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彰显了公平与正义这些永恒的话题的意义之所在,使得原剧的道德教育化这一庸常情节获得了升华,收到了让人震撼的艺术效果。
《灰阑记》第二处最明显的改写是布莱希特别具匠心给养母格鲁雪安排了一场颇为荒唐滑稽的婚礼。格鲁雪的哥哥拉弗伦第为了让未婚却带有孩子的妹妹好过一些,就给她找了一个垂死的男人尤普索,并与之结婚。在婚礼当天,“新娘走进门,新郎要咽气”[9]303,新郎的母亲害怕媳妇没进门,儿子随时可能咽气,于是她请来和尚,为儿子同时准备了一场丧礼。由此让人啼笑皆非的戏剧情节出现了:婚礼和丧礼两种仪式这两种绝不兼容的仪式场景在当天同时出现,最具戏剧化的情节是在现场哀乐与欢曲同时进行时刻,本来奄奄一息的新郎尤普索忽然“活了”过来。原来之前为了躲避战争服役,他在病床上装病装死装了整整一年,突然的复活,震惊了在场所有的人,也包括观看戏剧的观众,这一接二连三的“神转折”陌生化剧情安排,既让观众感到在滑稽荒诞之余,又忍不住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现实,尤普索之所以装病不难联想到人们对当时的法西斯战争的厌恶及反感,读来颇具讽刺意味,所以布莱希特直接在剧中写道:“这出戏同我们的问题有联系。”[9]256这就是布莱希特通过陌生化效果给人们带来的思考上的火花——“滑稽因素和陌生化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在笑声中,有可能突然迸发出认识的火花。”[16]234
而第三处最明显的改写则是与元杂剧包待制对应的法官阿兹达克形象的塑造。首先,包待制是典型的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传统判官;是一个很明显被人民所理想化的包公形象;是权力统治阶级的正面化身;是绝对的正义符号象征者。而布莱希特笔下阿兹达克则全然相反:首先他是一个贫民代表,阿兹达克和格鲁雪都出身贫民,总督以及总督夫人则是富人阶级的化身,这两种阶级对立的设定使主题从原剧简单的家庭纠纷扩大到贫富阶级斗争的层面。其次,阿兹达克这一人物的内心与表面充满了反差:外貌庸俗卑怯、吝啬贪财,一副昏沉沉色眯眯的样子,但是内心清醒、慷慨仁慈、善良负有正义感。这一反差性形象的设定让观众对这一人物的评价产生迷惑,引发观众的自主思考,使得读者无法用单纯的善恶、好坏等典型的二元对立的价值体系来认知和评价他,从而使法官这一形象产生巨大的张力效果。
最后,布莱希特还通过阿兹达克传达一种独特的处世哲学:与其在乱世中若无其事地装作道德、伪装正义,还不如就随心所欲地生活,即使会被人认为庸俗贪婪和荒谬愚蠢,但是内心依然有善恶的尺度,正义的原则,所以即使格鲁雪在法庭上骂他,他也依然会把孩子判给她,并且判她和装死的丈夫离婚,使格鲁雪最终能和爱人西蒙·哈哈瓦在一起获得圆满结局。案子结束后,阿兹达克便消失了,这种结局安排颇具“老子出关”的隐世意味,也符合布莱希特在柏林剧团演出的在节目单上所写的“故事现在讲的是一种崭新的智慧,一种建立在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的处世态度。”[16]132由此可观,老子思想对布莱希特影响之深远。
三、中国经典老子形象的创造性想象与加工
布莱希特一直坚持以“间离化”手法改革戏剧,力图破除亚里士多德以来对“共鸣”的强调桎梏希望拉开戏剧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增加观众对戏剧感知的难度,延长感知的时间,从而被迫引起观众对戏剧以及其中所寓意的现实生活的反思。这一“间离化”的戏剧革命式的尝试,也使他不得不从思想到形式,从文本创作到经典形象塑造去关注陌生的、异质的文化与文学成分,此时的异域东方中国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思想上,他取法老庄,从他们身上吸取古老的东方辩证法智慧;创作上,他借鉴中国传统的戏剧题材进行创造性移植;形象上,布莱希特则把他对中国文化最热忱的关注投注在一个人身上,他就是老子。在布莱希特笔下,老子被想象与加工成虚怀若谷的智者形象、自身流亡经历的映照以及中国人的理想化身。
布莱希特对老子形象的创造性想象与加工首先是着重把老子塑造成一个“虚怀若谷”的智者形象。布莱希特对老子的关注最早是在其青年时代,但青年时代那次友人的介绍还只是浮光掠影,并没有在布莱希特的创作中留下太多涟漪。布莱希特并没有真正结交认识过老子,他对老子形象的塑造更多的是融入自己的想象而进行天马行空地勾勒,真正能体现布莱希特对老子的接受和关注是他两次对“老子西出函谷关”的描述,第一次是在1925年的一篇散文《礼貌的中国人》中称老子为智者,对老子出关的始末缘由进行简略记载,这篇散文对布莱希特影响深远,他从老子的个人经历以及哲学思想中均找到了契合点,并且念念不忘,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他会再次撰写这一题材,最具代表性的是第二次1938年流亡丹麦时所写的长诗《老子西出关着道德经的传奇》。[6]157当然,“老子西出函谷关”的故事并非布莱希特杜撰,因为在中国的典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就有简略记载: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去,莫知其所终[17]。
这个故事载于多个德译版本的《老子》,卫礼贤也翻译《史记》并把他原文译出,所以布莱希特不难接触到。最为可贵的是,布莱希特没有囿于原始材料,通过一诗一文两篇有关的叙述,对这段老子出关故事以及老子的形象进行创造性想象与加工(2)这两篇文本的中文译本,均可在卫茂平的《异域的召唤》与《中外文学交流史 中国德国卷》一书中找到,此处不再赘述。。布莱希特在诗中举言必称“大师”“智者”,侧重把老子塑造为一个虚怀若谷的智者形象,同时函谷关令尹处处对老子表达尊重崇敬之意。
其次,在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术语中,任何“他者”都是一种“自我”的投射和映照,布莱希特对老子的关注与倾心是因为他在这个异域的东方智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布莱希特跨越时空的距离,带着长达15年放逐流亡的切身经历和老子相遇,他将“老子西出函谷关”传奇先后演化成散文和长诗,更像是反思自身的流亡生涯和经历。故此,不难推测布莱希特其实是借老子的智者形象和所受到的尊崇来表达对当局社会政治对文人知识分子的迫害的反讽和不满。所以形象学家达尼埃尔-亨利·巴柔(Daniel-Henry Barrow)指出:“形象就是一种对他者的翻译,同时也是一种自我翻译。”[18]长诗中,布莱希特还给老子添加了一头牛作为坐骑,一个牧童作为代笔人,全诗采用问答的形式,读来闲适自然,妙趣横生。这种诗风和原文中老子对现实的失意和不满而无奈选择西出函谷关的落寞感相去甚远。卫茂平认为这“虽属艺术加工,倒也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6]157同时,诗中老子出关所带的行囊中放置的:烟斗、白面包均是欧洲特产,而绝不可能是“中国的老子”所会带的东西,结合布莱希特流亡的真实生活现实,烟斗不离手,白面包入口。可以看出,布莱希特表面上是在刻画“老子出关”的故事,实际上却是将自己隐身于老子形象背后,而这首诗歌对“老子出关”的传奇化演绎也正是他反思自身流亡经历的结果。”[19]
最后,布莱希特还通过老子的这篇隐世的故事表达了他对中国人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人是礼貌的,并且一生都在奉行老子哲学作为处世准则——“据我所知,礼貌的中国人对他们伟大的智者老子的敬仰远胜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对他们师长的尊敬。”[7]286然而,事实上老子西出函谷关真正的原因恰是因为周王室的衰微,礼崩乐坏人心不古,而作为一个整理书籍周王朝的小史官,老子生前也没有像孔子那样得到世人的敬仰,甚至关于老子的正史记载也仅见于《史记》一书略带提及,由此观之,布莱希特认为中国人尊重智者,渴望真理,这些美好的品性这种叙述多半是建立在个人想象的基础之上,以此来表达他对中国“礼仪之邦”以及“尊师重道”这一美好品行的向往。所以,异国形象的塑造的真正问题和价值不是在于和本土国家的真实形象像还是不像,而是在于创作者怎样进行为我所用的加工和创作,因为它已经与创作主体的“自我”的社会集体想象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社会、一种思想或一个价值体系的一种映射[20]。
四、结语
哲学上取法中国先贤哲人的辩证法思想,创作上借鉴中国传统的戏剧题材,人物上塑造加工中国经典老子形象,这三种方式互为表里,共同体现了布莱希特对中国智慧的礼巡,对中国文化的整体“书写与想象”。从接受学的角度看,这是接受者基于本国的现实需要及个人趣味来处理他国的思想、文化,而不一定是真正认识到他国的文化价值。简言之,这是一种“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文化阐释策略。但是,从变异学的角度上看,这是一种积极的文学创作实践,也是一种促进异域文化交流的有益实践方式。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正是基于变异学基础上文学交流与实践,才使得一个民族之思想哲学、艺术文本、经典形象被世界接受、阅读、再创造而成为世界性的,才能最终为世界文学时代的真正到来描绘出可行性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