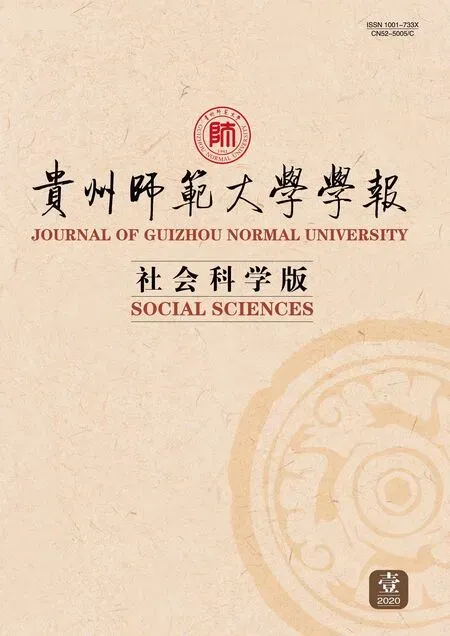肖江虹小说《傩面》中的魔幻叙事
2020-03-15余钢
余 钢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
肖江虹是贵州青年作家,1976年生于贵州省修文县,于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最早写小小说,后又学习写短篇小说,其2016年创作的小说《傩面》是作者“民俗民风三部曲”(《蛊镇》《悬棺》《傩面》)中的一部,并且属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范畴。2018年《傩面》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肖江虹立足于民间传统文化、着眼于贵州古老而质朴的民俗风情进行小说《傩面》的创作,纯熟的地域文化营养与独特的民间傩戏文化土壤给予了作家丰富的创作动力与写作灵感。小说《傩面》运用魔幻叙事的表现手法,讲述了傩村最后一个傩面师的死亡,反映出贵州边地独特的民俗文化景观和传统文化崩塌过程中的世道人心。在小说《傩面》中,无论是对傩面师秦安顺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对神秘傩文化的描写,无不打上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烙印,并且营造出含蓄而又深厚的传统民俗文化氛围。
一、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对小说《傩面》的影响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20世纪50、60年代在拉丁美洲兴盛起来的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它在拉美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欧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其最大的特征是“变现实为幻想而不失其真”。这一流派的作家既坚持在小说内容上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原则,又强调在小说创作方法上运用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引入大量超自然因素,使小说呈现出“幻化的现实”与“现实的幻化”的特点,这种把现实与幻景融为一体的创作方法,拉丁美洲的评论家称它为“魔幻现实主义”。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魔幻现实主义”这一词有着绝对重要的分量,给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之后墨痕日渐淡化,但它却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90年代乃至以后中国小说的创作。但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够影响中国当代小说界的创作并大行其道绝非偶然,主要因素有两个:第一个因素是中国文化传统与拉丁美洲文化传统有共通之处。中国文学早在《山海经》里就存在着神话传说故事,而无论是魏晋还是明清时期,中国志怪小说里描写鬼神精怪或奇人异事的传说更是多不胜数,这与拉丁美洲文学作品里常出现一些关于巫术文化、鬼神信仰的描写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第二个因素是十年“文革”给当时的中国文坛造成的影响与后果抑制了小说的创作活力。于是在这一大时代背景下,作家们纷纷学习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力图冲破单一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模式,积极探求新的小说创作方法。1982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成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传入中国文坛的重要契机,在此之后的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显现出浓烈的 “马尔克斯症候”,一大批优秀的作家纷纷学习并“模仿”马尔克斯。莫言、扎西达娃、韩少功和贾平凹等作家都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这足以说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对中国小说界的影响之巨大。在“马尔克斯症候”热潮期间,中国文坛上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寻根文学作家在小说的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上都存在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从具体作家来看,扎西达娃、韩少功、贾平凹、莫言、阎连科、范稳等作家都深受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其中莫言的“感觉魔幻”与“鬼神精怪魔幻”、扎西达娃的“宗教魔幻”以及范稳的“神灵现实魔幻”[1],都是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运用到民族文化当中的成熟典范。
肖江虹的小说《傩面》是继《蛊镇》后的一部作品,2017年4月28日,《傩面》获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小说奖’主奖”,组委会给出的获奖评语是“采用民俗叙事路径,记述了最后一个傩面师之死,反映了贵州边地独特的文化民俗景观和传统崩塌过程中的世道人心。作家采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让时间流转,使先人的往生与现实的观照完美融合,达到了珍视生命而又溢出现实的艺术效果。”这说明作家肖江虹的创作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那么作家肖江虹是怎样受其影响的呢?或许我们可以从文学评论家李云雷先生发表的微博《“多面手”肖江虹》中找到一些答案:肖江虹曾在访谈中坦言“早年读马原、余华、孙甘露这些人,对他们的技巧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读了卡夫卡、博尔赫斯、乔纳森·科伊这些人后,不禁哑然失笑。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这代作家大部分从先锋小说那里学会了技巧,然后又开始有意识地反技巧。其实在这个承接和抗拒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应该还是奠定了我们对小说‘艺术性’牢固的理念。这大概就是70后作家走不了市场的原因。我觉得一个成熟的小说作者,技巧是一种内化掉的东西,它应该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刻意在技巧上发力,弄一堆似是而非的东西,终归还是花架子。”[2]并且肖江虹曾是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当时给他上课的著名作家中就有写作魔幻现实主义的莫言。诚然,一个作家的成长总是与文学的熏染和其他作家的影响有关,著名作家林语堂就这两方关系做了精彩、形象的比方:“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喜爱的作家,即等于一个飘荡的灵魂。他始终是一个不成胎的卵子,不结子的雄蕊。所喜爱的作家或文学爱人,就是他的灵魂的花粉。”[3]这些事实都表明了肖江虹的确是受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熏染,但就肖江虹本人而言,无论是在吸收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还是在学习中国其他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风格上,他并不是一味地照搬,而是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再加上神奇而丰富的贵州民间传统文化提供的创作源泉,才促使他创造出了全新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傩面》。
二、《傩面》中魔幻叙事的具体表现
在小说《傩面》中,无论是傩面师秦安顺形象的塑造,还是打破生与死、人与鬼神的叙事手法,或是小说里所体现的独具匠心的时间叙事和神话叙事,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对其创作的影响。
(一)人物形象的魔幻性
对小说而言,人物形象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乃至灵魂成分,如何描写、刻画人物形象,描写、刻画怎样的人物形象是小说的重要任务之一,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也是如此,成功地塑造一个富有魔幻色彩的人物形象往往能够更好地为小说营造出某种魔幻效果。
小说《傩面》中,老人秦安顺是傩村最后一个傩面师,是乡村世界最后的守护者。这一带有神奇色彩的巫师形象,为小说营造出了一种魔幻氛围。傩面师本身就是不平凡之人,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他掌握着沟通天地鬼神、连接阴阳两界的神奇力量,如小说中写道,秦安顺作为傩村最后一位傩面师,担任着为过世者指引黄泉路的重任,德平祖去世时,他戴上傩戏面具成为引路灵童,不仅看见了德平祖的鬼魂,还与其对话,给死去的鬼魂指路。小说中的人物秦安顺与鬼神对话的神奇事件在《傩面》中已经不是新鲜玩意了:德平祖头七之时傩面师按照规定要给死者唱一出“离别傩”,由傩面师幻化成的灵官带领着鬼魂与亲朋作人世间最后的告别,帮助他们了却前尘往事。
除了能化身各路神灵与鬼魂对话交流之外,秦安顺也有其他通天本领,小说中的另一位主人公颜素容因不甘忍受傩村的闭塞和家乡的贫穷外出打工患了绝症,在万念俱灰后从城里回到傩村等待着自己的死亡,她因绝望而变得对人乖戾,还试图以自暴自弃的方式自绝于世,却被秦安顺救了下来,颜素容虽然不相信傩戏的释罪消怨的功能,但是还想要傩面师秦安顺给自己唱一出“延寿傩”,而要唱“延寿傩”,先要唱一出“解结傩”,以求消罪解结。然而颜素容不肯说出犯忌何事,却要求“把能想到的罪名都安上”。秦安顺写了“解结牒”,请出傩中之王伏羲神,号令翻冤童子和延寿仙姑,“移文换案,以求释罪消怨”。虽当夜只见着翻冤童子,不见了延寿仙姑,翻冤童子带回的神谕是“罪怨消,寿已尽”,不能两全,颜素容却又“真信”了,“居然相信了秦安顺能通过面具看到另外一个世界”[6]36,体现了秦安顺能替人消罪延寿的本事。除此之外,秦安顺戴上傩面具后更是具有了穿越时空壁垒的能力,本是早已不可得知的前尘旧事,因为傩神附体的神秘仪式,傩面师得以用另一种视角看到了父母从相遇、相知到相守的过程,并且在最后一次戴上伏羲面具后回到了自己刚出生之时,傩面师平凡而又伟大的前世今生,在伏羲傩面具后于死亡和诞生的瞬间完成了对接,其人、其事,实在是奇哉、怪哉。傩面带着秦安顺穿越了自己的生与死,最后安然走向死亡。
作者通过塑造傩面师秦安顺这一充满魔幻色彩的人物形象,在一张张神奇的傩戏面具背后,看到的是贵州边地独特的巫傩文化,感受到的是傩面师乐观淡泊而又珍视生命的人生观。
(二)叙事手法的魔幻性:打破生与死、人与鬼/神的界限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在书写现实、反映现实方面运用魔幻叙事手法,体现出了陌生化的艺术处理方式和奇幻的艺术效果。从艺术手法来看,中外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常见的手法有夸张、荒诞、象征、变形、打破生死界限等,在这一系列叙事手法中,陈光孚先生认为:“‘打破了生与死、人与鬼的界限’和鬼魂描写”是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一大体现,成为魔幻叙事的一种常见的表达方式[4]。在小说《傩面》中,其艺术手法最多的体现在打破生死界限和人与鬼神的界限。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自古有人鬼殊途、阴阳两隔的说法,意为活人与死者不可处于同一时空,但《傩面》中的傩面师秦安顺却可以凭借傩戏面具穿越时空壁垒到达鬼魂所在之地。小说中,本是活在现实世界的傩面师秦安顺戴上傩戏面具就能去往属于鬼魂的空间并且与其对话,指引道路;唱离别傩时,又化为灵官带领鬼魂与亲人告别,幻游一般经历了人间与神界的穿越。傩面师多次以“活者”的身份与“死者”鬼魂进行对话的行为,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生死界限,使小说达到幻化的现实与现实的幻化的魔幻效果。
《傩面》里除了打破生死界限之外,还有打破人与鬼神界限的描写。如上文所言,小说中多次写到秦安顺戴上傩戏面具后化身成为傩面具所代表的鬼神,并行使其义务与权利,他以一介凡身在鬼与神这两重身份中来回变换,人、鬼、神三者之间的身份界限早已模糊甚至被打破。小说有一次说秦安顺在午后自家院子里雕刻灵官傩面具,困意恼人,眼睛刚闭上他就被两个一般高矮的黑袍人带走,猜是判官来了,这便有了死的准备,并于此时看见了年轻时候的父母亲故与一场“归乡傩”,而唱傩戏的傩面师脸上的木刻面具更是在火光中开始慢慢软化、流淌,最后和脸孔融为一体,泛着黑色的油光。更为神奇的是在他醒来后,看见水缸里自己的样子变成了自己所雕刻的灵官傩面具的模样;傩面师秦安顺戴上伏羲傩戏面具后已然化身成为傩神,指挥着天兵天将在云端上为守护傩村排兵布阵。作者将现实世界与鬼神世界混为一体,沟通了人与鬼神二者之间的关系,以魔幻的笔墨写出了傩面师的现实生活和傩戏面具背后所存在的神秘维度。
(三)时间的游戏:时间叙事
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认为,时间在整个小说艺术形式的创造中通常处于核心的位置[5]。于魔幻主义小说而言,如何创造时间叙事模式已成为小说中的一门艺术,作家们手艺的好坏常常成为评价小说优劣的标杆,诸如马尔克斯和胡安·鲁尔福这些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小说中所建构的“循环时间”模式、“非时间”模式,都证明了他们是真正的时间游戏的高手,正是作家们将自己独特的时间叙事模式运用到其作品当中,才使得他们的小说充满了魔幻色彩,同时显示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在其小说时间模式的构建方面的独特性。小说《傩面》也是如此,时间叙事模式于肖江虹而言是组成小说魔幻叙事结构必不可少的重要成分之一,他将上文所说的“循环时间”模式与“非时间模式”与贵州边地独特的巫傩民俗文化结合起来,并以此为基础重构出属于《傩面》的独特的时间叙事模式,并把它成熟地运用于小说之中,使小说充满了魔幻色彩。
首先,循环时间模式对于我们来说并非完全陌生,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本就有永恒轮回的时间观念。如名著《三国演义》中那句勘透天下局势与世情的至理名言:“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再如中国人的八卦阴阳轮回时间观,这都是一种循环的时间模式雏形。
肖江虹小说《傩面》的循环时间结构正是借鉴了马尔克斯的“循环时间”叙事与中国的轮回时间观,将二者融为一体,并加以现代性的发掘与重构。在《傩面》这篇小说中,作者始终围绕傩面师秦安顺这一具有魔幻色彩的主人公,精心设计了一个圆形时间结构:傩面师个人的生死轮回就是如此,已经接近死亡边缘的傩面师秦安顺戴上傩面具后,先后看见了父母相亲、拿话(提亲)、结婚、怀孕、生子的情景,在临死之时他又套上伏羲傩面,便回到了母亲即将临产之时,“接着是一声清脆的啼哭”,现实中的秦安顺“脑袋一歪。万籁俱寂。”[6]37这时秦安顺的前世今生在伏羲面具后于死亡和诞生的瞬间完成了对接,“终”是“始”的开端,“始”是“终”的结束,这一番从终点直接起点再向终点正叙的回环中,贯穿着秦安顺对生的珍视和向死的从容,最后一位傩面师因生无怕惧而死无怕惧。时间在秦安顺生命的逆向运动中形成了类似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式的循环时间模式。扩展来说,如果我们将秦安顺现世经历看成是现在时的话,那么在秦安顺套上傩面具后看到的便是过去时,而秦安顺透过面具获得离世的预兆则是将来时,是站在过去的时空预叙“未来”,“过去——现在——将来”在这一逆向运动中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时间性圆圈;在小说结尾,颜素容在秦安顺死后拿起他留下的伏羲面具,慢慢套在脸上,瞬间“天光一下煞白,落日的余晖从窗户挤进来”,她听到屋外一个声音在喊:“颜素容,你个砍脑壳的,天都黑了,还不回家吃饭!”[6]37而小说第3节分明写到颜素容在刚进村看到自家房子的瞬间,耳畔自动想起她母亲高亢明亮的喊声“颜素容,你个砍脑壳的,天都黑了,还不回家吃饭!”,“震得远处的落日都跟着抖。”[6]也就是说,在颜素容慢慢地把乌黑的伏羲傩面戴到脸上,幻觉中传来的,是童年时母亲的呼唤,由此形成了另一个生命轮回圈;最后,如果我们将秦安顺的死亡视为傩戏民俗的终结,那么在颜素容套上面具回到过去的瞬间,傩戏也由死转生,此又是一个轮回圈。三个“圆圈” 构成了《傩面》的循环时间模式。
其次,《傩面》的时间叙事模式还体现在对胡安·鲁尔福“非时间”的时间模式的借鉴与重构上。胡安·鲁尔福“非时间”时间模式是一种无时之时,它拆除一切时间壁垒,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自由交叉穿梭。自然时序被分割成无数碎片,重组和拼贴时间碎片而形成自由的时间文本结构[7]。小说《傩面》借由秦安顺傩面师的特殊身份使得这一时间模式的实现成为可能:小说中的时间链条讲述的是傩面师秦安顺死亡的故事,但是小说在时间叙事上完全打破了传统的线性自然时序,链条与链条之间能够自由地组合。在小说中,秦安顺多次套上伏羲傩面,早已应该成为往事的父母年轻时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却历历在目,傩面师犹如旁观者般见证了先人的往生,并且在小说第17节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新婚不久母亲怀孕了,怀孕三月后“三婶”给母亲摸胎,而秦安顺就在她们看不见的旁边站着,突然“咯噔一下”明白了,自己就在母亲的肚子里。还有,有那么一刻,母亲突然抬起头,眼光朝秦安顺所站位置扫了过去,而且做了“异常短暂的停留”,于是“他坚信,就在那一刻,母亲肯定看见了他。”[6]9这说明在某一时刻里秦安顺的时间壁垒已被打破,“不同时空在那一瞬被接通了”[6]35,过去与现在这两个不同的时空维度在神奇的傩戏面具的作用下被接通了,我们看见了傩村最后一位傩戏师肉身的孤独和灵魂的富有,以及在生命的末尾内心的坦然和宁静。肖江虹笔下《傩面》中的时序并非是以自然线性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反而是像拼图一样被切分开来,成为许多 “时间碎片”,这些“碎片”经由作者重新拼接组合,使得小说中的时间结构形成了一种自由而且乱中有序的形式,并且由于自然时间结构的打乱与重组,小说《傩面》的人物傩面师也就能够从容地在事实与梦幻、人与鬼、生与死、过去与现在之间自由地来回交叉穿梭,时间在这里既是叙事对象,同时也是叙事手段。
(四)神奇的现实:神话叙事
何为神话叙事?神话叙事主要体现为对历史与现实加以神话式的处理,对民族社会与文化进行模拟性重构或者虚构,以及在叙事的过程中引入大量的神话、传说[8]。贵州边远古老的村庄存留着原始、诡异、神秘的自然景象,蕴藏着丰富、悠久的神秘仪式和神话传说,肖江虹借用神话叙事来表现小说《傩面》中所描绘的神奇现实,反映了神秘村庄存留的传统民俗的崩塌与消亡。
小说《傩面》中所描写的傩村是一个神秘村庄,这个村庄常年弥漫着浓稠的雾气,一年中有半年时间都在雾中,“傩村有半年在雾中。浓稠的雾气,从一月弥漫到五月,只有春夏之交为数不多的日子,阳光才会朗照。”[6]35巴掌大的地方爬过百岁的寿星就有六七个,作者将傩村借以这般神话叙事的描写,更显出傩村的神秘、传奇,而傩村作为小说人物的活动领地,在这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披有一层魔幻色彩的外衣,通过描写这些人看似荒诞不稽而又显得真实可信的日常生活,使得小说充满神话色彩:傩面师秦安顺没戴上傩戏面具之前只是一个平常老头,面具甫一上脸,立时化身各路神灵,并且具有自由穿梭于过去、现在的能力;文中的三婶也并非凡人,传说她有一天梦见药王菩萨,菩萨传给她治病救人的本领,第二天翻身下床就成了傩村的赤脚医生了;耄耋老人平素近乎痴人,分不清辈分,误把孙辈认作自个爹,但只要将傩戏面具往脸上一罩,天地立时澄明,唱词精准到位“东头居首的刚才还垂死般,面具甫一套上,手掌上举,把面具摩挲一遍,就知道自己的角色了。‘呔,土地老儿来也!’一声恶吼,老眼猛地一睁,刚才还混沌的眼神瞬间清澈透亮。”[6]4小说还包含着大量的神鬼事物和神秘气氛:死亡将至的秦安顺头顶上时常盘旋着一群乌鸦;倒给孤魂野鬼的饭菜一定要反手泼出,鬼魂才能收到;认为人死了会去往另一个地方,但路径不熟,得由引路灵童指引着走。小说中还出现了许多神鬼,例如伏羲、灵官、引路灵童、延寿仙姑等等,他们各司其职,掌管着世间万事万物。
诸如此类的传奇事件在小说中随处可寻,所有这些描绘出贵州边地古老而神秘的世界,神话与现实、巫傩民俗与风土民情相交融,亦真亦幻,神秘而荒诞,神奇而真实。这便也赋予了《傩面》神话般的非凡意义。
三、小说《傩面》中魔幻叙事的价值意义
作家肖江虹在创作小说《傩面》时努力寻求打破常规写作的模式,将魔幻叙事手法纳入小说创作当中,《傩面》的成功,最大的功臣也应当是其独特的魔幻叙事手法。小说《傩面》中的“魔幻叙事”绝不是徒有其表、披在文学作品上的花花外衣或作家故弄玄虚的噱头,而是一种标新立异和开拓创新,亦是作家通过魔幻叙事揭示民族神奇现实的手段,更是对魔幻表象背后隐藏的原始宗教、民族心理的深层次的思考。《傩面》中魔幻叙事的运用不仅是写作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必要手段,而且是丰富小说文化的内涵、体现小说文学价值的重要方式。
(一)《傩面》中魔幻叙事的文化价值:对贵州民间巫傩文化的开掘与关注
文学与文化并非两个毫不相干的领域,两者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是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积极关系。从包含关系上看,文化可视为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包含有文学,也就是说文学与文化之间存在着部分与整体之间的重合。文学作为一种文化信息与意义的载体,呈现或折射出文化的色彩。小说《傩面》作为文学作品,其魔幻叙事的文化价值最先体现在对民间巫傩文化(这里指傩戏唱词和傩戏面具)的关注与开掘上。韩少功提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9]。肖江虹注意到了贵州边地独特的巫傩文化,他说:“《傩面》这个小说,我写得很辛苦,前前后后写了两年。这部中篇小说光前期田野调查就做了六七万字,比小说字数还多。特别是小说中涉及到的大量傩戏唱词,都是傩面师唱一句我记一句,很多段落还得重新加工和梳理[10]。”在小说《傩面》中有大量的傩戏唱词,几乎每一出傩戏都有独立的唱词,并且有自己所独有的神奇用处,例如:专为归乡的游子和远征结束后返乡的士兵而跳的“归乡傩”:
一炷檀香两头燃,下接万物上接天,土地今日受请托,接引游子把家还。桃木剑指阴角处,妖魔鬼邪避两边, 口中吐火吞瘟癀,泥中奋出紫青莲[6]。
傩村有个说法,人远涉江湖,难免撞见不吉利的东西,这些东西会依附在人身上,慢慢吞掉人的灵魂,跳“归乡傩”能起驱邪除怪的作用,人死后的头七鬼魂会回来与亲人作最后的告别,傩面师会在坟前唱一出傩,化身成的灵官会告诉他们,故去的人去了哪里,这就是“离别傩”:
生离死别;连绵不绝;两眼一闭;阴阳两隔;眷恋凡间;临别掩泣;灵官驾到;听个真切;从此别后;无声无息[6]。
另外还有小说《傩面》中秦安顺为颜素容唱“解结傩”和“延寿傩”中的唱词等等,这些傩戏唱词都为我们留下了对贵州巫傩文化的了解的佐证。
除了傩戏唱词外,傩戏面具于巫傩仪式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民俗道具,在小说《傩面》中,傩戏面具已非普通面具,它代表着宗教与民俗,同时它不仅是神灵的象征和载体,更是通向生命“澄明之境”的通道。小说第一节就有对傩戏面具的具体制作原则的描写:首先,在选材上就不能马虎,傩面师秦安顺所雕刻的谷神面具选用的就是上了年岁的核桃木,最少五十年以上,只有这样神灵才容易附上面具;其次,面具动刀之前还有个仪式,得念上一段“怕惧咒”,这是为防止在雕刻时出现差错,“毁了面具是小事,神灵散去了就是大不敬了。所以下刀之前得有个说明,傩面师管这个叫礼多神不怪。”[6]18
小说《傩面》这些对巫傩文化事象的描写,不仅为后来的作家创作巫傩文化书写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可行性,而且作品本身也极具民俗学研究价值;除此之外,作者肖江虹也对现代理性引发的各种生活方式不断侵蚀着古老的民俗文化进行了反思,如今的傩村,傩面变成了商品,村长的儿子梁兴富将傩面变为生财之道,不相信傩面具后头有鬼神,并对秦安顺的傩戏嗤之以鼻。傩村人“脚跟脚的往城里跑”,傩戏已是“垂死的家什”,傩戏面具成了用不上的“破烂货”,随着最后一位傩面师秦安顺的离世,他的两个儿子毫无痛惜地将其留下的傩戏面具给烧了,“留着也没啥用”“反正这活也绝种了”[6],颜素容把剩下的最后一个伏羲氏的傩面抢救下来,可她已是将死之人,喻示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悬置于断崖之间,蕴含着深远的忧患意识,警醒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思考。
(二)《傩面》中魔幻叙事的文学价值
《傩面》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本身就蕴含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内涵,小说中的魔幻叙事从根本上说,与人物的生命状态和生存环境所体现的神秘现象有关,也即是表现小说文学价值的手段。
小说《傩面》中魔幻叙事的文学价值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文学“神秘叙事”或“神秘书写”的表现与继承上。我们可以在中国小说史上找到有关于“神秘叙事”或“神秘书写”的足迹,例如“证实有信”的汉魏六朝志怪、“尚奇有致”的唐人志怪和“匡世有讽”的明清志怪,都有力地说明了中国文学“不语怪力乱神”的成规被打破,意味着人们对神秘文化和鬼神文化的认知不再是“封建迷信”的简单判断,文学在鬼神灵异的想象领域拥有了极大的创作自由,但它的发展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发展过程,《傩面》中的魔幻叙事对巫傩文化中的种种神灵事象进行自由的创作想象,表达了当代作家对中国文化中的神秘文化的审视与认同,这既是对中国文学“神秘叙事”或“神秘书写”的体现,也是对中国文学“神秘叙事”或“神秘书写”的继承与发展。
其次,《傩面》中魔幻叙事的文学价值还体现在对小说美感特征的提升上。《傩面》中的魔幻叙事立足于贵州边地的神秘巫傩文化,神灵因素和原始宗教文化让小说具有浓郁的神秘、诡异气息,而这种种神秘事象使得小说的美感得到强化,小说也呈现出神秘而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貌。比如《傩面》中的傩村神秘渺远,宛如世外之地,那里人们信仰巫傩文化,几乎人一生中重要的阶段,都要在一场场傩戏中展开,“傩村人唱傩戏,一个面具,一身袍服,就能唱一出大戏”[6],往往每临刈麦收谷、婚丧寿庆、鬼节年俗等特别时日,都要跳傩唱戏,延请神祝,什么丰收戏,许愿傩,还愿傩,归乡傩,离别傩,天地咒,扫秽傩,过关傩,平安傩等等,不一而足。小说中亦写到不少奇异事物,包括门口那棵死去多年的紫荆树竟然开花了,预示人死亡的乌鸦,沟通神灵的傩戏面具等等,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事象,不仅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又强化了小说的奇异美感,使得小说的艺术审美表现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小说具有了独特的审美风貌和艺术魅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小说的美感特征。
四、结语
小说《傩面》以贵州边地民风民俗为写作题材,运用魔幻叙事的写作手法,反映了独特的民俗文化,于传统崩塌过程中书写世道人心,是一部具有独特审美风貌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肖江虹在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艺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了本民族传统文化,创作出独具匠心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小说《傩面》的创作在受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时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模仿和照搬,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选择以本民族传统民俗以及日常生活为支点,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精神层面上与相对外来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相融通;同时小说中运用的独特的魔幻叙事表现手法,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它将贵州边地的巫傩文化中的神秘魔幻色彩与小说中的魔幻叙事手法完美融合,使小说中的人物具有穿越时空壁垒、沟通阴阳/人神的能力,并且其小说中的神话叙事和时间叙事这两部分内容中也有巫傩文化的参与,可以说小说中的魔幻叙事和巫傩文化两者的奇妙相接,将神话与现实、想象与真实融为一体,揭示了贵州边地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呈现出了神奇而又神秘的现实。
尽管描写贵州边地民风民俗的文学作品还在少数,运用魔幻叙事手法来表达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但随着贵州传统文化逐渐被发掘出来,越来越多的人会看到这块土地的价值所在,相信有关此类小说的研究价值也会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