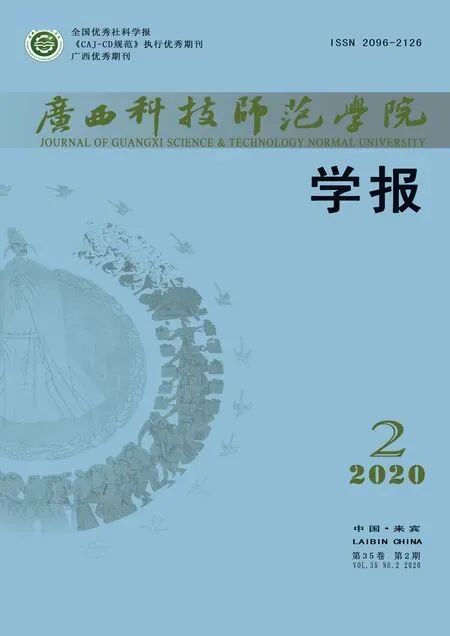西方“记忆理论”研究及其对我国少数民族记忆研究的启示
——“广西大瑶山瑶族文化记忆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2020-03-14雷文彪
雷文彪,陈 翔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广西来宾 546199)
从宏观视域考察,在西方传统的理论研究视域中,对于人类记忆的研究主要可分为“记忆”的心理学研究、“集体记忆”研究、“社会记忆”研究、“文化记忆”研究等四个维度。这些代表性的理论研究不仅推动了记忆研究的深入发展,促进了记忆理论体系的逐步完善;而且也拓展了记忆研究向社会学、考古学、文学、历史学、美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的融合发展。西方“记忆理论”对我国少数民族记忆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西方“记忆理论”研究的学术流变
(一)“记忆”的心理学研究
心理学对“记忆”的研究主要是将“记忆”作为人类个体或社会的一种心智活动来考察研究。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记忆”通常被解释为一种心理习得的“记忆术”,并将这种“记忆术”归结为“演讲术”的重要组成部分[1]154。柏拉图将“记忆”比喻为“蜡板”,认为每当我们要记住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的时候,记忆就如同“蜡版”呈现于感知和思想的面前,将印象印在上面,如此,记忆成了回忆理念世界的原型。苏格拉底将“记忆”比喻为一个大大的“鸟舍”,在这个记忆的“鸟舍”中不仅可以栖息各种各样的记忆之“鸟”,而且可以任其飞翔[2]。亚里士多德更是进一步论述“记忆”和“回忆”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回忆的过程蕴含了记忆,而记忆的过程也伴随着回忆[1]154。真正从科学意义上研究记忆的是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他是“第一位对记忆这种高级心理过程进行定量实验研究”的人[3]。艾宾浩斯通过反复实验,研究人的“记忆量”与“时间间隔”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被心理学界津津乐道的“艾宾浩斯记忆遗忘曲线”。他认为人对记忆事物的遗忘规律是“先快后慢”,但遗忘的进程并不是均衡发展的,遗忘从记忆结束那一刻开始,最初遗忘很快,以后逐渐变缓,经过一定的时间,几乎就不再遗忘[4]。心理学家米勒将记忆视为“通道容量”,认为人的记忆受到“通道容量”的限制,一旦记忆超出“通道容量”,错误将频繁出现。剖学家卡尔·拉什利则通过对老鼠的解剖实验研究中发现,如果皮层损伤得越多,那么记忆损害就会越严重。
可见,心理学与神经科学从人的生理机能层面对记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充分肯定了记忆在大脑和神经系统运作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是,心理学视域中的“记忆”研究仅仅是对“个体记忆”的研究,将“记忆”局限于个体的心理因素和认知能力的范畴,忽视了记忆与社会、记忆与历史、记忆与文化等之间的内在关联,无法揭示出人类记忆与人类历史实践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更无法揭示“社会记忆”“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的深刻内涵。
(二)“集体记忆”研究
直到20 世纪初,学术界对记忆的研究才从心理学领域转向社会学研究领域。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学术界对“记忆”研究从心理学向社会学转向。哈布瓦赫被学术界称为是“集体记忆”研究的开创者,他首次将人类的“记忆”赋予了社会学的内涵。在他看来,人类的“记忆”具有其内在的“社会性”,记忆只有参与到人类社会的互动与交往中,才能产生“回忆”,而人类有“记忆”生成“回忆”的能动性过程,就是人类“集体记忆”重要体现。何谓“集体记忆”?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将“集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5]335;并强调:“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5]93,“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5]106。
由此可见,从内在特征而言,“集体记忆”不仅具有对过去“历史记忆”的延续性而且具有现实的社会建构性,集体记忆是依托于过去的“历史记忆”,立足当下社会的需求,同时又规约未来的“想象性记忆”。从表现形态来看,“集体记忆”既具有客观的物质性又具有符号的表征性,“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5]24。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人类又是如何实现“集体记忆”呢?在哈布瓦赫看来,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主要通过“社会框架”和“社会交往”来实现集体记忆。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5]369。“社会框架”既是承载个人记忆的依托,也是唤起个人记忆的前提,人类如何记忆?记忆什么?完全取决于这个“社会框架”。同时,哈布瓦赫指出:“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5]70也就是说,集体记忆既受到人类既有的“社会框架”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受到现实社会交往情境的影响;集体记忆既是被历史、文化、政治等外界环境“形塑”的产物,也是记忆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建构”结果。
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研究主要贡献在于将人类社会的记忆研究由“生物性”延伸到“社会性”,将记忆研究从关注人类的“个体的心智”拓展到剖析人类记忆的“集体的社会属性”。他将涂尔干所追崇的形而上的道德力量对社会整合的作用,具体化为记忆对规范和整合人类社会集体行为的巨大作用。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研究是以“现在中心观”为核心,着重强调“集体记忆”的当下性。换句话说,记忆的“当下性”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他看来,任何“集体记忆”都是基于现实对过去的重建,“集体记忆”是通过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交往得到实现。然而,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研究更多是关注集体记忆的“和谐性”,他认为在集体中,人们分享“同一性”记忆,而忽视了因话语权力、社会环境、个体差异等造成“集体记忆”内在“异质性”。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尽管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研究将记忆从生物学的意义中剥离了出来,但是这种剥离并不彻底,他过多的强调个体意义在集体互动中的“塑造”,其所谓的“集体记忆”实际上是许多个体记忆的总和,真正使集体成为记忆的主体的,是哈布瓦赫以后的学者[6]。
(三)“社会记忆”研究
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是继哈布瓦赫之后,研究记忆理论的另一位代表性人物。他在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记忆”理论研究,并提出了“社会记忆”的理论。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将人类的记忆分为三类:即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社会记忆。保罗·康纳顿认为,人类主要是通过各种“纪念仪式”的“操演”和不断地“身体实践”来实现社会记忆。社会记忆在“纪念仪式上才能找到,但是,纪念仪式只有在它们是操演的时候,它们才能被证明是纪念性的。没有一个有关习惯的概念,操演作用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一个有关身体自动化的观念,习惯是不可思议的”[7]15。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是通过各种“纪念仪式”来传递和延续自身的社会记忆,而“身体实践”正是实现仪式“操演”重要前提和依据。同时,保罗·康纳顿指出,在人类社会记忆实践中,社会记忆与权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谓“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的等级”[7]1。社会记忆有力地支持着社会秩序的合法化存在;而权力在社会记忆的建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权力关系决定社会记忆,而社会记忆是建立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之上,无论是社会记忆还是社会遗忘都是权力关系的选择结果。
由此可见,相对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研究,康纳顿的“社会记忆”更加注重社会权力关系对记忆的影响。康纳顿认为,现存秩序的权力关系控制着“社会记忆”的生成、发展与建构,在“社会记忆”中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控制了“社会记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强调记忆在社会交往中“分享”特质,而康纳顿的“社会记忆”注重的是记忆在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中的“传递性”“延续性”“选择性”与“社会遗忘性”等品质,进一步拓展了记忆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当然,由于康纳顿过于强调具有政治权力意义的“社会记忆”行为和在“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上的“社会记忆”,忽略了更加广泛的人类文化中的“社会记忆”现象,以有限的“社会记忆”研究掩盖了人类“文化记忆”普遍性的事实。
(四)“文化记忆”研究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将“记忆”研究引入到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提出“文化记忆”理论。扬·阿斯曼在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基础上拓展了集体记忆的内涵与外延。在他看来,哈布瓦赫“集体记忆”概念是模糊不清的,而真正意义上的“集体记忆”可分为两种类型,即“交际记忆”与“文化记忆”,他认为“交际记忆”主要生成于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是在社会群体的言语交流中展开,具有日常性、口头性、流动性、短暂性等特点;而“文化记忆”则是与“日常生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它依靠仪式、节日、符号、纪念碑、文字等记忆媒介得到保存,通过牧师、教师、艺术家、诗人、学者、官员等“知识阶层”的表现、演示得到传承,相对于“交际记忆”,“文化记忆”具有稳定性、长久性等特征[1]155。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早期发达文化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认同》一书中,通过对古埃及、古希腊等古代文明的细致分析揭示了“交际记忆”与“文化记忆”的根本区别与内在联系,深入阐述了人类文化记忆在回忆历史、想象自我和建构身份的重要作用和意义[8]。
阿莱达·阿斯曼进一步拓展了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她认为记忆可以从“神经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三个维度进行区分和研究,并将记忆分为个人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等三大类别。在阿莱达·阿斯曼看来,个人记忆属于个体性的经验记忆,社会记忆属于“家族记忆”和“代际记忆”,文化记忆则是由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沟通凝聚而成的“具有象征性经验和知识”,个人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之间存在着相互互动和转化的内在关系。同时,阿莱达·阿斯曼将文化记忆细分为“功能记忆”与“存储记忆”两种形态,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记忆与历史的内在关系[1]156。阿莱达·阿斯曼认为人类历史的建构不仅需要记忆而且也需要遗忘,人类共同体的形成是历史记忆与遗忘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记忆还是遗忘:如何走出共同的暴力历史?》一文中,阿莱达·阿斯曼指出,记忆与遗忘从来都不是相互排斥的,在不同的社会实践和历史语境中记忆与遗忘都发挥着各自的功能。“记忆与遗忘之间并不是绝然对立的两极。遗忘与记忆都会有破坏和治愈的作用,到底两者孰优孰劣,取决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尤其是具体语境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和总体形势。”[9]于此,阿莱达·阿斯曼不仅阐述了记忆与遗忘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也揭示了文化记忆的历史性与建构性。
由此可见,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夫妇对记忆理论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文化记忆”概念,更重要的是他们拓展了“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研究范围及其内涵,将人类记忆细分为个人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将“集体记忆”区分了交际记忆和文化记忆,厘清了各种记忆的概念及相互关系,推动了记忆理论的深入研究。自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夫妇提出“文化记忆”理论之后,“文化记忆”研究成为了联接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美学等各学科交叉研究的主要对象,有力促进了各学科之间的融合发展。
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研究、保罗·康纳顿的“社会记忆”理论研究以及扬·阿斯曼、阿莱达·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研究堪称学界“记忆”理论研究的范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种理论范式研究之间存在着相互承接、不断深入细化的内在关联。这些研究不仅对深化“记忆”理论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对“记忆”研究延伸拓展到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西方“记忆理论”研究对我国少数民族记忆研究的启示
在人类社会中,“记忆”不仅是一种心理活动,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记忆”不仅是个体官能反映,而且是具有群体性、民族性的社会实践活动。任何民族记忆都将通过具体的文化表征形态呈现出来,而任何文化表征都蕴涵着一定的社会记忆和民族记忆。国外有关记忆的学理研究,对我国具体文化研究,特别是我国少数民族记忆与文化表征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和视域借鉴。
近年来,我国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领域,不少研究者将西方记忆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有机的结合起来,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如学者王明坷,借鉴西方记忆理论研究的相关成果,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视野,将民族记忆表征与族群认同有机地结合起来;作者通过详实的文献和深入地田野调查,探讨了以华夏边缘界定的华夏认同的形成、扩张与变迁,阐释了在历史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藉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与非华夏,揭示了我国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民族历史记忆、族群认同、资源竞争对维系民族记忆所发挥的重要功能[10]。覃德清教授通过对壮、布依、侗、傣、水、黎、仫佬、毛南以及越南的岱族、侬族,老挝的老族、泰国的泰族等族源的历史考察,指出这些民族不仅在族源上存在着“同源异流”的关系,而且在民族记忆上都是作为西瓯、骆越族群的后裔。他认为欧骆族裔在文化表征上都属于壮侗语族的民族,并非只是现代政治建构的产物,而是对被遮蔽的潜隐的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确认[11]。彭恒礼在论文《论壮族的族群记忆——从体化实践到刻写实践》中,对壮族族群中的共享性记忆形态的进行了考察研究,探讨了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壮族族群的集体记忆的传递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对族群的自我表象的影响,阐述了壮族民族记忆、自我认同的历史与文化表征之间的内在关联[12]。胡铁强、陈敬胜在《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一瑶族史诗“盘王大歌”的文化学解读》一书中,则以瑶族口传叙事文本“盘王大歌”为考察研究对象,阐述了盘王大歌中对瑶族历史文化记忆的表述与文化表征的建构[13]。
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凸显出了民族记忆理论对阐释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记忆所蕴含的巨大张力;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者,运用民族记忆相关理论研究、阐释我国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的自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