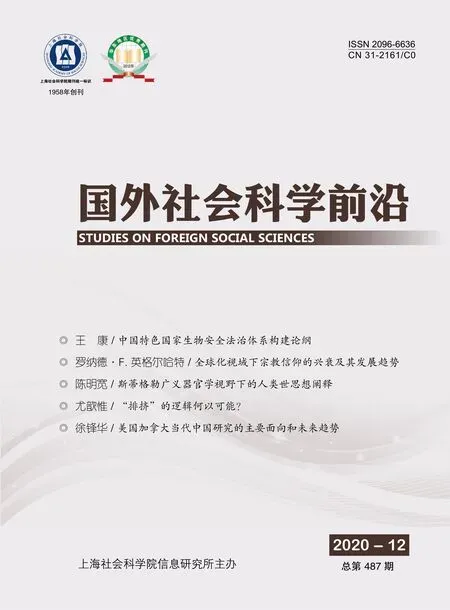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化与社会化之辩 *
2020-03-12陈祥勤
陈祥勤
内容提要 | 作为历史上率先步入现代社会的国家或地区,欧美等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展开的,由此形成了诸如资本主义的市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等现代文明建制;同时,诸如社会主义运动、社会政策和福利国家实践、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发育等社会性或社会化进程也在艰难展开,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面貌。20世纪以来,在北美和西欧分别形成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资本主义和以社会化为导向的“莱茵模式”的资本主义,这两种模式的资本主义分别代表了西方社会内部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之间的纷争。然而,不论是市场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还是社会化的“莱茵模式”,它们都臣服于资本逻辑的统治,因而也都无从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或危机。
欧美等西方世界是历史上率先步入现代社会的国家或地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资本、资本化或资本主义的主导下展开的,在此期间,诸如社会、社会化或社会主义要素也在艰难成长之中。在17—18世纪,西方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形成了诸如市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等现代文明建制;自19—20世纪以来,诸如社会主义运动、社会政策和福利国家实践、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发育等此类社会化元素,作为对治或矫正资本主义问题的历史运动或政治实践,开始参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北美和西欧分别形成的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为代表的“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和以“莱茵模式”为代表的“社会化的资本主义”,体现了资本化和社会化这两种逻辑在西方社会内部的纷争。尽管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着这样那样的社会化要素的制约,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资本化逻辑在西方社会的统治地位,甚至可以说,其社会化进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资本化进程在社会领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一、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资本化逻辑
欧美等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肇始于16—17世纪兴起的资本主义。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西欧和北美等西方世界的诸如市场或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或国家都臣服于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统治方式”。与这一“统治方式”相伴随的是资本的野蛮化趋势,以及资本主义的间歇式的经济社会危机和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
(一)资本主义的起源和西方现代性的发端
要探讨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就不能不探讨资本主义的欧洲起源,以及资本逻辑对于西方社会的决定性支配和影响。正如米歇尔·博德(Michel Beaud)在《资本主义史》一书中所说:“如果不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全世界带来的意义深远的巨变,就不可能了解当今的时代。”1[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吴艾美、杨慧玫、陈来胜译,吴艾美校,东方出版社,1985年,第1页。
其实,诸如汇票、信贷、铸币、银行、期货、财政金融、公债、海外殖民等,作为发端于商业、货币、信贷等资本形式或资本的价值形式,并非现代资本主义的发明,它们的“潜在”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有些东西甚至可以回溯到人类文明的肇始。与现代资本主义不同,用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话来说,这些商业、信用和金融形式尽管在过去的历史和世界的其它地方都存在过,但始终“活在一座封闭的‘钟罩’里,不能持续扩张”,也没有因为持续扩张而占据整个社会。然而在16—17世纪的西欧,资本关系、资本形式或资本逻辑开始跃出历史的“钟罩”,从商业和金融形式进展到工业形式,并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那里找到了自身的物质基础,逐渐发展出具有如此巨大创造力和破坏力的资本主义。2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699 ~ 722页。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 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资本主义,一旦从“历史的钟罩”里释放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能够不断自我增殖的经济社会体系,便成为新的世界文明的统治性法则。所以,在资本主义法则的统治之下,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开启了跨越几个世纪的现代性历史进程。
一是引发西方的金融革命。早在14—15世纪的中世纪晚期,西欧的某些城市就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和信用制度的萌芽。到了16—17世纪,商业活动的急剧扩大和远程贸易的拓展,为西欧社会的资本化注入了新一轮活力,由此引发了影响深远的“金融或信用革命”,推动了国家经济的货币化和资本化,导致了国家信用制度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商业资本主义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的过渡。正如比利时学者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所指出的,“商业是西欧生活变迁的引擎……西欧文化基本上是商业的产儿。”4[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 乐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 41页。到了18世纪,以荷兰为代表的商业资本主义开始衰落,它的地位开始让位于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资本主义。马克思在谈到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衰史时就指出,当“资本还是在一个和资本格格不入的、不以它为转移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基础上发展”时,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是“成反比例”的。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5页。从这个意义上说,荷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
二是引发西方的工业革命。在资本主义史上,英国具有典型的意义。正是在英国,随着以“圈地运动”为标志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展开,大量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成为自由买卖的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不仅是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开端,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的基础。因为当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增殖性的经济社会体系,才能找到自身的实体性的价值基础。这时,资本主义才有可能作为一种扩张性的社会生产方式,在资本增殖的逻辑下,推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促成产业革命的爆发,继而找到它自身的物质性的技术基础。发端于18世纪英国的西欧工业革命,开创了以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厂手工业的时代,也开启了现代工业史,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史和社会史,推动资本主义由商业和金融时代进展到了工业和科技时代。自此,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自我增殖的经济体系或生产方式,开始全方位地改造传统社会,继而向整个世界扩张,最终促成西方社会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根本转型。
(二)资本化逻辑主导下西方现代社会部门的形成
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既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时又是现代社会的基本部门的形成过程。一般说来,现代社会的基本部门分别为市场、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三个部门。其中,国家是代表公共领域的第一部门,市场是代表私人领域的第二部门,市民社会则是第三部门或第三域,它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
首先,资本逻辑促成了现代市场的产生。在传统社会,市场或经济关系“只占据一个狭窄的平台”,而不是扩张到整个社会的“体系”,因而作为某种“异质的独立世界”,处于传统社会的边缘。1[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244页。正是资本主义的产生,西方社会才可能从相互孤立的、有着诸多封建规制的传统集市转换为有着统一结构的、能够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具有增殖能力的现代市场;同时,现代市场体系一旦形成,就意味着社会的运转开始从属于市场,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2[匈]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0页相对于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在于,它第一次体现了财富积累的本能与财富的生产过程相结合这样一个历史性事实。正是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诞生,促成了欧美社会经济生活的市场化和现代化,同时促进了以欧美为财富、资本和文明中心的、统一性的现代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
其次,资本逻辑促成了现代国家的出现。从资本主义形成史来看,现代市场和现代国家之间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现代市场产生的一个历史性前提,就是国家经济的资本化、信用化和金融化,唯其如此,才能满足资本和市场对信用和金融的持久性的扩张需求。对此,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明确指出:“当国家成为借贷方时,信用或利润的积累才是可保障的;当国家的信贷或借贷成为永久的需求时,资本的利润和积累才是可持续的。”3[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民族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1页。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秘密’与亚当·斯密‘国民财富产生的秘密’确实是一个同步的过程”,4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31页。背后贯穿着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因此,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够在近代西欧能够形成,其深层原因在于,城市、工商业和远程贸易推动着当时的西欧在战争与兼并中打破了封建割据的局面,统一了民族市场,从而推动西欧各国由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
最后,资本逻辑促成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成长。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辖制下市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为准公共领域或准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或市民阶层也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现代城市、市场、工商业和资本主义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对此,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明确指出,现代意义的城市包含了“市民社会的阶级”和“城市组织”这两层含义,这两层含义是在现代城市、资本主义和工商业的发展中逐渐确立的。1[比]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5页。由于城市工商业文明的普遍化即资本主义化,市民阶层的自由和开放的生活方式或社会关系开始由城市扩展到农村乃至整个社会,将城市的市民身份赋予社会的所有成员,使得整个社会成为普遍拥有城市自由的市民社会。与此同时,那种以工商业文明和私有财产为内在基础的权利或法权观念便逐渐成为现代西方政治或法律科学的基石,成为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性的意识形态信仰,2Antony Black, Guilds and Civil Society in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London:Methuen & Co. Ltd, 1984, p.36.从而根本性地重塑了现代社会的观念结构。
(三)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症候
西方作为人类历史上首先步入现代文明的地区,其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变迁。但资本主义本身始终蕴含着在它自身之内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并为现代文明带来了诸多危机,包括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乃至环境或生态方面。
首先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自从资本主义作为现代世界“新的统治方式”以来,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就“一直为通货膨胀、经济萧条、货币贬值、动荡的汇率以及其他‘货币病’或‘商业病’所困扰”。3[英]约翰·F.乔恩:《货币史》,李广乾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页。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经济社会体系内在的深刻矛盾和不治之症。远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欧的一些大的经济中心就已经爆发过一系列信用震荡或商业危机。随着肇始于英国的西欧工业革命的爆发,资本主义的商业、货币或信用危机开始与生产领域的过剩危机关联在一起,随着生产过剩问题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危机也开始由商业和信用形式过渡到产业形式,成为困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可以说,一部现代资本主义史就是一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史。
其次是严重的社会撕裂或阶级分化。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基于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的体系”,资本主义的积累或增殖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或集中,另一方面是贫困的积累或集中,这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既在民族国家内部,也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分化、对立或撕裂,导致社会的资产阶级化(bourgeoisification)和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因为资本的积累必然伴随着劳动的积累,财富的积累必然伴随着贫困的积累,所以,资本主义必然伴随着社会的阶级分化和普通大众的无产阶级化。在18—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化还主要限于西方民族国家的社会内部;但自从19—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由欧洲体系扩展为世界体系,它的阶级分化已经表现为帝国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西方或北方对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东方或南方的剥削、掠夺或侵占。
最后是生态环境的危机或灾难。资源环境生态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进行的外部条件,资本主义的积累和无限扩张不仅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危机,而且还会引发资源枯竭、生态灾难和环境危机,如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植被、矿藏和水文的破坏、衰减与变质,生物多样性的锐减和生态系统的不可修复的破坏,等等。资本的逻辑是将一切商品化和资本化,并在其商品生产过程追求价值和资本的不断增殖,资本主义的积累和扩张是无限的,但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消化、净化和修复能力是有限的,这必然导致适合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的不断破坏”。4James O. Connor, The Meaning of Crisis: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Basis Blackwell Inc, 1987, p.33.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与资本主义的积累史和扩张史相伴随的是现代社会对自然资源、环境、生态的破坏史和转嫁史。
二、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化维度
西方是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形成了现代性的工业文明、城市生活、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族国家,因而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始终遭受资本主义的问题、矛盾和危机的困扰。在此期间,那些诸如社会性、社会化或社会主义因素,作为对治、矫正或遏制资本化或资本主义问题的社会实践和政策措施,也开始渗透到欧美等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之中。
(一)资本主义之替代性议程的社会主义
在西方近代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曾经为世人许诺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理想,然而在革命胜利之后,真正赢得自由和平等的不是社会化的个人,而是物性化的商品、资本与货币。这种由资本逻辑所统治的现代社会却始终受到一系列问题的困扰,诸如两极性的社会对立或阶级对抗、周期性的经济社会危机,以及资源、环境和生态的不可遏制的毁坏等。这些问题直接激发了那些追求平等、自由、解放和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现代左翼运动的崛起。
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的继承,是对这一革命的未尽事业的传承和发展。正如唐纳德·萨松(Donald Sassoon)所说: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实践“一方面朝向法国大革命没有实现的过去,一面朝向实现这些理想的未来”。1[英]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清、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页。它所质疑和反对的恰恰是资本主义辖制下的市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
一般认为,“社会主义”(socialisme)一词最初出现于19世纪20—30年代欧文主义的刊物《合作》杂志和圣西门主义的刊物《环球》杂志上,这个词表达了对资本主义所引发的症候、社会危机或文明灾难的愤懑,表达了对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集体主义的向往。它的最初含义,就是“以合作为基础,以大众的幸福和福利为目标的人类事务的集体管理制,所强调的不在于‘政治’,而在于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在于加强公民的毕生教育中的‘社会化’影响——教育他们在行为、社会态度和信仰方面遵守合作的而非竞争的方式”。2[英]G. D. H. 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1卷),何瑞丰译,俞大畏校,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0页。所以,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强调社会或社会性的维度,以便与个体或个体性相区分,当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对照的学说或行动的时候,它所强调的社会或社会化便与资本或资本化相对立,并试图用社会逻辑取代资本逻辑这一现代性文明的统治性法则。
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作为现代世界的左翼运动,它跟随资本主义跨越了19—20世纪,成为人们反对剥削和歧视、奴役和不公正的斗争的源泉。在西方世界,社会主义往往成为一种推动欧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的福利化、民主化和社会化的积极力量,成为这些国家或地区社会运动的崛起标志;在西方之外,社会主义——尤其是它的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版本,包括它在亚非拉地区的民族主义版本——往往成为东方世界反殖反帝的现代性的力量源泉,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推动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另一条道路选择。
自从18世纪社会主义的思潮和运动在西方兴起以来,不论是作为激进的革命运动,还是作为保守的改良实践,它都在客观上给西方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积极变化。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冲击,以及20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遭遇的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危机和历史上罕见的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社会开始吸收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元素,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实现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政策或体制调整,着力推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社会化进程。
(二)资本主义之改良性实践的社会政策
在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促进社会化元素的成长另一个重要动力就是现代社会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现代福利国家的产生。这是从国家的高度推进社会化因素的生长和发育。所谓社会政策,是指现代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了降低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带来的社会风险,克服资本主义的文明弊病,实现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政策或制度体系。
社会政策发端于17世纪的英国。1601年,英国颁布《伊丽莎白济贫法》,率先开启国家干预经济社会的先河,这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社会政策,但直至两个世纪后,1834年通过的《济贫法修正案》才标志着社会福利政策真正登上历史舞台。1O. William Farley and Larry L. Smith, Scott W. Boyle,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Allyn & Bacon, Boston, 2000, p. 18.一般认为,“社会政策”( Die Sozialpolitik)这一概念起源于德国。1872年德国学者组织成立“社会政策学会”,该学会倡导社会改良主义,主张通过政府制定法律,出台政策,以“财富的公平分配”为目标,来调节和化解社会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该学会的代表人物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明确指出:“所谓社会政策,就是采取立法和行政手段,以争取公平为目的,把分配过程范围内的各种弊害加以清除的国家政策。”2转引自王刚义、梅建明:《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当时的俾斯麦政府在社会政策学会的建议下,颁布了诸如《劳动法》(1881年)、《劳工疾病保险法》(1883年)、《工人赔偿法》(1884年)与《伤残和养老保险法》(1889年)等政策法规,初步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和福利保障体系。
西欧社会政策的出现,并且作为国家的一项义务或职责,被认为是自由资本主义对于集体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让步,国家已经承担了将社会带向社会主义的责任。3[英]迈克尔·希尔:《理解社会政策》,刘升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2页。社会政策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国家开始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着手某些改良性的社会实践。
20世纪20—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危机,促成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主义盛行。例如,罗斯福新政期间,美国相继颁布了《联邦紧急救济法案》和《社会保险法》。此后,凯恩斯主义进一步影响和推动欧美各国社会政策的发展,社会福利开始被视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纳入社会福利体系之中。二战之后,英国政府先后通过了《社会保险法》(1946年)、《国民医疗保健服务法》(1946年)等一系列社会立法或社会政策,在教育、健康、服务、社会保障、住房等领域实施“集体供给”,并于1948年宣称率先建成“现代福利国家”。此后,西方各国相继效仿英国,推动社会政策体系和福利国家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所谓福利国家,就是国家以社会政策为工具,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一系列社会福利,其基本标志就是,构建一个集全面性、义务性和国家性于一身的社会保障计划。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遭遇滞涨危机,西方的社会政策体制和福利国家模式开始遭受严峻挑战,诸如过高的社会福利造成政府的财政危机,过于平均化的收入结构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和经济体的竞争力,国家干预主义的效率受到普遍质疑。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在经济全球化和福利社会化的双重压力下,西方各国纷纷改革福利国家制度,将市场机制引入政府的社会政策体系,开始推动“福利型国家”向“社会投资型国家”转变。1参见[英]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3 ~ 132页。但是2008年以来,如去工业化、经济衰退、人口的老龄化和少子化,以及越来越严重的移民问题不断侵蚀着西方福利国家制度的经济、财政和社会基础,使得欧美各国社会政策的相机决策空间日益萎缩,福利体系陷入困顿而难以自拔。
(三)作为资本主义之社会化进程的市民阶层
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第三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就是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实际上,市民阶层或市民社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末期,追溯到这一时期西欧城市工商业繁荣的历史。市民社会的出现瓦解了传统封建制社会的等级或阶层结构,以及依附于其上的身份意识,逐渐培育出人们的自由意识和权利观念。
现代意义上“市民社会”(societas civilis)的生成与近现代城市工商业的兴起是密不可分的。最初,它以固定的城市居民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在欧洲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有城镇(town),没有城市(city)。城市的出现是12世纪之后的事情,英语中city与town的含义到14世纪才明确区分开来。2参见[英]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第43 ~ 44页。城市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劳动、就业和生活观念。因为“在城市出现之前,劳动是奴役性的;伴随城市的出现,劳动成为自由的了”。3[比]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3页。正如一句德国名谚所说,“城市的空气让你感到自由”。从公元11、12世纪开始,中世纪的西欧兴起了城市发展和城市复兴运动,这其实是一场争取城市独立、自由和自治权的运动。到了13、14世纪,西欧几乎所有城市都成为独立自治的社会实体,建立了“城市制度”,形成了“城市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是欧洲从中世纪迈向近代进程中的里程碑”,4Edward Cheyney, The Dawn of A New Era 1250-1453,.New York and London , Harper&Brother, 1936, p. 64.是西欧近代社会和国家的母体。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随着工商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到了16世纪,“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从政治上说,已经部分地消除了。”5[英]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355页。同时,伴随城市社会、市民阶层和自治性的城市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城市间、地区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以及跨区域的统一市场的形成,导致封建性的地方分割和行会限制纷纷被打破,市民可以在自由市场的前提下自由流动,自由组合成社会,即组合成为通常意义的市民社会。从17、18世纪开始,西方各主要国家相继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致使市民阶层从原先的“第三等级”(相对于传统的贵族和教士而言)上升为“第一等级”,成为国家生活的统治阶层。与此同时,市民阶层的自由和权利观念开始上升为新的政治观念或政治原则,推动西方民族国家由绝对主义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与之相伴随的是,民族国家体制管辖下的居民成为政治意义上的公民,并且赢得相应的公民权利。
在西方近现代史上,首先被发现的市民社会阶层乃是那些有纳税或支付能力的资产者或有产者,因而这一阶层也被赋予诸如选举、参政和参与殖民地贸易等国家让渡出来的“权利”或“法权”,从而赢得自身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统治地位。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无产者或劳动者得到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运动逐渐兴起,现代民族国家便逐渐将这一群体纳入市民社会领域,并赋予他们以相应的公民权利。随着欧美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市民社会的自由和权利要求开始由政治领域向经济和社会领域扩展,内涵也更为丰富,并且参与塑造国家,表达其社会化的权利诉求。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市民社会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拓宽,它所覆盖的领域或阶层不再局限于资产者或有产者,也不再局限于普通劳动者,还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等社会各个阶层;同时,随着市民权利(civil right)由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向社会权利(social right)的扩展,尤其是诸如劳动、医疗卫生、教育、保障和社会福利先后被纳入基本的市民权利范畴,使得市民社会逐渐成长为继民族国家、市场之后的现代社会的第三部门或第三域。
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抑或“莱茵模式”?
西方作为率先步入现代文明的地区,其背后贯穿的是资本、资本化或资本主义的历史与逻辑,但资本主义所导致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又激起社会、社会化或社会主义元素在西方社会的艰难成长,逐渐形成对资本主义不同程度的修正和改良,形成当代西方社会不同的形态或发展模式。其中,最为代表性的就是英美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欧洲大陆的“莱茵模式”,这两种模式分别代表“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化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代表“支配国家的资本主义”和“国家规范的资本主义”这两种体制之争,代表西方社会内部的资本化和社会化这两种逻辑之争。
(一)“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支配国家的资本主义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Anglo-Saxon Capitalism),又称英美模式,主要是指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通常涵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新西兰等国家,这些国家官方语言皆为英语,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具有许多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共同特征。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起源于英国,并在美国达到它的成熟形式。究其形成和发展历程来看,这一模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曼彻斯特阶段。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首先在18—19世纪的英国形成,这一时期也称曼彻斯特(Manchester)模式。这种模式以市场为本位,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的“自然秩序”为参照,主张市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随着英国经济的衰退和美国经济的崛起,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转移到美国,曼彻斯特模式随之也在美国扎根,并于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它的历史顶峰,但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中宣告了它的破产。
第二阶段是凯恩斯主义阶段。以1933年“罗斯福新政”的开启和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为标志,美国开始走向以政府的宏观政策和总量调控为基本标志的干预或管制资本主义的阶段。美国以罗斯福新政为开端,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开启了政府通过经济和社会政策全面干预经济生活、管理市场秩序、倡导充分就业、刺激有效需求、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先河,从而形成了政府管制的资本主义。但这一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欧美经济的滞胀危机中迎来了它的终结。
第三阶段是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阶段。20世纪70—80年代,美英世界迎来了“里根-撒切尔时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分别发动了所谓“保守主义革命”,即“国家最小化、市场最大化”的革命。他们重新以市场为本位,解除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削减社会事业或公共服务规模,将市场和资本逻辑引入国家社会政策体系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等。在此期间,“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重新变成“取代国家的资本主义”,1[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杨祖功、杨齐、海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33 ~ 234 页。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信条的“新美国模式”也由此产生。2008年,席卷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宣告了这种模式的失败。
纵观“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史,尽管它在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下,为缓解或克服资本主义所遭遇的危机或各种问题,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调整或革新,但是其基本特征还是一贯的,就是以资本、资本化逻辑主导市场秩序,以市场化逻辑主导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这一模式有两个基本特征:
一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自由市场秩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主体内容,就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秩序。即使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对于经济和市场领域的政府干预不论在程度还是在范围上都是最少或最小的。在美国,经济活动受政府影响的只占1/4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以维护市场秩序、确立市场规则为主要内容。鉴于英美世界长期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通常也被称为“自由资本主义模式”。2[英]戴维·柯茨:《资本主义的模式》,耿修林、宗兆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 ~ 13页。
二是以市场化为主导的社会政策和福利保障体系。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中,个人和社会需要的满足是要靠市场机制来实现的,因而诸如失业、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和就业保障、社会福利等社会政策或社会服务事业,往往是私人机构或公共机构从市场上购买,并且由这些需求者或享用者支付费用。尽管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曾宣称向贫困宣战,拟定建成“大社会”的计划,将普遍福利提到议事日程,但美国是以市场和资本逻辑为导向安排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因而,迄今为止也没有建立起公共性的全民健康保险或国家卫生服务制度。
(二)“莱茵模式”:国家规范的资本主义
“莱茵模式”(Rhineland Capitalism)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普遍采取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与美国不同,在欧洲大陆,除了自由主义等右翼思潮之外,19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左翼运动始终是欧洲政治和意识形态版图中的第三大力量。在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影响下,以德意志为代表的欧洲大陆试图走出一条有别于19世纪的英国模式和20世纪的美国模式的另一条发展道路。
作为“社会化的资本主义”,或者按照德国称谓,即“社会市场经济”,“莱茵模式”直接起源于二战之后的欧洲复兴时期。以德国为例,“莱茵模式”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发展时期:
第一阶段(1948—1966)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联邦德国围绕《基本法》制定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初步确立起经济秩序,以保障市场的自由竞争。同时,继承德国在俾斯麦时期以来的社会保障传统,制定一系列社会法规和社会政策,构建起完备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体系。
第二阶段(1966—1982)是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几次全面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也促使联邦德国吸纳了凯恩斯主义关于宏观调控、需求管理和经济干预的思想,将其运用到经济社会政策之中,进而使“莱茵模式”从“有限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转换为“全面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
第三阶段(1982—2000)是政府由全面干预转向减少干预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世界遭遇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一方面减少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缩减政府支出,改革社会政策,将市场原则有限引入社会政策体系和福利国家制度。
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是“莱茵模式”的自我调整阶段。在此期间,尤其是2008年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爆发,暴露了资本主义的严重问题。“莱茵模式”国家积极扩张信用,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国内需求,深化社会政策或福利国家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国家管制政策、社会保障制度与自由市场机制之间协调融合问题。
其实,“莱茵模式”作为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否定,它的历史可以回溯到德意志近现代史。19世纪上半叶,德国就形成了有别于英国政治经济学(如斯密主义)的国民经济学传统(如李斯特主义),如德国国民经济学家李斯特就明确反对经济学的“世界主义”,主张经济学的“国家主义”,揭示了国家在工业和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主导作用。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社会政策学派就提出了“政府活动扩张法则”(又称“瓦格纳法则”),即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不断扩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客观规律,这为政府通过扩张政策、财政和信用,来介入、干预和支撑市场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19世纪下半叶以来,尤其是1873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加速了德国经济由自由主义向国家主义转向,在实践领域以国家管制替代自由放任,以合作原则替代竞争原则,在制度层面形成了劳资共决的企业双层管理架构、为企业提供长期金融支持的全能银行机制、行业间普遍的卡特尔同盟、各类协会和研究机构、普遍化的工会等经济组织。这种经济体制中,拥有“话语权”的既非企业也非国家,而是一整套严密的组织体系,因而被称为“社团市场经济体制”。
这个所谓的“社团市场经济体制”,其实就是“莱茵模式”这一“社会市场经济”的前身。“莱茵模式”历经6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是由组织化的社会“进行有意识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1参见自[德] H.D.哈尔德斯、F.拉姆耶尔、A.施密特等:《市场经济与经济理论:针对现实问题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17页。这一模式试图寻求市场自由和社会公平、市场竞争与国家规范的有效平衡和适当配合,试图在“自由+秩序”和“效率+公平”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以自由竞争为基础、以国家规范为手段、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市场经济”。2参见张世鹏:《莱茵资本主义与全球化》,《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4期。
生1:垂线段法.如图8,过P作PQ⊥l于Q.求出直线PQ的方程:x-y+1=0;联立直线PQ,l的方程,求出交点Q的坐标(2,3),求出距离
(三)资本主义内部的资本化和社会化之争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作为当代西方社会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资本主义模式,它代表着资本主义内部的资本化逻辑与社会化要求之间,或者说市场支配国家与国家约束市场之间的冲突和纷争。前者是以资本逻辑主导市场,以市场逻辑主导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后者则试图奠定市场的社会化基础,并且试图通过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来保障这一基础的建构。
毫无疑问,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显然是资本主义模式,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自由企业制度、自由市场制度和自由民主制度;在社会领域,它推崇市场化、商品化和资本化的社会政策或福利体系。在20世纪80—90年代,这一模式在里根-撒切尔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中释放出它的能量,仿佛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滞胀问题,推动了商业、信用或金融的所谓创新,推动了经济的金融化、虚拟化或所谓的繁荣,因而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崇为“华盛顿共识”。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模式的根基。
一般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以自由市场体系为其制度原型的,这种观点似乎言之成理,但它往往遮蔽了这一模式的一个内在的基本事实,即这一事实所展现的原则“不是自由主义的市场供给方原则,而是重商主义的举债-金融化的需求扩张原则”,1[美]马格努斯·莱纳:《“第三条道路”的讣告:金融危机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5期。简言之,是以信用化(资产化和负债化)和金融化(资产负债转化为货币)为主要形式的资本原则。如此一来,这种由资本原则所支配的国家(尤其是其经济、财政和信用的高度资本化,深度卷入金融或信用市场)就已经成为经济增殖和市场扩张内在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了,因而也就不再是与市场相对立(以便限制或节制资本)的另一极力量了。美国模式之所以还有活力,乃是因为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本位或储备地位,致使全球70%左右的财富生产为其经济金融化的繁荣和自由创新服务,为其支付不断高企的商业、信用或金融成本。所以,一旦美元丧失其基本地位,美国这套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制也就难以为继了。
至于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莱茵模式”,一般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体制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管理和总量调控政策相结合的一种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曾经在20世纪70—8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滞胀危机期间遭遇严峻挑战。究其社会化的程度和水平来看,那些实施“莱茵模式”的欧洲大陆国家,社会化的程度和发展水平要远高于英美等发达国家,甚至被誉为“社会的成功”。2进入21世纪以来,北欧诸国一直被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列为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被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和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排在世界经济竞争力的前几位。——引者注以致有学者认为,那种注重社会公平和公正的“莱茵模式”已经不能再笼统地称为“资本主义”了,3参见王学东编译:《德国学者霍·海曼论“莱茵模式”和改良社会主义》,《国外理论动态》1997年7月。而是“资本主义的人道化”。4[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杨祖功、杨齐、海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33页。
“莱茵模式”能否被视为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化或人道化,能否被视为已经克服了资本主义问题的发展模式,这一点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这一模式的基础仍然是资本逻辑所支配的市场和国家,虽然是国家规范市场甚至约束资本,但国家(尤其是其经济、财政和金融属性)也已经深度卷入市场、资本和信用的增殖逻辑之中,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资本逻辑的支配和统治。因此,由资本逻辑所支配的国家来规范市场或约束资本,当然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症候、问题或危机。当市场在资本增殖法则的推动下普遍繁荣时,“莱茵模式”的一系列社会化安排及其运行当然没有多大问题,但当市场深陷资本过剩危机而导致普遍萧条时,这种模式的诸多社会化的政策、组织和制度安排就会遭遇经济、金融、财政乃至支付能力的危机。
众所周知,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就是一场典型的资本主义世界危机,而且这一危机很可能只是二战之后那种以美国、欧盟与日本等“三合会”(The Triad)国家5“三合会”(The Triad)国家指美国、欧盟、日本等北方世界(Global South)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和政治体,这些国家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表现为世界经济地图的发达地区。——引者注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更深层次危机的预演。
二战之后,世界经济历经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50来年的发展,西方各大经济体,不论是在个人或家庭层面,还是在企业和政府层面,都已经过度的信用化(即资产—负债化)、货币化和资本化了,这是资本的无限积累或扩张逻辑在市场、国家和社会领域的必然表现。资本逻辑所主导的市场推动资源、要素和产品的过度资本化或信用化,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社会生产能力过剩,同时导致资源闲置和失业。西方国家为了提高有效需求,一般都会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通过赤字或负债,进行财政、信用和金融扩张,以实现充分就业,支撑社会福利体系。一旦如此,整个经济体系必然遭遇滞胀危机,这是扩张性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必然后果。为此,西方国家为了缓解经济的滞胀、衰退和萧条,又开始奉行市场化、私有化和解除国家管制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政策,这又加剧了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和扩张,以及市场、社会和国家进一步过度的资本化、信用化和货币化。
当经济体的利润或真实财富的增殖再也无法补偿过度资本化所带来的利息或信用成本的时候,资本主义距离危机的爆发也就为期不远了。也就是说,当经济的过度资本化——体现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过度资产化和负债化——导致市场无法找到对资本的成本和利息补偿的实体性的价值和利润来源的时候,市场就会陷入衰退和萧条之中,这时的市场是不可能通过简单的出清来恢复其内在的活力和产能的。因为资本的过剩不止是表现为资本的量的过剩,而且还表现为资本化的市场关系或经济社会交易体系的过剩,这种过剩危机只能通过系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解决。此时,如果国家也因为财政和信用的严重透支或扩张,从而再也没有能力和空间支撑扩张性的经济或社会政策,那么这时,资本主义陷入长时期的萧条、系统性的衰退或崩溃性的危机,基本再也不可避免了。
2008年以来,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后危机时代”非但没有从资本、信用和债务过剩的泥潭中脱离出来,而且越陷越深。根据国际金融协会《全球债务监测》(Global Debt Monitor Report)的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全球债务总额高达惊人的253万亿美元,是全球生产总值的322%,欧美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债务占全球债务一半多,这些地区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高达383%。1参见新华社:《全球债务水平2019年创最高》,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1/15/c_1210439019.htm。此外,据世界银行等相关数据显示,2017 年,世界生产总值或全球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值约为75万亿美元,2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 Base,http://databank.worldbank.org /data /download /GDP. Pdf, p. 1.但全球衍生品市场据估计高达难以想象的1200万亿美元。3J. B. Maverick, How Big is the Derivatives Market?https://www.investopedia.com/ask/answers/052715/how-bigderivatives- market.asp.这一系列数据表明,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资本、信用和债务与实体经济相比,已经达到史无前例的严重过剩状态。不论是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政策主张,还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主张,都不可能是解决这场由资本过剩所引发的萧条、衰退或危机的良方。
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深陷史无前例的过剩危机,致使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开始走向它的反面,即逆全球化,导致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等右翼思潮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兴起。正如美国学者大卫·M.科茨(David M. Kotz)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体系在经历这次危机后,不论是转向“管制的资本主义”,还是转向“改良的资本主义”,甚至是转向右翼势力登上舞台的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政权,都是资本主义危机在当代世界的症候表现。4David M. Kotz,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Marxist Theory, and System Transforma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49, no.4, 2017, pp. 534-542.
四、结 语
纵观西方社会的整个现代化进程,其背后的主导逻辑或统治法则仍然是资本、资本化或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一旦从“历史的钟罩” 里释放出来,便成为新的世界文明的统治法则,作为一种增殖性的经济-社会体系,以及作为一种为增殖法则所推动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业体系,为现代社会打上了增长、发展和创新的烙印。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前现代的传统社会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而现代社会总是寻求“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所以,诸如资本的增殖、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乃至科学、技术或工业的革命和永不涸竭的创新,对于传统社会来说是外在的、陌生的,但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却是内生性的或本质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追求现代化的社会,它在制度形态的意义上体现为现代市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等文明建制,在社会生产的意义上体现为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增长、发展和创新的逻辑。
所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所展现的深层逻辑就是资本化的逻辑。这一逻辑不仅表现在社会的经济发展领域,如具有增殖性和扩张性双重特征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而且表现在社会的其他领域,如脱胎于近现代城市、资本主义和工商业文明的西方市民阶层或市民社会,以及以国家经济和财政属性的资本化或信用化为支撑的西方社会政策和福利国家体系。因此,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既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又是诸如市场、市民社会和国家等现代社会之基本部门的形成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世界的诸如市民社会的发育与成长、市民权利的形成与扩展,以及社会政策或福利国家体系的实践等社会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以资本化的逻辑为其内核与支撑的。在此期间,尽管市民社会的领域从原先的资产者或有产者扩展到全体社会成员,市民权利由原先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扩展到社会和文化权利,但这些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化进程或改良性实践。
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作为对治或矫正西方资本主义问题的社会化进程,在其内在性的意义上却是革命性和创造性的。因为社会主义就其本质性而言,是为了超越或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症候或问题而形成的历史运动;就其实践性而言,必然要形成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性方案或议程,用更高的社会化逻辑取代资本化逻辑,并且使之成为社会的主导性法则。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页。来取代迄今为止统治这个世界的资本法则。但在欧美等西方世界,作为社会化进程的社会主义运动更多地作为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实践(而不是作为另一种道路选择),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之中。
因此,不论是欧洲大陆的“莱茵模式”,还是英美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体制和模式之争,因而在面临资本主义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时,尤其在面临其体系性的症候和危机(如2008年以来欧美等西方世界在资本主义的衰退、萧条和危机中愈陷愈深)时,基本都是无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