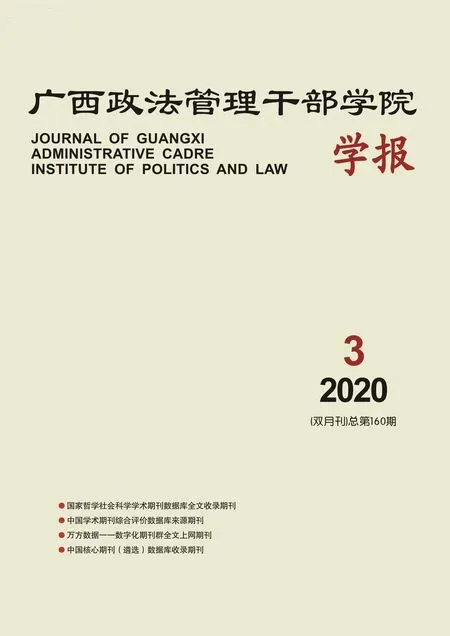英美侵权法之可预见性理论于因果关系认定的优越性
——以法律因果关系为视角
2020-03-12陈若冰王雪琪
陈若冰,王雪琪
(贵州财经大学 文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
从历史看来,英美侵权中的法律原因问题自始存在两种解决路径:一种为“介入原因路径”①介入原因曾是法律原因的主要标准,这种标准关注事件间的顺序,考察被告行为在引起损害发生事件序列中的位置,以及介入被告行为在引起损害间事件的性质。以区分条件和原因来解决法律中单称因果陈述的特殊问题。冯钰:《英美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或称“直接结果标准”②普若瑟认为,直接结果是指“在既存条件和已经发挥作用的力量配合下,按顺序产生于被告行为的效果,而不依赖于任何嗣后积极发挥作用的外部力量介入”。See William L.Prosser.Handbook of the Law of Torts[M].St.Paul,Minn.: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71:263-264.,另一种为“风险标准”或称“可预见性标准”。自20世纪以来,英美侵权法之可预见性理论在因果关系认定中渐占上风,其在合同法和侵权法均有适用余地,然其存在较大差异,可预见性理论于侵权法领域主要用以判断过失成立或以近因之名限制责任范围,而在合同法领域多以契约自由角度限制违约责任[1]150。合同法领域以保护经济利益为立法本意,对不可预见之财产损害及精神损失赔偿问题,侵权法之有效解决突显了合同法内容之苍白无力[2],行为的可责性无法独自解决责任范围问题,然风险标准直接诉诸法律政策,即制造责任的理由也应限制责任③此处主要指影响法益的政策考量。See Warren Seavey,“Mr.Justice Cardozo and the Law of Torts”,52 Harv.L.Rev.386(1939).,风险范围的可预见性为侵权因果关系概念提供全面实践。风险标准与过失限制、责任范围的一致性[3]446,责任承担的公正性与标准统一的简单性①“简单性”的具体释义。See A.L.Goodhart,“The Imaginary Necktie and the Rule of Re Polemis”,68 L.Q.R.533(1952);Warren Seavey,“Mr.Justice Cardozo and the Law of Torts”,52 Harv.L.Rev.386(1939).塑造了风险理论的优越性。限制责任的风险本质在于行为具有侵权性的风险②“行为的侵权性”可以通过外延分析法理解这个概念。在过失侵权案件中,“行为的侵权性”在于行为有过失,因而限制责任的风险是指使行为有过失的风险;在严格责任案件中,“行为的侵权性”在于行为具有异常危险,因而限制责任的风险是指某种活动或物具有的典型风险。冯钰:《英美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9页。,实际损害是潜在损害的实现达到风险标准限制责任范围的目的。
风险标准可以说是可预见性标准的概括形式,然米歇尔·摩尔认为可预见性标准与风险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可预见性完全不受过失的限制,无须考虑风险的预见合理性问题[4],而风险标准需要考虑风险是否合理的问题③有关“风险标准”的含义及影响因素。See Heidi M.Hurd and Michael S.Moore,"Negligence in the Air",3 Theoretical Inquiries L.340(2002).。哈特和霍诺里认为,可预见性和风险标准的不同不在于两种标准间的差异,而是可预见性和风险本身存在两种含义,只有在虑及损害严重程度及避险成本,理性人于通常情况下会采取措施防范损害发生者,是为“实践意义上的可预见性或风险”,否则为“理论意义上的可预见性或风险”。从可预见性标准本身而言,似乎只有实践意义上的风险标准和可预见性才符合理论基础要求[5]288-289。道伯斯(Dan B.Dobbs)是实践意义上的可预见性或风险标准理论拥护者,认为可预见性是一种“略缩语”,被告责任限于其过失行为危及之损害,行为人无须对行为时无法合理预见之侵害负责,损害本应是通过谨慎行事可避免为之[3]444-445。埃德格顿(Henry W.Edgerton)曾言,“非为行为人故意侵权之场合,可预见性要素于通常情势下直接影响理性人对归责公正性的判断。”[6]由此,可预见性理论于侵权因果关系认定之重要性可见一斑,其既用于区辨行为人注意义务之违反,又用于甄别被告行为与损害结果间近因关联之判断[7]。
一、问题的提出
哈特和霍诺里提出的两种类型的可预见性[5]263-264,即“实践意义上的可预见性”基本是指判断过失或注意义务的可预见性,因虑及前因后果之牵连,又称“复合意义上的可预见性”或“主观可预见性”;而“理论意义上的可预见性”基本是指判断近因或限制责任的可预见性,因比较纯粹、客观地考察预见性标准,多称为“纯粹意义上的可预见性”或“客观可预见性”[8]。前人之理论体系塑造后世之丰富理论内涵,如若“可预见性”是于实践意义上理解的话,将来损害之赔偿会因“预见可能性”之影响受此严重阻碍从而过分限制责任范围[5]273,而“理论意义上的可预见性”于逻辑适用上却可以融贯。因两者在虑及事实原因问题上考虑可预见性程度不同,故又称为过错否定模式与因果关系切断模式,其比较结论源于美国的“医疗事故并发症规则”,Weber④Weber v.Charity Hosp.of La.,475 So.2d 1047(La.1985)./Lamber⑤Lambert v.United States Fidelity and Guar.Co.,629 So.2d 328(La.1993).判例确立了该项规则,Dumas v.State案⑥828 So.2d 530(La.2002).对此进行了发展,规则的基本思路为“以近因证成注意义务,而非注意义务的自我证成”。举例言之,被告过失行为造成受害人身体损伤之情势,最初过失行为造成之结果在“并非不可能”或“并非极其不可能”意义下[5]264,医疗事故之损害发生者称“可预见”或“可合理预见”,初始行为人须对此损害负责,此为“理论意义上的可预见性”⑦从“理论意义上的可预见性”理解损害事实,不仅包括可能发生之情势,亦包括不是不可能或不是完全不可能之场合。See Jenny Steele,Tort Law:Text,Cases,and Materials,1st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86.于理论内涵与司法实践之适用常态。然若主张“实践意义上可预见性”将得出“初始加害行为对后续损害无法预见而无须负责”之结论,实与通常情态下常人理解不符,恐有初始过度限制行为人责任之隐患。
上述理论概述似与道伯斯、哈特和霍诺里最初主张理论应用相悖,实则可预见性标准于过失构成要件与因果关系认定上均有理论功能及适用余地,侵权因果关系认定中的可预见性不仅关乎责任成立判断,还涉及责任范围界定,此为责任之归因表述外围之限定损害赔偿责任问题[9]。然而,法律现实主义论者普若瑟认为,因果关系应为纯粹事实原因问题,因果关系确立后,所要解决的“近因”或“法律原因”问题只是借用“近因”之名限制责任归属范围[1]152,按此逻辑推理,理论与实践应绕开“近因”之名运用“可预见性标准”直接作责任限制判断。传统概念法学与现实主义法学的理论碰撞并没有消解为行为人划分损害赔偿责任范围的热情,可预见性标准的主要功能仍立足于责任范围之界定。鉴于此,为便于理论研究的妥当性及法学研习的科学性,笔者以概念法学为立场在因果关系二阶层的倡导下探讨可预见性标准于近因视角(或称理论意义上的可预见性)为未来法学发展发挥间接的限制理论功效。
“归因性原因问题”有多种称谓,如“法律原因”“近因”“遥远之损害”“责任范围”等。1928年美国的Palsgraf v.Long Island R.R.Co.案①Palsgraf v Long Island R.R.Co.,248 N.Y.339,352,162 N.E.99,103,per Andrews(1928).发展了近因法律概念,安德鲁(Andrews)法官认为:“近因之判断或源于方便,或源于公共政策,或源于朴素的正义观,法律往往倾向于果断地推动事件发展以合乎严苛标准,这不是逻辑推理,而是现实的政治判断。”②安德鲁斯法官观点的译文。[美]戴维·凯瑞斯:《法律中的政治——一个进步性批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9页。普罗瑟教授(William L.Prosser)称该案为“最重要的侵权法判例、最重要的普通法判例”[10],现实主义原因论者利昂·格林评价其为“近因理论的最高水准之司法表述”[11],然其不足之处在于Andrews法官没有平衡互相竞争的社会利益,使得权益保障有失偏颇。关于本案的责任限制原理,法院接受了Andrews法官的近因限制理论,将责任限制放在因果关系名下,而后学说判例也深受英美经验主义启发。有论者提出,让侵权人对其作为或不作为造成损害后果之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是否妥当之评价为责任范围考量要素[12],如Roche Mining Pty Ltd v.Jeffs案就是参照“合理可预见”标准明示限制赔偿责任范围。围绕近因理论,非为法律政策之考量要素不可解,正如Andrews法官思索的“通过何种近因理论限制无限后果划分”?实则可预见性标准既体现过错责任的一般思想,又体现冷静、理性的世界观用以适当切断因果链的需要,可谓融可归责性与责任限制于一体,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然而,我国对侵权法之可预见性标准的研究比较偏重过错或注意义务的判断,于限制责任范围问题上却略显不足,故本文以法律因果关系为视角探讨可预见性标准于侵权因果关系认定中发挥的理论功效,以期为我国今后理论依据与司法实践提供借鉴意义。
二、可预见性标准的理论基础
16世纪初,法国学者迪穆兰创立了可预见性标准[13],在学理上,可预见性标准由英国的古德哈特(Arthur L.Goodhart)和美国的弗莱明·詹姆斯(Fleming James Jr.)所倡导;在实践上,Griffith 法官在Mauney v.Gulf Refining Co.案③1942,193 Miss.421,9 So.2d 780.See William L.Prosser,Handbook of the Law of Torts,4th ed.,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71,p.251.中对可预见性标准作了精准评价,认为“侵权责任范围应在合理预见之圆周范围内,若以过失行为发生时为圆点,半径则需考虑时间、地点、起因等具体要素”④[1942]193 Miss.421,9 So.2d 780.。英国枢密院于Overseas Tankship (U.K.)Ltd V.Morts Dock and Engineering Co.(The Wagon Mound No.1)案中确定了损害赔偿之近因范围[5]255,即过失行为、责任范围都与损害可预见性相关,又称为“损害远隔性的瓦根·蒙德标准(The Wagon Mound Test of Remoteness)”⑤笔者以为此处“近因”与“远隔性”概念可相互替代。[英]阿拉斯泰尔·马里斯、肯·奥里芬特:《侵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21页。,此可谓可预见性标准之广义观点⑥Alani Golanski,A New Look at Duty in Tort Law:Rehabilitating Foreseeability and Related Themes,Albany Law Review,Vol.75,2011;Jeremiah Smith,"Legal Cause in Actions of Torts",Harvard Law Review,Vol.25,No.2,1911.。在近因方面,弗莱明·詹姆斯充分展现了社会政策导向与功能主义分析观点,并提出“所有赔偿体系均应是有限观念,以免压垮最终为损失‘埋单’之人”的观点。申言之,行为人责任承担限于常识因果原则(common-sense causal principles),制造责任的理由也应限制责任。在阐述完近因法律政策后,普若瑟指出,真正的、应该关注的问题应是社会政策导向问题[14]257,264,正是由于可预见性标准能够容纳多种考虑之广泛余地与灵活性观念,才能指引近因标准迈向最终胜利之终点[14]267。基于可预见性标准的法政策观念,法院一直以社会政策为基础开创创造性裁决空间,故多角度剖析理论本质为今后理论适用埋下基础理应为司法实践之适用空间。
(一)法哲学分析
哲学之于侵权法紧密关联,实现正义乃侵权法之基本使命,矫正正义哲学观念于哲学关照中命定当代社会担当作为个人责任伦理规则。“矫正正义”概念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矫正正义”法学派论者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 A.Epstein)支持将“造成损害”作为矫正正义理论基础①关于“损害结果”与“矫正正义”的具体关联。See Richard A.Epstein,"A Theory of Strict Liability",2 J.Leg.Stud.151(1973).,集中体现因果关系概念与矫正正义间的哲学关联。在古老的直接侵害令状条件下,因果关系暗含只在当事人间发挥作用的正义观念,为责任的目的在某处切断因果链以体现责任范围要素。矫正正义学派代表人物欧内斯特·韦恩瑞博(Ernest J.Weinrib)指出,古老的诉因及爱泼斯坦原因范式中,假定某种内部区分要素,武断地承认某些因果关系的法律重要性从而排除其他因果关系不相干要素②See Ernest J.Weinrib,"Causation and Wrongdoing",63 Chi.-Kent L.Rev.418(1987).。可见,可预见性要件直接与矫正正义观念相符,直接关系法律责任划分归属,当损害是不可预见发生态势,没有造成损害之人就全因其在不同替代行动方案间没有真正选择而没有过误[15]。凡自由选择之结果,一般是符合正义原则基础,表现价值论之中心观念以此分散、转移损害并平复或消除扭曲状态,以矫正给其他人造成损害之非正义基础。
(二)法社会学分析
法社会学之行为宗旨在于人之行为不仅受外部力量约束,更受内心尺度调节。人之观念、意识、道德、习惯、态度及基本精神之内心认同已逐步演化为法律规范之终极效力。法律规范存在社会化过程③法律规范往往伴随社会化过程。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99页。赵震江主编:《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199页。,权利义务关系可内化为人之性格结构、文化观念及自觉扮演之社会角色。在社会化观念渗透下,行为人应当且能预见行为之法律后果,使得法律规范之社会化为可预见性理论提供基础保证。法律规范之社会化主要涵盖个性发展、文化继承及角色学习三项过程,由社会化过程不断推动法律规范发展滋养形成。后天社会行为赋予人生理及心理条件,为机遇成长提供程度不等之可能,使得社会角色异质性逐步形成。通过后天学习与发明创造物质生活条件及确定基本利害关系与行为规则之制度层面,社会规则与基本精神更迭创新、不断传承。社会内部形态多划分为差异性极强异质性部分,分别执行不同社会功能,并相互协同、配合,形成完整社会结构功能,社会结构相互联系,表现为权利义务关系不断形成。人在社会结构中扮演不同社会角色与社会位置,社会角色之分工显现出预见能力不尽相同,行为人不仅能预见行为事实原因,也能预见相应法律后果,使得法社会学背景下可预见性理论也有较大解释余地。
(三)法经济学分析
法律经济学是以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为基础,政府的正当性行动为指南的交叉路径,然功利主义“计算”或“运算”幸福或福利总净余额却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困境[16],帕累托最优和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表明,只有从“财富”入手才能解决如此困境。以“财富最大化”形式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已逐渐成为经济学的隐含假设,科斯认为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效率,“价值极大化配置及使用资源”效率观为经济分析法学的重要思想,当法经济学家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法律问题时,法律领域似乎也在不断号召“财富最大化”④See S.F.D.Guest,"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in Roger Rideout and Jeffrey Jowell(eds.),Current Legal Problems,London:Stevens and Sons,Limited,1984,pp.233-245.目标以确保人民幸福感需求。波斯纳教授认为,效率或财富最大化为侵权法最佳规范导引,可从伦理哲学层面论证财富最大化根植于社会各项体系[17]56。当经济分析被用于侵权法时,卡拉布雷西认为实现财富最大化的方法通常被理解为“事故成本最小化”,事故的发生是社会成本问题,付出成本的目的在于求得收益,过去的成本付出后应着眼于将来的收益以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激励。
按照功能主义分析路径,卡拉布雷西(Guido Calabresi)主张侵权法有两项“赔偿目标”即分散损害和重新分配财富,将损失分配给相对易于承担负担之人,以实现事故成本最小化目标。卡拉布雷西将近因作为表示法律需要附加责任关系的标签,认为近因作为专门表达非因果关系政策的媒介对“赔偿目标”发挥部分限制作用,归纳出“近因要件不能解释因果关系为何成为侵权责任必不可少要素”①卡拉布雷西提出地“赔偿目标”包括分散损害和重新分配财富。See Guido Calabresi,"Concerning Cause and the Law of Torts:An Essay for H“近因要素”与“赔偿目标”之关联及限制性。See Guido Calabresi,"Concerning Cause and the Law of Torts:An Essay for Harry Kalven,Jr.",43 U.Chi.L.Rev.76(1975).的结论性意见。但是,因其未验证财富最大化是法律关注的恰当、合理且唯一目标,故卡拉布雷西设置的目标是否合理、是否能得到普遍支持尚有疑虑,因而未能得到侵权法学家认可。卡拉布雷西将侵权法规则立足于事故成本最小化、财富或利益最大化目标虽有待商榷,但将近因要件归结为与每项政策目标有关,验证了因果关系要件并非为责任的必要性依据,也进一步推动了近因要件政策考量之研究。波斯纳(Posner)认为,可预见性标准能指引知晓风险之行为人采取预防措施或要求为受害人之损失预防者或风险分散者承担损失风险以产生社会效益最大化分配风险激励[17]161-162。实则法律允许履行之价值在于判予损害赔偿,侵权法中的威慑要旨通常被认为是避免给他人造成损害,而非过度成本消耗问题,不能应允事故发生者为降低损害风险而付出巨大成本,潜在加害人和受害人产生预防损害之激励,避免损害发生才是侵权损害赔偿归属之法的效率最大化福祉,而非单一的效率分析工具。鉴于此,波斯纳将事故成本最小化立足于当事人最优注意水平,在需求及供给间寻求注意成本、事故概率及损失数量间的关系。在避免损害注意成本比事故风险承担付出成本低时,过失责任承担将会鼓励他人积极避免风险;反之,则不必苛以责任。同时,美国学者Posner和Landes认为,预见性概念有助于确定适当程度的法律阻吓机制,只有可预见性损害才具有阻吓功能②See W.Jonathan Cardi,"Reconstructing Foreseeability",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Vol.46,September 2005,p.955.。如若事件是不可预见的,则承担责任的后果也是不可预见的,若强加被告内部化不可合理预见之风险责任,预见风险的成本超过避免特定风险的效益,无疑会浪费交易支出成本,没有任何经济效益③See W.Jonathan Cardi,"Reconstructing Foreseeability",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Vol.46,September 2005,p.956.。在行为人对损害缺乏预见之情势下苛以责任显然未能阻吓未来他人之危险行为[18]。假设所有不可预见性损害都得以完满赔偿,提升法律阻吓功能则是无效率和不必要的,由此以法律上的原因为视角区辨不可预见性损害赔偿使被告人免于承担责任以产生社会效率最大化经济效益实属必要性观点。
三、可预见性理论于因果关系认定中之优势表征
英美法上的合理可预见说是指,被害人之损害结果在加害人不法行为制造危险范围内,且事件之结果系属因果历程正常而自然之结果,并别无独立中断原因介入,构成加害人合理可预见之结果。南非学者认为,“实际后果之结果对应于行为之‘自然与可能结果’或‘合理结果’是为可预见性结果。”[19]行为人预见之结果只能是一般性结果,而非高度异常、极不寻常和无法预料之结果[20]116-117,否则非属损害赔偿范围内结果。可预见性理论于损害结果之责任范围限制功能极为重要,各国也采取多元化实践路径以期解决侵权损害赔偿归因性要件问题。法国法对因果关系的证明通常采用“充分程度”可能性或“客观可能性”标准,有时辅以增加风险标准判定因果关系成立[21]。德国法对充分因果关系之分析为,“预见程度起决定性作用,如若行为导致特别无法预料、不可预见之结果,则欠缺因果关系。”[22]187在瑞士法中,官方正式定义的因果关系充分性标准并未提及预见性问题,但实践中可预见性、意图、规则之保护目的、对特定人发生损害之不可预见程度等要素均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此规则要素使官方定义黯然失色[22]188。侵权法之可预见性理论主要涵盖英美法之固有传统特别是司法传统而言,其理论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日益突显。哈特和霍诺里认为可预见性理论于侵权法律因果关系或限制责任范围认定上具有一致性、简单性与公正性等优点,对此理论界与学术界也颇为认可,对于理论制度本身的诸多优点下文则会分而述之。
(一)简单性
可预见性标准具有相对简单的优点,其不用查究某一行为所有不当方面是否都具有原因关联性,便可直接确立行为可责性方面是否能够限制责任判断归属问题。举例言之,在Sheehan V.City of New York案①See Sheehan v City of New York,40 N.Y.2d 496,387 N.Y.S.2d 92,354 N.E.2d 832(1976).中,一辆公共汽车在十字路口停下并允许乘客上下车,其后驶来的汽车刹车失灵造成事故追尾,导致公共汽车上一名乘客受伤。虽然公共汽车司机未将车停在路边给上下车乘客制造了风险,但因车辆在行驶时经常在十字路口停下,故司机未给乘客制造任何特殊风险,公共汽车公司不承担责任。可预见性标准在风险范围内为通向结论提供了便捷的途径,使得必要条件标准作简单化处理,简化了逻辑关系,使责任判断要素摆脱因果关系审究难题。约翰·弗莱明认为“并不缺乏给可预见性标准冠以‘逻辑必然’之殊荣的努力。”“若无,则不”“假若,没有”条件关联性在事实原因判断上的省略,使得“一般理性人”之预见与“直接的、自然性”进程直接联系,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寻求行为与结果间“自然性与可能性”之间存在关联,表现出可预见性标准之客观化与因果关系之价值性相互契合的概念。但是,建立可预见性一般标准,也不应拒绝与其他标准相互整合的余地,才能推进理论的进步、标准的统一。
(二)一致性
基顿(Keeton)法官认为“判断行为人对其行为所致之非故意损害负责之因素应以判断责任范围。”[23]在故意侵权责任范围中,可预见性标准固无适用余地,在严格责任侵权案件中,侵权人之责任限于要求行为人承担严格责任风险范围内之损害,而在非严格责任背景下,过失要件及责任范围均须考察预见性问题,可谓融可归责性与责任判断于一体。沃伦·西维(Warren Seavey)认为,主人对猎狗咬人之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对猎狗撞到他人之侵害不承担无过错责任。哈特和霍诺里认为,如若行为人在自己土地上实施爆破,只要损害处于爆破风险范围内,行为人应负有严格责任②Whitman Hotel Corporation V.Elliott& Watrous Engineering Co.,(1951)137 Conn.562,79 A.2d 591.。在近因判断上,“行为的侵权性”在于行为具有高度异常危险,限制责任的范围是指某种活动或物具有的典型风险。
在过失侵权案件中,可预见性标准将风险限于行为人有过失范围内,行为人对理性人通常会忽略之不可预见损害无须承担责任,即行为人可忽略很小或避险成本过高之风险。如若责任范围不受可预见性风险范围限制,行为人事实上不能忽略此种风险,与过失规则间存在冲突矛盾[3]446。实践中最先采纳可预见说的是The Wagon Mound No.1案③Overseas Tankship(U.K.)Ltd.V.Morts Dock & Engineering Co.[1961]A.C.388.,行为人过失地在悉尼港泄漏燃油,燃油漂到600英尺以外原告的码头,码头焊接时掉落的融化金属点燃浮在燃油上棉花废弃物,导致燃油起火,码头被烧毁。枢密院法官认为过失行为的责任范围应采用与认定过失规则相同的可预见性标准,唯一可预见损害为船坞污染,被告不应对火灾造成不可预见损害承担责任。在过失类案件中,“行为的侵权性”在于行为有过失,限制责任的范围在于行为有过失之风险。古德哈特(Goodhart)坚持“可预见性是过失的一个推论”,认为行为只能相对于特定结果为过失规则,被告对不可预见、并尽合理注意不能避免之结果承担过失责任,无疑是不合逻辑的④See A.L.Goodhart,"Unforeseeable Consequences of a Negligent Art",39 Yale L.J.(1930).。道伯斯认为,近因是过失规则的推论。在Tetro v.Town of Stratford⑤189 Conn.601,605,458 A.2d 5,7-8(1983).案中,法院认定“近因标准是确定实际发生损害是否与被告过失地制造可预见风险具有相同的一般性质的审查标准。”在赔偿范围问题上,可责性与赔偿标准是相同的,将救济限于可预见损害,估算赔偿额应与确定责任的根据保持一致,以解决在过误方与无辜方间分配损失的问题。可见,可预见性标准与过失规则、责任范围、赔偿损失间具有归因性问题的一致性。可预见性理论可同时适用于注意义务与近因要件之判断,使责任成立与责任范围标准获得法律适用的统一。
(三)公正性
依法经济学分析视角,对无法预见之损害予以赔偿未能激励行为人施加更高的注意义务,徒增社会治理成本,行为人负担事故损失毫无效率可言[24]。实证经济学理论将侵权规则建立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芝加哥学派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表明重新配置资源获得利润若大于实际损失,重新配置则比初始配置提高部分分配效率。在侵权法领域,公平即等于效率[25]。可预见性标准仅要求行为人对其不当行为之可预见性范围内损害承担责任,可避免对行为人责任过苛要求,反映出公正性理论观点。于受害人而言,可预见性标准将行为人法律责任延伸到一切可预见损害赔偿范围内,即便有介入原因成为最终损害之法律原因,初始侵权人仍未免除初始责任承担,受害人权利救济得以及时保障[20]58。于行为人而言,侵权行为人只在自己可合理预见之风险范围内承担责任,斩断不可预见之因果关系链条,避免行为人承担超出合理预见之风险。美国《侵权法第三次重述》认为,可预见性标准使行为人对最初侵权性行为负责之原因施加责任限制①See ALI,Restatement Third,Torts Liability fo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arm,Chapter 6-Scope of Liability(Proximate Cause),§29 Limitations on Liability for Tortious Conduct,Comment e.Rationale.。申言之,行为人秉承对自己行为负责之精神,受公正性观念权利保护之慰藉,以此建立可预见性理论核心之宗旨。
可预见性标准在面对个案侵权事实时,提供了一项足够灵活的标准以容纳对公正性价值的考虑。可预见性的评判标准是客观的,裁判者以行为时合理谨慎之人的可预见性损害角度出发,遵循ARP原则(average reasonable person)即“普通旁观者”传统②ARP原则坚持认为危险及其预防必须根据“客观”标准评估,阐释其负有实质注意义务及与其相适应行为。宋敏:《论侵权法上的义务》,博士学位论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7年。,坚持客观、公平原则以对因果关系之客观性公允评价,对行为人事实行为进行价值归属判断,通过价值判断使因果关系最终成为归责工具[20]59。因可预见性标准具有针对不同场景判断预见性的灵活性与妥当性,故其易沦为裁判者恣意操纵因果关系审查之手段。由于对事件描述的宽泛,发生后果的“类型”与“发生的方式”和“范围”间的区别易产生所谓公平分配不良运气的负担结果而被操控[26],但实则不然,操控的任意性问题可从裁判权的控制角度寻求解决以实现理论本身内涵。若裁判者真能站在客观公正立场适用此标准,其既能兼顾并协调行为人与受害人间的利益平衡,又能坚持因果关系客观性判断,无疑凸显出理论制度的公正性与优越性内涵。
可预见性标准如若应用于我国司法实践,必然离不开公正性价值判断、适当法律政策考量因素,以便呈现适用标准较强的社会妥当性。所谓“法律政策”③一般观点认为,法律政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法律政策是指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将国家或社会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考量原则或标准;狭义上的法律政策则指以个人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为原则的考量标准。赵克祥:《论法律政策在侵权法因果关系判断中的作用——以英美侵权法之最近原因的分析为中心》,《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4期,第61页。指被认为与责任问题直接相关的社会生活实际考量要素,须主观观念与客观事实相互权衡以体现社会观念价值性判断,考察所发生损害是否为谨慎之人可预见性范围,而非主观性任意决断。责任的不公正或不可预见表述之政策仅是事实上相信其他限制责任基础的替代物。实则法律政策观念事关社会公共利益,代表一般人的价值判断与道德标准[27],意在使社会团体成员之经济或政治福利得以整体改善,即便个人权利遭遇限制,政策也应贯彻落实[28]62。法官依据公平比例原则考量“风险实现之可能性、实际损害严重程度及降低风险所需费用间存在的适当关系”以便具体论证价值取向或政策考量之功能与价值④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3)万法民初字第08303号民事判决书。,本质属于自由裁量权范畴。在英美侵权法中,可预见性标准之政策考量因素可分别体现于过失规则与因果关系认定之中,然对于我国司法实践,基于受害人本位的救济目标及成文法国家传统,如若过失阶段就以政策因素否定过失成立,易造成受害人权益的不当剥夺,受害人权利救济必然难以保护。笔者以为政策考量于过失规则中应审慎应用,在过失要件或注意义务成立后,政策考量在法律因果关系认定上妥善运用,并以之合理限制责任范围,达到双方当事人利益平衡以实现侵权责任法立法目标。
四、可预见性理论于因果关系认定的借鉴意义
(一)外国司法实践
可预见性标准之适用、研究多见于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认为,“在故意侵权案件中,排除可预见性标准对因果关系问题的适用。”①ALI,Restatement of the Law,Second,Torts,§ 435A Intended Consequences.《侵权法第三次重述》强调:“大多数法院均在过失侵权案件中采纳可预见性标准用以限制责任范围。”[29]“损害结果确属‘高度异常’发生者,被告便可不对此高度异常结果承担责任。”②See ALI,Restatement of the Law,Second,Torts,§435 Foreseeability of Harm or Manner of Its Occurrence.英美学者认为:“在性质严重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侵权行为中,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范围无疑比单纯的过失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范围更宽泛,因为前一类案件,责任与过错不成比例的可能性要更小。”[30]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曾发表意见:“故意行为产生后果有相当性者,加害原告之故意行为排斥远因问题。”《欧洲侵权法原则》规定:“保护范围受责任性质影响,在故意侵害利益时,利益的保护程度更高,利益受损的可预见性要求可以放宽。”[31]59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侵权行为场合,可预见性标准并无适用余地,但也有极少数例外情况,如以“蛋壳脑袋(eggshell skull)”案件闻名的Dulieu v.White&Sons案,英国王座法院认为:“即便被告不能预见原告特殊体质并侵害,也非为减免责任之合理事由。”鉴言之,若仅因行为人未实际预见原告特殊体质就排除事故损害救济,对没有过错、未施风险之受害人实难谓公允[32]。世界各国法律绝大部分存在一种倾向,即在侵权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时,倾向于认定因果关系成立,但却没有考虑发生侵害后果之预见性问题,考虑范围多以过失为限,后再以近因之名附以预见性问题。实则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于某结果是否归咎于某原因予以甄别,即损害归责的方法问题,自然区分于普通意义下之因果律[33]。又如决定责任范围的重要参考因素繁多,如理由与动机的道德可归责性、诸行为所追求或预示的损害严重性、行为偏离合理注意之程度范围等③又如在南非,法庭对法律因果关系的处理,会综合考虑以下因素:合理可预见性、直接性、是否存在独立介入原因、法律政策、合理性、公平与正义(reasonable foreseeability,directness,the absence or presence of a novus actus interveniens,legal policy,reasonability,fairness and justice)。See James Grant,"Permissive Similarity of Legal Causation by Adequate Cause and Nova Causa Interveniens",South African Law Journal,Vol.122,Issue 4,2005,p.896,n.4.。可见,侵害后果的预见性问题对于世界各国司法实践都是一大难题。
(二)我国司法实践
在英美法系国家,早已将可预见性标准作为确定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重要原则,而在我国司法实践,由于理论研究的粗糙性及实践对理论借鉴的滞后性,可预见性标准应用于判断因果关系或责任范围的案例甚为少见。审判实践过程中,当事人时常有意无意间使用可预见性标准用于判断因果关系,有时未将可预见性标准间接限制因果关系,而用于直接限制责任范围,但在以可预见性为原则限定侵权损害赔偿范围时,又不能提供充分法律规范、法理及实践依据,故审判实践对该原则无法认可(袁田诉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④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云高民一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其次,可预见性标准的适用在因果关系认定上时常表达不清、界定不明,导致司法审判结果无法直接采纳该标准,部分判决存在语言表达上的偏差及逻辑关系混乱等表述问题,如“法律上必然可预见的因果关系”(周国全诉乐山市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⑤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3)乐中民初字第2605号民事判决书。或“无法预见多层因果关系之后的结果”(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案)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沪高民四(海)终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等错误表述方式。再次,重大过失场合一般排除可预见性情况之适用,即便适用也应是责任范围限制问题,但审判实务中仍有审查标准在因果关系二阶层前后不分等问题①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4)甬东民初字第490号民事判决书。。实则因果关系构成要件本身能发挥限制责任范围的功能,在因果关系认定中统一规定可预见性标准用以判断责任成立与责任范围,既能减少法律成本支出,又能减少因果关系二分法的质疑,间接作用与直接限制功能并没有明确界限,严格责任与非严格责任背景下均可以融贯。针对我国目前司法审判现状,可预见性标准于我国侵权责任法之因果关系认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可预见性标准对因果关系认定的借鉴意义
1.加强侵权法风险管控功能
侵权行为促成了风险意识法律化常态,将风险范围直接管控于合理界限内,使得风险防范意识形态稳步提高。现代经济分析法学越发强调事先风险防范管控功能,依据风险态度反映将风险分为偏好者、中立者及规避者三种类型,在行为人与权利人间权衡风险成本与利润收益拟解决侵权损害的可预见性问题。在过失的认定路径上往往采用“积分式”方法用以比较风险与收益的大小,按照实践意义上的可预见性,行为人之行为评估在于权衡损害发生之可能性、可能发生损害的严重程度及避险成本等因素,而后该行为仍有过失者,发生损害则为限制责任范围之风险。然则当实际损害只是严格责任条件下的非过错因素,实践意义上的可预见性用以限制责任的理由依旧合理与现实吗?
初始侵权人因缺乏注意义务产生初始侵害并滋生众多损害,基于风险范围的预见性,过于遥远损害者必然须及时排除与移转。在过失类侵权案件中,将过失侵权的合理注意限于可预见性风险,因缺乏法律上因果关系的筛选,仍无法挽救损害事故之风险标准。然则“制造责任的理由也应限制责任”,进入“风险清单”范围的风险因附加近因上的可预见性(即理论意义上的可预见性)使得事故事由再度筛选。“风险清单”范围似乎是庞大的,政策考量又涵摄“价值层级因素”“行政因素”“环境因素”“保险因素”“道德因素”及“社会保障因素”等多重参考因素[28]65-67,且各影响因素间表现方式不尽相同,或表现为彼此合作,或表现为相互竞争[34],此错综复杂之参考因素正是加强侵权风险范围管理、控制与警示、预防未来风险之有效途径。侵权法则之中心思想在于直接形成行为人与权利人间的风险防范功能,确立社会普遍性风险的一般预防,根据各因素间的强度与方向为评价主体寻得妥当权益分界点,精细化价值取向,以此逐步完善风险管控之防御机制。近因上的可预见性符合侵权法之中心思想,将非限责性事故进行过滤,细化损害赔偿范围,加强侵权法之风险管控功能,有利于建立法律合理管控机制,为完善侵权法之因果关系认定条款奠定理论基础。
2.培养行为人发展风险抗辩思维
“发展风险”又称开发风险,是指在投入流通时当时科技水平无法发现或控制,后被证实确实存在的产品致损风险[35]161。发展风险抗辩是行为人对风险无法预见从而行为与损害间无近因之抗辩,若有主张侵权损害赔偿事故者,便可以“发展风险”思维主张抗辩。发展风险抗辩与可预见性规则间存在密切关联,在产品追责方面生产者只对投入流通时可预见之风险承担责任,对后续发现、行为当时无法预见之风险免除责任,其不仅与过失责任相契合,与严格责任也不矛盾。
在过失侵权案件中,美国大多数法院承认发展风险抗辩主张②See Bexagia v.Havir Mfg.Corp.,60 N.J.402,290 A.2d 281 (1972);Balido v.Improved Mach,Inc.,29 Cal.App.3d 633,105 Cal.Rptr.890(1973).。如果从整体上认识过失成立要件,过失之认定需要考虑所有可能发生之风险,若以“事后认识”之审查视角判断行为当时预见路径,易引发实际损害全部或几乎都处于风险范围内,可预见性标准对限制责任路径将毫无意义。若拒绝采纳开发风险,将造成不确定性潜在责任,可能带来灾难性损害结局,更具说服力之政策考虑在重要性上完全可能超过那些注意文法纯正者追求之目标[35]161-162。在严格责任侵权案件中,现实存在某些损害如此新奇并极不可能发生者,侵权人承担责任显然极不妥当③See Benjamin C.Zipursky,"The Many Faces of Foreseeability",Connecticut Insurance Law Journal,Fall 2000,p.158.,此时必然须以法律上因果关系或近因要件判断考虑可预见性思考范围。“可预见性对责任范围的限制”看成近因而非过错问题,通过“近因”之名以可预见性限制责任与尽到注意义务之风险程度甚少关联,主张发展风险抗辩思维缓解严格责任对行为人的过度严格性,排除行为人非能承受并不必承受之损害,亦是减少与缓解社会矛盾冲突之应有之义。概言之,无论在过失要件抑或严格责任条件下均可主张发展风险抗辩思维,使得行为人在损害赔偿范围上划定有度,减轻侵权人赔偿责任负担,消减权利人利益保护过度现象,调解社会失衡体系,辅助实现侵权责任法之风险管控功能。
3.建立侵权体系不同类型损害赔偿机制
德国法学家格哈特·瓦格纳(Wolfgang Gerhardt)曾言:“侵权法因风险与损害类型之发展而随之变化。”[36]在侵权责任事故中,可预见对象主要指损害“类型”,而非具体损害“过程”与损害“程度”。侵权损害事件之通常发生者常易引发多种损害发生事故,侵权损害事件按不同分类标准可分为多种损害类型,按损害性质可分为人身损害与财产损害,按是否含有介入因素可分为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按损害发生次序,可分为原发性损害(或称初始损害)与继发性损害(或称后续损害),笔者以损害发生时间为分类标准将损害划分为即发性损害(或称即时损害)与潜伏性损害(或称将来损害)以期探讨可预见性标准于不同类型侵权损害的作用及影响。
侵权法具有不同法益在不同程度的社会公示性,权益的公示性及公示程度决定权益的损害是否能够可预见及预见程度之范围,损害的多样性因具有不同程度的公示性以体现侵权法益的对世性从而达到侵权抗辩之基础。不同类型的损害时常体现不同的法律可归因性,潜伏性损害的隐匿性很难期待行为人在行为当时能够预见,行为的法律可归因性明显较弱。若因行为人轻微过失便苛以灾难性巨额赔偿,即便受害人确属遭受此实际损害,未免仍有脱离法律面向未来之“规范意义”①规范意义指,在效力上包含“应当”或“应然”含义,与实然性状态相对,具有准则性及约束性效力以作为人们行为准则之标准。[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2页。,此亦是“发展风险抗辩”的制度基础。但是,科学研究的进步性使我们越来越能够经常在特定损害和很久以前发生之风险间建立必要条件关系[31]101。即便损害是将来甚至很远将来之损害,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及有效信息积累仍可支持某些因果关系成立。通过现有科技以“事后认识”之审查视角对因果链进行回溯,发现潜伏性损害存在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如若行为当时技术水平没有达到可预见程度,法律便不能要求行为人以超过通常人之高度技术水平加以预见,否则将超出法律可归责性的基本要求。对于无须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就可预见之潜伏性损害相对于须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才可预见之潜伏性损害存在较强的法律可归因性,但相对于即发性损害,行为的法律可归因性还是较弱,而对于事件发生很久后才出现的新损害,归因性明显应略微谨慎。侵权损害之可预见性的理论建构在于固有的不确定性[37],其是衡量归因性的重要依据,影响负担损害赔偿责任之最终结果。通过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确定赔偿责任范围时,行为与结果间可预见关系的密切性间接影响行为的法律可归因性,决定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风险的准确性。针对不同类型之侵权损害,行为人承担不同程度的损害赔偿责任,归因性越强,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自然越高,不同损害事实间理应审慎区别对待,如此既能保障行为人权益,又能安抚受害人心理,以便在双方当事人间实现侵权法益之利益平衡,为将来立法规定可预见性程度及相应行为的法律可归因性提供有效的借鉴意义。
五、结语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与部分高级人民法院虽出台了部分关于预见性程度及归责性范围的规范性指引用以限制责任范围,但在司法实践中,限制赔偿范围的可预见性损害,多以非有机的局部类型化方式展开。尽管司法判例中涉及诸多人身与财产类型损害,但因未形成固定化、成文化的可预见性一般规则,有些赔偿项目(如异常体质损害)是否以可预见性限制赔偿责任范围,不同法院判决仍截然相反。冲突判决的产生无疑与基本立法条款的欠缺直接相关,裁判者自由判断余地的宽泛,政策考量因素标准的欠缺,均易间接导致司法判决冲突局面的发生。实则可预见性标准于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可预见性规则的建立有利于加强侵权法风险管控功能、培养行为人发展风险抗辩思维、建立侵权体系不同类型损害赔偿机制,使得因果链条回溯指引更加精确化、体系化,最大限度减少同案不同判局面的发生,以此平衡各方当事人侵权法益。在形成以可预见性规则为中心的开放式法律原因判断体系中,可预见性标准与因果关系认定中的其他理论学说之间应融合、互补,发挥可预见性理论在构成责任与划定责任范围中的突出作用,并重视与其他因素的协同影响①例如,在意大利,法庭与学者对于因果关系的处理,就用了五种方法:必要条件理论(the conditio sine qua non theory)、可预见侵害事件理论(the theory of the foreseeable tortuous event)、相当因果关系理论(the adequate causation theory)、法规目的(the purpose of the rule violated by the wrongdoer)理论、事实权威(lordship on fact)理论。See Pier Giuseppe Monateri& Filippo Andrea Chiaves,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aws,Tort Law,Supplement 8.Italy(PartⅡ),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4,p.371.再如,在荷兰,已放弃了先前主流的充分原则(adequatie doctrine,即相当性原则——引者注),采用可归因审查,因而除通常的可预见性之外,其他问题也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损害的类型和错误的可归因程度都具有决定性意义;错误越严重,损害越可能归咎。欧洲民法典研究组、欧盟现行私法研究组编著,[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全译本)(第5、6、7卷),王文胜、唐超、李昊译,法律出版社,2014,第594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以上解释来看,荷兰法所谓“可归因审查”,其关注的问题包含但不限于因果关系,因为“损害的类型”和“错误的可归因程度”并不是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待实践中类型损害及司法案例的充实、丰盈,加之比较法经验的妥适借鉴及学术理论的深入研究,有望形成法律上可预见性一般条款与实践上具体经验相结合的侵权责任限定机制,以此建立动态、开放式的法律原因判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