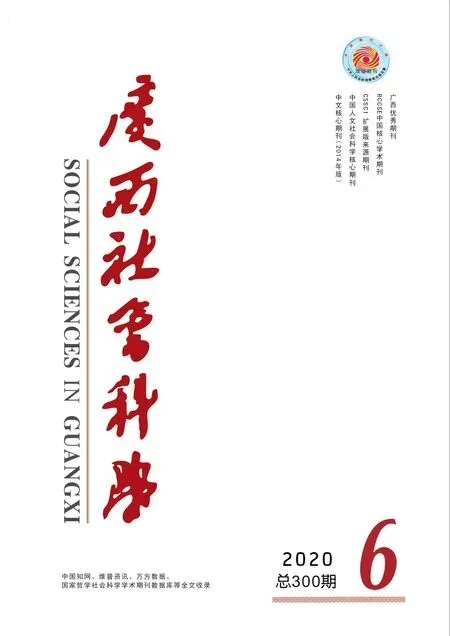救亡与审美的融通
——全面抗战时期叙事诗的艺术演进
2020-03-11
(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从被朱自清誉为“新文学中第一首叙事诗”(见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诗话》)的《十五娘》[1]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现代叙事诗随文学生态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整体上体现为三个发展阶段:1920年到1926年是现代叙事诗的初创期,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中国现代叙事诗的第二个阶段,而卢沟桥事变爆发则是中国现代叙事诗进入第三个阶段标志[2]。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抗战文艺动员的民族救亡需要,使内容丰富、篇幅较长的叙事诗暂时被富有煽动性、篇幅相对较短的革命现实主义抒情诗所替代。但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诗人们从最初的激情中冷静下来,抗战激流中见闻的丰富,以及在战火之中的洗礼,加深了对社会、民族、普通民众以及自身所面对的问题的思考,想要抒发的强烈的情感已经非一般短诗所能容纳,使得诗人在战时文学生态下对民族救亡需求与艺术审美追求作出了主动调适——“三十年代常见的那种纤弱的诗风和精致的意象结构被一种精力四射,雄浑壮阔的美学追求所替代”[3],艾青、臧克家、柯仲平、邹荻帆、王亚平、江宁等一大批诗人纷纷倾力叙事长诗创作,推进了叙事诗艺术的演进。
可以说,抗战全面爆发后叙事诗的发展,是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叙事诗的一个发展高峰,也是诗人们历经战火与硝烟,对现实认识深入发展和个体生命体验不断丰富,实现救亡与审美融通后的一个结果。
一、诗歌在抗战救亡中走向新的抒情
徐迟在亲历战争之后创作完成的《抒情的放逐》一文中曾说过:“也许在逃亡道路上,前所未见的山水风景使你叫绝,可是这次战争的范围与程度之广大而猛烈,再三再四的逼死了我们的抒情的兴致。你总是觉得山水虽如此富于抒情的意味,然而这一切是毫没有道理的;所以轰炸区炸死了许多人,又炸死了抒情,而炸不死的诗,她负的责任是要描写我们的炸不死的精神。”[4]这段话充满感伤气息,而徐迟所说的“抒情”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与现实的惨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或多或少地倾向于“歌颂”了。显然从现在回头去看那段历史,我们多少会觉得徐迟用是否具有以大自然为中心的古典感受作为诗歌抒情性的判定标准,不论是引用刘易士、艾略特,还是叶芝、奥登[5],其所指代范畴都相对狭小了些,甚至将诗歌艺术有意引入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之中,忽视了中国新诗发展在全面抗战时期所面临的独特生态。因为,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诗人们在向西南、西北等后方的撤离之中,虽几经战火,甚至是生离死别,眼见了许多战火之中的惨剧,但无论是站在民族救亡立场上的抗战宣传,还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发出的对敌人的诅咒,事实上也都是一种抒情的方式。与现代主义的浪漫的、唯美的抒情不同,它更转向了对现实的关怀。谭君强在《论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诗歌叙事学》一文中曾指出:“无论在诗人的写作中,还是在读者或欣赏者对诗歌的欣赏与解读中,都不会将抒情与叙事完全割裂开来……叙事诗中包含着抒情,或抒情诗中包含着叙事,在诗歌中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二者有时融为一体,难分难舍。”[6]所以,也正如穆旦所说:“假如‘抒情’就等于‘牧歌情绪’加‘自然风景’,那么诗人卞之琳是早在徐迟先生提出口号以前就把抒情放逐了。”[7]所以他认为:“如果放逐了抒情在当时是最忠实于生活的表现,那么现在,随了生活的丰富,我们就该有更多的东西。”[8]也就是穆旦所提出的“新的抒情”,这恰恰是新诗在新的生活或是文学生态下抒情的新发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全民族抗日救亡的激情冲击着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文艺队伍空前团结和凝聚,许多诗人疾呼着“伟大时代”的到来,纷纷唱响了救亡的诗篇。如果说自有诗歌以来,抒情就与诗歌如影随形,那么这一时期的诗歌仍然保留着这一抒情传统,甚至是更为炽烈的抒情。在诗歌大众化运动背景下,以高兰为代表的朗诵诗创作和诗歌朗诵运动,高唱着《我们的祭礼》,不仅“打开了新诗朗诵运动”[9]的局面,而且将诗歌中的情感直接通过朗诵者传达给听众,如高兰的《哭亡女苏菲》中痛失爱女的悲痛、悔恨、憎恨等情绪,每每朗诵都令听者动容。相反的是,缺乏情感的诗歌在诗人们看来不适宜朗诵。所以,臧克家说:“雄壮的诗使人听了奋发,悲哀的诗使人听了落泪,快乐的诗使人听了起舞”[10]。如朱自清的诗歌《不怕死——怕讨论》:“我们不怕死/可是我们怕讨论/我们的情绪非常热烈/谁要叫我们冷静的想一想/我们就撕他捅他/我们就大声地喊……无耻的阴谋家”[11]。诗歌情绪爆发激烈而充满力量,就如诗中所说的“我们只有情绪”“我们全靠情绪”,这种情绪在诗歌中的显现正是抒情。
除朗诵诗外,还有街头诗、方言诗等体式作品的创作,同样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的诗歌大众化运动中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都在为点燃民众抗战的热情而激烈的呐喊着。如林山的街头诗《给难民》中,向裹挟着疲于奔命的难民们呼喊着“去打仗呀!去报仇呀!去把鬼子赶走呀”,黄宁婴的粤语方言诗《边个重敢话?》中愤怒地叫骂着“汉奸种!杀绝他,杀绝他”!这些诗歌都充满着浓烈的抒情,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邹荻帆“折芦管吹奏故国的曲子,用泪水润着歌喉,低唱着‘故国呵……’”[12]的感伤情调和卞之琳等人浪漫的抒情不同,普遍高扬着中国诗歌会所倡导的“时代感与战斗性相结合的大众化写实诗风”[13]。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想象的、浪漫的、唯美的抒情暂时在抗战激情的喧闹中压低了声音,现实的抒情成为抗战初期诗歌审美的重要向度。这一时期之所以会形成“抒情的放逐”的观点,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于诗歌参与现实和干预现实的功能超越了审美功能,这是对时代需求主动回应的结果。因为在全民族伟大的抗战斗争中,“诗人们的诗篇,也必须是帮助这种神圣的战争”[14],所以诗歌朗诵运动、街头诗运动、方言诗运动等对诗歌大众化的实践路径不断被开拓,饱含着整个民族战斗的呐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抒情。显然,抗战初期的抒情已经因生态环境的变化而轰轰烈烈地将中国现代新诗引向了新的方向。
与此同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艾青、臧克家、卞之琳、胡风、穆旦、闻一多、王亚平、臧云远、柳倩、何其芳等人,不仅在撤离到西南的路上几经波折,而且许多诗人还以多种方式体验到了战争的残酷,目睹了战争的惨状和中华民族生活的现状。例如,穆旦曾参与到中国远征军中,在留下中国远征军累累白骨的野人山历经九死一生,所幸终于回到国内,这些经历成为他诗歌中最为重要的素材和思想源泉。臧克家、邹荻帆、王亚平、柳倩等诗人长时间在战区从事战地文化工作,对他们诗歌创作有重要影响。何其芳、卞之琳、林山等人在西北解放区不仅积极从事文化工作,而且接触到了红色根据地不一样的文化环境,卞之琳虽因这段经历遭到川大辞退,但这对他诗歌观念有着深刻影响;还有老舍、杨骚等人参与的战地服务团,在文化界都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经历对于诗人们而言,最重要的意义是为他们的生命体验注入了新的元素,感受到了书斋与外面现实世界之间巨大的差距,从而在带来心理震撼的同时,更为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活力。
短小精悍的“战歌”随着抗战的持续和诗人们对现实体验积累的增加,已难以承载一部分诗人抒情的需要。例如,臧克家曾在抗战全面爆发初期所创作的《我们要抗战》《别潢川》等诗歌中呼吁:“诗人呵!请放开你们的喉咙,除了高唱战歌,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15]但在抗战后期,他却对此表达出了颇多遗憾。所以,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进入抗战相持阶段之后,文艺界几乎一致进入了反思的阶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的激情减退了,高调的呐喊声也变得嘶哑了,而诗人们对于现实的积累终于再次迎来了叙事诗发展的一次高峰。王亚平在谈到他创作叙事诗《湘北之战》的经历时,也自我总结认为:“这试验是失败了,内容太复杂,偏重于事实的描绘,忽略了诗的真正抒情。”[16]所以说,向新的抒情的进发是新诗的自我发展目标,是战时生态下诗人们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实践和对新的现实适应的结果,也是新诗对自我的新的解放和革命,在现实的描述、故事的叙述中,叙事成为诗歌表达和抒写情感的一种途径。“叙事诗顾名思义就得叙事;但它是诗,又得抒情,因为诗毕竟是以抒情为其职能的。由此看来,抒情化叙事是叙事诗艺术追求的核心内容。”[17]
所以,如果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在文艺为抗战服务及诗歌大众化运动中所发展起来的朗诵诗、街头诗、方言诗及其他的现实主义诗歌和现代主义诗歌,或多或少都显现出为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服务而充满了政治抒情色彩的话,那么,20世纪40年代初到抗战结束这段时间的长篇叙事诗,则因它承载了诗人们在这个史诗般的时代中“对抗战本质的认识、对战时生活的理解、对未来的渴求以及自己深沉的思想”[18],从而在延续写实性的“时代感与战斗性相结合”的诗风而富有政治抒情色彩的同时,又增添了历史抒情的色彩,使诗歌的抒情走向广度和深度。
二、诗歌内容随现实体验深入而丰富
胡适认为:“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19]而不论是诗歌的形式,还是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变化,都依赖于一定的生态环境。艾青曾指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由于现实生活的不断的变化所给予他的新的主题和新的素材,由于他所触及的生活的幅员之广,由于他所处理的题材,错综复杂,由于他的新的思想和新的感觉的浸润,他已繁生了无数的新的语汇,新的辞藻,新的样式和新的风格。”[20]因而可以说,新诗对救亡与审美的融通是以诗人在现实中的生与死、血与火的体验,对个人、国家与民族的思考为基础,具体体现在叙事诗内容上的丰富。
文学讲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总是要置身于其所身处的时代并反映这个时代。中国现代新诗从第一首叙事诗《十五娘》开始,每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所创作的叙事诗,虽然发展的状态和成绩各有差异,并整体上随现代新诗的发展而趋于成熟,但总体上都体现着那个时代所独有的风貌。在现代叙事诗初创期的1920年到1926年,是五四运动方兴未艾之时,五四运动所倡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军阀混战下中国社会的深重灾难以及“新青年”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等成为时代的主题,刘半农的《敲冰》、郭沫若的《洪水时代》、玄庐的《十五娘》、朱湘的《王娇》、冯至的《蚕马》《吹箫人》等作品集中反映了这些内容。但是,“这种现实主义的生活反映是广度有余而深度尚嫌不足的:以神话和历史题材写成的叙事诗占了较多的份量,写爱情婚姻的也多了一点,从审美情调看,未免凄迷和飘忽了些”[21]。作为中国现代叙事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段时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内外交困的时期,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愈加残酷,人民大众在阶级压迫下的苦难生活及其反抗等富有时代感的现实主义内容,在现代叙事诗中占据了主流。殷夫以自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经历写就的叙事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不仅以现实主义笔法描述了革命斗争中血雨腥风的现实生活,而且以较高起点开启了叙事诗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蒋光慈的《乡情》、罗澜的《暴风雨之夜》、杜力夫的《血与火》、蒲风的《六月流火》、臧克家的《自己的写照》、柳倩的《震撼大地的一月间》等作品也分别从不同角度书写了这些内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族矛盾成为压倒一切矛盾、斗争的重中之重,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民政府经营西南、建立抗战大后方等一系列在战争逼仄下形成的新秩序,以及诗人们在战火之中所历经的一切,构成了叙事诗在新时期发展的新生态,从而也为叙事诗的创作提供了新的丰富的内容,叙事诗创作也进入一个繁荣的时期,“概括生活的广度,反映现实的深度,这时期的现代叙事诗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时期”[22]。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的叙事诗如朗诵诗、街头诗等大众化运动的诗歌产物一样,内容更追求于直接地表现在战争中人民的遭遇、英雄的事迹等,以适应抗战文艺动员的需要。像田间的《她也要杀人》就集中以战争中民族仇恨的怒火和抗战的鼓动性为基调,塑造了白娘这个反抗者的形象,她在家破人亡、遭受侮辱后,从一个蚂蚁也不敢踩死的善良农村女性被逼得“要杀人”了,几乎延续了田间善于在对比之中显现矛盾冲突的抗战诗歌的写作方法,集中于抗战内容的书写,也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这类诗歌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就是在内容上直指抗战救国的民众动员,取材相对集中,更为直接地体现出服从和服务于抗战文艺动员的时代要求。
叙事诗创作的高潮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仅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叙事长诗就有臧克家的《淮上吟》《古树的花朵》《向祖国》《感情的野马》,艾青的《火把》《吴满有》,还有柯仲平的《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江宁的《难民行》、杨刚的《我站在地球中央》、邹荻帆的《木厂》、老舍的《剑北篇》等作品。经历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激荡的抗日热情,在战火与硝烟之中的辗转迁移,前线的血与火的考验,后方无休止的轰炸和近在咫尺的死亡、工作的流离、物资的匮乏、生活的无着落,诗人们接触到了更多的社会现实。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和激情的消退,更冷静的思考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所见所闻的累积,无疑成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最为丰富的内容。臧克家《古树的花朵》中的“新型民族英雄”范筑先、艾青《雪里钻》中历经枪林弹雨的战马以及《他死在第二次》中对祖国怀有崇高感情的受伤后又参加战斗的农民战士等,都是直面战争,以战争中的人、事、物等为主要内容的叙事诗。虽然写法上有全景式的、片段式的,也有特写式的,但战争必然是叙事诗的主要书写内容。但是,战争如果是这一阶段唯一的内容,那么与抗战全面爆发初期相比又还有何发展?
显然,激情消退和对社会了解愈加深入的诗人们,不会仅仅将目光投注在战争之上,而是“怀着‘复仇的哲学’挣扎在‘暴戾的苦海’里,为自由、民主和人民的不幸命运献出了一首首郁愤的悲歌”[23]。如艾青在离重庆去延安之前创作的叙事长诗《火把》,将他身处重庆期间所感受到的国统区纷繁芜杂的社会书写了出来,诗中以唐尼在李茵启发和游行的火把所象征的抗日力量的强烈感召下的心路变化为线索,整合了在侵华日军战火下遭受蹂躏的同胞们凄惨的遭遇、青年对爱情的憧憬、投敌汉奸奴颜婢膝的可耻嘴脸等时代内容于诗歌之中,融象征、抒情于叙事之中,激昂地高喊着“我们是火的队伍,我们是光的队伍”,要那些“软弱的”“卑怯的”“昏睡的”“打呵欠的”都滚开,呼号着“我们来了,举着火把”,想要以游行队伍发出的如“霹雳的巨响”,去“惊醒沉睡的世界”。这里,诗人想要惊醒的何止是唐尼,更是整个中华民族,是那些不愿意“同奴隶结婚”、不愿意“做奴隶儿子的母亲”、不愿意“直到死做个奴隶”的人们!整体上看,诗歌的内容已超出简单的战争动员,也超出了对现实的简单描述,更是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从一个守着“向自然界的猛虎复仇”祖训的贫农家族几代人的悲剧命运,深入到向戕害自己的命运之神复仇,继而在觉悟后才意识到,真正害自己的是那剥削和残害劳动者的黑暗的社会制度,也只有用比弓箭、笔更好的武器,才能实现复仇。虽然我们都痛恨这场战争,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战争无疑丰富了这一时期的诗歌内容。
三、诗歌语言随诗歌形式发展而扩容
新的生态环境下的新事物表达的需要及其表达内容的丰富,促使叙事诗在语言上形成了一些新的变化,所以说,新诗的发展还体现在叙事诗语言的扩容上。
姚雪垠在《中国作风与叙事诗》一文中认为:“西洋和印度古代的伟大史诗都是从民间口传文学发展起来的,或者是天才诗人根据民间口传文学改造制作的。这一方面说明了民众创造力量的伟大,一方面说明了史诗同民众的密切关系。”[24]从较早的白话诗中白话的确立,再到方言入诗,以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间歌谣、民间谚语、俗语、俚语、鼓词、小调等的入诗,新诗自诞生以来,始终在探寻着诗歌语言发展的问题。从新诗诞生初期胡适的《尝试集》起,新诗就倡导句子长短不定[25],讲究句子的自由灵活,自然也就对诗歌的长度未加限制。虽然部分抒情诗如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沈玄庐的叙事诗《十五娘》等有一定的长度,但从胡适的《蝴蝶》(初题为《朋友》)、《鸽子》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不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整体上短诗成为创作的主要倾向。“抗战以来,中国的新诗,由于培植它的土壤的肥沃,由于人民生活的艰苦与复杂,由于诗人的战斗经验的艰难与复杂,和他们向生活的突进的勇敢,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多少倍地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充实更丰富了。”[26]不仅朗诵诗、街头诗、方言诗、讽刺诗等诗体纷纷出现,而且叙事诗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也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
相比较而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初期以朗诵诗、街头诗等短诗较多。其中,朗诵诗、街头诗、方言诗等诗歌是诗歌大众化实践的主要成果,而这些诗体由于传播的独特要求,在诗歌长度上有一定的限定。如朗诵诗,既要考虑到便于朗诵者识记甚至背诵,又要考虑到朗诵的时间长度,因而诗歌本身既不能太短,也不能过长,一般控制在数十行到百余行。街头诗主要依赖于街头巷尾墙壁、电线杆、路边大石头等为传播载体,对象是路人,因而在长度上更是需要严格控制,少则三两行,多则不过十余行,从而既便于书写,也便于阅读和阅读后的口耳相传。方言诗所针对的读者以地域为范围,且以普通底层民众为主,其阅读和传播讲究口语化、通俗化,内容与表意集中,因而一般也不长。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诗人们抗战初期激情的逐渐消退,冷静的思考和抗战初期境遇的积累,使得诗歌内容丰富的同时,诗歌书写的长度也在悄然变化着。不仅有艾青的《火把》等上千行的叙事诗,而且还产生了臧克家的五千余行长诗《古树的花朵》、张泽厚的七千余行长诗《花与果实》等长篇叙事诗,与抗战初期,乃至于新诗诞生以来的诗歌形式显现出截然的差异。这些鸿篇巨制,并不是长度的简单拼接,而是对社会复杂而伟大历史的现实描写,是在诗歌长度上对社会历史发展内容的主动适应。
叙事诗,特别是叙事长诗,在内容上由于篇幅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短诗,因而,对语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这并非要求语言更为精练和概括,也并非更为含蓄或是富有表达的深刻意蕴,而是能在满足丰富的内容书写需要的同时,在语言上的不断变化,以适应内容书写需要的同时,显示出语言的丰富性。其实,经过30多年白话新诗的发展和积累,诗歌语言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官方白话的范畴。前文我们也谈到过,不论是早期的胡适、郭沫若等,还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诗人如臧克家、艾青、田间、穆木天、高兰、冯至、穆旦等,他们的诗歌语言以官方白话为主,但同时又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地方方言、俚语、民间歌谣、小调等入诗,从而丰富了诗歌的语言和文化内蕴。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文艺大众化、诗歌大众化运动之中,口语与书面语、方言与官方白话之间的相互妥协、影响,一直在并行着。即便到了今天,不仅日常生活中方言和普通话的影响和转化一直存在,而且还扩散到了网络与书面语言、口语言之中。而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诗歌大众化运动背景下的朗诵诗、街头诗等诗体对民间歌谣、俗语、俚语、谚语、方言等的借用、吸收,某种程度上成为新诗语言“扩容”的一次高峰。相对短小的朗诵诗、街头诗等诗体尚且为适应战时文学生态而在语言上做出了大幅度的调适,更何况内容更为丰富、长度更长的叙事诗。
相对于前20年的新诗发展而言,这一时期叙事诗在语言上延续了新诗语言探索的传统,在适应新的时代内容和时代发展要求的背景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如老舍在创作《剑北篇》时,就尝试了以大鼓调进行创作,他在自述中还说道:“大体上,我是用我所惯用的白话,但在逼不得已时也借用旧体诗或通俗文艺中的词汇,句法长短不定,但句句要有韵,句句要好听。”[27]不论是语言上,还是韵调上,都是老舍在文艺大众化背景下对诗歌创作所做出的一种调整,以适应战时生态的需要。臧克家的长诗《古树的花朵》作为一部战争史诗题材的长诗,虽以主要历史人物范筑先的事迹为主线,但同时贯穿着抗战时期许多大小历史事件和场景,为适应表达的需要,臧克家句式上或长或短、自由安排,语言上多采用如“老太婆们可怜的小脚,挪动着身子,象挪动着泰山……”“飞机,一队刚去,一队又来填,抬头只见飞机,不见了青天”等生动、丰富的口头语言,“形成生活化、群众化、民族化的风格”[28]。《向祖国》诗集中收的长诗《敲》和《“为抗战而死,真光荣”》与《古树的花朵》相似,以丁铁珊、徐铁蛋等抗日战士为主要人物,诗歌用通俗化的口语活灵活现地重塑了抗日英雄形象,突出了“抗战光荣”的时代主题。
四、结语
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必有其时代性任务,这本身也是文艺自身生存价值所在。在抗日战争硝烟的弥漫之中,救亡图存的民族革命现实,首先逼迫着诗人们向现实进发,而叙事诗作为社会具体变动的直接影响产物,总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大量出现,与历史、与时代同行。因此,叙事诗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现实主义特征[29],这种时代色彩和现实主义特征也正是诗人们对时代需求的主动回应。
茅盾在《叙事诗的前途》一文中曾指出:“中国的新诗有一个新的倾向: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二三十行以至百行的诗篇,现在已经算是短的,一千行以上的长诗,已经出版了好几部了……‘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虽然表面上好像只是新诗的领域的开拓,可是在底层的新的文化运动的意义上,这简直可以说是新诗的再解放和再革命。”[30]全面抗战时期是中国现代叙事诗发展的黄金时期,是中国现代新诗在战时生态下的一次沉淀,它在概括生活的广度、反映现实的深度等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掀开了中国现代新诗发展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