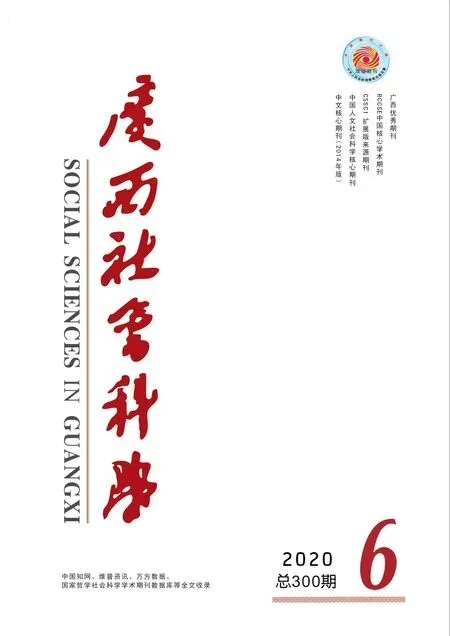走向杂字整理的新境
——从《清至民国岭南杂字文献集刊》说开去
2020-03-11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杂字是明清日常生活中习见的识字读物,采辑日常生活的常用字汇编而成,主要满足民众生活基本用字。它们不仅是讨论明清识字问题的直接材料,还包含着日常生活史的丰富信息。但较之族谱、契约、账簿、碑刻等民间文献的整理,其系统性、规模化的收集才刚刚起步。学界对杂字的关注,至少可追溯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1932年,刘半农从北京海王村公园书摊淘得道光删补本《元龙杂字》,认为倘能获得更古的完本,对语言名物的研究尤为有用[1];1936年,郑振铎注意到几种杂字,认为杂字是童蒙识字所用的基本书[2];1940年,常镜海在分析传统教育选用的蒙学课本时,亦提及十余种清代以来的杂字[3-4];而王重民则在版本目录研究中考辨明代《新编对相四言杂字》的版本[5]。
在欧美学界,较早注意杂字的是曾执掌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部的恒慕义(Arthur Hummel),他在1946年谈及一本首刻于1436年的看图识字课本(《新编对相四言杂字》),并留意到书中包括一幅算盘图;1959年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第三册,指出最早的算盘图例见于该杂字,从而将日常生活中的算盘历史推前了几百年①参见商伟《一本书的故事与传奇》,收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带东亚图书馆编《新编对相四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页。。日本学界在20世纪上半叶也留意到杂字的价值,利用杂字分别对中国法制史、日常教育史和戏剧史做了开创性研究。目前,这些学者利用的杂字主要保存在内阁文库、京都大学图书馆等处②具体包括: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奴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版,散见第一部第九章和第三部第十三、十四章讨论;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类书と庶民教育》国土社1958年版,第126-131页;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刘岳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2010年版;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布和译,吴真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176页。。
虽然以上学者的工作已显示出杂字文献对诸多不同学科具有重要价值,但他们的搜集颇为零散细碎、研究也大都点到为止。相较之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史学倡导“眼光向下”,普通民众各式史料备受瞩目,《清至民国岭南杂字文献集刊》(以下简称《集刊》)就是其中影响的成果之一。《集刊》以岭南地域范围为线索,通过田野调查、网络搜寻、从收藏家处购置等方法抢救征集民间通俗坊刻、手抄杂字百余册。这批俗陋的下层识字读物,在当时主要用于应对民众生活世界(lifeworld)的——用舒茨的术语来说——基本“知识储存”之一部分[6]。因此,它们不仅为捕捉民众日常生活的细节提供了宝贵契机,还推动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历史文献学的构筑,对传承乡邦文化、童蒙文化亦具重要价值。本文主要基于日常生活的视角,择要评述这15册资料集出版的学术意义及其未尽之处。在此基础上,鉴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民间收藏家等处还有海量杂字留存情形,通过比较近年出版的杂字文献样态,借此指出适切的杂字整理规范以期杂字整理走向新境,从而为学界贡献理想的、可资深度加工利用的杂字汇编。
一、《集刊》的重要贡献
《集刊》主要影印广西杂字近20册,其中桂林杂字9册,贺州3册,玉林4册,南宁2册;广东地区杂字70余册,其中广州39册,佛山9册,江门1册,肇庆14册,云浮3册,湛江1册,梅州1册,韶关1册,潮州2册;还有在文化层面受岭南地区影响的香港、东南亚等地杂字近10册。可见,《集刊》包含的杂字数量颇丰,达到百余册,纵使剔除内容相同或相近版本,亦有70余种不同的杂字,种类较为多样。这些不同类型的杂字,大都是以往收集、整理者未曾披露过的。对于《集刊》出版的意义,编者所作绪言有概要说明,认为这些文献对岭南地区的民俗文化、语言文字、童蒙教育等方面有着重要价值[7]。在此以外,笔者基于日常生活史视角,认为这批杂字对以下具体议题的讨论,亦是弥足珍贵的材料。
其一,助推明清以降的基层社会识字史研究。杂字文献是下层民众识字的直接材料,但以往研究注意的是“三、百、千”之类的通用识字教本,相对忽视与乡民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地方性杂字。识字问题研究作为社会文化史的基本问题,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曾满怀期待地认为,识字领域研究的总趋势应是越基础的东西,研究的人越多[8]。确实,在西方史学界识字史的论著早已汗牛充栋,但在中国史领域却一直是极富挑战的课题。对识字问题的专门探讨,自1979年罗友枝(Evelyn S.Rawski)《清代的教育与民众识字》问世以来,并无实质性的推进[9]。一方面既源于中国史领域对民众“识字”的界定充满争议[10],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底层民众识字材料的匮乏。近年来,民间识字读物的大量发掘,无疑为窥探传统中国民众的识字提供了难得机会[11]。
其二,为书写底层群体的书籍史、边缘地域的出版史提供了可能。识字读写能力是阅读行为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大众读者形成的最基本要素[12]。以往中国书籍史研究主要关注士人对书籍的收藏和阅读,对其他阶层使用书籍知之甚少,对普通民众的书籍世界更是几乎处于“失语”状态。然而,这些民间坊刻本虽印制粗劣、手抄本笔迹拙劣,但却使得乡野中文化水平较低的村氓也有可能与印刷文化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日用识字文本的生产流传,主要满足当地和临近市场的需求,即使无法对这些地方性出版进行充分研究,但尝试收集整理这类底层书籍产品,却能弥补以往关注全国性大型出版中心(南京、苏州、杭州、建阳、徽州等)的缺陷,关照到各个小地方的刻书、抄本流通情况。此外,岭南杂字文献不少是在边疆社会流传,因此,对这些杂字文献的整理研究,既绘制了古代中国晚期印刷文化向边疆拓展的版图,也丰富了学界对中国古代整体出版史的认知。
其三,为重新认识“乡土”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等经典议题提供了进一步审视的空间。费孝通曾论述在“乡土性”社会,乡民生活中没有文字的需求,甚至文字既有缺陷又无必要,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13]。这种按人类“基本需要”的功能图式来解释语言与文字的做法,在一个有文字文明的社会复制了“无文字”部落社会的形象[14]。费氏“文字下乡”议题的本意虽是对当时推行平民教育的工作者进行批评,但乡土中国的“无文字”观念却对学界影响深远。近年学者对费孝通知识构成的研究指出他国学功底不深,尤其出于方法论的立场,不太情愿用历史资料分析问题[15]。杂字文献根植于乡土,其生产、流传和使用都与乡土社会密不可分,因而,这些历史上流传的民众识字文本可从社会文化史的维度为“文字下乡”提供直接依据和阐释材料。岭南杂字文献还有其特殊性,即其存在的土壤大都地处明清王朝的边疆,而彼时边疆的土民以口述为主,不谙官语,不识汉字。王朝国家为了有效掌控这一地域,最要者便是文教的普及,尤其是文字的推广工作[16]。但学界以往留意的只是“自上而下”的“同文治理”实践,忽略区域社会自身的因应力量,特别是边疆地区承袭内地传统的民间识字教育传统。然而,恰恰是《集刊》中的材料从民间社会观察文字进入西南社会提供了过程性证据。值得留意的是,这些文本用方言识读,与各种正音书、官话识字教科书不同,是正字、官话之外的知识体系,延续的是一个多语言文字的边疆社会,这种多元性从语言文字使用视角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并置。
其四,推进明清民众日常生活史的总体研究。杂字文献的功能主要是识字,但在文字识读过程中还兼有其他生活知识功用,如《集刊》第5和第10册共收4册《一串珠杂字》①《一串珠杂字》的多种原本要感谢梧州学院王建军教授惠示。此外,在该校民间文献研究中心课题“西江流域的童蒙识字文献整理与研究”资助下,笔者还找到了6种其他版本。。第5册中《蒙学一串珠杂字教科》例言指明“子弟若作工商等艺,将此杂字习熟晓写,胜过读多两卷经书”[17],封面红色字体广告还提示其对礼仪习得的影响“此杂字乃蒙学之书,初等科之要用。不但此也,若系生意场中,甚为好用。有志之子弟诵读者,更益于身心处世之良图也”[18]。又如《集刊》第10册还有抄本《应酬杂字》,抄写者标注“我十五岁时读书抄此杂字”,文本序曰:“盖人生日用,必须应酬,苟于杂字一款,弗先考究,未有不临时阁笔者。余于课读余闲,偶将旧本细订讹字,再加扩充,既分类以各陈,复举物而详载。果能留心记录,勤力观看,将会而通之,类而推之。洵足为酬应之一助,慎勿视为粗浅。”[19]这册杂字包含海味海鲜、衣服、广货、药材、病症等36种不同生活侧面文字,用以满足现实应酬的各类需要,其文本字汇呈现的就是民众日常生活百态。当然,岭南杂字文献中还包含诸多关涉礼仪习俗规范、农业经验传授、账簿文约习得、法律知识的普及等内容,这些文字触及日常生活史诸多重要议题——“礼下庶民”“送法下乡”等。此外,《集刊》还有地域生活特色鲜明的杂字,如专为广州七十二行各类手工业群体识字服务的《七十二行杂字》。因此,透过杂字对这些社会文化史议题的讨论,还将极大推进明清日常生活史的总体研究。
二、《集刊》的部分局限
应该指出,《集刊》的编纂思路主要以地域空间为纲,将杂字文献的文本内容影印出版,这种办法固然抓住了杂字文献最显著的特征——地域性,但将书籍刊刻地等同书籍流通之地,遮蔽了书籍的流动与开放性;而将所有重心都放在杂字文本内容的呈现上,只是彰显了书籍“文本性”与“物质性”正反两面中的“文本性”,忽视了杂字书籍的另一重要面向——“物质性”特征②“文本性”与“物质性”主要是西方古典学研究中提出的概念,在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中也颇受重视。中国中古史学界较早引入并应用到研究中,参见荣新江《唐研究》第23卷《文本性与物质性交错的中古中国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对研究而言,文献的“物质性”传递了文字内容上难以表达的文化意涵,无视杂字书籍的物质形态(纸张、尺寸等)将使文献的原生态信息削弱,大大降低了杂字的研究价值,难免有遗珠之憾。
首先,《集刊》以“岭南”划分文献的收罗范围,主要包括广东、广西杂字,旁及澳门、香港、新加坡和越南的杂字。不过,“岭南”这一概念本身是历史不断建构的产物,是一个变动的地域概念。学者指出清代广东取得了对“岭南”的垄断,以岭南专指广东[20]。因此,在借用区域文化地理概念时要异常谨慎,《集刊》囊括的文献七成是广东的,但其他文献显然超出了“岭南”的范围。退一步来看,即使回到宋代设立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将“岭南”宽泛视为广西、广东,《集刊》中有些杂字也不能归属于“岭南”。如《集刊》第2册所收《七言杂字备览蒙童捷径须知》,该书后附“桂林堂梓行”印记,编者执念于“桂林”而误判为广西桂林杂字,忽略了堂号前“汉南”二字的限定。据笔者经眼内容相同的20余种不同版本的该种杂字,以及结合杂字中地方性知识判断,此杂字主要在陕西、山西、甘肃交错地带刊刻,而不可能是岭南地区杂字。同一册还有《六言杂字》也不是桂林的杂字,而是湘西一带的,这册杂字前有缺页,无题名和书坊信息,难以判断其地域。不过,文本中教导诉讼的文字提到:“常德府衙递纸,澧州道台跟□,布政按察投到,长沙抚院伸(张?),总督大人具告,五府六部通传”[21],这些针对读者的“地方性”律法知识提示该杂字主要是在常德府流通。再如,《集刊》第3册所收《新刻七言杂字》,编者归属于广西南宁的杂字。但据笔者经眼内容相同的其他版本,却主要是在湖南长沙和湘中的邵阳各大书坊刊印。因此,用行政区划作为杂字书籍区域性的参照系,可能会产生不少误导。毕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并不重合,而杂字书籍是区域文化的产物,存在跨政区的流通,兼具地域性与跨区的可能。用行政区域约略划分杂字书籍的方域,只是权宜之计,研究者对此须心中有数,保持清醒。
其次,搁置杂字书籍的“物质性”特征,忽略了书籍生产和使用的历史语境。书籍的文字是恒定的,但当呈现它的物质形式变化,文本的意义也可能随之变动[22]。杂字书的物质性,主要是书籍在物质意义上的呈现,特别是书籍外观形态——字体、纸张和尺寸等对书籍的生产、传播、阅读环节深具影响。它们不但可以揭示杂字的图书市场和读者群体,还是窥见杂字阅读史的直接材料。以文献尺寸为例,何谷理对晚期古代中国通俗小说的研究,就是通过检视书籍本身的物理外观的变化,认为这些物质形态变动预设了不同的读者群,由此可确定其“阅读大众”的范围[23]。李友仁也是通过大数据的办法,以WorldCat中保存的三万五千条1500—1799年所刊古籍记录为样本,通过分析文献的尺寸大小,得出古代中国晚期印刷出版的总体趋势[24]。因此,书籍的物质特征承载着不可言说的文化意义,甚至包含书籍带给受众的阅读体验。
最后,对杂字文献的定位,编者似乎过于广泛、宽松,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虽然关于杂字的“杂”存在不同释义,学者们对杂字文献界定不一,但至少像《集刊》所收的《幼学信札》和《对类引端》之类的文献,是以往研究中早就熟悉的文类——教人写信的尺牍、初学学对的楹联,这些文献显然不能当作杂字。还有部分文本前后残缺,编者轻易判定为杂字,如《集刊》第13册收《礼仪杂字》4种。实际上,这些文本名称是编者私拟的,并无线索依据,不过从内容判断它们是乡间常见的礼仪称呼、帖式之类的民间日用类书。其内容虽是礼仪知识的传授,但仍不足以称之为《礼仪杂字》。以上对《集刊》局限性的指摘,或许过于严苛,但绝无訾毁之意。订讹规过的初心绝非为了批评,何况这些评论充其量不过是个人有限知识结构的认识,丝毫不会影响《集刊》的独特价值与重要意义。
三、杂字文献整理的规范
上文对《集刊》的粗浅评介,只是一个受众(读者)对一套大部头的资料汇编的反应,希冀这样的读者观感反过来可以对后来的杂字整理提供镜鉴。目前,仅据王建军的收集粗略估计传世的杂字就至少上万册[25],更何况民间社会当有不见于整理的海量杂字留存,如太行山文书、徽州文书、山西文书、闽东文书等已有不少杂字发掘①如宋坤、邹蓓蓓《太行山文书中民间识字教材“杂字”研究》,载《河北学刊》2014年第6期。不过,其中的杂字是否归属太行山文书,还可再讨论。。因此,确定基本的整理规范,是杂字文献出版急需解决的核心问题。不过,为更好地整理出版杂字文献,似有必要对以往杂字整理工作稍做梳理。
自20世纪30年代起,杂字文献的搜集工作就已展开,但进展缓慢,直到20世纪50年代,张志公在《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中附录传统中国蒙学读物,系统列出杂字书目近30种[26]。这是首次对杂字文献进行规模化的整理,但遗憾的是只有部分书影。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史兴起,倡导“眼光向下”看历史,杂字文献的整理出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限于篇幅,本文仅举其要者。大致而言,这些出版路径分成两类:录文整理点校,按文本类型或地域分布的影印整理。
第一类出版路径是录文整理点校。代表有1989年喻岳衡主编出版两种在湖南流传的《捷径杂字·包举杂字》[27],1995年来新夏主编、高维国编校《中华幼学文库·杂字》,整理出版了山东、徽州、天津等地4种杂字,并附录经眼和未见杂字书目52种[28]。这种路径的整理出版,固然揭示了杂字文献的文字内容,但文献的原生态样貌几乎完全丧失,原有文献中的字体、版式、旁注、分页、土俗字等均无法保留。对于正统文献而言,文字内容占主导位置,点校出版问题不大,但对于杂字这种民间俗文献而言,大都以韵语形式编排行文,标点几乎没有意义,保留文本的物质形态反而更加重要。若要将这些文字载体的物质形态,放到现代版本的点校本中,还需诸多编辑方法的调整,难度不小。因此,这种整理出版的方法不宜提倡。
第二类出版路径是影印整理。这种方法可分为两种样态。一种是按杂字文本类型的影印出版,这种方法是将内容相同的杂字文本汇集一处,其代表是李国庆汇编的两套杂字类函。2009年李国庆编《杂字类函》收集杂字168种版本(实际上部分不是杂字),80种不同文本[29];近十年后,李国庆又与韩宝林合编《杂字类函(续)》,新增杂字98个版本,并附录新中国成立以后编印的23种杂字书目提要[30]。这两套杂字类函影印出版了目前最大规模的杂字,意义非凡。此种整理出版方法明显的优点是有利梳理文本的版本源流及其流传,但缺点也很突出,即不便于确定杂字所在的地域,难以找到文献的主人,以致不能情境化解读杂字,反会给研究者识读杂字带来困难。另一种按地域影印出版,这种出版形态应以《集刊》为代表,其虽不利于考辨文本的版本变迁,回到文本的历史脉络和流传情形,但不可否认这种整理办法有助于文献的“落地”,可将文献置于特定地域社会“研读”。
以上两种影印整理出版方法,前者似乎更有利于历时性研究,后者便于共时性研究展开,各有可取之处。两者孰优孰劣,笔者无意置喙,更紧要的关切应是剩余的巨量存世杂字如何进行有效整理出版。杂字无疑是民间历史文献的种类之一,而以往学界多年对民间文献整理累积的经验,恰好能为杂字文献整理提供重要参照[31]。结合杂字文献的特殊性,笔者认为以下三项原则是以后杂字整理应当遵循的。否则,杂字还是俗陋的底层文献,难以激发引人入胜的学术话题,更遑论开启民间历史文献的数字人文研究。一是最大限度地保留杂字文献的原生性。在整理出版过程中,不仅要呈现杂字文本的内容,还要关照文本的物质载体对文本解读的意义,起码须注明杂字文献的尺寸(纸幅、版框)、纸张、版式、页数、破损情况等,做到文献的“文本性”与“物质性”兼顾,最大限度地还原文本的原生样态。在黑白影印的最低保障下,部分页面原色影印,特别是写、抄本中的眉批、旁注或涂鸦信息,是窥探民众读写实践不可或缺的稀见材料。这些材料不但是书籍史、阅读史的重要线索,还推动着中国古代写本文化、语文学等新兴领域的研究。二是全力维护杂字文献的完整性。用说明性文字登记杂字的收藏地、来源、寻获经过等,尽可能恢复文献留存状态,保存杂字文献原有的社会脉络和关系网络。不论是田野调查、图书馆寻获还是文物市场收集,一定要尽力弄清楚杂字来源,这意味着杂字的整理出版,从收集之始就已开启,唯有如此方为回到特定时空解读文献提供了可能。尤其是整理一家一户为单位的杂字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切忌只单独抽取杂字影印出版,而是要保存、登载一户人家中的各类文献。否则,将杂字抽离文献流传脉络,会导致杂字离开所产生地方的文献网络而显得支离破碎,以致研究者对杂字的解读充满陌生或距离感,甚至导致研读的偏差或误读。三是充分寻绎杂字文献的关联性。地方文献碎片化的情状决定了单件文书不能孤立看待,需在“文献群”中才能被解读。杂字是民众识字的入门文献,有着文献自身的特殊性,其“进阶”学习的背后营造并关联了系列相关的民间文献(账簿、契约、书信等)。一本礼仪杂字、账簿杂字或文约杂字不会是孤立的,而是在认读学习后造就了一种或数种民间文献文类。因此,发掘杂字周边的关联性文献,甚至,连杂字中夹带的任何文字纸片都要予以整理,如此才能建立相对完整的文献系统,形成多元的关联史料群。只有在史料群中杂字才构成进阶流动的文化,从而得以在整体上深入、系统地被解读。这三项基本原则,既是杂字作为民间识字材料展开深度文本发掘的保障,也为开启民间历史文献的数字人文研究准备了核心的“元数据”。
四、结语
《集刊》的整理出版,不仅为明清杂字文献的发掘之路增添了厚实的一环,披露了诸多前人未曾留意的杂字种类,而且对推动明清以来日常生活中的识字、书籍、文字、礼仪等诸多话题的讨论亦有非凡意义。此外,因不少文献地处边疆社会,从而也为考察边疆民间社会如何应因王朝国家的文教普及提供了珍稀材料。还应指出,民间文献还是中国本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料宝库[32]。随着各式民间文献井喷式的发掘,学者认识到民间文献不仅充实了史料的类型与数量,丰富和提高了历史信息的内涵与完整度,而且还在于其书写、使用和传承本身就是“文字下乡”的历史过程,是构成中国历史乃至文明发展史至关重要的一部分[33]。杂字读物的生产就是“文字下乡”结果之一,是民众应对日常生活文字所需的产物。反过来看,它也是促成这一社会文化进程形成的基本文类,因此,种类丰富的杂字可从“发生学角度”解释民众如何习得各种文字读写能力。
概言之,杂字不但是以上日常生活史课题的绝佳素材,还应是民间历史文献生产的基础性材料,透过对各种杂字文献的“顺藤摸瓜”,有望阐释民间文献如何形成和发展。目前,还有海量的杂字深藏国内外各大图书馆或乡间田野尚未发掘整理,但从已出版的杂字来看,都或多或少存在不足。因此,为有效整理、深入解读杂字,须汲取民间文献收集整理累积的经验,充分尊重杂字文献的原生性、完整性和关联性。唯有遵循这些基本规范,才能跳出“边整理边破坏”的民间文献出版怪圈,迈向杂字整理的新境界。由此通过杂字这类民间基础文献推进民间历史文献学的构筑,深化传统中国日常生活史的总体研究,乃至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话语与概念体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