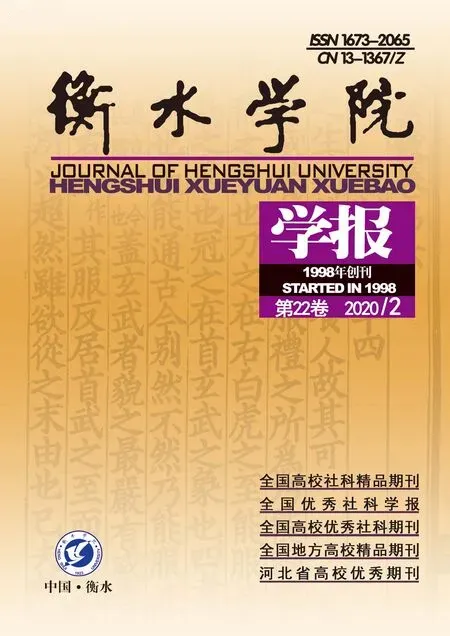《春秋繁露》“董仲舒真篇”新探
——以“贤良对策”检索《春秋繁露》的尝试
2020-03-11
(北九州市立大学 文学部,日本)
这里所谓《春秋繁露》“董仲舒真篇”,以历史事实为前提,建立在以下思维之上:《春秋繁露》不是董仲舒的原著,而是后人将一些失而复得的董仲舒的文章编成的书物,其中可能混入了一些和董仲舒无关的“伪篇”,但也不乏和董仲舒有关的“真篇”,笔者将这些可能存在的“真篇”称为“董仲舒真篇”。针对以往的《春秋繁露》文献研究大都集中于寻找“伪篇”的倾向,笔者企图开创一种根据一些可靠的文献,采用文献研究的方式,确定这些“真篇”的具体存在位置的新研究方法。如果说到目前为止一些寻找“伪篇”的研究所用的是消极性排除法的话,笔者寻找确定“真篇”的努力采取的是肯定性渐进思维,力图根据肯定性的理由来推导出答案。
为此,本文率先尝试以《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贤良对策”(以下简称“对策”)检索《春秋繁露》,认为《春秋繁露》中凡是和“对策”在文本上有互见关系,思想趋向上又基本一致而互不矛盾的文章,都是“董仲舒真篇”。这种方法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但希望本文提出的方法和所作的尝试能够引起学界对董仲舒文献研究的关注。
一、以思想理路论真伪——到目前为止《春秋繁露》研究的主要缺点
《春秋繁露》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汉代思想的重要文献。但关于《春秋繁露》的文献真伪问题,一直缠绕着董仲舒研究者们。
众所周知,《汉书·董仲舒传》云:“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但在《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董仲舒名下,收录了《董仲舒》123篇,没有提到《春秋繁露》这一书名。《汉书·艺文志》又在“春秋”类中,著录了《公羊董仲舒治狱》16篇。《春秋繁露》这一书名最早出现于5世纪或6世纪初的《西京杂记》(卷二,《四部丛刊》本)中,在阮孝绪(479-536年)的《七录》中,《春秋繁露》这一书名才与《汉书·艺文志》中为董仲舒所列的条目联系在一起,最后被载入《隋书·经籍志》。
由此可见,《春秋繁露》这一书名没有和著者同步出现,该书成书较晚,成书过程不明,和董仲舒的直接关系没有确证,所以关于其真伪,特别是和董仲舒的关系,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未能定夺。明代胡应麟综合各家观点,说:“余意,此八十二篇之文即《汉志》儒家一百二十三篇者。仲舒之学究极天人,且好明灾异,据诸篇见解,其为董居然,必东京而后,章次残缺,好事者因以《公羊治狱》十六篇合于此书,又妄取班所记《繁露》之名系之。而儒家之董子世遂无知者。后人既不察一百二十三篇之所以亡,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从出,徒纷纷聚讼篇目间,故咸失之。当析其论春秋者,复其名曰《董子》可也。”(《少室山房笔丛》丙部《九流绪论》中)认为是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换言之,《春秋繁露》以与董仲舒有关的“真篇”为主编辑而成,但也有可能混入了一些和董仲舒无关的“伪篇”。
到了近现代,随着现代学术方法的确立,特别是海外《春秋繁露》研究成果传入中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综观中外学界争论的焦点,全盘肯定论①全盘肯定论者大多是中文世界的思想史家,如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威熊(《董仲舒与西汉学术》,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版)、王永祥(《董仲舒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有之,全部否定论有之(中国的孙景坛、日本的福井重雅甚至提出班固《汉书》董仲舒本传捏造论[1]),五行诸篇否定论有之(如日本的庆松光雄②庆松光雄《春秋繁露五行诸篇伪作考》(《金泽大学法文学部论集(哲学文学)》第6号(1959),第25-46页)。中文由笔者翻译,载《衡水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台湾的戴君仁[2]),五行诸篇前四篇肯定、后五篇否定论有之(如日本的田中麻纱己③田中麻纱巳《关于〈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的考察》(1969年《集刊东洋学》22号)。中文由秦祺、邓红翻译,载《衡水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和近藤则之[3]),这种首尾两端的现象,堪称中国思想史文献研究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然而否定论者有一共同倾向,那就是“先认定《春秋繁露》肯定有伪作,然后再去寻找的先入为主法”[4]。殊不知“宣布《春秋繁露》有伪篇和宣布《春秋繁露》没有伪篇都属于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都必须要有严格的论证和可靠的材料”[5]274。再就是否定论者们采取的寻找伪篇的方法,不是采取文献研究学的方法,而是,“先发明一种理论,认为董仲舒的思想应该是这样,然后对繁露的文章群进行考察,如果其中的某些文章符合这一假定理论,他们就宣布这些文章是董仲舒的;如另一部分文章不符合这一假定理论,他们就宣布这些文章是赝作”[5]271。由于否定论者热衷于这样的“以思想理路论伪”的成见[6]去寻找《春秋繁露》的伪篇,从而犯有不同程度的以逻辑推断代替文本考证的研究方法上的谬误。
其实这种方法自古以来有之,如宋代的程大昌怀疑《春秋繁露》的理由之一便是“辞意浅薄”(《秘书省书繁露后》),黄震怀疑《春秋繁露》的理由也是“余多烦猥”(《黄氏日抄》卷五十六中),便是典型的“以思想理路论伪”。而如庆松光雄和戴君仁所说董仲舒在《汉书》本传、特别是在《汉书·五行志》中只讲阴阳而不讲五行,所以《春秋繁露》中的五行诸篇都是伪篇的观点,便是典型的“以逻辑推断代替文本考证”④庆松写道:“董仲舒在当时不仅是公羊学者的第一人,即精通阴阳说,对五行说也颇有造诣,堪称阴阳五行兼备的大家,开创了自己独自的学说。带着如此观念,再去翻阅《汉书》本传和《五行志》,人们都会有如下发现。那就是在本传或《五行志》中,他的阴阳说随处可见,然在那有名的答武帝对策,或在以五行为题的《五行志》里,却找不出片鳞半爪五行说来。以上是我对《春秋繁露》五行诸篇产生怀疑的主要理由。因为《汉书》是远比《春秋繁露》更值得信赖的资料,以之可以作为检验《春秋繁露》的证明。”,庆松的论文甚至没有对他的“怀疑”进行过论证。
话又说回来,到目前为止的《春秋繁露》肯定论者则是大多以“以思想理路论真”。前面引用王应麟所说“仲舒之学究极天人,且好明灾异,据诸篇见解,其为董居然”便是一个典型。《四库全书总目》所说“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则可说是标准的“以逻辑推断代替文本考证”。人们也可以反问两句:“根极理要之言”很多,就是董仲舒的了?不是“根极理要之言”便不是董仲舒的吗?
正因为如此,最近发表的江新《〈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真伪考》[7]和程苏东《〈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形成过程新证》的两篇文章引人注目。
两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将《春秋繁露》和《汉书・五行志》(江新)、《春秋繁露》和《管子》《淮南子》《汉书・五行志》《南齐书・五行志》《隋书・五行志》等(程苏东)进行文本互见比较,力图从文献学研究的方式,突破“以思想理路论真伪”的套路。
尽管两篇文章的大致主题还是在寻找董仲舒“伪篇”,但江新的文章在寻找完伪篇之后,还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寻找起《春秋繁露》的“董仲舒真篇”来。他说:“《五行对第三十八》是董仲舒针对河间献王‘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的问题所作的策对。文章开头为‘河间献王问于温臣(城)董君曰’。在我们已经证明了董仲舒是有五行思想的情况下,我认为此篇不可能出于伪造。《五行之义》的思想和《五行对》基本一致,都是用五行思想来论证儒家忠孝伦理。所以,如果《五行对》是董仲舒的作品,那么《五行之义》就肯定是董仲舒的作品。”[7]
以五行来论证儒家忠孝思想的文字,都可以认作是董仲舒,这还是走上了“以思想理路论真伪”的老路。尽管如此,江、程两篇论文对笔者的启示在于:既然文献学研究的方式可以寻找《春秋繁露》的伪篇,何尝不可以用同样方法寻找《春秋繁露》中的“董仲舒真篇”呢?再就是《春秋繁露》中像《五行对第三十八》那样的明确标明“董君曰”之类的其他文章,可不可以都算作是“董仲舒真篇”?
二、以“对策”检索《春秋繁露》的结果
要以文献互见关系来寻找《春秋繁露》“董仲舒真篇”的话,首先我们想到的是不必舍近求远,而是可以直接以“对策”来检索《春秋繁露》。
为此,我们先从“对策”中找出了一些和董仲舒思想密切相关的关键词,然后再以之来检索《春秋繁露》中类似的话语,得出了以下结果。和“对策”有互见关系的部分都打上下横线。
(一)“任德不任刑”
“对策”有: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
关键词为“任德”。用“任德”二字检索《春秋繁露》,得到以下五处。相同之处都用下横线加以注明,以下同。
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春秋繁露・竹林第三》以下只注篇名)
难者曰:“阴阳之会,一岁再遇,遇于南方者以中夏,遇于北方者以中冬,冬,丧物之气也,则其会于是何?”曰:“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从阴阳,相与一力而并功,其实非独阴阳也,然而阴阳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阳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阳因火而起,助夏之养也;少阴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阴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阴虽与水并气而合冬,其实不同,故水独有丧而阴不与焉。是以阴阳会于中冬者,非其丧也。春,爱志也;夏,乐志也;秋,严志也;冬,哀志也。故爱而有严,乐而有哀,四时之则也。喜怒之祸,哀乐之义,不独在人,亦在于天;而春夏之阳,秋冬之阴,不独在天,亦在于人。人无春气,何以博爱而容众?人无秋气,何以立严而成功?人无夏气,何以盛养而乐生?人无冬气,何以哀死而恤丧?天无喜气,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无怒气,亦何以清而冬杀就?天无乐气,亦何以疏阳而夏养长?天无哀气,亦何以激阴而冬闭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乐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气者,合类之谓也。匹夫虽贱,而可以见德刑之用矣。是故阴阳之行,终岁各六月,远近同度而所在异处。阴之行,春居东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上,此阴之常处也;阳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阳之常处也。阴终岁四移而阳常居实,非亲阳而疏阴、任德而远刑与?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阳者,岁之主也,天下之昆虫随阳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随阳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随阳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幼者居阳之所少,老者居阳之所老,贵者居阳之所盛,贱者居阳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当阳。不当阳者,臣子是也。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礼之尚右,非尚阴也,敬老阳而尊成功也。(《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阴与阳,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春俱南,秋俱北,夏交于前,冬交于后,并行而不同路,交会而各代理,此其文与!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阳之出,常县于前,而任岁事;阴之出,常县于后,而守空虚;阳之休也,功已成于上,而伏于下;阴之伏也,不得近义,而远其处也。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阳出而前,阴出而后,尊德而卑刑之心见矣。阳出而积于夏,任德以岁事也;阴出而积于冬,错刑于空处也;必以此察之。(《天道无二第五十一》)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阳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举而上者,抑而下也,有屏而左也,有引而右也,有亲而任也,有疏而远也,有欲日益也,有欲日损也,益其用而损其妨,有时损少而益多,有时损多而益少,少而不至绝,多而不至溢。阴阳二物,终岁各壹出,壹其出,远近同度而不同意,阳之出也,常县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县于后而守空处,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第五十三》)
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故数者至十而止,书者以十为终,皆取之此。……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阳阴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天志仁,其道也义,为人主者,予夺生杀,各当其义,若四时;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恶戾,任德远刑,若阴阳;此之谓能配天。(《天地阴阳第八十一》)
另外,《阳尊阴卑第四十三》还有“务德而不务刑”:
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远天之所远,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
分析起来,“对策”的关键部分在于最后一句“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因为天道一阴一阳,阳主生而阴主杀。天道的目的又是为了生养万物,所以为政者要“任德教而不任刑”。整个逻辑是先讲生养之天道,再讲治道。
再看上面这几篇《春秋繁露》的文章,“任德而不任刑”(《阳尊阴卑第四十三》与“务德而不务刑”)的文字基本一致,且除《竹林第三》外讲述的逻辑和顺序也是一致的。
首先,讲天道阴阳的规律是阴阳配合、阳成阴辅,如《阳尊阴卑第四十三》的“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天地阴阳第八十一》的“故明阳阴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天志仁,其道也义”,《基义第五十三》的“阳之出也,常县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县于后而守空处,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
其次,讲天道的目的是“生养”,和治道一致,所以为政者要“任德而不任刑”,这在“对策”是“顺天”的大问题,而在《天地阴阳第八十一》称之为“配天”,《基义第五十三》称之为“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辨在人第四十六》称之为“天之制”,不然则叫“逆天”(《阳尊阴卑第四十三》)。总之,“任德而不任刑”是从阴阳秩序总结出来的天道。
(二)“灾异”与“天谴”
“对策”有: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以“灾异”和“谴告”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以下结果。
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必仁且智第三十》)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故书日蚀,星陨,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陨霜不杀草,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有鹳鹆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虽甚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贵微重始是也,因恶夫推灾异之象于前,然后图安危祸乱于后者,非《春秋》之所甚贵也,然而《春秋》举之以为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岂非贵微重始、慎终推效者哉!(《二端第十五》)
《必仁且智第三十》的文字和“对策”完全一致,堪称“对策”的底本。而《二端第十五》的文字,则是对“天谴论”理论由来的阐述。首先说明灾异谴告的理论来自《春秋》经传,“《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其次将谴告上升到“天”的层面,讲“《春秋》举之以为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至此谴告已经变成了“天谴”“天威”。最后将避免“天谴”的渠道归结于君主行仁政,“明善心以反道”。这用“对策”的话说叫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三)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
“对策”有:
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
以“改正朔,易服色”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以下结果:
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已,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徒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楚庄王第一》)
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顺数而往,必迎来而受之者,授受之义也。(《二端第十五》)
《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改正之义,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称号正月,服色定,然后郊告天地及群神,远近祖祢,然后布天下,诸侯庙受,以告社稷宗庙山川,然后感应一其司。(《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
“对策”关于“改正朔,易服色”有两个层面的意思。
其一,“改正朔,易服色”为显示王者接受天命而王。“对策”叫“顺天命”,《楚庄王第一》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二端第十五》叫“王者受命“,《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叫“王者必受命而后王”。所以在这一点上,《楚庄王第一》《二端第十五》和《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三篇文章不但词句和“对策”一致,意思也是相同的。
其二,“对策”说:“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楚庄王第一》说:“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字句和思想完全一致。《二端第十五》和《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没有讲这一条,则是针对的事情不同。《二端第十五》主要从中引出灾异“天谴”论,而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二端第十五》的“天谴”论和“对策”是高度一致的。《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则是讲改制的历史渊源和程序。
(四)“元”“正”
“对策”有: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
以“元”“正”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以下结果:
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惟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恶施于人?大其贯承意之理矣。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玉英第四》)
《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王道第六》)
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惟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恶施于人,大其贯承意之理矣。(《重政第十三》)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二端第十五》)
《春秋》大元,故谨于正名,名非所始,如之何谓未善已善也。(《深察名号第三十五》)
“对策”对“元”“正”的重视,来自对春秋经传的解释。以“元”为时间的开始,延伸到万事万物的起源。以“元”的起源说发挥出“正”的重要性,“正”就从时间概念转换到了政治概念,从名词变成了动词。所谓“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
上举几篇《春秋繁露》的文章在解释“元”“正”时,也从阐明春秋经传的关于“元”“正”的微言大义开始,完成了两个转换。如《深察名号第三十五》说“《春秋》大元,故谨于正名”,便是从时间概念转换到了政治概念;《二端第十五》说“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便是从名词转换成了动词。
(五)春生夏长秋(霜)收(杀)
“对策”有: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
以“春生夏长秋(霜)收(杀)”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如下结果。
是故春气暖者,天之所以爱而生之,秋气清者,天之所以严以成之,夏气温者,天之所以乐而养之,冬气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春主生,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生溉其乐以养,死溉其哀以藏。(《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阴阳义第四十九》)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四时之副第五十五》)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春生夏长,百物以兴,秋杀冬收,百物以藏。(《人副天数第五十六》)
是故东方生而西方成,东方和生,北方之所起;西方和成,南方之所养长;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故天地之化,春气生,而百物皆出,夏气养,而百物皆长,秋气杀,而百物皆死,冬气收,而百物皆藏。(《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为政之理,不可不审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后发德,必先平然后发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对策”讲春生夏长秋(霜)收(杀),少了一个冬,也许是有漏简,或者是上奏时大概觉得对策文不应太长,加以了省略。《威德所生第七十九》的这一段文字,除了“冬”系列以外,和“对策”完全一致。《春秋繁露》的其他五篇文章在春夏秋三个方面的叙述也基本上和“对策”一致,只是没有省略“冬”而加以了详细的叙述。
在理论建构上,“对策”叙述四季的功能,是要阐明“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也就是说,四季的功能是“天意”的显现,天不但以四季成岁,也以四季的功能体现人道,也和古今治理人世间的方法制度是同样的道理,拿《阴阳义第四十九》的话说,叫“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繁露》的几篇文章也在如此天意四季显示古今治道方面着意阐述,如《人副天数第五十六》说:“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威德所生第七十九》说:“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为政之理,不可不审也。”
(六)天者群物之祖
“对策”有: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
以“天者群物之祖”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如下结果。
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广大无极,其德昭明,历年众多,永永无疆。……故受命而海内顺之,犹众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沧海也。(《观德第三十三》)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顺命第七十》)
“天者群物之祖”“天地者万物之本”“天者万物之祖”,三者在字面上只有微小的差别,而其后的文字,都是在阐述为什么天是群物之祖。“对策”和《观德第三十三》都是用天道自然来进行的表述,而《顺命第七十》则是用阴阳与天地参合来解释的。
“对策”中16次提到“教化”,下面这一段专门讲王者之教化:
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
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
以“教化”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如下结果:
是故肃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祢,举显孝悌,表异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谷,开辟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雍庠序,修孝悌敬让,明以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立元神第十九》)
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势之不足独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为人者天第四十一》)
首先,不但强调“教化“的作用,而且都讲“教化”的内容为仁、谊(义)、礼、孝。
其次,“对策”提出王者为了“教化”,需要“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也就是在地方上建立“大学”“庠序”那样专门从事教化的教育机关。这和《立元神第十九》所说“立辟雍庠序”是完全一致的。
(七)正其谊不谋其利
此句在《汉书・董仲舒传》的“对策”后:
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曰:“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繇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
而上述本传和《春秋繁露》的《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第三十二》的内容大同小异:
命令相曰:“大夫蠡、大夫种、大夫庸、大夫睾、大夫车成、越王与此五大夫谋伐吴,遂灭之,雪会稽之耻,卒为霸主,范蠡去之,种死之。寡人以此二大夫者为皆贤。孔子曰:‘殷有三仁。’今以越王之贤,与蠡种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为越有三仁,其于君何如?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伏地再拜,对曰:“仲舒智褊而学浅,不足以决之,虽然,王有问于臣,臣不敢不悉以对,礼也。臣仲舒闻:昔者,鲁君问于柳下惠曰:‘我欲攻齐,何如?’柳下惠对曰:‘不可。’退而有忧色,曰:‘吾闻之也:谋伐国者,不问于仁人也,此何为至于我?’但见问而尚羞之,而况乃与为诈以伐吴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观之,越本无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三王是也;《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诈,诈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童子言羞称五伯,为其诈以成功,苟为而已也,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五伯者比于他诸侯为贤者,比于仁贤,何贤之有?譬犹珷玞比于美玉也。臣仲舒伏地再拜以闻。”
或可认为本传是这一篇文章的缩写本,或者是间接引用文。
三、检索结果分析和结论

表1 以“对策”检索《春秋繁露》的结果

续表1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结论:
(1)和“对策”的文献与思想一致的文章,一共涉及24篇。而《二端第十五》出现了三次。由于这些文章和“对策”有高度的文字重合,内容也基本一致,所以都可将之看作是“董仲舒真篇”。
(2)《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第三十二》标明为董仲舒回答胶西王的策问,其内容又和《汉书・董仲舒传》大致相同,也可认为是“董仲舒真篇”。
(3)《五行对第三十八》和《郊事对第七十一》也同样标明了是董仲舒的策对文,是否也可以将之算进“董仲舒真篇”内?
(4)《止雨第七十五》讲董仲舒如何教民众止雨法,其中有“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午,江都相仲舒告内史中尉”的字眼。二十一年为“江都易王二十一”,即元光二年,如果以董仲舒对策在元光元年的话,刚好符合《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的事迹。而在江都求雨之事,见于《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传》:“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而《止雨第七十五》也有董仲舒所说止雨的原理为“止雨之礼,废阴起阳”。所以这一篇也可以看作“董仲舒真篇”。
综上所述,本文初步确定的“董仲舒真篇”为28篇。
最后存疑的是:《春秋繁露》中有许多“曰”那样的似乎是董仲舒的直接引语的文章,特别是《繁露》前面所谓“春秋学部分”。而我们知道,《春秋繁露》的“春秋学部分”,各家大都以为是《春秋繁露》的《楚庄王第一》到《俞序第十七》①如赖炎元《春秋繁露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韦政通的《董仲舒》(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版),而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认为还应加上《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爵国第二十四》《仁义法第二十九》《必仁且智第三十》《观德第三十三》《奉本第三十四》等篇。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的前面部分。而这17篇和本文确定“董仲舒真篇”有6篇重合。而属于“春秋学部分”但不在本文确定的“董仲舒真篇”之列的《玉杯第二》《精华第五》,和“董仲舒真篇”的《楚庄王第一》《竹林第三》《玉英第四》《王道第六》这四篇体例大致相同,都在“传曰”之后紧接着有“曰”的部分,直接对“传曰”部分进行了解释,所以可不可以都看作和董仲舒有关的呢?何况《玉杯》之篇名和《竹林》同样,都在《汉书・董仲舒传》里面出现过①《汉书·董仲舒传》云:“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