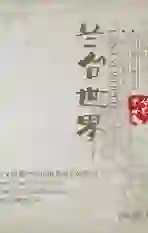抗日战争中的洛阳:城市地位与城市发展
2020-03-08王鑫宏
摘 要:洛阳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战争双方争夺的主要目标,呈现出以军事地位为主导的战略性城市特征。一方面,洛阳因服务于抗战需要,城市发展出现阶段性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战争对城市的破坏,洛阳不可遏制地最终衰败。
关键词:抗日战争 城市地位 城市发展 洛阳
中国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9-05-17
★作者简介:王鑫宏,河南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抗战史研究。
Abstract Luoya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rategic real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Luoyang provided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war strategy, and became the main goal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presen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strategic city dominated by military status. The Anti-Japanese War made the city development of Luoyang show the trend of phased growth and final decline. On the one hand, because Luoyang served the needs of the war, the city development experienced a stage-by-stage growth.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ity caused by the war, Luoyang went to the inevitable decline eventually.
Keyword the Anti-Japanese War; city status; urban development; Luoyang
抗日战争对我国城市地位和城市发展造成重要的影响。本文以洛阳为例,拟从战争对城市地位和城市发展的影响作以探讨,以展现战争与城市的多维互动关系。
一、城市地位:洛阳呈现出以军事地位为主导的战略性城市特征
洛阳的抗战地位随抗战历程演变呈现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提出迁都洛阳的设想,并于“一二八”事变之后将迁都付诸实施,因而洛阳曾短暂地被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洛阳为国民政府“行都”。1932年11月,国民政府秘密进行对日备战,洛阳是国民政府国防建设的重镇。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驻洛,河南省党政机关也一度迁至洛阳办公,洛阳逐渐演变为河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是中原的“神经总枢纽”。这段时期,洛阳成为陇海铁路东段的起点,是连接华北和西北的必经要道。中共在洛阳设置八路军办事处,是国共合作的重要舞台。1944年5月,洛阳沦陷后,成为日军在华北的重要军事据点,更是对河南掠夺的重要基地,洛阳人民深受其害。中共建立的豫西抗日根据地,把争夺洛阳作为重要城市工作之一。中国抗战胜利后,洛阳曾一度被蒋介石定为第一战区受降所在地。从以上关于洛阳抗战地位演变的概述中可以看出,洛阳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突出的城市地位,体现出其以军事地位为主导的战略性城市特征。
城市自身的专有属性及其在战争中的特殊地位,对战争中的攻防双方而言,在整个战略、战役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充分满足了战争对其实施集中打击和致命打击的客观需要[1]71。對于中国的抗战来说,洛阳在对日战略中具有战略性意义。其表现主要有四:其一,战时首都的选择。要实现抗战的胜利,必须为这场扩日持久的战争寻找到一个能支持持久抗战的战时首都。正因为此,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提出迁都洛阳。中日停战后,国府很快迁回南京,证明洛阳事实上并不是最为适合的战时首都。最终蒋介石确定重庆为战时首都。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是洛阳城市发展史中一个重大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国家对其资源配置的多寡,决定了其集聚能力的大小。显然,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开始为洛阳城市发展注入强大的外生动力。因此,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不仅将洛阳与抗战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成为洛阳抗战史的开端,也是洛阳实现阶段性增长的起点,在洛阳城市发展史上具有突出标志性意义。其二,国防城市的巩固。在对日备战中,巩固要塞,即巩固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的城市和交通要道是国防建设的中心。其中,类似洛阳这样具有突出军事战略意义及交通要道的城市远比邻近海岸线较近的大都市更为重要。因此,对日备战中,国民政府在洛阳展开一系列建设,将洛阳打造成国防核心城市。其三,关于作战线的选择。就作战线的转换而言,蒋介石早有定见,但没有具体的文字表述[2]25。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在1935年10月15日的日记中提到:“蒋先生看定日本是用不战而屈中国之手段,所以抱定战而不屈的对策。前时所以避战,是因为与敌成为南北对抗之形势,实不足与敌持久。自川黔剿共后,与敌为东西对抗,自能长期难之,只要上下团结,决可求得独立生存,虽战败,到极点亦不屈服。”[3]318显然,蒋介石在1935年就形成了与日作战采取从东至西的作战线。基于此,蒋介石决定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因而,蒋介石极为关注洛阳的备战建设。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则对洛阳的安危极为关注。这些足以说明洛阳是中国对日战略中具有突出军事意义的城市。其四,中心城市的争夺。城市是战争首选的主要军事打击目标,同时也是重要的战争防御据点。战略攻击目标的选择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要“看一个地域的战略地位是否重要,主要是看其军事上的价值和资源是否富足”[4]50。在抗日战争中,洛阳的军事价值显然是极为重要的,甚至远远超过上海、南京等大都市。蒋百里指出,战争之中,虽然中国可能会失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一个纽约可抵半个美国,一个大阪可抵半个日本,中国因为是农业国家,国力中心不在都会,敌人封锁了与内地隔绝的上海,只是个死港,点缀着几所新式房子的南京,只是几所房子而已,它们与中国的抵抗力量,完全没有影响”[5]185。蒋百里还指出,日本的武力中心放在第一线,我们却放在第二线,而且在腹地内深深地藏着,使他一时有力没用处。这恰恰说明了类似于洛阳这样的城市对于中国的抗战事业影响巨大。因此,在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蒋介石亲自遥控指挥了洛阳保卫战,并对指挥中的失误后悔不已,对洛阳的沦陷痛心疾首。而一向主要经营敌后革命根据地的中共也对城市重视起来,正如毛泽东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过去人民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这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6]158国民党河南战场溃败后,中共采取“敌进我进”战略。1944年9月,中共中央派皮定均、徐子荣率“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到豫西,在三点(指郑州、洛阳、许昌)两线(指陇海和平汉铁路线)之间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豫西抗日根据地,这也体现了中共对战略性城市的争夺。
二、城市发展:洛阳呈现阶段性增长与最终衰落的趋势
城市是现代战争控制的重要目标,战争既可以给城市以毁灭性打击,也可以给城市发展带来机遇和活力。有学者指出:“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与社会的发展相一致的,每当社会发生动乱时,城市也遭到破坏。”中国城市总是在“发展——衰落——破坏——恢复——发展——衰落——破坏,如此周而复始地循环”[7]11-12。造成城市这种周而复始地循环的因素虽多,但毫无疑问,战争是最不能被忽视的因素。顾城林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一书中,对近代中国具有一定代表性的61个城市进行了考察,其中认为洛阳在中国近代属于增长型城市[8]154-157。但这是从宏观把握洛阳在中国近代发展轨迹基础上所得的结论。事实上,洛阳在中国近代应该是阶段型增长与衰落共生的城市。而在抗日战争中,洛阳城市发展即体现了阶段性增长,也体现了阶段性衰落,体现了战争对于城市发展的双重作用。
第一,战争的特殊阶段推动城市的发展。洛阳在隋唐时期曾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城市文明之最,然而,频繁的战争使这座城市一次次重建,又一次次毁于战祸,直到近代末期,其城市人口和城市规模也不足其历史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一[7]417。抗日战争为洛阳的城市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可以说,抗战即是洛阳城市发展的元素,也是洛阳城市发展的背景。洛阳在抗日战争以前只是中原一个区域性的军事城堡,以地方行政职能为主,工商业并不发达。抗战将洛阳城市发展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改变了洛阳城市发展的传统轨迹,促进了洛阳城市的快速发展。抗日战争中,洛阳的城市发展主要是在外力主导下实现的。洛阳城市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城市建设的推进。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在洛阳设置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创办电厂,修建洛阳桥等,推动了洛阳城市发展。其二是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总量是考察城市规模的重要依据。目前虽未找到抗战前后洛阳城市人口总量的确切数字,但是从抗战时期,驻军的增加、党政机关的入驻、难民的迁入等方面推断,洛阳城市人口显然是有大幅增加。以至于洛阳给外人留下一种“人口非常密集”[9]214的印象。其三是城市空间的拓展。抗日战争对洛阳城市空间的拓展主要体现在西工。由于洛阳军分校、洛阳航空学校的入驻及对西工的开发,西工从过去单纯的军营逐渐发展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并在抗战中成为大部入驻党政军机关的驻地。“作为半现代化省会的附属机构仍在活动。近郊铁路、机关区、天主教会、基督教会、飞机场、发电厂。如此等等,都在运转和活动。”[9]212其四是城市的多元功能。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之后,洛阳在外力嵌入与内力推进相结合之下,实现了城市的发展,在传统军事、政治、文化功能进一步强化的同时,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也发生了演变,推动着洛阳发展成为多功能综合性的区域中心城市,增强了城市的集聚力和辐射力。抗日战争中,洛阳逐渐发展成为区域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因为此,洛阳虽处于国防前沿,但绝大多数时间“城内依然是都市的景色,精致的包车,镶着黄铜皮的花边,比成都或重庆都好看得多,万景楼、川湘菜社、百货商行、照相馆、剧院往来的肥头大耳的巨商,都是都市的良好点缀物”[10]15。以上这些说明,抗日战争中洛阳城市发展,实现了阶段性增长。
第二,战争不可遏制地导致城市的衰落。由于城市是战争的首要攻击目标,因此凡是成为战场的城市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一旦城市被攻占,那么这个城市就会面临灭顶之灾[7]410。就抗日战争中的洛阳而言,在抗战中洛阳因战争被破坏程度达到60%[11]。战争对于城市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日军对洛阳的轰炸。据统计,日军利用空军对洛阳进行了百余次轰炸,动用战机469架,投弹635枚,炸毁房屋1600余间,伤亡520人[12]2。其二,驻军的破坏。1939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征派民工拆毁洛阳城墙,据说是为了战略需要,新筑城墙,临时修建,基松墙薄[13]185。而作为国民政府迁都遗产之一的中原社会教育馆,战争开始后,馆房大部为第一战区警备司令部、河南粮政局、中央通讯社等机关占用,馆的业务更形冷落,陷于停顿状态[14]61。其三,工业及人口的内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等内迁。而“早在三年前,日本人危急这城市时,洛阳那薄弱的工業企业就撤走了。大多数生产性企业迄今仍难在这样一个充分暴露于敌前的地区兴建”[9]211。显然,工业、人口的内迁使得洛阳的城市发展缺少了重要依托。其四,日军占领时期对洛阳的破坏。日军进攻洛阳,造成无法统计的财产损失,仅洛阳县党部房屋损失项目就包括:地基包台40方、砖墙674、大门楼1、东西楼房6、东西对房6、二门1、大礼堂9、后院房16、会议室9、办公室4、石板110、柱石136、铺地砖5万,合计损失32536300元[15]。日本对洛阳经济控制掠夺的结果,不仅使他们获得了经济利益,而且严重摧残了洛阳经济的发展。其五,战后外力动力的不足。抗战胜利后,伴随国民党方面党政军机关的迁出,洛阳城市地位下降,外生动力荡然无存,衰败乃是必然。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中的洛阳具有突出的地位,是对全国抗战具有重要影响的战略型城市。抗日战争中的洛阳因服务战争需要,一度实现了城市增长,但战争的破坏性不可避免,洛阳也最终因战争而衰败。以上这些,体现出了战争与城市的相互作用与影响。
参考文献
[1]蔡云辉.战争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吕芳上.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 (二) 军事作战[M].台北:“国史馆”,2015.
[3]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三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4]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斯大林军事文集[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5]皮明勇,候昂妤.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蒋百里、杨杰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