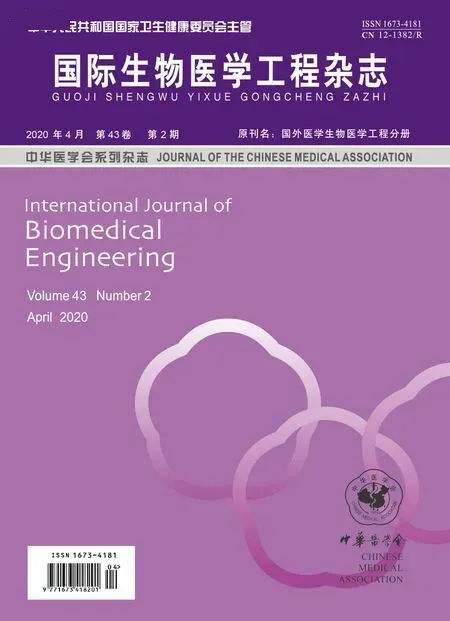肠道菌群与肿瘤免疫治疗关系的研究进展
2020-03-07张宝忠赵晶晶章文成庞青松
张宝忠 赵晶晶 章文成 庞青松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疗科,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市“肿瘤防治”重点实验室,天津市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300060
0 引 言
肿瘤的治疗技术在近些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手术治疗、化学治疗(化疗)、放射治疗(放疗),靶向治疗发展至免疫治疗;在专注于研究治疗手段的同时,研究者们也在关注如何充分发挥各种治疗手段的疗效、减少治疗副作用,致力于研究影响各种治疗技术的侧面因素以及能够预测治疗效果的生物学指标。近期备受关注的免疫治疗在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均取得了较好的结果;同时,研究者们发现肠道菌群的结构组成和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免疫治疗的疗效,甚至通过检测肠道菌群的结构即能预测免疫治疗是否有效。人们对肠道菌群与宿主之间复杂关系的关注可追溯到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20世纪初期,Ilya Ilyich Mechnikov最先使用活微生物维持肠道健康并且延长寿命。随着技术的发展,研究者们逐渐发现了肠道菌群与炎性肠病、哮喘、过敏性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I型糖尿病及多发性硬化等多种疾病存在关系[1]。本文将近年肠道菌群与机体及肿瘤免疫间的关系进行综述。
1 肠道菌群与机体的免疫机制
人和动物的胃肠道内栖息着大约30属500多种细菌,主要由需氧菌、兼性厌氧菌和厌氧菌[2]组成;菌群含有人体10倍数量的细胞,100倍数量的基因,并具有代谢功能[3]。哺乳动物肠道内的共生菌不仅能够为宿主提供重要营养物,帮助降解宿主本身不能降解的化合物,还可帮助宿主抵抗机会致病菌及塑造小肠结构[4]。哺乳动物的基因结构并未编码健康所需的全部信息,而微生物基因组的产物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此方面的不足,在帮助宿主抵抗多种疾病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因此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共生菌群与宿主相互依赖共存,哺乳动物免疫系统的某些基本功能需要与肠道微生物群落的相互作用来维持[6]。
肠道菌群的存在对于宿主免疫功能的构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作用在人或动物出生即存在。肠道菌群帮助塑造肠相关淋巴组织(gut 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GALT)并维持其功能。GALT是人体重要的免疫器官,动物模型证实,肠道菌群的存在与GALT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无菌动物体内的GALT严重不足[7],共生菌一方面可帮助机体抵抗感染和某些疾病;另一方面其包括的一部分条件致病菌有可能诱发炎症反应,因此共生菌既能诱发抗炎反应,又能诱发前炎症反应,维持菌群结构稳定与正常免疫功能的关系很大。肠道菌群的存在,能够长期刺激肠黏膜下Peyer’s淋巴结和肠系膜淋巴结,促进淋巴滤泡的发展和成熟[8]。有研究结果表明,肠道菌群能够维持淋巴细胞(辅助T细胞Th、调节T细胞Treg)表达肿瘤坏死因子(TNF)、干扰素-γ(IFN-γ)等前炎症因子的水平[9]。因此,肠道内共生菌群的存在不断刺激、激活并维持了肠道黏膜的固有免疫功能,使宿主机体能够抵抗外来病原体的入侵[10]。另外,肠道菌群结构的变化与某些炎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11],如克隆氏病、哮喘、过敏性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I型糖尿病及多发性硬化等通常被认为是由T淋巴细胞驱动的;在动物模型和人体研究中均表明菌群变化导致的调节T细胞Treg功能的下调或缺失会导致炎性肠病、哮喘、过敏性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I型糖尿病、多发性硬化发病率的上升。近些年,动物实验结果显示,某些菌(如Clostridium)能够增强获得性免疫中的抗炎作用,导致外周循环中Foxp3+Treg细胞扩增[12],Treg细胞能够表达 IL-10、CTLA-4、IL-2、TGF-β、IL-35 等因子,诱导免疫耐受和免疫抑制;而IL-10对维持表面环境(如肺和小肠)的免疫稳定起着重要作用[13]。
T细胞在肿瘤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14],而菌群在T细胞的成熟、分化、募集等方面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啮齿动物模型中,分段丝状细菌刺激GALT而产生前炎症成分[15-16],导致树突细胞分泌IL-17、IL-23、IL-6以及辅助T细胞-17(Th-17)的募集,但此反应从未在成年人的菌群中检测到;相反,有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反应在人类幼年时存在并可能具有潜在的作用[17]。
2 肿瘤的免疫治疗现状
现代肿瘤免疫治疗方法是通过增强人体自身免疫系统的免疫能力,提高对肿瘤细胞的识别和杀伤,同时抑制促肿瘤免疫机制来发挥作用。目前人们最关注的以及临床证明最有效的免疫治疗靶点是CTLA-4和PD-1/PD-L1。PD-1抑制剂单药的应用只在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有效率突破了60%,而在绝大多数实体瘤的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中,单独使用PD-1抑制剂的有效率只有10%~30%,因此目前所有针对PD-1/PD-L1的抑制剂均是通过与其他治疗手段联合应用的,如化学治疗、放射治疗及靶向治疗等。PD-1抑制剂联合化疗目前已被推荐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非鳞癌,一线靶向治疗靶点阴性的)的一线治疗。PD-1抑制剂联合CTLA-4单抗已被批准用于晚期转移性恶性黑色素瘤的治疗;而PD-1/PD-L1抑制剂联合放疗、靶向治疗以及其他免疫靶点(IDO、TIM-3、LAG-3)阻断剂的动物模型实验和临床试验也正在开展,其中涉及肾癌、宫颈癌、肺癌、胃癌、肠癌及乳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18-20]。
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只有约20%的患者能从PD-1/PD-L1药物中获益,因此临床上需要有效的预测因子来指示对于哪些患者能够从PD-1/PD-L1抑制剂的治疗中获益,而目前FDA批准能够用于预测PD-1/PD-L1抑制剂疗效的标记物有PD-L1表达水平和高微卫星不稳定性(MSI)。PD-L1表达主要位于肿瘤细胞表面,目前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表达≥1%的患者对PD-1/PD-L1抑制剂的敏感性表达较好,而达到高表达(>50%)的效果会更好。但是,临床研究中也有结果与此结论不符[21-22],高微卫星不稳定性(MSI-H)广泛存在于多种恶性肿瘤细胞,而MSI-H的肿瘤患者均可能从PD-1药物中获益;另外,还有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al burden,TMB)、肿瘤浸润T细胞含量、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率(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NLR)也可能预测PD1/PD-L1的疗效。有研究结果显示,肿瘤细胞TMB的水平与患者PD-1抑制剂治疗的有效率相关,但TMB的预测水平在不同肿瘤中存在较大差异。PD-1/PD-L1治疗的根本在于激活T细胞,使其更好地对抗肿瘤,因此,肿瘤中T细胞的含量是药物发挥作用的基础。NLR是全身炎症的标志物,且与各种肿瘤的治疗疗效相关,包括化疗和分子靶向治疗,目前也有研究结果显示,NLR与PD-1抑制剂的疗效相关。
3 肠道菌群与肿瘤免疫治疗的关系
机体免疫功能的主要武器是T淋巴细胞,如前文所述,菌群在机体环境中对调节性T细胞、辅助性T细胞的刺激以及其功能维持具有重要的作用。十年前有研究者报道了菌群,更准确地说是一些次优势菌群如何在小鼠器官内促进T细胞的募集[23];近期有研究者否定了以往认为器官和肿瘤内是无菌环境的观点[24],证实一些种类的细菌能够伴随肿瘤的生长,并随着肿瘤的转移而迁移[25],如有研究发现Fusobacteriumnucleatum存在于结肠癌中,同时存在于原发肿瘤和肝脏转移灶中,其存在与预后差存在相关性[26]。在小鼠体内移植患者Fusobacterium nucleatum阳性的结直肠肿瘤,抗生素能够延缓肿瘤的生长[25]。研究结果显示,Fusobacterium nucleatum可与天然免疫系统受体(TLR4)相互作用,调节自噬、减少凋亡及引起化疗耐受[27]。最新的数据显示,肿瘤组织中存在的细菌即使在远离胃肠道的恶性肿瘤中也能通过免疫抑制来调节免疫反应,如胰腺导管腺癌内的内生细菌数量远高于正常的胰腺组织,其通过抑制单细胞分化使T细胞失去功能[28]。有研究报道了特定菌种在体外对化疗效果的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同时也报道了在体内,瘤内细菌的存在对某些化疗药物效果有负面影响(如吉西他滨)[29]。另外,一个利用小鼠的结肠癌模型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瘤内细菌的代谢功能可能是导致吉西他滨化疗耐药的原因[30]。另有研究结果发现,菌群能够调节某些特定化疗药(如奥沙利铂、环磷酰胺)的疗效,是因其能够促进抗肿瘤的免疫反应[31-32]。
基因完全相同的小鼠移植不同来源的菌群后,对免疫治疗产生不同的反应;相反,同笼养殖的小鼠不会产生类似的差异。直接摄入双歧杆菌属(Bifidobacteriumspp.)能够刺激肿瘤内抗原提呈细胞,进而增加肿瘤特异性免疫以及对抗PD-L1免疫治疗的反应[33]。另有研究结果发现,抗生素治疗后的小鼠和无菌小鼠均缺乏对CTLA-4阻断的反应,并建议对与此相关的菌群种类进行鉴定(如Bacteroidesfragilis)[34]。
关于肠道菌群与肿瘤的免疫治疗,近两年内有3个研究组报道了人类相关数据。在不同类别的上皮肿瘤(非小细胞肺癌、肾细胞癌、尿路上皮癌)和恶性黑色素瘤中,某些肠道菌群对免疫治疗的疗效具有预测作用。免疫应答者和无应答者的菌群表型可通过菌群移植而发生改变,无菌小鼠或抗生素预处理的小鼠移植了应答者或无应答者的粪便菌群后会获得相应的表型。通过饲喂特定的菌种(Akkermansiamuciniphila)可让无应答表型的小鼠重新获得应答表型[35-37];但对免疫治疗有应答患者所关联的菌群,在这3项研究中均不同[38]。
一些吞噬黏蛋白的细菌能够影响对免疫检测靶点抑制剂的反应(如A.muciniphila,B.longum),理论上其能够让一部分上皮细胞暴露给它们和一些其它细菌,由此诱发前炎症反应[39]。Zitvogel等假设了不同的肠道菌群引起的免疫刺激可能是由多种机制作用的,包括微生物和肿瘤抗原间的交叉反应、对模式识别受体的刺激,在这些过程中微生物代谢产物有可能发挥系统调节效应[40]。
4 肠道菌群的稳定与变化
血液肿瘤和实体瘤的初步实验数据发现,肠道微生物结构的变化或抗生素干预能够影响小鼠模型的过继细胞治疗的疗效[41-42]。小鼠实验和人体试验结果证实,饮食影响我们的微生物组学,肠道生态环境是在长期的饮食习惯中形成的,而调节菌群的可能性手段包括饮食细化、避免不合理应用抗生素、粪便菌群移植、益生元/益生菌摄入等[43],如Bacteroides属和Prevotella属的阳性率分别与动物蛋白/脂肪为主的饮食和植物碳水化合物为主的饮食有关系[44],饮食变化造成肠道菌群生态的改变通常可在短时间内发生[45]。
纤维素的摄入影响体内短链脂肪酸的产生和特殊菌种的占比(Faecalibacteriumprausnitzii,Roseburiaspp),短链脂肪酸能够通过G蛋白藕连受体43(GPR43)直接影响系统免疫调节[46]。与此类似,ω-3脂肪酸与GPR120发生作用,调节炎症和胰岛素敏感性[47-48];多不饱和脂肪酸亦能短暂引起产短链脂肪酸菌属增加,并有效促进生态平衡的恢复[49-50]。有研究结果表明,生活习惯,尤其是饮食中纤维素的摄入量能够影响抗PD-1治疗的反应率[51]。粪便菌群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可治疗Clostridiumdifficile感染和炎性肠病IBD。而现有的临床研究数据证明,FMT应用到高强度化疗或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过程中,可恢复肠道微生态治疗患者难治性的急性抗排异反应,或用在免疫治疗中,能够提高无应答患者对免疫治疗的应答率[52]。
5 结语
在当前免疫治疗的研究过程中发现,肠道菌群不仅在宿主免疫机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与多种炎性疾病相关可作为一个重要的生物标记物对多种疾病进行预测,甚至对某些疾病治疗的疗效进行预测。在肿瘤发病率日渐上升的现阶段,对肿瘤的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等各种治疗技术发展突飞猛进,许多临床研究和动物模型实验均发现肠道菌群与抗肿瘤治疗疗效、并发症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综上所述,肠道菌群可成为医疗干预的靶点,有效地改变肠道菌群表型甚至能够改变个体对治疗的敏感性,是肠道菌群发挥重要作用的另一个领域。而菌群的作用不仅限于此,人体共生菌群数量及其包含的生物信息量非常庞大,与人体免疫机制的关系错综复杂,现有的成果只是其冰山一角,其潜在功能亟待进一步研究和发掘。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