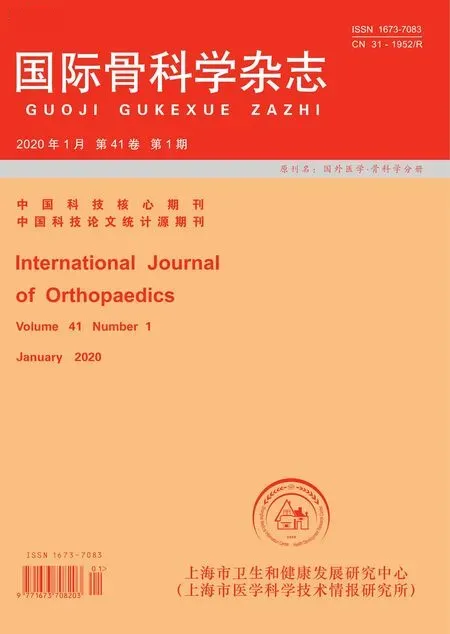关节造影对发育性髋关节脱位闭合复位治疗的影响
2020-03-07卢晓坤林然陈顺有
卢晓坤 林然 陈顺有
发育性髋关节脱位(DDH)是一种儿童早期髋关节畸形和发育缓慢的状态,涉及髋关节发育不良的一系列畸形,包括完全脱位、半脱位和不稳定,以及股骨头和髋臼发育不良[1]。对于DDH患者,早期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最新指南推荐,对18个月以下DDH患儿使用闭合复位加石膏固定治疗[2]。尽管对于闭合复位前应否行髋关节造影仍无定论,但已有研究明确显示,术前髋关节造影有助于术者判断真实的髋关节形态,分析复位阻挡因素,评估复位质量等。目前,关于18个月以下DDH患儿闭合复位前行髋关节造影对其预后的影响仍不明确,相关研究也较少。我们对厦门大学附属福州第二医院骨科诊治的DDH患儿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髋关节造影对指导18个月以下DDH患儿复位治疗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标准:①年龄<18个月的DDH患儿;②Pavlik吊带治疗失败或未经过治疗;③随访时间≥2年;④术前、术后及术中造影资料完整。排除标准:神经肌肉性、创伤性及畸形性髋脱位。
查找2015年1月至2018年4月厦门大学附属福州第二医院诊治的DDH患者病例资料,依据以上标准共纳入57例患者(61髋)为研究对象。髋关节脱位程度采用Tonnis分度[3]。造影组30例(33髋),年龄为4~18个月,随访时间为24~30个月,平均(26.2±4.2)个月。对照组27例(28髋),年龄为3~18个月,随访时间为24~37个月,平均(33.6±7.9)个月。两组间在性别、脱位侧别、年龄、Tonnis分度上均无差异,见表1。

表1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1.2 手术方法
患儿术前均行常规检查,包括双髋关节正位及蛙式位X线片。
行全身麻醉。麻醉起效后,患儿如有内收肌紧张则行内收肌松解,必要时同时切断髂腰肌肌腱。以Ortolani手法闭合复位髋关节并记录安全区角度。术者于C臂X线透视下确认并维持头臼同心圆复位,根据复位安全区行人类位石膏固定术。行髋关节造影者采用内侧穿刺入路,于内收长肌下方进针,朝同侧肩锁关节方向刺入髋关节腔,每髋注入约0.5~1 mL碘海醇。根据造影图像评估闭合复位疗效并进行相应调整。采用Bowen造影标准评估闭合复位是否成功。若出现头臼间隙较大或软组织卡压等不能复位或不可接受的复位情况,则行切开复位。Bowen造影复位成功的标准为:①股骨近端干骺端低于H线水平;②软骨股骨头水平半径的2/3位于Perkin线以内;③股骨头在复位后处于盂唇外缘下[4]。未行造影者则根据闭合复位成功的标准判定,包括:①复位成功时有弹入感;②感觉股骨头稳定且股骨头的骨化核(存在时)与Y型软骨相对且在Perkin线内侧; 如果股骨头的骨化核不存在,则采用基于Von Rosen线和完整Shenton线的评估。
1.3 随访情况
所有研究对象随访时间均≥2年,比较造影组与对照组末次随访时的髋臼指数(AI)、中心边缘角(CE)、髋关节再脱位率、切开复位率及股骨头坏死发生率。股骨头坏死的分级采用Kalamchi 和 MacEwen法[5]。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定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符合正态分布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不符合者采用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定性资料无序者采用卡方检验,有序者采用秩和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末次随访时,造影组AI为26.09 °±4.62 °与对照组(26.62 °±4.41 °)无差异(Z=-0.536,P=0.592);CE角为12.14 °±5.03 °小于对照组(17.84 °±7.44 °)(t=3.549,P=0.001)。造影组14髋出现坏死(Ⅰ型5髋,Ⅱ型9髋),坏死率为42.4%(14/33);对照组12髋坏死(Ⅰ型6髋,Ⅱ型6髋),坏死率为 42.8%(12/28),两组间无差异(χ2=0.001,P=0.973)。造影组7髋再脱位,再脱位率为 21.2%(7/33),对照组3髋再脱位,再脱位率为10.7%(3/28),两组间无差异(χ2=0.572,P=0.449)。造影组 6髋切开复位,对照组则无,两组间存在差异(P=0.027)。
3 讨论
对小于18个月的DDH患儿,治疗目的主要为获得中心性复位并维持这种稳定的复位方式,以促进髋关节的正常生长发育,防止股骨头坏死。在该年龄段,闭合复位为首选治疗方式。
单纯闭合复位时主要根据手术中术者感觉及X线透视下股骨头骨化核的位置来判断复位情况。但对于股骨头尚未出现的患儿,以及在判断较大关节间隙中是未骨化股骨头还是卡压的软组织时,术中X线透视无法提供有效信息。同时,X线透视对投射体位的要求常导致对间隙距离判断的误差,而术者感觉取决于其经验,无法进行量化标准的评判。因此,有必要引入新方法帮助术者评估复位情况。
闭合复位时采用髋关节造影的优势在于:①能够了解股骨头的真正形态及其与髋臼的关系;②可显示盂唇、关节囊、圆韧带等软组织的形态,分析阻挡复位的因素;③可评估复位后的头臼间隙及复位情况;④可结合复位的安全角度,判断是否需切开复位,有助于降低切开复位率;⑤根据复位情况,术中即可动态调节髋关节体位,有助于选择最佳固定位置。与单纯闭合复位相比,髋关节造影辅助复位有其独特优势,使之成为判断闭合复位效果时的常用方法。X线透视时,若内侧造影池(MDP)<2 mm,即为满意的中心复位。有研究表明,MDP在2~7 mm且无明显间置物时,一些病例可通过“靠港”效应达到复位[6]。MDP>7 mm或MDP>16%股骨头直径则提示头臼间有软组织卡压,为不可接受的复位[7-8]。
一些学者已对DDH患儿闭合复位时采用髋关节造影的作用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在髋关节造影下,测量中心盂唇边缘角可以预测髋臼发育情况,其比CE角或AI更准确[9]。Zhang等[10]对髋关节造影引导下闭合复位治疗的126例DDH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他们发现,在造影下股骨头覆盖率≤30%为不可接受的复位标准,且其可做为预测髋臼残余发育不良的指标。一项对162例DDH患儿采用闭合复位治疗的前瞻性研究发现,于髋关节造影后测量,患髋的髋臼软骨角>24 °的患者均需行髋臼成形术;在闭合复位2年后,AI角<30 °为髋臼发育良好的标志[11]。 另一项前瞻性研究显示,经5年以上随访发现,DDH患儿闭合复位时采用髋关节造影者其股骨头坏死发生率明显低于不采用髋关节造影者(7.6% 对28.9%)[12]。我们的研究中,造影组与对照组股骨头坏死发生率均较高(42.4%和42.8%)且无差异。但是,股骨头坏死的分类为Ⅰ型和Ⅱ型,其预后较好,而前述研究中则有Ⅲ型和Ⅳ型股骨头坏死,其预后较差。此外,我们研究中选择的造影评估方式与前述研究不同,且随访时间较短,这些原因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差异。
再脱位是治疗中另一较严重的并发症。我们的研究显示,造影组与对照组再脱位率分别为21.2%和10.7%,两组间无差异。Biçimogˇlu等[13]的研究显示,髋关节造影术后再脱位率为19%,与我们的研究结果大致相同。我们的研究中,对照组患儿行手法复位时均成功,并达到闭合复位成功的标准;造影组中MDP较大者,不符合复位标准,共6髋予切开复位,关节囊紧缩缝合,两组间有较显著差异。“靠港”理论认为,如果髋部保持在适当位置(头臼实现对位),股骨头可对阻止同心复位的软组织产生持续压力,将其推挤开,使髋关节能够缓慢复位,即所谓的“靠港”效应[6, 14]。此次研究中我们发现,造影组CE角小于对照组,这可能由两组随访时间不同导致,造影组随访时间较短,其“靠港”效应可能小于对照组。
我们的研究发现,术中造影确定复位成功者仍存在股骨头坏死及再脱位发生,且发生率不低,其原因可能为髋关节造影无法完全评判复位情况。术中MDP的测量常因C臂X线机投射位置及患者肢体体位的影响出现误差,存在一定局限性。已有不少学者发现,MRI检查对评估DDH患儿闭合复位后的并发症发生有重要作用,并可降低术后股骨头坏死及再脱位等的发生率。Gornitzky等[15]的研究发现,闭合复位后立即使用增强MRI检查,可通过评估股骨头血管分布情况降低股骨头坏死发生率。Westhoff等[16]对15例DDH患儿(21髋)行术中关节造影和髋人类位石膏固定,固定后立即作MRI检查,发现3髋为不满意复位。他们建议使用MRI检查来评判复位情况。
DDH闭合复位术中行髋关节造影,虽操作简便,费用较低,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无法完全评判复位情况。术后行MRI检查将是我们未来研究的重点。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样本量较小。因回顾性研究中许多病例丢失,不符合纳入标准,导致纳入研究的病例数较少。第二,造影组随访时间较短,造成研究结果的一定偏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