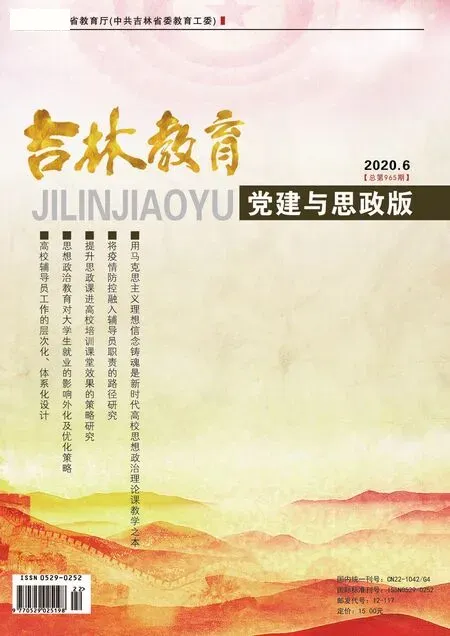马克思经济哲学视域下新自由主义自由观批判
2020-03-04梁方婵
梁方婵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广东 茂名 525200)
自由是众多新自由主义者共同的追求,是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其经济政策的立足点、出发点。马克思充分肯定人的社会性,作为人的属性的自由也应该是社会的而不是孤立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仍然摆脱不了“物的依赖”,是不可能得到事实上的自由的;而且,社会是发展的社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自由的内容也应该随之变化,所以自由的具体内容不应是也不会是永恒的,而是变化发展着的。
一、新自由主义自由观否定人的社会性
在对旧自由主义经济逻辑和哲学思维继承的基础上,新自由主义者进一步把个人和市场推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在新自由主义看来,集体和政府的决策是武断的、片面的、非科学的,来自集体和政府的干预是自由的桎梏。为了确保个人的自由度、保持自由的状态,社会所提倡的自由必须是消极的“免于……的自由”。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观有这样一种倾向:集体是不自由的同义词,只有从个人出发,以个人的意志作为唯一的价值评判标准,才能实现自由,免于走向极权政治的道路。处于这种自由的人,是建立在自私自利、独来独往的基础上的,其中的每个人都是零散的、孤独的、冷漠的。但是,自由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个人和社会的双重视域,既没有脱离个人自由的社会自由,也没有脱离社会自由的个人自由。
个人对于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进步的作用,马克思与新自由主义者是持有相同态度的。他强调,人类社会是由人所创造的,如果没有生命个体,人类社会也就不复存在。而且,如果没有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人类社会应会失去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社会也会停滞不前。但是不一样的是,马克思更为辩证地看待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肯定个人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之余,亦意识到社会对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人的社会性是与生俱来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是在所难免的。个体的形成是以社会化的生产活动、实践活动为前提条件的,而生产与实践活动又源于人与人之间交换的需要。因此,人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孤立的个体,人的背后隐藏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才是区分人与人的根本尺度。
因而,从马克思的视角来看,人都不可能是超社会性的,而是置身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任何个体都不能离开共同体而独立存在,个人存在与社会关系不可能是非此即彼的。因而新自由主义脱离各种社会关系的自由观是虚幻的、不现实的,自由在本质上既是个人的自由,也是社会的自由。
二、新自由主义自由观具有阶级局限性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拥有资本和财富的资本家才拥有自由,对于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而言,自由是遥不可及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雇佣制度的形成,工人们在工作与否、工作地点的选择等方面有了一定的选择权,看似比奴隶要更为自由了,但是一旦回到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支配上,工人依然是被奴役的对象,只是在制度的遮掩下,一切变得合理化和合法化而已。
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始终坚持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包括劳动力买卖在内的全部交换都是公平的、民主的,进行商品交易的双方是清醒的、独立的、平等的,劳动力的买卖本身也不具有强迫性,是自由自愿的。对此,马克思并没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这种自由平等与交换价值之间存在着正相的关系,一方面,自由平等关系以交换价值为前提条件,没有交换价值就没有自由平等关系的存在;另一方面自由平等关系是实现交换价值的内在保障,没有自由平等关系,交换价值就难以实现。
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剥开自由平等关系的外衣,对资本主义市场交换做出了更为深刻的考察和分析。马克思认为工人的劳动力在进入市场买卖的前置阶段就存在着不公平,这样的不公平将直接决定了后续买卖的非正义性。这样的不公平,源于工人从一出生就是一无所有,并没有像资本家那样占有生产资料。因而,与资本家依靠原始积累和劳动剥削获得财富不一样,工人们只能出卖自己仅有的劳动力以求生存。在这样的既定的自然事实前提下,劳动力的买卖实际上是不可能自由进行的,在过程中充满了资本的强迫与工人妥协的博弈,否则工人们就会饿死在街头上。在劳动力买卖的过程中,工人们无法选择他们出卖劳动力的必然性,可以选择的是出卖给哪家企业而已,但无论是哪家,都意味着被剥削的开始。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剥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在交换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自由平等,不过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掩盖工人窘迫现状的“遮丑布”而已。
然而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劳动力是工人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而进行买卖的,是建立在自愿的、平等的基础上的交易,并不是在他人强迫下进行的。而对于交换之前的不公平是工人阶级先天形成的,是一种无法跨越的自然限制,就像人不可能长生不老是一样的道理,并不属于他们管辖的“人为”的不公平和强制的范畴,因而不必理会。但新自由主义者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主张的“消极自由”是对资本的妥协,恰恰是以出卖自由为前提。即使是依据这样一种“免于人为强制”的自由概念,工人所遭受的强制和不自由仍然是确定无疑的。
三、新自由主义自由观具有历史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历史现实的客观基础出发,从对表象的总结升华到对人的本质把握,再由这个抽象的本质,在现实的生产生活中展开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进而总结了人的三大发展形态也即人的三种自由状态: 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社会处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能力低下,个人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个人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在这个阶段,社会是人支配人的社会,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无法自由地发展,都无法获得自由。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第二种形态,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资本家支配着社会和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一阶段,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不断增加,但是生产却是在异化的状态下进行的,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为物的关系,人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也以自身对立物的异化形式存在。这个阶段社会与人受到物的约束,一切活动都是以物为中心和目的展开的,因而无法实现自由。在这个阶段,一方面资本推动生产发展,为社会向前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无产阶级持续性地进行无偿的剥削,使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认识到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冲破资本对人的支配和束缚,把资本家无偿占用的剩余劳动时间转变为人们自由支配、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他们辛苦创造的却被资本家剥削的物质财富完全转变为人们能自由支配的财富,才能扬弃劳动的异化、解放生产者,实现每个人乃至全人类的自由发展。从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看,马克思认为人的真正自由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实现。这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一个以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为目标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在这个阶段,交换依然存在,但是在社会分工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交换,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基础上的交换,是以全体成员的自由发展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进行的交换。社会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社会,人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而且个人的自由与整个社会自由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个人的自由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自由和进步。
而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自由依然是立足于资本社会且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发展阶段,个人自由仍然受到来自外部的资本的“异化”力量的统治,这个阶段的自由只是一种抽象的、形式上的自由,其导致的是事实上的不自由。但新自由主义者却始终认为资本主义阶段的自由是永恒的,它不像马克思具有历史性的自由观,把自由放在各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来考察,最终是要说明人类的历史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积累,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终点,而人的自由发展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的,社会历史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的自由也相应达到什么程度。因而我们应该跟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步伐,循序渐进,追求与具体的生产力水平相对应的自由,而不是不切实际地盲目追求当下还不具备现实社会条件的自由,如此只会像新自由主义那般,极力鼓吹自由却不得自由。我们应该向马克思学习,坚持自由与社会历史形态相结合,反对超前的、虚假的、不现实的自由,鼓励大力发展生产,改善生产关系,只要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社会进步了,人的自由才能迈向更高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