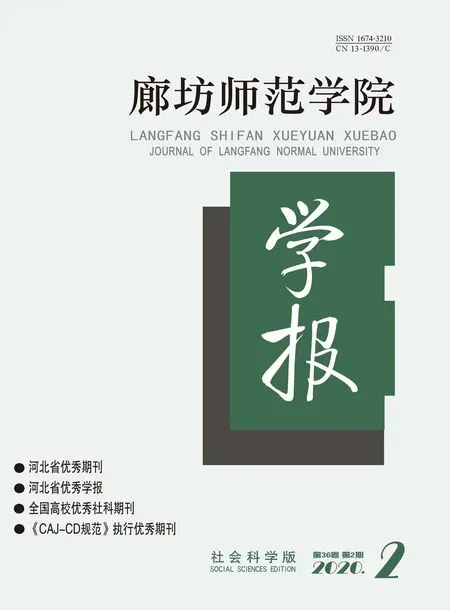耶稣会士对明清时期司法体系的异域审视
2020-03-04郑朝红
郑朝红
(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耶稣会士在17—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将西方科学引介过来的同时,也将中国文化译介到西方。明清时期的司法体系是他们关注的一项重要内容,利玛窦(Matteo Ricci)、曾德昭(Alvaro Semedo)、安文斯(Gabriel de Magalhaes)、李明(Louis Le Comte)以及《耶稣会士中国书信集》的供稿者都着墨于此。他们的著作经教廷审查出版后,旋即成为西方了解中国最新状况的权威文献,社会各界都从中寻找自己所需。其中的司法信息引起了伏尔泰、孟德斯鸠、魁奈等启蒙思想家的注意。他们认为,司法与政体密切关联,是政体的外在体现形式。源于此,他们在耶稣会士传递的中国司法信息的基础上,分别塑造了自己心目中的中国政体形象。厘清上述史实有助于理解近代欧洲中国政体形象构建的学理路径,既是有价值的学术话题,又可为当前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借鉴。
一、耶稣会士关注中国司法体系的缘由
耶稣会士的著作大都涉及明清时期的司法体系,对中国的司法感兴趣并非单纯的巧合,而是以下原因使然。
首先,与中国司法制度的独特性有关。耶稣会士对中国的观察,是基于哺育他们成长的欧洲社会,任何与欧洲相异的社会现象都易于吸引他们的眼球。明清王朝的司法制度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自成体系、迥异于西方,自然会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
与明清时期的中国不同,16—17 世纪的欧洲缺乏自上而下的集权机构和完备的官僚体系,司法还带有浓厚的中世纪遗风。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是旅华耶稣会士的主要来源国,这些国家的司法大同小异,都缺少中央集权的司法体系。西班牙和法国曾竭力推广通行全国的法律,但收效甚微。尽管法国号称是绝对主义王权的典型,却也没能建立统一的司法制度,法官基本由有专业知识的地方贵族担任,不由国王任命,国王难以建立起监察法官行为的有效制度。此外,随着专制主义的加强,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秘密审判成为一种趋势。欧洲大陆部分地区,为彰显司法官员的特权,强化审判的恐怖感和神秘性,审判朝着秘密的方向发展。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表现尤为明显,无论是教会还是世俗社会,都采用秘密方式进行审讯。耶稣会士熟悉的异端裁判所就是用秘密侦察、拷打、逼供等手段进行审判的典型。
其二,耶稣会士因身陷“教案”,有堂审、牢狱经历,对明清时期司法制度有切身感受。亲身经历对凸显所传信息的真实性异常重要,故而他们对此不惜笔墨。当时,尽管耶稣会士采取了“入乡随俗”的传教方针,并取得了部分士大夫、乡绅甚至宫廷的支持,但社会上对他们一直存在敌对情绪,该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教案。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大规模教案有三次:明末的南京教案、康熙亲政前的杨光先教案和雍正禁教后的教案,而地方起诉耶稣会士的案件则不计其数。受到指控的耶稣会士一般要经历堂审、押监等司法程序,有的还遭受过刑罚。《大中国志》的著者曾德昭、《中国新史》的著者安文斯、《耶稣会士书信集》的撰信者艾若望都有此种体验。相对于明清臣民,耶稣会士受到的惩处一般从轻,主要是笞刑、杖刑,在监狱也只受锁刑,被铁索缠身。但刑罚对他们的肉体仍造成了极大伤害,安文斯就死于脚踝部拷刑的后遗症。与欧洲民众分享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还可以彰显他们笃信上帝、坚贞不屈的形象,进而唤起欧洲对他们传教事业的支持。
第三,与其他教派的竞争有关。在耶稣会士之前,基督教的多明我(Dominican Or⁃der)、奥斯定(Augustinian Order)、方济各(Or⁃do Fratrum Minorum)等其他修道院的会士都曾在中国东南沿海短期传教。他们固守欧洲的传教规矩,又缺乏与地方官员的有效交流,不久就被当地政府驱逐出境。他们在华时间短暂,不可能较全面地了解中国,但基于其所闻所见而成的书籍还是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当时传播比较广泛的有盖略特·伯来拉(Gale⁃ote Pereira)的《中国报道》、加斯帕·达·克鲁士(Gasper da Cruz)的《中国志》和马丁·德·拉达(Mardin de Rada)的《记大明中国事》。奥斯定会士门多萨受教宗之命,在这些著述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大中华帝国志》(1585 年),在短时间内就被译成多国语言,成为当时欧洲了解中国的必备书籍。该书亦在教会内广泛流传,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都通过此书了解中国。耶稣会士作为后来者,必须在前人基础上添加新信息,才可能获得在欧洲宣介中国的话语权。他们不仅需要回应先前著作涉及的明朝司法机构、法官监察、刑罚、监狱等内容,还要记录所见所闻尤其是加上亲身经历,以显示自己在介绍中国方面超越了前人。
二、耶稣会士对明清司法体系记述的两大特征
耶稣会士对明清司法体系的记述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一,从制度层面揭示明清中央集权的特质;其二,通过案例展示司法的实际运行。
(一)对制度层面的关注
从中央集权角度看,明清时期,为维护皇权而设计的等级森严、垂直管理、同级监督的司法体系,远胜于同时期的欧洲。这引起了耶稣会士的注意,并将其作为中华文明的集中体现,向西方推介。概括起来,他们的介绍基本聚焦于司法机构和法官监控两方面。
首先,司法机构方面。耶稣会士之前的教士活动多在沿海,结交之人基本为社会底层小商贩等,缺乏打入京城政府机构的渠道,故其书只介绍了省级司法机构。这一缺憾由耶稣会士填补。入乡随俗的传教策略、汉语交际能力的提高,扩大了耶稣会士的活动范围和交际圈。居住京城的耶稣会士通过结交上层官员,阅读中文书籍,获取到明清王朝中央机构的某些政治信息,并借助教会内部网络,与其他在华耶稣会士共享,使那些未在京城居住的耶稣会士也能了解到明清王朝的中央司法制度和机构。值得注意的是,耶稣会士是将明清时期的司法机构纳入到政府机构中一并介绍,很少单独成章,并不像西方那样与行政分开。例如,他们谈及中央政府机构时,提到了刑部、大理寺和监察院,谈及省级机构时提到了(提刑)按察使司,在记述州县衙署时突出了其司法职能。他们可能受到明清“志书”的影响,当时含有政府机构信息的《大明一统志》《续文献通考》等都采用这种体例。除了常设司法机构,耶稣会士还注意到了非常态化的三堂会审、六部会审等集体堂审临时机构,以及清朝独有的宗人府(该机构是清王朝特设负责宗室诉讼案件的部门)。
其次,法官监控方面。耶稣会士通过记述,向西方详细介绍了明清时期皇帝如何通过回避制度和监察制度直接控制各级官员。例如回避制度。明清时期官员的回避制度事项繁杂,包括亲属、师生、地缘等回避,可能受限于信息来源,耶稣会士仅观察到了籍贯回避,利玛窦、曾德照、安文斯、李明等人都在著述中提及,但评价不甚相同。利玛窦的评价比较正面,认为“这是为了防止偏袒亲友而采取的预防措施”①[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页。,曾德昭则认为这项制度是为了“促进和校正统治而采取的特殊手段”②Alvarez Semedo,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London,1655),p.145.。再如监察制度。明清时期对官员的监察主要有两大系统。其一是吏部的例行考核,京官五年为限,地方官三年为期。以考核结果作为官员升、降、调、改、迁、谪、免等处理的依据。其二是由监察院稽查各级官员,其中司法案件判决公正与否是监察的重要内容。监察结果关乎官员的命运,威慑作用显著。此外,还有钦差大臣代替皇帝不定期巡视各地的专项监察。由于中国的法律事务官员并未像西方那样专业化、职业化,因而对所有官员的监控制度也同样适用于他们,耶稣会士们在记述中也就没有做出特别区分。
近代早期,欧洲诸国普遍追求建立中央集权模式,在当时全球文明中,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可谓独树一帜,因此西方便谋求从中国政体中寻求理想的范例,于是耶稣会士对自上而下的中国监察体系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希望欧洲能从中得到启示。如利玛窦介绍了明朝吏部的考核事项,以及科、道之官的权威与职责③[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60—61、52—53页。;曾德昭介绍了明末中央科道和省级察院的权力④Alvarez Semedo,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pp.126—127.;安文斯介绍了清初都察院官员的品级、权责、权威和监察事项等⑤[葡]安文斯:《中国新史》,何高济、李申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109页。。上述司法机构的建置、对法务官员的监控之所以成为这些耶稣会士在制度层面上关注的重点,也恰缘于此。
(二)以案例介绍来展示明清时期的司法运作
欧洲非常重视判例,判例是司法实践的结果,并能作为以后判案的依据,所以他们从西方的视阈出发,不仅关注明清王朝的司法制度,而且非常重视明清时期的司法实践。与制度层面的概括叙述相比,耶稣会士更多通过案例向欧洲具体展示明清司法中的审判、刑具、行刑、酷刑和监狱等方面内容。
利玛窦讲述了其在肇庆诉讼一案的所见情景,提及被告、原告、证人、法官、师爷、听审民众等“人”,还提到了申诉、宣判程序。①[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75—179页。曾德昭记述了在南京教案中的亲身经历,描述了衙役数量、站列情形、所持刑具、施杖刑的情景,以及申诉人跪呈诉状的细节。②Alvarez Semedo,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pp.139—201.限于个人经历,利、曾二人所述都是省城所在地的司法审判过程。有过在刑部过堂经历的安文斯,则介绍了京城六部的申诉程序③[葡]安文斯:《中国新史》,第97—98页。。巴多明在宣扬皈依的宗室苏努家族表现坚贞不屈时,不经意间也记录了宗人府的审问程序和刑部的议罪程序④[法]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3卷),朱静译,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这些耶稣会士描述的审案场景,使欧洲读者对申诉、公开审讯、当庭取证、宣判、执行、民众听堂等明清时期法庭审案的特色一目了然,清晰地展示了司法审判的公开透明。
独具特色的中国刑具与刑罚也是耶稣会士译介的关注点。他们对明清《刑令》中的笞、杖、徒、流、死等五刑都有涉及,以笞刑、杖刑的介绍最为详细。这是因为惩戒轻微犯罪的笞、杖两刑较为常见,也是耶稣会士目睹、甚至有切身感受的刑罚。他们对笞、杖刑具的材质、行刑的计数方法、行刑过程以及行刑者如何作奸犯科都做了细致描述。当犯人收监后,则要依照罪行轻重配带桎梏刑具,经历过教案的耶稣会士饱受其苦,对此也着墨记述。
除常规刑罚,耶稣会士还向欧洲介绍了凌迟、枷刑等明清时期的酷刑。利玛窦讲述了万历年间妖书案主犯皦生光被处凌迟的惨酷场景:“罪犯被剐1600 刀,且要亲眼目睹自己被肢解的过程。”⑤[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40页。虽然没有一个耶稣会士受过枷刑,但曾目睹教友遭受此难的其他会士,将枷的形状、重量以及对囚犯的伤害一一列出,其中以龚当信(Contancin, Cyr)的描述最为细致。他的记述被杜赫德整理编入《中华帝国全志》后,成了欧洲人对这一刑罚认识的标准。对于这些刑罚,耶稣会士基本持否定态度,谓之为酷刑。即使五刑中的轻微惩罚杖刑,在他们眼中,已是非常残酷了,更遑论凌迟等极刑。法国的耶稣会士李明就认为,“身体羸弱的人只要被打上一板子,就有可能昏死过去,而且很多人在受杖刑之后,丢掉了性命”⑥[法]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郭强、云龙、李伟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耶稣会士似乎对监狱不感兴趣,对此专述的人很少。曾德昭只是在叙述牢狱经历时顺便提及一些内容。客观而言,曾德昭对明清监狱的记述比前人内容更丰富,包括内部构造、规章制度、狱吏的舞弊行为等。有过礼部和刑部牢狱之灾的安文斯也记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让欧洲读者对明清京城的最高监狱有所了解。
较之先前的著述,耶稣会士对明清司法制度以及实践的审视,在真实性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诸多不足。首先,对明清时期的司法机构仅有初步认识,对其运行机制尚认识不清,所以很少就此阐发议论,充其量只是将之与欧洲简单类比。其次,存在着毁誉并存的矛盾。他们大都崇尚和称赞中国的司法制度,同时谴责执法官员,指责他们贪污受贿、欺上瞒下、徇私舞弊、官官相护。一般而言,良好的制度应该能令官员执法公正,官员腐化的广泛存在恰恰表明制度存有结构性缺陷,因而耶稣会士对明清司法自相矛盾的评价有些匪夷所思。再次,耶稣会士对同一事情的叙述有时互有出入。尽管耶稣会士用严格的审查制度强调著述的传承性和一致性,但审查重点在于和教义相关的内容,其他方面不甚严格。例如,利玛窦和李明对凌迟某些细节的描述就彼此矛盾。
三、耶稣会士的记述与西方对中国政体形象的塑造
通过这些耶稣会士的记述,西方人增强了对明清时期司法体系认识的真实感。这样既容易理解又让人印象深刻,对欧洲读者产生了很强的冲击力。虽然之前有关中国司法的书籍在欧洲也产生过影响,但没有刺激新思想的萌生。耶稣会士的对华描述给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提供了一个域外文明的范例,成为他们或抨击或称颂本国政治制度的素材。伏尔泰、孟德斯鸠、魁奈都从利玛窦、曾德昭、李明的著作以及《耶稣会士书信集》《中华大帝国志》中寻找灵感和论据。这些著作中有关中国司法的部分对他们的影响最大,当时欧洲思想界普遍认为司法是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耶稣会士译介到欧洲的中国司法制度和案件,便成为思想家认知中国政体的重要原料。由于解读角度不同,不同的思想家借由耶稣会士提供的诸多信息在欧洲塑造的“中国政体形象”也不同。
启蒙运动巨擘伏尔泰曾在耶稣会士创办的圣路易公学求学七年。在校期间他耳濡目染地知晓了许多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的事情,后来他也与旅华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 Francoise Foucquet,1665—1741)等人多次交流。与耶稣会士的密切接触,让他很关注耶稣会士撰写的书籍。在其著作《路易十四时代》中,他就提到了利玛窦、曾德昭、李明等人,而《耶稣会士书信集》《中华大帝国志》是他撰写《风俗论》的重要参考书目。他依据《耶稣会士书信集》有关雍正皇帝审核死刑犯的事例①[法]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吴模信、沈怀洁、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01页。,判断中国政治具有“理性”传统,中国君主是开明统治。随着伏尔泰著作风靡欧洲,他塑造的中国政体形象也被部分欧洲知识界接受。
与伏尔泰不同,孟德斯鸠同样利用耶稣会士提供的资料,却把中国塑造成一个“使用棍棒统治”的专制主义国家形象。影响孟德斯鸠形成其中国观的司法信息主要来自两个渠道:其一,与旅法华人黄嘉略、耶稣会士傅圣泽等人的谈话交流。在与黄嘉略的谈话中,中国的酷刑是主要话题②许明龙:《黄佳略与法国早期汉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7页。;其二,耶稣会士的著作,尤其是《耶稣会书信集》以及在此基础上编辑而成的《中华大帝国志》,孟氏所著《论法的精神》涉及中国的事例皆出自这两本书。孟德斯鸠认为“严峻的刑罚比较适宜于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政体”③[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98页。,耶稣会士笔下的酷刑案例成为他判定中国专制的证据。尤其是巴多明对满清皇室苏努家族因皈依基督教而遭受迫害的细节描述④[法]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3卷)。,为孟德斯鸠建构“棒喝下”的中国统治提供了详细材料。
魁奈也利用耶稣会士提供的资料来阐述他的政治观。与孟氏有所不同,他认为中国是“合法的专制主义”。魁奈对耶稣会士提供的信息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认为是“粗略观察的结果”,并带有“因宗教偏见掩盖真相”⑤[法]弗兰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谈敏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6页。的倾向。但他也明确知道,若要了解中国,除了传教士的报告以外,没有可以依据的东西⑥[法]弗兰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第26页。。他撰写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大量参考了耶稣会士的著述。该书第五章的审判机构、刑罚、官吏三节内容均来自《耶稣会士书信集》和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甚至直接摘抄其中的某些段落。魁奈记述的凌迟、枷刑等刑罚基本与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和龚当信信函的相关内容雷同。他也注意到巴多明对苏努家族教难的描述,但得出的结论却与孟氏不一致,认为中国惩罚犯人与其他国家没有不同,不能凭借刑罚就断定中国的统治者暴虐。并且,在他眼中,“中国的刑法相当宽大的”①[法]弗兰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第87页。,杖刑不令人感到耻辱,因为皇帝也用杖刑惩罚显贵之人,且刑后仍对他们一视同仁,枷刑也不那么使人痛苦。②[法]弗兰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第88页。总之,他认为中国的专制主义应加上“合法”二字,还倡导“已启蒙的欧洲统治者向中国学习”③David Martin John,The Image of China in Wester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New York:Palgrave,2001),p.27.。
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反对本国的专制,渴望得到“他者”的经验作为参照,恰在此时,耶稣会士将毁誉并存的中国司法信息传递到了欧洲。孟德斯鸠、伏尔泰、魁奈皆想通过“他者”来评判欧洲,所不同的是,孟德斯鸠将“他者”当作本土的负面形象加以批判,伏尔泰、魁奈则将“他者”看作理想的化身。他们出于不同的需要,为西方人塑造了不同的中国政体形象,这些形象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随着欧洲的发展而发生着改变。大致来看,工业革命前,西方仰慕中华帝国的政体和强大,故伏尔泰等人的“颂华”观点大行其道。此后,随着欧洲实力的增长、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传播以及殖民扩张,西方逐渐形成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孟德斯鸠有关中国政体的负面认识开始备受追捧。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更加速了其观点的流行,对中国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