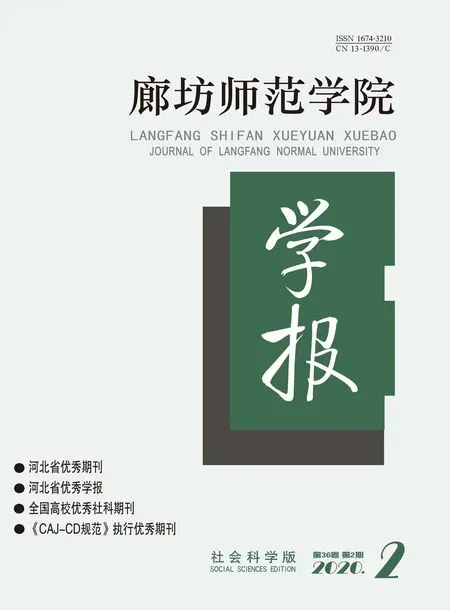1980 年代“城乡分立”视域中的乡村叙事探析
2020-03-04贾鲁华
贾鲁华
(枣庄学院 文学院,山东 枣庄277160)
在1980 年代的乡村叙事中,“好日子”的想象与构建是一个有着多种面向和层次的复杂结构体:它不仅仅容含着农民“吃”的自然性需求,也容含着如梁三老汉、许茂①梁三老汉和许茂是小说《创业史》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人物形象,二者皆为珍视土地的老农民形象。等老农民对土地的想象与追求;它不仅容含着农民生活的物质性需求,亦包蕴着不断变换的时代性农村伦理构建。农村空间与农民的想象结构不仅是农村内部元素的变动亦或稳定,更是整体社会大空间结构的一个元素。由此,农民对“好日子”的想象不仅限定在农村内部结构之中,还会受到作为“他者”存在的城市空间的影响。但是,在以西方现代化为楷模的话语构成中,城乡的关系并非是平行式的两个不同空间,而是一种上/下或文明发展过程中前/后式的层级性结构关系。或可直接说,乡村被设置为一个在历史文化发展中要被抛弃的过程,只是在1980 年代“被”并置在一个社会结构中,从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自然/文化空间。但事实上又不得不承认:城市空间作为一种与农村空间有差异性的元素进驻到农村“好日子”想象结构之中,使农民产生了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想象。
一、“城乡意识形态”的生成
1980 年代初期,高晓声在“创作谈”中依据自己的经历与生活经验对城乡差异性进行了一个较为形象的比较:
我恢复工作后,经常出差,住招待所。……我往往住进了较好的房间,住一晚要付五六元、七八元不等。我想苏南农民劳动一天,通常只有七八角收入,住一夜倒花掉农民近十天的工资,悬殊实在太大。……这种情形,农民不但不知道,告诉他们,他们都不信。反笑我说海话。……因此我想,若能让他们去住一夜,就会相信了。①高晓声:《谈谈有关陈奂生的几篇小说》,《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3期。
高晓声把这种经历与体验放置在了小说《陈奂生上城》之中。农民陈奂生得益于“承包制”及其相应分配方式的实施,在满足了“吃”的需求后,开始追逐“穿”的改善——买一顶帽子,而买帽子的钱是通过“卖油绳”这种商品交换行为获得的。这一连贯性的买卖行为已然离开了陈奂生生长、生活的乡村空间,是在城市空间中进行的。
陈奂生为多卖点钱而陷入病痛之境,巧遇吴书记将其送至招待所。只有农村生活经验的陈奂生醒来后看到了一副令其“眩晕”的现代化的“物”世界:
原来这房里的一切,都新堂堂、亮澄澄,平顶(天花板)白的耀眼,四周的墙,用清漆漆了一人高,再往上就刷刷白,地板暗红闪光,照出人影子来;紫檀色五斗橱,嫩黄色写字台,更有两张出奇的矮凳,比太师椅还大,里外包着皮,也叫不出它的名字来。再看床上,垫的是花床单,盖的是新被子,雪白的被底,崭新的绸面,呱呱叫三层新。②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
这一颇为震撼性的体验已然超出了陈奂生的所有生存经验。在比较中,城市的“好”在农村的“不好”映衬下显得那么令人向往,从而使得城市想象开始介入农民对“好日子”的构想结构之中。但陈奂生显然有着清晰的意识:此地虽好却非久恋之所。这不仅仅是因为陈奂生生长、生活与想象的空间仍然牢固地被放置于农村空间,更重要的是一天五元钱的住宿费绝非陈奂生所能负担得起。此种方式构建的农民的贫穷体验迥异于农村空间内部生产的贫穷体验,农民从中体验的苦难也就有了别样的意味,除了对苦难的无奈忍受,还有了对现代化城市的某种向往。虽然陈奂生明确了自己的生活趋向并非是进城,但他回乡后却因为在城里的遭遇而得到了乡邻们的尊崇,此等尊崇当然来源于陈奂生坐过的“小轿车”和诸多乡邻们从未见过的五元一晚的充满了现代化之“物”的招待所。
此时,乡村就被搁置在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中,成为了一个具备流动性质素的空间,而城市则成为了乡村人民向往却不能至的美好世界。此即为徐德明先生所说的“城乡意识形态”。在徐德明看来,无论是“前工业”社会还是当下的社会结构中,都存在着大量城乡交往的行为与话语,在这些行为与话语中,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话语元素:封闭而显得没有见识、无法理解的物质欲求。从而,乡下人成为了被城里人看不起、讽刺的对象。“叙述中包含的社会态度、价值观与生活信仰构成了一种崇城抑乡的整体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告诉人们,不论前/后现代,被叙述的人们都生活在一种城/乡文化架构中。”③徐德明:《“乡下人进城”叙事与“城乡意识形态”》,《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二、“城乡分立”映照下的乡村叙事
1980 年代,农民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想象事实上已然拓展到了城市空间/现代化空间。这是一个由自然空间、现代化话语/文化空间和身份空间构筑的复杂结构体。由此形成了1980年代乡村叙事中上城/进城的不同话语指向。面对城市,农民需要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化性身份认同,而这种认同里边明显含有文明/愚昧或富裕/贫穷指引下的“城乡分立”。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城市也是人们向往“好日子”的现实性需求,或者说,城市民众相较于农民生活而言的物质甚或文化充裕必然会作为一个元素进入农民对“好日子”的构建,并且作为农民向往“好日子”的精神力量乃至于现实力量存在着。
事实上,作为农业文明的代表与根源地的农村,在1980 年代西方成为唯一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文化构成中只能作为一种要被抛弃的空间而勉强存在着,而城市空间则以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阵地傲立于世。或者说,在“新启蒙”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在城市/现代化的映照下,农村势必会作为“文明与愚昧”的“愚昧”一极出现并被逐渐抛弃。
古华发表于1981年的《爬满青藤的木屋》①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十月》1981年第2期。是较早触及这一主题的小说,其中构筑了一个温润、寂静而又与世隔绝的“古朴”生活空间——绿毛坑。这一生活/生存空间只有一条小土路可通向外界,护林员王木通一家生活于此,形成了一种尊卑有序、各就其位的古老生活模式。在男人王木通看来:“女人是他的,娃儿是他的,木屋山场都是他的。”②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十月》1981年第2期。他疼爱自己的老婆和一双儿女,但同时也会以“封建家长”的威严偶尔借酒疯殴打自己的老婆和儿女。在山里生长、连场部也才去过一次的女主人公盘青青与家人在那封闭的寂静空间中相安无事地生活着,时不时“睁大了乌黑乌亮的眼睛,心中充满了新奇”地听着丈夫带来的外边世界的消息。当然,丈夫王木通口中外边的嘈杂世界绝不能与安静、无事的绿毛坑相提并论,他提起它的目的乃是为了维护这相安无事、古老的生活状态。
如果不是城市青年李幸福落户绿毛坑,王木通一家的生活状态或许会遵循千百年来中国乡村的稳定性特征而得以长时间传承。然而,这位在红卫兵大串联中丢掉一只手的残疾城市青年却带来了会唱歌的收音机、洗脸用的香皂、雪花油等一系列现代化的“物”。这些物出现在了绿毛坑,给封闭生活空间中的盘青青和一双儿女带来了巨大冲击。这是封闭的乡村与现代化的城市开始交流的象征性叙事,这种交流的结果必定会是盘青青及其孩子们逐渐开启了向现代化寻找自我理想生活状态的趋向。孩子们喜欢去李幸福的小屋,盘青青也要李幸福帮忙买牙刷、收音机等物品。这显然是一种现代化主体的培养模式。然而,盘青青换来的却是作为“封建家长”王木通的无休止殴打与羞辱。
此时,启蒙与被启蒙以及启蒙的障碍被古华在绿毛坑这一小社会中完美呈现出来。但古华在1980年代初期似乎并不完全信任启蒙者,李幸福在小说中虽然被塑造为一位下乡知识青年,但是包括收音机等在内的现代化的物(符号)并未让其被改造的身份有所改变,甚至被王木通压制而产生了嫌弃自己有文化的想法。李幸福的身份是一名被改造者,但同时又是现代文明的拥有者/携带者与传播者,这也是李幸福在小说中既是启蒙者又是懦弱到想要没文化的妥协者的根源所在。同时让我们感到矛盾的形象是王木通,他是一个没文化的粗人,酗酒、家暴,俨然一个封建家长的典型。倒是盘青青在短短的叙事中呈现出一种毫不迟疑的成长,这种成长表现在其日常生活中对收音机、镜子和雪花油的物质需求及其承载的精神需求,更表现在其成长起来的反抗意识。
古华在这篇小说中典型地展示了“新启蒙话语”的模式:把现代/前现代的时间观念搁置在了文明/愚昧的话语空间中,并且二者往往被具象为城市/乡村的形象,而文本构筑的则是一个现代世界的“启蒙者”闯入“前现代”世界并带来精神文明的故事,从而构成了一个“闯入者”叙事模式。这是1980年代“城乡分立”结构烛照下的乡村小说经常出现的叙事方式:“闯入者”介入乡村日常生活的构建、进入农民对“好日子”的构想之中,从而也现实性地召唤着乡村的变革,并且规训了乡村变革的所谓现代化方向。然而,不能不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小说中出现了几个异于经典“新启蒙话语”的情节:李幸福的懦弱和王木通的强势、故事结尾处李幸福与盘青青的消失、王木通换了个林场继续着原来的生活状态。不得不说,古华在1980 年代初期构筑了一个“有限度”的启蒙结构。而他通过这个故事想展现的,或许只是在现代化烛照下凸显绿毛坑的古朴甚或愚昧,从而确定了其指向乡村需要精神文明的话语构建。①在古华的创作谈中,引用了他认可的一位评论家的评论作为结尾:“这篇小说,是对精神文明的呼唤。”古华:《木屋,古老的木屋——关于〈爬满青藤的木屋〉》,见《新时期作家谈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
千百年形成的乡村生活结构,在另外一种生活观念进入其中的时候,必定会因原有的生活惯性受到阻碍而被激发出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有时是作为利益冲突者的形象出现的,比如王木通之于李幸福;但有时却是以农民日常生活的惯性呈现于世,比如路遥的《人生》中就出现过诸如此类的情节。乡村知识分子高加林依据自己掌握的现代化知识发动了一场“卫生革命”:在其视为脏的水井里投了漂白粉,此举因为与乡邻生活习惯不一样而引起了乡邻的质疑和恐慌;巧珍听取了高加林的建议,在众目睽睽下刷牙的戏剧性情节,人们惊奇地“看”着巧珍刷牙,是因为巧珍冲击了乡邻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显然,此等叙事的内在逻辑是:现代化/文明的生活方式进入乡村的时候,凸显了乡村生活世界的前现代/愚昧性,进而被具象为贫穷与苦难。而二者的生产不仅仅来源于农村内部基本物质资料与现代化精神的缺乏,更多的是一种“眼光”的生产,这种眼光使得乡村与城市自然性地对比起来,从而生产了贫穷的乡村。乡村愈穷、城市愈好;城市愈好,乡村愈穷。
《鲁班的子孙》中小木匠的归来也可归属于乡村“闯入者”叙事模式之列。小木匠虽然生长在农村,但是却在被迫离开农村后进入城市,并接受了所谓现代化的一系列“物”与思想。而小木匠的再次离开显示了农村的伦理容纳不了现代化的作为,或者说,农村必须要依据现代化的规则改造自己的传统社会关系与伦理观念,才可能容纳现代化的作为。然而,城市的急剧化发展尚未容纳农村的现代化转变就已经抛弃了它!在整个1980年代(及其后)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农村是一个被逐步抛弃的空间,农村并未参与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化过程之中。但是,生存于1980 年代及之后的农民,因为有了现代化“物”的刺激逐渐要求分享国家的改革红利,就不得不抛弃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家园,于无奈中走进城市。
三、城市/现代化介入乡村生活世界的话语构筑
如果说《爬满青藤的木屋》《人生》《鲁班的子孙》中的“闯入者”最终在与乡村“固有”的生活观念之矛盾冲突中“离去”,从而构成了一个“未完成性”的“闯入者”叙事模式,那么在西方经典的现代化进入中国1980年代的文化构成并最终成为指引中国发展方向的模板时,《哦,香雪》中的火车便以“闯入者”的“身份”事实性地介入并在最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村生活世界的结构,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闯入者”叙事模式。
近代以来,包含了“进化论”观念的西方现代性思想介入中国文化结构,使得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当作为自然性空间差异的城乡被设定为时间性/文化性空间差异的城乡关系时,城市就被注入了进步的指向、成为了现代文明的表征,成为了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向与未来。
即是说,人们生产了一个凋敝、苦难的乡村,生产着文明/愚昧、先进/落后的二元结构,也生产着城乡的分离与对立。那么此时,人们也必定生产着一个富足、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城市空间,生产着一个农民逃避落后与愚昧的意识与趋向。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最明显、最深刻的变化就是延伸性的城乡关系变成了分立式的城乡关系,从而使得城市被注入了“现代”的内涵,而乡村则相应地成为了“前现代”的空间。此时,作为现代化表征的城市不仅是一个自然性生活空间,更意味着一种先进的生活方式。因此,对于乡村和农民而言,城市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空间。但是,如若具体到1980年代的文化空间,农民究竟如何想象城市/现代化?当它们介入农民的“好日子”构建时,究竟向农民指引着什么样的美好追求?
1982 年,铁凝发表了一篇触及1980 年代城乡/ 现代化问题的重要小说——《哦,香雪》。这是一篇日后引起诸多关注与讨论、享有较高声誉的小说①有学者大致梳理过有关《哦,香雪》的评论:“《哦,香雪》甫一问世即获前辈奖掖,受同侪艳羡;此后的三十多年里,铁凝以颇可嘉许的勤奋不断刷新、拉伸她的作品谱系,并为自己在读者群、批评界和文学圈赢得了持续的关注度。可以这么认为:《哦,香雪》在这三十多年的持续关注中从未失去过受赞誉的地位,而这赞誉,如今已凝为一种文学史结论。”见王侃:《“城/乡”现代化与现代性叙事逻辑——重读〈哦,香雪〉》,《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2期。,但对这篇小说进行主题解读仿佛也并非难事,2004 年作者铁凝对此小说的回溯性解读就可作为一种总结性的阐释来看待:“(苟各庄)土地的贫瘠和多而无用的石头使这里的百姓年复一年地在困顿中平静地守着日子,没有怨恨,没有奢求。这苟各庄的生活无疑是拮据寒酸的,滞重封闭的……”②铁凝:《文学·梦想·社会责任——铁凝自述》(赵艳整理),《小说评论》2004年第1期。,但由于火车的进入,逐步打开并冲击着小山村的封闭与滞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循环往复式时间观念在“香雪”们心中逐步转变为了求变的、直线式发展型的时间观念。她们摒弃了一天的劳累,刻意打扮了自己,去接受一种希望的洗礼,“火车”成为了这群孩子们“梦想的开始”和“希冀的起点”。③铁凝:《文学·梦想·社会责任——铁凝自述》(赵艳整理),《小说评论》2004年第1期。
在之后的诸多解读者的阐释中,铁凝叙述的故事与鲜明的思想取向就被作了一种模式化的解读:火车作为现代文明的表征介入了一个封闭/落后的乡村空间,从而询唤着乡村年轻人(女孩子们)的美好/现代化想象;也会把诸如“希望”“明天”这类的字眼作为火车穿越乡村的预示,并进而把香雪看作是向往城市/现代化生活的“先驱”。这样的解读或许在对城市/现代化生活热切期盼的农民心中或“新启蒙”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中,展现出了对农民求变意识的充分挖掘与形塑,从而成为了1980年代的时代主题——追求现代化——而被嵌入颇为灿烂的历史之中。④如在1984年的一篇文章中,陈丹晨说:“对于未来生活充满美好的幻想和热烈的追求却比谁都强烈执著,因为换取那梦寐以求的铅笔盒子,她冒失地登上列车,被载驰而去……”见陈丹晨:《天真的、单纯的、真诚的……——记铁凝的创作》,《萌芽》1984年第1期。雷达在文章中也直接表明过类似的看法:“她的追求绝不是什么‘铅笔盒’,否则就太藐视我们的香雪了;她追求的是‘明天’,每一个不同于昨天的新的‘明天’。”见雷达:《铁凝和她的女朋友们》,《花溪》1984年第2期。恰如王侃所言:“《哦,香雪》是一个假借‘乡土’的琴壳弹拨‘启蒙’这一弦外之音的短篇小说。”⑤王侃:《“城/乡”现代化与现代性叙事逻辑——重读〈哦,香雪〉》,《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2期。这或许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香雪为何追求“凤娇”们并不关注的书包与铅笔盒?香雪与“凤娇”们在追求着一个不一样的明天吗?
在诸多评论者的阐释中都出现了一个1980 年代较为现代的物象:铅笔盒。在小说中,铅笔盒作为一个现代物象主要出现在两个场景中,最先出现于香雪在公社中学的同学处,而后香雪又在“火车”上看到并且得到了铅笔盒。这两个场景都出现于台儿沟之外的世界,铅笔盒由此被赋予了一种现代内涵,并成为了现代意识指引下美好明天的表征。但它的意味究竟是“吸引着乡村迅速向现代文明迈进”①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35页。的物象化想象,还是一种迫切走出贫穷山村的手段?这样的区分是必要的,因为它们必定会指引着乡村向不同的方向迈进。事实上,在人们对于现代化的想象中,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取向,人们对文明的美好想象不仅仅是走出贫困与苦难的乡村世界,更是走出愚昧、走向培育人的尊严的美好文明空间。
作为工业文明/现代文明表征的火车开进了一座大山的褶皱中,其巨大的嘶鸣确实震颤着宁静而封闭的台儿沟。这种震颤不仅仅在某种意义上打乱了“滞重封闭”的台儿沟的日常生活秩序,更在被阐释为“明天”的过程中确定了自己的现代化意义。于是“香雪”们每天必至的“看”火车必定会开启某种被“启蒙”的程序,同时也自然地呈现为“被看”的对象。恰是在这“看”与“被看”的关系中,“香雪”们通过具体的物象逐步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乃至于主体性。
但同时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香雪与“凤娇”们因为看到了不同的物象而使其呈现为似乎有些不同的身份认同。在火车停靠在台儿沟的一分钟中,“凤娇”们看到了“妇女头上的金圈圈”和“比指甲盖还小的手表”,但香雪却看到了“皮书包”。事实上,书包对于“凤娇”们来说是没有用处的,因为香雪是村里唯一一个考上公社初中的学生。学生身份的缺失使得“凤娇”们看到了能够让她们新奇的现代化“物象”,而香雪的学生身份让她看到了书包,其中当然也寄寓着铁凝和迫切向往现代化的人们对于乡村被启蒙先驱的殷殷期盼及启蒙方式。但是,在罗岗和刘丽看来:“‘铅笔盒’的‘现代光环’却并非自动获得的,相反,它是通过一系列‘遗忘’和‘压抑’的机制‘生产’出来的。”②罗岗、刘丽:《历史开裂处的个人叙述——城乡间的女性与当代文学中个人意识的悖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其中作为“物”的“铅笔盒”质素就被“遗忘”和“压抑”进了“香雪”们、“启蒙者”们的现代化想象之中。
于是,在现代化的文化想象与生产体系中,她们之间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看到的物象的不同与学生身份的有无上,更在于通过这些物象与学生身份究竟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明天。此时,有理由相信,就如陈丹晨与雷达所说的,香雪一定会努力学习,通过现代化知识的取得追求书包承载的那个文明、现代化的明天;而“凤娇”们只能跟随时代主题的变迁或留在农村或进城打工,依凭自己的辛苦劳作换取一些现代化的“物”而已。
好像香雪与“凤娇”们追求明天的起点就是不一样的,因为香雪“是台儿沟唯一考上初中的人”,学生身份的有无似乎决定了她们的起点不同,进而好似她们的前途也会不一样。这样一种平滑的逻辑似乎表征了火车会成功带着台儿沟迈进现代文明,铅笔盒也会成功地带着香雪走进美好的明天,连“凤娇”们都会有一个与昨天不一样的新的明天。日常里,香雪和“凤娇”们一样,在一分钟内,拿着自己家产的核桃、鸡蛋、大枣等换取在台儿沟很少见到的挂面、火柴、发卡、香皂,甚至还有纱巾和尼龙袜等外边世界的物象。唯一有区别的是,稍显洁净的香雪总是比“凤娇”们生意做得顺利。直到有一天,香雪看到了一个“装着吸铁石的自动铅笔盒”,似乎香雪和“凤娇”们的前途就不大一样了。
然而,在看似凸显了香雪的学生身份与美好前途的背后,却显然展示了香雪和“凤娇”们走向明天的起点其实是那么的一致。香雪用了40个鸡蛋,走了30里的夜路,才换得了那个铅笔盒。香雪缘何对“能自动开关的铅笔盒”费那么大的心思?难道真的如雷达所言,是“对于未来生活充满美好的幻想和热烈的追求”③陈丹晨:《天真的、单纯的、真诚的……——记铁凝的创作》,《萌芽》1984年第1期。?
事实上,香雪对铅笔盒最初关注的根源,是来自于一种贫穷的屈辱与尴尬,这种屈辱更直接来源于两顿饭还是三顿饭的对比与疑问。作为唯一从台儿沟去15里以外的公社中学读书的初中生,香雪在与同学们言行举止的对比中,确立了自己来自于“穷”地方的“穷人”身份。这种身份的确立更是来自于同学们每天吃三顿饭与自己家每天吃两顿饭的比较中,还有笨重的木铅笔盒与别人“宽大的泡沫塑料铅笔盒”的对比中。因此,铅笔盒生产了香雪的一种贫穷的尴尬,它激发了香雪拥有对作为“物”的“铅笔盒”的热切追求与期盼。也可以说,香雪看到的“铅笔盒”与“凤娇”们看到的发卡等都首先是一种“物”形态,其次才被重组进现代化想象结构之中,并且在对比中“铅笔盒”呈现出了更大、更强烈的现代化“光环”。
此时,或可直接说,香雪对铅笔盒的关注并非来自于现代化的觉醒,而是贫穷促成的尊严感缺乏,进而生产出的一种对“物”的热切期盼。生长在宁静的大山褶皱里的香雪,应该没有如陈丹晨先生等知识分子的现代化“眼光”,当人们过度审美化香雪的时候,事实上也就过分审美化了现代化。当然,她的确是铁凝们这些知识分子眼中的现代化想象!此时,对美好明天的追寻与走出贫困的手段合二为一了,看似香雪身上呈现出的现代意识成为了其克服贫困的手段,成为了香雪走出父母物质贫困的路径,但这其实是一种颇为隐蔽且吊诡的结合或置换。然而,这并不能阻挡香雪对美好明天的想象:在用40 个鸡蛋换得自己心仪已久的铅笔盒时,她所熟悉的山村俨然成为了铁凝笔下的“风景”①借用柄谷行人语。见[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式描述,进而这种“风景”就按照现代化生产装置有了一个“美好”的明天:
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要是再碰上今晚这种情况,谁都能从从容容地下车。②铁凝:《哦,香雪》,《青年文学》1982年第5期。
显然,这是一个现代化浸润之后、想象中的台儿沟,是一个在现代化烛照下有了某种主体性的香雪心中的台儿沟形象。③虽然,有学者质疑香雪们在城/乡或现代化轨道之中的“主体性”建构,而是“引入时间性和技术展开方式的分析角度”,认为香雪和凤娇们“超越了传统共同体框架和市场逻辑规定的现代个体形式,而由此带来的‘个体化’特征,也超越了作为劳动力资源的经济个体”,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1980年代的“现代化”生产装置的难以突破。见王钦:《新时期文学表征中的“个体化”难题——重读〈哦,香雪〉》,《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此时,如何能够验证这种“美好明天”究竟如何?无他,只能溢出1980年代的话语生产语境,看一下香雪及“凤娇”们的“美好明天”究竟是什么样的。
如若可以把时间段拉得足够长,就可以让人们看一下2004年铁凝笔下现实的“香雪”们在新世纪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铁凝带着一个问题切入了“香雪”们曾经的美好明天,火车除了带着所谓的现代化质素以及由此而来的物质想象之外,还带着什么介入了苟各庄的生活世界?新世纪初期,苟各庄被发展为河北著名的旅游景点,“香雪”们/“凤娇”们的日子富裕起来了,终于再也不用像等情人一样地等着看火车,她们穿着干净、时兴的衣服,平静、自信地面对着南来北往的来客。这样的日子,确实是1980年代“香雪”们/“凤娇”们想象的“美好明天”,由火车带来的现代化文明也好似确实带动了乡村的现代化发展。
在富裕起来的苟各庄或者以此为代表的乡村世界中,终于知道了致富带来的生活是如此之美好。但是,也“就有了坑骗游客的事情,就有了出售伪劣商品的事情,也有个别的女性,因了懒和虚荣,自愿或不自愿地出卖自己的身体……”①铁凝:《文学·梦想·社会责任——铁凝自述》(赵艳整理),《小说评论》2004年第1期。这里,不再有羞涩而善良的“香雪”“凤娇”们。当然,或许香雪凭借着贫穷激发的尊严考上了大学,走进了城市,但是这种在明天的故事里并不具有典型意义的乡村想象,究竟在现实中落实了怎样的现代化?或者说,火车给台儿沟究竟带来了什么?
在铁凝的思考中,把火车称作“温柔的暴力”。即是说,当现代化为人们带来物质的丰裕之时,也带来了某种道德或精神的沦丧,只是它并没有物质丰裕来得那么显明与体面而已。人们不能因为纯净与善良的“香雪”们的丢失而拒绝着现代化为我们带来的丰裕的物质与便利的生活,这当然是一种不负责任且毫无意义的讨论。但是,罗岗、刘丽在解读《哦,香雪》和《奔跑的火光》时指出:
……这个悖论式的过程表现的正是一种普遍性的状况,从“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只能孤零零地暴露在“市场”面前,成为“市场逻辑”所需要的“人力资源”,“解放”的结果走向了它的
对立面。“个人意识”如此异化的效果,必然造成“个人”产生强烈“认同”的需要。②罗岗、刘丽:《历史开裂处的个人叙述——城乡间的女性与当代文学中个人意识的悖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这当然是一种令人沉痛而悲愤的发现。1980 年代,当城市/现代化介入农民对“好日子”的想象时,讲述明天的故事直接指向了走出贫穷、走向富裕的“美好明天”。然而,这种话语体系中内含着只要物质充裕,一切都无所谓的“缺陷”式想象趋向。因此,如若站在当下全面市场化及其困境中回视1980年代乡村叙事及城乡分立的话语构筑,对以下问题的重新考察就显得尤为必要:
在这种似乎无可奈何的“发现”中,人们要关注的应该是农村如何分享改革红利。那么,在农村分享改革红利的过程中,如何保持“香雪”们那份纯净与善良?如果二者不可兼得,那么如何在物质丰裕的过程中阻止这“温柔的暴力”以生产出与之匹配的精神文明甚或道德重构?人们究竟应当如何在乡村“好日子”的构想中不仅生产着“吃”的欲望与满足,更生产着尊严的主体性,以不至于让人特别是农村人陷入资本趋利的陷阱进而成为其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