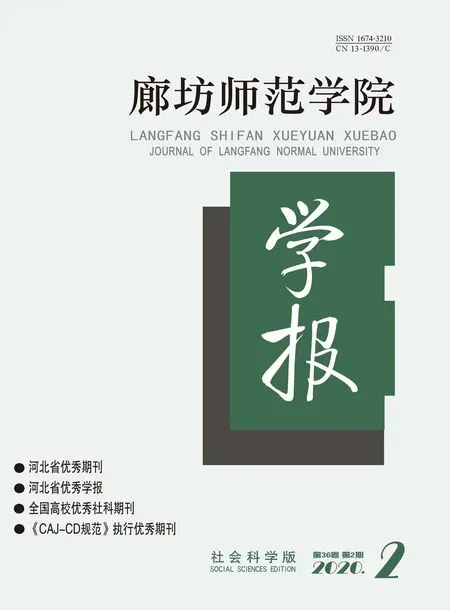中庸、变通与仁爱
——汤因比中国文明观中的儒家思想
2020-03-04刘宝
刘 宝
(南京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
作为20 世纪西方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汤因比打破“国家”界限,从“文明”的新角度观照世界历史及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纵观其一生,汤因比于不同时期对中国文明的态度发生过巨大转变,甚至在后期彻底颠覆了前期的态度。①刘宝:《汤因比早期中国文明观探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其态度变化的整个过程中,汤因比始终坚守一个精神内核从未动摇,那就是对中国早期诸子思想的理解、欣赏和实践。
汤因比自幼接受古典教育,熟知希腊古典哲学,自然了解自苏格拉底(约前479—前399)到普罗提诺(Plotinus,约203—262)的那个时代,极具创造力的希腊哲学家们所形成的“黄金的链条”。然而,这个“黄金的链条”却充满不幸:在其起点,希腊文明开始衰落;在其终点,罗马文官制度已经解体。或可说,这链条伴随着社会持续动荡不安而存在。值得庆幸的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哲学家因较少卷入混乱社会生活的物质结构而创造出具有更多价值且更为持久的成果。“当罗马行政官员建立希腊化大一统国家时,哲学家却给他们的子孙留下了这样一些遗产:学园派、逍遥学派(Peripatus)、拱廊、花园、犬儒学派关于大道与障碍的自由、新柏拉图派哲学家们超凡脱俗的理想世界。”②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Abridgement of Volumes I-VI by D.C.Somervell(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372.在时间大概相同的中国,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思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正面临着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不断、战乱频仍的局势。与希腊“黄金的链条”一样,不安定的社会环境激发了以儒、道、墨为代表的诸子思想的绚烂光芒,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次高峰。两千多年后,汤因比也生逢乱世,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多次地区与国家间战争,即使到了晚年也并不认同自己所处的两极争霸的世界可被称为真正的和平状态。但社会的不幸,造就了历史学家的“大幸”,汤因比从一开始就持有的整体历史观念与后期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对人类前途的关注,都离不开他所身处的乱世背景带来的影响和推动。汤因比历史哲学认为,文明具有“同时代性”,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时代与他自己的生活世界差距虽有两千多年,但充其量也不过转瞬之间。①刘宝:《汤因比文明观念的对话主义内涵与“星丛”归宿》,《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他自幼接受的希腊教育、他自身所处的时代经历,都与中国先秦那段产生哲学思想高峰的乱世背景大致吻合。正因如此,汤因比在思考中国文明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涉及诸子百家思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等都有所提及。比如,他关于文明起源最重要的“挑战—应战”理论,从一开始就借用“阴阳”观念解释一个社会从静止状态向活动状态的过渡,并将此观点大加宣扬且一以贯之,至去世前都未作任何替代甚至修改;谈及文明起源的神话线索,用“阴”(Yin-state)的状态描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的生活图景;在展望教会的未来、探索潜意识心理如何与上帝协调一致的时候,称消极极乐状态为“阴”,认为“一旦‘阳’创造出人类的意识和人格,这种状态也就一去不返”②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Abridgement of Volumes VII-X by D.C.Somervell,p.104.。另外,对于法家在中国统一时期的作用、名家的产生和衰落等内容,也都或多或少有所涉及。
汤因比在其一生中,对中国文明的态度不断变化,甚至晚年走向了早期的反面,但在巨大转变中隐藏的这条始终不变的线索,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本文选取先秦诸子中汤因比提及最多,对他本人影响最大的儒、道、墨三家中的儒家思想进行分析,以探寻汤因比与中国文明契合的思想根源。
一、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重要内容,它既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也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在汤因比对中国儒家思想有了深入了解和广泛应用的前提下,我们摘取其思想与作品中较为突出的三个方面来探索汤因比历史哲学中“中庸之道”的具体表现和实践。
首先,关于文明起源的“挑战—应战”理论。
汤因比在谈到“挑战与应战”关系的时候,罗列了五种刺激类型——艰苦环境、新地方、打击、压力和缺失,提出“刺激是否会随挑战增强也无限增加”的思考,并最终将“挑战—应战”法则确定为“挑战刺激力的最高值出现在挑战不足和挑战过度间的临界点上”的“中庸之道”理论。③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Abridgement of Volumes I-VI by D.C.Somervell,p.140.这个“中庸之道”是两极中间的一个中点,挑战不足时,反应较弱;挑战的严重性超过中点时,应战成功程度不升反降。所以,“挑战—应战”之间的关系服从“报酬递减原则”;刺激在中点处达到最强,这个中点就是挑战的“最适点”。
汤因比列举了严峻的人为挑战例子——战争。面对波斯侵略的破坏,雅典成了“全希腊的学校”;面对拿破仑侵略的破坏,普鲁士变成了俾斯麦的德国。这都是战争适度刺激得到成功应战的情况。而汉尼拔对意大利的蹂躏,则是一种过度的极端刺激,超过了“中庸之道”的中点,就未能如前面二者产生因祸得福的结局。意大利耕地被破坏,农村人口减少,大批无地农民涌入城市沦为赤贫无产者,这种破坏直到汉尼拔撤出意大利之后的第三代人身上依然延续,而政治动乱频发,使得罗马共和国局势更加失衡。这种刺激的强度,已不仅是挑战,而是致命和毁灭。汤因比将最重要的文明起源理论架托于“中庸之道”,因为挑战与刺激并不以固定强度和大小出现,也不受人为约束和控制,这一点与儒家“中庸”本质内涵吻合。中庸“并非不偏不倚,而是在动态中实现力量的一种均衡”④樊海源、崔家善:《中华儒家思想之理论旨要与时代价值》,《学术交流》2015年第3期。。
其次,关于美苏争霸不可调和的关系。
1950 年代之后,汤因比对中国文明的态度虽有所好转,但其关于世界和人类前途命运的解决方案实则寄托于美苏两国。然而,经过冷战后多年观察和苦苦等待,汤因比终于发现美苏两国不是实现其理想的媒介和载体。一方面,他认识到两个超级大国尽管从军事和经济上势均力敌、此消彼长,但都因对工业和军事的狂热竞争而导致过度工业化、过度掠夺和对资源与环境的严重破坏。这种潜在二元体系下隐藏的不是中庸之道,而是给环境与人类带来的更大的危险。儒家经典《礼记》强调“以德取物”的生态伦理思想,强调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资源物产要有约束,要因时因地有节制地获取,要“取物而不尽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汤因比的观念与此相通。即使美国和苏联任何一方以其巨大的核力量统一人类世界,付出的也是自身以及整个生态环境的代价。
另一方面,汤因比认识到美苏两国虽然并存,但不同的阵营和意识形态却导致二者无法退让或调和,两个超级大国建立在各自“争霸”的目标之上,冷战后期取得的缓和并没有改善这种枉顾整个人类世界和生物圈福祉的态度。这也导致汤因比放弃对美苏两个大国的幻想,并在其晚年将希望转向中国文明。或许,对于有历史远见的汤因比来说,即使冷战后期美苏两个超级力量有更多方面的协作和调和,但意识到西方文明在走下坡路的他,也不可能继续从两个大国身上寻找出路。牟钟鉴教授曾引用西方开明的新儒家学者杜维明教授的一段话:“现代西方文化一方面创造了很多价值,但同时也把人类带到了不仅是自我毁灭,而且可能把经过亿万年才逐渐发展出来的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生活环境亦同归于尽。”“现代西方文明完全以动力决荡天下,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浮士德精神的无限的扩张、无限的发展、无限的争夺这种心态作为主导,必须重新反思。”①[美]杜维明:《杜维明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转引自牟钟鉴:《是天下一家还是弱肉强食——儒学天下观的当代意义》,《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期。牟钟鉴教授据此断言:“如果地球毁于人类之手,那么必将是毁于西方文化而绝不是东方文化。”②牟钟鉴:《是天下一家还是弱肉强食——儒学天下观的当代意义》,《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期。牟教授这段话本意是否定西方文化引导国际形势走向和平的能力,并非针对冷战时期国际形势而言,但我们将其拿来理解汤因比当时面临的困局,一样中肯合理。
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论语·中庸》)他把“中庸”当作人们应该遵循的最高美德。虽然中庸思想有主张调和的一面,强调对立双方的平衡,“但它不是折中主义。因为孔子在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等问题上一直都是立场坚定、态度明确的”③苏俊霞:《孔子的中庸思想解读》,《齐鲁学刊》2014年第3期。。汤因比晚年对美苏争霸这种有失美德的行为感到失望之后,态度毅然转向中国文明,一如孔子当年在鲁国希望破灭后毅然离去,周游列国。
最后,重点探讨汤因比屡次提及中国文官制度的利弊盛衰。
在汤因比的历史著作中,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比如希腊、埃及等在历史上出现的文官制度被经常提及,而中国文官制度涉及最多。
汤因比对经由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而走向政坛的文职官员的社会功能大加肯定。神化王权的存在首先需要一个受过教育的文官群体,没有他们的支持,国王们几乎无法坐稳自己的宝座。比如古代埃及,文官不仅是王权幕后的实权派,也经常会走到台前发挥巩固王权的作用。汤因比比较了古罗马文明与古代中国文明的文官制度:
奥古斯都面对惨遭蹂躏、混乱分裂、积弱不振的国家,创立新的文官制度,其成就可与150 年前中华世界的汉刘邦相媲美。当然,就汉刘邦体制和屋大维体制的寿命而言,那位中国农民建立的行政体制要远胜于罗马城市市民屋大维的体制。奥古斯都的体制延续700 年之后就已彻底瓦解,而刘邦的体制一脉相承,一直延续到1911年。④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Abridgement of Volumes VII-X by D.C.Somervell,p.69.
如果将罗马文官制度与汉朝文官制度的历史进行比较,便可发现汉朝文官制度生命力更长的原因所在:汉朝自刘邦起,即面向所有社会阶层开门纳贤。公元前196年,刘邦恢复秩序后第6 年,便颁布诏书,令各郡行政当局选拔贤士作为公职候选人,并将其送到首都,由中央政府官员决定取舍去留。至汉武帝时,中国新文官制度形成了确定的体制:文官候选人必须擅长儒家经典,能对儒家哲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于是在公元前2世纪,儒家学派被帝国政权巧妙地变成合作伙伴,这可能大大超出孔子在他自己时代所能预料的范围。与戴克里先时代希腊世界单纯模仿古代文学相比,“儒家学派枯燥的政治哲学能够更好地在官僚集团中激励起一种团队敬业精神,不管这种政治哲学有多么迂腐,却能够提供一种罗马帝国文官制度所缺乏的传统道德规范”①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Abridgement of Volumes VII-X by D.C.Somervell,p.70.。
汤因比认为,儒家思想在培育中国文人道德和智识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在讲到东印度公司职员从掠夺成性、残忍贪婪的无赖转变为不以个人私利为念、不滥用政治权力的文官的变化过程时,汤因比说有理由将他们所接受的道德教育和智力训练“与中国儒家经典的教育相提并论;中国的儒家教育确定于两千年前,之后始终是中国文官的必备条件”②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Abridgement of Volumes VII-X by D.C.Somervell,p.72.。汤因比曾提到中国文明和唐王朝在755—763年的混乱中得以幸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文职官员的存在。“文职官僚以反对分裂、反对革新为代价,强固了中国社会的结构。”③Toynbee,Mankind and Mother Earth(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447.
在肯定文官制度的同时,汤因比也深刻指出了文官制度的缺陷,认为它导致文人官僚很容易越过中庸之道的“中点”,从而激发难以调和的矛盾。文官因其重要地位而拥有不从事繁重辛苦劳作的特权,更容易变本加厉地把沉重负担加诸于下层民众。汤因比引用了古埃及《都亚夫的教谕》来说明文官的特权和对人们的诱惑力。都亚夫在将儿子佩皮送到经院学校和文官的孩子们一起学习的时候,对儿子进行了这样的劝诫:
我见过被打的人,被打得很惨:所以你们一定要专心读书。我见过被免于劳役之苦的人:所以你们记着,任何事情都比不上读书。任何挥舞斧凿的人都比其他人更感到疲倦。石匠在各种坚硬的石头上完成工作,工作做完,手臂也已毁掉,整个人都十分疲惫……在田地耕作的人们永远在不停谋算……他的辛苦难以言喻……工场的纺织工的命运比任何女人都更悲惨,他的腿要长久蜷曲着抵着腹部,几乎不能呼吸……让我再告诉你渔夫的命运,他在河里的工作,难道每天不都要面对凶狠的鳄鱼带来的致命危险吗?……记着,除了文官以外,没有任何官吏能够使唤你,文官才是领导者。④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Abridgement of Volumes I-VI by D.C. Somervell, p.325.
与其说这是一名父亲对儿子学习和前途的劝诫,不如说更是对文官所拥有特权的侧面描画。汤因比认为,中华世界的官僚机构与埃及“文官制度”同样可怕,而且还有着更为久远的先辈传承。“三世纪的中国也存在着精神上的真空。儒家出身的文官因滥用权力而使儒家学说斯文扫地,中华帝国已两度在他们对私利的追逐中瓦解。”⑤Toynbee,Mankind and Mother Earth,p.353.这些儒家文官不愿付出任何努力来减轻成千上万贫困人口的负担,“他们蓄着长长的手指甲,除了写写画画之外便毫无用途”,“他们在维护自己残酷统治的过程中已经学会了埃及同行的顽固”⑥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Abridgement of Volumes I-VI by D.C.Somervell,p.325.,或许我们无法证明这个论断正确与否,无法确定中国儒家文官的传统习惯与埃及存在相互学习或模仿,但重要的是,直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到来,也没有动摇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处世之道。到汤因比创作《历史研究》之时,科举考试早已废除,但“文官们照样可以骑在农民身上耀武扬威,凭借的只不过是一张芝加哥大学或者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文凭”⑦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Abridgement of Volumes I-VI by D.C.Somervell,p.325.。
另外,汤因比通过对希腊、中国和印度文明历史中大一统国家的比较,更加深入地揭示了官僚制度的两面性。奥古斯都及其后继者把贪婪成性的罗马商人改造成优秀的文官,汉刘邦及其后继者把巧取豪夺的封建贵族改造成优秀的文官,康沃利斯及其后继者也把大肆搜刮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业代理人改造成优秀的文官……这些事例结局虽各不相同,却都暴露出文官制度特殊的缺陷。官僚精神的两面性解释了它们为什么会最终归于失败:缺乏热情、不思进取、不愿承担风险等陋习抵消了“廉正”的最高美德。文牍主义和文官选拔体制的逐渐僵化,同时使文学也受到了巨大的压制。儒家传统的文官不可救药地痴迷于中国古典文学,推行文化压制政策,根本不允许大众文学展现旺盛的生命力。直至元代蒙古征服者统治时期,儒家文人暂时遭到罢黜,儒家传统文学陷入极端艰难的逆境之中,充满生机的白话(vernacular language)大众文学才得到了迟来的发展机会,长期湮没无闻的白话文学得以公开进入中国社会生活。①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Abridgement of Volumes VII-X by D.C.Somervell,p.199.一直到元朝灭亡,儒家传统得以恢复之后,它们仍然流传下来。明朝虽然恢复了通过儒家经典进行科举考试来选拔文官的制度,但它已变成一种僵死的形式,固执地维持到1905 年被取消。然而无论如何,明代文学和哲学却充满了生气,大量小说和戏剧作品不断涌现。“新题材的创作者们还略带羞涩,遮遮掩掩,但他们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可等同于但丁之于西方文学、阿肯那顿之于埃及文学。”②Toynbee,Mankind and Mother Earth,p.512.
在汤因比文明体系所包含的三代文明中,自相残杀的战争成为导致文明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在第一代文明中,它毁灭了苏美尔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在第二代文明中,它毁灭了巴比伦文明、印度河文明、叙利亚文明、希腊文明、中华文明、墨西哥文明和尤卡坦文明;在第三代文明中,它毁灭了东正教世界主体及其俄罗斯分支的东正教文明、远东文明的日本分支、印度文明和伊朗文明。然而,埃及文明和远东的中华文明似乎是毁于一种不同的偶像,即大一统政权以及日益臃肿的寄生官僚制度。③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Abridgement of Volumes VII-X by D.C.Somervell,p.312.这种文官制度,从它最初对皇权的帮扶和支撑,到之后导致大一统政权的解体,恰恰充满了违背儒家中庸之道精神的行为。孔子谈到为政时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宽和猛互相补充,互相调整,才能使政治达到“和”的局面。如果套用到文官制度上来,不管是文官们日益享有的特权,还是走向僵死的入仕制度,甚或是对儒生和考官独立思考能力的遏制、对文学样式的压抑,都说明了本应以中庸之道为方法论和行为准则的儒家官员们,偏偏迈过“中点”而走向“猛”的极端的悖论。
二、变通之道
《易传·系辞》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儒家思想倡导顺应时势,善于变通。孟子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孟子·公孙丑》)此处所说“乘势”,即指顺势而为。《孟子·离娄上》第十七章有一段人们熟知的对话——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儒家虽以礼为先,讲究男女之妨,但“嫂溺”之时可以伸手相助,这就是“权”,就是权衡情况而变通。至于后来到西汉时期,儒法结合、儒道互补,再后来儒释相互融合,都体现了儒学思想的变通、会通精神。
汤因比是个讲变通的学者。结合他的中国文明观点来看,其变通思想最直接而明显的表现是对“阴阳”观念的多次应用。“阴”和“阳”两种状态的运动和相互转化,构成了文明起源的主要途径,但在汤因比看来,这种运动和转化不是简单的对立和融合,还有“变”的节奏存在。汤因比曾把人类文明的前进以织布机梭子作比喻,梭子从织布机的一端到另一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如同“阴”“阳”不断相互转换,然而梭子的每一次往复,织布机上的图案都产生了新变,都有新图案出现,正如人类文明在“阴”“阳”交互转换的过程中也不断产生新变,进而让人类文明不断得以延续和发展,走向“变则通,通则久”的状态。
汤因比一生最重要、最宏大的变通思想在于隐含的不断变化的“文明中心”理论,以及最后对“爱”的寄托。汤因比对中国文明的态度有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的变化,其背后隐含的是对“文明中心”之所在的不断思考和改变。汤因比早期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者,不仅在作品中对中国文明有较多贬损之处,同时认为世界所有其他文明都在经受西方文明的辐射和同化,是文明“一极”的单数隐喻。中期汤因比对中国文明的描述态度有所升温,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关注也在增加,从更深层次来看,这就是汤因比的“变通之道”。汤因比思想中期,冷战后美苏争霸成为国际政治主要趋势,虽然他偶有对这种局面的担心,但他仍寄希望于两个超级大国,将文明中心的考虑从“一极”单数转换为“两极”复数。到汤因比思想后期,其对中国文明的态度出现了“一边倒”的礼赞。这是其在对两个超级大国主导世界文明和人类前途感到失望之后的“变通之道”。汤因比看到了两个大国之间无法调和,也看到了新中国的崛起之势,从而将文明中心在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下置于中国文明之上。
除了文明中心在三个不同阶段的转变之外,汤因比在后期对“生物圈”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并对“终极精神”进行了思考。希腊哲学斯多葛学派说,“人是宇宙的一员”,中国新儒学派哲学家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又说:“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按照王阳明的世界观来说就是:“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其视天下犹一家焉。”①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8页。这一切给汤因比以新的思考,让汤因比从对人类的关注转向对人类所赖以生存的整个“生物圈”的关注。在晚年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汤因比提到在宇宙的某个地方有“终极精神存在”,他认为这种终极存在就是“爱”。
我赞成王阳明的格言:“至极者,明德新民之极则也。”爱意味着付出甚至牺牲自我,即便如此,人类也始终要接受爱的引领,服从于爱。爱是一种精神冲动,它不是一味去索求,而是主动奉献。爱的冲动把自我引回到跟宇宙相调和,自我之所以为宇宙所疏远,就在于自我中心性。这种自我中心性是天生的但又不是不可克服的。②[英]汤因比:《展望21 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20页。
为了“生物圈”的生存和未来,汤因比最终想到“爱”,这与孔子所说的“仁爱”相通。作为孔子思想核心的“仁”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超越境界,“‘仁’之人道精神有其‘感通’之义,而这一‘感通’的最终一层,是人与天的感通”③郭齐勇:《儒家人文主义与道家自然主义》,《船山学刊》2017年第5期。。儒家思想中,人与天道的通——贯通、感通——对圣凡统一的强调,喻示人与天地万物皆有神性,生物圈中的人与各种动植物、各种非生命物都有自身的意义和价值。
对西方文明的失望,让汤因比从文明的一极走向两个超级大国的复数表现;对美苏之间既不能调和又无法通过一己之力在不进行毁灭性核战争的前提下实现人类政治统一的失望,让汤因比摒弃文明复数中心的论调转而将重任交与中国文明;在对过度工业化与战争给“生物圈”带来的威胁进行抵抗而又无法解决时,汤因比试图寻找“爱”的途径解决人类面临的困境。这一切,都是汤因比在困难和窘境面前进行“变通”的表现。汤因比不是一个脑筋固执的人,他的思想随着时代和现实条件的不同而进行转变。在汤因比一生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或许会忽略他及时而又成熟的“变通之道”,但假如我们将他一生的时间压缩,把他理想屡次受到挫折而做的变通行为凸显出来,我们在汤因比身上看到的就是一个孔子,一个向鲁定公进谏未果而毅然周游列国、向齐景公进谏未被采纳而再次率弟子离开、秉持所谓“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顺应时势变化变通思想的孔子形象。
三、仁爱之道
“仁”的概念,早在西周时代即已存在,孔子将“仁”提升到哲学范畴,并进而发展成系统的仁爱学说。《学而》中说,“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然后做到“泛爱众”,就接近了孔子“仁”的标准,这个“仁”的核心就是“爱”。
孟子因袭孔子的仁爱观念,并在其基础上有了发展和进步,但孟子认为“爱有差等”,这自古以来一直受到部分学者的批评。汤因比晚年大力提倡用“爱”去解决人类面临的困难和危机,用“爱”为人类文明寻找正确的出路,而其早期著述中却未见到这种用“爱”解决问题的痕迹。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在孟子作品中或能找到一些思考的线索。《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有“以羊易牛”的故事,孟子认为这并不是吝惜财产、去小留大的行为,而是“仁”的行为。“在讲述‘以羊易牛’这件往事的过程中,孟子实际上关心的是‘易牛’,而不是‘以羊’,他所关注的是在‘易牛’这种举动当众所体现出来的仁心善性,而不是为什么要以羊来易牛。”①吴先伍:《“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儒家“仁”之论析》,《孔子研究》2016年第5期。孟子认为用羊来代替将死之牛“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上》)这其中“见”与“闻”对于孟子来说,是产生“仁”的直接原因,因为见到,所以不忍,因为听到,所以不忍,如班固在《白虎通·性情》中说,“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孔子东奔西走周游列国,本身就是对“见”与“闻”的实践,没有亲身体验的现实情境,任何道德观念都无法凭空而产生。也正因如此,吴先伍教授解释了孟子常被人诟病的“差等”之爱的道德根源:
孔子之所以强调要以孝悌作为仁之本,孟子之所以强调仁爱要从身边的亲人开始推扩,而不直接从一般的他者讲起,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自我与亲人在这种频繁的相见当中,名字对于彼此来说,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其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时时刻刻都烙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他们与我们之间真正是密切相关、一体相通的。亲人们所遭受的任何伤害都会让我们感同身受,都会在我们内心当中留下永恒的创伤,所以,我们才会自觉地承担起对亲人们的责任。②吴先伍:《“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儒家“仁”之论析》,《孔子研究》2016年第5期。
因此,孟子提倡“亲亲”,就是“见”“闻”这种物理过程引起的情感共通性的表现。对于齐宣王来说,“以羊易牛”的决定是因为“见牛未见羊”,“见”与“未见”就决定了“牛”与“羊”到底是一个觳觫而立的具体形象,还是一个抽象的名字,也就进一步决定了齐宣王内心和情感上不同的反应。
放到汤因比身上,他从前期未有提及,到后期将“仁爱”当作人类文明和“生物圈”的唯一出路,其原因也就此昭然若揭。汤因比从幼年到青年,学业和事业一帆风顺。即使在他开始创作《历史研究》之前已经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政府官员身份参与战争期间与战后事务,但那对年轻的汤因比来说,更多是享受事业与仕途的成功和成就感。然而,随着世界局势的不断变化,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以及汤因比前往受战争影响和破坏的国家和地区的亲身经历,使他在晚年和池田大作对话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我如今已85 岁,是少见的幸运者。……在这种幸运的状况中生活得越久,我就越悲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的人们的命运,他们是和我同时代的人,那时仅有二十来岁。更使我悲伤的是一个比我小三个月的至交,他已经死了。但死对他来说莫如说是幸福,因为在死前他的衰老越来越厉害,以致使他感觉到将终的命运,使他长期陷于痛苦不堪之中。③[英]汤因比:《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105页。
《论语·乡党》中说,“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是孔子尊重生命的“仁爱”表现,汤因比也正是如此。他亲历了战争的破坏和人们的死亡,唤起了他对生命的尊重,也激发了他“仁爱”的理想。或者说,正是“见闻”构建了汤因比的“仁爱”理想。在澳大利亚游历期间,他以白蚁为喻,表达了对所看到的战争的厌恶:
在过去一百万年里,这些社会性昆虫一直在等待着人类——这一在它们的古老领地上侵略成性又不讲规矩的暴发户——等着他们铸成大错,自行消亡……“到了下一次,”毫无疑问,白蚁们今天在自言自语道,“我们地球上的人类入侵者会自行覆灭。在生存了不到一百万年以后,这些善于发明创造的生物就已经发现了大规模自杀的办法。”唉,可怜的白蚁们,你们的分析预测忽略了关键的一点:如果人类果真在核战争中自我毁灭了,核战争也可能毁灭你们和你们的友邻,从热带鱼到形成珊瑚的微生物,再到浮游生物,统统都会覆灭。可能将会毁灭掉这个星球上的全部生命。因此,白蚁们,你们最好和尼赫鲁先生站在一起,全力以赴,相互妥协解决纷争,实现和平共处。①Toynbee,East to West:A Journey Round the World(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p.33—34.
当然,和白蚁的交谈侧面体现了汤因比“生物圈”的平等概念。汤因比不仅因为见到人类的灾难会产生共通的同情,见到其他生物也产生相同的情感。如果不解决这些贪婪短视的行为对整个生物圈造成的伤害,人类也将陷入自杀性的后果。张载《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②张载:《正蒙·乾称篇》,见《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页。人是天地所生,受天地之性,只有与天地合德,才不愧为人。思想在此与汤因比合拍之处在于,不仅老百姓是我们的同胞兄弟,连自然万物都是我们的朋友。汤因比认为,人类是能够善良的,人类的良心是对罪恶的反抗证明。惟有借助居间的“博爱”理想,把“博爱”理想变成现实,人们才会有“上帝如慈父”,才会有“人人如手足”。③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Abridgement of Volumes VII-X by D.C.Somervell,p.341.
结 语
中国的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互有你我,融合相通。从汤因比作品涉及的内容与态度来看,儒家与道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在伯仲之间,但如果把眼光放到汤因比人生最后20 年左右的时光,其思想有朝着儒家倾斜的明显倾向。或许是人生经历的丰满和对解决人类未来发展问题的方法进行探索之后的失望,他不断同现实妥协,逐渐将对世界物质力量的期望转移到“仁爱”的道路上来。
汤因比晚年认为,作为伴随人类生活的基本伦理问题,“爱”的问题在新时代亟需解决。人类在未来必须作为单一家族,走上共同生活的道路,而原子能被用作武器却使地理距离从战争角度被消灭。汤因比认为,从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向来看,技术的不断进步,是把人类引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因此人类避免集体自杀的途径,只有通过“爱”的道路,别无他法。与此同时,国家主义的狭隘性日趋明显,每个国家都在坚持自己的国家主权,家庭结构的规模也在不断缩小,传统的大家庭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变成了两代人的居住方式,子女对父辈、父辈对祖辈的抚养义务被逐渐抹杀。在这种情况下,汤因比说:“在家庭关系中强调义务的儒家主张,今天再合适不过了。”④[英]汤因比:《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