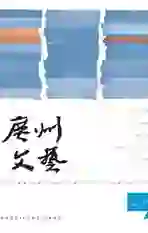个人的都市性
2020-03-03程旸
一般人研究王安忆创作时比较注意都市性的共同特点,例如上海建筑、弄堂社区和日常生活等,这是都市题材作家普遍具有的特点,却容易把她个人的都市性给忽略了。
王安忆之所以在四十年文坛独树一帜,我认为保持这种个人都市性是关键。可以说,没有它,就没有这位作家创作最鲜明的艺术风格。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个人都市性:一个是王安忆家庭出身和身份的影响;另一个由此形成的她创作的对上海的俯瞰性视角;最后通过与金宇澄简单比较,可以发现她身上的都市性与金宇澄是有明显区别的。
一、家庭出身对身份意识的影响
我写过《淮海路上的外省人——论王安忆的“军转二代”身份》①一文,明确指出王安忆不是典型的上海人,而是一个居住在淮海中路几十年的“外省人”。这种外省人意识、感觉和眼界,使她的小说跟大多数本地的上海作家很不一样。
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南京军区军队大院,父亲王啸平和母亲茹志娟是前线歌舞团的导演和演员,他们都是新四军老战士。王啸平祖籍福建,新加坡华侨子弟,1940年回国参加新四军。茹志娟是浙江绍兴人,抗战时随大哥投身革命。1956年,茹志娟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王安忆姐妹随迁上海,住进单位分配的淮海中路的宿舍,这是中上等社区的弄堂房子。后来,父亲转业到上海歌剧院任导演。
她父母的交往圈子,是上海的军队战友、文艺家群体,长篇小说《启蒙时代》中的军队子弟,应该多半是王安忆父母战友孩子的原型。中篇小说《好婆和李同志》中那个转业女干部李同志,也有母亲茹志娟的影子。由此来看,王安忆出身于军队大院,成年后在上海又与军队大院子弟来往。在她人生经历中,构成了一个“大院单位外省人”的一连串的节点。
在她1970年春下乡插队(十六岁)之前,家庭对她进行的是军/民关系模式的教育。父母担心王安忆会沾上“上海小姐”的骄逸奢侈,称这些都是“地方”的,用的是军人那种严格自守的做人标准。她回忆说:“我们的父母都是所谓的革命干部,他们给我们的生活全都是没有本土色彩的——革命干部的生活就是没有本土色彩的生活,家里面是说普通话的,所以我到很大才会说上海话。”①也就是说,即使在进城后,这种“军队/地方”的两重标准,依然在王安忆的人生教育中发挥着重要影响。由这双重标准所形成的家庭教育和影响,大概是她很长一个时期里,都与纯粹的上海市民保持着某种疏离感和距离感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也难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军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优越,即使在物质供应紧张年代,他们的生活标准和生活圈子,也明显高于附近周围的居民。当代著名作家有两个出身于军队大院,很多人注意王朔,不太注意王安忆,这是一个有待发掘的文学史边角材料。
由于家庭工资高,加上茹志娟②的稿费,王安忆从小说中就体现了生活优越。“这样的弄堂人称‘新式里弄,我们这一条又是‘新式里弄里的更新式,体现在‘蜡地钢窗,即打蜡地板和铁制窗架。我们家,来自军队粗放生活的上海新市民。”③她拥有很多玩具,包括有一般家庭没有的电动玩具,甚至十分稀罕的放映电影的幻灯机。“这台幻灯机使我们不仅在孩子里,也在大人中间,大出风头。我们常常在家中开映,电灯一关,人们立刻噤声,电影就开场了。这台幻灯机伴随了我们很多时间”,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寂寞的日子”④。她的散文随笔中,有在淮海路高档西餐店吃西餐的记述。小说《好婆和李同志》则写到了李同志家庭吃饭风格的粗放和浪费。
王安忆虽然住在弄堂,但基本不跟弄堂本地孩子玩。她上的也是一般家庭很难上的重点小学和中学。这种家庭及其交往圈子,实际把她与上海弄堂世界隔离了开来。她是隔着某些篱笆,來观望上海弄堂家庭、子女、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的。这是美学的篱笆,同样也是她人生的篱笆。这种身份造成了她的“外省人”意识和与上海本地人隔离感,同时也增加了她小说审美上的陌生化效果。具体来说,弄堂经验,一定意义上是王安忆小说创作的“地域性”之体现。这种地域性,因此成为了作家“上海文学书写”的前提。但是这种身份的两重性或说矛盾性,又与上海的“本地人”作家是明显不同的。对1990年代为什么会花如此大精力和笔墨去写这座城市,王安忆有自己的解释:“我最早想叫它为‘上海故事,这是个具有通俗意味的名称。取‘上海这两个字,是因为它是个真实的城市,是我拿来作背景的地名,但我其实赋予它抽象的广阔含义。”她之所以要选这个题材,是与自己这种独特的身世身份有直接关联的:“我能以什么词来概括这东西呢?我想到‘寻根二字,可‘寻根这词令人想起的也只是纵向的世界,虽然横向的世界其实于我们人生也具有‘根的意义。”⑤ 这就是说,她的取材不仅是出于一个作家的需要,更重要的也出于重审自己“人生”问题的需要。因为,除去南京的两年、淮北和徐州的八年之外,她大半辈子都是在上海这座现代大都市里度过的,这里有太多太多的记忆和感情,也有太多的茫然和思考。上海,毫无疑义正是她自己的“第二故乡”,这种深刻且深沉的“地域性”成为她创作中最重要的资源,应在意料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弄堂上、下层社会只是王安忆弄堂经验世界的外围和延展,她最熟悉的还是夹在中间的中产阶层。在解放前,这个阶层是医师、教授、会计主任、公司经理、工程师、烟叶商、成功的演员、建筑业包工头、股东等等;解放后,住在这种弄堂公寓里的,是国家干部、文艺界人士、医生、国企中上层管理人员,也包括王安忆父母这种“南下干部”等。对于他们这一类人群来说,他们最熟悉的自然是自己这个阶层的社会意识、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交往方式,经过长时期的沉淀发酵,形成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观察社会的特殊视角。而从这一阶层中走出去的作家,则将这种社会意识、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转换为栩栩如生的文学作品,从而创造出不朽的文学形象。作为中国现代都市题材小说的“传人”,王安忆的弄堂经验给了她源源不断的创作资源和灵感,也造就了这位优秀的作家。仅就王安忆的创作而言,我们认为她的“弄堂经验”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这种经验使她转型后的小说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都市题材发生了最密切的联系,决定了她创作的取材、视角和表现手法;二是弄堂经验经过审美提炼被沉淀为王安忆非常个人化的生活感觉和文学语言,这是她深入触摸和揭示上海弄堂人物的最直接的途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王安忆小说那种半方言半普通话的语言方式形成的过程和结果,正是这种深厚的弄堂经验之结晶;第三,在此基础上构成了她小说的叙述风格。王安忆个人的叙述风格可以概括为一种“弄堂讲述者”的讲故事风格。这是一种细腻、世俗、写实和充满生活实感的艺术风格。它有些唠叨、拐弯抹角,然而有体贴入微和世故老到。她通常喜欢用这种讲述来掌控人物命运,乃至作品的结构。虽然表面上她非常尊重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注意揣测时代的脉动规律,但我们分明看到,这种气场是一种贯穿其作品始终的支配性的力量。这是因为,王安忆的思想观念和小说理念中没有张爱玲那种“宿命论”,而是通篇充斥着雨果、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那种必然性的力量气质。因此,笔者发现王安忆对她笔下的“弄堂世界”在生活习俗方面是认同的,但是在思想意识方面则是保持距离和批判性的。这也可以说就是作家小说中始终保持的对于上海的俯瞰性视角的由来吧。
二、小说对上海的俯瞰性视角
长篇小说《长恨歌》一开篇就是对上海汪洋大海般的弄堂世界的俯瞰性全景描写:“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成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李欧梵很欣赏她对上海都市的描写,可能不知道这种俯瞰性视角不光是技术手段,还潜藏着她“军转二代”的优越意识。
这种俯瞰性视角除了“军转二代”的优越意识外,还与她的文学观念有关。她对刘金冬说:“我的写法是最传统的。你去看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还有托尔斯泰的东西”,都是“直接切入主题,我觉得小说就是那样子的”①。这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为人生的文学观念,“五四”新文学也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秉持着这种精神的王安忆对上海市民社会的态度,这就是用批判性的眼光表现他们的生活。
在《长恨歌》里,王琦瑶对于王安忆来说,就是一个随着历史而浮沉的花瓶、外室之类的小市民,虽然对她有同情。《我爱比尔》里那个因虚荣而堕落的女大学生比尔,是被作者嘲讽的对象。《好婆和李同志》中的李同志,对好婆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文革”轶事》对落难的资本家的女儿明显有同情,对从棚户区进入这个家庭的大嫂、女婿赵志国身上的市民习气,一点都不加掩饰的表现出鄙夷的态度,这类描写可谓是入木三分。短篇小说《小饭店》,像是把1990年代以后从广东、浙江、山东、四川和河南等地到上海的小生意人和打工者一网打尽了。它像是一部摄像机,把外来人口的里外生活拍摄得极其真实生动。你读这些小说,明显感觉作者与人物之间有距离感。这种距离感是批判的、讥讽的,作品虽然写了他们的生活,但并不认同。这与本地上海作家如程乃珊等有很大差异。
所以我说,俯瞰性视角只是小说技术,作者是要把自己摆到比市民社会更高的位置上。这种位置是批判性的、审视性的,或者是十九世纪文学那种批判精神。
不过,正像上海当代名作家陈村所指出的,王安忆即使对弄堂人生有批判,这种批判仍然是温情的、有余地的,不是一棒子打死的。她笔下很少出现绝对的坏人与好人。“她在日常的生活场景中找寻失落的美丽和意义。我想,她大概也是最后的小说家了,以后没人这样做小说了。”①陈村的评价恰好给我们一个提示:一方面应该注意王安忆与“弄堂阶层”的这种辩证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她虽与这个阶层有距离感,有批判性,却始终是有温情和分寸感的。我们不妨看看作家散文中的文字:这位小书摊老板的“眼囊还要臃肿一些,嘴唇也更厚,推着平头,一看就知道出自路边剃头挑子之手。他斤斤计较,决不允许你在书架上挑拣过久,要就租,要就不租,要想在挑拣时偷偷看完一本,没门!收摊的时间一到,他便飞快从人手中抽走小书,不管你看完还是没看完,想再看,要就借回家,要就明天再来。他清点小人书的样子,就像一个水果贩子在清点他的桃子或者梨。他有时甚至会为了一本借阅过久的小人书追到小孩子的课堂上。他的口音里带着鼻音,但他决不属于上海那些来自山东的南下干部,风范大异。说起来,和那开烟纸店的妇女也是小异,可不知道怎么的,他们就是一路的脸相,一种小私营者的脸相。”②这种距离感和温情,是一种对这位小书摊老板命运处境的“换位思考”,即使说他吝啬,也能处处照顾他经营人生的艰难。这就是王安忆。一个是在弄堂里生活过五十年的上海人;另一个是对这个地域既有爱也有恨的作家。“弄堂”是王安忆小说创作的“根据地”,同时也是她安身立命的地方。她的小说学,正是这环境的给予,但这是一种来自弄堂又高于弄堂的小说学。
但王安忆对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又很欣赏。这一方面是受到张爱玲及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她长期生活在弄堂社会、耳濡目染的见闻有关。这影响从她谈张爱玲、苏青的创作时反映了出来:“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种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为此,她用欣赏的口气评价道:“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她在接受刘金冬采访时,坦率说到了对张爱玲观察上海市民生活哲学的赞赏态度:“欲望是一种知识分子理论化的说法,其实世俗说法就是人还想过得好一点”,“就是一寸一寸地看。上海的市民看东西都是这样的,但是积极的,看一寸走一寸,结果也走得蛮远。”①这反映出王安忆与上海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某种非常矛盾的地方。而这种矛盾性,正是她个人都市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另一方面,王安忆对日常生活叙事的重视,是对中国传统小说的认祖归宗,是一个积极自觉的艺术尝试。在治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学者石昌渝看来,宋明文言小说的地位下降后,白话小说渐成创作的主流。白话小说来自民间“说话”,它是一种民间艺术,虽也会进入贵族士大夫圈子,但与下层民众的关系更为密切。由于是“说话”艺术,作者毫不掩饰自己的叙述者身份,所以“客观的叙述应当是小说叙事方式的上乘境界。中国古代长篇小说采用客观叙述的作品最上乘者是《红楼梦》”②。这就找到了王安忆日常生活叙事的历史渊源。可以说,经由张爱玲这個中介,她1990年代小说创作似乎回到了中国传统小说的长河之中。这种判断,是以她在复旦大学讲授的小说课内容为根据的。她说,写小说时,“我们只能用一些最最日常化的语言,而且我个人也觉得最好的小说应该用最日常化的语言。比如我说你应该吃饭了,那我无论如何都得用‘你应该吃饭了,而不能用别的语言去说”,“所以我们所用的材料——语言,是非常写实化的”③。这与石昌渝所谓小说是“说话”之艺术的看法比较接近。
让我们用一些具体的作品情节作例子来说明的话,《长恨歌》中老实忠厚的程先生追王琦瑶。好高骛远的她不马上拒绝,想给自己留个退路:“程先生是一个已知数,虽是微不足道的,总也是微不足道的安心,是无着无落里的一个倚靠。倚靠的是哪一部分命运,王琦瑶也不去细想,想也想不过来。但她可能这么以为,退上一万步,最后还有个程先生。万事无成,最后也还有个程先生。总之,程先生是个垫底的。”作者显然认可她这种上海人的务实。《妹头》肯定不是最出色的作品,但却是人物心理最丰富的作品之一。作品带着欣赏眼光描写上海女孩子的家居生活点滴。小学时代的妹头非常仰慕玲玲的二姐,二姐虽只是淮海路一家国营饮食店的新店员,但“她是娇小苗条的身材,穿一条花布长裙,系在白衬衫外面,腰上紧紧地箍一根白色的宽皮带。头发是电烫过的,在脑后扎两个小球球,额发高高地耸起,蓬松的一堆。肩上背一个皮包,带子收得短短的,包正到腰际。这是她这样刚出校门,又走进社会的女青年的典型装束,标明了受教育和经济自立的身份。”令妹头崇拜激动的是,玲玲二姐绷着一张粉白标致的脸,“目不斜视地走出了弄堂”。这位好奇的小姑娘不单密切观察她上下班的一举一动,还悄悄追到了玲玲家里,连二姐周末洗衣晾衣的情形,也未能逃过她的眼睛。她二姐姐先用丫叉把晾竿杈下来,擦拭干净。她用抹布也很讲究,叠成六叠,擦一面换一面,每根晾竿擦拭三遍,擦拭四根晾竿,正好面面俱到,准确得很。她把晾衣竿先搁在窗台上,另一头插在低处的篱笆缝里,等晾满一竿就送到高处,架牢,再用丫叉送上这一头。衣服的每一个部位都扯平整,卷起的口袋沿拉上去,窝着的衣领抻开来,袖管、裤管,更是绷了又绷。对裤子,不像大多数人那样,穿进一条腿,垂下一条腿,而是将垂下的裤管用衣夹夹在穿进的裤管上,这样就不会被过路行人的头顶蹭脏。妹头注意到,玲玲二姐穿出来的衣服都像熨过一样,实际是,她在晾衣时已经把折折缝缝都仔细扯平了。这样的例子,在王安忆1990年代以来上海都市题材小说中比比皆是。但王安忆毕竟是作家,有距离感的创作视角在其作品中是始终存在的。她认同张爱玲小说“世俗性”的东西,却在小说叙述中一直有意保留着讽喻性的意味。在张爱玲这里,如果说作者叙述的“距离感”是从人生“虚无感”中产生的;那么对王安忆来说,这种“距离感”则暗含着一种温和性的批判张力。用她的话说,自己是比较认同“古典作家”也即是十九世纪小说的,相信那才是自己的“整个教养”。所以,她肯定西方作家在表现日常生活时,采取的是“不苟同”的态度。他们作品中始终保持着一种超越性的力量,那是神的和艺术的东西。“我觉得西方作家有一种本能,就是说他是把自己和创作物分开的,比如詹姆斯·乔伊斯,你看他自己的生活非常惨的,很坎坷的,可他写的又是什么?都柏林,都柏林人,那样心怀仁慈、力求公正的批判,好像是他生活以及生活的焦虑是无关的,他没有把他生活当中这些东西往里填充。”“他们好像分得很清,我是我,你是你,他是他,我创作的东西和我的关系是脱离的,最终是脱离,那才是艺术的存在。”①这种看法是就能够解释王安忆所谓作家在处理“日常生活材料”与“小说独立性”之间关系时面临的难度。也可以解释,“军转二代”固然是一个小说家视角,但也仅仅是客观条件而已,而重要的是,“我创作的东西和我的关系是脱离,最终是脱离,那才是艺术的存在”,这一对王安忆来说最为关键的是小说家的态度。于是,读王安忆的小说,能时时感受到她对笔下世俗性的东西及人物状态有讽刺,但也是温和适度的,这可能是她与乔伊斯“心怀仁慈、力求公正”的情怀心有灵犀的缘故。进一步说,这也是她与张爱玲的区别,她相信“上海市民是很安分的”,他们“懂得生活的哲学,懂得美学”②。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她对上海市民的“距离感”中有暖意,在讽刺中有保留,是那种错落有致和充满了辩证关系的。进一步说,张静在《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一书中界定说:“身份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其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从事规则,还包括该权利、责任和忠诚存在的合法化理由。”社会中每一个成员,都是以自己的“身份”来思考和行动的。所以,“身份系统的基本功能,是对社会成员所处的位置和角色进行类别区分,通过赋予不同类型及角色以不同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在群体的公共生活中形成‘支配—服从的社会秩序”。根据该理论分析王安忆对日常生活认同与讽喻的矛盾态度,她在小说写作实践上,可能是无意的、下意识的或并非刻意的。但这正是这种无意识行为里深藏着的“逻辑结构”,支配了王安忆“军转二代”的叙述视角,支配了她小说创作的实践过程。
综上所述,“俯瞰”与“有保留”“距离感”与“欣赏”相互是矛盾的,但在王安忆小说里又是统一的。它们被奇怪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作家小说独特的叙述张力。在我看来,这是王安忆个人都市性,在小说创作上的独特表现。
三、与金宇澄的比较
要说王安忆个人的都市性,就得与金宇澄比较。可以说,金宇澄是最近四十年上海本地作家最成功的一个。也因为如此,拿他与王安忆来比较最有说服力。
我认为他们在三个方面有差异:一是出身和身份。王安忆是“军转二代”,金宇澄父亲是地下党,祖父是资本家,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二是文学观念。王安忆的小说观念是以十九世纪文学为底子,再加上点海派文学、西方现代派小说。金宇澄则直接是从海派文学那一脉过来的,完整继承从晚清通俗文学、《海上花列传》、苏州说书这一本地文学的传统特色。
在《繁花·跋》里,金宇澄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就是要用旧小说的话本形式来写现代上海。他以十分欣赏的语气说:“话本的样式,一条旧辙,今日之轮滑落进去,仍然顺达,新异。”而“我的初衷,是做一个位置极低的说书人,‘宁繁毋略,宁下毋高,取悦我的读者——旧时代每一位苏州说书先生,都极为注意听众反应,先生在臺上说,发现有人打呵欠,心不在焉,回到船舱,或小客栈菜油灯下,连夜要改。我老父亲说,这叫‘改书。”他自愿做一个“位置极低的说书人”,做“宁下毋高”的小说家①。这就与王安忆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观念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第三个方面,我认为两个人的差异,还表现在作家身份意识和语言风格上。对王安忆来说,第一,她作品的读者是知识精英阶层,即以大学生和城市知识青年为主体的读者群体。第二,王安忆创作的上海都市题材小说,虽有鲜明的地域性色彩,但使用的语言主要是普通话。这跟王安忆的“军转二代”和“外省二代”身份有一定的关系。第三,王安忆小说的“地域性”,是在1985年“寻根文学”思潮的刺激下形成的,这是一种“外来者”视角,而非清末海派小说和金宇澄小说那样具有鲜明的“本土性”。与此大概相反,一是金宇澄的读者是市民阶层,《繁花》初稿就挂在上海本地一个网站,虽然正式出版的版本做了很大修改,例如大量沪语被改成普通话,但读者仍然是面向这个阶层。二是我认为《繁花》受张爱玲的影响小,受晚清韩庆邦的《海上花列传》影响大,包括苏州评弹、苏白的影响非常大。你把这部小说改成评弹和苏白,把普通话改回沪语和苏州话,可能又是一部《海上花列传》。也因为如此,《繁花》刚出版时在上海很受欢迎,在北京一直受冷淡,直到出版社和作者北上宣传,获茅盾文学奖和其他奖才红遍全国。但我知道,大多数批评家从心底里还是不怎么喜欢它。原因就在,他们仍然把作品看作是海派小说,是身段很低的那种文学样式。并且,与王安忆小说的主体语言普通话不同,《繁花》初稿尽管删掉了很多上海方言,但它仍然是经过改造过的沪语小说。例如,“不欢喜”“软脚蟹”“晓得”“闷声不响”“瘪三”“客气啥”“不响”“十三点”“嘴巴清爽点”“掼石锁”“汏浴”和“捏了一记”等。另外,作品语言还吸收了许多旧小说“话本”“说书”的句式,例如,“徐老师已脱了眼镜,香气四溢,春皱桃玉睏衣,搨了唇膏,皮肤粉嫩,换了一副面孔”等。这种语言特色,凸显出作品的“本土化”色彩,形成与王安忆小说迥然有异的艺术效果。还有一点笔者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有别于王安忆的“外来者”视角,金宇澄小说显然是“本地人”的视角。这是因为,他虽在《上海文学》执编多年,与全国文坛的交往频繁,其创作状态却是封闭的,有一种典型的自我姿态。之所以形成这种封闭性,一是由于其创作处在业余的状态,自信心并不充足;同时,也与他更愿意师法于旧文学的心理有关。但这种与众不同的创作姿态,却塑造出金宇澄独具一格的小说风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王安忆来说,金宇澄小说是勘察她之“地域性”的一个有意思的参照。当然,这种参照系也包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的其他上海都市题材小说,例如陆星儿、陈村、孙甘露、王小鹰、陈丹燕、卫慧、路内和韩寒等作家的作品。在这个外部大格局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安忆“地域性”的独特地位。不过,就创作的实际成就和影响力而言,王安忆和金宇澄在这些作家中具有代表性。如果说,王安忆小说是一种“向外转”的地域性,那么,金宇澄小说的“向内转”倾向是更加显著的。从两人作品的传播渠道看,王安忆小说是面向全国读者的,这种因为她使用普通话的小说创作能为不同地域的读者所接受,而金宇澄这种沪语版话本小说,则阻碍了它与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北方地区的读者的交流。如果这样看,金宇澄更多继承的是上海本土版的海派小说余脉,是地地道道的上海本地人写的小说;王安忆尽管受到张爱玲和苏青的某些影响,但她的创作面向仍然是全国性的。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两位作家看待上海“地域性”的想法和角度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性,既与他们的人生经历有关系,也与文学观念有关系。总的来说,王安忆属于当代文学的主流性作家,她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与新时期文学潮流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而金宇澄则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历史有更多的渊源,尤其是清末民初盛行于上海的海派小说,具有天然的师承的关系。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地域小说”迥然不同的风貌,也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思想和艺术趋向。
我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研究王安忆个人的都市性,不应只看重上海建筑、弄堂和日常生活等外在形式,还应关注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作家,回到作者的内部来。具体地说,出身决定作家的意识,也决定了她怎看上海这个大都市的视角和眼光。最后,王安忆个人的都市性是有矛盾的,但正因为这种矛盾性,才是她都市性的最鲜明的特色。因为一个“外省二代”来上海这么多年,显然已经是上海人了,但骨子里又顽强保持着外省人的意识和观念,这在上海作家群中十分罕见。
因此在我看来,王安忆个人的都市性,是外省人怎样看上海的那种都市性。如果我们研究这位作家时,仅仅把都市的共同性强加在她身上,而不顾及她个人的都市性,就不能说真正进入王安忆的小说世界,也很难谈出真正的问题来。
① 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
① 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② 茹志娟上世纪五十年代因茅盾推荐的短篇小说《百合花》登上文坛,是那个年代一线的女作家。长期任《文艺月报》的编辑和上海作家协会的领导。
③ 王安忆:《空间在时间里流淌》,选自《空间在时间里流淌》,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④ 王安忆:《儿童玩具》,选自《王安忆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49—55页。
⑤ 王安忆:《纪实与虚构·跋》,选自《王安忆自选集之五·长篇小说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① 王安忆、刘金冬:《我是女性主义者吗?》,《钟山》2001年第5期。
① 见王安忆小说集《文工团》“封底”之陈村“推荐语”,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② 王安忆:《寻找上海》,选自《海上》,华东师大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这篇文章在王安忆多本散文随笔集里都出现过,这说明作家重复选用的情况,同时可以看到她对该文章的重视。
① 王安忆、刘金冬:《我是女性主义者吗?》,《钟山》2001年第5期。
②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8—27页。
③ 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① 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1、43页。
② 王安忆、刘金冬:《我是女性主义者吗?》,《钟山》2001年第5期。
① 金宇澄:《繁花·跋》,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责任编辑:朱亚南
作者简介
程旸,文学博士,青年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八届客座研究员,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