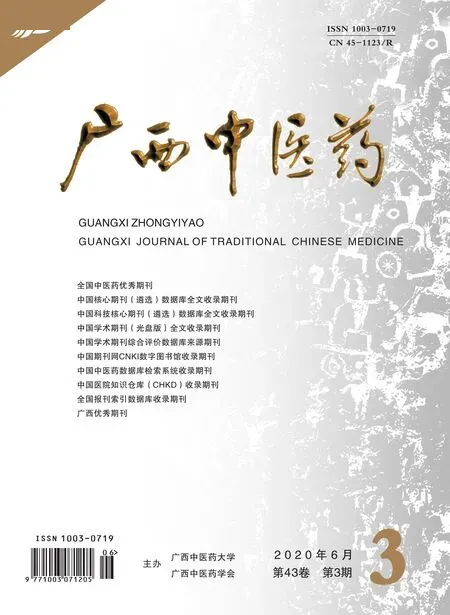针刺治疗术后肠梗阻的机制研究进展
2020-03-03李倩
李 倩
(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 410208)
术后肠梗阻(postoperative ileus,POI)是在腹部外科手术后常见的并发症[1],以恶心、呕吐、腹胀、腹部压痛、排气时间延长及肠鸣音异常为主要临床表现[2],其发病率可高达17%~20%,尤其在肠道手术后更常见[3]。术后肠梗阻通常持续2~4 d,有时甚至会长达7 d以上,部分患者会发展成长期肠梗[4],其治疗周期长,恢复慢,增加了患者和社会的医疗负担[5]。目前临床主要是在常规术后防治,在减轻胃肠负担的基础上避免肠梗阻的发生。近年来国内外的临床研究及动物试验研究均证明针刺对术后肠梗阻有确切的疗效,且无不良反应。本文对近十年来针刺治疗术后肠梗阻的机制研究的相关文献综述如下。
1 POI发病机制
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POI的发病机制主要有两大方面:神经机制及炎性机制。手术创伤可直接造成神经的损伤,同时也会造成传入神经的激活,从而引起肠肌肉收缩和肠蠕动受损,其后创伤及疼痛所导致的交感神经兴奋进一步抑制了胃肠蠕动[6]。此外,手术后自主神经移位引起的胃肠动力障碍可以通过激活脊柱中心而延续[7]。然而手术直接造成的神经创伤,并不是临床术后肠梗阻的主要原因,KALFF等[8]研究表明,术后12 h、24 h小肠肌肉功能下降,而白细胞数量随时间增加,与肌肉功能下降呈反相关。而炎性因子白介素-10(IL-10)的缺乏可降低术后中性粒细胞趋化因子的表达,从而减少了术后中性粒细胞外渗进入肠壁,最终保护小鼠免受POI的侵袭[9]。可见,神经机制及炎性机制共同作用导致了POI。
2 针刺治疗术后肠梗阻的机制
针刺治疗术后肠梗阻的疗效是肯定的,且未出现不良反应的报道[10]。针刺治疗术后肠梗阻的机制主要有2个方面:针刺促进小肠Cajal间质细胞(interstitial cells of Cajal,ICC)恢复及调节自主神经的作用。
2.1 促进肠道ICC细胞恢复 肠道ICC既可承接来自肠神经信号调节胃肠蠕动,又可节律性自发性去极化,产生电信号,并传导至平滑肌细胞,产生肠道慢蠕动波,ICC及其网络结构对于维持正常胃肠动力有着重要作用[11]。研究[12-13]表明,肠道手术会因为肠壁炎症反应,并破坏ICC的结构功能等,而针刺可以促进肠壁ICC数量、形态及网络结构的恢复,从而促进胃肠蠕动的恢复,ICC的恢复主要跟以下几方面有关。
2.1.1 调节组织中一氧化氮(NO)的含量 NO是主要的消化道抑制性神经递质,以扩散的方式进入平滑肌细胞,介导平滑肌舒张,减弱胃肠动力[14]。NO由L-精氨酸在一氧化氮合酶(NOS)催化下生成,而NOS包括3种同工酶:内皮型(eNOS)、神经型(nNOS)和诱导型(iNOS),前两种又称为结构型NOS(cNOS),主要存在于内皮细胞和神经细胞,cNOS活性只能维持几秒到几分钟,由它们催化生成的NO量较少,但具有广泛的生理功能;iNOS是在内毒素脂多糖(LPS)和/或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1(IL-1)、γ-干扰素(IFN-γ)等诱导下生成的,主要存在于心肌细胞、血管平滑肌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及炎症细胞中,一经诱导生成,在非调节状态下可持续数小时,诱导产生大量NO。NO作为气体性神经递质,无法贮存,所以NOS的含量是控制NO量的关键。邓晶晶等[15]研究发现,POI大鼠NO的含量较空白组显著增加,针刺后NO的含量较模型组明显下降,虽未能恢复至空白组水平,但提示针刺具有抑制术后NO增加的作用。POI模型组大鼠结肠iNOS的活性较空白组明显增强,cNOS活性反而有所下降;针刺干预后,针刺组iNOS的活性降低,cNOS的活性增加,从而调节结肠内NOS的总体活性,使之趋于正常;针刺组的c-kit阳性ICC较模型组增多,着色稍深,吸光度上升,与空白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肠道推进率较模型组明显升高,故针刺可以调节术后ICC修复环境中的NO含量和NOS活性,促进ICC修复,加快胃肠蠕动恢复。DENG等[16]发现,在POI模型中,eNOS mRNA水平下降,不利于ICC的存活,而针刺双侧足三针,可以逆转POI模型组c-kit和eNOS相关的mRNA水平降低,升高eNOS的含量及c-kit的含量,从而促进ICC的修复。
2.1.2 抑制肠道炎性因子 研究表明,肠道术后巨噬细胞和肥大细胞衍生的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会增强炎症,募集额外的循环白细胞,损害肌肉收缩性,减少神经递质的释放,甚至可以造成组织损伤[17],且白细胞数量随时间增加[8]。相应研究[18-19]发现,电针足三里可以抑制肠道手术引起的血浆炎症细胞因子TNF-α增加,并显著促进ICC网络和数量的恢复。此外,针刺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太冲穴可抑制巨噬细胞的活化和IL-6的释放,降低miR-19a表达,使得POI模型大鼠的c-kit表达增加,从而促进ICC的恢复。miR-19a是一种炎症相关miRNA,靶向c-kit蛋白,实验发现,巨噬细胞数量和IL-6表达与miR-19a表达呈正相关,但与kit及ICC呈负相关,IL-6可以触发信号传感器的激活和转录激活因子(STAT)-3,上调miR-19a表达式[20]。
2.1.3 调节一氧化碳(CO)平衡 CO是一种细胞信号分子,主要由血红素氧合酶(HO)催化血红素分解产生,在胃肠道中作为抑制性神经递质介导平滑肌的松弛效应。邓晶晶等[21]研究发现,结肠吻合术后3天,模型组大鼠结肠组织CO含量较正常组显著增高,之后随时间推移逐渐下降,术后10天恢复正常。针刺组术后3、5天的CO含量均低于模型组,其中术后5天已与正常组无明显差异。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小肠推进率在各时点均下降;与模型组比较,针刺组小肠推进率在各时点均增加,证明针刺可促进术后肠蠕动。与此同时,术后3天,针刺组的ICC形态较模型组好,c-kit较模型组多,模型组及针刺组ICC均随术后时间延长而恢复。研究证明,术后明显升高的CO对胃肠动力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与c-kit的含量也呈现反相关,而针刺可以抑制结肠组织中CO的含量,同时促进ICC恢复,提高小肠推进率。
2.2 调节自主神经
2.2.1 针刺增加NTS兴奋性,促进胃肠蠕动 NTS是髓质中接收躯体传入信号的主要中心,也是构成迷走神经反射的副交感神经中枢。FANG等[22]研究表明,术前抑制迷走神经系统,阻断胆碱能抗炎通路,并不影响EA对POI的调节作用。相反,阿托品在术后注射时能显著阻断EA对POI的调节作用。表明EA对POI的治疗作用依赖于术后EA对胃肠道NTS的促进作用。FANG等[23]进一步研究发现,电针足三里穴显著增加了正常大鼠NTS中兴奋神经元的数量和NTS神经元的峰值频率,接受腹部手术的大鼠,其NTS神经元兴奋性明显被抑制,峰值频率也降低。但与空白对照组和模型组相比,EA刺激在术后6 h显著上调NTS神经元兴奋性,并增加峰值频率。术后12 h~24 h,与模型组相比,EA显著刺激NTS神经元,增加了峰值频率,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
2.2.2 抑制迷走神经,兴奋交感神经 MURAKAMI
等[18]发现,与假电针组相比,电针足三里及内关穴能促进小肠运输和胃排空,改善了小肠慢波的规律性。实验中利用HRV的光谱分析对自主神经功能进行无创评估,发现模型组与对照组相比,其迷走神经活动受到抑制,交感神经比值增加,而电针足三里及内关穴可以阻止这一过程。
3 讨论与展望
肠梗阻在中医学属“肠结”范畴,中医学认为胃肠均属六腑,《素问·五藏别论》曰:“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六腑需保持畅通,以有利于饮食物的及时下传及糟粕的按时排泄。故曰:“六腑以通为用,以降为顺”,腹部手术易造成气机郁结、气滞血瘀,从而导致腑气不通,传化之物停滞,气机不畅则胀,腑气不通则痛,治疗上以通腑行气为主,但行气之力不能过猛。针刺对胃肠道的影响是一种良性、双相性调整作用,当适宜的针刺刺激作用于机体后,在通常情况下,特定的病理变化会朝着正常生理状态方向发展转化,对于胃肠功能紊乱性疾病有其独到疗效[24-25]。腹部术后胃肠功能障碍的肠道ICC细胞都有不同程度受损,而ICC细胞在胃肠道自主慢波节律电位产生、慢波电位传导和神经递质调节中充当着重要角色,但其机理复杂,靶位众多,而以单一靶点作用方式的化学药物则很难达到治疗效果。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针刺可以通过多途径促进ICC细胞的恢复,加快术后胃肠功能的恢复;此外,还可以调节自主神经系统,加强胃肠道的蠕动,是一种安全无创且经济的治疗方法。
现阶段,对于针刺治疗POI的机制研究可为临床治疗提供更明确的依据,但仍有许多问题:①目前的实验研究多集中于某些炎症因子或神经递质,对于神经通路方面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小的靶向点,缺少整体连贯性的认识;②机制研究主要以动物实验为主,缺少典型病例的研究;③各个研究取穴、刺激方式、刺激量尚未统一,没有临床应用的标准。未来应更多注重提升临床试验的质量,将经过验证和标准化的治疗结果应用于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