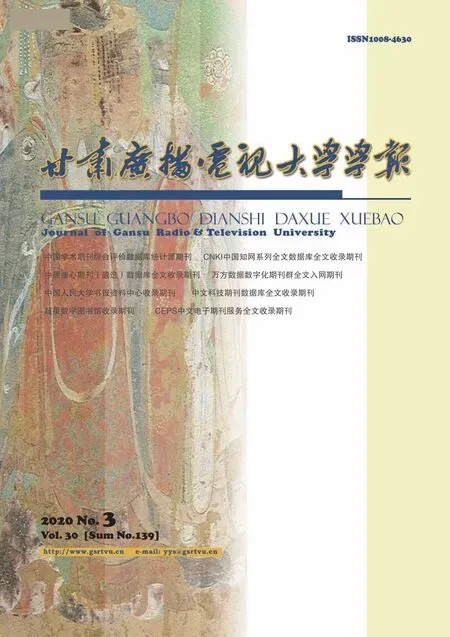从《西游记》看猴行者形象的变异
2020-03-03王腾腾
王腾腾
(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24)
中国古代神魔小说的代表作,明代章回小说《西游记》塑造了一系列不朽的艺术形象,其中以“孙行者”的形象最为瞩目。关于“孙行者”形象的渊源,学界长期存在争议,“外来说”①、“本土说”②和“混同说”③相持不下,至今没有定论。这一完全虚构的天生石猴到底从何而来?大批学者试图从文学世界、现实世界以及不同历史阶段“孙行者”形象的演化等角度追寻这一虚构形象的原型,并由此进一步探究作者的创作意图及作品主旨。因此,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在吴本④《西游记》中看到的神通广大、善良果敢的“孙行者”应当是作者运用“杂取种种,合成一个”⑤的方法生成的全新艺术形象。从现有传世文献来看,“孙行者”的原型最早可追溯到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下简称《取经诗话》)。关于这本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身份历来是争议的焦点,考证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对于解读这部作品意义非凡。尽管这一问题当前学界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形象正是吴本《西游记》中“孙行者”的雏形。
下文基于孙悟空这一人物在两个文本中的出场方式、身世和姓名的不同书写,寻求二者之间的差异与内在联系,基于文本塑造的人物神力和性格,观照人物内在能力和性格变化,进一步了解孙悟空形象的前世今生,解读从“猴行者”到“孙行者”这一人物形象变异的深层原因。
一、“猴行者”与“孙行者”的出世
(一)“猴行者”与“孙行者”的出场
人物出场的描写是文学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取经诗话》共十七节,第一节和第八节⑥已轶,现存十五节。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等记载推测,第一节很有可能是记叙取经缘起及玄奘奉敕等事。第二节行程遇猴行者,“猴行者”以不期而遇的方式出现在读者的视野当中:
行经一国已来,偶于一日午时,见一白衣秀才从正东而来,便揖和尚:“万福,万福!和尚今往何处?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经否?”[1]3
一个来路不明的“白衣秀才”突然出现在法师一行六人面前,也闯入读者的视野。文本中对他来历的交代仅有两个字“正东”,而法师正是从东土大唐而来,此处“正东”也许暗合二人“志同道合”之意。这位白衣秀才的突然加入留给我们很多疑问。首先,他上来报明身份“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但姓甚名谁并不明了。其次,他第一次发问:“和尚今往何处?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经否?”“再”字清楚地提醒书中人和读者,他是一个洞悉今古、参透世事的存在。随后,他清晰地表明来意:“我今来助和尚取经。此去百万程途,经过三十六国,多有祸难之处。”虽然文中有交代他因偷盗蟠桃被罚的经历,但并未说明这与他护送法师西天取经有何关系。由此来看,他帮助法师取经是一种主动自愿的行为,而预知前世今生的神力使他轻松获得了法师的信任和欢迎,当即改称他“猴行者”。“行者”在佛教语中指出家而没有剃度的佛教徒,这与《西游记》中“孙行者”的名讳和身份是前后一致的。
《取经诗话》中“白衣秀才”的出场其实有很多未解之处:他自称来自“花果山紫云洞”,但此山此洞位于何方?是否远在东土?作者并未交代;他自称“铜头铁额猕猴王”,但他此时现身却是“白衣秀才”,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如何解释?作品亦未作说明。
上述问题,在《西游记》中则有说明和交代。在《西游记》第一回“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中,“孙行者”第一次以一块“石卵—石猴”的形态亮相。
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胎,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2]2
这是一块混沌未分、鸿蒙未破之时就已经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仙石。石猴则是受“天真地秀”孕化而成的仙胎,它的出生地正是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这与《取经诗话》中猴行者自称来自“正东”的出身也相一致。这石猴从出生之时起便注定非同凡响,他很快学爬学走,拜了天地四方。“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如此华丽不凡的出场连天上众仙乃至玉帝都惊动了。他由天地精华孕育的“仙胎”化育而成,这样他此后展示的各种超现实能力就有了令人信服的根砥。
(二)“猴行者”与“孙行者”的身世、姓名
无论是“猴行者”还是“孙行者”,他们的身世始终是一个谜团。一个是从正东而来的“白衣秀才”,一个是天地精华所孕育的“石猴”,没有人知道他们从何时存在、姓甚名谁、父母兄弟如何。
《取经诗话》中,白衣秀才这样自报家门:“我不是别人,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1]3他自称曾目睹法师前世两回取经,可见他与法师前世已结下因缘。前面两回取经他是否曾相助护送?取经大业与他有何干系?作者全都没有交代,只说“我今来助和尚取经”,单从文本来看这是一个专为护送法师西去灵山而存在的人物。当即法师唤他“猴行者”,这一名称自此出现。严格来说,这并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名字,“猴”和“行者”都是他身份的表征,仍然不能解答他从何而来的问题。
对《取经诗话》中这些语焉不详、令人疑窦丛生之处,吴本《西游记》都逐一做了解释、说明及描述。《西游记》第一回到第七回属于一个独立的故事体系,讲述猴王从横空出世到拜师学艺、大闹天宫以及最后被如来佛祖镇压在五指山下的英雄故事。第一回清楚地交代了石猴的出生地。
这部书单表东胜神洲海外有一国,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那山顶上有一块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二丈四尺围圆按政历二十四气;上有九窍八孔,按九宫八卦。[2]1
这一段交代了“孙行者”的祖籍:东胜神洲海外傲来国花果山。这座山是“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孕育猴王的石头在天地未开之时已经存在,汇聚了天地精华。随后石猴出世之后一系列不凡的表现迅速让他从猴群中脱颖而出,成为猴王。此后在求仙访道之时拜菩提老祖为师,获得名姓。据菩提祖师所言:
你身躯虽是鄙陋,却像个食松果的猢狲。我与你就身上取了姓氏。意思教你姓猢,“猢”字去了兽傍,乃是个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阴也,老阴不能化育。教你姓狲,“狲”字去了兽傍,乃是个子系,子者男儿也,系者婴细也,正合婴儿之本论。教你姓孙罢。[2]5
把“狲”字去兽傍,乃为人之“孙”姓。此时的石猴尚未入俗世,但已脱离兽性,具有人性,犹如初生的婴孩。孙悟空的姓氏择选绝不是随口而得,作者借菩提祖师之口为孙悟空择选姓氏是对孙悟空精神人格的设定,“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3],道家推崇的至高人格即是婴孩。婴儿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同时代表了一种与道同在、心无瑕疵、尚未被世俗名利沾染的本真状态。而“空”字在佛道两家则有不同的内涵。在道家话语体系中,“空”与“有”相对,共同构成宇宙的一部分。佛家讲究四大皆空,“空”则被推至万物之本质的至高地位。“悟空”之名以“悟”字当头,悟得人世虚空,契合佛教对于宇宙万物的体认。从婴孩而始,以“空”字而终,即是得道成佛,孙悟空姓名的确定侧面影射出这一时期佛道文化的深度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在《取经诗话》中“猴行者”以白衣秀才的形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但法师却称呼他为“猴行者”,直接以“猴”字冠于他的“行者”身份之前,“猴”字应当不是姓氏。这里他以“白衣秀才”的形象示人,法师却以“猴”作为他形象的表征。文中他并未以猴形象示人,却被冠以这个名字,其中原因值得推究。联系文本可以发现,直接原因是他介绍自己是猕猴,间接原因就是《取经诗话》文字粗糙、前后照应不周,很有可能仅仅是说话人使用的底本,因而只是一个粗略的故事梗概,为说书人留下了极大的补充细节、延展故事的发挥空间。而在《西游记》中菩提祖师为石猴取了“孙”姓和“悟空”之名。“孙行者”虽以猴的形象示人,但却拥有了人的姓氏和名字。菩提祖师为他取名“悟空”,隐含顿悟虚空之意。显然,“猴行者”与“孙行者”之间呈现出奇妙的关联,“猴行者”是从“人”到“猴”的呈现结果,提示出白衣秀才奇特怪异的出身;“孙行者”则是从“猴”到“人”的演进,强调的是出身神异的石猴的人格化进程。但不管怎么说,“孙悟空”这个名字是高度人格化的,其中的佛教含义和道教含义是“猴行者”中完全不具有的。“猴行者”仅仅提示了身份特点,而“孙悟空”则隐含了深刻的文化含义,作者藉由对其姓名的设定,完成了对这一艺术形象精神和人格特点的最初建构。
二、“猴行者”与“孙行者”的性格
《取经诗话》受文体所限,故事情节相对简单、人物单薄,前后联系较弱,与伏脉千里、前后钩连、情节跌宕的百回本《西游记》的文学价值难以相提并论,但其作为《西游记》的雏形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其中从“猴行者”到“孙行者”的人物性格变异值得关注。
(一)猴行者:神力弱化,谨慎胆小
《取经诗话》的第二节“行程遇猴行者”中,猴行者先谈起法师前世之事:“和尚生前两回去取经,中路遭难,此回若去,千死万死。”[1]3他凭借这种知晓过去的能力迅速取得法师的信任,随后言明“此去百万程途,经过三十六国,多有祸难之处”[1]3,更突出自己加入取经队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事实也是如此,他这种预知未来的能力让他在取经路上充当起向导的角色。在《取经诗话》中共有四处出现“猴行者”为法师指明前路的情况,分别是:第四节入香山寺,猴行者曰:“我师前去地名蛇子国。”[1]10第五节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猴行者启:“我师前去即是狮子林。”“我师前去又是树人国。”[1]13第十一节入王母池之处,猴行者曰:“我师且行,前去五十里地,乃是西王母池。”[1]31每行经一处,猴行者都能提前告知法师所到之处的信息,这种知过去、晓未来的本领帮助了没有法力的法师能够通往灵山。此外,这里的白衣秀士的法术基本上停留在空间位移和通晓过去、未来的层面上,实际上帮助应对妖魔的是大梵天王及其赐予的隐形帽、金环锡杖等一系列法器。《取经诗话》中的一些幻术的使用,比如在入九龙池处与九条馗头鼍龙斗法,将隐形帽化作遮天阵,用钵盂盛万里之水,将金镮锡杖化作一条铁龙,此类斗法幻术在《西游记》中已十分常见。
另外,与吴本《西游记》中的孙行者相比,《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不仅神力有限,性格上也表现出与孙行者迥然相异的一面。最典型的体现在入王母池一节,猴行者自述他在二万七千年前偷吃蟠桃的经历,“我因八百岁时偷吃十颗,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铁棒,配在花果山紫云洞”[1]31。因为此番偷盗事件,他被发配到花果山紫云洞,这段经历令他心有余悸,“至今犹怕”。而在吴本《西游记》中“孙行者”因为大闹蟠桃会而引发众仙围剿,最终被压到五行山下,等待取经人的搭救。如此大胆敢为,自由恣意的石猴与“至今犹怕”的猴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了“猴行者”性格中谨慎胆小、敬畏神佛的一面。《西游记》中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浓墨重彩的铺陈描写,以及取经过程中孙悟空不止一次地在自我介绍时对自己当年大闹天宫的经历津津乐道,自矜自夸,这些都彻底颠覆和重塑了《取经诗话》中猴行者的形象。
(二)孙行者:神通广大,勇敢桀骜
吴本《西游记》中的“孙行者”生来不凡。年少时曾师从菩提祖师,后大闹天宫被如来佛祖镇压在五指山下等取经人搭救,随后顺利拜唐僧为师,法号行者,自此开启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行程。他一路降妖除魔,成为取经团队中最关键的人物。
孙行者性格刚烈,神通广大,斩妖除魔、开山辟路大多是他的任务。这一角色延续了《取经诗话》中猴行者取经路上领路人的角色。不同的是,孙行者师从菩提祖师,拥有了通天的本领,师从唐三藏,一心一意护他西天取经。在《取经诗话》中,猴行者的形象更多地像一个宗教使徒。猴行者参与取经,是主动行为;而《西游记》中,“孙行者”拜师西行是大闹天宫后的惩罚,也是对唐三藏搭救之恩的报答。同时,从石猴出世到拜师学艺、大闹天宫、西天取经,作者草灰蛇线、前勾后连,将人物性格、深层心理变化写得丰富饱满。
猴性、人性、佛性同时在孙行者身上得到了统一。他尖嘴猴腮的外貌保留了猴子这一动物的基本特点,拜师学艺时稍有成绩,便在师兄弟面前卖弄,展露出一副顽劣的猢狲相;他拥有明察秋毫的火眼金睛,习惯了辨察、判断、决绝,却对过程和人的情感漠不关心,在三打白骨精时,难免显露出桀骜不驯的一面;他向往自由,随性洒脱,却带上紧箍,一心一意护送三藏西行。这一形象身上既有猴的兽性和妖性,也有人的品格和性情,同时还有神的法术和能力。
细读全文,不难看出《西游记》的作者对“孙行者”这一角色的偏爱。他大大丰富了《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的形象,赋予了孙行者传奇般的经历和通天神力。其“乃天地精华所生”[2]2,童年时期从猴群中脱颖而出,成为群猴之首;后拜师学艺,更是天赋聪颖,学有所成。后来大闹天宫、拜师西行,走上了通往灵山的取经之路,并最终完成取经大业,成为“斗战胜佛”。《西游记》的作者不惜笔墨地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本领通天、自由活泼、具有反叛精神的“孙行者”形象。
三、“行者”形象演进的原因
从《取经诗话》中谨慎敬神的“猴行者”,到《西游记》中神通广大的“孙行者”,不难看出,在取经故事的演进过程中“行者”的形象及性格都有了质的变化。这种演变的动因是什么?笔者根据作品的产生时代、传播特点、作者动机等因素,将其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西游故事从文本而言出自说经话本,从题材而言出自玄奘取经的佛教史实,与佛教的关系极为密切。
《取经诗话》的成书时间历来是学界争议的焦点之一。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以李时人、蔡镜浩为代表,他们对作品的体制形式、思想内容和语言现象等方面进行考辨之后推断,《取经诗话》的成书时间不晚于晚唐、五代[4]。另一种是依据诗话的体制推断该书写作于宋元之际。“经过10世纪初至14世纪的五代和宋元二代,禅宗占据中国佛教主流地位。”此外,杨曾文谈到,“禅宗最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最善于吸收佛教各宗思想和其他文化成份丰富自己,倡导在人间修行,在人间觉悟,最接近现实社会民众的生活”[5]。可见,无论是晚唐、五代还是宋元,禅宗思想在这一时期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它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使得这一时期佛教为了拉近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开始从庄严神圣的佛门走入市井百姓之中,呈现出世俗化、生活化的趋势。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取经诗话》中谨慎敬神、神力弱化的“白衣秀才”已经呈现出更加人性化的一面。
吴承恩历经五朝,其中嘉靖时期官方组织了祈神等一系列以救灾为目的的道教活动,客观上提升了道教的地位,虽然政策上呈现出明显地对道教的偏向,但仍是佛道兼奉。与此同时,王阳明心学和狂禅之风对程朱理学的僵化模式提出了挑战,对个性和人的七情六欲给予了充分肯定。此后士人不断发展这一观点,反对盲目迷信神佛,宣扬以个体为中心的价值观,反映出晚明士人宗教观念的转变。在《西游记》中,一方面唐三藏一行人的终极目标是求取真经来拯救众生,另一方面取经路上却屡屡有佛祖、菩萨的手下出来作恶,可见佛教世界并非净土。作品中交织的崇佛抑佛思想,展现出吴承恩在官方政策和士人宗教观念的影响下对佛教的矛盾态度。
(二)作者身份、写作时代不同
作者的身份决定了作者为谁说话。有关《取经诗话》作者的身份,学界也未能达成共识。一种观点基于文中用到的佛教用语及典籍推断作者应当精通一些佛典及佛理知识,《取经诗话》应当是当时寺院僧人“俗讲”的底本[6]。另一种观点认为作者应为市井说书人,《取经诗话》中的法师的一些不合身份的行为,是说书人在面对听众说书时为追求书场热闹效果而做的改动[7]。基于《取经诗话》中塑造的鼓动偷盗、屡屡破戒的唐三藏形象与佛门精神相悖,因而从文本角度考虑,笔者更加认同后者的观点,并由此推断,从天而降的“猴行者”形象的塑造,更多是作者追求故事的合理化与趣味性的结果。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并非佛教、道教信徒,年少时期屡试不第,科场失意,一生壮志未酬。儒生出身的他借助手中健笔诉尽胸中不平之意,“孙行者”身上集中体现了吴承恩崇佛抑佛的矛盾思想。在《西游记》的取经故事中,终极目标虽然仍是求取真经,但取经核心人物已经从唐三藏转移到了“孙行者”。孙行者从天生石猴到最后取得真经,被封为斗战胜佛的身份转变体现出作者的弘佛思想。但孙行者的性格中又突出了对自由的追求、反叛的精神,可见吴承恩对佛教的矛盾态度。此外,从故事设定和人物塑造不难看出作者对这一角色的偏爱,可以说,“孙行者”这一形象身上强烈的自我意识、过人的胆识能力、至纯至真的心性以及动人的反叛精神,寄托了作者对于美好人格的追求。但这种设定不像《取经诗话》中单调、模式化的人物,对于这个天生石猴身上顽劣自大的一面作者也毫无遮掩,由此,一个集动物性、人性、神性于一身的“孙行者”便跃然纸上了。
(三)面向的读者不同
《取经诗话》简单朴拙,故事性不强,情节上粗陈大概、缺少铺垫,人物缺乏细节刻画,其文学价值与吴本《西游记》不可同日而语。此外,这部作品追求娱乐化和宣扬佛教的双重目的,使得它在趣味性和宗教性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有时平衡失当,难免顾此失彼。前面提到,《取经诗话》的作者很有可能是市井说书人,由此推测,《取经诗化》只是一个“底本”,即很有可能并非是供读者阅读的写定本,而是一个供说书人使用的故事梗概,缺乏细节描写。所以《取经诗话》的体制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面面俱到,这也留给说书场上的职业说书人很大的发挥空间。
吴本《西游记》写作于元末明初,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极大地壮大了市民阶层,文人士子和商人之间的交往增多,形成了一批世俗化的文人群体。这一时期,文人市民化和市民化读者群体的出现推动了文学创作者和作品的转型。读者表达自己思想和生活的需求对说书人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客观上推动了一批说书人和进步文人向创作者转型,出现了“作家”这一职业。小说在明代呈现空前繁荣,《西游记》正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令人瞩目的优秀作品。多样的读者需求要求作家在创作中增强作品的故事性和趣味性,由此,一个形象鲜活饱满的“孙行者”便出现了。
四、结语
《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是吴本《西游记》中“孙行者”形象的发轫和雏形。无论是来去无根的白衣秀才,还是生来就未曾感知过母体温暖的天生石猴,他们生来就是不凡的。这种“不凡”既带有民间传说的影子,也抹不去深刻的时代烙印。从“白衣秀才”到“天生石猴”,完成了从《取经诗话》中标签式、类型化的“猴行者”形象到立体丰满的“孙行者”形象的转变,同时也折射出西游故事从民间叙事到文人叙事的嬗变。
注释:
①参阅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的观点,他认为孙悟空的原型很可能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神猴。此外季羡林、陈绍群、连光文等人也都支持此观点。
②参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的观点,他认为《西游记》的孙悟空形象可能受到了唐传奇《古岳渎经》中的无支祁水怪的影响。
③参阅萧兵《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对“混同说”的论述,他认为孙悟空的构成既是多元的,又是统一的。
④《西游记》的作者尚有争议,本文采纳吴承恩一说。
⑤参阅鲁迅在《〈出关〉的“关”》一文中的观点。
⑥“节”之名称乃沿用王国维之说,出自《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附录一中的《王国维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