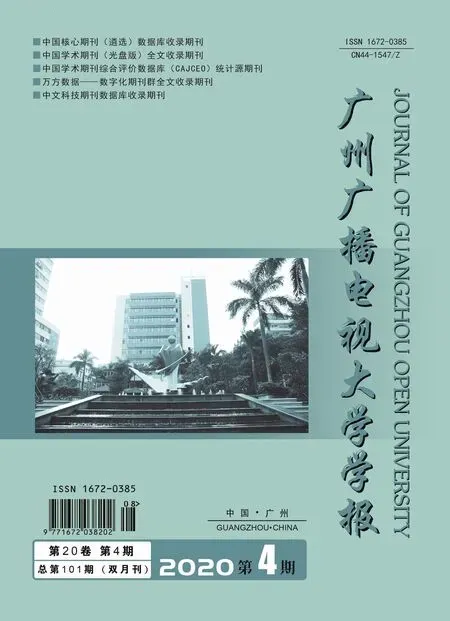论《聊斋志异》中的幻术故事类型、特点及成因
2020-03-02王家曼
王家曼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1119)
引言
幻术孕育于中国先秦时期,随着西域幻术的传入而兴盛于汉代。幻术,也称幻戏、魔术、幻技,隶属于“百戏”艺术,是一种综合性的民间艺术。许慎《说文解字》:“幻,相诈惑也”。幻,有迷惑、欺骗的意思。许慎《说文解字》:“术,邑中道也”,段玉裁注:“邑,国也,引申为技术”。[1]综上,幻术就是带有迷惑意味的技术。幻术故事是我国古代文人笔记、小说的创作题材,中古志怪小说如干宝《搜神记》、葛洪《神仙传》中已经大量收录此类故事。本文即以《聊斋志异》中的幻术故事为切入点,对《聊斋志异》幻术故事的表现手法和其幻术故事的特点、成因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出蒲松龄幻术故事的魅力所在。
近年来,在《聊斋志异》幻术故事的研究方面,王青教授做了很大的贡献,其《古典小说与幻术》中对《聊斋志异》中《偷桃》与《种梨》两篇幻术的表演方式和其表演与西域幻术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解析。此外,王燮山、赵兴勤对于“偷桃”故事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流变进行了探讨。刘卫英对《聊斋志异》中《鼠戏》《蛙曲》中“禽戏”的表演方式和技艺渊源方面有所研究。在艺术特点方面,周先慎对《种梨》篇中的叙事手法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寓讽刺于叙事之中的特点。孙巍巍则着重分析了《巩仙》篇中的道士形象和其“袖里乾坤”的理想仙境。
总之,学界目前对《聊斋志异》中幻术故事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并且主要集中在《偷桃》《种梨》两篇,研究的重点在于幻术表演方式的解密,对于书中其他幻术略有涉及,但缺乏对蒲松龄幻术故事以及其笔下幻术世界的系统性研究。此外,对于幻术故事题材与蒲松龄本人的人生态度和艺术倾向的关系亦缺乏探讨,这不利于我们全面把握蒲松龄的幻术故事创作,因此本文即以上述问题为重点进行解读。
一、《聊斋志异》中所见幻术类型
《聊斋志异》中幻术故事类型多样,大致可以分为种植幻术、搬运术、傀儡术、隐身术、易形术、缘物上天术、禽戏、投符念咒术等,现择要进行论述。
(一)种植幻术
所谓种植幻术是使得植物迅速生长的幻术。这种种植速生的幻术由来已久,是幻术的一种主要形式。《聊斋志异》中的种植幻术主要出现在《种梨》《济南道人》两篇中。《种梨》篇中写道士向卖梨乡人乞梨不得,于是取梨核,用镵挖了一个数寸深的洞,将梨核种下,并用沸水浇灌,万众瞩目之下,梨树即刻结果,道士分食众人。道士走后,卖家回头看自己的车,梨子已经没有了,又从墙角找到了自己车上的断靶,才明白梨树实际上是车靶幻化而成的。这种幻术表演实际上是“高彩”技巧的运用,指将展示道具压缩在非常狭小的空壳内,表演之时将其扯开,就可由小变大,由低变高。[2]此外,《济南道人》中亦称有道人于寒冬种荷满塘,这种能颠倒生物、种果速生的技艺实际上也是一种幻术。
(二)搬运术
搬运术则是指将物体在空间上进行位移的幻术,《聊斋志异》中记载戏人可以用中空无底的大桶取米,利津李见田能将六十余瓮凭空搬运到距离陶厂三里外的魁星楼。此外,《聊斋志异》中还记载了以壶取酒的幻术,《济南道人》中,道人可“以壶入袖中,少刻出,遍斟座上”[3]。《真生》篇中所展示的幻术则更加神奇,真生可以使用无底玉壶重复取酒。除了取酒之外,道人的袖中还能取物,《单道士》:“单(道士)亦至……袖中出旨酒一盛,又探得肴一簋,并陈几上。陈已,复探;凡十余探,案上已满。”[4]《济南道人》中也记载了道人在墙壁上绘“双扉”,然后从中取酒取肉的故事。
(三)傀儡术
《聊斋志异》的幻术故事中往往会由道士幻化出各类美人,如《巩仙》中记载道士从袖中出美人,扮《瑶池宴》,《劳山道士》中以箸幻化出嫦娥,最初不过尺长,后来逐渐等身,作霓裳舞。这种故事听来荒诞不经,但这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傀儡戏”。《聊斋志异·木雕美人》中就详细描述了这种幻术,美人“高尺余,手自转动,艳妆如生。又以小锦鞯被犬身,便令跨坐。安置已,叱犬疾奔。美人自起,学解马作诸剧,镫而腹藏,腰而尾赘,跪拜起立,灵变不讹”[5]。傀儡戏是指用木偶进行表演的杂戏。“高尺余”说明这种木雕的体量很小,手腕灵活,制作精巧;傀儡从狗腹翻转到腰部再滑落到狗尾,“蹬”“赘”“跪拜”“起立”等动作,潇洒流畅,说明当时的傀儡戏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而《木雕美人》强调“美人自起”,但这种幻术实际是利用障眼法将牵引物隐藏起来,而使“美人”栩栩如生。
(四)隐身术
“隐身术”,又称“隐遁术”, 是幻术的基本技法之一。《聊斋志异》中就记载了不少此类幻术。如《单道士》篇中记载单道士“画门隐遁”。另,《巩仙》中记载了一种“假死隐遁”的幻术,巩仙已死,鲁王准备棺木葬之,而后有行人在途中遇之,鲁王挖开坟墓。只剩空棺。《搜神记》中也有此类“遁术”的记载,徐光被人斩首却无血,其人后又碰到徐光对他招手微笑,这说明巩仙和徐光未死,只不过掌握了隐身幻术。此外,移形术也是隐身术的一种,移形即移步换形,《劳山道士》中记载原本席位上的三人进入用纸变幻而成的月亮,众人还能看到三人坐在月中饮酒,就如同影子出现在镜子里一般。
(五)易形术
易形术在《聊斋志异》中也常常出现。如《番僧》中记载僧人可以伸缩胳膊至六七尺长。《巩仙》中的道人则可将身体变为铁质,“弹其额”,有铁釜声;“刺以针”,针不能入;“推之”,不动;“十余人举掷床下”,仿佛千斤石头坠在地上。另,《偷桃》篇记载了一种肢解复原术,它是易形术的一个变种,表演时,先肢解身体,随后复原。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幻术可能是用动物肢体代替人的肢体,并与移形术结合而成。[6]此外,易形术不仅可以变幻人之形体,有时也能变幻物的形状,如《劳山道士》中的“剪纸成月”,《颠道人》中的“黄盖化蛇”,《真生》中的“点石成金”。《红毛毡》中更是记载了一种能将一块毡布变幻到一亩多大的幻术,毡布上面可以容纳数百人。
(六)缘物上天术
《聊斋志异》中的缘物上天术主要有两种,一是《偷桃》中的“缘绳上天”,其可以拆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掷绳直立,术人将数十丈的绳子引一端向空中投掷,绳子悬在空中,愈掷愈高,进入云中。然后是攀绳上天术人手持绳索,盘旋而上,渐入云层。实际上,在表演中,这种幻术使用的是一种带有钩子的特殊绳子,表演前将某种细线固定在某一高点,抛绳之时将绳子挂在事先准备好的细绳上,然后利用现场的光影效果创造视觉盲点,使得攀绳之人在众人眼前消失,达到“幻”的效果。[7]另一种是“踏肩之戏”,《郭秀才》篇中记载十余人攀肩踏臂,如缘梯状,望之可接霄汉。这种幻术,实际上就是民间百戏中的“叠罗汉”,以人体作梯,后人攀登而上。
(七)禽戏
《聊斋志异》中利用动物进行幻术表演的故事是《蛙曲》和《鼠戏》。《蛙曲》是将不同种类的蛙放在木盒之中,演奏时敲击其头顶,使蛙发出云锣或者其他特殊乐器声音的一种表演。《鼠戏》是利用鼠而作的一种配乐戏剧,乐声响起,鼠自囊中出,戴着假面,穿着小型服装从术人背后爬上肩头,像人一样站起来跳舞。这两种幻术都是禽戏,即训练动物、昆虫进行表演的一种古老的民间技术,具有一定的动物学和生理学根据。其训练对象不仅可以是青蛙、老鼠,也可以是乌龟、泥鳅、蛤蟆、小雀、蚂蚁等,种类繁多,这种幻术多是江湖艺人谋取生活的手段。[8]
(八)投符念咒术
符咒术是道家的一种常见的幻术,《聊斋志异》中也有此类幻术。如《赌符》中,族人携带韩道士之符便可以一掷成彩。又如《雨钱》中老翁用十数钱做母钱而作术,禹步念咒,随后“钱有数十百万,从梁间锵锵而下,势如骤雨,转瞬没膝,拔足而立,又没踝。广丈之舍,约深三四尺余”[9]。秀才十分欣喜,但是等到取用之时,满室钱财化为乌有,只剩十几块母钱,这样的结果说明了满室钱财不过是老翁的幻术,不劳而获实不可为。
二、《聊斋志异》幻术故事的特点
通过对《聊斋志异》所载幻术故事类型的划分,我们不难发现《聊斋志异》的幻术故事存在以下特点:
(一)叙事手法的成熟性
《聊斋志异》幻术故事的叙述方式具有渐成熟的特点,最基础的是单一叙事,如《戏术》《蛙曲》《鼠戏》《木雕美人》等篇,通常粗陈梗概并且简单描述某一场面,是片段式的故事,这类叙事中也有篇幅较长的,如《偷桃》篇,全文用近千字描写了一场大型幻术表演,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开场表演、掷绳直立、缘绳偷桃、身体肢解、讨赏复原。但实际上仍不能将其视为完整的小说。而另外一部分故事如《种梨》《劳山道士》《济南道人》《巩仙》等都是经过精细加工的幻术故事,不拘泥于故事梗概而从生活逻辑和故事情节出发,在原有幻术故事基础之上充分发挥想象,编造细节,记叙委婉,细腻生动,行文及其语言都独具匠心。
以下试以六朝志怪小说《搜神记》中的“徐光乞瓜”故事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种梨》进行比较。《搜神记》记载:“吴时有徐光者,尝行术于市里。从人乞瓜,其主勿与。便从索瓣,杖地种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实。乃取食之,因赐观者。鬻者反视所出卖,皆亡耗矣。”[10]《搜神记》所记故事篇幅短小,全文采用单一叙事,交代事件。而《种梨》开篇即交代了道士与卖家的矛盾:
“有乡人货梨于市,颇甘芳,价腾贵。有道士破巾絮衣,丐于车前。乡人咄之,亦不去;乡人怒,加以叱骂。道士曰:‘一车数百颗,老衲止丐其一,于居士亦无大损,何怒为?’观者劝置劣者一枚令去,乡人执不肯。”[11]
卖家为何执意不与道士梨,其原因耐人寻味,而《种梨》篇中详细描述了矛盾的产生原因。首先梨价昂贵,卖家自然不肯随意赠与道士,于是呵斥道士快走,道士不走,这是矛盾的第一层,随后两人起了争执,卖家怒骂道士,道士强辩,由此,矛盾已然升级。观者劝和,卖家执意不给,随后路边店铺伙计出钱买了梨子赠与道士,想要平息矛盾,但此时,道士仍是不服,于是才施展种梨幻术报复卖家。蒲松龄详写起因,这是对先唐志怪小说的发展。同时,其场面描写也更趋细腻,蒲松龄把梨树生长的过程描述得更加详细。梨树从发幼芽再到“渐大”,强调变化的过程,而“俄尔”“倏而”强调的是瞬间的变化,“硕大芳馥”则是视觉与嗅觉的双重体验。
这类精细加工的幻术故事在《聊斋志异》中占比很小,但是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脉络,即是由简单的为“补史阙”,而逐渐成长为“有意为小说”,从而获得小说的独立体格。
(二)人物形象的传奇性
《聊斋志异》一书,通过对幻术的描写塑造了一批神通各异的奇人形象,如隐身移形的单道士,“点石成金”的真生,袖中出“乾坤”的巩仙,穿墙而过、剪纸成月的劳山老道等,幻术的加入增强了人物的传奇性。
单道士身怀隐身术法,韩公子奉其为座上宾,并要求学习术法,单道士唯恐术法传出坏其道行,自己反倒成为济恶宣淫之徒,而不肯教授。韩公子恼怒,私下谋划鞭笞而侮辱道士,用细灰铺在麦场上以使得单道士显出足迹,但是一经鞭打,灰尘就扬起,单道士趁机脱逃。单道士不畏强权而坚守道德,被人为难之际仍可借助幻术脱逃,逃亡之际仍旧不忘旧友,取酒菜佳肴款待之后才又隐身逃走,实乃有情有义之辈。《聊斋志异》的幻术故事中塑造了很多正面的道士形象,他们或者像《种梨》和《济南道人》中的道人一样运用搬运术惩戒锱铢必较的俗人,宣扬兼济之道;或者像《巩仙》中的巩道人以幻术帮助有情人终成眷属,其袖子还可做药救人,他们有情有义、匡时济俗,寄寓了蒲松龄的人生理想。
《真生》篇讲述了真生与贾子龙两人相知、相交、相绝,最后冰释前嫌的故事,以“点金术”为线索贯穿全篇。真生本寓居咸阳,贾子龙偶遇之,欲与其交往,三顾茅庐而不得见,于是派人跟踪,认定其在家而上门拜访,真生闭门不出,贾子龙强搜其住所,真生不得已才现身。贾子龙偶然发现真生空壶取酒幻术,欲学其术,真生认为其“贪心未竟”而不肯教授,贾子龙辩解称“徒以贫耳”。后两人仍旧亲密无间地相处,每当贾子龙困窘之时,真生便以黑石点金赠与贾生,但仅够其日常所用。贾生贪婪,就偷了真生的黑石要挟他,真生愤怒不已,认为贾生实在不可相与就搬走了。之后过去一年多,贾子龙偶然捡到一块奇石,与真生的那块石头很像,便带回家珍藏。过了几天,真生回来索要石头,并且点明该石就是点金石,贾子龙向其索要报酬,真生称给他一百两金子,贾生称一百两太少,便要求学习点金口诀,真生本来不相信他后来勉强同意,贾子龙谎称以半块砖头试验口诀真假,私下点触了砖头下面的大石头,真生大惊,称木已成舟,其将获罪于天,询问贾生是否愿意布施棺木一百口、棉衣一百件,挽回自己的罪过。贾子龙允诺。后贾子龙履行诺言,真生感激不尽,二人和好如初。
这篇文章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截止到贾生偷石,而真生离开,这部分主要讲述了两人的相交、相绝的过程,真生施恩于贾生,而贾生却恩将仇报,偷窃石头要挟真生。第二部分作者设计偶然情节,又使得两人因石相遇,真生交代点金石真相,实际上是仙人赠与,自己醉后丢了石头,希望贾生可以归还,这里两人的身份发生了转换,贾生成为了施恩者,其贪求钱财、蒙骗朋友的本性暴露无疑。而第三部分则情节突转,贾生得金之后一边布施一边行商,真生感激其真乃“信义人”,两人欢饮如初。情节几经反转,奇之又奇,人物形象也更加饱满。
(三)叙事视角的民间性
蒲松龄始终以观照世情的视角看待幻术表演,对于“种幻术”“禽戏”“傀儡戏”等民间杂技幻术的关注承前启后,这些幻术经过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从“蚩尤戏”开始,直到与西域幻术共同融合,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民间文化的一部分[12],是古代士大夫主导文化下的一股暗流。蒲松龄为民间幻术文化代言,给幻术表演的发展赋予了极强的生命力。
在幻术故事之中,蒲松龄甚至以“异史氏”述愤的形式直接表现自己社会文化观念。明清时期,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已经成熟,但在理学思想盛行的封建社会末期,作家往往特别重视作品的教化意义,过于强烈的议论要出现在作品中,往往会破坏小说的整体性,这种借由“异史氏”抒发议论的表现形式实际上是社会思潮和文学创作结合的时代产物,往往点明或者深化小说的主题思想。
如《种梨》篇中对于“素封者”的批判,富人们往往对亲朋好友十分吝啬,有人劝其扶危济困就私下计较钱财,甚至父子兄弟之间也锱铢必较,富贵之人尚且如此,又怎么能责怪乡人的吝啬呢,《赌符》中异史氏也表达了对于赌博的厌恶和对贪欲的否定。《劳山道士》中异史氏的补录更是揭露了一种普世真理,王生急功近利,那些嘲笑王生的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蒲松龄致力于社会缓和,主张移风易俗,以清醒的观者视角对世俗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这也正是他借幻笔写世情的一种创作手段。
三、《聊斋志异》幻术故事形成的原因
《聊斋志异》中的幻术故事倾注了蒲松龄的创作心血,其光怪陆离的幻术世界建立在其广博的文学知识和“集腋为裘”的创作精神之上,以下试分论之。
(一)受先唐志怪小说的影响
在题材选择上,蒲松龄受六朝小说影响巨大。其在《聊斋自志》中也提到:“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13]蒲松龄自言“有意为小说”,其创作又受《搜神记》《幽冥录》的影响,充分说明了蒲松龄创作题材有一大部分来源于先唐志怪小说。
《偷桃》故事见于《狯园·偷桃小儿》,除用木梯代替绳子外,故事情节大体一致,其故事经过《原化记·嘉兴绳技》《九龠集·蟠桃宴》等的影响与融合,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幻术故事。[14]《种梨》故事来源于《搜神记》中的“徐光乞瓜”的故事,据王青在其《<种梨>与西域幻术——古典小说与幻术之一》中考证,《太平御览》卷七三七、《法苑珠林》卷六一中都提到过此幻术。[15]《鼠戏》中的“禽戏”表演,最早见于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二“禽戏”条,朱梅叔《埋忧集》卷四“田鸡教书”条中运用大小“蛤蟆”的声音来模拟教书场景的方法,与《蛙曲》有异曲同工之妙。[16]
在创作手法上,蒲松龄继承了六朝志怪小说现实主义的风格。六朝时期战乱频仍,战争带来的心灵创伤使得作家们更加关注现实,他们的创作以搜集畸人异事等民间传说为主,怪而不诞,幻而不虚,常常有据可查,在现实生活中汲取治愈精神的力量。蒲松龄继承了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植根于民间文化,在其幻术故事中标注事件主人公,如《铁布衫法》中的“沙姓回人”,《戏术》中的“利津李见田”,故事若来源于友人转述,也必定表明来源,王子巽、白有功等人都是其幻术故事的提供者。蒲松龄在创作过程中,兼之为奇人术士作传,幻术故事创作必先涉及人物名姓、籍贯、居所、身份,即使大多数人物信息无处可考也必提及,人物往往以“巩道人”“韩道人”“济南道人”等称呼。
在叙事风格上,先唐志怪小说多简明扼要,用简短的语言概述故事情节。蒲松龄的幻术故事继承了这一特点。《聊斋志异》中的幻术故事大多篇幅短小,仅百字,记叙简单,较长的《种梨》《巩仙》也不过千字左右。在有限的篇幅之中,呈现最曲折动人的情节和细致入微的描写,这是蒲松龄高超叙事艺术的体现。
(二)蒲松龄的个人经历
蒲松龄是一个长年生活在农村的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耕读传家的封建家庭之中,他不可避免地投入到举业之中,但是学识渊博的蒲松龄却因不能“袖金输璧”而屡试不中,南游初试官场,最终也因家中困窘而不得不放弃,四十八岁再考时又名落孙山。蒲松龄曾作《寄紫庭》:“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17]暮年壮志未酬,科考失败成为了蒲松龄一生的隐痛。
由于官场上的失意,蒲松龄在五十岁后就专心坐馆著述,先后在本邑沈家、王永印家、本县毕家等缙绅家中“坐馆”,即当家庭教师。其子在《柳泉公行述》中说:“自析箸,薄产不足以自给,故岁岁游学,无暇举子业”[18],这里的“游学”指的就是坐馆授徒。这种谋生手段使得蒲松龄接触了不同阶层的人物,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也有了深刻的了解,《偷桃》故事就是蒲松龄的自传式故事,是其亲眼看到的民间技艺。
但是,蒲松龄对于幻术故事的搜集不仅来源于环境的熏陶,与其“雅爱搜神”的兴趣爱好也不无关系。他在《聊斋自志》中就提到其对于搜集民间故事的热爱,终其一生,他始终没有放弃过对民间故事的收集。《蒲松龄评传》中就记载了创作素材的搜集过程,蒲松龄常常设茶、烟于道,每遇过路者,必强行与人交谈。这种爱好的根源无从探究,或根源于少时挑灯举酒所读《游侠传》,但是却表明了蒲松龄对于奇人异事的好奇与向往。后蒲松龄在南方游历之时作《途中》一诗,其中也提到,“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摇意欲仙”[19],这种对民间故事坚持不懈的搜集,是其《聊斋志异》得以撰成的重要原因,也是他“集腋成裘”创作手段的具体表现。
仕途上的失意使得蒲松龄终其一生都在“幻”境中寻求安慰,他感慨于巩仙的“袖中乾坤,”篇末借“异史氏”之口描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即“中有天地、有日月,可以娶妻生子,而又无催科之苦,人事之烦,则袖中虮虱,何殊桃源鸡犬哉,设客人常住,老于是乡可耳”[20]。天地日月是上苍恩赐,又可娶妻生子全人伦之乐,无科考之苦,实在是桃源福地。
四、结语
幻术表演经过千年的发展,早已融入了民间文化,魏晋志怪、唐传奇、明清小说,以历史性的继承,承担着记录这些文化的使命,终于使那些不见经传的奇人异事重新展现在文学与史学的视野之中,蒲松龄充分吸收这种文化,并运用其高超的叙事魅力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幻术世界。《聊斋志异》中的幻术故事体现了蒲松龄根植于现实主义的浪漫情结,是蒲松龄在先唐小说的继承、创新和民间情感的表达过程中,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