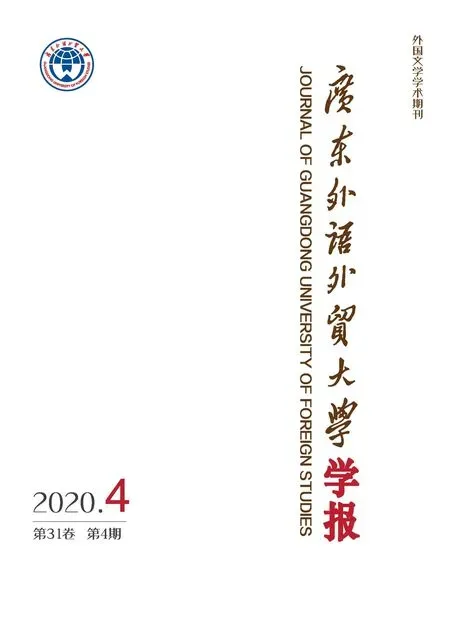基于生态伦理学的奥尼尔戏剧解读
2020-03-02王占斌
王占斌
引 言
生态伦理学是二十世纪中期兴起的应用伦理学,这门学科属于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以生态或环境道德为研究内容,从伦理学视角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真正提出生态伦理学概念和学科的是法国哲学家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和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前者提倡人类应该崇拜、敬畏、维护和完善生命的伦理价值取向(施韦泽,2015),后者强调应该把道德伦理扩展到自然界,关乎自然界的一切存在(利奥波德,1992)。生态伦理学向传统伦理学展开挑战,它将研究范围由以前仅限于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的“道德法则”进行拓展,运用到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刘永杰,2014)。生态伦理学包含更具体的道德指向和辩证逻辑,人类只有宏观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自然的神圣不可侵犯,才能反思和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所以人类精神与自然生态的伦理关系对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具有直接指向的影响。
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面临生态伦理的异化与挑战,美国文学便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书写处于生态危机的人类命运,追索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重新定位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追问生命的归属,用文学艺术的形式从思想上解决人类面临的危机。除了小说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外,剧作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也是其中的一位,他用戏剧表演的形式展现了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和失衡,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精神异化和灵魂荒芜,具有明显的生态忧患意识。本文基于生态伦理学理论,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奥尼尔不同时期三部戏剧进行阐释,探究其作品中蕴含的积极的生态伦理意识,以及伦理意识影响下的伦理叙事和人文关怀。
奥尼尔生态伦理意识的形成
聂珍钊(2007:27)认为,“现代科技破坏了正常的人际关系,给人类带来隔阂、孤独、冷漠、失望和痛苦,造成精神贫乏和人性异化”。奥尼尔就是要为异化的灵魂寻找可以安魂的地方,使飘荡的灵魂能有所归宿。奥尼尔的戏剧具有深刻的哲理意义和超越意识,他的思考由“物质生态伦理上升到精神生态伦理”(王占斌,2018:256),表现了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关怀。那么,奥尼尔的生态伦理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奥尼尔的海洋生活促使他生态伦理意识的形成。奥尼尔酷爱大海,怀念航海的日子。他喜欢坐在海边的岩石上,用简笔画描绘着沿泰晤士河顺流而下的帆船,就像《天边外》中的罗伯特·梅约一样数着过往的船只。大学时期的奥尼尔就对海洋小说产生浓厚的兴趣,对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水仙号”的黑水手》(TheNiggeroftheNarcissus)爱不释手,被康拉德笔下浩瀚的海洋弄得神魂颠倒。正如多丽丝(Doris Alexander,1962:139)所言,“尤金一下就被康拉德的描写倾倒了,康拉德用天空和海洋象征巨大而不可思议的神秘的自然环境,他笔下的人能够在这种神秘环境下创造出非凡的高贵”。奥尼尔对海洋的迷恋是因为他想挣脱令他窒息的现实世界,在自然中“找到自己的归属”(Gelb,1973:144)。奥尼尔对大海的痴迷可以从一九一八年纽约《呼声》报评论人奥林·汤斯采访奥尼尔时的一席谈话清楚地感受到:
你是否听到过大海唱歌的声音?……那个无法无天的海魔王,唱起歌来可真美妙动听,但又凶暴无比。他们知道,讨好他也没用。他们如今是接着他的歌声的节拍,按着浪涛的节拍拉缆绳。啊,不过,我真希望你能听到那种歌,尝一尝在海上颠簸的滋味,我希望你能倾听前甲板上透过风声和波涛声传来的手风琴演奏声。(刘德环: 97)
早年的航海生活孕育了他对大海的理解和热爱,奥尼尔诗歌散文里几乎没有离开赞美海洋。他在《自由》里称赞海洋为:渴望狂暴的大海/让灵魂自由翱翔/浪花翻飞彩虹戏/狂吻波涛美味里。在《大海的呼唤》里海洋被描写为:热带的夜晚星光闪闪/躺在舱盖上真快活/天空晴朗星星近在咫尺/船的尾流成了一条光流。
奥尼尔一生都在寻找宜居的海边房屋,普洛文斯顿郊外的房子坐落于海边,除了小沙丘和海浪声,没有喧嚣和嘈杂,显得遥远和静谧。尖顶山庄(Peak Hill)的房屋怀抱大海,“海洋和海风的雄壮和浩瀚”洗涤着他的心灵(Gelb,1973:393)。博林(Norman Birlin)认为奥尼尔具有海洋情结,他的住处基本上没有离开海边,他“一九一八年在科德角,一九二五年在百慕大,一九三一年在佐治亚州的海岛,一九四六年在位于大西洋的马萨诸塞州的马布尔黑德”(Birlin,1982:30)。
航海经历使奥尼尔亲身感受到大自然伟大而神奇的力量,这些激起他对自然的爱怜和敬畏。奥尼尔深刻领会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并且用戏剧歌颂人与自然不可利用和占有的伦理法则。自然并非“他者”,自然是主体,人和自然是“我与你”的关系(布伯,2002:5),人只有与自然融为一体,才能找回精神的归属。
奥尼尔的生态意识源于西方艺术哲学的泽溉。西方戏剧家易卜生(Henrik Ibsen)和斯特林堡(Augllst Strindberg)是奥尼尔推崇的两位大师,对他的戏剧创作艺术和生态伦理意识的形成有直接影响。易卜生对人与自然或者人与环境的关系非常关注,并从中观察和掌握人之本性和社会形态,揭示生态问题导致的一系列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具有高度的生态伦理关怀。斯特林堡把“自然主义逻辑发展到了顶点”(Cargill,1970:108-109),剧中人物往往把尔虞我诈、物欲横流的环境误判为和睦、和谐的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他们无所适从。
奥尼尔热爱希腊悲剧,阅读和研究了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等悲剧大师的作品,他认为希腊悲剧张扬人性,歌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伦理价值开阔了奥尼尔的创作视野。所以奥尼尔觉得“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希腊悲剧”(Nethercot, 1960),他从希腊悲剧中体悟到人与命运的抗争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典型显现。奥尼尔用戏剧诠释了这种生态伦理观:人是由命运决定的,命运其实就是自然或者某种神秘的力量,它会“驱赶你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Gelb,1973:352)。
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哲学对奥尼尔生态伦理意识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尼采厌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极力推崇自然主义的道德价值,尊重和敬畏生命。奥尼尔深受尼采人与自然关系哲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尼采的超人哲学。奥尼尔最喜欢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他认为“没有哪一本书比得上这本书对我的影响”(Gelb,1973:121)。
东方的道家文化对奥尼尔生态伦理意识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奥尼尔酷爱东方文化,他还用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建造一幢取名“大道别墅”(Tao House)的中国式楼宇。在奥尼尔的“大道别墅”里,藏有两种不同版本的《道德经》和《庄子》的英译合译本。奥尼尔认为东方道家哲学倡导的旷达隐逸、陶情遣兴的价值观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自然、社会都是相互并存的,他通过戏剧用道家包容的思想批判和解构了西方对立的二元思维形态。
以罗伯特书写和谐自然的归宿
《天边外》(BeyondtheHorizon, 1918)的主人公罗伯特·梅约(Robert Mayo)热爱读诗,富于幻想,渴望山外面的大海。罗伯特从小喜欢做梦,他相信天边外是“漂亮仙女的家乡”和“太阳藏身的地方”。 罗伯特的梦想听起来像是一些记忆的碎片,但如果我们把他梦中的零碎拼凑在一起,发现它是由美、东方、神秘和自由组成的,这些元素都包含着东方道家回归自然的影子。现实生活中的罗伯特陷于痛苦、困惑的身份危机中,梦想从乌托邦世界寻找自我灵魂和肉体的归宿。
罗伯特婚后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他不谙农活,心也不在此,原来父亲经营兴旺的农庄破败不堪,“窗帘又破又脏,书桌上积满尘土,壁纸都是霉迹,地毯开了窟窿,桌布污痕斑斑,铁炉子上一层黄锈”①。家庭债务累累,父母的离世和孩子的夭折使罗伯特已经难以承受现实的重担。罗伯特面对残酷现实无能为力,只是失望、无奈和痛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挣扎着爬到小山头,遥望天边外,露出久违的快乐和满足。他临终前的一段充满惆怅的独白,催人泪下、发人深省:
你不要为我难过了。你没有看见,我最后得到幸福了,自由了,自由了!从农庄里解放出来,自由地去漫游,永远漫游下去!瞧!小山外面不是很美吗?我能听见从前的声音呼唤我去,这一次我要走了。那不是终点,而是自由的开始,我的航行的起点!
罗伯特像奥尼尔剧本中的众多人物一样,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所适从,处于孤独和疏离的状态,一生在寻找生命的归属,最后终于在自然中求得一席之地和身份认同。罗伯特在生命即将结束时与天边外拥抱了,告别了现实生活的喧嚣和躁动,与自然能够更亲近地触摸和交流。道家讲究生死轮回,生命无限。罗伯特最后幸福地微笑,正是他新生的复苏,自由的起点。《天边外》表现了人类在努力寻找一条出路,通过死亡与自然合一。博加德(Travis Bogard,1988:352)在评论《悲悼》时写道:“那些地平线远处的幸福岛屿与自然相濡以沫,这里远离罪恶,这里就是生命之源”。
奥尼尔通过本剧所表达的是,在现实与理想冲突的困惑中,只有回归自然,人才有可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归属感。罗伯特对天边外和海洋等怀有无限的憧憬,但是经营农庄的现实生活和周围亲人及邻居的物质中心主义死死压在他身上,他的希望和憧憬变成一种无望,他在无望中寻觅和探索希望,具有深刻的悲剧意义。奥尼尔的《天边外》隐含着积极的生态伦理意识,冷酷的现实和命运束缚着罗伯特的自由,他的生活定格在与命运的斗争中。
剧本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如果人的选择违背了自然规律,那么人再也达不到心里的和谐和平静,这是自然对人的惩罚。罗伯特由于错觉而放弃了追求的梦想,从此便陷入心理失衡,并耗其一生寻找身份的归属。福尔克(Doris Falk)认为,奥尼尔一生不停地“与上帝抗争,但是现在与自己抗争,与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归属抗争”(Falk,1958:34)。罗伯特死亡前的话包含人生哲理,他有生命的时候与自然不和谐,经受了痛苦、彷徨和孤独的精神折磨。死亡可以把他与自然牢牢地融合在一起。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的奥尼尔最后安排罗伯特快乐地、积极地面对死亡,幸福地接受死亡。奥尼尔借着剧本诠释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伦理意识。
以胡安书写东方乌托邦世界
《泉》(TheFountain,1921)中主人公胡安(Juan)骁勇善战,战功显赫,同时又富于浪漫气质和冒险精神。胡安认为男人不应该在儿女情长上浪费自己的青春,应该胸怀世界,奔赴疆场,保家卫国,为荣誉而战,和平“意味着停滞不前——勇士的懈怠,歌声的停息,还有玫瑰的凋谢”。胡安对深爱自己的玛丽亚说:“你所说的爱,它们只不过是情绪的变化,是一两个夜里的梦想,是贪欲的冒险,虚荣的表示,也许,可我从来没有爱过。西班牙才是我把心交付的女人,西班牙和个人的抱负”。他对朋友路易斯的诗歌“爱情是鲜花/盛开永不败/生命是清泉/喷涌永不衰”的评价是:“太动人了,不过这只是个谎言,让魔鬼去抓住你的花儿吧!”胡安把一切与荣誉和财富联系起来,其它都不值一提。
胡安的内心世界是复杂的,他并没有觉察到自己对爱和美的追求,他用荣誉和梦想压抑着自己的潜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剧情的发展,胡安的潜意识战胜了一直控制自己的意识。他鄙视贵族、财富和荣誉,追求东方神秘世界,他要远航寻找路易斯所歌颂的东方“青春泉”;他指责气势威严的舵主哥伦布,认为哥伦布之流统统“都是土地的抢劫者”,他们打着探索世界之奥秘,实则是掠夺和杀戮,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奥尼尔认为,“人只有放弃物质财富的占有,接受物质欲望的破灭,回归精神信仰,才能得到救赎。在追逐物质财富时,人否定了理想的美德”(Carpenter,1957:71)。奥尼尔早期的戏剧中对物质主义进行深刻地批判,对人类的生存和人与自然的不协调表现出急切的担忧:
我们拥有一切,但是注定要遭到报应。我们跟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沿着同一条自私、贪婪的道路前进。我们谈论美国梦……难道更多地是物质占有的梦想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有时认为美国是全世界目前看到的最大的败笔。我们以史上所闻的最高价格出卖了我们的灵魂。(Murphy: 135-36)
对战争的批判是奥尼尔生态伦理意识的最具体表现,他认为战争是贵族们践踏人性、灭绝生灵、破坏生态。在剧本《泉》中,贵族们联手掠夺东方国家的财富,占领土地,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奥尼尔强烈批判战争和武器的野蛮性和毁灭性,他不无嘲讽地说:“原子弹是伟大的发明,因为它可以毁灭人类”(Carpenter,1957:62)。奥尼尔的剧本向我们充分展示了人类、自然、战争和生态的关系:人不是自然生态的主宰者,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就是在毁灭自己。奥尼尔对人类生态危机的担忧显示了他伟大的自然情怀,也促使他通过悲剧的形式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解决人类的困境。在《泉》中,奥尼尔借路易斯之口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乌托邦世界:
在东方某个遥远的国度里,在中国,在日本,谁知道呢,有一个地方,大自然界是跟人类分开的,被赋予宁静。那是一片神圣的树林,在人踏入之前一切事物都处在古老的和谐之中。那里到处充满了美……每一种声音都是音乐,每一种食物都是风景。树上结着金色的果子。在丛林中央,有一口喷泉,它美丽得超出人的想象,在喷泉的彩虹中映射出人生的方方面面。少女们在这口喷泉的水里嬉戏、歌唱。(第一幕:第一场)
剧中的英雄胡安处于两种身份的焦虑之中:“年轻时,他梦想有一个伟大、辉煌、仁慈的西班牙帝国;作为官员,他又必须战斗,所以他的梦想被击碎”(Robinson,1982:101)。奥尼尔研究专家弗洛伊德(Virginia Floyd,1981:XIX)认为:“从个人角度看,外在追求财富和内在追求自我实现的二元对立必然导致个体性格的分裂”。胡安弥留之际产生了幻觉,看到了青春泉,他分裂的人性愈合了。罗宾逊(Robinson)在《东方思想》中写道:
从道学的视角看,(胡安)的幻觉就是对二元对立的消解。比如,随着诗人和牧师手拉手围成一圈,象征着和谐与统一,东西方文化冲突顿时消失了。当胡安感觉到一切都与“永生同一节奏”时,老年和青春的二元对立被解构了。生命和死亡就在同一周期上。(Robinson: 107)
胡安在生命的最后终于找回了自我,他感到自己与晚霞和黎明共生死,与土地和生物齐歌唱,呼吸着大自然的灵气,与自然心心相印。他说:“永恒之泉,你是一切归一,而一又在一切之中,永恒的变化才是真正的美”。胡安快乐地死了,他的死并非悲剧,是生命的开始和再生,是永恒自然的循环往复。奥尼尔对生态认识可以说得到了超越。
以阔阔真书写爱与美的复活
《马可百万》(MarcoMillions, 1927)男主人公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受教皇派遣的贸易使者。可汗的孙女阔阔真(Kogatin)单纯可爱,天真活泼,她暗中爱上了马可,把他看成“从奇异的西方来的、陌生而神秘的梦中骑士,一个不可思议的、具有一种惹人喜爱之处的男子”。当马可进殿拜见可汗时,阔阔真心情激动,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他,带着无限赞赏的神情,希望能得到他的一盼”。阔阔真无数次含蓄地向马可吐露自己的爱意,有时不顾公主的面子直率地示爱,可只关心一百万金币的马可根本不能理会公主的表白。面对麻木不仁的马可,公主用尽全力去激活马可被物质迷失的心灵,她说:“在我的生命中没有我所不愿意给的东西,没有我所不愿意做的事情,看我的眼睛,如果你看不到那里有什么东西,我一定会死!”然而一切都是徒劳。
奥尼尔借阔阔真之言严厉地批判了西方物质中心主义,他认为金钱把人变成一头没有灵魂的畜生。温泽尔(Winther,1934:206)指出,马可·波罗就是西方消费文化的典型,他代表了“西方文明的腐朽,只注重追求物质利润,忽视事物内在的真善美”,《马可百万》是对“西方理想主义整体体系的控诉”。西方工业化促使人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失去了精神支柱,完全以物质占有的多少来衡量自我的价值和存在感。正如绝望的阔阔真指责马可·波罗的:“甚至在爱情上你也没有灵魂,你的爱情无异是猪的交配”。
阔阔真公主是东方道家思想的产物,崇尚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了道家的生态伦理之美。而马可把自然视为获取利润的源泉和实现其发财致富的工具,他为了利益在扬州大肆搜刮,破坏扬州的自然生态和传统文化;为了赚取钱财,他竟然向忽必烈兜售杀人武器,用血腥的战争屠杀人类;为了快速装船,他不在乎六个奴隶被活活累死。马可对自然地掠夺使他失去了人性,没有了灵魂,俨然一个贪婪和残忍的野兽。
《马可百万》描写了人的物质欲望与其精神追求的冲突。西方的商业文化主义价值理念阻止了人与自然的融合,麻木了人对自然之美的感觉。马可的眼里只有利润,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就连他与杜纳塔的婚姻也不例外,因为杜纳塔家能给他带来持续的经济利益和巨大的财富。在商业文化充斥的社会里阔阔真公主的悲剧是必然的。阔阔真公主把物质财富视为粪土,她憧憬的是精神之美和自我超越。评论家墨菲(Murphy)认为:
从某个不同的角度看,马可百万代表着文化的对立面,奥尼尔借《马可百万》对处于物质贪欲和灵魂超越冲突的美国商人赋予了时代性的讽刺。奥尼尔剧本中的马可·波罗从问世之日起,就被很多人拿来与辛克莱·路易斯的巴比特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马可“缺少人的灵魂,只有占有的本能”。《马可百万》中奥尼尔展示了由马可代表的物质主义的西方和富有思想的东方之间的分裂,前者对于自己眼前的美视而不见,而后者珍视智慧和美。(Murphy;139)
墨菲的阐释入木三分,暗示了奥尼尔剧中包含有明显的生态伦理关怀,同时也说明奥尼尔应用中国道家思想去寻找拯救西方生态伦理幻灭的意识。阔阔真的死亡说明中国道家文化在与西方物质中心主义的对抗中失败了,剧本最终以悲剧结尾。弗吉尼亚·弗洛伊德认为本剧的目的是在说明“人类的悲剧是因为物质的追求蒙住了人们的眼睛,致使人们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美和爱的世界,拼命地在黑暗中抢夺财物”(Floyd,1981:300)。正因如此,奥尼尔安排了阔阔真公主死去,她的死是“为爱而爱,为美而死”,是与自然的融合。道家认为生命是不朽的,生的胚胎与死的归宿,是互相协调的,最终要与自然融为一体。
奥尼尔个人并不认为《马可百万》是悲剧,他在给剧院提交剧本时写道:“尽管是个历史剧,实际上它是美国人写的讽刺我们的生活和理想的讽刺喜剧,我相信剧中的爱情故事和东方悲剧具有真正诗意的美”(Gelb,1973:572-73)。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什么奥尼尔安排阔阔真公主复活一幕。他满怀希望地用道家的天人合一、生死轮回的思想消解西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伦理价值,希望人与自然的和谐伦理会最终战胜物质中心主义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对立态势。也许我们用奥尼尔对本剧的自我评价更有说服力,人类面临的危机“要人们在物质方面(即世俗的)的成功与向更高的精神层次迈进两者之间做出抉择”(Floyd,1981:334),这个抉择就是选择和谐的生态家园还是堆砌物质大厦的生态伦理问题。
结 语
本文仅选了三部戏剧诠释奥尼尔的生态伦理意识,其实奥尼尔近乎每部作品都是对西方伦理生态危机的忧患和反思。奥尼尔的戏剧美学思想深受其伦理思想的影响,他的叙事是伦理的叙事。奥尼尔在剧中安排罗伯特、胡安、阔阔真公主的归属都是死亡,他们的死固然是悲剧,是物质主义泛滥对精神追求的扼杀;他们的死亡也是喜剧,是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实践。罗伯特的死象征着精神世界的回归,胡安的死象征了精神世界的超越,阔阔真公主的死是希冀精神世界的复活。奥尼尔对生态伦理的认识富有预见性和超前性,他在二十世纪早期就预示了人类即将面临的潜在生态伦理危机,所以他的生态伦理意识超越了时代,对当下生活的我们具有深刻意义。
注释:
①论文中来源于剧本中的背景语言和对话一律不做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