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灰烬里来 (创作谈)
2020-02-29文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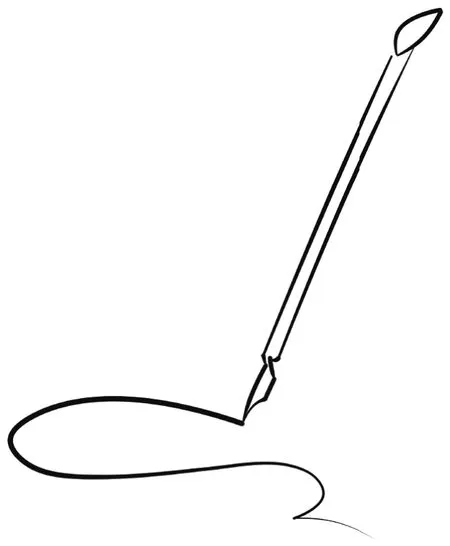
初中三年我是在一所被称为学霸工厂的中学里度过的,那里聚集了来自于东三省、内蒙以及关外内地的开拓者或叫海滨倾慕者的子女。家长们坚信他们会经由各种路数的迁徙,使自己和后代抵达黄金海岸,而本地教育机构也极尽能事,为新移民的下一代铺垫前程。这应该是桩好事,大家都笃信教育可以决定一切。可问题是—— 一个个形状各异大脑沟回也各异的脑袋,怎么可能被锻造成整齐划一的标准件?
我的一位老师是学俄语出身的,也是新移民,她曾是吉林省的省劳模,奔赴辽东半岛南端,想来也必定带着让光环继续闪耀的期待。但显然在某些环节上出了岔,相较于尖子班的几位年轻教师,她每每显露出一副疲态。有一堂课让我至今记得,某个冬日外面雪花纷纷,教室里粉笔末飘洒,她给我们讲普希金,讲《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讲她第一次读俄文原著时的震撼。那时她的眼里是晶亮的。那一瞬我突然理解了她日常里的疲态。
不知是否为了平复中学三年太过呛口的震撼教育,后来我读了一所普通高中,又上了一所普通大学,在一些传闻中达成了学校所描绘的那种平庸。几年前我看娄烨的《苏州河》,有个画面是周迅穿着拙劣的美人鱼道具服,在苏州河畔的夕阳金辉下灵俏地拍打尾巴,犹如波提切利笔下的人物,清冷离群,眼含忧郁。不知为何,后来多次在梦里遇见那条人鱼,与我打着某种征兆般的招呼。后来去上海旅行,领略了魔都的复式公寓,即上床下桌的魔改蜗居,田子坊遍地是举架宛如霍比特人村庄的小楼。再看外滩夜景与陆家嘴的未来都市,实在是魔幻得像焰火溅射出的镁粉,发狂地燃烧着,有的落下成了繁华霓虹的一部分;有的顺流而下,而今不知在何处继续流浪。听上海人说来务工的多为苏北农民,恍若隔世般地想到,东三省多少人背井离乡去到我们那片半岛谋生活。上世纪60年代,美国依靠公路和高普及度的私人汽车,完成了逆城市化的社会转型,不知道今天凭着互联网和高铁,需要多久我们才能不需忧虑地回归故里。
李沧东导演的《燃烧》中,男主角曾发此感慨:“这个时代为什么有这么多盖茨比”。村上春树的原著配上韩国极度割裂的阶级差距,将这部电影的文学部分的张力发挥到极致。写作《路河》时,显然被它那迷惘且不置可否的语气感染了,并将我经历到的,看到的一些人与事放置在微缩的熔炉之中。写作的过程中,一些往事浮现,想到了在那所出现在我人生关键节点的永恒牢笼,确实让我学到了一些东西,有关平静的。如果要获得某种超脱的平静,那它必定在创作间隙生发。
我曾因看过《燃烧》而久久不能平静,遂写下一段文字:可我们总是在不断的燃烧,燃烧是为了更好的明天,在执着中,最终烧掉了那些真正重要的人与事。写下了又觉得少了些什么,似乎与我心中某种诗意的燃烧相去甚远,在那个阶段又说不上来。
再以后,毕业失业独自生活,经历了一些现实的窘迫,几度在庸碌的生活中沉沦,慢慢地又从燃烧中嚼出一句:我从灰烬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