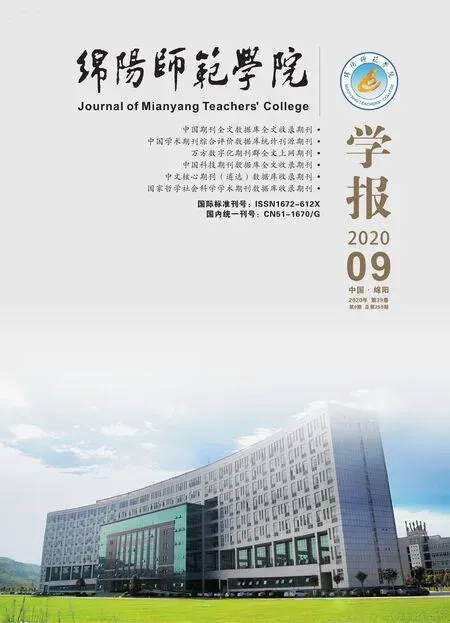论伍尔芙的“雌雄同体”观
2020-02-28温宇新
温宇新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6006)
英国女作家艾德琳·弗吉尼亚·伍尔芙是西方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她的小说和散文都体现了非常浓厚的女权主义思想。伍尔芙最早把“雌雄同体”观引入文学理论,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标准。在随笔散文《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芙首次探讨了男性价值与女性价值的问题,并由此推及论述了性别与写作的关系,“雌雄同体”观正是她探讨女性写作与女性价值的重要思想。
一、“雌雄同体”观的提出
“雌雄同体”这一观点虽然是由伍尔芙正式引入文学批评,但它并不是伍尔芙的首创。“雌雄同体”这一词的来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语andro(男性)和gyny(女性)构成了雌雄同体如今的拼写方式androgyny。在西方的神话、宗教、哲学里,也涉及到“雌雄同体”观念,如古希腊神话中同时带有男女性别特征的阴阳神赫马佛洛狄忒斯,兼具男性勇敢果断、所向披靡的气质和女性美丽端庄、和善可亲气质的胜利女神雅典娜,他们都是雌雄同体之神的代表。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借戏剧家阿里斯托芬的神话,指出人类除了太阳所生的男性和大地所生的女性外,还有月亮所生的双性人,这种人比单性的男人或者女人更完美,更有超越性,然而宙斯害怕双性人的力量,便将他们一分为二。柏拉图的这则故事预示了某种人类学的隐喻,即人类在这时出现了明确的性别意识,双性人由于其性别的超越性而被代表着父权意识的男性统治者们所惧怕,因此被割裂在性别划分之外。现代心理学也讨论到“雌雄同体”观,如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指出,无论是在心理学意义上还是在生物学意义上,都没有纯粹的男人或纯粹的女人;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也指出,男性在无意识中潜藏着一个女性人格,女性在无意识里也藏着一个男性人格,荣格称前者为阿尼玛,称后者为阿尼姆斯,只有让人格面具与阿尼玛或阿尼姆斯和谐共处,才能达到个体内部人格的和谐以及个人心理的完善。最早将“雌雄同体”观引入文学创作领域的是柯勒律治。柯勒律治在《席间漫谈》中批评了与他同时期的作家科伯特。他指出科伯特在写作上咄咄逼人、强势好斗、盛气凌人,这是男性气质过剩的具体表现。他反对这样强势的写作,推崇既能体现男性气质又能体现女性气质的“雌雄同体”写作。柯勒律治虽然首次把“雌雄同体”观引进文学领域,但他的“雌雄同体”只是作为拥有女性气质的男性作家而言的,忽略了女性作家中的男性气质,因而带有片面性和单边性[1],而伍尔芙在柯勒律治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雌雄同体”观的含义,她同时指出了“具有男性气质的女人”和“具有女性气质的男人”,重新审视了女性气质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
在伍尔芙的早期创作中,她的许多作品已经表现出了对雌雄同体的向往,如写于1915年的首部长篇小说《远航》,伍尔芙把女主人公蕾切尔塑造成了善于思考、渴望自由、精神独立的形象。这种形象兼具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女性变得有个性起来了。在随后的创作里,伍尔芙继续延伸了这种带有独立个性的女性形象。在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月与日》(1919)中,女主人公凯瑟琳不仅拥有独立的思想,还在温柔顺从的外表下酝酿着叛逆的精神。她反对“女性应当乖巧被动”的传统社会认知,毅然决然地争取婚姻的主动权。在《达洛维夫人》(1925)中,伍尔芙又塑造了少女时期“幻想改造世界”,到了中年却只能充当上流社会交际花的达洛维夫人,描述了如达洛维夫人这样的上流社会女性被婚姻、社会文化压制而只能依附男性的困苦状态。达洛维夫人的遭遇与伍尔芙相似,正处于写作生涯中期的伍尔芙深入反思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压抑的命运,她寻求以超越男女对立的性别模式来打破女性受压制的现状。1927年,伍尔芙出版了意识流小说《到灯塔去》。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兼具男性的理性与女性感性的女性角色莉丽。莉丽是一位艺术家,她既能以男性的思维来思考问题,又能通过直觉和个人经验领悟外部世界,最后她融合了理性和感性,创作出带有永恒瞬间的艺术作品。在伍尔芙看来,男性与女性的融合是超越性别矛盾和男女对立的前提,它以超越性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以艺术的完满性作为男女融合结局的思想在伍尔芙的小说《奥兰多》中表现得更为彻底。小说《奥兰多》的主人公奥兰多原是一位贵族少年,他勇敢好动,同时又天真热烈,在一次意外下他突然由男性转变成为了女性,性别的转换并没有困扰奥兰多,反而让他同时体会到男人和女人的魅力及其缺陷。他开始以一种雌雄同体的思维去思考世界,而这时,他在男性时期曾遭到否定的诗集《大橡树》,在他变成女人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诗歌的成功意味着奥兰多真正实现了性别超越,她的艺术创作也由此走向了完满。伍尔芙对雌雄同体思想的表述往往是跟艺术的走向结合在一起的,在1929年时,她出版了随笔散文《一间自己的房间》,深入揭示了艺术创作与女性历史、女性经济以及社会地位的关系,并首次提出以“雌雄同体”来代替传统的男权中心主义的写作思维。
《一间自己的房间》一书首先介绍了女性坎坷的写作史。在伊丽莎白时期,女性即使拥有跟莎士比亚同样天才的头脑,也会因为是个女人而受到嘲笑,最后“在村外的某个孤独茅舍里了结一生”[2]533;到了18世纪,少数妇女开始通过写一些蹩脚的小说来挣钱了,此后女人们开始参与文学创作;19世纪,小说已向女性敞开大门,并且出现了简·奥斯丁和勃朗特姐妹等杰出的女作家,女性作家甚至能占据“几个书架的隔板”。女性与写作的关系虽然到19世纪时看似有所改善,但是这个时期妇女们的全部文学训练,均来自“对性格的观察和对情感的分析”[2]549,就算是奥斯丁、勃朗特姐妹这样的天才作家,也因为长期生活在狭隘的环境中,而使她们的才能受到了折损。图书馆、教区和学校依旧不允许妇女进入,大部分的女性得不到正规的教育,也没有经济收入来源。她们不得不早早嫁为人妇,生下许多孩子,除了少数成为艺术家的女人外,大多数女人几乎没有机会去写作。可以说,在20世纪以前的艺术创作中,两性气质并非处于平衡地位的,男性气质极大地压制了女性气质,相较之男性创造的辉煌灿烂的艺术作品,女性艺术家则少得可怜。这种女性气质的缺席表现在文学创作里,就可见男人们把女人表现得多么单一刻板:女人不是“善良得超凡入圣”,就是“堕落得穷凶极恶”。女人总是在“与她们男人的关系中来予以理解的”,没有个性,没有自我。伍尔芙非常反感这种单向性别的写作,她认为这样会使他们的头脑中“横着一条黑色的直杠”[2]580,虽然能令男人感到“富有象征意义”,但在女人看来是“粗糙而又不成熟的”[2]582,他们无法创作出完满成功的艺术作品。伍尔芙主张消解男性中心主义的写作思维。她认为每个人的头脑都被两种力量统辖着,一种是女性,一种是男性。世界上不存在纯粹的男性头脑,也不存在纯粹的女性头脑,能同时从两个性别的角度去考察、思索,艺术才能得到完满、成功的展现。伍尔芙引用柯勒律治的“伟大的头脑都是雌雄同体的”来概括这种思想,相较之于单向性别的脑子,“雌雄同体”的脑子更具有共情性,更能没有障碍地表达感情,也就能更大程度地使艺术臻于完满。在此,“雌雄同体”观正式在伍尔芙这里提出了。可以说,“雌雄同体”观的提出,既对女性写作和女性气质进行了重新审视,又撕开了男权话语体系下文学性别书写的矛盾,为男女两性未来的相处方式以及20世纪的文学发展提出了一种构想,同时也为后来的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从《一间自己的房间》窥探伍尔芙对“雌雄同体”观的阐释
伍尔芙的“雌雄同体”观,不同于柯勒律治仅指带有女性气质的男人,而是同时指出了女人身上的男性气质与男人身上的女性气质,并且同时肯定了男性的创造力和女性的创造力,她的阐释极大地丰富了“雌雄同体”观的含义。首先,“雌雄同体”意味着两性平等交流、和谐共存,而不是两性对立或者是一个性别压倒另一个性别,她反对男女之间因对抗而走向互相仇视[3]。为此,伍尔芙批评了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认为这本书放大了个人的愤怒,“包含了太多那种激烈和愤慨”[2]552。这种激烈的情感永远也无法使她的天才完全表现出来,她的书是“变形的、扭曲的”,因为夏洛蒂太过于宣泄情绪,对男性的不满直接暴露在小说之中,使得本应该将情感自然流露的小说遭到了扭曲和变形,然而对男性的怨恨并不能使女性受到增益,反而还会削弱她们的才智。伍尔芙又讨论了玛丽·卡麦尔的小说《人生的冒险》,她认为卡麦尔的小说较之于勃朗特等人优势的地方,是对她来说“男人不再是反对派了”,“她用不着浪费时间去抱怨他们”,“在她对男性的处理中,恐惧和仇恨消失了”[2]573。伍尔芙认为卡麦尔并不算是一个天才,但是她的作品却比她的先辈们更具有“广泛、热烈而且自由的感受性”[2]573,这是因为她并未脱离小说的情境而把个人化的怨气发泄到男性身上,她的小说体现了更加自由而和谐的创作。在伍尔芙看来,对立与仇视并不能带来艺术的升华,两性平等、亲睦、和谐共处才是最理想的状态,同时也是写作的最理想状态。她主张消除性别对立意识,像一个女人那样写作,但又像一个忘记了自己是女人的女人那样写作[2]574,即把性别意识暂时抛诸脑外,让身心获得解放,让精神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样艺术创作才能得到完满的升华。
伍尔芙的“雌雄同体”观虽然强调消除性别对立,在写作中“忘记”自己的性别,但是她并没有主张消除性别的差异,反而要求承认并正视差异,甚至要求在另一个性别中寻找差异互补。男女之间有着思考方式的差异,女人使用的语句、词句跟男人有所不同,但恰好是这种差异,造就了更加丰富的世界和更加有创造力的思想,伍尔芙感叹道:“倘若女人写作像男人、生活像男人、长得像男人的话,那将会是遗憾之至。”[2]569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是无法改变的,而且我们的教育也并不是要让我们改变这些差异,适当的差异还能让我们在与彼此的观照中看到自身的局限。因为不论男女,在头的背面都有一个自己永远看不见的先令大小的斑点,而描述那个头背面的先令大小的斑点,便是男女两性之间能达到的最好的互惠条件之一[2]571。在与另一个性别进行对照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自身性别中的瑕疵之处,男女两性在互补互助中,能达到最完美的互惠,这也是因为“世界的巨大和多样性”,“一个性别应付不了”[2]569的必要结果。
“雌雄同体”意味着两种性别是平等的,他们各有优劣,且价值互补,而正是因为如此,女性更要正视自身的价值,男性也要脱离男性中心的维度,重新审视女性的创造力。伍尔芙认为,女人本身是非常丰富和有趣的,连“墙壁都渗透着她们的创造力”。她赞叹女人是“高度发展的”和“极为错综复杂的”,人们只要走到任何街道,走进任何一间屋子里,都可以感受到女人的那种复杂和丰富的气息扑面而来[2]568。但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创造力是无法用工具去精确估计的,世界上并没有一标一尺能衡量一位母亲和妻子的价值,而男性也被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所限制,觉得“足球和体育很重要,但是时装和追求美丽微不足道”,“某书描写了战争,所以它是重要的,某书描写的是起居室里女人的生活,所以它是微不足道的”[2]556。伍尔芙认为这种价值观和写作观是狭隘的,这样会导致头脑中“横着像字母I一样的阴影”。它把它身后的女人给遮蔽了,同时也把男性的创造力给逼到狭隘的范围内。为此,伍尔芙主张价值重塑,女性不以男性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接受自身的“错综复杂的气息”,同时,男性也应当跳出男权话语中心的范围,看到“字母I”背后的世界。
最后,“雌雄同体”观是两种性别的交融,男性可以像女性一样写作,女性也可以像男性一样写作。为此,伍尔芙设想了这样一幅情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各自走过,他们二人各不相干,且都有自己的事情,但他们进了同一部出租车,看起来就像达到了某种和谐的交融。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有纯男性或纯女性的头脑,一个女人必定和她头脑中的男人部分有着交流,一个男人也必定同他头脑里的女人部分有着交流,头脑中的男人部分和女人部分是存在于一体的[2]78,艺术的完成需要男女的共同合作。伍尔芙批评了当时一些男作家的创作,认为这些男作家们虽然才华横溢,但只运用了他们头脑中男性的一部分。这导致了他们创造的东西似乎被分离进不同的房间,其中的创造力没法从一个房间带到不同的房间[2]581。女人不能从他们中受益,找不到他们作品中的“永生的源泉”。当他们的句子带进头脑时,便沉重地落在地上死去了。伍尔芙的此番批评揭示了现代小说中单一性别意识的弊害,抨击了男权话语体系对艺术创作的伤害。她呼吁超越性别的写作方式,试图通过“雌雄同体”来突破男性中心主义的创作理念,让男性和女性都可以超越性别而自由创作。基于这种“雌雄同体”观,伍尔芙在她的小说中创造了大量有着“雌雄同体”特征的人物,这些兼备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人物形象,打破了男权社会对女性形象的单一规定,改变了现代小说在描写人物性别时所秉承的刻板印象。
从逻辑学的思维范式来看,伍尔芙对“雌雄同体”的阐释出现了一些矛盾之处,如她在阐述男女性应忘记性别进行写作时,又认为两性之间的差异无法消除,要正视两性的差异;在提出女性应正视自己的女性气质和女性价值时,又让女人像男性一样去争取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希望女性脱离物质上的贫穷现状,却又想不出什么实际可行的方法,以及在解释“雌雄同体”问题时,出现一些言辞上的模棱两可。但是“雌雄同体”观的提出,颠覆了男权社会男性至上的思维模式,解构了男性统辖下的文学叙事方式,使女性突破了男性构造的话语体系,为男女在未来的相处方式提出了较为合理的构想,同时也对之后的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雌雄同体”观与20世纪西方思潮的动向
20世纪以来,受科技和经济的影响,社会结构和社会思潮发生转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机器的普及,女人也可以脱离家庭去寻找工作机会,女性可以跟男性一样,运用知识和智慧来获得收入来源。然而男权社会下的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却阻碍了女性的发展,女性仅能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伍尔芙把“雌雄同体”看作当时解决女性附庸问题的方法,旨在促进男女平等,转变人们对女性地位的看法[4]。“雌雄同体”观虽然只是一种构想,但它却深刻地体现了20世纪西方思潮的动向。伍尔芙将“雌雄同体”作为其小说的思想导向,不仅迎合了20世纪以来的思潮的转变,也体现了20世纪之后的文学理论前景。
在伍尔芙生活的年代,西方社会流行把女性称为“房间里的天使”,要求女性乖巧文雅、温柔单纯,只做男人们的妻子、情人或者母亲。“房间里的天使”代表的是西方男权中心主义思想,这种将女性乌托邦化、去人格化、去主体化的意识,其实质正是男性霸权话语对女性思想的侵蚀。伍尔芙反对将女人称为“房间里的天使”,她认为女性要勇敢地走出狭小的客厅和起居室,努力通过写作以及其他谋生手段来为自己争取经济独立[5]。从这一角度来看,“雌雄同体”观具有反对男性霸权的性质,而男性霸权的实质,则是西方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或者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雌雄同体”观在反对男性霸权的同时,也在解构着西方思想的逻各斯主义、二元对立和真理本体论传统。西方社会自古希腊以来,就有着对事物进行剖析分类的思想传统,如柏拉图的理念现象的二重分体系,柏拉图认为理念是现象的本体,现象则是理念的映射,理念是根本的、永恒的,现象是其次的、变化的,因此现象服从于理念[6]22-23。这种分类意识投射到男女关系中,被显现为男性优于女性,男性是本体的、关键的,女性是附庸的、从属的,女性要顺从于男性,男性在女性面前有着绝对的地位。伍尔芙以“雌雄同体”观来代替男性本体的意识,用男女“共存”“和谐”精神解构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模式,用两性“平等”“互助”瓦解男性霸权主义传统,体现了她对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消解和颠覆。事实上,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在20世纪遭受了阐释危机,现代主义小说、意识流小说等体现出来的书写模式以及人物形象描写,已经无法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来分析了。文学写作模式的复杂化加速了传统思维方式的解体,伍尔芙提出“雌雄同体”的观点以及“雌雄同体”的写作要求,正好迎合了20世纪的思潮转向。从这一点上看,“雌雄同体”观有着深刻的前瞻性和现代性。
伍尔芙的“雌雄同体”观虽然对后世女性主义思潮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迎来了众多的批评与指责。如肖瓦尔特认为,所谓的雌雄同体不过是一种策略性的退让,是刻意讨好男性的一种手段;女性主义评论家蕾切尔·鲍尔比认为,伍尔芙的雌雄同体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观念,其中还隐约体现着男性霸权的思想[7]。这些后来的批评家对“雌雄同体”观的见解固然非常独到,但运用的仍旧是西方传统二元对立的模子,即困囿于男性/女性的对立形态,认为女性的弱势和受歧视是由男性的偏见导致的,女人要通过与男人的斗争来获取话语权和其他权利,这种非此即彼的对抗很容易滑入“女性至上”“男人是敌人”的另一种男性/女性的对立形态里[8]。伍尔芙的“雌雄同体”观本质上是反对对抗,提倡和谐共存。她观念中的男性和女性并非是单向的、静止的概念,而是会随着时代、经济、政治环境以及交往对象的改变而流动变化。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伍尔芙设想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共同进入出租车的情景,若对这一情景进行补充想象的话,可知男人和女人进入出租车后,一定会有交流、攀谈。他们互相影响着彼此,还会把受影响的部分传递给其他的男人或女人,自身也会因为交流和传递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两性之间是有互动和交往的,这似乎可以解释伍尔芙“要像女人一样去写作”和“忘记性别去写作”的叙述矛盾。性别概念的建构归根到底就是本质概念的建构,“雌雄同体”消解了男性本质或女性本质的思想,让性别呈现出如同互文话语般流动的形态。男人可以在交往对话中变成女人,女人亦可以变成男人,男女在对话与交往中自由地流动。此外,双性的流动并不意味着否认主体,伍尔芙对“雌雄同体”的界定是带有诗性张力的,她在消解主体本质的同时又在构建主体,旧的主体被消解后,通过流动性的对话和交流又会发展成新的主体。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还设想了一位丈夫“打开了客厅或者儿童室的门”,从女人的“错综复杂的气息中”获得“活跃的创造力”的情景。男性正是在同另一性别的交往中获得发展动力的,同理女性也一样。伍尔芙主张“要像女人一样去写作”,应被理解为女性在与男性的交往和对自身的探索中,发展出了属于女性新的主体。这一主体与作为另一主体的男性,共同交流、互动与发展。在伍尔芙的思想中,男性与女性都是一种流动的、未完成的且不确定的因素。后来的批评家对“雌雄同体”观有着诸多解读,如巴特将“雌雄同体”看成同时拥有两种性别的“双性人”[9];埃莱娜·西苏提出以多元化的女性书写来代替伍尔芙的“雌雄同体”[10]。他们都把“雌雄同体”的性别概念看成是固定和已生成的概念,未注意到其中的流动性和未生成性,这无疑是一种阐释缺憾,同时也说明了“雌雄同体”观的巨大阐释空间。可以说“雌雄同体”观在体现20世纪上半叶思潮转向的同时,也隐含了20世纪中后期的反本质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多元主义思想的土壤,伍尔芙小说中隐含的“雌雄同体”写作手法,甚至可以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或者互文性视角去解读。
诚然,伍尔芙的“雌雄同体”观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学理论土壤。从这一视角下,我们能够从中窥探到整个20世纪的思潮动向,但是它在转向新思潮的同时,还带着许多不成熟的因素。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伍尔芙并未明确说明“雌雄同体”的定义,她是作家,并非理论家,这决定了她的思想带有非常浓厚的诗学特性,传统的科学主义分析法难以评析她的思想,而且以逻辑学的思维范式去看待她的文学理念,常常能找出许多逻辑上漏洞,因此,无法用某种单独理论去归纳成了一大问题。由于“雌雄同体”观没有单一理论的规束,伍尔芙对它的阐述也还处于诗性语言阶段,事实上伍尔芙在叙述中也多次采用了语言学的视角,如她认为男性创造的传统的语句并不适用于妇女,女人要设计出适合自己创造力的句子,于是新的文学体裁小说成为了女人的阵地。这种分析似乎有其合理性,因为女性确实可以通过创造另一种话语来消解原本僵死的男权语言体系。然而话语天生就带有权力性质的,当解构了男权中心话语后,如何促使女性话语跟男性话语权力对等,而不会反被话语本身的解构性所反噬,伍尔芙带有诗意性的解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再者,伍尔芙提倡以一种“雌雄同体”的语言来代替僵化的男性中心话语,让作家不拘性别束缚,更自由地创作,然而这种创作趋向能否真正实现,还只是停留在乌托邦层面的构想,伍尔芙也没有给出答案。总之,相较于20世纪中后期的女权主义学者,如波伏娃、克里斯蒂娃、西苏等人,伍尔芙的思想依旧有许多不成熟之处。她用诗性语言来阐述“雌雄同体”观时,给“雌雄同体”带来了更加丰富的阐释空间和更加深邃的寓意,同时也给它带来了诸多的模糊性和矛盾性。我们在解读伍尔芙的“雌雄同体”观时,既要看到它带有的解构性、流动性和未生成性的诗性张力,也要看到它在各种不确定涵义中滋生的各种阐释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