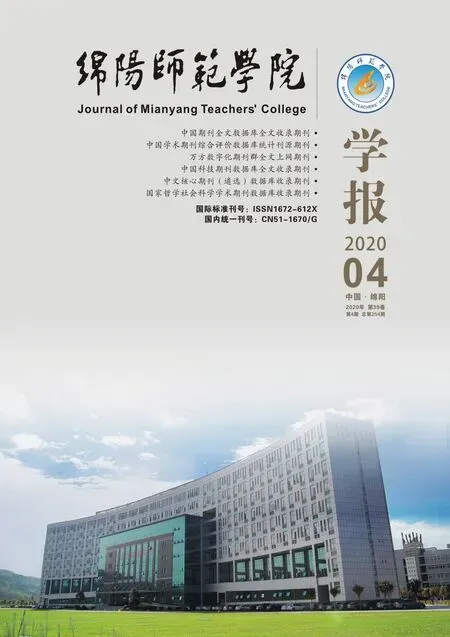被拒斥的“真空”
——论埃科《波多里诺》中的虚构与真实
2020-02-27马心悦
马心悦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200)
一、引言
《波多里诺》(Baudolino)是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创作的第四本小说,出版于2000年。小说讲述了发生在主人公波多里诺(Baudolino)身上近60年来的经历:从公元1155年他被腓特烈二世(Emperor Frederick)带走并收养,到公元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在对自己的经历回顾和重新赋予意义之后,波多里诺重新踏上了寻找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的王国的路途。因为作者埃科是著名的符号学家,所以解读这本小说的研究大都从符号学理论入手,而忽视了小说作为文学文本的独特结构和叙述技巧。因此,笔者试图从叙事结构和内容两个角度入手,阐释小说在真实与虚构交错中形成的独特魅力。
在对小说进行详细分析之前,笔者认为应该先辨析“真空”一词的含义。“真空”作为《波多里诺》这本小说中重复出现的意象,具有象征意义。真空是一片被剥夺主体的空间,然而“空间本身就是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3]310,因而按照上帝和自然的意旨,真空不可能出现。而“阅读小说的基本法则,是读者心照不宣地接受一个虚构约定,即柯勒律治所谓的‘悬置怀疑’”[2]117,在虚构世界中,读者接受作者的设定,并认可这是小说内在的真实,在此基础上进行小说阅读。而在《波多里诺》中,真实与虚构的交织使得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契约被打破,读者无法区分小说中的真实与虚构,于是主体和主体之间的紧密关系被打破,二者之间出现缝隙,而这缝隙就是在小说中作者营造的“真空”所在。
二、叙事结构中的“真空”——两名叙述者和三层视角
在叙述上,除了第一章是波多里诺的日记之外,其余三十九章都由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执行叙述功能。这一视角的叙事主要可以被分为两个时空:第一时空是1204年波多里诺在君士坦丁堡救下尼塞塔(Niketas Choniates)之后随他前往塞林毕亚,一路上波多里诺对尼塞塔讲述自己半生的经历并请求他为自己的故事赋予意义。第二时空是从波多里诺对尼塞塔的自述,即从他被腓特烈二世收养到他逃出助祭的领地这五十多年的历史。为了分析方便,尽管这两个时空的叙述视角之间并没有根本区别,笔者依旧将这两个时空的叙述者分开,将叙述第一时空的叙述者,也就是读者进入小说首先遇见的这名叙述者称为叙述者A;将叙述第二时空的叙述者称为叙述者B。
在叙述者A的叙述时空中,波多里诺在君士坦丁堡救下尼塞塔,并对他讲述自己的经历。这一叙述时空的主要内容是波多里诺和尼塞塔二人的对话,但是这一部分却被作者有意切割,即作为片段被放置在第二时空的缝隙之中,作为注解存在,引导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思考甚至判断。尽管在这段对话中,叙述者A主要作为记录者和观察者出现,但是在引导读者对波多里诺进行判断的时候,叙述者A作为小说中的幽灵却常常附体到对话中的倾听者和评判者即尼塞塔的身上。布斯(Wayne C. Booth)在《小说修辞学》(TheRhetoricofFiction)中认为:“在小说中,我们一旦碰到一个‘我’便会意识到一个体验着的内心,其体验的观察点将处于我们和事件之间”[4]141,即当读者由叙述者A引导进入尼塞塔的内心并倾听他对波多里诺的评判时,作者暂时将尼塞塔变成了叙述者,读者透过他的视角来看待波多里诺讲述的故事。而尼塞塔的视角有一个关键词,即“谎言”。“波多里诺让他惊讶的是,不管他嘴里说什么,总是偷偷瞥和他对话的人,像是在警告他们别把他这个人当真。”[3]13从听到波多里诺的故事开始,尼塞塔就在怀疑波多里诺是个骗子,这种怀疑笼罩了叙述者A叙述的整个时空。小说的结尾有一段这样的对话:“你确认他的故事是真的吗?不确定,我知道的一切都出自他的口中,就像我也从他的口中得知他是一个骗子一样 ”[3]531,尼塞塔接受了帕夫努吉欧(Paphnutius)给出的建议,将波多里诺的故事看作是作家的虚构而非历史的真实。但是从另一方面进行考虑,尼塞塔得出结论的唯一依据是波多里诺的讲述,证据或者证人在二者的对话中从未出现。
经由前面的论述可知,第一叙述时空中的三层视角即叙述者A叙述尼塞塔与波多里诺对话、尼塞塔倾听并评判波多里诺的故事、波多里诺的叙述。这一叙述时空的核心在于波多里诺的讲述是真是假。在波多里诺的叙述中,的确有一部分被他自己承认是谎言,而尼塞塔恰恰基于这一部分而指认波多里诺是骗子:“你告诉我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骗子,而你认为我会相信你。你要我相信,除了我之外,你对所有人都说了谎 ”[3]40,即尼塞塔对波多里诺的指认是基于波多里诺承认的虚构。这里就引发了一个著名的逻辑上的“说谎者悖论”,即如果将“说谎者”定义为说每一句话都为假的人(即尼塞塔对波多里诺发出指控的依据),那么当说谎人讲述他所说的谎言的时候,谎言便成为了真实,“一个骗子否认的时候就代表承认 ”[3]44,而波多里诺承认虚构的事物(如圣杯、约翰王的信)又被确认是虚假的,那么基于他的谎言而认为他讲述的故事全部是虚构则成为一个悖论。而如果不将波多里诺定义为每一句话都为假的骗子,则尼塞塔对波多里诺的怀疑又无法成立,即波多里诺讲述的故事可以为真。又因为波多里诺讲述的故事并没有任何证据,即无法证实或证伪,所以尼塞塔的怀疑同样无法被证实或证伪。“虚假对任何建立真实理论的意图提出质疑 ”[5]152,波多里诺的骗子身份成为小说最大的谜团,它包裹着无数的谎言,却始终存在于迷雾之中。因此在第一时空中,因为作者独特的叙述结构和设计上的多重视角,读者对波多里诺的任何评价和判断都被悬置。
而在叙述者B的时空中,他讲述了波多里诺在遇见尼塞塔之前的经历,这一部分是小说叙述的主体。第二时空尽管与波多里诺在第一时空中对尼塞塔讲述的故事几乎完全重合,但是叙述者却并不是波多里诺自己,即叙述视角并不是由“我”来开展。考虑到波多里诺对尼塞塔讲述的目的是让他帮助“重组遗失的过去 ”[3]11,并为他的故事“找出意义 ”[3]12,而讲述本身就是一种赋予意义的方式,因此可以说在第二时空中叙述者B代替尼塞塔完成了这个赋予波多里诺故事意义的行为。不论叙述者B是何身份,由他者赋予波多里诺意义这一行为象征了波多里诺作为故事第一讲述者主体性的消弭,作者取消了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进行整合和评价的能力,而将这一任务交由叙述者B进行。第二时空的存在基于波多里诺这位主体,而叙述者的转换则将这一时空存在的基石抽离,波多里诺在第一时空中是自己故事的讲述者,而在第二时空中却成为了“演员”。尽管叙述者B的叙事营造了一种完美的戏剧性幻觉,但是故事讲述者(波多里诺)和叙述者B的分离却将这一戏剧性幻觉打破,提醒读者叙述者B的叙述行为不过是一种在原始材料之上加工的“虚构”,波多里诺作为第二时空的真实经历者的主体性被隐去,真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被模糊,叙述者B不再可靠。
尽管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虚构,但是在小说的世界之中,读者依旧会在阅读中去寻求一种真实,即区分真实和谎言。而在对小说叙事结构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在《波多里诺》这本小说中,作者利用精心设计的视角转换和多层叙事,使读者与故事主体之间的距离被“真空”隔开,并将小说叙事中的真实和虚构混淆。读者没有任何能够确认真实的凭借,于是他们被抛入到作者精心设计的轨道之上,可以进行无数种猜测却只能顺着小说的既定轨道前行,探求“真实”的努力变成一种徒劳。
三、内容上的“真空”——故事的三层同心圆
《波多里诺》这本小说的主要线索是波多里诺对祭司王约翰王国的追寻。这一意象首先出现在奥托主教的口中:“在教皇恩仁三世的任期之内,带着亚美尼亚大使前来晋见教皇的叙利亚主教贾巴拉对教皇表示,在接近伊甸园的远东地区存在着一个祭司王约翰的王国,虽然他是聂斯脱利教派邪说的信徒,但毕竟也是基督教的国王。而他的祖先就是朝拜初生的耶稣、同时身为国王和祭司、却拥有非常古老智慧的东方贤士 。”[3]47因为主教认为腓特烈大帝在还有一个教皇发号施令的地方只能算半个皇帝,所以他要波多里诺许诺哪怕以编造的方式也要把腓特烈的注意力引向东方,他认为“以伪装的方式为自己认为真实的事情作见证,那是一种善行,因为那是为存在或已经发生的事情补充不足的证据 ”[3]58。在主教的要求之下,波多里诺开始着手编造祭司王约翰的信,在信被左摩西复制并传播出去之后,他又虚构了“葛拉达”,并利用“葛拉达”促使腓特烈二世允许他出发前往祭司王的国度。在腓特烈二世意外身亡后,受“不可抑止的欲望 ”[3]332的驱使,波多里诺一行十二人踏上寻找祭司王的王国的路途。经过长途跋涉,他们进入“妖怪的国度 ”[3]351,并最终踏上了助祭的土地,波多里诺虚构的怪物和奇景在这片土地上成为了真实。然而白汉斯人的入侵终止了波多里诺的旅途,在被狗头人俘虏后,他们乘着洛克鸟飞离,并降落在君士坦丁堡。在指认“诗人”是杀死腓特烈二世的凶手之后,波多里诺杀死了“诗人”并同他的伙伴们分开。之后波多里诺无意间救下尼塞塔,并开始对他讲述自己的经历。最后在帕夫努吉欧的提示下,波多里诺发现自己才是杀死养父的凶手,在隐士柱上赎罪和冥想了一年后,他决定重新出发,继续寻找祭司王的国度。
但是在对小说内容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小说内容的深层结构由三个同心圆构成。如果把小说内容看作是三个层层相套的圆,那么这三个部分分别为:最外层是作为历史小说的与小说外部世界相连的理性世界,中间虚构与真实相互转换混淆的“真空”地带,而作为波多里诺的欲望中心却从始至终从未出现的祭司王约翰的国度即“空白”世界则处于最中心的位置。下面笔者将对这三个世界分别分析并阐释他们之间的联系。
第一层是理性世界。理性世界有两个特点。
其一,波多里诺的虚构被确认为幻想。在助祭的土地出现之前,即小说前五分之三的内容中,祭司王约翰的王国一直是作为波多里诺的幻想而存在的,小说细致地描述了波多里诺是如何虚构祭司王的信和“葛拉达”的:信上写的是他和朋友们的幻想,而“葛拉达”只是他父亲去世后留下的木碗。又因本书出版于2000年,可以预设埃科在写作时的目标读者是经过科学教育的现代人,读者清楚祭司王的王国和这片国度上的奇景在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
其二,其中的人物与事件同真实世界一一对应。在理性世界出现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历史中取材,比如腓特烈二世和亚历山大城的修建,而故事的发展脉络也基本与史实对应。综合上述两个特点,可以说理性世界中的叙述遵循了历史小说的模式,并可与真实世界对应。
第二层是“真空”地带,这部分内容主要有三个特点。
其一,波多里诺的虚构成为了真实。助祭的土地出现之后,波多里诺虚构的怪物和奇景都在这片土地上成为了真实。在祭司王约翰的信中,波多里诺提及了这片土地上的奇景:“那地方必须住有大象、单峰驼、骆驼……人头马、长角的人、羊足人、人头羊、侏儒、狗头人、四十肘高的巨人、独眼人。”[3]147发自伊甸园的森巴帝翁河流滚着石块和沙尘,长着四条腿、只存活在火焰中的大蛇也生活其中。而在进入助祭的土地之后,他们见到了和虚构中一样的森巴帝翁河,遇见了蛇怪,萨提洛斯人人头羊身,俾格米人是侏儒并且射鹤为生,独眼巨人和狗头人也一一出现,波多里诺的虚构在这个世界中真实存在。
其二,外界的理性世界在这里成为了虚构。“真空”地带不光是一个从虚构中走出的世界,还是一个夹在真实和空白之间的“真空”地带,不仅波多里诺的虚构在这里成为了真实,外在的理性世界也在这里变成了虚构。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既不知道理性世界的存在,也不能确认祭司王王国的存在,在这里现实和虚构交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真空”。助祭的土地上的一切规约都建立在对这个世界之外的虚构的知识的了解之上,比如他们的社会建构基于约翰王王国对他们的规定,可故事从始至终这个王国或者任何来自那里的人都没有出现,也没有任何人真正去过这个王国,可以说他们的社会建立于传言之上。另外,从波多里诺对助祭讲述外界的景象这一段叙述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我也编造了一些故事,为他描述我从来不曾造访的城市、我从来不曾参与的战役、我从来不曾占有的公主 ”[3]412。尽管从主观出发,波多里诺的编造是为了为助祭的生命重新点燃活力,但是不可否认,外界的理性世界在波多里诺的口中成为虚构并作为“真空”地带中的“知识”存在。
其三,当理性世界入侵“真空”地带时,“真空”地带瞬间消失。白汉斯部落作为千年以来对这个世界的威胁一直存在于“真空”地带人们的想象之中,但是他们甚至不知道白汉斯人长什么样子,然而这个建立在想象中的威胁作为知识却是存在的。当白汉斯人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之中,作为理性世界的一部分入侵助祭辖地时,就像是一根针扎破了两个世界之间隔着的薄膜,这片土地和之上的所有怪物全部以一种极其荒诞的方式消失掉了,被上帝拒斥的“真空”瞬间被空气填满。
当然,尽管“真空”地带在小说后半部分即波多里诺到达助祭的土地时集中呈现,但是助祭的土地并非是唯一的例子。在小说第十八章即叙述波多里诺的第二段爱情经历时,“真空”地带作为波多里诺追寻行为背后的幽灵曾显露出它的面目。波多里诺的孩子变成了一个畸婴,“就像祭司王约翰王国里那些我们想象出来的物种一样……我的儿子是大自然的一个谎言……我的精液也制造了一个谎言,一个死去的谎言 ”[3]238。在理性世界中,“真空”地带作为谎言和畸婴以死去的方式令波多里诺顿悟,他觉得这就是他的命运,“如果你继续编造谎言的话,就编造一些一开始不真实,但是最后会成为真相的东西 ”[3]239,“真空”地带的突然闪现激发了波多里诺寻找祭司王约翰的动力,也成为小说中“真空”存在的一种暗示,预示着虚构和真实在主人公波多里诺的身上交织,他们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将被彻底模糊。
第三层是纯粹的“空白”世界,即波多里诺追寻的核心意象祭司王约翰的王国从未出现,并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存在。在整个小说中,祭司王约翰只存在于虚构和幻想之中,他的养子助祭也在怀疑这个王国是否只是一个谎言。而在小说结尾,波多里诺决定重新出发去寻找这个王国,但他的传奇也到此为止。正因为这个王国的不在场,波多里诺的欲望对象被转移至“真空”地带上,这个不存在的核心保证了“真空”存在的可能性,追寻的空白使得波多里诺的行为成为永恒并注定毫无结果的追寻。然而波多里诺身上浓厚的悲剧性却被“真空地带”的存在削弱,他成为了被抛入“真空”的堂吉诃德。
四、结语
小说内容中的三层同心圆使得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被模糊,于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试图追求真实却一无所获。结构和内容中的“真空”相互呼应,形成了小说独特的美学特质。埃科在这本小说中推翻了传统小说写作的契约,使得小说整体被笼罩着一种虚幻的谜团。在《悠游小说林》(SixWalksintheFictionalWoods)中,埃科曾经分析过人们接受现实世界和小说世界的不同,“我们接受现实世界的方式,与我们接受虚构世界的方式并无二致……其中分野在于信任的程度 ”[2]139,现实世界中的一个证据或许可以推翻庞贝古城毁灭的日期,然而虚构世界中包法利夫人的死亡却是必然事实,无法否认。埃科认为,“我们之所以阅读小说,在于小说给了我们一种生活在真实观念毋庸置疑的世界里的愉悦感受 ”[2]140,而《波多里诺》则有意打破了这种幻觉。在信任崩塌的情况下,读者不光被抛入“真空”,还会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一种荒诞的现实感。因为现实中绝对真实的空缺使得读者试图在小说中寻求真实,而埃科的玩笑和颠覆却像是在嘲笑这种逃离的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