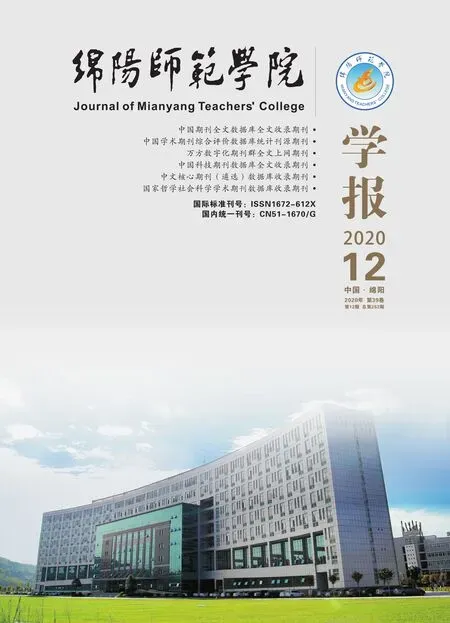王世贞的诗、书、画相通说
2020-02-27江婷
江 婷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241)
诗、书、画发展到明代,有着丰富的创作实践,形成了诗、书、画一体的文人画形式;明代也有着深厚的理论积淀,在对前代理论进行不同角度的研究时,也在不断产生新的著述。明代文人对诗、书、画的深刻认识使得他们能够进行横向地比较论述,发现三者的异同之处。王世贞作为明代中后期主持文坛二十多年的文人,涉猎广博,著述宏丰,于诗文、书法、绘画的创作以及欣赏都有所得,在此基础上,他尤其注重三者的交叉论述。童庆炳关注到了王世贞对于诗、书、画相通的论述,但是只列举了两条材料[1]1395,其他学者偶引王世贞相关论述来论证“书画相通”理论,但都没有针对王世贞的诗、书、画相通说展开系统性的分析。本文拟从意象思想出发,从体用、品评、创作三个角度研究王世贞的诗、书、画相通说。
一、诗、书、画的体用
从诗、书、画的价值来看,王世贞对这三者有清晰的排序:“画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绝矣;书力可八百年至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绝矣;唯于文章更万古而长新。”[2]7053这一句话基本概括了王世贞对此三者重要性的认识,三者之中,最为重视诗文,次而书,最末为画。王世贞从体用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书画可临可摹,文至临摹则丑矣,书画有体文无体,书画无用文有用,体故易见,用故无穷。”[2]7053王世贞将书画归为一类,诗文单独被拈出来,书画有体而无用,诗文无体而有用。书画相比诗文来说,更为重体,学习时可以从临摹其象入手,摹写其象进而领略其意。诗文则不然,相比书画的具象而言,诗文之象是抽象的,不能直接临摹,而更重其意。
这种观点是建立在王世贞对书画本质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书画都是象的艺术。王世贞辑录了《古今法书苑》《王氏画苑》,收录了前代重要的书画理论。他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从意象思想角度探讨了书、画的源起。从书“源”来看,在《古今法书苑》的序言与后跋中,王世贞明确表达了书法是意象的艺术:“羲画八方,人文所由萌,圣人取夬以代结绳,颉窥鸟迹而尽泄厥灵。爰析六书,指事、象形,及有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旁出异名,以察百官,以治兆氓。赫赫六经,是冯是征,述书源第一。”[2]3445书产生于仰观俯察的取象活动之中,而具体的书形则是通过“六书”的方法产生。王世贞关于画的源起的讨论集中在《古今名画序》中,在此文中他猜测画出于八卦,是“形”的艺术:“考之画曰形也,一曰畛也,象田畛畔也,又曰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然则伏羲之画八卦也,其画之所由防乎?画之通于画也,卦之为挂也,亦可思已。自六书之学行而其言曰画,不过其一耳,然而不然,盖颜光禄之训曰:图理而为卦也,图识而为书也,画所谓图形,鼎立而三者也。”[2]3449二者从本源上来说,都是从观物中取象而成,所不同者,书以“六书”的方法形成不同的字形,绘画则直接从自然中取象,“则悉取九牧之贡金而为鼎,而象其州之山川百物”[2]3450。
王世贞在《古今名画苑序》中从体、用的角度更为细致地论述了书画关系,其结论是:“是故,画之用狭于书,而体不让也。”[2]3452“体”在先秦典籍中的拟象意义指的是卦体,《周易略例》谓:“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则一体之变,由斯见矣。”[3]409王世贞也从这个角度理解书画之“体”。画体为“形”,“考之画曰形也,一曰畛也,象田畛畔也,又曰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书之体为圣人之言:“其识者曰,圣人之立言,与书相表里者也,言无体以书为体。”[2]3450圣人之言出于字,字源于俯仰取象:“夫画法之源流,自庖羲氏观天地人物,始作易以垂象焉。及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初作书。象形而有文,形声相益而有字。字孳浸多,著于竹帛而有书。”[4]1即书画之体都从取象中来:“且夫有仓颉,则有史皇神禹之告成功也,而见于书者,若钟若调,戈若峋蝼之石,而至于画,则悉取九牧之贡金而为鼎,而象其州之山川百物。”[2]3449-3450但是书画之用有所区别:“书之用圆,圆则广;画之用方,方则隘。”[2]3450书可以用在政治、观察、纪录等方面,“今夫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八荒,以同六籍以纪,皆书为之也”[2]3450。但是画的用处较为狭隘,“神奸而置之魏阙之上,不亦略于书而详于画哉”[2]3450,用以画出形象,辨识能害人的鬼神怪异之物。尽管“用”的范围有所分别,但是用的效果能够相通,能达到物我相通、情景交融的效果,如:“今夫睹古圣喆之懿,宁不翼然而思齐者哉?其于淫慝,宁不懊然而思戒者哉?玩仙释之逍遥,而不寄惊于尘外者哉?即小乘报应之微,而不惕然而内自讼者哉?山郁然而高深,水悠然而广且清,而不悦吾之性灵哉?夭乔飞走之若生,而有不动吾之天机哉?”[2]3450在书画的比较之中,“意”与“象”的关系又有所不同,论书强调象在意先,倡导学习魏晋书法,重新重视象在书法中的本源地位,“书法至魏、晋极矣,纵复赝者,临摹者,三四刻石,犹足压倒馀子”[5]286。论画则根据不同的题材处理意象关系,如“人物以形模为先,气韵超乎其表;山水以气韵为主,形模寓乎其中,乃为合作。若形似无生气,神采至脱格,皆病也”[2]7055。从中见出王世贞复古思想在书画领域中的不同倾向,王世贞有自觉的历史意识,认为书法有时代优劣,应该取法前朝,尤其是纠宋书“尚意”之偏而应该宗法魏晋;论画则有所调和,关注不同绘画题材中的优点:“书法故有时代,魏晋尚矣。六朝之不及魏晋,犹宋、元之不及六朝与唐也。画则不然,若魏晋,若六朝,若唐,若宋,若元,人物、山水、花鸟、各自成佛作祖,不以时代为限。”[2]7054-7055可见王世贞意象思想之灵活细致。
诗文则与书画不同,诗文之体不可见,王世贞论书画强调具象,而诗文之象与其有别。自然之物象不能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呈现在诗文作品之中,而是经过诗人的想象创构之后成为拟象。《周易·系辞上传》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6]576自然之象幽深难测、造化无穷,诗人通过主体想象力的发挥,神与物游,虚实结合,创造出与主体情意交融的整体。王世贞对这种创造的过程有精炼的描述:“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7]39通过创作者主体的“才”与“思”对自然之象进行提炼后,创造形成具有“格”与“调”的拟象,融入了主观情思,完成对形式的超越,最后呈现出完整的审美境界。王世贞论书强调由象入意,论画则根据不同的题材处理意象关系,论诗文则欣赏“意象协矣”的圆融境界。他在为汪淮所作的《汪禹义诗集序》中称汪氏于诗能“意象协矣”[8]卷四十三。在《青萝馆诗集序》也赞赏盟友徐中行的诗“意象合矣”[2]3320。诗文要达到“外足于象,而内足于意,文不减质,声不浮律”[2]3147的谐和境界,达到意与象合、物我交融的融适之境。
在此基础上,王世贞从体用方面综合比较了诗、书、画:“书画可临可摹,文至临摹则丑矣,书画有体文无体,书画无用文有用,体故易见,用故无穷。”今道友信的解释比较契合,他认为王世贞所言之“体”是“有形的物体”,其“用”是“意义作用”:“书画是有形的物体,故易见,与物体共存亡,文章则以意义作用为主,装载功用的文体,代代变化,其功用本身却永无止境。同是艺术,书画与诗文却有这样的差异。”[9]54书画之体为具象,诗文之体为拟象,其用有所不同,但是三者相通无碍。
二、诗、书、画的创作
在对诗、书、画的价值进行论述时,王世贞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书画可临可摹,文至临摹则丑矣”,这是三者在创作中的异同。从创作方法及取法对象看,文章不能临摹,其体不可见;而书画都是“象”的艺术,不论是自然之象,还是前人之作,都有体可以临摹。王世贞对诗、书、画的宗法对象持不一样的看法。王世贞论诗倡导复古盛唐,论书则尚魏晋,二者所要反对的共同对象是宋代之风,反对宋诗受理学影响而抛弃以“象”达“意”的路径,反对宋书的尚意倾向而导致“意”与“象”离。但王世贞画论中的复古意味并不强烈,于各个时代皆有所取,更能见出王世贞对不同艺术形式的把握。
除了取法对象不同,诗、书、画在创作过程中还需处理取“自然之象”与“古人之意”的关系。就书法而言,王世贞认为应该由“象”入“意”,但是就绘画而言,王世贞的态度则没有那么一以贯之。文字源于象,在发展过程中渐渐符号化,对于书法家来说,符号化的书失去了仰观俯察得来的象之生气,所以王世贞强调书法应该由象入意,侧重于书的“象”。而绘画则与书法不同,画家直接面对自然之象,象的生气直接展现在画家眼前,不需要再去强调“象”的存在感,所以画家可以在深味前人之意的积累上再灌注己意。王世贞论诗歌的重点不在“形似”问题,而认为应该要“假象见意”。明代诗歌因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如唐宋派等人认为文章以明道为主,作诗文应直陈胸臆,企图在诗歌创作中抛去物象而直陈其理。王世贞在《明诗评》后叙中直接批评唐宋派之王、唐二人:“黜意象,凋精神,废风格。”[10]100认为王、唐过于强调主体之精神,为了突出理而损害文,尤其废黜了文中之意象、风格。可见,王世贞对诗、书、画创作过程中的意象关系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在诗、书、画的具体创作过程中,王世贞注意到不同艺术创作过程中意象的瞬间性特点。在不同的艺术中,创作主体发挥的时间节点都不一样。总体来说,艺术创作过程中,思维过程都是瞬间的,这与“知觉”的思维过程并不一样。萨特认为:“在知觉中,认识是缓慢形成的;而在意象中,认识是瞬间性的。”[11]28朱志荣关注到了意象创构过程中的瞬间性特点:“意象的创构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瞬间达成的,是主体以虚静之心在瞬间即景会心,是一种当下的直觉活动,审美经验在其中起着支配作用。”[12]王世贞也认识到了意象创构过程中瞬间性的特点,并且更为细致地区分了这三种类型中的用意时间之不同。他在《艺苑卮言》中说:“书道成后,挥洒时,人心不过秒忽;画学成后,盘礴时,人心不能丝毫;诗文总至成就,临期结撰,必透人心方寸。以此知书画之士多长年,盖有故也。年在桑榆,政须赖以文,寂寞不取资生,聊用适意,既就之顷,亦自斐然。乃知欧九非欺我者,少学无成老而才尽,以此自叹耳。”[2]3451-3452从时间长短看,在技艺成熟的基础上,书法在创作过程中,物我交融的时间只需“秒忽”,绘画稍长。二者在面对具体的感悟对象时,瞬间以情会物、迁想妙得,获得创作过程中的畅神感受。王世贞戏言,这或许就是书画家长寿的原因吧。而诗文创作过程中,审美经验的积累更为重要,主体对“象”加以提炼,还需要经过心意的酝酿,在“临期”的高峰中表达出来。尽管不能立刻物与神会,需要调动以往的审美经验,但是诗文耗费心力的创作所达到的效果也更为深刻,能够“透入心方寸”,也呼应了“唯于文章更万古而长新”的价值高度。针对这一点,朱志荣有中肯的论述:“所谓的瞬刻永恒,实际上是指意象创构超越了现实的具体时间,体现主观的时间,并且与具体空间及其背景相结合。在审美活动中,主体的高峰体验,肯定会有一个时间上的点。高峰体验具有偶然性和突发性的特点。妙悟正在于此刻瞬间。”[12]
诗、书、画在创作技法上也可互相借鉴。书画这两种艺术所观都是自然之象,观物而取象,然后通过书和画的不同技法表现出来。在对自然之象进行体悟的过程中,书家和画家有各自的取象方式,形成不同的技法,如书家所创的飞白、篆籀等,画家所塑造的“高峰坠石”“百岁枯藤”等。技法来源相同,所要表现的对象相同,二者的技法当然可以互相借鉴。王世贞就从技法方面列举了书画互相借鉴的多种用法:
语曰画石如飞白木如籀;又云画竹干如篆枝,如草叶,如真节,如棣。郭熙唐棣之树,文与可之竹,温日观之葡萄,皆自草法中得来,此画与书通者也。至于书体篆糠如鹄头、虎爪、倒薤、偃波、龙凤、麟龟、鱼虫、云鸟、鹊鹄、牛鼠、猴鹦、犬见、科斗、之属,法如锥画、沙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高峰坠石,百岁枯藤,惊蛇入草,比拟如龙跳虎卧,鼓海游天,美女仙人,霞收月上及览韩退之送高闲上人序,李阳冰上李大夫书,则书尤与画通者也[2]7062-7063。
绘画可以借鉴诗文“赋比兴”的创作方式。王世贞《古今名画苑序》中说:“自五代而上,其画有赋者,有赋而比者;五代而下,其画有赋者,有赋而兴者,拟于诗,则皆风雅颂之遗也。”[2]7062-7063赋比兴是文学意象创构的重要方式,通过比附与兴象的方式托物寓情、婉言胸臆,言有尽而意无穷。王世贞在批评汉赋时点出了“象”的艺术创作方法上承屈原,《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洛神赋》精彩之处虽然在于赋中之“意”,但是汉赋假象见意的创作方法本于屈原:“其妙处在意而不在象,然本之屈氏‘满堂兮美人,忽与余兮目成。’‘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变法而为之者也。”[7]92可知,“赋”的艺术与象紧密相关。王世贞认为“比”和“兴”有所差别,比为比类,兴为意兴。王世贞在《何大复集序》中评何大复诗说:“其缘情即象,触物比类,靡所不遂。璧坐玑驰,文霞沦漪,绪飙摇曳,春华徐发,骤而如浅,复而弥深。”在评论王维的诗歌说:“凡为摩诘体者,必以意兴发端,神情傅合,浑融疏秀,不见穿凿之迹,顿挫抑扬,自出宫商之表可耳。”[7]80可见,五代之前“有赋而比者”,更为重象之比类;五代之后,“有赋而兴者”,更为注重意兴之发挥。这也跟绘画题材相关,“大抵五代以前画山水者少”,而以人物画为主,人物画重形模,山水画重气韵。在《重刻古画苑选小序》中王世贞重提了画与诗文的相通:“故夫画之用,饶才情者以为无声之诗,而爱纪述者以为无文之史,良有意也。”[8]卷五十四
三、诗、书、画的品评
王世贞作为后七子之首,在文坛享有极高的声誉,诗文评论在明代文坛有较大影响。王世贞于书画虽不能创作,但是作为收藏家,他与当时书画名家交往密切,或鉴赏作品,或赞助创造,品评也有独到论述。特殊之处在于,王世贞在品评诗、书、画时,经常将三者并举,论其相通之处。王世贞在推举诗、书、画之典型时,就同时列举三者:
坡老言诗至杜工部,书至颜鲁公,画至吴道子,天下之能事毕矣。能事毕而衰生焉,故吾于诗而得曹、刘也,书而得钟、索也,画而得顾、陆也,为其能事未尽毕也。噫,此未易道也[5]377。
吴中如徐博士昌穀诗,祝京兆希哲书,沈山人启南画,足称国朝三绝[7]331。
吴中人于诗述徐祯卿,书述祝允明,画则唐寅伯虎。彼自以专技精诣哉、则皆文先生友也,而皆用前死,故不能当文先生。人不可无年,信乎文先生盖兼之也[2]3931。
书法至魏、晋极矣,纵复赝者,临摹者,三四刻石,犹足压倒馀子。诗一涉建安,文一涉西京,便是无尘世风,吾于书亦云[5]495。
针对具体的人物,他也是从诗、书、画三方面进行综合性评价。王世贞对文徵明评价极高,认为其画有意味,其书有姿态,其诗有韵味:“文太史画,闲窗散笔,在有意无意间,是以饶意;其书在中年,是以饶姿;诗不作应酬语,是以饶韵。此十帧可谓文氏碎金,置山房中,敌吾家琳琅矣。”[5]377在比较赵孟頫与文徵明时,也是从诗、书、画三方面进行评价:“余尝谓吴兴赵文敏公孟頫,风流才艺,惟吾郡文待诏徴明可以当之,而亦少有差次。其同者,诗文也,书画也,又皆以荐辟起家。赵诗小壮而俗,文稍雅而弱,其浅同也。文皆畅利而乏深沉,其离古同也。书,小楷赵不能去俗,文不能去纤,其精绝同也。行押则赵于二王近,而文不能近,少逊也。署书则文复少逊也。八分古隶则文胜,小篆则赵胜,然而篆不胜隶。画则赵之入唐宋人深,而文少浅,其天趣同也。其鉴赏博考复同也。”[13]卷四
在具体评价标准方面能见出王世贞意象思想的体现,他在品评诗、书、画时,“古雅”“有意无意”以及“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圆融境界是三者的相通之处,“象外意”则是三者有无穷回味的原因。
首先是“古雅”。“古雅”说是王世贞复古思想在诗、书、画领域中的体现。王世贞虽没有言明“古雅”的内涵为何,但是从具体品评中可看出与意象密切相关。
论诗文的古雅,欣赏其中流动之意:
《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长沙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张潘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处[7]91。
论书法之古雅,深味其中幽深无际的趣味:
此表小法楷法,十各得五,觉点画之间真有异趣,所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昔人故不欺我也[5]70。
论绘画之古雅,从柴桑之景见前人之意:
吴兴钱选舜举画陶元亮《归去来辞》独多,余所见凡数本,而此卷最古雅,翩翩有龙眠、松雪遗意,第少却“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一段柴桑景,当是兵焚时不免破镜耳[5]533。
其次是“有意无意”。王世贞论诗、书、画之优劣时,“有意无意”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创作者在创造过程中,触物感兴,于“有意”处创造,发挥主体能动性,灌注主体精神。在技法上不穿凿模拟,不须用力过猛,“无意”造之,浑然天成。
“有意无意”是文章之妙用:
王武子读孙子荆诗而云:“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此语极有致。文生于情,世所恒晓。情生于文,则未易论。盖有出之者偶然,而览之者实际也。吾平生时遇此境,亦见同调中有此。又庾子嵩作《意赋》成,为文康所难,而云:“正在有意无意之间。”此是?辞,料子嵩文必不能佳。然有意无意之间,却是文章妙用[7]121。
就书法而言,王世贞同样欣赏“有意无意”之作:
昔人评赵吴兴“如丹凤脚霄、祥云捧日”,余谓正书不足以当之,独以尺牍行草得山阴父子撅拓法,而以有意无意发之,盖不负此评耳[5]101。
绘画作品中若有意若无意的审美意味如西子轻妆:
云林生平不作青绿山水,仅二幅留江南,此其最精者也。若近若远,若浓若澹,若无意若有意,殆是西施轻妆临绿水,不胜其态,仓卒见之,靡不心折[5]474。
最后是要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圆融审美境界。王世贞的《艺苑卮言》受严羽影响,在诗学上推崇盛唐诗歌:“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14]欣赏诗文作品空灵剔透、含蓄蕴藉之美。诗文的境界相通于书画,诗歌能揭示画的真味,画能传达诗歌的意境:“王右丞诗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是诗家极俊语,却入画三昧。黄子久《江山胜览图》是画家极秀笔,却入诗三昧。”[5]472王世贞在跋吴地殳生之画时感慨其画达到了圆融无迹的境界:“昔人论诗‘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噫嘻,岂惟诗而己哉,殳生其勉之。”[5]579鉴赏书法时,王世贞欣赏“无意”之作而否定“有意”之作。有意则伤:“王雅宜宠小行五绝句,是初变旧体者,遒骨颠姿,与冶态并见,而不免伤有意,然尚足压卷。”[5]218无意乃佳:“作书有全力而无先意,乃得佳耳。”[5]100“有意”能凸显个人风格,显示主体精神,但是留有痕迹,伤于刻露,“无意”的圆融姿态,更能显出书之韵味。
在此基础上,王世贞还欣赏诗、书、画的“象外之意”。诗、书、画都能于象外得意,突破物象本身的局限,离形得神,把握艺术作品的精神力量,使欣赏者回味无穷。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评论梅圣俞曰:“思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其诗文观点受严羽影响,诗歌之韵味不止在象内,不仅是对景色的客观摹写,还应该饶有余味。同样,他在品评王履吉的书法作品时,也注意到其“超轶象外”的特点:“第二十三册《庄子·逍遥游》,王履吉之从孙慎修书也,《逍遥游》横肆奇诡,超轶象外,而以圉圉未倚之笔纪之,殊不相当也。”[5]246王世贞对绘画中“意”的欣赏,体现为对“象外意”的体味,王世贞尤为肯定赵孟頫兼有“精密”与“象外意”的特点,如评《赵松雪画山水》:“赵承旨书画垂三百年,赏鉴家愈宝购之,以其能集大成也。此图布景设色极精密,而时时有象外意,不作残山剩水一笔,当于辋川、营丘间求之。”[5]531评《长江叠嶂图》:“赵文敏公此图冲澹简远,意在笔外,不知于李营丘如何,骎骎欲度荆、郭矣。”[5]470以及欣赏文徵明画中的象外意,认为文徵明的绘画“丹青游戏,得象外理”[2]3929,品评具体画作时认为“此三十六纸真待诏得意笔,闲窗散怀,出倪入赵,极有意无意之妙”[5]495。于明人还欣赏唐寅:“吾尝以七月望登赤壁,酒酣耳热,歌坡老所作二赋,飘然欲仙者久之。然坡后赋所纪及伯虎此图,俱与景不甚似,当相赏有象外意耳。”[5]555王世贞对诗、书、画三者的鉴赏不仅停留在物象本身,还能超越其艺术门类、艺术题材、艺术材质的局限,鉴赏三者超然的象外之意,在审美感受上相通。
王世贞的诗、书、画相通说是建立在他对各个艺术门类都有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王世贞出身名门,家有财资,加之吴地文风兴盛,王世贞得以与书画名家交往。参与文学复古运动,继李攀龙之后成为后七子之首,执掌文坛二十多年,对诗、书、画的创作与欣赏都有自己的审美标准。意象思想贯穿其中,王世贞从意象角度对诗、书、画的本质、创作和欣赏都有细致的论述,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三种艺术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