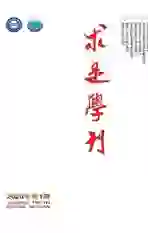“传统”“民间”的化用与创造
2020-02-26王学谦
摘要:莫言新作《锦衣》《故乡人事》是其创作固有的对传统的创造性发挥,既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之中,又融入了莫言个人的创造性。《锦衣》是对传统戏曲美学趣味的亲和,同时又加入了莫言个性的点睛之笔,融入了现代体验。丑角王婆、王豹的充分表演是对传统戏曲的改造。王豹的性格塑造则是对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承续。王豹的性格具有阿Q性格的一面:卑怯。王豹的革命类似阿Q革命。《故乡人事》是莫言的“笔记体”小说,有传统“笔记体”的意味,近似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对奇人异事的记录,也在神韵上沟通了魔幻现实主义;同时融合了鲁迅短篇小说的笔法和神韵,注重白描,更注重人物内心状态,直抵人物内心深处,传统与现代高度融合。
关键词:莫言;传统;民间;鲁迅
作者简介:王学谦,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130012)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0.01.015
2017年秋天,莫言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戏曲文学剧本《锦衣》(2017年第9期),又在《收获》上发表短篇小说《故乡人事》(2017年第5期)。这是他获诺贝尔文学奖五年之后首次发表作品。这五年期间,莫言受到国内外前所未有的关注,他的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比以往急剧增多,他成为媒体的焦点,他的一言一行都成了新闻材料,往往会被迅速传播,成为文坛和社会议论的话题。面对这组作品,我首先想到的是,如果不是莫言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作品就会像小溪流水一样悄悄地过去,就像他以往的那些短篇小说那样,不会引起大家的特别兴趣。因为现在的文坛完全是长篇小说的天下,短篇小说很难引起广泛的文学影响。但问题在于莫言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些作品又是他获奖之后首次发表的新作,这就足以引起社会和文坛的普遍好奇心。文坛和大众永远是势利的,人们更愿意把目光聚焦于成功者的身上。作为莫言的忠实读者,我自然格外兴奋,觉得莫言终于拿出了新作,证明了自己的文学活力和实力。但转念一想,还是应该冷静下来,放弃这种肤浅的心理,认真理解它更为重要,而理解它的最好方式就是回到莫言本身,把它放在整个莫言文学世界之中,放在当代文学的大气候之中,找到一个适合的位置,厘清它的来龙去脉,感悟它的美学品质,这也有助于我们对莫言的深入理解。
一、一次真正的大踏步后撤?
在《丰乳肥臀》之后长达五年左右的时间里,莫言没有发表长篇小说。2001年,莫言拿出他最完美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在《后记》中,莫言说:“《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還不够到位。”①在此,莫言有意舍弃了早期创作中过于浓厚的魔幻现实主义因素,强化了“民间”因素:“突出了猫腔的声音,尽管这样会使作品的丰富性减弱,但为了保持比较多的民间气息,为了比较纯粹的中国风格,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牺牲。就像猫腔不可能进入辉煌的殿堂与意大利的歌剧、俄罗斯的芭蕾同台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不大可能被钟爱西方文艺、特别阳春白雪的读者欣赏。就像猫腔只能在广场上为劳苦大众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只能被对民间文化持有比较亲和态度的读者阅读。也许,这部小说更适合在广场上由一个嗓音嘶哑的人来高声朗诵,在他的周围围绕着听众,这是一种用耳朵的阅读,我有意地大量使用了韵文,有意地使用了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制造出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②仅仅从外形上看,《檀香刑》(也包括后来的《生死疲劳》)的确是大踏步撤退,如果进入它的内里却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这是莫言又一次大胆而勇敢的艺术探险,就如同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一样,充满激情和激进。他对“民间”资源的使用完全是先锋性的探索,而非对传统的归顺。《檀香刑》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大面积、高强度的残酷叙事,那种对家庭伦理、社会伦理规范的瓦解,那种对人心黑暗的深度剖析,那种对历史的彻底绝望,那种人生如戏的深刻虚无感,都无法用“民间”美学和趣味进行诠释,只有放在莫言80年代的先锋精神中才能获得充分的意义和合理的解释。它应该放在《红高粱家族》《欢乐》《红蝗》《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序列之中,是这些作品精神的一次更加淋漓尽致、更加严谨、更加完善的艺术发挥。《檀香刑》不是“民间”化,而是化“民间”,是进入“民间”而超越“民间”,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天才的艺术家往往有着超强的胃口,总是善于吞噬、消化环境变异所提供的各种食物,就如同“铁孩儿”以铁为粮也能够生存、成长一样,莫言将“民间”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血肉,使自己的艺术躯体变得更加强健。莫言所说的“作为老百姓写作”,是对“庙堂”写作的对抗,也是“个人写作”的另一种说法。莫言说:“我想可以大胆地说,真正的民间写作,‘作为老百姓写作,也就是写自我的自我写作。”③“民间”遍地都是,关键的不是作家简单套用一些东西,而是更为个人、积极、艺术的处理能力,这里需要的是作家个人的思想能力和艺术才华。当我们不断使用“民间”去评价作家创作的时候,不应该忽视作家个人的才情和创造。这正如莫言对他自己的家乡高密东北乡的叙述,所有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故乡,为什么仅有少数作家才能真正写出自己的故乡?关键不在于故乡经验,而在于对故乡的体验即艺术处理能力的深度和广度。高密东北乡在本质上是莫言的一个发明。
和《檀香刑》等比较起来,《锦衣》才是真正的撤退,它的步伐要比《檀香刑》大得多。自“红萝卜”以来,莫言一向是以深刻而犀利的怀疑主义见长,天马行空,挑战历史叙事成规、传统伦理成规,“魔幻”是他叙事的有力翅膀或尖锐的利器,在历史与人之间构建一个复杂而巨大的张力,一方面将历史作为一种平台,将人架在上面拷问,另一方面又依托着特定时期的历史状况,在剧烈的颠覆中完成深沉、厚重的悲剧叙事。其“民间”意味也如上述所说,是对“民间”营养的吸收和化用,本质上仍然是浓重的现代性。莫言的话剧《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锅炉工的妻子》很明显是莫言小说一贯的叙事原则的体现。这三部话剧的共同特点是以高度戏剧化的冲突打入人物性格的深处,将他们的灵魂展示在舞台上。但是,《锦衣》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是对传统戏曲和民间美学趣味的皈依。剧本的基本结构是“大团圆”,辛亥革命党人攻克高密县,革命获得胜利,宋春莲与季星官的爱情获得圆满的结局,有情人终成眷属;知县庄有理被炸死,他的儿子庄雄才也被王豹抓获,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确符合中国民间、大众的欣赏口味。人物性格脸谱化、定型化,好人坏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善恶清晰,爱憎分明,民间大众可以像欣赏那些传统戏曲一样,谈笑间就可以评断是非,褒贬善恶。对此,莫言自己相当清醒,他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锦衣》是一部“中规中矩”的作品,是对传统戏曲美学的皈依,是老百姓的民间智慧。①就文体而言,莫言一贯“求新求变”,不断突破外部和自己的叙述规则,大体属于浪漫/先锋精神的体现;就传统而言,莫言的文体属于刘勰所说的“破体”精神的现代升华,突破正统文体,天马行空,并无“宗经”的束缚。《锦衣》是对自己曾经的“破体”的“破”,返回具有悠久传统的民间美学正统,是向民间大众和传统的一次亲和。或许这也是莫言的一次新的尝试和探索吧,既然社会、文坛如此呼唤“民间”、传统,莫言也不妨试验一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表现莫言强大的创作力。
但是,问题也并非那样简单,莫言的文学个性仍然有意无意地投射在剧本中。莫言认为,《锦衣》也有一些和传统戏曲不同的地方,就是增加了丑角份额。王婆、王豹这种丑角在传统戏曲中往往仅仅是走过场、调节戏曲氛围的次要角色,但在这部剧本中却占据重要的位置,有更多的表演内容,变成了主要角色。这种丑角为主的戏剧,让我想起东北二人转。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相比,当代二人转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丑角占据突出的位置。相对于正角的表演,丑角灵活机动,更少束缚,往往具有更大的自由空间,更容易融入作者的丰富体验,也更能适合大众的口味。这种丑角戏好像莫言小说的异常叙述视角——莫言总是善于选择最适合表达自己体验的叙述视角,许多小说都有特异的视角,不仅有儿童、傻子,有各种视角的频繁置换,还有《生死疲劳》那样的动物视角,能达到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仔细品味剧本,王豹、王婆的丑角戏的确是整部剧本最具魅力的地方,它和缓地延续着莫言小说一贯的美学风味,熔铸着莫言更为深沉的艺术力量:对世态人心的拷问,透露着耐人寻味的人性伦理和历史信息——王朝崩溃,动荡混乱,群魔乱舞,人欲横流。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很难彻底抛弃他的“才华”“灵气”,即使在进行一种新的哪怕是与他以往的创作截然不同的尝试、探索,也会不知不觉地露出他的才气和本性。这正如莫言所说:“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应是一种灵气的凝结。在创作过程中可以借鉴,可以摹仿,但支撑作品脊梁的,必须是也不会不是作家自己那点点灵气。只有有想象力的人才能写。”②
最深刻的是王豹这个人物。这是莫言精心创造的一个角色,熔铸着人性拷问、历史思考的深度。他是衙役,又是庄雄才的跟班帮凶,八面玲珑,集社会恶劣品德于一身,用“民间”语言概括他的性格就是打瞎子,骂哑巴,踢寡妇门,踹瘸子腿,挖绝户坟。作为衙役,他跻身官场,深知权力的重量,内心深处涌动着难以遏制的权力饥渴,无时无刻不渴望爬上更高的权力宝座,却又将这种贪婪压抑在内心里,随时能够变成驯服的奴才。最具戏剧性也最具批判深度和力度的是他的两面性格:当他面向权势者的时候,是不折不扣的奴才相,为虎作伥,狐假虎威,尽心尽力;当他面对比他更弱的人的时候,又奸诈狠毒,敲诈勒索,贪得无厌,无所不用其极。在这个意义上,王豹的性格更集中地表达了莫言对人性的反思与批判。在莫言眼中,人性是有限的,无论怎样也摆脱不了动物性的局限。在某种情景之下,人性的凶残超过动物。人把他的凶残融入他所能够触及的一切事物之中,遍布于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又处处用文化的面纱巧妙地遮盖起来,一旦遇到适当的土壤,就很容易流溢出来。在谈到“红高粱”里剥人皮的情节的时候,莫言说:“我觉得,人要是真的坏起来就会超过所有的动物,动物都是用本能在做事情,而人除了本能以外,还会想出许多办法来摧残自己的同类。人一方面可以成佛、成仙、得道,可以是无限的善良,但要坏起来就是地球上最坏的动物。”①莫言喜欢司马迁,他不止一次地引用司马迁的那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发现许多作家“在掩盖灵魂深处的很多东西”,②因而,莫言对鲁迅有着强烈的共鸣,因为鲁迅执着于人的灵魂的开掘,往往探究人的心灵最深处的秘密动向。莫言说的写出人性不可克服的弱点包含着人的恶性欲望。
同时,王豹的性格里也深藏着鲁迅和五四文学所反思、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③“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人们恐怕总不免同时含有这两种性质,只看发现时候的情形怎样,就显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区别来。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④剧本的结尾更值得思考。王豹反水将庄雄才抓获,投奔革命,“弟兄们,大清完蛋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咱们也革命了吧!到新政府里混个小官做!”王豹的“壮举”实际上也构成了对“民间”的颠覆,颇有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的意味,也近似鲁迅的阿Q革命。关于阿Q革命,鲁迅说:“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但此后倘再有革命,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在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⑤这是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但也是对历史的超越性认识。革命自然会吸引更多的民众,但民众的革命和最初的革命者的革命未必是一回事,从而使革命变得更为复杂。在鲁迅和莫言的文学世界里都有深沉的怀疑主义精神,不相信历史会存在着一个绝对的正道,甚至将历史看作无边的混乱和动荡。在最悲观、最深刻的地方,鲁迅把自己当成一个生命的“过客”,历史是无限的存在,个体生命仅仅是短暂的存在,在无限的原野上行走,虽然一直朝前走,却并不知道前边到底是什么,即使知道也无能无力。“黄金世界”也会将“异端”处死,意味着即使最理想的社会也会对个体的存在造成压抑、摧残,历史深处存在着个人无法把握的庞大力量,这种历史大势汇合、交织着难以言说的东西,近乎无法操控的机器,只是响亮地发出自己的轰鸣。莫言的历史叙事被看作新历史主义也就在于此。《红高粱家族》所说的那种“种的退化”即“人的退化”,也暗示着历史的退化。莫言小说的历史叙事从晚清到当代,即使仅仅是那些长篇小说,我们也看不到历史平顺地前行,更多的是芜杂、紊乱与荒凉。《檀香刑》结尾最后一句话是孙丙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戏……演完了……”⑥
有意思的是,和《锦衣》同时发表的还有莫言的诗歌《七星曜我》(《人民文学》2017年第9期),这是莫言与一部分国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不同程度的交往的记录,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莫言的文学趣味——他从国外作家身上发现了自己,也是对自我文学价值的确认。德国已故作家君特·格拉斯的创作风格和莫言有近似之处。莫言很早就谈到他的《铁皮鼓》,似乎有很深的共鸣。许子东说格拉斯如果在中国就变成了莫言。莫言与日本文坛有比较多的交往,大江健三郎和莫言交往已久,算是老朋友,而且当初他曾经预言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还去过莫言的家乡高密,去过莫言曾经居住过的老屋。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也曾经到过莫言家的老屋。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曾经于2008年访华,2009年马丁·瓦尔泽在德国慕尼黑曾经和莫言有过一次对话,对话内容经记者整理发表在《南方周末》上,又被收入《南方周末》主编的《说吧,莫言》中。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北岛对其评价极高,称为当代伟大的诗人,两次坐轮椅参加了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活动。奥尔罕·帕慕克是土耳其作家,莫言曾经与他两次会面。印度裔英国作家V.S.奈保尔,2001年在上海参加了新书《大河湾》的发布会,并和读者做了交流。莫言在《七星曜我》中表达了对其小说《米格尔大街》的喜爱。我推想,莫言把这组诗歌与《锦衣》一起发表未必没有一点考虑。他愿意将自己置身于世界之中,因为这和他的文学理想息息相通,文学是人类共有的,具有普遍的人性和思想。高密东北乡不是封闭的空间,而是开放的精神故乡或文学家园,和他所推崇的福克纳家乡一样,是人类所共有的。这显示了莫言文学一贯具有的世界性与本土性交融的开阔眼光。他立足高密东北乡,同时强调超越高密东北乡,用世界的经典标准处理笔下的素材及其与传统、现实的关系,将自我的本乡本土与世界联通一气。回归传统,并不意味着离开世界。在中国传统与世界文学之间,莫言不想制造障碍,其间没有间隔。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这两种审美力量高度融合在莫言的精神世界之中。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深切地感受到,文化沖突及其压力仍然坚固地存在着,并内化在莫言的内心深处。
二、“聊斋体”与“鲁迅风”的融合
小说《故乡人事》显然比《锦衣》更复杂一些。从标题上看,就显示了莫言一贯的植根故乡的文学特色。从崛起的时候开始,他就一直将故乡当成自己的文学基地。这与其说是他故乡经验丰富,还不如说是他的想象力发达,总是能够最大程度地将自己的叙述收纳在故乡大地之中。各种人和事一旦进入他的故乡也都会变得生气勃勃,活力十足。“我”的视角更是直接把故乡拉到读者的眼前,让你感到自己正在跟着他来到故乡,但是,这个“我”又不像红高粱家族那个童年的“我”那样完全融入其中,而是保持一份冷静、超然。从文体方面看,这种风格的小说大体属于莫言20世纪90年代初期创作的“笔记体”/“聊斋体”小说,其突出特征是以奇人异事为聚焦点,有《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味道,关涉现实,也不乏犀利的灵光,但又与现实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以避免过度的紧张关系,像是纯粹的个人趣味,却又不仅仅拘囿于个人趣味,笔法灵活,不拘一格,又融合着五四以来鲁迅等白话小说的格局、意味,像是小说,也像是散文。和《红高粱家族》《爆炸》《球状闪电》《欢乐》等小说那种汪洋恣肆的感官挥洒不同,其语言内敛,平淡隽永,意味深长,是那种简约的白描笔法。
20世纪90年代初,李洁菲曾经评论《猫事荟萃》(1987)说,这是莫言的另一面,“《猫事荟萃》无疑可以视为对鲁迅语言风格的一个临摹”。①说的就是那种不事张扬的白描语言,鲁迅小说就擅长于这种白描语言。其实,莫言在最初崛起的时候就具有这种语言能力,只是当时人们被他那芜杂、淋漓、恣肆的感觉性语言所吸引,忽视了他那白描语言。他那些写实类型的作品《枯河》《白狗秋千架》《大风》《石磨》《五个饽饽》大致属于这种白描语言,有时虽然繁复一点,但绝对不属于强烈、放肆而芜杂的感受性语言。《透明的红萝卜》的语言大部分也是白描语言,只有少量段落的语言感觉性更强一些。还有,莫言第一部散文集《会唱歌的墙》中也有大量作品是采用白描语言的。他在一些具有先锋意味的小说中往往大量使用让全部感官活跃起来的感觉性语言,而在另外一些作品中却使用白描语言。莫言大部分散文的语言也节制、内敛,显得规规矩矩,大量使用白描语言。从容、沉稳、平实的叙述、描写,间杂着幽默、讽刺以及锐利的社会批判。到了90年代初期,莫言集中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地道》《辫子》《人与兽》《飞鸟》《夜渔》《神嫖》《翱翔》《地震》《铁孩》《灵药》《鱼市》《良医》等,即我们上边说的“笔记体”或“聊斋体”小说。这些小说以灵活的笔法记录奇人异事,将现实、传说和想象混杂在一起,拉开与现实的距离,或是呈现出一种非紧张性的松弛关系,却也暗含着社会批判和人性思考。《故乡人事》就是这样的小说。
莫言自1985年在文坛上崛起,在先锋探索和寻根文学浪潮之中形成巨大的艺术冲力。莫言在文体上锐意“求新求变”,天马行空,既有表现类的“魔幻”/浪漫/先锋性作品,也有再现类写实性作品。但是令莫言困扰的是,那种表现类作品往往被认为是对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简单借用。魔幻现实主义的确对当时文坛具有重要影响,对莫言也有很大的启发,甚至可以说,马尔克斯让他发现了小说的写法,但是莫言也同时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那种自我创造性被笼罩、压抑的感觉。这也是当时文坛一种普遍的焦虑,一方面要走向世界,奉行大胆的“拿来”主义,另一方面,“拿来”之后却又有一种丧失自我的痛苦和焦虑。莫言当时说:“我现在恨不得飞跑着逃离马尔克斯、福克纳。这两个小老头是两座灼热的火炉子,我们多么像冰块。我们远远地看着他们的光明,洞烛自己的黑暗就尽够了,万不可太靠前。”①从创作《天堂蒜薹之歌》以后,莫言就有意识地避免马尔克斯式的魔幻因素,并逐步走出了马尔克斯的笼罩。他找到自己的根源或底蕴,那就是山东齐文化的鬼神、“聊斋”传统,从蒲松龄那里获得了巨大的自信。莫言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学习蒲松龄”的幽默短文,像小说又像散文。莫言说,他的马贩子祖先托梦给他,让他去见蒲松龄,拜师学艺,蒲松龄“从怀里摸出一只大笔扔给我,说:‘回去胡抡吧!”②阿城在《闲话先说》中提到莫言时说,莫言承续了蒲松龄的传统,善于讲鬼怪传奇故事:“到了魏晋的志怪志人,以至唐的传奇,没有太史公不着痕迹的布局功力,却有笔记的随记随奇,一派天真。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的世俗构成。像我这类1949年后城里长大的,只知道‘阶级敌人,哪里就写过他了?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1986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过有一次他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进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的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趟到水里,小红孩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故事,因此高兴了好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尽,重为天真。”③更为重要的是,莫言意识到:
伟大作品给予我们的真正财富,我个人认为,不是坐着床单升天之类诡奇的细节,也不会是长达一千字的句子。这些好像是雕虫小技。伟大作品毫无疑问是伟大灵魂的独特的陌生的运动轨迹的记录。由于轨迹的奇异,作家灵魂的烛光就照亮了未被识别的烛光照亮过的黑暗。④
这意味着对伟大作品的真正领会和接近,不是模仿其外在的技巧,更重要的是走进灵魂,从伟大的灵魂里领略的神韵、风光,才是自我创造的强劲力量和营养。
三、小说就是要“盯着人写”
《故乡人事》包括三部短篇,即《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这三篇作品的基本结构是典型的莫言式小说结构。所谓典型的莫言式小说结构当然也不仅仅是莫言这样结构作品,而是莫言最重视也最愿意这样结构小说的结构。这种结构是:在一个时代背景之下,聚焦于人物性格和命运。时代/社会历史状态是人物的舞台或实验室,人物性格、命运成为小说叙述的重点。时代/社会历史状态一方面对人物性格、命运构成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人物自身又具有主体性,按照自己的心理逻辑行动,有自己的性格、命运,并非是作家的傀儡,更不是社会、时代的传声筒。他是时代的又是属于他自己的,他和时代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参差不齐乃至有所冲突的交叉、分离的复杂关系。当我们仅仅用社会学的眼光去审视他的时候,就会觉得不那么贴切,有所隔阂,他迫使我们去思考人性的复杂性;当我们仅仅用人性的眼光去看他的时候,也显得不够充分,他似乎又是被特定时代所影响、塑造的。这种结构一方面触及社会历史,有足够的外向拓展力量,另一方面向内开掘,又给人性留下巨大的空间。在人和历史之间有着巨大而复杂的冲击波。当然,这里最重要的是人物性格的塑造。莫言特别注重小说的人物塑造,他说:“小说理论千变万化,但小说总是免不了写人写事,许多新的说法不过是旧小说的重新包装。”①莫言相信沈从文“贴着人物写”的观点:“沈先生的经典之言就是:‘小说就是要贴着人写。在前不久,我又稍微改了一下,改为‘盯着人写。贴着人写就是尽量地要让情节服从人物,要让你所有的描写都服从塑造人物的需要。要把写人和塑造典型人物作为写小说的第一个任务,最重要的任务。”②“我改之为‘盯着人写,意思与沈先生差不多,但似乎更狠一点,这是我的创作个性决定的。”③这是人性论文学的重要尺度,也是莫言小说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最重要叙述原则之一。莫言多次表达这样的观点:“我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掌声)作家是有国籍的,这毫无疑问,但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掌声)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運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④
《地主的眼神》和《左镰》都是写地主的,把地主放在当代社会变迁之中去刻画他们的性格,表现他们的命运,对于迫害、歧视地主的“极左”政治给予猛烈的抨击和批判。但是小说最具魅力的地方却是“盯着人写”,把地主当成人来写,写出地主的复杂性格及其当代命运。他们是属于社会的或时代的,同时,他们也是他们自己。在《地主的眼神》中,地主孙敬贤成为地主,也仅仅是因为多了那么一点并不算好的土地,粮食产量并不高。这点多出的土地也仅仅因为他喜欢种地,像许多农民那样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这正如孙敬贤的孙子孙雨来说的那样:“我好鼓捣机器,喜欢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俺爷爷就爱土地,这大概也是遗传吧。”在人民公社里,孙敬贤和许多社员一样,割麦时也磨洋工,并不卖力气,但他却是一个割麦能手,“老地主割下的麦捆,麦穗整齐,麦茬儿紧贴地面。地下几乎没有落下的麦穗。……我看到他黄眼珠子里露出一闪而过的得意”。孙敬贤是一个善于割麦、热爱劳动的地主,并非如“文革”时期宣传所说的那样,地主个个好逸恶劳。莫言曾经和王尧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爷爷割麦子的故事,也讲到地主的劳动:“我爷爷割麦子的技术在方圆几十里、在整个高密东北乡都是鼎鼎大名的,很潇洒。”⑤“我们割麦子要换上最破的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还把袖口、裤腿扎起来,我爷爷看了就冷笑,他割麦子的时候,穿着很板的白褂子,用手挽一下袖子,身上根本没有灰尘的,看他割麦子真是一种享受。”⑥“我爷爷他们是真正的高手,他实际上技术已经很好了,他说他还不行,真正的高手都是提着画眉鸟笼子,身后跟着跟班的,镰刀的柄上镶着象牙。都是大地主。大地主也会干活?摇芭蕉扇来,其实很多地主都是干活高手,从小劳动出来的。在劳动过程当中,他们实际上也体验了很多乐趣,他出来打短工,是寻开心、过瘾,在地头上吃饭也是很开心的。”⑦孙敬贤的丧事办得特别隆重,是因为他的儿子秉承了他争强斗胜的性格,喜欢打肿脸充胖子,或许这种争强斗胜也是一种人生的动力,他的儿孙们才成为种粮大户。但是,孙敬贤却又并非是《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那样的“好地主”,而是掩藏着强烈色欲的人。他的儿媳在与“我”的交往中揭露了他的乱伦欲念。这种书写复杂人格、拷问人性的倾向,是莫言对个体生命的尊重。莫言的写作往往触及作为人的存在的不同层级,看到人的各种属性,阶级性、文化性、自然性,同时也穿透这些层面,进入个人之为个人的最深层的那种动力。
《左镰》是写地主和他的儿子。地主田千亩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仅仅出现在一个小片段中,仅有几句简短的对话,似乎并不引人注意,读完全文后回味一下,就会感到心惊肉跳,震撼力十足。想想看,地主田千亩因为儿子田奎欺负傻子——其实仅仅是儿童的顽劣而已,就将儿子右手剁掉,然后再给他打一把“左镰”——左手使用的镰刀。这是莫言书写残酷、直面惨淡的人生的艺术本性的显现,但是,在这里莫言并没有像以往《红高粱家族》《檀香刑》那样直接将残酷的暴力叙述出来,而是留下大片的空白,让读者想象、回味和思考。田千亩无疑是一个凶恶的人,但是虎毒不食子,他的凶恶、残暴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吧。可以想象,当刘老三气势汹汹地找上门的时候,作为地主出身的田千亩会承受怎样的压力?一个地主的儿子欺负贫下中农的孩子在当时意味着什么?他无法承受这种压力,又不敢对抗刘老三,便把自己的极端愤怒、凶暴发泄在儿子身上。同样是地主,孙敬贤和田千亩又完全不同。莫言要写出地主,更要写出一个个的地主,写出不能被概念轻易统一的地主。这里既有莫言一贯的“人性恶”的观念,也有其社会批判的尖锐性及对人生的悲悯。田千亩的儿子田奎却完全是无辜的受害者,因为地主出身,他就无法升学,虽然他学习很好。而且,竟然因为一件小事儿被父亲剁掉了右手,还要靠左手劳动,绝望地生活着。这个形象寄寓着莫言对人生的极大悲悯。
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这两篇小说都有一种内疚和忏悔的情绪在里边。莫言把自己当成罪人来写,在挖掘出人性深处普遍存在的暗影的时候,不是将自己抛开,而是放在里面。叙述者“我”虽然并不一定就完全代表莫言,但是,想到莫言的写作原则——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我”这个叙述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莫言的良苦用心。“我”写过一篇作文《地主的眼神》,“在我的作文里,那個老地主周半顷就是一个阴险的坏蛋,他装病逃避改造,他伪装可怜,但心里充满仇恨,时刻梦想变天,他的眼神,泄露了他内心的秘密。我至今也认为孙敬贤不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但我那篇以他为原型的作文确实也写得过分,尤其是因为我那篇作文,让他受了很多苦,这是我至今内疚的”。正因为“我”的这篇作文,孙敬贤吃了更多的苦头,孙敬贤的不幸和“我”的作恶也不无关系。在《左镰》里,本来是孩子们一起起哄、欺负傻子,当刘老三找到“我”家的时候,“我”和“二哥”在遭到父亲暴打之后,却推说是田奎领头打的,把责任全部推给了田奎,因为田奎是地主的儿子,好欺负。可以想象,刘老三会怎样去找田千亩算账。因而田奎的悲剧并非和“我”没有丝毫的关系。这种直面自己的罪恶的写法无疑增进了作品人性反思的深度:一些悲剧的发生,固然有来自外部的社会原因,但是,人性内部的因素也不可轻视,人人都可能是罪恶的制造者,有时甚至是不经意间就对别人构成了巨大的伤害。这让我想起了《酒国》中的那个作家莫言。莫言尽管深知酒国市的腐败,也知道“吃人”的事情,但是,当他来到酒国的时候,却难以抗拒酒国的诱惑。在通往酒国的列车上,莫言意识到自己的矛盾:“我像一只寄居蟹,而莫言是我寄居的外壳。莫言是我顶着遮挡风雨的一具斗笠,是我披着抵御寒风的一张狗皮,是我戴着欺骗良家妇女的一幅假面。有时我的确感到这莫言是我的一大累赘,但我却很难抛弃它,就像寄居蟹难以抛弃甲壳一样。在黑暗中我可以暂时抛弃它。我看到它软绵绵地铺满了狭窄的中铺,肥大的头颅在低矮的枕头上不安地转动着,长期的写作生涯使它的颈椎增生了骨质,僵冷酸麻,转动困难,这个莫言实在让我感到厌恶。”①文化的假面之下存在着一个动物般肮脏的莫言。虽然令人厌恶,却也难以摆脱。在莫言的人性观之中,人性距离动物性仅仅隔着一张薄薄的纸,在人性背后深藏着动物性,这种动物性也可以称为人的局限性。人是无法完全克服其存在的有限性的,其动物性的一面随时可能流露出来。因而,人人都是有罪的,自己也是罪人。《酒国》的重要元素是对鲁迅的自觉模仿、戏仿,也具有鲁迅式的我也吃过人的自我剖析和审视。《檀香刑》是写历史,也是写人心。从人心的角度看,人都是动物,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在《蛙》之后,莫言特别强调这种自我审视、批判的意识,他说:“《蛙》在我的写作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因为这是一部开始执行自我批判的作品,是我提出的‘把自己当罪人写的文学理念的实践。”①
《斗士》写两种偏执的“好斗”人格,方明德和武功虽然身份、地位相差悬殊,方明德曾经是村党支部书记,武功是一个出身不好的底层农民,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好斗”性格。这种“好斗”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都有时代的原因,同时也是他们内在自我的显现,就如同某些好斗的公鸡一样,“我斗故我在”。方明德在村里当了几十年的支书,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也仍然沉醉在“文革”时代,对于现实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不要做当下的“顺民”,在梦中也能梦到毛主席,毛主席教导他要战斗。然而,事实上他也并非如他自己所标榜的那样“大公无私”地去战斗。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里,他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发泄私愤,报复武功。因为武功不愿意将一副象牙象棋卖给他,他就寻找机会——怀疑武功偷了生产队小车的轱辘,动用酷刑拷打武功。武功的说法是可信的:“你不知道他有多狠啊!他让他侄子反绑着我的胳膊把我吊到房梁上——这些强盗,私设公堂,在房梁上安装了一个定滑轮,轻轻一拉,就让我离地三尺。他说,‘武功,你小子,终于落到我手里了,说吧,你把轱辘藏到什么地方啦?我说,我不服,我冤枉。他说,你是咱们村嘴巴最硬的,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大叔,你不知道,你们无法想象啊,他让他侄子把我拉上去,一松手,我啪唧跌在地上;再拉上去,又一松手,啪唧跌在地上……”方明德死后,他的儿子秘不发丧,夜里悄悄地抬出去,为的是继续领取每年一万的荣军补助。他天性好斗,却打着冠冕堂皇的宏大旗帜,当你从宏大的角度去看他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也是一种私欲的表达方式。在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中,这种人物十分典型。《檀香刑》中的刽子手赵甲对自己的亲家孙丙施以残酷的檀香刑,口口声声是效忠大清,执行大清的律法,实则是他内在自我欲望的满足。在这种酷刑之中,他才能克服卑微身份的局限,显示出自己的价值。
武功的“好斗”则是弱者的存在方式。作品最后一句话是对武功性格的一种概括:“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他家庭出身不好,相貌也遭人厌恶,媳妇也娶不上,他是在绝望中生活,自暴自弃。但是他采取的是猛烈的攻击性姿态,敢于拼命,以命换命,用自己卑贱的命换取仇敌的命。方明德将他吊打,他不屈服;王魁将他打趴在地上,打得半死,他拄着拐,依然大骂王魁的儿子是方明德的。方明德死后秘不发丧,他去告发。长久的绝望使他变得格外敏感乃至心理变态,脾气怪诞,不仅仇敌必遭到他的残酷报复,稍有冲突他也会全力报复。即使成为“五保户”,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仍然愤愤不平。然而,“他放了那么多次火,干过那么多的坏事,竟然没被人捉住,这也真是一个奇迹”。
武功命运的“奇迹”是莫言小说叙事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从传统上说是“传奇”,从现代来说就是对偶然性的运用。许多小说家都喜欢偶然性,但是现代的偶然性与传统的偶然性之间还是有着重大的差异的。传统的偶然性往往寻求必然性的强大支撑,即所谓偶然中有必然,而现代的偶然性却消解了必然性,是离开了必然的偶然,从而达到对古典价值观的颠覆,有一种彻底的荒凉感。《左镰》最荒凉,田千亩和他的儿子田奎都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掳掠到永无天日的深渊。田千亩砍掉儿子的右手,并非仅仅是社会、时代的原因,还有大自然的狂暴、肆虐,人们无法控制外部的自然力,也不能完全控制来自内部的自然力,在莫言的残酷叙事之中往往透露着这种极具超越性的荒凉,在大自然之中,人不过是小小易碎品。孙敬贤同样如此,不同的是,他有个好的结局:轰轰烈烈的葬礼。在世人看来,也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他能够获得充胖子的机会,也是出于偶然,并非他格外英明,他无法改变什么。我以为,这种直面大自然的写作境界,并非仅仅是传统笔记体/聊斋体所能够承载的,那里面有太多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简陋世界观。《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作品,大多数作品打着“因果报应”的烙印,这是传統、民间文学的重要特征。古人普遍愿意活在一个一切都分明、一切都有必然性的世界之中。莫言小说却根本没有这些。这意味着莫言对“传统”“民间”的选择、改造和升华。当我们强调莫言与“传统”“民间”的联系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是站在现在的大地上,不要忽略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他没有把“传统”“民间”作为一个死的教条,而是作为一种开放的活水源头,大胆拿来,自由创造。传统是继承,但更是一种发明。
①莫言:《檀香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518页。
②莫言:《檀香刑》,第517—518页。
③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演讲》,载《小说的气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①《莫言谈新作〈锦衣〉:获诺奖五年里都在忙些啥?》,http://v.ifeng.com/video_8585685.shtml。
②管谟业:《天马行空》,《解放军文艺》1985年2期,第89页。
①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
②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第186—187页。
③鲁迅:《忽然想到(七至九)》,载《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0页。
④鲁迅:《忽然想到(七至九)》,载《鲁迅全集》第3卷,第61页。
⑤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载《鲁迅全集》第3卷,第379页。
⑥莫言:《檀香刑》,第510页。
①李洁菲:《在另一面——莫言三年前的一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6期,第28页。
①莫言:《旧“创作谈”批判与新“创作谈”》,载《怀抱鲜花的女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40页。
②莫言:《学习蒲松龄》,载《与大师约会》,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98页。
③莫言:《阿城》,载《会唱歌的墙》,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257—258页。
④莫言:《舊“创作谈”批判与新“创作谈”》,载《怀抱鲜花的女人》,第34页。
①莫言:《陈旧的小说》,载《写给父亲的信》,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47页。
②莫言:《文学与我们的时代》,《中国作家》2012年14期,第222页。
③莫言:《序·盯着人写》,载《我们的荆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第1页。
④莫言:《优秀的文学没有国界——在法兰克福“感知中国”论坛上的演讲》,《上海文学》2010年3期,第76页。
⑤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第14页。
⑥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第15页。
⑦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第17页。
①莫言:《酒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11页。
①兰传斌:《莫言:“把自己当罪人写”》,《大众日报》2011年8月21日,第7版。
The Application and Creation of“Tradition”and“Folk”
——On aesthetic pursuit of MO Yans“Brocade Clothing”and“People and Things in Hometown”
WANG Xue-qian
Abstract:MO Yans new works,“Brocade Clothing”and“People and Things in Hometown”, are the creation to the tradition as his style, which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blended into his personal cre? ativity.“Brocade Clothing”is an affinity to the aesthetic taste of traditional opera. Meanwhile, it adds MO Yans personal touch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modern experience. The full performance of the clowns, WANG Po and WANG Bao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opera. WANG Baos character is a continuation of LU Xuns“reforming the national spirit”. WANG Bao was as cowardly as AH Q. His revolution was similar to Ah Qs.“People and Things in Hometown”by MO Yan is a kind of“note-taking”novel as traditional“notetaking”. It is similar to PU Song-lings Strange Tales from a Lonely Studio, which records strange people and strange events, and also conveys magic realism in charm. At the same time, the style and verve in LU Xuns short stories are integrated with the emphasis of line drawing, which can touch the inner state of the charac? ters. The tradition and modern on literary style are highly integrated.
Key words: MO Yan, tradition, folk, LU X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