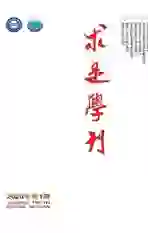马克思科学无神论思想的真理之维
2020-02-26叔贵峰张笑笑
叔贵峰 张笑笑
摘要:无神论思想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理论研究上可以将马克思对宗教的理论态度定位为科学的无神论,但不能将其“科学”视为自然科学或数学意义上的科学,而应把握为超越科学的真理性维度。因为在马克思的无神论思想中蕴含着理性对于知性、辩证法对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上的超越与变革,这就决定了它的内涵已超出了“科学”而达到了“真理”无神论的理论层次。自西方近代以来,18世纪的法国无神论是仅就宗教表象进行批判的,应隶属于知性的科学无神论;马克思的无神论立足于宗教的实践“内容”,是辩证思维层次上的真理无神论。
关键词:马克思;无神论思想;科学与真理;知性与理性
作者简介:叔贵峰,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阳110036);张笑笑,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沈阳11003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黑格尔派到马克思的历史观演进逻辑研究”(18YJA720010)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0.01.007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是其进行社会现实批判的理论前提,我们在其宗教批判的整体思想中也能清楚地看到其不信神、否定神以及痛恨一切宗教偶像的无神论立场,更能洞悉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主要是通过消除生产异化的方式来让人类从宗教的精神“鸦片”中得以最终解脱的,可以说,“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下的神”①就是马克思标榜自己无神论思想的“座右铭”。在理论研究中,我们经常用“科学无神论”来定位和表达马克思的无神论思想,因为它更加直接地彰显出马克思无神论思想的正确性、彻底性和对其他非科学无神论思想的超越性。正如任继愈先生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在无神论问题上的彻底性,并不在于它主张科学无神论的坚决性,而在于它科学地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和走向消亡的客观规律。”②然而,由于“科学”概念在应用上更主要地指向的是自然科学和数学,这便导致我们常常以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科学正确性”来解读和阐释哲学内容的正确性,用科学作为标准来衡量、评判甚至裁断哲学的思维方式,结果导致“哲学科学化”的研究方式大行其道。理论研究上的与时俱进要求我们,不能再用“科学无神论”来标识马克思的无神论思想,否则就会导致存在于马克思无神论思想自身中的真理性质被遮蔽起来,这不仅会让马克思的无神论思想有被误认为知性解读的可能,而且也忽视了马克思无神论与以往无神论思想在“科学与真理”之间的实质性区别。而要恢复马克思无神论思想之中的真理之维,首先要将“科学”与“真理”的内涵放置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然后再从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扬弃”关系中重新审视马克思“科学无神论”中蕴含的超越科学的真理本性。
一、德国古典哲学中“科学”与“真理”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
哲学自古希腊产生以来就担负着运用人的理性去把握本体并形成真理的知识论使命,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就是人类运用理性(语言、话语)对内在于宇宙之中的“原理”进行逻辑上的真理表达,而阿那克萨哥拉的“奴斯”则是要求理性通过克服欲望的方式而不断地向上、追求本体之“真”,正是这两种哲学精神的“基因”之间的相互融合与促进,使得哲学与最高的知识、第一哲学等真理之学之间始终保持着“形上”的同一性,“爱真理”、“爱智慧”、努力追求形上真理也成了哲学的终极使命,而此时科学的萌芽还潜在地埋藏在哲学的母体之中。到了近代,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为独立的理论形态从哲学的母体中脱颖而出,科学知识由于其具有的普遍必然性而成为那个时代一切知识的典范,并成为近代哲学建构其理论形态的“模板”,进而“哲学科学化”也成为当时打造形而上学的时代理念。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适应,英国出现了经验论哲学;与数学的发展相适应,欧洲大陆哲学家们试图用数学方法来建构其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正如斯宾诺莎说的那样:“在研究和传授学问时,数学方法,即从界说、公设和公理推出结论的方法,乃是发现和传授真理最好的和最可靠的方法。”①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科学对哲學的影响达到了最高峰,二者高度融合,哲学首先必须是科学的,哲学要像科学一样为人类提供精确的、普遍的必然的知识。然而,当休谟的怀疑论出现后,这一良好的哲学愿景被无情地打破了,休谟直接对科学知识中“普遍必然性”的来源提出了质疑并导致了知识论危机的出现。诚然,知识论危机并不是科学本身出现了“危机”,而是让哲学家执着地效仿科学来建构哲学的理想化为了泡影,若要重建形而上学,方向只有一个,即突破“哲学科学化”的原有模式,重新考量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并且只有将哲学打造成为超越科学的真理之学,哲学才能重获新生,因此,“超越科学”就成为德国古典哲学重建形而上学的共同理念。
德国古典哲学的目的就是要将哲学打造成为具有真理性的知识论形而上学,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为“科学何以可能”率先找到了主体的先验根据,从而化解了近代哲学陷入的知识论危机。在康德看来,科学知识虽然具有普遍必然性,但它仍然不是绝对知识,因为它不具备真理的性质。因为科学的普遍必然性并非是“第一性的”,而是由主体中先验认识形式的普遍性所决定的,科学知识只是关于现象的相对知识,而不是关于事物自身的真理性知识。同时,未来的形而上学也不能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建构,因为自然科学的方法经不起怀疑论的拷问;数学的方法虽然可靠,但却局限于先验的时空形式,从而不能对现象的内容形成知识。因此,未来的哲学将建立在主体先验的基础之上。以“质、量、关系和模态”为根基建构起未来的形而上学,康德称这种哲学方法为“建筑术”。“我把一种建筑术理解为种种体系的艺术。”②但由于康德将未来的形而上学建立在先验的主体自我之上,而关于事物自身的真理则被排除在人类的知识之外,所以,康德虽然在形而上学建构上首次完成了哲学对科学的超越,但严格说来,这种“超越”仍然局限在主体之内,康德的先验形而上学只能作为现象世界的最高知识,它具有先验性,还不具备切入事物自身内容的真理性。费希特沿着康德的先验道路将形而上学提升到最高的知识学,而科学则成为知识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非我限制自我的理论知识,知识学是包含科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的最高原理和根据。费希特的知识学虽然超越了经验主体,进入到了纯粹先验主体之中构成了最高知识,但其知识学对科学的超越仍没有走出“唯我论”的主体困境。谢林充分地意识到作为最高的哲学知识不能只与主体的理性活动有关,而与事物自身的内容无关,这会让哲学知识失去客观实在性的基础。谢林主张,“一切知识都以客观东西和主观东西的一致为基础”。①因此,谢林认为最高的哲学知识必须要超出主观和客观两者之间非此即彼的存在论立场,而转向主、客同一的知识学立场,真正的哲学要以主、客观存在之上的同一“绝对理性”为对象,才能让哲学达到最高知识的“真理”之学,而科学作为客观理性无非就是存于自然物质世界之中的“绝对”而已。因此,科学隶属于同一哲学之下,哲学是最高的知识,是科学的科学。可惜的是,谢林虽然将哲学确立为真理,但在如何把握“绝对”进而得到真理的认识方式上却诉诸于个人天才的艺术直观,从而给哲学真理蒙上了神秘的面纱。黑格尔反对谢林的神秘直观,主张诉诸于辩证逻辑的方式,这便将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提升到思辨理性的认知方式之中,最终确立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黑格尔首先明确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本质区分:一是科学是有限性的知识,自然科学是基于事物表象而形成的知识,数学知识的对象(数和几何图型)就是抽去了事物所有内容的纯形式。“几何学可以下许多好的界说,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空间,是一个异常抽象的对象。”②因此,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都不是关于事物自身“内容”的知识。而哲学对象是存在于事物自身之中的理念和内容,哲学就是要对事物的“内容”形成真理性的、整体性的知识。因此,科学只是相对的知识,它停留在事物的表象或形式之上,而哲学知识才是绝对真理。二是在黑格尔看来,科学与常识和以往的形而上学一样都是运用知性思维来形成知识,这种知识本身具有其所不可克服的先天“缺陷”,即知识所抽象出来的概念是无“内容”的抽象普遍性,知识所形成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事物自身的必然关系,它只是外在于“内容”的、彼此之间隔离的偶然联系。正如黑格尔所批判的那样:“然而在一般经验科学的范围内,一方面其中所包含的普遍性或类等等本身是空泛的、不确定的,而且是与特殊的东西没有内在联系的。”③哲学运用的是思辨思维,并对事物自身的“内容”形成知识,它以事物的“理念”作为内容,而将表象与表象间的关系视为以“内容”作为根据相联系的有机环节,是全体真理性和环节必然性的统一,从而达到人类对于事物的真理性知识的把握。因此,在黑格尔看来,科学是知性的表象知识,而哲学则是理性的内容真理,这便在认识的层次上严格地区分了科学与真理的界限。三是科学方法属于知性方法,不能做哲学的运用。科学运用分析和综合两种方法,自然科学主要运用分析方法,而数学主要运用综合方法。分析方法只是将事物表象由整体向其构成的部分不断地拆分,而综合方法无非是把纯粹的形式进行抽象的演绎罢了。对此,黑格尔说“:一切科学方法总是基于直接的事实,给予的材料,或权宜的假设。”④而哲学的方法不是外在于事物的“形式方法”,而是与事物内容的存在与展开相一致的方法,黑格尔称这种哲学方法为“既分析又综合”的思辨方法,“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⑤黑格尔虽然严格地区分了科学与哲学,但却没有将二者的关系对立起来,黑格尔认为作为事物内容自身的发展包含知性的肯定、辩证的理性和思辨的理性三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环节,理性对于知性的超越不是外在的超越,而是将知性包含在自身之内完成了对它的超越,即内在超越。哲学对科学的超越关系也是如此,哲学是将科学作为进入真理的环节而包含在自身之中,从而完成哲学对于科学的内在超越。“思辨的科学与别的科学的关系,可以说是这样的:思辨科学对于经验科学的内容并不是置之不理,而是加以承认与利用,将经验科学中的普遍原则、规律和分类等加以承认和应用,以充实其自身的内容。”①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整个过程蕴含着哲学对科学的超越,特别是黑格尔不仅指出了科学知识之中存在着自身无法摆脱的知性局限,而且将哲学提升为理性思维层次的真理之学。哲学之所以成为真理,在于其运用思辨的方式把握存在于事物自身的内容、理念,从而在哲学中树立了“思辨思维”和“辩证法”的知识论权威。当然,宗教也是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对宗教的认识也突破了以往的知性宗教观,并将对宗教的理解提升到思辨理性的理论高度。
二、西方近代以来知性无神论与理性无神论的理论实质分析
回顾西方哲学近代以来的无神论思想史,我們可以发现有两种理论形态:一是指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无神论;二是指19世纪30—40年代青年黑格尔派中布鲁诺·鲍威尔的思辨主义无神论思想。前者处于近代“哲学科学化”的时代背景中,其无神论思想中存留着知性的认知局限,而后者则是充分地吸收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其无神论思想已然达到了思辨理性的认识层次。更为根本的区别是,法国无神论是基于科学展开的宗教批判,而鲍威尔的无神论则是基于黑格尔思辨哲学而展开的宗教批判,因此,分析这两种无神论思想的理论实质,会让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到无神论思想由知性向理性认识发展的过程。
18世纪法国无神论以伏尔泰、梅叶、狄德罗以及霍尔巴赫为主要代表,在他们看来,只有经验世界是最真实的存在,只有在人们感觉中呈现出来的存在才是可信的,而超出经验世界和感觉之外的任何存在都不是真实的。因此,科学的发展已经证明了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之内根本没有什么神的存在,一切宗教中的神都是个人出于某种目的的编造和虚构。宗教产生于欺骗,而相信宗教等同于“傻子”,宗教无非就是“第一个傻子遇到了第一个骗子”而产生的荒唐闹剧。狄德罗对此讽刺道:“一个人若为一种他认为虚伪的宗教信仰而死,他将是一个疯狂的人。”②由此可见,法国无神论是站在自然科学的立场之上,用经验世界的“真”来揭露宗教世界的“假”,用科学知识的正确来驳斥和否定宗教教义的虚构,其批判的结果就是将宗教与科学对立起来,从而形成了以科学揭露宗教的无神论的理论形态。但事实上,法国无神论尽管充满着对宗教的无情嘲弄和辛辣讽刺,但其批判的理论性质仍停留在知性思维的层次。所谓知性思维就是仅仅围绕事物表象而展开的认识活动,黑格尔称知性思维为表象思维,“表象思维的习惯可以称为一种物质的思维,一种偶然的意识,它完全沉浸在材料里,因而很难从物质里将它自身摆脱出来而同时还能独立存在”。③如此看来,法国无神论批判的只是宗教的表象或现象,只是在宗教的“表象领域”将科学与宗教对立起来,批判的结果只是在经验的世界中达到“无神”化。然而,这种批判只适用于原始宗教、自然宗教以及各种低级迷信,对于经过了上千年神学洗礼的基督教却并不适用。一方面,基督教中的上帝本身就是超验之在,用经验世界的“真”无法证伪超验世界中上帝的“假”;另一方面,法国无神论对宗教表象的批判不能替代对宗教内容的批判,而无内容的批判也不会撼动基督教据以存在的理性神学根基,而只能沦为貌似深刻、实则肤浅的“科学无神论”。恩格斯也极为反对对基督教做简单且肤浅的理解:“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1800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④
第二种无神论理论形态出场在黑格尔之后由青年黑格尔派发起的宗教批判运动中,其中布鲁诺·鲍威尔运用自我意识哲学对基督教的产生和实质进行猛烈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卢格称鲍威尔是“神学的罗伯斯庇尔”,切什考夫斯基称鲍威尔的无神论是“科学的恐怖主义”。鲍威尔是黑格尔的学生,其宗教批判思想直接源于黑格尔对于宗教的理论态度。在黑格尔看来,宗教批判的矛头不能指向宗教的表象,而应审视宗教表象所依附的“内容”——理念,宗教内容作为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一个环节,就是用基督教教义中父、子、灵的宗教形式间接地表达了理念、自然和精神之间的辩证发展过程,因此,宗教的根据在于其理念和精神的“内容”。“真正的宗教,精神的宗教,必须具有一种信仰,一种内容。”①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是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改造,自我意识与绝对精神相比,是一种更具有能动的理性精神力量,它是一切产生的根据,也是摧毁一切现实存在的原始力量。“自我意识一旦在一种形式、一种实体中得到实现,这种形式、这种实体就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而必须由一种更高的形式取代之。”②基督教的教义产生于当时罗马世界中人们对于尘世绝望的“苦恼意识”,而“苦恼意识”就是自我意识发展到罗马时代的具体样态,因此,基督教产生的根据是自我意识。同时,基督教作为非理性的意识形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与自我意识产生冲突和对抗,直至成为自我意识的最大“敌人”。当自我意识的“内容”发展要求必然突破宗教的“形式”时,宗教就成为自我意识予以铲除的对象。因此,鲍威尔无神论理論的归宿就是:当自我意识发展到最高阶段就会消灭一切宗教的表象和形式,让自我意识在一个“无神”的理性国家之中完成自我的实现。
黑格尔将宗教观提升到了思辨理性的高度,鲍威尔则将其推向了具有思辨性质的无神论。这种无神论已经超越了18世纪法国无神论的仅就宗教表象进行批判的方式,而是将无神论理论由知性的、科学的批判推进到了理性的哲学的批判。从批判的理性思维“高度”上看,黑格尔和鲍威尔均超越了知性的批判,而深入到了宗教存在的理性“内容”。但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和鲍威尔所说的理性、精神以及自我意识无非都是人的理性和精神,只是被他们非法地从人身上抽象出来变成了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而已。因此,他们据以得到的关于宗教的所谓真理也只是远离现实社会的抽象的、彼岸的真理。诚然,马克思并不否认应该从思辨理性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宗教,但他更赞同针对宗教的内容来说明宗教的表象的解释原则,马克思认为宗教赖以存在的“内容”绝不是理性或精神,而是根置于人类物质生产领域的实践。因此,马克思是在批判和驳斥鲍威尔的思辨主义无神论的前提下确立了其以实践为根据的无神论,最终确立了实践无神论的真理的理论形态。“那种使人们满足于这类诸精神史的观点,本身就是宗教的观点,因为人们抱着这种观点,就会安于宗教,就会认为宗教是causa sui[自身原因](因为‘自我意识和‘人也还是宗教的),而不去从经验条件解释宗教,不去说明:一定的工业关系和交往关系如何必然地和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而和一定的国家形式以及一定的宗教意识形式相联系。”③
三、马克思无神论思想中的真理内涵及其理论价值
马克思的无神论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青年黑格尔派,是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转向社会现实批判的进程中确立起来的,正如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那样:“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④当然,这个“转向”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不再关注宗教问题了,而是马克思认为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仅仅将社会政治的现实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是行不通的,也不可能真正地解决当时普鲁士的社会现实问题,而应该变革被异化了的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将宗教上的政治解放提升为以实践为根据的现实人类解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表象”,应该从人类社会的生产实践中来说明其相关的一切问题。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中便蕴含着其对宗教诠释的新的理论维度。“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以及社会主义,意在通过从哲学到共产主义实践的转变成为无神论时代社会共同体的新的信仰。”①如果我们仅以“无神论”思想作为线索来考察马克思和鲍威尔无神论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可以发现马克思无神论是对鲍威尔无神论思想的直接“扬弃”,即马克思以实践为根据的无神论完成了对鲍威尔以“自我意识”为根据的思辨理性无神论的超越与变革,具体分析这一“变革”的内在逻辑,会让马克思无神论思想中的真理性质清晰地呈现出来。
鲍威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之中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如《神圣家庭》就是对鲍威尔及其伙伴们的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论犹太人问题》直接批判的就是鲍威尔本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对鲍威尔“自我意识”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鲍威尔虽然在宗教批判中达到无神论,但究其理论实质,他仍然停留在黑格尔确立的思辨唯心主义框架之内,其无神论思想虽然在宗教领域达到了理性对于宗教及信仰的清算,但宗教领域不是人们存在的现实领域,宗教批判的结果仍然无力改变人们由于社会现实苦难而信仰宗教的事实。而且,鲍威尔用“自我意识”铲除了宗教中的上帝之后,“自我意识”便成为主宰一切的现实力量,“自我意识”变成了理性的上帝。于是,鲍威尔在消解了宗教中上帝的神圣形象之后,又为人们重新确立起了“自我意识”的神圣形象。因此,鲍威尔的无神论无非是以理性的上帝取代了基督教的上帝,其理论实质仍然是一种新的理性宗教而已。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鲍威尔“‘完善的和‘纯洁的批判的最后结果就是以思辨的黑格尔的形式恢复基督教的创世说”。②马克思正是看到了鲍威尔无神论思想中的唯心性,才将宗教的根据放置于人类物质生产的实践之中,实现了无神论思想由理性“唯心”向实践“唯物”的现实转向。
马克思无神论思想转向到实践的根基之上,仍然保持着超越科学知性的辩证法的理论高度,是理性真理与人类实践的高度结合。具体来说,马克思无神论思想中的真理性内涵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宗教作为“表象”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宗教表象所依附的内容则是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只要人类生产方式中存在着人的本质的异化,那么,宗教就是这个异化了的“颠倒世界”的意识反映。因此,马克思的无神论并没有基于“宗教表象”进行批判,而是对“宗教内容”做出真理性反思。二是既然宗教存在的根据在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就应当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说明宗教的产生、运动和发展的全部过程,宗教中的任何神秘性质都应该在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说明。“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的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③这样,宗教从其产生到灭亡的整个过程就被视为根据“生产方式”而展开的必然性环节的全体性,这又符合“真理即全体”的辩证真理观。三是马克思将黑格尔和鲍威尔的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还原为人的实践主体能动性,将宗教的根据由抽象的精神实体还原到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这便将无神论思想奠定在人类实践的现实基础之上,既实现了马克思对鲍威尔无神论的实践超越,也将蕴含在思辨理性之中的真理性维度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马克思的无神论内含着以实践为“内容”的真理观。“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科学无神论的高级形态,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它继承了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唯物主义、19世纪德国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等人类优秀思想的成果,通过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的发现而展示出来。”①
将马克思无神论思想提升到辩证思维的理论高度上来理解,充分把握其真理性内涵,在理论研究上是十分必要的。一是可以有效防止将马克思无神论降低为知性理解的理论倾向。当我们将马克思无神论定位为“科学无神论”时,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科学与真理之间的严格界限,自觉地将马克思的无神论归结到超越科学的“真理无神论”之上,知性的无神论不仅不是马克思的无神论,而且正是马克思所极力反对的无神论。英国著名学者麦克莱伦深刻地指出:“马克思对宗教的很多评论都富有理论的洞察力和启发性,但是,如果把宗教仅仅定性为社会缺陷的反映,则无法穷尽宗教的意义和重要性。”②二是可以自觉地站在马克思无神论的真理立场之上,正面驳斥和回应一些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哲学做宗教化的解读模式。与马克思的无神论相反,西方当代一些学者对马克思哲学做“有神论”的阐释并借以攻击和质疑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性。如本雅明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充满着“弥赛亚”的宗教观念,卡尔·洛维特更是将马克思歪曲为宗教式的、能够预言历史的“先知”,认为唯物史观就是一部弥散着宗教色彩的救赎史。“《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全部历史程序,反映了犹太教-基督教解释历史的普遍图式,即历史是朝着一个有意义的终点目标的、由天意规定的救赎历史。”③事实上,马克思对鲍威尔无神论思想会导致“理性神”已经进行了充分的批判,并且认为只有将宗教的根基回落到实践的基础之上,才是避免让世界再次“神圣化”的唯一途徑。因此,唯物史观恰恰是对将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归为上帝或理性精神的主观意图的最有力的批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内容”。由这个“内容”展开的历史进程才是历史本身的、客观的目的。因此,本雅明和洛维特等人企图再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拉回到“有神论”的做法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歪曲和误读,根本不符合马克思哲学所坚决捍卫的实践无神论的根本立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90页。
②任继愈:《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奋斗》,《任继愈文集》第1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2页。
①斯宾诺莎:《笛卡尔哲学原理》,王荫庭、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5页。
②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09页。
①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页。
②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14页。
③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48页。
④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48页。
⑤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243页。
①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49页。
②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1页。
③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9页。
①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13页。
②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陈启伟、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6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①邹诗鹏:《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思想之辨析》,《现代哲学》,2011年第1期,第2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7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9页。
①习五一:《无神论是人类社会文明和思考的结晶》,载《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7页。
②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论宗教》,平川译,《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3期,第56页。
③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53页。
TheDimensionofTruthinMarxsScientificAtheism
SHU Gui-feng, ZHANG Xiao-xiao
Abstract:The thought of atheis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s philosophy. We can position Marxs theoreti? cal attitude toward religion as scientific atheism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but cannot regard such“science”as science in natural or mathematical sense of science. However, we should take it as the truth dimension beyond science, because Marxs atheism thought contains the transcend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reason to under? standing and dialectics to metaphysics, which determines that its connotation has gone beyond“science”and reached the theoretical level of“truth”atheism. Since the western modern times, the atheism from France in the 18th century only criticized the religious appearance and should be subordinate to the intellectual scientif? ic atheism. Marxs atheism, based on the practical“content”of religion, is the truth atheism on the level of di? alectical thinking.
Key words: Marx, atheism, science and truth, understanding and rea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