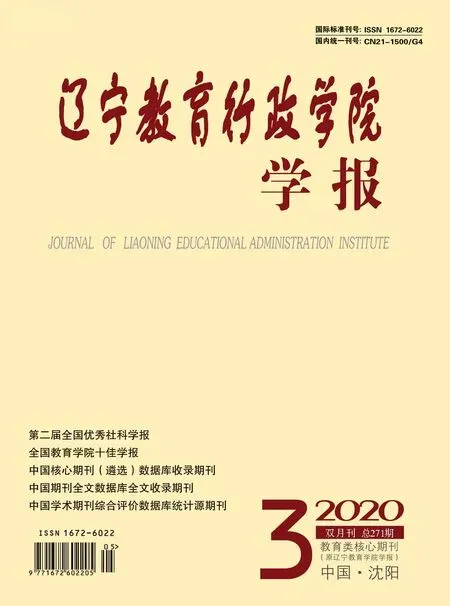生态环境安全的资本逻辑批判及其治理策略
2020-02-26张首先
马 丽,张首先
成都医学院,四川 成都 610500
生态环境安全主要包括空气安全、水质安全、土壤安全、食品安全、生物多样性安全等,它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根基和前提。生态是一种复杂的巨系统,它以“生”为出发点,以“生生不息”为价值旨归,以“存在意义”或“意义世界”的生成为价值追问。海德格尔认为:“关于存在意义的问题,是一切问题的问题。”[1](P8)人的吃、喝、住、穿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吃、喝、住、穿如果处于不安全的状态,将会对人类的发展构成重大威胁。因而,构筑生态环境安全有利于维护人类生产、生活、生存的安全之网。
一、生生不息:生态环境安全的哲学意蕴
生态“安”则人“安”,生态“危”则人“危”,生态“安危”关乎人的“安危”;反之,人的观念之“妄”、行为之“狂”同样关乎生态演变之安危。生态之“在”是人之“在”的全面展开,人根基于生态,“依寓”于世界,海德格尔对“依寓”的理解非常深刻,他认为“依寓”并非“比肩并列”而是相互依寓、同存亡、共命运。[2](P64)
一是空气安全。在人类哲学史上,气早就成为重要的哲学范畴,自然之气与正义之气成为人类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在中国哲学中,最先把气上升为哲学概念的是老子,在西方哲学中,最早认为气是世界本原的是米利都学派。气最本真的含义就是空气,空气是呼吸生物之本源存在,人有气而活(人活“一口气”),天地有气而生,气是变化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违背了气的变化规律,天地就会失序、失衡、失生。万物之生育繁衍,天地之动静聚散,无不源于气。
二是水质安全。如果说气在人类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那么,水的哲学地位并不亚于气,水的品性接近于道。在中国古代的五行说中,水居“五行”之列,在《管子·水地》篇中,管仲认为,人来之于水,水“凝蹇而为人,而九窍五虑出焉”;在《荀子·宥坐》篇中,荀子阐明了水性与人性的关系,他认为,水性与人性相通,水的“不争”“不言”“不刚”“不僵”等可比于人之“道”、“德”、“仁”、“义”等善性,水之道在于处卑示弱,水之德在于“遍予而无私”,水之仁在于“所及者生”“受恶不让”,水之义在于“万折必东”“昼夜不竭”等。水之清浊与人之清浊相“通”,水是不能玷污的,对水的污染就是对人的戕杀。
三是土地安全。人和土地是无法分离的,土地是万物之母,每一个人的吃、喝、住、穿都来源于土地,她像母亲一样生育滋养着人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孟子在《孟子·尽心》篇中明确表明诸侯之宝有三:“土地、人民、政事”。历史生活中的每一代人的历史活动都离不开土地,每一代人都有责任保养好滋养人类的土地,因为土地不是仅仅属于某一代人的,而是属于世世代代永续发展的人类。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形态,土地都不能让个别人完全所有,人们只是土地的使用者、利用者,人们使用土地的目的就是保证人与自然持续不断的“物质交换”,一旦“交换”中断,人类的生存就会戛然而止,因而每一代人都应该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保养好、改良好,然后一代一代地持续不断地把土地传给下一代。
四是食品安全。食的价值与空气、水、土地的价值一样,对于人来说具有现实的直接规定性,“民以食为天”,凸显了食的绝对重要性,而“食以安为先”强调了食品安全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决定性。食自身所蕴涵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种理性的意义只能在与人的关系中展现出来,因而,人可以利用食的工具理性实现自己的目的,但必须运用食的价值理性满足人的正常需求,如果以食品安全为代价,片面强调食的工具理性,那么人就会丧失人之为人的本性从而丧失自身。
五是生物多样性安全。生物多样性是物质循环、能量转换、信息交流、环境涵养、新陈代谢的重要载体,人与丰富多彩的生物共处于同一价值体系之中,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丰富与美丽,陶冶人的情操、启迪人的智慧,为新的创造提供不竭源泉;生物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个国家、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如果导致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人类必然失去“和生万物”的繁荣生机而陷入“同则不继”的绝境。
二、现代性危机:生态环境安全的资本逻辑批判
空气、水、土地等作为人类的“命根”,在现代性危机面前已引起人们的高度焦虑,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现代性危机,在给现代人类带来了一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风险和伤害。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逻辑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向全球扩散,其生成力量和运行方式,逐渐渗透到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血脉之中,它把人与世界之间的一切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3](P34)资本逻辑在表现它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资本的利己性、渗透性、残酷性等“恶”的本性,已一同暴露无遗。
从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到生物多样性减少,整个生态系统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全球生态环境安全的现实困境,已成为人类不可回避的焦点问题。
空气污染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健康,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称:严重的空气污染导致全球每年大约700万人过早死亡,比艾滋病、疟疾等导致的死亡人数还要多。[4](P6-7)仅 2006年,大气污染在我国所造成的环境损失与健康损失占中国GDP的7%。[5]水污染对人的伤害更为严重,被称为“世界头号杀手”,20世纪最早出现的由于水污染造成的一系列的环境灾难是日本神东川的骨痛病事件(1955)、水俣病事件(1956)、莱茵河污染事件(1986)等。同样,被称为人类母亲的大地,其污染(主要指土壤污染)同样不可小觑,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曾出现过严重的土壤污染事件。吃、喝问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前提,而这第一前提却成为人类现代化的焦灼之痛,从全球角度来看,食品安全问题更是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比如,美国加州的“李斯特菌”奶酪污染事件(1985)、欧洲“疯牛病”事件(1986)、日本“雪印乳业”事件(2000)、加拿大食品污染事件(2008)等。生物多样性保护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问题。[6](P73-74)导致生物灭绝的原因,少部分是自然原因,大部分是人为原因。中国的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同样形势严峻,从森林生态系统来看,东北、西南、华中、华南的森林生态系统减少速度较快;从草原生态系统来看,内蒙古、西藏、甘肃等地的草原“三化”程度在增加;从荒漠生态系统来看,塔里木河中下游、艾比湖地区的沙漠化面积在逐年增长;从湿地生态系统来看,长江中下游地区天然鱼类数量急剧下降、淡水资源存在隐忧;从海洋生态系统来看,胶东沿海、渤海湾的海产资源日益减少、海南珊瑚礁破坏比较严重。[7](P85-97)
空气、水、土壤等生态资源的严重污染和系统破坏,直接导致现代人类的极度恐慌,现代性危机给人类带来的物质丰裕确实是短暂的,从长远来看,如果人类的生态根基被严重破坏,所谓的物质丰裕将会成为一种想象的历史。全球发展的事实表明,很多发展中国家确实遭到资本逻辑、生态殖民的严重伤害,在国际资本的垄断和操纵之下,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分工体系的最低端,当发展中国家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到来的时候,经济发展的困境和社会动荡也会随之而来。
我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全球化背景下资本逻辑的生态殖民,从历年来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产业地图》显示的数据来看,我国的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曾遭到掠夺式的开采,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在不同区域时有出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2018年我国全面打响“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近年来,我国大气环境质量显著提高,人民的蓝天幸福感明显增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江河湖泊碧波荡漾。土壤污染治理有方,广袤净土鸟语花香。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美丽中国、美好生活的愿景正在实现。
三、借鉴与超越:生态环境安全的治理策略
推进生态环境安全的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对子孙万代的责任担当,要在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广泛借鉴、吸取世界生态环境安全建设的优秀成果,在批判、继承传统治理理念、制度、技术、模式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变革和超越。
第一,生态环境安全制度的科学化。生态环境安全制度的科学化,是生态治理主体理性精神的结晶,是对有效保证国家生态安全行为的规制与约束。它不是治理主体的主观臆造,必须遵循生态系统演进变化的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创新生态环境安全制度,并把一系列制度法治化。法治化过程能增强制度的权威性和人们对制度的忠诚感。法治化程度越高,制度对人的价值就越大,人们执行制度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就会得到有效提升。
第二,生态环境安全主体的多元化。生态环境安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等不同主体,都要在生态环境安全理念、方法、行为、过程等方面,实现整体性、系统性的变革。作为不同层面的生态环境安全主体,在设计、选择、优化、构建生态环境安全体制机制过程中,要从相互关联的整体角度,把握生态环境安全宏观结构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切实转变生态环境安全主体的传统的角色定位,确立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理念。
第三,生态环境安全技术的人本化。技术是人对自然规律的科学揭示,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和价值追求,技术的先进程度与社会的文明程度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必须摆脱资本逻辑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对技术的无情解构和扭曲,从命运共同体层面,把技术回归到本应具有的“人是目的”的本质,技术的人本化,彰显了技术的文明价值、解放价值、和谐价值、审美价值、自由价值等,人—自然—社会共生共荣的价值向度。
第四,生态环境安全模式的复合化。生态危机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理区域具有不同的特殊性,可以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比如,多元治理模式、全球合作模式等。多元治理模式内在,要求多元主体利用自身各自的优势,形成生态综合治理的强大合力,全球合作模式,客观上要求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本着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态势,主动、积极地提升国际合作的水平和层次。
第五,生态环境安全能力的现代化。生态环境安全能力的现代化,是指作为重要生态治理主体的政府,所应具备的组织、动员其他生态治理主体,运用治理理念、治理知识、治理制度、治理方法等取得生态治理绩效的能力。其能力主要包括资源配置的能力、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能力、化解生态风险和维护生态安全的能力以及社会对政府生态治理的支持能力等。
第六,生态环境安全成果的长效化。生态环境安全成果的长效化建立在有效性的基础之上。生态治理的有效性问题,就是生态环境安全的效率、效果问题,在实现同一目标的过程中,优先选择付出成本最小的方案。提高生态环境安全的有效性需要实现价值创造的最优化,价值创造主要体现在“非帕累托改变”“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三个方面。[8](P5)生态环境安全实际上就是“帕累托最优”,因为生态环境安全能给所有人带来利益,在国家统筹生态环境安全时,需要加强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部门与部门、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协同性、耦合性,减少相互之间的摩擦、冲突,避免相互运行中的“零和博弈”和顾此失彼。在整体推进生态环境安全的过程中,要把实践上升为理论、把经验固化为机制、把能量汇聚为动力、把有效治理转化为长效治理,持之以恒,久久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