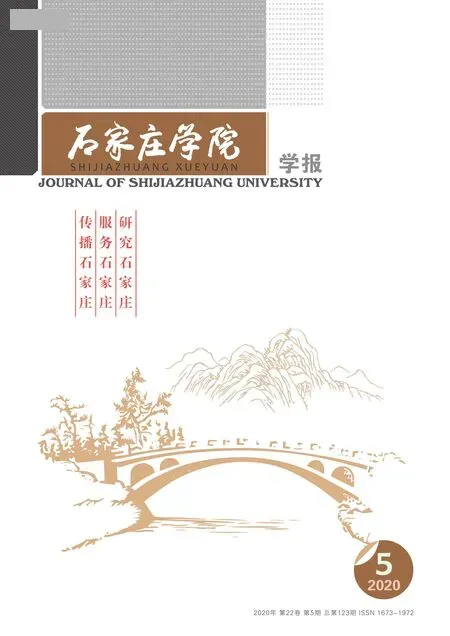《宋史》采录笔记小说途径研究
2020-02-26李颖燕
李颖燕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510000)
宋代笔记小说创作繁盛,数量与质量均达到新高度,所载内容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迹,尚真务实、详尽可信,极具史料价值,为《宋史》编撰重要取材来源,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国老谈苑》:“虽间或抑扬过情,而大致犹据实可信。如范质不受赂遗,窦仪议令皇帝开封尹署敕,赵普请从征上党,曹彬平蜀回囊中惟图书诸条,《宋史》皆采入本传中。”[1]722刘叶秋也在《略谈历代笔记》中肯定宋代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由于宋代史学昌盛,文士多精史笔,故历史琐闻类笔记最为发达,其特点是以‘亲历’‘亲见’‘亲闻’来叙述本朝的轶事与掌故,内容较为切实。”[2]84
取材途径,是指编纂者获取素材的路径,即借由何种方式接触到引用内容。研究《宋史》采录笔记小说的路径,可以分析反映史书对笔记小说的态度与处理方式,有助于探究正史与小说之关系,构建中国叙事体系。
一、直接采用笔记小说
直接采用笔记小说,指《宋史》编纂者接触的是笔记小说最初的文字,即笔记小说为第一手史料,采录内容直接脱胎于此。袁桷在《修宋辽金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中提出修史应广采史料:“一纂修史传,必当先以实录小传,附入九朝史传,仍附行状、墓志、神道碑,以备去取。”[3]1848其中谈到的笔记小说有25部:《涑水纪闻》《邵氏闻见录》《春明退朝录》《梦溪笔谈》《龙川略志》《归田录》《续归田录》《可谈》《谈丛》《师友杂志》《晁氏客语》《师友谈记》《杨文公谈苑》《麈史》《能改斋漫录》《石林燕语》《嘉佑杂志》《东斋纪事》《谈圃》《渑水燕谈》《避暑录》《却扫编》《挥麈录》《挥麈录后录》《挥麈录三录》。当然,这只是修史筹备阶段的书目,《宋史》编纂过程中考证的笔记小说不局限于此。
根据笔记小说是否为唯一记录者,此种取材途径又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采录内容出自笔记小说,且未被其他书籍转载。如“崔福故为群盗”条,早于《宋史》记载此事的仅《齐东野语》一书,且二者文字几无差异:
崔福,故群盗也,尝为官军所捕。会夜大雪,方与婴儿同榻,儿寒夜啼,不得睡觉。捕者至,因以故衣拥儿口,儿得衣,身暖啼止,遂得逸去。因隶籍军伍,累从陈子华捕贼,积功至刺史、大将军。[4]243
崔福者,故群盗,尝为官军所捕,会夜大雪,方与婴儿同榻,儿寒啼不止,福不得寐,觉捕者至,因以故衣拥儿口,遂逸去。因隶军籍。初从赵葵,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又累从韡捕贼,积功至刺史、大将军。[5]12564
《齐东野语》为南宋周密据“耳目闻见”所作,“多载南渡以后时事”[4]386,有极高史料价值,李慈铭赞其“宋末说部可考见史实者,莫如此书”[6]974。对比两段文字,无较大出入,且并未发现其他书籍有类似记载,因此应是《宋史》直接引用《齐东野语》。
第二种情况,有其他书籍转载笔记小说内容,但未改动文字。《宋史》的许多参考书目曾引用笔记小说,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宋朝事实类苑》《三朝北盟会编》。但这些书籍常采取“全录原文,不加增损”[1]642的转载方式,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王文正笔录》:“曾练习掌故,所言多确凿可据,故李焘作《通鉴长编》,往往全采其文。”[1]718因此,无论《宋史》采录是否借助中间媒介物,接触到的都是笔记小说最初的文字,都属直接引用。如“赵普坚持举荐太祖不喜之人”一事,笔记小说《涑水记闻》、史著《五朝名臣言行录》、《宋史》记载如下:
太祖时,尝有群臣立功,当迁官。上素嫌其人,不与,赵普坚以为请。上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将若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上怒甚,起,普亦随之。上入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上寤,乃可其奏。(右皆赵兴宗云)[7]10
太祖时,尝有群臣立功,当迁官。上素嫌其人,不与,赵普坚以为请。上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将若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上怒甚,起,普亦随之。上入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上寤,乃可其奏。(记闻)[8]
有群臣当迁官,太祖素恶其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竟得俞允。[5]8940
此事记载赵普不畏皇威,坚持举荐,突出其以天下事为公、刚毅果敢的精神。这段文字最初载于《涑水记闻》,文末标记“右皆赵兴宗云”,点明信息为作者亲身听闻。《五朝名臣言行录》诸字未改,直接引用,且在文末标记“记闻”,进一步佐证引自《涑水记闻》。因此《宋史·赵普传》采录此事时,无论经由哪部书籍,所见均是笔记小说原貌。再如“王安石恶无择”一事,最初载于《邵氏闻见录》,后被《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等书转载,但内容与前者无异,因此《宋史·王安石传》无论借由何书引用此事,其取材途径均属直接采用。
值得注意的是,中间媒介物的转载,有利于笔记小说的传播与保存。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跋》所言:“宋一代杂史、小说家不存之书,亦可赖以传其一二。”[9]17江少虞作《宋朝事实类苑》,记宋太祖至宋神宗时期之事,引用大量笔记小说,如《涑水记闻》《东轩笔录》《归田录》《青箱杂记》《景文公笔记》《杨文公谈苑》《湘山野录》《梦溪笔谈》《春明退朝录》《丁晋公谈录》《东斋记事》《渑水燕谈录》《玉壶清话》《倦游杂录》《金坡遗事》《王文正公笔录》等。此书与笔记小说同作于宋代,引用内容颇为可信,可补失传之书。如《杨文公谈苑》原书已佚失,《说郛》与《类说》对其引用条数较少且内容多有删减。而《宋朝事实类苑》录入此书一百多条,较好地保留原文内容,其中不乏《宋史》采录条目。如“仲放母焚其笔砚,劝其转居穷僻”一事,为《宋朝事实类苑》所录,且被《宋史·仲放传》征引。
二、间接采用转引史著
间接采用转引史著,指中间媒介物(一般为史著)改动笔记小说内容,《宋史》以此为底本进行采录。但文字的变动也是基于史书与小说的叙事差异,正史的采录亦可体现其行文诉求。因此,借由这种途径采录的笔记小说内容同样具有研究价值。
有一群在博物馆参观的年轻人,听了这个故事都笑了起来。原来大文豪鲁迅,也曾这样痴迷爱情。这也正如他本人所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宋代笔记小说的补史之功被普遍接受,为史著所采。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跋》中提到,著书“分注、考异详引他书……《东斋纪事》《涑水记闻》《东轩笔录》《湘山野录》《玉壶清话》《邵氏闻见录》《笔谈》《挥麈录》之类”[9]17。但著述者通常会根据史家笔法,对笔记小说内容进行考证、调整,“递相稽审,质验异同”[1]272,使其合乎史书叙事行文。改造后的文字自然要比之前更贴近信史,《宋史》选取传主事迹时,也通常会以此为底本。如“韩亿出使契丹”一事,《江邻几杂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记载如下:
韩忠宪使虏,其介,刘太后之姻,庸而自专,私于虏使云:“太后言两朝欢好,传示子孙。”韩了不知,忽置一筵,遣臣来伴,因问太后有此语,何故不传?忠宪答云:“皇太每每遣使,使人帘前受此语,戒使人令慎重尔。”于是以手顶礼云:“两朝生灵之福也。”[10]175
乙丑,工部郎中、龙图阁待制韩亿为契丹妻生辰使,崇仪副使田承说副之。诏亿名犯北朝讳,权改曰意。承说,皇太后之姻也,庸而自专,妄传皇太后旨于契丹,曰:“南北欢好,传示子孙,两朝之臣,勿相猜沮。”亿初不知也。契丹主命别置宴,使其大臣来伴,且问亿曰:“太后即有旨,大使宜知之,何独不言?”亿对曰:“本朝每遣使,太后必于帘前以此语戒敕之,非欲达于北朝也。”契丹主闻之,大喜,举手加额曰:“此两朝生灵之福也。”即以语附亿令致谢。时皆美亿能因副介失辞,更为恩意焉。[9]2413
除龙图阁待制,奉使契丹。时副使者,章献外姻也,妄传皇太后旨于契丹,谕以南北欢好传示子孙之意,亿初不知也。契丹主问亿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独不言?”亿对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欲达于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两朝生灵之福也。”人谓副使既失辞,而亿更以为恩意,甚推美之。[5]10298
《续资治通鉴长编》文末记“此据苏舜钦所作亿墓志及江休复杂志删修”[9]2413,故《江邻几杂志》为此段文字来源之一,但《宋史》中副使的背景介绍,“太后即有旨,大使宜知之,何独不言”的对话内容,“大喜”的心理活动,又都是《续资治通鉴长编》所增内容。因此,《宋史》的取材途径为转引史著的间接采录。
再如“赵德昭自刎”一事,《涑水记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赵德昭传》记载如下:
魏王德昭,太祖之长子,从太宗征幽州,军中夜惊,不知上所在,众议有谋立王者,会知上处乃止。上微闻,衔之,不言。时上以北征不利,久不行河东之赏,议者皆以为不可,王乘间入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未晚也!”王皇恐还宫,谓左右曰:“带刀乎?”左右辞以禁中不敢带。王因入茶果阁门,拒之,取割果刀自刭。上闻之,惊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痴儿,何至此邪!”[7]36
初,武功郡王德昭从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上所在,或有谋立王者,会知上处,乃止。上微闻其事,不悦。及归,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议者皆谓不可,于是德昭乘间入言,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惶恐,还宫,谓左右曰:“带刀乎?”左右辞以宫中不敢带。德昭因入茶酒合,拒户,取割果刀自刎。上闻之,惊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痴儿,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谥曰懿。[9]460
四年,从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上所在,有谋立德昭者,上闻不悦。及归,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德昭以为言,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闻惊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痴儿何至此邪!”赠中书令,追封魏王,赐谥,后改吴王,又改越王。[5]8676
《涑水记闻》文末有“王宜父云”,故司马光是根据所闻记载,事应首出于此。《续资治通鉴长编》文末记“此据司马光《记闻》”,佐证其直接采录于笔记小说。《宋史》所记文字如“军中尝夜惊”“上闻不悦”“太原之赏”“赏未晚也”等,同于后者,异于前者。因此可以推断,《涑水记闻》首次记载此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其转载改写,《宋史》又以后者为底本进行采录,这也是间接采用转引史著的常规流程。对比三段文字,可发现从笔记小说到史著,再到正史,文字逐渐减少,情节逐步简化,这些变化也是史家与小说家叙事差异的具体表现。
三、采录路径之对比
《宋史》编纂者对两种采录路径而来的内容,在处理上有所侧重,以完成传记体系的建构,满足史书功用之诉求。
首先,在史料价值层面,直接引用的史料价值低于间接引用。“士大夫作小说,杂技所见闻,本以为游戏”[18]33,创作态度的“游戏性”与编纂过程的“随意性”,让笔记小说重记录、轻考证,使史料价值大打折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渑水燕谈录》“所记诸条,多与史传相出入。其间如谁传佳句到幽都一诗,乃苏辙使辽时寄其兄轼之作,而误以为张舜民;又如柳永以夤缘中官,献醉蓬莱词,为仁宗所斥,而以为仁宗大悦之类,亦间有舛讹”[1]718。而间接引用的采录途径,经过史料媒介物的稽审考证,删改失真内容,文献的史料价值有所保证,如李心传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时对司马光的《涑水记闻》进行考辨,认为其虽“朝廷政事,公卿士大夫议论,宾客游从,道路传闻之语,莫不记录”,却“未暇照据年月先后,是非虚实,姑记之而已,非成书也。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孙植皆不以示人,诚未可传也”。[19]1692
其次,在叙事内容层面,直接引用多体现人物性情,间接引用多佐证朝政大事。笔记小说善抓取精妙细事,展现人物性情风骨,如王思任在《世说新语序》中说:“前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小摘短拈,冷提忙点,每凑一语,几欲起王、谢、桓、刘诸人之骨,一一呵活眼前,而毫无追憾者。”[20]528直接引用的逸闻轶事,虽史料价值不高,却可使传主形象更全面、完整、饱满,亦可增加史书的文学性与可读性,如黄宗羲言:“叙事须有风韵,不可擔板。今人见此,遂以为小说家伎俩。不观《晋书》《南北史》列传,每写一二无关系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动,此颊上三毫也。”[21]271但朝政之事关乎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真实是此类事件的第一原则与核心价值,如刘知己在《史通》谈到:“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擅雄伯,自相君臣。经书某使来聘,某君来朝者,盖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国之大事,不可阙如。”[13]231故对于涉及国家大政之事的内容多为间接引用,以确保史料价值。
再者,在结构编排层面,直接引用多入文末补叙,间接引用多入主干叙事。叙事结构的编排是文章布局的重要一环,正史传记叙事结构大体由主干叙事、文末追述二部分组成。主干叙事是对传主生平事迹的勾勒,描写方式大致遵循“姓名——籍贯——家世——幼年——仕途——逝世”模式,这部分内容是传记文之主体,对文献史料价值要求较高,故采录路径多为间接引用。文末追述是对传主生平介绍完毕后,追叙一些小事,以多方面展现传主性情,这类事迹大多为琐粹小事,无关国家军政、劝善惩戒,故多采取直接引用。
综上,《宋史》通过直接采用和间接转引两种途径获取笔记小说内容。《宋史》的采录肯定了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对其内容之采录也印证了正史之叙事功用与逻辑。探究二者的关系,有助于还原古人的叙事观念,构建中国叙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