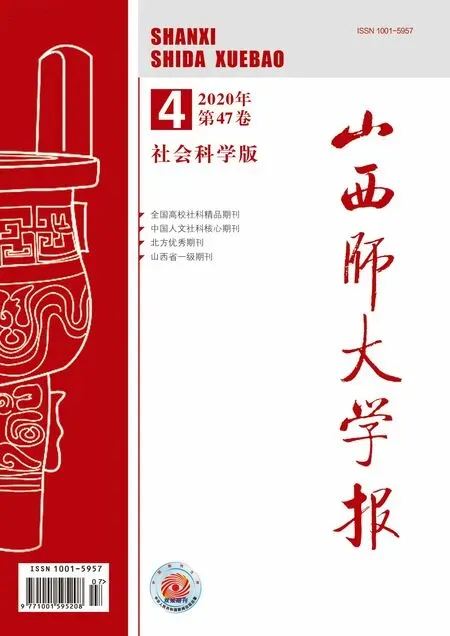我们从何而来,又想到何处去:’95世妇会与全球化
2020-02-26闵冬潮
闵 冬 潮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今年是’95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5周年,本应是全球妇女在世界各地纪念这一盛会之年,但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迫使这些全球性的纪念活动不得不按下暂停键。
此时此刻,全球化向哪里去,似乎谁也说不清。在此背景下,再谈全球化与妇女性别研究,真有些不知从哪儿说起。
在此,我想以“我们由何而来,又想到何处去?”(1)这句话出自于’95世界妇女大会秘书长蒙盖拉夫人,具体引文见后。为题,先围绕着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这一主题,谈谈我和我们对其历史、理念的认识,再转入我对’95世妇会后妇女性别研究的一个案例——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的观察,来看我们是如何在全球化中将世界和本土接轨的。之所以选择这个案例,除了我对其做过实地考察之外,更想通过这一实例来展现在’95世妇会前后,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共卫生与妇女/性别研究的理念如何走进中国的社会和寻常百姓家。最后,返回到全球化的主题。
一、对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我们知道多少?
我对世妇会的认识晚了20年。
197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第一次在墨西哥城召开,当时正值中国文革后期,闭关锁国,一般民众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文革结束,国门重启,1980年,第二次世妇会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印象中,见到报章消息,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率团参加了此次大会。这回,我才第一次听说有这个会议。这到底是个啥会?没人深究。那时,妇联代表国家参与国际事务,主要具有外交上的意义,与普通民众好像关系不大。到了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妇女研究和女性主义浮出历史地表,世妇会已召开了三次,但国门刚刚打开,相关信息很少,我们对此也只能是一知半解。
直到1991年,中国政府作出承办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FWCW)的决定,我们才开始有了了解这个世妇会是怎么回事的需求。因为会在中国开,有了切身的关联,也才感到它对我们的重要。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全球50,000名妇女在北京聚首,这么大规模的外国妇女进入中国,好像也是自1949年以来的头一回。
我当时人在国外,没参加这次大会。事后补课,对联合国妇女大会的历史才略知一二。人称这次大会标志着“全球女性主义的诞生”。
为什么这么说?看一眼95大会的前史就会知道,从联合国1975年妇女大会到1995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20年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5年到1985年,在1975年墨西哥城的第一次大会和1980年哥本哈根第二次大会上,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妇女之间充满了敌视、误解,痛苦激烈的争论不断。争论和斗争的焦点到底在哪里?比如,哥本哈根大会上,来自第一世界的妇女就认为,全世界妇女面对着共同的问题,诸如性、生育等,因此,妇女之间在阶级、种族、国族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而来自第三世界的绝大多数代表和第一世界的少数代表则坚持,性别压迫是与国族、阶级和种族的压迫分不开的。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成为哥本哈根大会争论的焦点问题。因为参加会议的西方妇女们觉得只有她们才代表着真正的女性主义,而来自后殖民地国家的妇女感到这是另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无疑,哥本哈根大会暴露了东西方、南北方之间妇女们的深刻分歧。建立全球女性主义之间的联系和开展运动,似乎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十年过去了,在1985年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上,这种对立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首先是“天时地利”,参加会议的总人数大约是13,500人,南半球妇女人数明显增加,其中,仅肯尼亚妇女就有3,000人,(2)NILUFER C, CAREN C and AIDA S:“The Nairobi Women's Conference: Toward a Global Feminism”, Feminist Studies, 1986,12 (2), Summer,402.人数的增加也就意味着力量对比会发生变化。另外,会议的地点选在非洲,使得第一世界的妇女亲眼看到了第三世界的妇女深受经济危机所带来的食品、燃料和饮水等方面的生存困境。生存问题直接进入了女性主义的“视野”。同时,第三世界的妇女也认识到,为妇女的特殊问题而斗争也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议题。在此基础上,转机发生了,大家开始承认妇女在阶级、种族、国族之间的差异绝不可“忽略不计”,要看到妇女们所面对的问题、所代表的观点是多种多样的。与会妇女之间的认识和了解加强了。
发生这种巨大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来自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加速,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形势远不如十年之前。不论是第一世界的妇女,还是第三世界的妇女,都受到了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伴随而来的还有意识形态的右倾趋势增强,例如,保守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抬头,这种转向加剧了妇女的性别次等地位,这些类似的经历,促使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妇女从自身的处境出发,提出诸如女性的贫困化、贷款债务、国际军事化、暴力等问题,并就此进行了广泛和富有成效的对话。会议讨论的质量比联合国前两次大会也明显提高了,与会代表在肯定妇女之间的多种差异的前提下,开诚布公地讨论了什么是发展的本质,如何理解女性主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毕竟,1985不是1975,内罗毕也不是哥本哈根!
从内罗毕大会到北京大会,全球的女性主义者们致力于消除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妇女之间的误解,创造世界各国妇女之间的联盟。于是,从地区到全球,跨国妇女运动网络逐渐形成。当然,全球女性主义理念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演变。不能否认,这一变化与女性主义者们对全球化的研究密切相关。在1970年代,女性主义对全球化的调查研究就起步了。由于关注性别问题,女性主义关于性别与全球化的研究无一例外地从“女人在哪”和“男人在哪”开始。她们首先发现,从上世纪70 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工业转型,不论是第一世界的女工,还是第三世界的农村妇女,受到的冲击都非同小可。于是,女性主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可以说,女性主义研究者对全球化研究是与经济全球化同步的,并且从认识论上打开了新的思路。
可以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使全球女性主义的发展达到高潮。从代表们提出的议题来看,从环境保护到人权,从人口问题到社会发展,无一不涉及关乎全球发展的大问题,以至于大会秘书长蒙盖拉夫人表示“根本就不存在妇女的议事日程这回事,只存在一种国家的,一种全球的议事日程。但是妇女们在这些问题上将有她们不同的重点和不同的优先的考虑,这些又建立在她们由何而来,又想到何处去的基础上”(3)AMEDE O L: “Feminism, Globalisation, and Culture: After Beijing”,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1997(4),363.。这里,蒙盖拉夫人强调的“妇女问题”不是“妇女的问题”,而是国家和全球发展的问题,旨在转变主流社会那种将妇女、性别问题边缘化的一贯做法。同时,她也期待着妇女们站在全球发展的新高度,来开拓全球女性主义的新视野。这一视野中也必须要考虑妇女们从何而来,又想到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是说,每个国家、民族的妇女所面临的问题是有区别的,而且妇女走的道路与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方向是分不开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互为表里。
女性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到来了,《行动纲领》的制定就是其明证。它提出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诸如妇女人权、妇女与发展、对妇女的暴力、妇女健康、生育健康,等等。重中之重是贫困的女性化问题。现在看来,全球女性主义的视野与议题仍然不过时,“全球化思考,在地化行动”(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仍需大力提倡。
带着对世界妇女大会“前史”的一知半解,中国妇女参与了北京世妇会的一系列活动。从我们中国妇女的角度来说,北京世妇会无疑像是一阵春风,一扫1980年代末之后的沉闷气氛。很多中国妇女研究的学者和行动家,都用打开门窗,看到一个新世界来形容参与这次大会的激动心情。“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表达了这种与世界接轨的急切心情。(4)参见黄婉玲主编:《女性的反响——一群曾参与九五妇女大会国际筹备会议的中国女性的心声结集》(内部读物),北京:福特基金会,1995年。接轨,这一形象的比喻建立在这样一种想象之上:中国长期以来被排斥于国际社会之外,当她回到国际社会之时,应该把自己的“轨道”与国际对接。中国与世界接轨的这一重任,首先就由中国妇女担了下来。
对中国妇女研究和运动来说,“接轨”在理念上和组织上双管齐下。理念上,主要是将gender(社会性别)概念引入中国。组织架构上,则是将NGO(非政府组织)引入中国。没有思想理念的转变,缺乏组织架构的衔接,就像铁路扳道岔,轨道接不上,车行受阻。于是,’95世妇会在北京召开时,我们迅速地与“国际接轨”,期望赶上“全球女性主义”这趟车,尽快加入国际女性主义的大家庭。不错,这些年跨国妇女运动的实践,使我们增长了见识,加强了力量。然而,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之后,我们会发现,“全球女性主义”更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在跨国妇女运动的多重方向的轨道上,我们需要不断地问自己:我们走到了哪里?
二、通过“做项目”,我们走了多远?
1997年夏天,我去南京参加中国妇女与发展会议。会上会下,经常听到一个词就是“做项目”。大家一见面,都互相问道有没有项目。听起来,几乎与会的每位妇女研究的学者和活动家都多多少少参与了一些项目,这些项目大多来自国际组织、国外基金会。对我来说,这还真是个新鲜事。在我的经验里,自上世纪80年代参与妇女研究的教学与研究,基本上就没有做项目这一说,没钱也干了不少事。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很好奇,为什么大家要做项目?这些项目从哪来的?到底对中国的妇女与性别研究意味着什么?
在这次会上,我还遇到了一个新型的NGO——云南生殖健康研究学会。来自昆明医学院的张开宁教授是该研究会的创始人和会长。在他的发言里,多次提到女性主义对妇女生育健康研究产生的影响。据我所知,自20世纪80年代妇女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后,主流学术界很少有人使用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男性学者更是避而不谈女性主义。为什么张教授敢于大谈女性主义?而这样一个具有“前卫”思想的组织出现在中国一个偏远穷困的省份——云南,他们是如何把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同当地现实结合起来的?怀着这样一种好奇心,我决定把该研究会作为我的博士研究田野调查对象之一。
1999年3月,从北京乘火车到昆明,开始了我的田野调查。这两天两夜的路程是如此的漫长,使我对什么是“偏远地区”有了切身的体会。这种“偏远”首先是由于云南所处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偏远”还往往与贫穷相联系。然而,自1990年代中国步入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之后,云南在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上所处的边缘位置却为它提供了与国际机构接轨的机会。在所谓“落后地区”出现了以“发展”“扶贫”“环境保护”等新的国际“话语”。众多的国际组织、基金会在云南派驻机构和人员。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昆明一地,就有美国福特基金会、香港乐施会、英国儿童救助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劳工组织、欧盟、美国温洛克国际农业开发中心等十数家机构的派出人员,在云南从事与扶贫、禁毒干预、林区和江河保护、传统文化,以及与社区自立的尝试、妇女儿童权益的保障、跨境人口问题的疏导、基层民选的观察和扶持,等等项目。(5)郑凡等:《全球化视角的中国云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1页。在这种迅速与国际接轨的形势下,云南也由原来的“偏远地区”进入了全球化的网络,这些网络,不断改写着中心与边缘的“位置的政治”,而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可以说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组织之一。
到了昆明之后,我首先想知道:为什么在云南这样一个“偏远地区”会出现当时颇具“先锋”意义的生育健康研究会?张开宁告诉了我这个组织成立的来龙去脉。1992年,张开宁在英国访学时,看到一份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双年度报告,内容是关于人类生育的专题报告。他发现,从1980年代开始,人类生育方面的研究已经注重应用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而且女性主义的观点越来越多。在避孕节育措施方面有不少很有见地的论文,证明女性能不能控制避孕药剂、方法,对整个世界影响是不一样的,等等。这些观点在国内是闻所未闻,对从事公共卫生研究的张开宁震动不小。(6)1999年3月笔者在昆明对张开宁的访谈。
此时的张开宁正在剑桥进行博士学位研究。但不久由于偶然的原因,事情发生了变化。1992年,张开宁参加了英国发展研究所(IDS)组织的一次关于中国农村妇女生育健康的学术研讨会,会上遇到了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他们手里拿着福特基金会有关农村贫困地区生育健康的一个三年的大项目,正在满世界寻找合作者,到中国贫困地区的农村做调查。为了给他在昆明的教学、研究找到机会,张教授下决心放弃了继续在剑桥读博士的机会,带着这个三年的项目回到了云南。
回国之后,张开宁要面对的现实是国内科学研究的因循守旧。妇女健康研究局限于生物医学或者人口统计学领域,非常缺乏医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研究。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同样也很少,非政府组织(NGO)还是个陌生的事物,更不要说他们之间的合作了。因此,他回到昆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搞社会科学和搞医学的人聚在一起,开展有关方面的学习与研究。
1994年,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正式成立了。“该研究会是一个以中青年研究者为主体的朝气蓬勃且富有奉献精神的群体,会员来自医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人文科学及法学等领域,会员也包括妇女活动家及医务工作者。这些会员每个月在昆明有一次学术活动。该研究会出版《生育健康与社会科学通讯》,组织学术讲座,为项目提供设计及指导,将有关资料译成中文,积极交流,并在云南省就生育健康的有关话题进行研讨,寻找问题并力图解决”(7)白梅:“序”,见赵捷、张开宁、温益群、杨国才主编《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页。。以上描述来自一位福特基金会的官员,这是个比较“官方”的评论。而私下里的访谈,则让我了解到研究会很中国也很“云南”的一面。张开宁这一代人都是上山下乡的知青,文革之后恢复高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分布在昆明的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因为昆明城市不大,这些过去的知青伙伴很快就被张开宁联络到了一起。可以说,云南当地原有的知青网络为研究会直接借用,并为下一步的跨学科研究、基层农村的调查与服务、政府部门政策与职能的改进奠定了基础。
生育健康概念的出现,标志着对人口与发展的认识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冲击着以单纯控制人口增长数量为目的的人口政策,强调要以人为中心,将解决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并重,逐步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状况。因此,这也就意味着过去那种妇幼保健的思维模式或做法已经远不能适应生育健康的需要。必须改变那种仅仅为了家庭幸福和下一代的健康才关注妇女,要把妇女的权益及妇女健康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生育健康的概念从一开始便带着以妇女为中心的鲜明特点。
研究会最初进行的讨论,围绕着“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这个议题, 讨论始终在两个维度中进行:一是基于中国是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实情,以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参与全球生育健康的讨论;二是以此为议题,在研究会内部开展医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交流与培训。可以说,研究会从一开始就具有中国的和跨学科的特点。
研究会里大多数人同意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这一新名称,然而,对此又有多种诠释。这一看来是不言而喻、不论自明的论点,首先在翻译上出现了疑问,张开宁认为:“中文里讲的‘中心’,往往就是要被抓住且抓牢的东西。而在英文中,这种为了某种目的要去牢牢抓住的东西,却应当是objects或 targets,是与 Women-centered背道而驰的!”(8)张开宁:“综论(一):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概念、背景及多学科研讨的价值”,见赵捷、张开宁、温益群、杨国才主编《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2页。他所关注的生育健康的概念是以妇女为主体,而不是把妇女作为客体来“抓”。更重要的是,如何立足于东方文化与中国国情来理解和发展我们自己的生育健康的理念和政策。
实际上,张开宁注意到了对“中心”的不同解释会带来对“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的概念的不同理解,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一个问题。在讨论中,大家注意到,在计划生育的工作中,妇女一贯是被作为主要的“防范”对象,而不是服务对象。据有关调查,当时几乎90%以上的避孕工具和药品是由妇女使用的,多数绝育手术实施于妇女,还有成千上万例人工流产手术,等等。如果,把妇女作为客体的“中心”来抓,那么这一现实早已实现,并在继续进行着。(9)赵捷:“综论(二):生育健康以妇女为中心——定义、内涵及研究和服务模式构想”,“生育健康中的女性困惑与启示”,见赵捷、张开宁、温益群、杨国才主编《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5、54、167、182页。
在确立了妇女在生育健康中的主体地位之后,如何尊重妇女的看法,力求从妇女的角度看问题,使妇女真正受益,成为研究会追求的目标。而如何使妇女真正受益?我当时了解到,研究会与云南省计生委合作,提出了怀孕妇女有“知情选择”的权利,开始改变计划生育工作中那种生硬强制的做法。具体来讲,就是针对云南贫困地区双北县缺少女乡医,解决孕妇要翻山越岭去看医生的问题,开展培训女乡村医生的工作,等等。这些都是把“以妇女为中心”落实到了实处的结果。
当研究项目向纵深发展时,面对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妇女群体,如何把外来的理念与“当地”妇女主体意识接轨,可能是当时要面对的难题。例如,当研究会的赵捷和她的研究团队去苗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她们发现当地妇女在“选择的权利”的问题上,并不像女性主义者想象得那么简单。比如白天开会时,请苗寨妇女们把当地的常见病排序,她们把家里老人孩子的病排了一堆,唯独没有排上自己的病。到了晚上,这些妇女到赵捷她们团队的住地,才说一些白天公开场合不愿说的事,非常强烈地想知道如怀孕、例假等妇女自身的问题。这件事,使研究者很是犯难,到底什么是妇女们的真正意愿?是不是一个好女人就不应该过多地考虑自己?(10)1999年3月笔者在昆明对赵捷的访谈。
显然,当妇女健康的问题与贫困、传统文化及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等范畴相遇时,如何做到“以妇女为中心”便成为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了。研究会的女性主义研究者们从研究项目中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一方面与医学界合作,为这些妇女编写一些有关妇女健康的通俗易懂的手册,让她们了解关于自身健康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拓宽关于妇女与性别的研究范围,在1999年成立了“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小组”(GAD),将妇女健康问题与贫困、性别与发展等议题连接起来。
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的建立,突出地呈现了通过做国际项目进行“接轨”的特点。首先,是全球化的网络较早地进入了云南,张开宁和研究会作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起到了连接国际网络(世界卫生组织(WHO)、福特基金会、英国发展研究所(IDS)等)的关键作用。同时,国内改革开放的局面对生育健康提出了新的研究与服务的要求,研究会与云南各级地方政府的合作与互动,对推进这些改革工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研究会成员带着项目直接进村,不但获得了第一手的资料信息,同时,也将妇女生育健康工作落实到了最基层。这样一种“接轨”的模式,也是接地气的行动,显示了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具有实践性和实用主义的特点。在短期内,研究会快速消化吸收国际项目的理念、方法,“全球化思考,在地化行动”的特点,一目了然。
三、我们想到何处去?
自’95世妇会之后,25年弹指一挥间。可以说,“全球女性主义”的提法已经不再陌生,但在诸多全球问题上,仍然无法达成妇女们的“全球共识”。比如,仅从妇女与发展问题来看,《行动纲领》主要考虑到妇女个人的权利,而忽视了妇女权利的整体发展,特别是与经济全球化、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相关的妇女经济权利。开出来的药方,当然也治不了大病。例如,被大会推荐的小额贷款问题,当年曾轰动一时,在发展中国家,大小项目在滚动,中国也不例外。这些项目确实给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妇女们提供了机会,以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蛋糕,但最终能分享到多少?现在看来,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再从与本文讨论的问题联系密切的妇女与健康问题来看,虽然有妇女本身的特殊问题需要特别关注,但如果没有或缺乏全民医疗体系的保障,对大多数妇女来说,健康就是一句空话。看来,当年困扰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特别是贫困的女性化问题,对全球妇女来说,至今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
全球化思考,代替不了自己的思考。我们先从认识全球化起步。
怎样看全球化?这本身就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葡萄牙学者鲍温图拉·得·苏撒·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在这方面的研究,或许对我们认识全球化有所帮助。他提出,不存在单一的全球化,必须要研究全球化的多样性。他提出了全球化的四种形式。第一种,全球性的地方主义(globalised localism),这是以跨国公司、美国化为代表的全球化;第二种,地方化的全球主义(localized globalism),主要以全球主义强加于“边缘”的国家影响为代表,如滥伐森林,自由贸易区等;第三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指NGO,环保和工会组织等全球性联合的发展;第四种,人类共同遗产的保护,包括臭氧层、亚马逊河等。桑托斯同时强调要区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区分霸权主义的和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他认为,第一二种是自上而下的全球化,而第三四种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注]Santos, Boaventura de Sousa “Towards a multicultural conception of human rights”, in FEATHERSTONE M and LASH S (eds.), Spaces of Culture, City, Nation, World,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1999, 214—229.桑托斯作为一位研究法律的社会学家,关心的是全球化与人权问题。他提出最终的中心任务是将人权理论与实践从全球性的地方主义转换为世界主义。桑托斯的贡献在于,一是看到了反对经济全球化的运动其实也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运作的;二是要区分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的不同种类的全球化过程。那么,我们需要的是哪种全球化呢?
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大暴发,对全球化的声讨和呼吁不绝于耳。全球化,再次成为人们关注和思考的“热点”。在“闭关锁国”的同时,也催生着对全球化的新思考。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急迫的全球性问题,促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全球化的复杂性和矛盾。一方面,各个地区、国家的隔离是抗击疫情的必要措施,势必引起民族主义的抬头。另一方面,新冠病毒不断冲破地区和国家的边界,无孔不入,使国家领土的概念在病毒面前失去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需要世界各国的互相支持与合作。如何平衡与协调隔离与反隔离的矛盾,不但是WHO的难题,也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地方、每个国家要面对的困境。在世界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的情况下,与世界共享我们的经验和知识,在这个时代变得更为迫切。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另一个急迫的问题是建立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全民医疗保健系统。我们所见的事实是,公共卫生体系的失灵造成的灾难深重。凡是建立了全民医疗保健体系的国家和地区,在这次疫情中都发挥了比较好的作用,如在我们的邻居中,有经济发达的国家——韩国,也有发展中国家印度的喀拉拉邦,都交出了不错的考卷。反之,那些没有建立这一体系的国家,在疫情面前不堪一击,美国即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例。从全球来看,除非所有的人都得到医保,否则就谁也没有安全。如果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换取自身的安全,最终是把所有的入都带向毁灭。因此,如何在中国建立和完善全民医疗保健体系,将是疫情之后重要的任务之一。妇女/性别研究已经有如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等的宝贵经验可寻,在这次疫情中也有大批女性医务工作者的突出贡献,我们期待着,在疫情之后,将会有更多的妇女/性别研究者参与到建立完善公共卫生和全民医疗保健体系的工作之中去。在“全球化思考,在地化行动”的同时,还必须有“在地化思考,全球化行动”,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