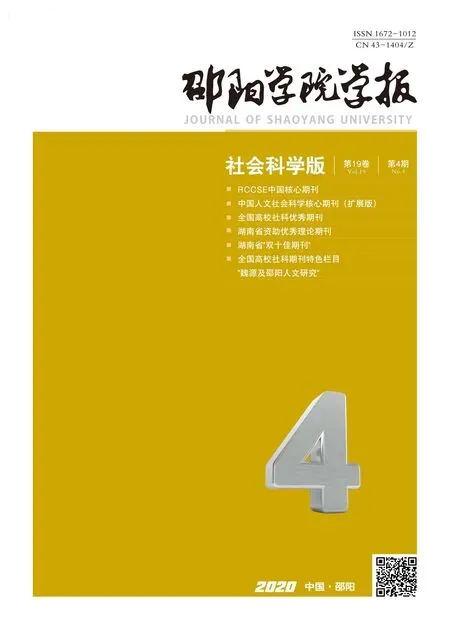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制度研究
2020-02-26冯晓青
冯晓青, 郭 珊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 北京 100088)
商标合理使用制度源于美国,是美国为了限制商标权不适当扩张而发展出来的商标侵权抗辩制度。其主要包括叙述性合理使用和指示性合理使用,还有新闻报道中使用、滑稽模仿等非商业性使用。我国商标法仅对叙述性合理使用进行了明文规定。
在我国,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制度最早规定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1999年发布的《关于商标行政执法中若干问题的意见》(现已失效)中。而后2002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商标法实施条例》)也作了规定(1)其第49条规定:“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但是其仅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直到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才将叙述性合理使用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
《商标法》虽然对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作了规定,但内容较为简单,也基本上是借鉴国外,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不论在理论界还是实践界都存在诸多争议。由于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是外来制度,因此本文将从其来源开始分析,探究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理论基础、性质地位以及认定标准。在上述基础上,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为我国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制度提出完善建议。
一、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概念与理论基础
(一)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概念
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指的是生产经营者在描述商品或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产地、质量、功能等特点时,使用的描述性表达与他人的商标相同或相似,但由于使用的善意性和正当性而不构成侵权的情形,也被称为描述性合理使用或说明性合理使用。现行《商标法》第59条第1款对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进行了规定,但其使用的是“正当使用”而非“合理使用”(2)笔者认为,这二者所指相同,且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常被混用,因此本文并不加以区分。,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情形:
1.对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使用
根据《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指的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约定俗成的名称、图形、型号,其中名称包括全称、简称、缩写、俗称”。这里的通用名称和型号是为了交易的方便和效率而存在的商品的指代性符号,通用图形又是商品的天然属性或常规形状。如果将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注册为该类商品的商标,其他生产经营者在指称自己的商品时会受到诸多限制,进而阻碍交易的正常进行,因此这类标志本应处于公共领域供所有人使用,而不能被注册为商标。但是,《商标法》也有一个例外规定,即此类标志在经过使用获得显著性后可以作为商标进行注册。当然,即使可以被注册,商标权人对这种商标的垄断也是有限的,当他人仅为了说明商品的名称、图形、型号而对这类商标进行了使用,商标权人无权禁止。
2.对描述性词汇的使用
描述性词汇指的是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词汇。在商品交易市场中,生产经营者在对商品特征进行介绍时一般需要使用描述性词汇,这些词汇与其所描述的商品联系十分紧密,消费者通常不会将其视为识别商品来源的标志,因此这类词汇就会因为缺乏固有显著性而无法注册为商标。与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相同,《商标法》规定当这些词汇经过使用获得显著性后可以作为商标注册。只是由于这类词汇是连接商品特征与消费者选择的重要媒介,有利于商品信息的传达,《商标法》也允许生产经营者在描述商品特征的正当范围内合理使用这类词汇。
3.对地名的使用
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只有在具有其他含义或者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组成部分时能够获得注册,否则不能作为商标。《商标法》对地名的限制也不仅存在于注册层面,还体现在使用层面。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尤其是地方特产时,会特别注意商品或原材料的产地,因此地名即使被注册为商标也不能被商标权人绝对垄断。当生产经营者为了体现商品的质量或纯粹描述商品产地而使用地名时,应被认定为合理使用而不构成侵权。
(二)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理论基础
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已得到各国的承认并发展成为商标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理论基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利益平衡理论
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知识产品本身就具备信息的属性,能够被广泛传播和分享,其无形性也使得其无法像有形物质一样被控制,因此知识产品最初都处于公共领域。知识产权制度的设立为知识产品的创造者赋予了一定期限的专有权,这种知识产品的私有化也是对本属于公共领域资源的占有,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众对知识的获得和传播,因此知识产权制度需要在私人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平衡。然而,在知识产权中,商标权与著作权、专利权有所不同。著作权和专利权保护的客体都是智力成果,其权利的创设是为了鼓励创新,推动文化和科技的进步,因此著作权和专利权需要平衡的是权利人的私人利益和社会创造、传播知识的公共利益。比较而言,商标权的客体是区分商品来源的标志,最初对商标权的保护是为了防止生产经营者使用与他人相同或近似的标志对消费者进行欺诈,属于商业竞争领域。权利形成基础的不同使得它们所需平衡的利益也有所不同,商标权应衡量的公共利益主要体现为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对于商品的通用名称等显著性较弱的商标,如果由商标权人绝对垄断,那么其他生产经营者则无法正常地对自己的商品进行介绍和描述,从而造成不正当的市场竞争。因此,商标权的保护应当限于一定的范围内,允许其他生产经营者善意且正当地使用他人商标中的商品通用名称、描述性词汇、地名等对自己的商品进行描述,而不构成侵权。
2.搜寻成本理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威廉·M.兰德斯(William M.Landes)和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 A.Posner)两位学者就从经济学角度对商标权制度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搜寻成本理论[1]。商标的本质是符号,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区分商品来源。另外,经过生产经营者长期努力的经营和维护,商品稳定的质量能够在商标上积累商誉,因此商标还能够起到保证质量的功能。作为消费者与商品之间的媒介,商标能够指示消费者购买其认可的来源或质量所对应的商品,大大减少了消费者在选择和购买商品过程中的搜寻成本。这一理论为商标权的设立和保护提供了基础。美国学者马克·A.莱姆利(Mark A.Lemley)和史黛西·L.道根(Stacey L. Dogan)指出,搜寻成本理论不仅可以为商标权的保护提供支持,也能够作用于商标权限制制度[2]。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旨在限定商标专有权的范围。从搜寻成本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加以认识:首先,由于描述性词汇等标志显著性较低,当生产经营者单纯使用这类词汇来描述自己的商品时,消费者通常不会将之视为区别来源的标志而产生混淆,因此并不会增加搜寻成本。其次,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时,对商品的质量、产地、原材料、功能等特征具有知情权,这些特征也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购买的重要因素,如果这类描述性词汇被某一生产经营者垄断而导致其他人无法使用,则消费者需要花费更多搜寻成本去了解这些信息。因此,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制度的设立,不仅不会增加搜寻成本,还有利于市场信息的传递和交流,并未与商标法宗旨相悖。
3.表达自由理论
除了臆造性标志,被注册成为商标的标志通常都具有其原本的含义,这些标志在成为商标前都存在于公共领域中,是人们进行表达和交流的文字工具。商标权能够赋予权利人对该标志的合法垄断权,如果其他人因此无法正常使用这些标志,则会阻碍自由表达。商标权的设立本来就是对公共领域资源的“圈地”运动,因此当其他人对商标的使用并不容易产生混淆时,则应充分尊重其他人表达自由的权利。商标的本质是符号,而符号可以具有多重含义。首先,每一个标志都具有其原本的文字含义,这种含义是在人类社会中逐渐发展而来的,商标法中称之为“第一含义”。其次,当标志被使用在商品上而建立起了其与生产经营者之间的联系时,又会产生不同于原本含义的指示来源的新含义,相对于原有含义是“第二含义”。为了协调商标权与表达自由之间的冲突,商标法仅在第二含义的层面保护商标,并不阻止他人在第一含义的层面使用该商标对应的文字、符号等,因此权利人对商标使用的垄断并非是绝对的,这种制度安排是在言论表达权与商标权之间进行价值权衡的结果。
二、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性质与功能
合理使用来源于著作权法,是著作权侵权的抗辩事由,也被认为是著作权的限制。后来合理使用沿用到商标法中,因此学界多通过类比著作权制度来理解商标权合理使用,认为商标权合理使用也是商标权限制的体现。然而也有学者对商标合理使用提出了质疑,认为商标合理使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合理使用,且没有存在的必要[3-4]。就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而言,他们认为商标法所保护的是商标的第二含义,而商标叙述性使用根本不构成商标法所保护的商标性使用,当然不能被纳入侵权范围,也谈不上合理使用或权利限制。笔者认为,对于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性质,应该追根溯源进行理解和分析。
(一)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商标合理使用抗辩最初在1946年被美国《兰哈姆法》确立为成文规则,而商标合理使用制度的出现也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发展。美国第一部成文商标法于1870年通过,与版权法和专利法一样,其宪法渊源是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第8项的“专利与版权条款”(3)U.S.C.A. Const. Art. I § 8, cl. 8.,然而由于商业标识并不属于科学和艺术领域的智力创造,该法被联邦最高法院认定为违宪。而后美国重新制定商标法,现行商标法即1946年通过的《兰哈姆法》,其宪法依据不再是“专利与版权条款”,而是第1条第8款第3项的“贸易条款”(4)U.S.C.A. Const. Art. I § 8, cl. 3.。可见商标法所保护的并非是类似于发明创造的智力成果,而是商业贸易秩序。其目的在于防止生产经营者通过使用与他人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志进行欺诈,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1.美国商标法发展初期:侵权判定标准严格
在美国商标法实施初期,法院对商标侵权的认定较为严格,通常将商标侵权案件作为不正当竞争案件对待,主要对假冒他人商标的欺诈行为进行规制,并要求商标侵权人必须具备欺诈的主观意图,否则不能被认定为侵权。如在1901年的“Elgin”商标案(5)Elgin National Watch Company, Appt., v. Illinois Watch Case Company, Thomas W. Duncan, and Myer Abraham, 21 S.Ct. 270 (1901).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在认定商标侵权时须证明侵权人具有欺诈意图,如果权利人的商标臆造性较强,其他人对该商标的使用可以直接推定为具有欺诈意图;而如果权利人的商标本身显著性不高,则需要充分的事实来证明欺诈意图而不能直接推定。在该案中,最高法院认为“Elgin”本身是一个地名,被告在自己的商品上使用“Elgin”标志是为了说明产地,而不会起到指示来源的作用,不能认为具有欺诈意图,不构成侵权。可见当时法院对商标侵权判定的严格标准能够将叙述性使用这类情形排除出侵权范围,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商标合理使用尚没有存在的必要。
2.美国商标法发展中期:商标权保护范围不断扩张
随着美国商标法的发展,商标权所保护的范围逐渐扩大。从商标权客体看,已经由最初的文字或图形标志,扩大到对颜色组合标志、三维标志、声音标志等的保护;从商标权利范围看,商标权人享有的禁止权由最初的禁止混淆性使用扩大到禁止淡化性使用;最为重要的是,从商标侵权标准看,要求也逐渐放松,不再局限于欺诈行为,而侧重于对消费者的保护,只要会造成消费者的混淆就可认定为侵权,且其对混淆的要求也非常低,但凡消费者有一点混淆的可能,就可构成侵权。
3.美国商标法发展后期:商标合理使用制度的出现
商标权保护范围的扩大提高了对商标权人和消费者的保护水平,却限制了其他竞争者对商标的正当使用。如对于一些描述性较强的商标,当其他生产经营者在第一含义的层面上使用来对自己的商品进行描述时,由于与他人商标相近似,则有可能被认定为商标侵权。但是司法机关发现,如果将这种行为认定为侵权会阻碍正常的商业表达,限制自由竞争,因此美国衡平法开始对商标权进行限制。在多个涉及描述性标志的案件(6)Barton et al. v. Rex-Oil Co., Inc., 2 F.2d 402(1924); Richmond Remedies Co. v. DR. Miles Medical Co., 16 F.2d 598(1926); Hygrade Food Products Corporation v. H. D. Lee Mercantile Co. et al., 46 F.2d 771(1931).中,法院均指出,描述性标志通常不能被用作商标,若描述性标志在使用的过程中获得能够指示商品来源的第二含义,则能够受到商标权保护。但是商标权人对此类标志所享有的权利是有限的,这类标志的第一含义仍处于公共领域。当他人使用这类标志对自己生产经营的商品特征进行描述且采取了适当措施不易使消费者发生混淆,则不应被认定为侵权。在美国衡平法的推动下,1946年美国《兰哈姆法》正式将叙述性合理使用确定为立法规则。
笔者认为,从美国商标法的立法历程看,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是对商标权不适当扩张的限制,这与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著作权法或商标法实施初期,侵权类型都较为单一,但是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如果认定为侵权则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因此,为了平衡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衡平法中开始出现例外情形,而后逐渐发展为成文法,最终形成较为成熟的制度。
(二)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与商标性使用
认为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没有存在必要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商标性使用是认定商标侵权的前提条件,而叙述性使用根本不构成商标性使用,当然不构成侵权,也并不存在合理使用的适用基础。为此,要明确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性质,还需要厘清其与一个关键概念“商标性使用”之间的关系。
1.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之非商标性使用性质
“商标性使用”是一个学理概念,我国《商标法》中仅出现过“商标使用”而未出现过“商标性使用”的概念。对于这二者,学界并没有明确的区分,通常将二者进行混用。笔者认为,学理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商标识别来源的特征,将商标的使用与一般的使用区分开来,才使用的“商标性使用”的说法;而《商标法》中的“商标使用”也强调了其必须是能够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因此《商标法》中的“商标使用”与学理上的“商标性使用”应当是同一概念,本文统一采取“商标性使用”的说法。
根据《商标法》第48条的规定,商标性使用主要有如下构成要件:(1)在商业环境中使用;(2)与商品密切联系,如用于商品包装、容器上或交易文书上;(3)能够起到识别来源的作用。商标叙述性使用一般都能够满足前两个要件,但是其作用是描述商品的质量、功能、用途、产地等特征,消费者通常不会将之认定为区分来源的标志,因此商标叙述性使用并不构成商标性使用,而属于非商标性使用。
2.商标性使用应作为认定商标侵权的前提条件
商标性使用在商标侵权中的地位,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是肯定派,即认为商标性使用是商标侵权的前提,不能过度扩大商标法的适用范围,只有该行为构成了商标性使用行为,才能进一步探讨商标侵权问题,商标性使用相当于商标侵权判定的一道门槛。[5-7]一种是否定派,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商标权保护的是商标识别来源的功能,应当将侵权的判定标准定位在是否侵害商标功能,而不论其是否属于商标性使用,这样可以防止一些侵害商标功能的不法行为逃脱侵权的惩罚[8-9]。另一种是折衷派,一方面承认商标使用在商标侵权认定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又认为其不应作为前提条件[10]。笔者认为,商标性使用应当作为认定商标侵权的前提条件,理由如下:
首先,商标的价值在于使用,商标的使用也是贯穿商标法体系的关键。由于商标法的宗旨是防止来源混淆,因此这种使用并不是对商标外在表现出来的符号的任何形式的使用,而必须是能够起到区分商品来源的使用。在商标侵权中也是如此,只有在未经商标权人授权的情形下对其商标进行了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才属于商标侵权的范围。
其次,防止混淆是商标法的功能,但并非只有商标法能实现此功能,竞争法也可以对此类行为进行规制。一些不构成商标性使用但有碍竞争的行为可以由竞争法进行规制,而不必加重商标法的负担。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4月21日颁布的《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企业名称因突出使用而侵犯在先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依法按照商标侵权行为处理;企业名称未突出使用但其使用足以产生市场混淆、违反公平竞争的,依法按照不正当竞争处理。”在这类案件中,是否突出使用是判断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的关键,而这里的“突出使用”指的是通过放大或加粗字号、改变颜色、单独使用等方式,使具有识别特征的商标部分相较于其他部分产生突出效果,而能够起到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可以理解为商标性使用。因此商标性使用能够作为认定商标侵权的前提。
最后,从司法成本和效率的角度,将商标性使用作为认定商标侵权的前提,能够在认定商标侵权的第一步就将不属于商标性使用的情形排除出商标侵权范围,而避免了商标近似、商品类似、商标知名度、混淆可能性等后续判断,能够节省司法资源。
(三)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功能
如前所述,商标性使用是认定商标侵权的前提。基于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非商标性使用的性质,这是否意味着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没有必要?笔者认为不然。
首先,从起源和发展过程看,商标叙述性使用是在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商标侵权的例外,而后才成为明文规定,因此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源于实践。而一直以来,立法和司法都未将商标性使用确立为商标侵权的前提要件,也没有过多关注这一问题。随着贴牌加工、关键词搜索等非传统的商标使用形式出现,商标使用这一议题才逐渐被推向前沿,关于是否应当将商标权保护范围限定为商标性使用,以及是否应当将之作为认定商标侵权的前提条件成为了讨论热点。因此商标合理使用理论与商标性使用理论的发展路径有很大不同。但二者之间也有密切联系,上文已经论述过,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属于非商标性使用,因此两者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在“一般”理论尚未形成时,“特殊”规则的制定往往能够较为及时地顺应现实趋势,避免出现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不平衡。从“特殊”到“一般”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和发展,直到现在商标性使用理论仍存在争议。在商标性使用理论尚不成熟的当下,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在商标侵权认定中仍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否定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制度的观点认为,只有在商标性使用的前提下,合理使用才有适用的基础。然而笔者认为,这种理解脱离了制度的起源和历史。在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制度出现时,商标法并未明确规定商标的使用必须是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因此对商标标志任何形式的使用,都有可能落入商标权侵权范围。基于当时的背景,虽然叙述性使用的对象是商标的第一含义,但也属于对商标的“形”的使用,此时将商标的叙述性使用确立为一种合理使用是合情合理的。后来逐渐出现了将商标使用限定为商标性使用的讨论,才引起了对商标合理使用的质疑。故对于合理使用的理解不能拘泥于形式要件,而应从根本进行理解。
最后,由于权利妨碍规范中的商标合理使用限制与商标侵权认定中的商标性使用前提要求的本质是相同的,因此从制度设置看,立法只需其中一个制度便能实现目的,如果二者同时存在,就可能在形式上产生冲突,学界对于合理使用的争议也源于此。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形式上的冲突在逻辑上也是立不住脚的。从形式上看合理使用是侵权的抗辩,只有在侵权基础上才能提出。但侵权的认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由双方当事人共同推动的,司法机关须衡量双方当事人的主张和抗辩后才能得出结论,因此侵权抗辩应当是在侵权认定过程中提出,而非侵权基础上提出。应当打破对合理使用抗辩的固有理解,不再以侵权基础为前提。笔者认为商标性使用前提要件与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是可以共存的。一方面,承认商标性使用在商标侵权认定中的前提地位。另一方面,将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理解为对商标性使用的否定和抗辩,二者共同作用。这样的好处在于,实践中商标性使用与非商标性使用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司法机关很难加以判断,如果将非商标性使用的具体情形作为合理使用抗辩进行规定,则可以由当事人直接提出。这种由司法机关与案件当事人共同作用的机制,有利于减轻司法机关的负担,且有助于明确商标性使用与非商标性使用的区别,并更好地对商标侵权的范围进行界定。从这一角度看,在肯定商标性使用前提地位的条件下,对商标性使用进行反面规定,继续发挥商标合理使用制度的作用,是更为合适的选择,也是国际立法和司法的选择。
三、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认定
(一)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与混淆可能性的关系
在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认定过程中有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即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与混淆可能性的关系。下文将通过分析和总结国内外司法实践的不同观点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
1.美国司法实践的做法
作为商标合理使用制度的发源地,美国对于这一问题也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以美国第六和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为代表,其认为商标合理使用与混淆可能性是不可共存的,如果对他人商标的使用会导致消费者混淆,则商标合理使用抗辩没有适用的空间。另一种观点以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为代表,其认为商标合理使用与混淆可能标准是可以共存的,即使商标合理使用可能会导致消费者混淆,只要其满足了商标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就可以免除商标侵权责任。
直到2004年的KP案(7)KP Permanent Make-Up, Inc. v. Lasting Impression I, Inc., 125 S.Ct. 542(2004).,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在该案中,持久印象公司于1993年获得了包含“micro color”文字的商标的注册,其诉称KP化妆公司在他们所生产的某类化妆品包装上使用“micro color”一词的行为侵犯了其商标权。KP化妆公司则称其早在1990年或1991年就开始在广告传单和瓶装上使用该词汇,并提出这种使用并非是用作商标而是对产品的描述,属于合理使用。对此,第九巡回法院认为KP化妆公司使用“micro color”文字的行为可能导致消费者混淆,因此不能构成合理使用。最高法院驳回了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观点,认为商标合理使用和混淆可能性是相互独立的制度,商标合理使用可以对抗一定程度的混淆可能性。主要原因在于,既然权利人选择描述性词汇这种显著性较弱的标志注册为商标,就要承担他人在第一含义上使用而导致混淆的风险。然而对于商标合理使用可以兼容何种程度的混淆可能性,法院没有进一步进行探究。
2.我国司法实践的做法
通过对我国叙述性合理使用认定的相关司法判例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司法实践对于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与混淆可能性的关系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将混淆可能性作为判断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因素之一。如在“东阿阿胶”商标案中,一审法院指出:“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描述性组成要素,他人基于说明或客观描述商品特征、用途、产地等目的,以善意、合理的方式在必要范围内使用,在不会造成相关公众混淆的前提下,应当属于正当使用”(8)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知)初字第26212号民事判决书。。又如在“稻花香”商标案中,二审法院认为被诉侵权人在其生产销售的大米包装上使用“稻花香”这一通用名称是为了说明大米品种来源,主观上出于善意,客观上也未造成混淆,因此属于正当使用(9)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74号民事判决书。。虽然最后再审法院认为“稻花香”不属于通用名称而撤销了二审判决,但是二审法院对于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仍具有代表意义。在这两个案件中,混淆可能性都是认定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重要因素,在“东阿阿胶”案中,一审法院甚至将不会造成混淆视为前提条件,即如果对他人商标的使用会造成混淆或误认,则一定不会构成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这种做法与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早期观点相似。
第二种观点认为混淆可能性是商标侵权判定的核心,即使认定构成正当使用也仍需对混淆可能性进行判断,或者直接将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作为混淆可能性的考量因素之一。如在“随堂通”商标案中,被诉侵权人在其出版的涉案图书上将权利人注册商标“随堂通”作为图书名称的组成部分进行了使用,二审法院先对这种使用行为进行了判断,认为该行为构成正当使用,并由此得出其“并未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或误认”,从而认定不构成侵权(10)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0124号民事判决书。。此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的逻辑恰好是相反的,但混淆可能性在其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其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即如果对他人商标的使用可能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和误认,则一定构成侵权,合理使用并不能对抗混淆可能性。
第三种观点将商标性使用作为认定商标侵权的前提,如果对权利人商标的使用属于叙述性合理使用而不构成商标性使用,则不必进一步对混淆可能进行判断。如“拍客”商标案中,二审法院指出,《商标法》规制的侵权行为是商标性使用行为,而被上诉人在专门服务拍客的软件上对“拍客”的使用属于第一含义层面的使用,不构成商标性使用,因此对于是否构成商标侵权没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11)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民终字第114号民事判决书。。根据此种观点,商标性使用的判断与商标侵权的判断存在先后顺序,这也意味着,非商标性使用能够完全对抗混淆可能性。
3.混淆可能性在商标合理使用中的作用
国内外司法实践对于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与混淆可能性关系的争论核心在于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能否对抗混淆可能性。前文已经论述了商标性使用是认定商标侵权的前提,因此从逻辑上看只有当构成了商标性使用时才需要对是否能够导致混淆和误认进行判断,二者在侵权判断中存在先后顺序,它们之间应当是相互独立的。但是商标性使用与混淆可能性之间无疑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通常只有将他人商标用作识别来源的标记时才有可能会使相关公众对来源产生混淆。如果对他人商标文字的使用只是为了对商品进行描述,消费者就难以对来源产生混淆。因此,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制度本身已经对混淆可能性进行了考量,是对商标权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平衡后的结果。美国学者斯蒂芬妮·M.格林(Stephanie M. Greene)也指出,美国《兰哈姆法》§1115(b)(4)规定的商标合理使用抗辩在制定时已经考虑了混淆可能性,该抗辩要求这种合理使用“并非作为商标使用”且必须“具有善意”,这两个条件本身就意味着这种使用不易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11]。这样一来,如果已经满足了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实际上也已经通过了混淆可能性的考验,无须再对其是否会造成混淆和误认进行判断了,这也说明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能够对抗一定程度的混淆可能性,且这种程度在商标合理使用制度设立之初立法者就进行了衡量,司法机关无须再判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了商标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将2004年发布的解答中规定的“使用不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这一构成要件删除了,说明在认定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时,不需要对是否会造成混淆和误认进行判断,这一修改与上面的论述也是相符的。
(二)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认定标准
上文对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与混淆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首先可以将混淆可能性排除出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结合司法实践对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认定,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要件。
1.使用目的
要求对他人商标的使用是为了描述或说明自己商品的特征,而不是用以区别商品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将其他使用目的也纳入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情形。如在“花开富贵”商标案中,被诉侵权人在产品包装上使用了与他人注册商标“花开富贵”相同的文字。法院认为,“花开富贵”的第一含义是“牡丹花开、繁荣富贵”,被诉侵权人在瓶贴上将“花开富贵”配合牡丹花图案使用,是对“花开富贵”第一含义的使用,瓶贴文字和图案共同作为商品包装装潢,其目的在于美化其商品,并基于此将这一使用认定为合理使用,不构成侵权(1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0054号。。在本案中,“花开富贵”属于描述性词汇,但是被诉侵权人对“花开富贵”的使用并非是出于说明和描述商品的目的,而是用作装饰来美化商品,对于此类使用目的,是否也能够纳入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范围?笔者认为,不能扩大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适用范围,而应限制为以说明和描述为目的的使用。商标叙述性使用不构成侵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描述与商品本身的特征是相符或具有密切联系的,因此相关公众一般不会将之视为识别来源的标志。如果是用作包装、装潢,即使使用人主观上是在第一含义的层面上使用,由于其与商品本身联系不大,且包装和装潢本身就具有识别来源的属性,也很容易被视为区别来源的标志。《商标法实施条例》第76条就把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潢使用、误导公众的行为,认定为商标侵权,这条规定说明将他人商标用作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潢,都应当属于商标性使用,而是否构成侵权,则要对其是否可能造成混淆和误认进行进一步判断。
2.使用方式
商标叙述性使用对于使用方式也有要求。首先,这种使用方式必须是合理的,要能够使相关公众认为其仅仅是在说明或描述商品,而并不是区别来源的标志。实践中较为合理的方式包括:避免将与他人商标相同的商品通用名称、描述性词汇、地名等突出使用;另外附上自己的商标,将二者予以区分。其次,这种使用应当是必要的。虽然商标法不能阻止公众在第一含义的层面使用与他人商标相同的标志,但是这种使用也并不是毫无限制的。对于他人已经获得商标法保护的商标,应当予以尊重。文字博大精深,描述性表达也很多,因此可以尽量避免使用与他人商标相同的文字,以防公众混淆。最后,这种使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个案中应有所不同。如果商标的知名度高,那么生产经营者知晓该商标的可能性就更大,在对自己的商品进行描述和说明时就应当更加谨慎注意;如果商标的第一含义被公众广泛使用于描述某类商品,生产经营者在该类商品上进行使用时就更加合理,商标权人的容忍程度也应更高。
3.主观状态
除了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要求使用人主观上应当具有善意。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发布的《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2条就规定:“被诉侵权人为描述或者说明其产品或者服务的特点而善意合理地使用相同或者近似标识的,可以依法认定为正当使用。”这里就强调了这种使用必须是“善意”的。美国《兰哈姆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抗辩中,也要求这种使用“in good faith(善意)”。“善意”的要求也是《商标法》第7条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在商标合理使用制度中的体现。在使用商品的通用名称、描述性词汇、地名等对自己的商品进行描述时,应当遵循诚信原则,不能有攀附他人商誉的恶意。这种主观状态固然可以通过上述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这种更为客观的标准来进行推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要求就是多余的,因为主观状态的判断因素很多,并不限于上述两种,而且“善意”其实属于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核心,可以作为原则性要求存在。
四、完善我国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制度的建议
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制度是确立商标权保护边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规则借鉴于国外,但是我国的立法模式和司法实践与国外差别很大,制度的立足基础也有所不同。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制度在我国仍存在定位不清晰、法律规则不完善、认定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因此,在厘清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制度的性质后,需要结合我国的立法和司法现状对这一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立法完善
现行《商标法》将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规定在第59条第1款,采用了列举的方式,只规定三种情形。面对日新月异的商品市场,这种立法模式具有一定局限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将商标合理使用制度体系化
目前各国规定的商标合理使用主要包括两种,商业性合理使用和非商业性合理使用,前者包括叙述性合理使用和指示性合理使用,而后者包括新闻报道中使用、字典中使用、滑稽模仿等情形,但是我国立法只对叙述性合理使用进行了规定。且前文已经论述过商标性使用是商标侵权的前提,而非商标性使用虽包含商标合理使用中的这几种情形,但也并不限于这几种情形。因此在《商标法》未明确商标性使用的地位且商标合理使用制度又不完整的情形下,会使得不属于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其他非商标性使用情形也纷纷寻求《商标法》第59条第1款的救济,不当扩大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美国《兰哈姆法》虽然也只对叙述性合理使用进行立法,但是美国是判例法国家,其判例中已经确立了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抗辩制度。我国是成文法国家,需要在立法上予以明确。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对商标合理使用制度进行补充和完善,将指示性合理使用、非商业性合理使用等非商标性使用都纳入立法中来,构建完整的商标合理使用体系。
2.采用“概括+列举”的方式进行界定
具体到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规定本身,各个国家主要存在三种立法模式:概括式、列举式、概括+列举式。我国所采取的是列举式。笔者认为,列举式尤其像我国限定为三种情形的列举式是具有弊端的,商品的说明和描述方式多种多样,立法通常难以列举完全,且新的方式层出不穷,这种列举式立法具有滞后性。因此应当采取更为灵活的“概括+列举”的方式,一方面通过“概括”对叙述性合理使用的内涵进行界定并明确其构成要件,另一方面通过“列举”明确实践中较为典型的情形,为司法实践者提供直接参考,节约对叙述性合理使用进行界定的司法成本。
“概括”的立法方式可以明确叙述性合理使用的界限,并且能够作为“列举”的各种具体情形的兜底条款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于“列举”的要求,立法仍应当尽可能地将实践中存在的叙述性合理使用的情形列举出来,以使得行为人更加明确侵权的边界,也使得司法机关更加明晰侵权的界定标准。目前,除了《商标法》中列举的三种行为,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其他情形,如在“陈昌银”商标案中,陈昌银将其姓名注册为商标,核定使用在麻花、面条等商品上,并许可原告重庆市磁器口陈麻花食品有限公司使用。被告重庆喜火哥饮食文化有限公司九龙坡分公司在其生产的麻花产品包装袋上使用了公司调味师“陳昌江”这一姓名标志。后原告以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起诉被告。虽然该案最后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但法院对自然人姓名的正当使用和姓名商标侵权进行了区分。法院指出:“在已有以姓名为注册商标标识存续的前提下,并非他人完全没有使用类似姓名作为商业标识的权利……如果碰巧与正在使用的姓名商标相近似,后使用者在不会造成与在先注册商标混淆的程度上,仍可在原有范围内使用。”(1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渝民终335号民事判决书。这说明,除了商品的通用名称、描述性词汇以及地名之外,对姓名的使用也有可能构成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且国家商标局在1999年发布的《关于保护服务商标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中也规定,他人“以正常方式使用商号(字号)、姓名、地名、服务场所名称,表示服务特点,对服务事项进行说明等,不构成侵犯服务商标专用权行为”,其中也包含了对姓名的使用。因此,如果使用与他人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姓名来对商品进行说明和描述,且不会被消费者认为是识别来源的标志,也应当纳入叙述性合理使用的范围,但是前提是使用的姓名应确与商品有关,例如,可以是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的姓名。对于这种实践中已经出现的立法之外的叙述性合理使用的情形,建议也在立法中明确予以列举。
(二)我国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司法完善
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和判定标准的不统一,司法实践在对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进行认定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在立法尚存在缺陷时,司法机关也应通过法律解释等方法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利用司法来推动立法进程。
1.明确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在商标侵权判断中的地位
上文有提到,司法实践对于商标合理使用的性质仍不明确,因此判定商标侵权的逻辑也有所不同。有的将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作为混淆可能性的判定因素,而有的将混淆可能性作为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判定因素,也有的不就混淆可能性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将商标性使用作为商标侵权的前提要件,如果是非商标性使用,则可排除出侵权范围。商标叙述性使用属于非商标性使用的一种情形,因此,如果被诉侵权人的行为已经满足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则无须再对混淆可能性进行判断,可以直接认定为不构成商标侵权。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0年6月15日发布的《商标侵权判断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第3条第1款规定:“判断是否构成商标侵权,一般需要判断涉嫌侵权行为是否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的使用。”说明认定商标侵权时需要对是否属于商标性使用加以判断,虽然《标准》并未明确商标性使用在商标侵权认定中的前提地位,但是将本条作为一般性条款置于首位,也足以说明其相较于混淆可能性判断的优先地位。这一《标准》的发布,确实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商标侵权认定逻辑的厘清以及标准的统一,值得肯定。
2.统一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
在对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进行认定时,司法机关的判断标准并不统一。虽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对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进行了明确,但是其效力具有地域性,并不适用于其他地区的法院。立法的缺陷是审判标准不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立法完善之前,司法机关也应当在实践中尽可能地统一标准,以防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发生,如其他地区的法院可以优先参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审理规范对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进行认定。其次,描述性词汇、使用方式、使用目的等问题的认定本来就具有一定主观性,难以形成完全统一的标准,因此司法机关在判断时应当采取尽可能客观的方式,如从一般消费者的角度进行考虑,减少个人主观感受的干扰。另外,商标叙述性使用的对象都是与之有紧密联系的商品,因此在判断时也要注意结合所指定使用商品的特征,进行个案判断。
五、结语
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制度来源于美国,从其司法和立法的起源和发展看来,其产生于对不断扩张的商标权保护边界的限制。作为非商标性使用的一种情形,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制度与商标性使用理论的作用殊途同归,二者能够通过共同作用实现对商标权保护边界的界分:一方面,承认商标性使用在商标侵权认定中的前提地位;另一方面,继续保留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规定,通过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抗辩来对商标性使用进行否定,使商标性使用与非商标性使用之间的界限更加清晰。
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与商标混淆可能性的关系,一直是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理论及实践中争论的重要主题。由于商标混淆可能性以商标性使用作为前提,而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并非商标性使用,因此可以认为混淆可能性并非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制度产生之初实际上就对混淆可能性进行了考量,是利益平衡后的结果。在明确上述关系的基础上,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明晰其构成要件。总结前述司法实践经验,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如下:第一,从使用目的看,应当是为了描述或说明自己商品的特征,而不是用以区别商品来源;第二,从使用方式看,应当合理且必要;第三,从主观状态看,应当是善意的。同时,随着我国商标保护制度的完善,也需要进一步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完善我国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