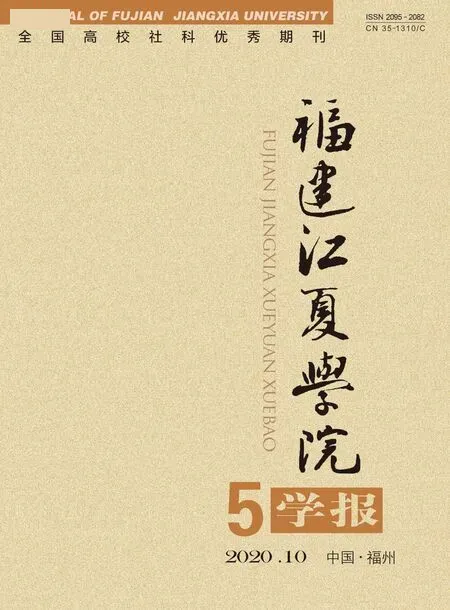试说“光采玄圣 炳耀仁孝”
2020-02-25魏伯河
魏伯河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国学研究所,山东济南,250031)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的“赞”中“光采玄圣,炳耀仁孝”两句里的“玄圣”所指为谁,各家解读颇不一致。今稍作梳理,并略陈己见。因为字不离句、句不离篇,所以要确定具体语词在特定语境中的意义,不可避免地需要涉及《原道》全篇,谨此说明。
一、“光采玄圣,炳耀仁孝”的不同解读
了解《文心雕龙》的“赞”与原文关系的读者不难发现,《原道》“赞”中所谓“光采玄圣,炳耀仁孝”,是由原文正文里面“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和“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等句意凝练而成。而正文中的这三组对偶句,刘勰反复申说的其实只是一个意思,即所谓人文,系由庖牺(即伏羲)画八卦创始,至孔子删述六经而集其大成。不过为了避免字面重复,刘勰在行文中不得不对人物的指称一再变换其辞。对庖牺(即伏羲),本名之外,又称作“风姓”,再称作“玄圣”;对孔子,先称作“仲尼”,又称作“孔氏”,再称作“素王”。其中的“玄圣”,清人黄叔琳曾援引班固《典引》的用例,注云:“玄圣,孔子也。”[1]5但其说已被纪昀所明确否定。纪昀评曰:“此玄圣当指庖牺诸圣,若指孔子,于下句为复,且孔子亦非僻典也。”[1]7台湾学者张立斋在《文心雕龙注订》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玄圣指庖牺,创典指始画八卦也。素王指孔子,述训指好古敏求,述而不作也。……黄注以玄圣指孔子,非是。”[2]纠正了纪昀评语中“庖牺诸圣”的含糊之处。另一位台湾学者李曰刚在其《文心雕龙斠诠》中也指出:“玄圣创典:指伏羲氏始画八卦也,应上文‘伏羲画其始’句。……素王述训:指孔子删述六经也。应上文‘仲尼翼其终’及‘夫子继圣’云云而言。”[3]指出了其与前面文句的对应关系,更有说服力了。就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各种注译本来看,将正文中的“玄圣”认作孔子的已不多见,但认为其并非专指庖牺者仍时有其人。如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注为“玄圣:上古时代的的圣人,指伏羲、神农、黄帝等。”[4]7张长青《文心雕龙新释》则释为“玄圣:远古圣人。”[5]似此将专称视为泛称,说明注释者或许受到纪昀评语影响,并且未能紧密联系前文,以致有失准确。
而对“赞”中的“玄圣”,分歧意见却变得更多,以致不无治丝益棼之憾。
首先,原文是“玄圣”还是“元圣”成了问题。杨明照先生认为,此处应为“光采元圣”,并且认定其所指为孔子。在他著名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一书中,此处有校记云:
光采元圣“元”,元本、弘治本、活字本、汪本、佘本、张本、两京本、王批本、何本、胡本、训故本、梅本、凌本、合刻本、梁本、秘书本、谢抄本、别解本、尚古本、冈本、文溯本、崇文本、文俪、诸子汇函作“玄”。按“元”字是。《书·伪汤诰》:“聿求元圣。”枚传训“元”为大,此亦应尔。《史传》篇:“法孔题经,则文非元圣”,正与此同。诸本作“玄”,盖涉篇中“玄圣创典”句而误。[6]17
在所有二十几种版本都作“玄圣”,而没有列举出任何版本为“元圣”的情况下,杨先生力排众议,径直校改为“元圣”,其勇气固然可嘉,但其结论却值得怀疑。就笔者这些年所见多种注译本来看,赞同这一校改者除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7]和龙必锟《文心雕龙全译》[8]外,更多的版本仍作“玄圣”,应该可以说明问题。
然后,“玄圣”所指也出现了分歧。杨明照先生认为:“篇中之‘玄圣’系指伏羲诸圣,此句之‘元圣’则指孔子,不能混而为一。”[6]17同样认为指孔子的还有: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光采:指自然之道的光采。玄圣:指阐明自然之道的古代圣贤,主要是孔子。”[9]周振甫《文心雕龙全译》:“光采的大圣孔子,明显地宣扬仁孝的伦理道德。”[7]15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此处注为:“玄圣,此指孔子。”其译文则为:“光辉的圣人孔子,使仁孝之类的伦理道德发扬光大”。[10]
与之不同,认为“玄圣”指庖牺者仍然占多数。其中又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两句分指庖牺和孔子,如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释为:“玄圣创典,光采普照;素王述训,炳耀仁孝。”[3]张国庆、涂光社《〈文心雕龙〉集校、集释、直译》译为:“伏羲经典光彩夺目,孔子仁孝辉光闪耀。”[11]另一种是认为两句均指庖牺,如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译为:“开拓这条光明大道的是伏羲氏,最辉煌的教义就是仁和孝。”[12]11陈书良《文心雕龙(释名+经典直读)》译为:“光明的庖牺氏啊,最辉煌的教义就是仁和孝。”[13]
此外就是把“玄圣”宽泛解读为“远古圣人”者,如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译为:“远古的圣人,阐明了这些道理,宣扬了忠孝仁义。”[14]23祖保泉将此处之“玄圣”注解为“大圣”,将“光采玄圣”释为“玄圣遗训焕发光彩”[4]8;王志彬则译为:“既使伟大的圣人显示了光彩,又宣扬光大了仁义忠孝。”[15]采取这种处理方式者颇多。不过,像这样泛化的一般性解读,似乎回避了争议,但却掩盖了矛盾,问题并没能解决。
这样几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读,反映出学者们对这两句“赞”语的理解颇不一致,因而有专门加以探讨的必要。
二、“光采玄圣,炳耀仁孝”之我见
在对《原道》“赞曰”“光采玄圣,炳耀仁孝”二语的不同解读中,笔者赞同前后分指庖牺和孔子的解读。理由如下:
其一,尽管称孔子为“玄圣”自汉代以来颇有其例,但“玄圣”作为专用名词,在同一语言环境中所指称对象应该是一致的。既然前文“玄圣创典”指的是庖牺,“素王述训”指的才是孔子,此处就不应该再以“玄圣”指称孔子。否则便与前文无法对应,也不符合语言常规。何况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并没有刘勰称孔子为“玄圣”的另外例证。《史传》篇“法孔题经,则文非元圣”一语中,以“元圣”指称孔子,当是为避免与本篇之“玄圣”相混。明乎此,就会知道刘勰不至于在《原道》一文中,拿“玄圣”既用以指称庖牺,又用以指称孔子,而令人莫名其妙了。
其二,“仁”和“孝”是孔子开始确立的儒家核心观念和道德范畴,并且当时还没有连文,直到《史记·留侯世家》里才出现“窃闻太子为人仁孝”[16]的用法。庖牺氏是文明初创时期的远祖,当时应该还没有形成这样的观念,因而将“玄圣”认作庖牺,再把两句贯通起来作一句解读是不能成立的。而且“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和正文中“玄圣创典,素王垂训”,和前两句“道心惟微,神道设教”、后两句“龙图献体,龟书呈貌”一样,是对偶关系,贯通解读之后,两句之间的对偶关系也便不能成立了,不符合刘勰写“赞”主要用对偶句的常规。
其三,前文已指出,所谓“光采玄圣,炳耀仁孝”,是由《原道》正文里面“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和“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等几组对偶句凝练而成。在刘勰的表述中,上述对偶句涵盖的都是人文从创始到成熟的全过程。如果将这两句解读为均指庖牺,便无法体现原文核心段落对孔子的赞美;而以为两句均指孔子,将“仁孝”仅理解为其思想学说,则不仅“玄圣创典”之功在“赞”中无从体现,而且与原文中每组对偶句表达的语意也无法保持一致。
笔者的结论是:此处之“光采玄圣”仍指庖牺,下句“炳耀仁孝”才指孔子。这两句紧承上两句,意思是“道心”(亦即“神理”)“光采于玄圣,炳耀于仁孝”。郭晋稀先生指出:“(这里的)光采、炳耀,形容词当动词用”[12]10,是正确的。可惜主此说者的译释均不甚到位,未能从语言学角度提出证据。前引李曰刚的释文“玄圣创典,光采普照;素王述训,炳耀仁孝”,显然算不得现代白话文,且不无增字解经之弊。张国庆等人将原文语序调整,译成“伏羲经典光彩夺目,孔子仁孝辉光闪耀”,就语意把握来说虽无不妥,但译文改变了原文的句式,而又缺乏必要的说明,所以对说服力不无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仁孝”在这里是一种借代用法,是用其学说的要义(仁孝)代指其人(孔子),借以与上句“玄圣”相对。这种用法固然并不常见,但刘勰受赞语“四字之句”“数韵之词”而且必须对偶、押韵的要求限制,不得已而为之,亦非无由。毕竟孔子的仁孝学说经过汉儒宣扬早已家喻户晓,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不会误解。对此我们应给予同情之理解。更重要的是,这样解读,与原文内容既能保持一致,也与前两句“道心惟微,神理设教”的内容联系更为密切,应该是比较妥帖的。
三、“赞”所体现的全文主旨
文后有“赞”,始自《汉书》,系由《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演变而来,不过其时尚为散行文字,直至《后汉书》才一变而为四言韵语。史书中“赞”的作用,如刘勰所说,为“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是史书作者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论。史赞之外,汉晋以来,还流行一种为人物画像、作品图谱作赞的风气。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下,“赞”逐渐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体。刘勰《文心雕龙》论“文体”,设有《颂赞》篇,专门对此进行论述。他指出,此所谓“赞”,并非一般的赞美之意,而是“明也,助也”。其文体特点是:“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词;约举以尽情,照灼以送文。”“赞”与“颂”关系密切,但地位并不相当,“赞”属于“颂”的“细条”即分支,所以二者有时可通用。刘勰受史书和图赞的影响,为《文心雕龙》每篇作“赞”,是文论著作首次在篇末使用赞体,应该属于他的创举。
一般地说,“赞”并非原文整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按照全书确定的体例要求另行添加的文字,属于对全文内容要点的另一种表述。至于为人物画像、作品图谱所作的赞(也有的叫“颂”),往往与图画作者并非一人。例如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列女传》的“颂”,据笔者的研究,作者很有可能是其子刘歆(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17]。《文心雕龙》的“赞”与正文固然同出自刘勰手笔,但在“赞”相对独立于正文方面,亦别无二致。就此而论,某些注译本将“赞曰”译为“总之”“总结说”或“总而言之”,视为全篇结语,并不准确,因为正文末段已经有了总结性文字。写作者对“赞”固然要精心结撰,字斟句酌,力求言简意赅,便于传诵,但其作用并不在于在篇章之外再阐发出什么新意,而是对原文的画龙点睛。《文心雕龙》的赞也正是如此。每首“赞”包括四言八句,每两句为一组,各组之间有着内在逻辑关系,不容错乱,更不容误读。就《原道》篇“赞”的语意来看,和正文中的关键语句均存在对应关系:其中所谓“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只是“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另一种表述。而所谓“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如前文所说,是“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等三组对偶句的变换其辞。所谓“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则是“《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和“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的缩略之语。至于“天文斯观,民胥以效”,则不过是“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的另一种表述。周勋初先生(1929—)指出:“赞语可分前后两节:(一)强调‘道沿圣以垂文’,(二)强调‘圣因文而明道’”。[18]此说甚是。所谓“画龙点睛”者,此之谓也。刘勰通过“赞”再次提示读者,他通过《原道》所要揭示并告诉读者的,就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样一种道-圣-文(经)三位一体的关系,其他都是为此服务的。
根据“赞”的一般特点和本篇“赞”的表述,可见“赞”与原文有互相印证的作用,对阅读全篇确有助益。据笔者体会,其主要作用,是有助于把握全篇的主旨,矫正阅读中产生的偏颇。
由“赞”回看原文,就会发现:原文第一段(从“文之为德也大矣”至“有心之器,其无文欤?”)由天地万物无不有文推论出人也必然有文的内容,在“赞”中基本无所体现,可知该段在全篇中所处的只是铺垫或介绍知识背景的地位。钱钟书先生(1910—1998)说:刘勰由天文推论人文,“盖出于《易·贲》之‘天文’、‘人文’,望‘文’生义,截搭诗文之‘文’,门面语、窠臼语也。刘勰谈艺圣解,正不在斯,或者认作微言妙语,大是渠侬被眼谩耳。”[19]经过“赞”的验证,更觉其说可信。“赞”主要概括的是文章第二段(自“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至“晓生民之耳目矣”)追溯人文发展的历史、突出庖牺—周公—孔子等圣人作用的内容,据此可知第二段乃是全文的主体和中心。至于原文第三段(自“爰自风姓,暨于孔氏”至“乃道之文也”),概述人文发展历程、揭示出“道—圣—文”之三位一体的关系,本来就是全篇的结语,其中除“观天文以极变”一语和第一段还略有关联之外,所总结的也只是第二段的内容。这足以启示我们,《原道》从天地万物之文讲到人文,重点是落实在人文上,天地万物之文只是铺垫或引子:就内容说,都是当时的常识;就语言说,只是流行的套话。按照王夫之《姜斋诗话》里“诗文俱有主宾”[20]的说法,第一段只是“宾”,第二段才是“主”。把握文章主旨,应该从其重点段落着眼,否则就可能偏离主题。由此可以引起反思的是,多年来人们对第一段的过度关注,包括对其中个别词句如“文之为德也大矣”“自然之道也”之类的过度解读,很有可能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是被其“眼谩”,选错了方向,枉费了力气,因而才会求之弥深而惑之弥甚。
笔者本文所作的探讨,借用童庆炳先生(1936—2015)的话说,目的在于“获取真义”而非“焕发新意”[21],因为如果对文本不能正确释读,就会影响到对原著主旨的把握,进而影响到对其理论价值的认识。近百年来,关于《文心雕龙》的校、注、译、释可谓多矣,然而仍有不少疑点未能解决。这说明,在“获取真义”方面目前还有一定差距,尚需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