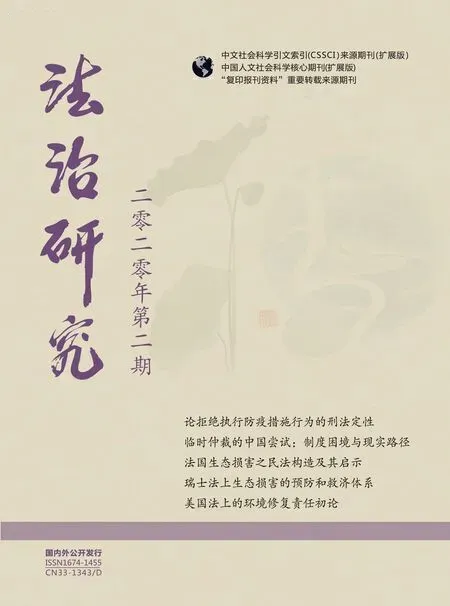瑞士法上生态损害的预防和救济体系
2020-02-25梁神宝
梁神宝
一、前言
我国近些年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空气质量差、土壤重金属超标、水质恶化等环境问题常见于媒体。2013年初北京雾霾压城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也为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敲响了警钟,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法律是预防和治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就法制层面而言,我国生态环境方面法律涉及刑法、民法和行政法等多个部门法,且有《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及《土壤污染防治法》等专门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就生态损害赔偿问题,我国法律正从改革试点阶段向稳定成熟阶段迈进。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联合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已废止),在试点省市经验基础上,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要求从2018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推行这项改革。《改革方案》对“生态环境损害”的定义是: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森林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以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不能归入“生态环境损害”的是,个人人身伤害、个人和集体财产损失。
尽管就生态损害问题我国已发展出相应规范,学者已展开了深入研究,但尚有一些问题存在争议,例如因生态损害提起诉讼的性质、环保组织能发挥何种作用等。
研究外国生态损害法律及其实际运行状况,对我国有借鉴意义。本文以瑞士法上生态损害预防和治理中的部分法律问题为研究对象,依据问题是否紧扣我国当下生态损害法律争议焦点,选择以下两点研究:一、生态损害适用侵权责任法还是适用公法规范;二、环保组织在应对生态损害时的法律地位。
二、生态损害公、私法救济立法进程
无论采公法或私法路径,涉及的都是采取措施的费用的承担问题,①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的补偿在瑞士法上并未成为一个话题,本文不讨论这一问题。本文所言生态损害是指预防、保护生态和恢复原状(替代恢复)所采取措施支出之费用。即预防、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所采措施的费用由公众共同承担还是由原因者或侵权人承担。在工业化社会之前,虽然人类也会有破坏生态的行为,但生态本身有自我恢复能力,生态损害并未进入立法者视野中。进入工业化时代,污染更加严重,超过生态环境自身净化和恢复能力,政府治理生态环境需要花费大量资金,由谁最终承担这笔费用,便成为立法者关心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开始,瑞士法律界从公法和私法的角度尝试解决保护生态的措施最终费用承担的问题,以下分别阐述。
(一)公法立法上的成果
公法上与生态损害相关的一个原则是“原因者付费”原则(Verursacherprinzip)。这一原则最先在经济学理论中发展出来,其内容是:环境破坏是因环境利益的过度使用,而环境利益作为一项集体利益没有市场价格机制,环境利益虽然有价值但没有价格,因此需要用税费和其他市场机制来防止过度使用。②瑞士学者借用英国学者Arthur Cecil Pigou的环境税理论。Griffel Alain, Die Grundprinzipien des schweizerischen Umweltrecht,Zürcher Habilitation, Zürich 2001, N 210 ff.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若环境污染成本未被计入商品价格,而由公众一起承担后果,会对其他经营者造成不公平竞争,原因者付费原则旨在使外部成本由经营者自行承担,从而促进公平竞争。③Rausch Heribert/Marti Arnold/Griffel Alain, Umweltrecht–Ein Lehrbuch, Zürich/Basel/Genf 2004, N 78.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将费用转嫁给原因者,可以促使原因者为避免承担费用而减少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有利于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目的。
瑞士《水域保护法》(1971年通过,已废止)最先将“原因者付费”原则落实到法条。根据该法第8条,主管机关防御直接急迫的水污染以及确定和消除污染而采取措施,所支出费用可转嫁给原因者。1983年通过的《环境保护法》(1985年1月1日生效)第59条延续了《水域保护法》(1971年)第8条的规定,只是用词稍作修改,将“污染”(Verunreinigung)修改为“不利影响”(Einwirkung)。④Haftp flichtKomm-Wagner Pfeifer, Art. 54 GSchG, N 9.1987年《水域保护法》修订时对第8条的表述再作修改,将“可”改为“应”,行政机关对是否转嫁支出之费用不再拥有裁量权,而是依法应当转嫁。⑤Haftp flichtKomm-Wagner Pfeifer, Art. 54 GSchG, N 10.1991年通过的新《水域保护法》第54条延续了旧《水域保护法》(1971年通过,1987年修订)第8条的内容,继续落实“原因者付费”原则。
上述条文是“原因者付费”原则的具体化,而原则本身以法条形式规定在法律中,则是1983年通过的《环境保护法》(1985年1月1日生效)第2条,1997年修订《水域保护法》新增第3a条。
原因者付费原则如何在司法中运用以及进一步的理论剖析将于后文再展开。
(二)私法上的尝试
现行瑞士法下,从制定法角度来看,生态损害并非侵权法上可赔的“损害”,无法依据侵权责任法得到赔偿(恢复原状或金钱赔偿)。⑥Dreifuss Thomas Widmer, Geltendmachung von Haftpflichtansprüchen aus Umweltschäden im Zivilprozess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chweizerischen Zivilprozessordnung), in: URP 2009, S. 443 ff.; Beck Peter, Umwelt- und Ökoschaden - Haftung und Versicherung, in: HAVE 2009 S. 299.但司法实践个别案件中,行政机关依据侵权责任法诉请生态环境加害者恢复原状(或恢复原状的费用),法院判决支持此等请求。⑦BGE 90 II 417此案是河流水污染导致野生鱼虾死亡,政府请求赔偿清理死鱼虾和投放新鱼虾幼苗的费用; 127 III 73此案是汽车撞死公共树木,政府要求赔偿; Dreifuss Thomas Widmer, Geltendmachung von Haftp flichtansprüchen aus Umweltschäden im Zivilprozess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chweizerischen Zivilprozessordnung), in: URP 2009, S. 443 ff.在这些个案中,生态损害被纳入侵权法下的损害概念。
以侵权责任统合生态损害赔偿曾是瑞士法上一个重要话题。1992年联邦司法与警察部委托两名学者起草侵权法修订草案,2000年10月9日草案被提交到联邦委员会进入征求各界意见阶段,该征求意见稿第45d条专门规范“生态损害”,将因预防、保护生态和消除生态损害而采取措施支出之费用规定为侵权法中可赔偿的“损害”。这一规定在征求意见阶段遭到猛烈批评,最终未被立法采纳。现行瑞士法主要以公法解决所采措施支出费用的转嫁问题,仅在制定法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始得适用私法路径。后文将详细阐述瑞士法律界尝试以私法解决生态损害问题的整个发展过程。
三、公法路径——“原因者付费”原则
1983年通过的《环境保护法》(1985年1月1日生效)第2条、1997年修订《水域保护法》新增第3a条已将“原因者付费”原则写进法条,即“谁引起了本法规定的措施,谁负担采取措施之费用”。2000年瑞士宪法修订时将该原则写入瑞士《宪法》第74条第2款“联邦应致力于避免有害或者负担性环境影响。因避免或者消除有害或负担性环境影响所采取措施的费用由原因者负担。”
上述条文是对原则的表述,原则一般不能直接在司法中适用,不能作为费用转嫁的直接法律依据,立法机关需要在联邦或州法中将原则具体化。⑧Haftp flichtKomm-Wagner Pfeifer, Art. 3a GSchG, N 16.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学者提出广义与狭义的“原因者付费”原则。这两者的区分标准是环境影响行为与外部费用之间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⑨Griffel Alain, Die Grundprinzipien des schweizerischen Umweltrecht, Zürcher Habilitation, Zürich 2001, N 210 ff; Griffel Alain,Zur Unterscheidung zwischen dem Verursacherprinzip im weiteren und im engeren Sinn, in: URP 2005, S. 293 ff.; Haftp flichtKomm-Wagner Pfeifer, Art. 3a GSchG, N 28.狭义“原因者付费”原则要求具体的环境影响行为或者状态与因此采取的措施并进而产生的外部费用间有直接因果关系,仅可转嫁能计算出的外部费用;广义“原因者付费”不需要两者间有因果关系,只要求原因者的行为对环境有影响即可,不需要知道到底产生了什么环境损害以及消除此等损害需要花费多少金钱。⑩Griffel Alain, Zur Unterscheidung zwischen dem Verursacherprinzip im weiteren und im engeren Sinn, in: URP 2005, S. 293 ff.
实现广义“原因者付费”原则的法律工具是环境税,瑞士联邦政府基于“原因者付费”原则获得了环境征税权能,因为通过征收环境税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此类税被称为Lenkungsabgabe)。⑪Haftp flichtKomm-Wagner Pfeifer, Art. 3a GSchG, N 18.狭义“原因者付费”原则实现工具是行政命令(die Verfügung)⑫Haftp flichtKomm-Wagner Pfeifer, Art. 3a GSchG, N 28.,行政机关责令原因者采取预防危险、消除影响等措施,或者由原因者承担行政机构采取措施支出的费用。
(一)广义的“原因者付费”原则
广义的“原因者付费”原则是针对环境污染行为征税,从而实现外部费用内部化。⑬就此点,瑞士学者借用英国学者Arthur Cecil Pigou的环境税理论。Griffel Alain, Die Grundprinzipien des schweizerischen Umweltrecht, Zürcher Habilitation, Zürich 2001, N 210 ff.税收法定原则于此仍适用,需要有制定法明确规定相应的征税要件始得征收环境污染税。⑭Rausch Heribert/Marti Arnold/Griffel Alain, Umweltrecht – Ein Lehrbuch, hrsg. von Haller Walter, Zürich/Basel/Genf 2004, N 85 und 104; Adler Denis Oliver,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Verursacherprinzip und Haftp flicht im Umweltrecht, Zürich/Basel/Genf 2011, S. 7.例如,因空气污染导致社会医疗费用增加,增加的费用应由原因者承担,需要立法者通过立法向空气污染者征税来实现。⑮Adler Denis Oliver,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Verursacherprinzip und Haftp flicht im Umweltrecht, Zürich/Basel/Genf 2011, S. 7.
环境税征收,不需要证明某项环境污染行为与具体的环境侵害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通常是众多的污染行为共同造成了污染的后果,所以无法证明某一项污染行为与环境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某行为或者状态只要是对环境有危险或能破坏环境的,即可成为环境税的征收对象。⑯Rausch Heribert/Marti Arnold/Griffel Alain, Umweltrecht – Ein Lehrbuch, hrsg. von Haller Walter, Zürich/Basel/Genf 2004, N 84.广义的“原因者付费”原则无须证明因果关系,因为现代环境问题极少是单个原因导致的,绝大多数情形是多种原因共同合力形成的,原因越多,就越难确定因果关系和明确责任归属,无须证明因果关系则避免了举证上困难而无法将影响环境的不利后果转嫁给原因者。⑰Rausch Heribert/Marti Arnold/Griffel Alain, Umweltrecht – Ein Lehrbuch, hrsg. von Haller Walter, Zürich/Basel/Genf 2004, N 84.
现行瑞士法上,环境税在多部法律中有规定。例如瑞士《环境保护法》第32a条、第35a条以下以及《水域保护法》第60a、60b条,规定了联邦和各州有权就垃圾和废水清理向原因者以征税或者其他方式转嫁费用。⑱Adler Denis Oliver,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Verursacherprinzip und Haftp flicht im Umweltrecht, Zürich/Basel/Genf 2011, S. 7.制定法上的这些规定,成为政府征收环境税的基础。
(二)狭义的“原因者付费”原则
1.概述
狭义的“原因者付费”原则要求原因者的环境影响行为或状态与导致的外部费用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⑲Haftp flichtKomm-Gähwiler, Art. 15 BGH, N 2.狭义“原因者付费”原则实现的途径是行政命令(die Verfügung)。在制定法中表述为“谁引起制定法规定的‘措施’,谁承担实施该‘措施’的费用。”⑳《水域保护法》第3a条和第54条,《环境保护法》第2条和第59条,《自然和文物保护法》第24e条b项 。其意义在于改变了以前行政机关自行承担消除环境危险和修复措施的费用。
与广义的“原因者付费”原则相比,狭义的“原因者付费”原则要求环境负担行为与产生的外部成本之间存在独立化的因果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直接原因。例如,工厂排放重金属污水导致河流污染,且排放污水的工厂仅此一家或者确定的数家,则可以确定排污行为与污染所产生的外部费用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反之,排放废气,由于空气的流动性,一般难以确定具体的一个或数个排放者与空气污染间的直接因果关系,难以对单个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量化并进而确定该行为引起的外部费用,也就难以适用狭义的“原因者付费”原则要求特定的排放者采取清洁措施或承担相应措施的费用,更合适的方法是适用广义的“原因者付费”原则对所有排放者就排放废气征税。
狭义“污染者付费”原则的理论脉络是“环境影响行为——采取措施——措施所需费用之承担”,其中核心概念是“措施”(Massnahme)。谁引起了环境法律中的这些“措施”,谁就应承担采取措施的费用。21《环境保护法》第2条,《水域保护法》第3a条。作为核心概念的“措施”需要制定法予以规定,那些没有在制定法中规定的措施,因之而产生的费用不可依据“污染者付费”原则转嫁给原因者。22HaftpflichtKomm-Wagner Pfeifer, Art. 3a GSchG, N 31.例如第三人自愿修复他人造成的环境损害,不属于《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措施”,因此不能依据“原因者付费”原则转嫁费用。23HaftpflichtKomm-Wagner Pfeifer, Art. 3a GSchG, N 31.狭义“污染者付费”原则仅仅是费用归属规则,并没有提及措施由谁作出。24Kommentar USG-Seiler, Art. 2 USG, N 30.可能是行政机关责令原因者采取措施,原因者自行承担费用;如果原因者不履行,行政机关可以代为履行而由原因者承担费用;原则上行政机关不能直接代为履行而由原因者承担费用,除非是紧急情形(例如《环境保护法》第59条规定的情形)或者法律规定了原因者之外的采取措施义务人。
虽然在许多情形原因者同时是采取措施义务人(例如《环境保护法》第10条第1款、第11条、第 26~28条、第 29a~29f条和第 31c条),但也有规定第三人(尤其是政府)作为采取措施义务人。25Kommentar USG-Seiler, Art. 2 USG, N 33.原因者与采取措施义务人分离的情形有:其一,涉及国家行政职权而政府有义务采取的措施,例如许可、控制、责令他人采取措施等;其二,个人不适合采取而交由国家采取措施,例如居民垃圾清理、土壤保护领域的措施;其三,虽然规定原因者作为采取措施义务人,但是原因者并未履行,国家代为履行;其四,原因者作为采取措施义务人,但他并不是唯一原因者,例如废弃物处理点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其五,虽然不是引起环境影响的人,但是由其采取措施更好,例如土地所有权人有义务采取隔音措施防止外界噪音(环境保护法第20条第1款、第21条、第22条第2款和第25条第3款)。26Kommentar USG-Seiler, Art. 2 USG, N 33.
“原因者付费”原则(确定费用承担人)和采取措施义务人是不同的问题,应区分。后者考虑的不仅仅是原因者是谁,还考虑恢复原状符合法律规定状态的实际可能性,而确定费用承担人只需考虑谁引起了环境负担,不必考虑谁有恢复原状的可能性(BGE 102 Ib 203, E. 2)。27Kommentar USG-Seiler, Art. 2 USG, N 34.
2.“原因者”释义
《环境保护法》第2条明确“原因者付费”原则,但并未定义“原因者”的概念。这一概念仍须借助具体化的法条以及司法实践来填补。28Kommentar USG-Seiler, Art. 2, N 59.
为了界定原因者的范围,司法判决和理论中发展出“直接因果关系”理论。29BGE 118 Ib 407, E. 4c = URP 1993 87; BGE 114 Ib 44, E. 2a; 102 Ib 203, E. 3; 101 Ib 410, E. 5b; BGer, ZBl 1987 301, E. 1; BGer,ZBl 1982 541, E. 2a; Kommentar USG-Seiler, Art. 2 USG, N 62.此处的因果关系并非是行为与环境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可归因于原因者的状态与采取的措施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需考虑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所产生费用是否可归责于(基于公平正义考虑)某个原因者。30Botschaft USG 1979, S. 780; BGE 119 Ib 389, E. 4b = URP 1994 1这一理论须做以下解读:
如果情形是《环境保护法》第59条,政府基于急迫危险采取措施并由原因者承担费用,根据“直接因果关系”理论,仅当某人的行为(或者违法不作为)或由其控制之物的状态直接导致危险事实的发生,他才为此承担费用。31这一表述首次出现在BGE 102 Ib 203; 参见Kommentar USG-Trüeb, Art. 59, N 31.并且需要危险值超过了警察法上规定的限值。32BGE 118 Ib 407, E. 4c; HaftpflichtKomm-Wagner Pfeifer, Art. 54 GschG, N 51.
如果是垃圾清理(《环境保护法》第32条第1款)或者环境许可(《环境保护法》第48条)这类并不涉及危险防御的情形,则“直接因果关系”是某人的行为(或者违法不作为)或其控制之物的状态与法定“措施”之间的因果关系。33Kommentar USG-Seiler, Art. 2, N 62.例如垃圾持有人应为清理垃圾付费、环境许可申请人须为许可付费。
“直接因果关系”作为限定承担费用者的范围的一项法律工具,与侵权法上“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并无很大区别,也有学者在确定原因者时提出类推适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34Kommentar USG-Seiler, Art. 2, N 63; Kommentar USG-Trüeb, Art. 59, N 32.两者本质上都借助价值评价限定责任主体,难以作出实质区分,35Kommentar USG-Trüeb, Art. 59, N 32.就环境法领域“原因者”的界定,本文采瑞士司法和学说通用的“直接原因理论”这一表述。
是否属于直接原因,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公式通过逻辑推理可以直接得出答案,需要在个案中借助价值判断来发现,进行价值判断时应顾及公平理念。36相当因果关系价值判断的例子:BGE 123 III 110, E. 3; BGE 116 II 480, E. 3,其思考路径对于直接因果关系同样适用。理论上又区分行为原因者(Verhaltensstörer)和状态原因者(Zustandsstörer)。行为原因者是指其行为或不作为引发(警察法上)违法状态;状态原因者是指其所控制之物直接构成危险源,而非因第三人之前的行为导致它成为危险源。37Kommentar USG-Trüeb, Art. 59, N 32; Haftp flichtKomm-Wagner Pfeifer, Art. 3a GschG, N 25.所有权人、承租人、管理人、受托人等都有可能成为状态原因者。38Haftp flichtKomm-Wagner Pfeifer, Art. 3a GschG, N 25.
3. 哪些“措施”之费用可转嫁
“原因者付费”原则的脉络“环境影响——措施——费用”中,处于核心连接地位的是“措施”,只有法律规定的措施才可转嫁费用给原因者。《环境保护法》第2条和《水域保护法》第3a条都采用相同的表达“谁引起本法规定的措施,谁承担相应的费用”。以《环境保护法》为例,该法第2条所言“措施”既包括预防措施也包括恢复原状和消除损害的措施,检验和监督措施也包含在内(BGE 119 Ib 389, E. 4b)。39BBl 1997 I 249; BGE 120 Ib 76 E. 3a; Kommentar USG-Seiler, Art. 2, N 49.但第2条本身并不是据以确定哪些措施由原因者付费的依据,还需经由其他法条明确第2条所指措施有哪些。40Kommentar USG-Seiler, Art. 2, N 49.例如,《环境保护法》第10b条规定需要环评的设施,建造人需要制作环境影响报告,费用当然由当事人承担,无须法律规定费用归属,因为任何人承担自己行为的花费乃理所当然之事,法律未规定费用转嫁之规定,则费用留在原处。行政机关对环境影响报告的评判(第10c条)之费用,从《环境保护法》中并不能判断是否由当事人承担,不能以《环境保护法》第2条作为费用转嫁的依据,需要借助其它法律。41Kommentar USG-Seiler, Art. 2, N 105.《环境保护法》第10条规定设施经营者或持有人有防范灾难的义务,为防范灾难所应采取的措施是其义务之内的事,其费用理所当然也是由设施经营者或持有人承担。42Kommentar USG-Seiler, Art. 2, N 106.但防噪方面,法律规定有所偏离“原因者付费”原则。一方面,噪音是排放物(Immission)之一种,适用排放物防范的一般规定,噪声源的持有人是采取措施义务人,须为消除噪音承担费用(《噪音防治条例》第16条第1款;BGE 120 Ib 76,E.3a);43Kommentar USG-Seiler, Art. 2, N 110.另一方面,噪音防治领域有其特别规定,在一定要件下受噪声干扰的建筑物所有权人应采取防噪措施(《环境保护法》第20条第1款、第21条第1款、第22条第2款、第24条以及第25条第3款),费用由建筑物所有权人承担(BGE 120 Ib 76,E. 3d und 4b),仅在特别规定情形,所有权人可请求噪声源持有人赔偿防噪之花费(例如《环境保护法》第20条第2款)。44Kommentar USG-Seiler, Art. 2, N 110.垃圾清理,《环境保护法》第32条第1款规定由垃圾持有人承担费用,不论法律规定清理义务人是谁。《环境保护法》第59条是“原因者付费”原则重要的具体化条文,在急迫危险情形,行政机构可以直接采取措施预防和消除危险,费用由原因者承担。这里并未限定“措施”的种类,任何必要且合理的防御和消除急迫危险的措施皆可,行政机关有裁量权,但前提是需要存在具体的直接危险(BGE 114 Ib 44, E. 2a)。45Kommentar USG-Seiler, Art. 2, N 130.
(三)“原因者付费”原则的实现
“原因者付费”原则在具体情形中是如何实现的呢?
首先,如果原因者也是采取措施义务人并且他也采取了法律规定的措施,那么他已经承担了相应的费用,实现了“原因者付费”原则追求的费用内部化的理念。46BGE 118 Ib 407, E. 3b und c.
其次,如果原因者是采取措施义务人但他不履行,则政府可以代为履行并由原因者承担费用,此种费用转嫁无须制定法另行规定,它是行政执行程序的应有之义。47BGE 105 Ib 343, E. 4b; Kommentar USG-Seiler, Art. 2 USG, N 37; Häfelin Ulrich/Müller Georg/Uhlmann Felix, Verwaltungsrecht(5. Au fl.), Zürich/Basel/Genf 2006, N 1154 ff.
再次,如果原因者与采取措施义务人不同,法律规定政府为采取措施义务人时,费用首先由政府负担。政府若要转嫁这比费用,可通过征税或者其他费用转嫁条款实现费用转嫁。依据税收法定原则,需要制定法明确授权政府征税始得征收。48Kommentar USG-Seiler, Art. 2 USG, N 37. 税收法定原则相关判决参见:BGE 126 I 180, E. 2a; 125 I 173, E. 9; 123 I 248, E. 3;123 I 254, E. 2; 120 Ia 265, E. 2a; 118 Ia 320, E. 3a.《环境保护法》第35a~35c条具体规定了政府的环境征税权能。《环境保护法》就紧急情况下政府采取的检查、监督和修复措施直接规定了费用转嫁条款,依该法第32d和第59条,此等费用由原因者承担。
最后,如果法律规定一个不同于原因者的个人作为采取措施义务人,那么在原因者和采取措施义务人之间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后者可以向前者依民事法律请求损害赔偿(例如依《民法典》第679条或者《环境保护法》第59a条)。49Kommentar USG-Seiler, Art. 2 USG, N 40.例如依《环境保护法》第20条第2款和第25条第3款,噪声引起者应赔偿不动产所有权人(作为采取措施义务人)采取防噪措施的费用;依《环境保护法》第32d条,废弃物清理点的污染,原因者承担其所占原因相应比例的费用。如果不存在损害赔偿关系,则采取措施义务人承担最终费用。
四、私法路径——侵权损害赔偿
(一)侵权法全面修订与生态损害赔偿
随着20世纪世界科技的发展,瑞士债法制定时(1911年颁布,1912年生效)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的侵权责任法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立法机关陆续颁布了一些单行法应对特殊侵权,但也导致侵权法出现条文矛盾之处以及复杂难懂只有专家才能理解,因此长期以来法律界希望能够对侵权法做一次全面修改。50延续多年的侵权法全面修改的讨论,其历史发展参见:Widmer Pierre, Die Vereinheitlichung des schweizerischen Haftpflichtrechts-Brennpunkte eines Projekts, in: ZBJV 130/1994 S. 385 ff.; Weber Stephan, Revision des Haftpflichtrechts, in: HAVE 2002 S. 221.
从学者提议、讨论到官方重视,这个过程中第一个分水岭事件是1988年秋季联邦“司法与警察部”(EJPD)组织“研究委员会”(Studienkommission)研究损害赔偿法(涉及整个侵权法以及影响到侵权法的法规)的全面修订。51Widmer Pierre, Die Vereinheitlichung des schweizerischen Haftpflichtrechts- Brennpunkte eines Projekts, in: ZBJV 130/1994 S. 388.历时近3年(至1991年9月5日),该研究委员会向司法与警察部部长提交了最终报告。在这之前,侵权法全面修订推动已有20多年。1967年第101届瑞士法学家大会议题就是“侵权法统一的若干问题”,报告人 Emil W. Stark和 François Gilliard报告了瑞士侵权法存在的问题,这其中许多问题Karl Oftinger教授在他的《瑞士侵权法》(1940年版)一书中已提出。从瑞士债法制定以来,陆续又就机动车、轨道交通、电力、狩猎、航空运输、管道设备、原子能生产、水域保护、易爆物等领域侵权责任制定了特别法律。这些新法律与债法侵权责任条文并不完全协调,促使瑞士法学会在20世纪60年代讨论侵权法的全面改革。52Widmer Pierre, Die Vereinheitlichung des schweizerischen Haftpflichtrechts- Brennpunkte eines Projekts, in: ZBJV 130/1994 S. 387.
学界的讨论并没有激起立法者的重视。不过当时的司法部长(联邦委员之一Von Moos)接受了建议,他的继任者(联邦委员之一Kurt Furgler)为侵权法全面改革计划还特意雇佣了一个员工。国会里在侵权法领域也有零星的修法和立法动议,例如修订《轨道交通责任法》(Eisenbahnhaftpflichtgesetz)的动议,之后出现关于慰抚金和无过错产品责任的法律动议。
由于立法者并不重视,全面修订侵权法的计划眼看要进入废纸堆,事情却发生了突然的转机。1986年11月1日,瑞士巴塞尔一个叫Schweizerhalle的工业区(近巴塞尔)一家叫Sandoz的制药公司仓库起火,导致化学制品和大量杀虫剂进入莱茵河,河水污染,鱼和其它水生生物大量死亡。这一事件被称为“Schweizerhalle事故”。53Giger, Walter. (2009). The Rhine red, the fish dead—the 1986 Schweizerhalle disaster, a retrospect and long-term impact assessment.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16 Suppl 1. S98-111. 10.1007/s11356-009-0156-y.6个月前的4月26日,前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境内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件,举世震惊,也引起瑞士人的紧张,将瑞士立法者从对侵权法修订的冷漠中拉出,再加上几个月后莱茵河严重污染事件的社会影响,几十个立法动议递到联邦委员会,联邦委员们再不能对侵权法全面修订敷衍了事,必须要处理这事。54Widmer Pierre, Die Vereinheitlichung des schweizerischen Haftpflichtrechts- Brennpunkte eines Projekts, in: ZBJV 130/1994 S. 388.在这个背景下,1988年秋季联邦“司法与警察部”(EJPD)组织“研究委员会”(Studienkommission)研究损害赔偿法(涉及整个侵权法以及影响到侵权法的法规)的全面修订。55Widmer Pierre, Die Vereinheitlichung des schweizerischen Haftpflichtrechts- Brennpunkte eines Projekts, in: ZBJV 130/1994 S. 388.3年后,该研究委员会向司法与警察部部长提交了最终报告。56报告内容见Widmer Pierre, La réforme du droit de la responsabilité civile, in: AJP 1992 S. 1099 ff.1992年联邦司法与警察部委托研究委员会的两名成员在最终报告的基础上初步起草侵权法全面修订草案。初步草案实际上不晚于1994年即已完成,571994年的一篇文章提到初步草案实际已经完成,而文章的作者是草案起草人之一,参见:Widmer Pierre, Die Vereinheitlichung des schweizerischen Haftpflichtrechts- Brennpunkte eines Projekts, in: ZBJV 130/1994 S. 389.但直到2000年10月9日提交联邦委员会进入征求各界意见阶段(Vernehmlassungsverfahren)。2000年草案征求意见稿有书面材料可查,1994年到2000年之间草案的变化过程则无从查起,若无特别说明,本文所称草案条文指2000年征求意见稿。58征求意见稿的全文参见瑞士联邦司法部网站:https://www.bj.admin.ch/dam/data/bj/wirtschaft/gesetzgebung/archiv/haftpflicht/vnve-d.pdf(德文版)。1994年草案中即已提到了“生态损害”,将生态损害赔偿纳入侵权法中。根据前一年(1993年)在瑞士卢加诺召开的欧洲司法部长会议达成的“生态损害恢复公约”规定,不处于或不能处于任何人权利之下的生态法益受侵害或毁损的,应采取修复措施或者赔偿修复之费用。59Widmer Pierre, Die Vereinheitlichung des schweizerischen Haftpflichtrechts- Brennpunkte eines Projekts, in: ZBJV 130/1994 S. 401.这也影响到瑞士生态损害立法。侵权法全面修订草案中“生态损害”条文属于私法性质的侵权责任规范,请求的对象是采取预防、保护和恢复措施支出之费用,请求权人是主管机构或环保组织。就相关措施支出费用的转嫁问题,《环境保护法》和《水域保护法》中已有规定,但这两部法中并非以侵权责任的形式来规定“生态损害”,而是以行政法上的“费用分担”(Kostenauflagen)将预防生态危险、修复生态损害的费用转嫁给原因者(现行《环境保护法》第59条,《水域保护法》第54条)。形式上看是行政法上的费用分担,实际效果相当于承担侵权责任,联邦法院也直接称呼为侵权责任(Haftpflicht)。60BGE 114 Ib 48; Keller Alfred, Haftpflicht im Privatrecht Band I (6. Aufl.), Bern 2002, S. 357.侵权法修订草案将行政法上的费用转嫁规则私法化,61Widmer/Wessner, Revision und Vereinheitlichung des Haftp flichtrechts - Erläuternder Bericht, S. 385,这是侵权法全面修订草案的起草人对草案做的说明报告,该文件在瑞士联邦司法部网站可查:https://www.bj.admin.ch/dam/data/bj/wirtschaft/gesetzgebung/archiv/haftpflicht/vn-ber-d.pdf, 2019年8月23日访问;Keller Alfred, Haftpflicht im Privatrecht Band I (6. Aufl.), Bern 2002, S. 357.成为侵权法一项归责标准。草案中,除了政府外,环保组织也被列为生态损害赔偿请求权人。
2000年公开的侵权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延续了以侵权法来规范生态损害的思路,将其规定在第45d条,条文如下:
第45d条 [对环境的影响]
1.对环境影响的情况下,可赔偿的损害尤其包含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采取以下措施的费用:
a.防止急迫影响发生;
b.减轻持续影响或者发生的影响的负面后果;
c.毁损的环境要素恢复原状或者以同等价值的要素替代。
2.如果受危害或被毁损的环境要素不是物权客体,或者权利人不采取必要措施的,则有管辖权的集体、瑞士全境或者区域性的环保组织在实际准备了相应措施或者已经采取措施并且依法有权采取措施的情况下,得请求损害赔偿。
侵权法全面修订草案遭受了激烈批评。62Roberto Vito, Schweizerisches Haftpflichtrecht, Zürich/Basel/Genf 2002, S. 6 N 15 ff.; Portmann, Revision und Vereinheitlichung des Haftpflichtrecht, in: ZSR 2001 I, S. 327 ff.联邦委员会征求意见结果显示,对于散落于各处的损害赔偿法规进行形式上统一,大部分人表示支持,但对于内容上的更改遭到强烈的反对。63征求意见结果于联邦司法部网站可查:https://www.bj.admin.ch/dam/data/bj/wirtschaft/gesetzgebung/archiv/haftpflicht/ve-ber.pdf,2019年8月23日访问,文件正文第1页以下是支持和反对草案的情况统计。因此联邦委员会决定暂停推进此项立法(暂停时间2003~2007年)。64Amtliches Bulletin 08.1007: Revision und Vereinheitlichung des Haftpflichtrechtes, https://www.parlament.ch/de/ratsbetrieb/suchecuria-vista/geschaeft?AffairId=20081007, 2019年8月22日访问。2009年1月21日,联邦委员会正式放弃对侵权法全面修订和统一化的工作。65瑞士联邦司法部网站上的文件记录了从1988年成立“研究委员会”研究全面修订和统一侵权法到2009年最终放弃的过程,网址参见https://www.bj.admin.ch/bj/de/home/wirtschaft/gesetzgebung/archiv/haftplicht.html,2019年8月23日访问。
在征求意见阶段,就草案第45d条生态损害赔偿条文提出的意见有:66侵权法全面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结果第176页以下,网址:https://www.bj.admin.ch/dam/data/bj/wirtschaft/gesetzgebung/archiv/haftpflicht/ve-ber.pdf,2019年8月24日访问。1.影响环境者需要对必要措施的费用予以赔偿,此点得到认同;2.《环境保护法》第59条、《水域保护法》第54条以及其他环境领域法律已经规定了对必要措施费用的赔偿,采取的是行政法上的路径,急迫情形行政机关可直接采取必要措施并由原因者承担费用。非急迫情形,行政机关责令原因者采取必要措施,若原因者不采取措施,行政机关可以替代履行并由原因者承担费用。必要措施的费用是通过行政法上费用转嫁(Kostenauflagen)实现的,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以行政命令(Verfügung)的形式向原因者收取费用,无必要改为民事诉讼途径来请求必要措施的费用;3.现行环境保护法律规定的原因者承担必要措施之费用,其思想基础是“原因者付费原则”,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原因者侵权责任情形,也常见于没有违法行为的情形,例如垃圾清理、废水处理依原因者付费原则其费用转嫁给原因者。同样都是将环保所采措施之费用转嫁给原因者,没有必要视行为是否违法而依据不同的法律程序。67侵权法全面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结果第178页。且《环境保护法》《水域保护法》等法律一直以来以行政程序处理采取措施的费用转嫁,争议时由行政法院审理,行政法院对环保类案件较为熟悉。68侵权法全面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结果第179页。若将行政机关环境保护职能混杂行政和民事程序,增加了行政机关的工作量,对于行政执法是个弊端,也给法院增加负担。69侵权法全面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结果第180页。此外,行政程序与民事程序诉讼费用也不同,采取民事程序时,当事人很可能交纳更多的诉讼费。
公私法救济之争的结果是,放弃以私法来规范生态环境保护中所采措施的费用赔偿问题,坚持以公法解决所采取措施的费用转嫁问题,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例如《基因技术法》第31条、《环境保护法》第59abis条第9款)。
(二)《基因技术法》与生态损害赔偿
侵权法全面修订是一项耗时长久的工作,在这期间立法者颁布了《基因技术法》。《基因技术法》的条文受到侵权法全面修订的影响,立法者等不及侵权法修订时将生态损害赔偿纳入侵权法,在制定《基因技术法》时便于该法第31条引入了相似规范。70Schöbi Felix, Der Umgang des Gesetzgebers mit Umweltschäden, in: URP 2009 S. 475.须提及的是两点:第一,《基因技术法》中规范的生态损害是因基因编辑技术而引发,不包含其他情形;第二,损害赔偿请求权人是主管机构,环保组织不是请求权人。
《基因技术法》制定时,在附件4中一并修订了《环境保护法》,新增《环境保护法》第59abis条,该条第9款就病原体导致的生态损害规定了生态损害赔偿,请求权人是主管机构。
无论是侵权法全面修订草案第45d条、《基因技术法》第31条,还是《环境保护法》第59abis条规定的生态损害,指的都是为了预防、保护生态和消除损害所采取措施支出的费用,不包括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生态服务功能在瑞士法上原则上不可赔偿,仅当制定法有特别规定时才有赔偿的可能(例如《自然与文物保护法》第24e条规定,当恢复原状不能时,可以判决赔偿适当金额)。
《基因技术法》第31条和《环境保护法》第59abis条与侵权法全面修订草案第45d条都源自相同的立法思想,即以私法路径解决生态损害问题。前两条被立法者纳入法律而后一条被废止,形成了现行瑞士法上生态损害救济的局面:主要以公法救济,但因基因编辑和病原体感染而导致的生态损害,主管机构可以依据侵权法请求损害赔偿。
(三)联邦法院的判决
将目光回溯到1964年联邦法院的一则判决(BGE 90 II 417),这一判决是现在瑞士法讨论生态损害民事救济路径必然要讨论的案件。在BGE 90 II 417这个案例中,化工厂排污导致河流污染、鱼类死亡。判决没有涉及水质治理问题,争议点在鱼类死亡是否赔偿。这个案件,水产作为生态之一部分,遭受破坏恢复原状之费用,联邦法院认可了侵权损害赔偿。但赔偿的仅仅是清理死鱼和投放新鱼苗的费用。投放之新鱼苗与原来之渔业资源相比的损失,法院判决不予赔偿。判决理由是,河里原来的鱼,州政府并无所有权,因此新鱼苗与成年鱼的价差不在赔偿范围。清理死鱼虾和投放鱼虾幼苗,其目的在恢复生态,生态恢复并不在于回复到和损害发生前一模一样的状态,没有必要投放同等大小成熟的鱼虾,只要投放幼苗即可实现生态恢复目的。
几年后,1973年12月14日通过的《渔业法》将渔业资源的损害赔偿纳入到该法第51条。立法者制定该条恰恰基于对上述联邦法院判决的不满。71BBl 1973 I 677, S. 698.立法者认为上述判决没有赔偿成熟鱼虾与幼苗之间的差价,减轻了引起损害者的责任,因此第51条明确规定渔业水域受损时赔偿范围包括水产的经济损失,这个损失不是以可证明的捕捞量来计算,72指与过往的捕捞量相比,现在的捕捞量降低数额。而是以水域中受损害的全部水产数量来计算,即便这些水产属于公共资源。73Schöbi Felix, Der Umgang des Gesetzgebers mit Umweltschäden, in: URP 2009 S. 473 f.; Haftp flichtKomm-Gähwiler, Art. 15 BGF, N 18.这一规定被1991年《渔业法》第15条沿袭。
在另一则涉及野生动物的联邦判决,74BGer Urteil 4C.317/2002 vom 20. Februar 2004, E. 4 und 5 = AJP 2004 1262.此案原告以民事诉讼请求损害赔偿,法院未支持,并不能排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假设行政机关以行政程序责令射杀秃鹫者恢复原状或者承担恢复原状的费用,则首先须检查其行政行为有无法律依据。与野生鸟类保护有关的法律是《狩猎及野生哺乳动物和鸟类保护法》《自然与文物保护法》以及作为环境保护的基础性法律《环境保护法》。检索相应法条,有可能作为法律依据的是《自然与文物保护法》第24e条,行政机关据此责令射杀者恢复原状或承担恢复原状的费用(第24e条第1、2项)。本案恢复原状则是重新投放一只野生秃鹫,这是否可能不无疑问。笔者以为,野生秃鹫无法通过市场购买获得,虽然通过实验室培育然后放生有可能但这一措施超出了合理范围,本案射杀秃鹫对生态之影响无法恢复原状。无法恢复原状的,行政机关可以责令射杀者赔偿一定金钱(第24e条第3项),该笔金钱并非是损害赔偿,有学者将其比作慰抚金(参见:Dupont Anne-Sylvie, le dommage écologique, Le rôle de la responsabilité civile en cas d'atteinte au milieu naturel, Genf 2005, S. 134; Felix Schöbi, Der Umgang des Gesetzgebers mit Umweltschäden, in URP 2009, S. 480.)。除了行政责任外,还可能依据《狩猎及野生哺乳动物和鸟类保护法》第17条承担刑事责任。被告射杀了环保组织培育后放生的野生秃鹫,环保组织要求赔偿,联邦法院认为,野生秃鹫一经放生即为无主物,野生秃鹫被射杀,属于“纯粹生态损害”,不是侵权法上可赔偿的损害,法院未支持赔偿请求。这一案件常被引用来说明“纯粹生态损害”民事上不可赔偿。75BBl 1993 II 1445, S. 1150; Schöbi Felix, Der Umgang des Gesetzgebers mit Umweltschäden, in: URP 2009 S. 475.
上述两则联邦法院判决,同样是野生物种,河里的鱼虾资源得以赔偿(联邦法院限于恢复生态,《渔业法》除了恢复生态外还规定赔偿经济损失),未被认定为“纯粹生态损害”,而野生秃鹫被射杀被认为是“纯粹生态损害”,不属于民事损害,不予赔偿。同样是无主物,民事上有不同的裁判,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瑞士法上“生态损害”这个概念并未被定义,而侵权法中“损害”概念弹性很强,法官通过扩张解释可以将一些新情形纳入“损害”概念下。第二,司法实践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判决是否可依据侵权法赔偿时,更多是考虑被损坏之物是否有经济价值,76有瑞士学者认为,对于公共环境法益之侵害,侵权法有可能适用。侵权法适用的前提是,需要触及公共经济利益。参见:Beatrice Wagner Pfeifer, Umweltrecht - Besondere Regelungsbereiche, Zürich 2013, N 1821.而不在于该物是私人所有、集体所有抑或是无主物。有市场经济价值的鱼虾,即便为无主物,但它属于有经济价值的资源类物品,政府仍可请求侵权损害赔偿;没有市场经济价值的野生秃鹫,则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1964年联邦法院的判决(BGE 90 II 417)也有其时代背景,当时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公法并不完善,借助私法才能实现恢复生态的目的。随着环境保护公法的发展,以私法解决生态损害问题已难见于联邦法院判决之中。1964年的这则判决可以看作是偏离法律体系的一个例外。依据现行法,应该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命令原因者投放新鱼苗。
五、公、私法路径之思考
(一)公、私法司法适用上的差异
生态损害发生后,谁有权采取何种法律措施来应对,涉及法律适用问题,应采取私法救济还是采取公法救济,并不是由权利人恣意选择的,而应在本国法律体系中查找可适用的规范,将案件事实涵摄进构成要件,如果案件事实满足了构成要件,则相应的法律效果适用于该案件。
在法律适用问题上,行政法和民法存在区别,进而导致面对新问题时,应首先考虑采取行政法进路还是采取私法进路。若考虑行政法进路,新问题在既有行政法框架下没有具体规范,因而产生法律漏洞,可否通过类推适用来填补法律漏洞呢?行政法学上,并未否定填补法律漏洞之可能性,但若涉及干涉人民自由权利的行政行为,普遍适用法律保留原则,须有法律授权始得为之,不可类推适用。77陈敏:《行政法总论》,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54页。该文献提及: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4条明文规定“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处罚,以行为时之法律或自治条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对行为时未规定应予处罚之行为,自不得类推适用其他处罚规定,裁处行政罚。在其他干涉行政领域,亦应避免以类推适用或者目的性限缩方法创设或加重人民之负担,以超越实定法之法律续造创设或加重人民之负担,自更非所许。台湾行政法院60年判字第417号判例明示“公法之适用,以明文规定者为限,公法未设明文者,自不得以他法之规定而类推适用,此乃适用法律之原则。”行政法院60年判字第278号、司法院释字第151号、第210号都表明这一原则。行政法一个基本原则是依法行政原则,包含三项内容:1.法律的拘束效力;2.法律优越原则;3.法律保留原则。78翁岳生编:《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以下。依法律保留原则,行政权之行动,仅于法律有授权之情形,始得为之,故在法律无明文规定之领域而为行政行为,有违反法律保留原则之可能。79同注78,第191页以下。就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领域,有各种理论,80同注78,第193页以下。但就干预行政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并无争议。据此,行政权侵害国民之权利自由或对于国民课以义务负担等不利益之情形,须有法律根据。81同注78,第193页。
与行政法规范相比,民法规范的适用空间则更具弹性。以本文涉及生态损害赔偿问题为例,体系上可能定位于侵权法中。即便未设生态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从法律适用的角度,也会自然将目光置于侵权法中寻找规范。瑞士债法第41条第1款“因故意或过失,不法致他人损害者,应负赔偿责任”,这一侵权责任一般规范本身高度抽象,越抽象的法规可涵摄的案件事实越丰富。在以第41条处理生态损害赔偿问题的时候,一个焦点问题是“生态损害”是否被债法第41条“损害”所涵摄。民法上传统的损害概念,是不包括“生态损害”的,但民法规范解释上,有很大的弹性,通过目的性扩张等解释方法,使得“生态损害赔偿”被债法第41条涵摄成为可能。82我国有学者主张将生态损害通过拟制条款纳入侵权法损害概念下,参见李昊:《损害概念的变迁及类型建构》,载《法学》2019年第2期。
公法与私法在法律适用上的上述区别,导致了在新问题出现行政法上欠缺规范时,据依法行政之原则,无法以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相反,民法不仅有一些一般性规定,因其抽象而涵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在规范的解释上,可通过目的性扩张等手段,发现原来并不在文义范围内的裁判规则,以使新问题得以适用该规范。生态损害适用侵权法规范便是突破了“损害”的传统概念。
(二)瑞士法采公法路径的原因
将目光置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瑞士生态损害在当时法律上还是一个新问题,对此无论公法还是私法都缺少规则。但由污染者承担生态损害修复费用在理论上已经得到法律界认可,法院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从法律适用技术上落实费用转嫁的思想。鉴于依法行政原则,在欠缺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公法进路难以从技术上实现费用转嫁,采取私法进路便成为备选项。前文提及的1964年联邦法院的一则判决(BGE 90 II 417)便可佐证瑞士法院曾经以私法进路技术化处理生态损害。
瑞士环境领域立法进展很快,1971年颁布的《水域保护法》便将“原因者付费”原则具体化为可运用于司法审判的具体规则。经过十多年的发展,1983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将“原因者付费”原则一方面以原则形式规定在该法第2条,另一方面以规则形式规定在该法各处,尤其以第59条为明显。至此,公法立法已经回应了生态损害问题。
与公法的快速回应相比,瑞士侵权法则迟迟未能以立法的形式回应生态损害问题,还停留在零星判决和学者讨论上。当公法立法解决这一问题之后,再以私法解决这一问题显得没有必要。这就形成了瑞士现行法主要以公法路径解决生态损害问题,仅在转基因和病原体导致生态损害情形,因法律有明确规定,可以适用侵权损害赔偿。
(三)我国生态损害救济路径
从理论上说,我国生态损害救济路径也可从公法和私法两个视角观察。我国学者所言生态损害,除了预防、保护和恢复生态所支出费用的转嫁外,还涉及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本文仅仅探讨所支出费用的转嫁问题。
从公法视角观察,费用转嫁的原理是“原因者付费”原则,而司法上适用“原因者付费”原则必须满足依法行政原则,也即需要有具体的制定法规则。以我国《环境保护法》为例,该法第5条提到“损害担责”原则,可以作为“原因者付费”原则的表述,但原则本身并不能作为行政命令之制定法依据,尚需具体化的条文方可。但我国《环境保护法》并未规定具体化的费用转嫁规则,给生态损害公法救济带来困难。83《环境保护法》第 59 条规定违法排放污染物的罚款,罚款数额考虑防治污染设施的运行成本、违法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或者违法所得等因素确定。违法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可否理解成包含采取预防、保护和恢复措施所支出的费用,难以明确。《水污染防治法》等环境领域立法也同样未规定具体可运用于司法的费用转嫁规则。
公法上欠缺费用转嫁规则时,私法路径自然进入人们的视野。2015年12月中办与国务院联合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已废止),到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再到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第七章“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规定的以私法路径解决生态损害问题,私法路径解决“生态损害”问题,立法上已经走在了公法路径之前。
生态环境保护涉及的是公共利益,并非民法上所保护之利益,从法律逻辑上看,以公法保护为佳;但法律逻辑并不能限制立法者,对立法者而言,无论是公法路径还是私法路径,不存在可不可以的问题,最多只是立法技术佳与欠佳问题。
我国立法者选择私法路径解决生态损害赔偿问题,这一路径在比较法上也可寻其踪迹,瑞士法上公、私法路径之竞争便是佐证,只是瑞士立法者最终选择了公法路径,而我国立法者选择了私法路径。84以私法路径解决我国生态损害问题,参见李昊:《损害概念的变迁及类型建构》,载《法学》2019年第2期。
六、环保组织的地位
(一)环保组织与行政公益诉讼
瑞士法上,与行政公益诉讼有关的概念是“协会诉愿”(Verbandbeschwerde),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85Baumgartner Samuel P., Class Action and Group Litigation in Switzerland, in: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Business Volume 27 Issue 2 Winter 2007, p. 331.与之相对应的民事程序是民事公益诉讼(Verbandklage)。
就协会得提出的行政诉愿类型,瑞士学界归纳为四种:86Griffel Alain, Das Verbandsbeschwerderecht im Brennpunkt zwischen Nutz- und Schutzinteressen, in: URP 2006 S. 97 f.第一种,为了协会自身利益,当行政行为触及协会自身利益时,协会得提起行政诉愿。此种类型,协会与自然人在程序上地位没有区别。第二种,以他人名义且为了他人利益提起行政诉愿,这类程序中协会的地位与律师地位相同,不是诉讼当事人,而是代理人。第三种,以协会的名义,但为了成员的利益提起行政诉愿,87德文术语为egoitische Verbandbeschwerde.典型情况是行业协会针对州颁布的影响成员利益的法规提起行政程序,这种程序上地位是司法实践发展出来的,制定法并未明确规定。第四种,并非为了协会本身或者会员的利益,而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提起的行政诉愿,笔者将其译为“公益型协会诉愿”(Ideelle Verbandbeschwerde)。此种程序涉及的利益是抽象的,提起程序的协会不用证明存在具体受保护的利益。但此类程序仅当制定法特别规定才可提起,法无规定协会不得提起此类诉愿。
环保组织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应归类于上述“公益型协会诉愿”,制定法明确规定情形,环保组织始具有提起诉愿资格。
瑞士法上,环保组织的公益诉愿资格是因其在环保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立法者顺水推舟赋予其此等地位。瑞士法上第一次明确规定公益型协会诉愿是在1966年《自然与文物保护法》88Bundesgesetz über den Natur- und Heimatschutz (NHG) vom 1. Juli 1966 (SR 451).第12条。《自然与文物保护法》的立法背景是:89Griffel Alain, Das Verbandsbeschwerderecht im Brennpunkt zwischen Nutz- und Schutzinteressen, in: URP 2006 S. 99 f.二战后,瑞士居住区和工业区前所未有的增加,加上国道网建设、山间水坝建设以及农业,自然和风景受到巨大负面影响。但直到1962年宪法修改前,并未规定联邦政府保护自然和文物的义务(同时也是职权)。很长一段时间,自然和风景保护都是自然与文物保护协会的事。正因为自然与文物保护协会在政府缺位时发挥了先锋作用,立法者在起草《自然与文物保护法》时才考虑赋予此等协会行政公益诉愿主体资格。90形成历史详见:Enrico Riva,Die Beschwerdebefugnis der Natur- und Heimatschutzvereinigungen im schweizerischen Recht, Diss.Bern 1980, S. 49 ff.
在《自然与文物保护法》开创性的规定“公益型协会诉愿”制度后,1983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第55条也采纳了该制度。此后,1985年颁布的《人行道和徒步道法》(Fuss- und Wanderweggesetz)、1995年 颁 布 的《 平 等 法 》(Gleichstellungsgesetz)、2002年颁布的《残疾人平等法》(Behindertengleichstellungsgesetz)以及2003年颁布的《基因技术法》(Gentechnikgesetz)都规定了协会诉愿权。从实践角度看,目前仍发挥作用的是《自然与文物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协会诉愿权,其他法律中的协会诉愿权实践意义不大。91Griffel Alain, Das Verbandsbeschwerderecht im Brennpunkt zwischen Nutz- und Schutzinteressen, in: URP 2006 S. 100 f.
制定法在规定“公益型协会诉愿”时,对适用要件作了严格限制,以防协会滥用诉权掣肘行政执法。以现行《环境保护法》第55条为例,一方面对有权提起诉愿的环保组织作了限制,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可提起公益诉愿:第一,须在全瑞士范围内活动;92州法可以赋予仅在该州从事活动的环保组织诉愿权利。第二,追求公益目的;第三,提起诉愿的领域须该组织作为章程目的已践行10年以上;第四,联邦委员会列该组织为有权提起公益诉愿的组织。除了对诉愿主体的限制外,诉愿事项也受限制,公益诉愿并不适用于全部行政命令,制定法特别规定其适用事项,《环境保护法》第55条第1款规定,公益型协会诉愿适用于规划、建设、变更设施需要环评情形的行政命令。该法第55b条规定协会未积极对规划等提出质疑的,可能丧失诉愿权利的情形,是对诉愿权利的进一步限制。
瑞士法上环保组织的“公益型协会诉愿”权利,受到支持与质疑两种思想的影响,体现出一定的特点:一方面受到支持者观点影响,因此制定法采纳了公益型协会诉愿制度;另一方面受到质疑者观点影响,因此严格限制该制度的适用空间。
支持“公益型协会诉愿”制度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为环境保护提供与环境利用平等的法律武器。93Griffel Alain, Das Verbandsbeschwerderecht im Brennpunkt zwischen Nutz- und Schutzinteressen, in: URP 2006 S. 105.公法在适用时,常需权衡各种公、私利益,以期实现利益的协调和平衡,生态环境不会说话,不能维护自己利益不能委托律师,因此制定法有必要为其安排代言人,以便公法适用时可以考虑到生态环境保护。利用生态环境和保护生态环境是一对对立的利益,在权衡二者时,利用生态环境的利益考虑常占上风,因为它显得具体、明确、急迫且必要,执法机构在做决定时,常受到政治、经济等影响,无论从私人利益还是公共利益看,利益生态环境都有其推动因素。相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单个来看,常常破坏性不大,因此难被重视,个别行为累计起来,则影响明显,但在行政机关利益衡量时,生态环境保护的考虑不如生态环境利用迫切,因此需要为生态保护提供代言人,实现法律武器的平等。
第二,预防作用。94Griffel Alain, Das Verbandsbeschwerderecht im Brennpunkt zwischen Nutz- und Schutzinteressen, in: URP 2006 S. 106.因为协会拥有诉愿权利,因此促使项目开发者从一开始就遵守相关环保法律,行政机关为避免被诉,也会谨慎作出决定。
第三,从争议走向磋商。95Griffel Alain, Das Verbandsbeschwerderecht im Brennpunkt zwischen Nutz- und Schutzinteressen, in: URP 2006 S. 107.法律程序是保护生态环境最后的保障,更好的途径是环保组织从项目规划开始就积极与工程开发方和行政机关进行磋商,避免生态损害。如果没有协会诉愿权利做后盾,工程开发方和行政机关不会赋予环保组织磋商的权利,有了这个后盾,磋商才变得可能。从争议走向磋商的模式,也受到各方的欢迎。
质疑协会诉愿权的观点认为,第一,生态环境保护是主管行政机关的事,行政机关才是生态环境的守护人;第二,协会行使诉愿权使得行政行为被延迟或阻止,有碍行政;第三,环保组织可能滥用公益诉愿权利。96Griffel Alain, Das Verbandsbeschwerderecht im Brennpunkt zwischen Nutz- und Schutzinteressen, in: URP 2006 S. 109 ff.瑞士环保部上世纪90年代委托日内瓦大学法律评估研究所评估协会诉愿权的实施情况。1996-2003年的数据显示,协会诉愿引发的行政诉讼在全部行政诉讼中的比例不到1%,平均每年7.5个协会诉愿,胜诉率63%;而平均每年行政诉讼达989个,胜诉率18.6%。97Griffel Alain, Das Verbandsbeschwerderecht im Brennpunkt zwischen Nutz- und Schutzinteressen, in: URP 2006 S. 109.专家得出结论,98Alexandre Flückiger/Charles-Albert Morand/Thierry Tanquerel, Evaluation du droit de recours des organisations de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Hrsg. BUWAL, Schriftenreihe Umwelt Nr. 314, Bern 2000, S. 40 f., 80 ff., 247 ff. (Länderberichte); dieselben, Wie wirkt das Beschwerderecht der Umweltschutzorganisationen? (Kurzfassung der Evaluation, bearbeitet von Urs Steiger, hrsg. vom BUWAL),Bern 2000, S. 11 f. Zur neueren Rechtslage in Deutschland Marion Rosenbaum/Dirk Tessmer, Das Verbandsklagerecht in Deutschland,Entwicklung und verbleibende Defizite, in: natur + mensch 3/2003 (Hrsg. Rheinaubund), S. 22 ff.; Rausch/Marti/Griffel (Anm. 19), Rz. 796.环保机构在行使权利时相当克制并且进入法院的公益行政诉讼胜诉率远高于行政诉讼平均胜诉率。数据足以反驳质疑者的观点,第一,行政机关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但从公益行政诉讼胜诉率看,行政机关并未充分履行这一任务;第二,诉愿权虽然阻止或延迟了行政执法,但正是因为行政违法,才有协会诉愿权的必要,诉愿的胜诉率说明纠正行政违法的必要性;第三,从数据可得出,环保组织并未滥用公益诉愿权利。99Griffel Alain, Das Verbandsbeschwerderecht im Brennpunkt zwischen Nutz- und Schutzinteressen, in: URP 2006 S. 109 ff.
(二)环保组织与民事诉讼
依现行瑞士法,环保组织就生态损害并无民事诉讼资格。因我国法律界就生态损害尚在讨论民事损害赔偿路径,环保组织也可对破坏生态环境者提起民事诉讼,故介绍瑞士法律界曾经提出的以侵权法处理生态损害以及赋予环保组织原告资格,可资比较。
瑞士曾开展侵权法全面修订和统一工作,征求意见草案第45d条第2款规定,如果受危害或被毁损的环境要素不是物权客体,或者权利人不采取必要措施的,则有管辖权的集体、瑞士全境或者区域性的环保组织在实际准备了相应措施或者已经采取措施并且依法有权采取措施的情况下,得请求损害赔偿。
据此,环保组织就生态损害所采取措施花费之费用得请求损害赔偿。但此规范在征求意见阶段,遭到大部分参与者的批评,其理由是,保护生态环境是政府的义务,应由其垄断采取相应措施的求偿权。100征求意见结果第176页以下,瑞士司法部网站可查(https://www.bj.admin.ch/dam/data/bj/wirtschaft/gesetzgebung/archiv/haftpflicht/ve-ber.pdf),2019年9月1日访问。环保组织的诉权应限于公益诉愿,起到监督行政的作用,不应赋予它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随着侵权法全面修订工作被放弃,生态损害主要以公法途径救济,例外是仅在制定法有明确规定的情形才可适用民事损害赔偿,且请求权人是主管的政府部门,101例如《环境保护法》第59abis条第9款;《基因技术法》第31条第2款。环保组织未被赋予请求民事损害赔偿的权利。
七、结论
瑞士法上,生态损害预防和救济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引起人们注意,公法和私法对此都给予了高度关注。瑞士《水域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环境立法迅速被制定和修改,全面贯彻“原因者付费”原则,使得生态损害问题在公法上得到及时回应。与之相反,私法的回应停留在学术讨论和零星判决中,侵权法全面修订草案虽然将生态损害纳入侵权法,但2000年才提交联邦委员会征求各界意见,时间上已经远远落后于公法的更新。在公法路径能够胜任解决生态损害问题的背景下,征求意见时各界都反对浪费立法资源再改以私法来解决生态损害问题。仅《基因技术法》以及制定该法时于该法附件4中顺带增加的《环境保护法》第59abis条,就转基因和病原体导致生态损害规定以私法路径救济。这两条也可看作是以侵权法解决生态损害思路在立法中遗留的标志。从瑞士法上也可见,生态损害问题的解决路径并非是逻辑选择的结果,更是立法资源的配置问题,瑞士公法对生态损害问题及时回应,将“原因者付费”原则贯彻落实,而私法的修订耗时太久,难以及时回应,因此在生态损害赔偿问题上,公法路径最终胜出。
与瑞士法相比,我国应对生态损害问题,公法上虽确立了“原因者付费”原则,但无可适用于行政执法的具体条款,“原因者付费”原则没有得到具体落实。借助民法典法典化的立法工作,将生态损害纳入侵权责任编予以规制,可以节省立法资源,虽则于法律体系观之并非最佳方案,但也是可以选择的方案之一。
生态环境保护涉及公共利益,应是行政机关的事,但行政机关尚有保护生态环境不周之处,故而有必要赋予环保组织提起“公益型协会诉愿”(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之资格,起到监督行政机构之作用。因而,瑞士法上赋予环保组织“公益型协会诉愿资格”,但未赋予环保组织对破坏生态环境者提起民事诉讼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