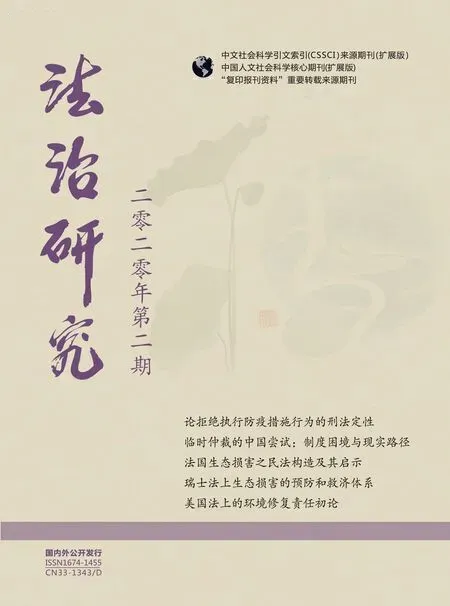论美国判决要约规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20-02-25庞晓
庞 晓
一、引言
Offer of Judgment Rule中文译为“判决要约规则”或者“合意判决”,这一概念源于美国。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规定,判决要约规则是指被告向原告发出包含具体条款的要约,如果要约被原告接受,则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交要约书或者承诺书及其送达回证,书记官可据此直接作出判决,如果要约被原告拒绝并且终局判决的结果并不比未接受的要约更好,则原告应当承担被告发出要约后所产生的费用。根据美国《学术百科全书》(Academic American Encyclopedia)的解释,判决要约规则的目的在于鼓励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以控制不必要的纠纷进入庭审。近些年,随着美国法院附设ADR功能的扩展,其已渗透到司法领域,形成了新的纠纷解决机制,同时判决要约规则与即决判决、调解、仲裁等并列成为未经审判而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不仅在理论上得到联邦法院和许多州法院的认可,而且在实务中也被当事人和律师认可。如今,美国大多数民事案件是以和解的方式结案,只有少数的案件进入庭审,而且以正式审判的案件数量成明显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美国的民事诉讼成本非常高昂,当事人为了节省诉讼成本自愿地进行和解,而且判决要约规则作为鼓励当事人达成和解的有效工具,并且规定了惩罚性赔偿,所以当事人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一方当事人自愿地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要约,另一方当事人也会谨慎地考虑是否接受要约。实践证明,美国判决要约规则奠定了它普遍适用的基础,即90%以上的案件在审前程序得到解决。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一直是学界涉猎的一个领域,学界对其存在的问题,一般主张重构诉讼和解制度、增设条文延伸诉讼和解制度以及赋予诉讼和解公法上的既判力和执行力等修改建议。学界既有的研究为诉讼和解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缺乏促进当事人达成诉讼和解的工具和惩罚性赔偿的深入研究。本文在立案登记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案件繁简分流以及“五五改革纲要”的背景下,剖析我国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在立法规范和司法实务中存在的问题,检视问题的成因,进而为提高立法者对诉讼和解制度的重视和当事人充分利用诉讼和解制度解决纠纷,提出我国应当借鉴美国判决要约规则作为辅助当事人达成和解的工具,以此来保障我国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得到承继与拓展。
二、美国判决要约规则的立法概况
美国判决要约规则作为一种未经开庭审理就能解决纠纷的主流形式,是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产生和发展到一定阶级的产物,主要表现在判决要约规则的立法发展历程、立法的具体内容以及救济属性三个方面。
(一)判决要约规则的发展历程
美国判决要约规则最早肇始于1884年《纽约州民事诉讼法典》,历经50余年的发展,后来被1938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所采纳,并将其置于第68条共4个条款。判决要约规则从颁布至今历经了1946年(1948年施行)、1966年(1966年施行)、1987年(1987年施行)、2007年(2007年施行)以及2009年(2009年施行)五次非实质性修订,修订后的判决要约规则,仍被至于《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共4个条款。“自1938年开始,各州均受到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极大影响,各州诉讼程序逐渐开始以联邦诉讼程序为主要依据”。①齐树洁:《美国民事司法制度》,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页。所以目前美国的50个州中,有28个州的《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规定了与《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内容。显然,这表明美国联邦和许多州的民事诉讼规则均规定了判决要约规则,但是也有13个州的判决要约规则与联邦判决要约规则存在明显的不同,甚至有的州将判决要约规则称之为和解要约规则(Settlement Offer Rule)。随着各州民事诉讼规则的发展和判决要约规则问题的出现,在20世纪初,大约有20个州对判决要约规则作了不同次数和不同程度的修订。
(二)判决要约规则的具体内容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用4个条款规定了判决要约规则的内容,可将其归纳为:(a)款②See Rule 68.Offer of Judgment(a) Making an offer: Judgment on an Accepted Offer.At least 14 days before the date set for trial,a party defendingagainst a claim may serve on an opposing party an offer to allow judgment on specified terms,with the costs then accrued.If,within 14 days after being served,the opposing party serves written no-tice accepting the offer,either party may then file the offer and notice of acceptance,plus proof of service.The clerk must then enter judgment.以“单边要约”③美国联邦和一些州只允许被告发出要约,但有些州认为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发出要约即“双边要约”。参见Menis E.Ketchum,Rule 68:Offer of Judgment:Should the Rule Be Bilateral or Be Abolished,3W.Va.Law26 (2012)。的方式规定了发出要约的主体只能是被告,原告不享有发出要约的权利;被告以书面形式在开庭审理前14日④在美国由于案件的审判和听审的具体日期,当事人难以提前预测,通过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五次修订,将其修订为:在审判或者听审日期确定前14日内发出要约。这改变了前四次修订后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均规定在审判开始前或者听审举行前10日内发出要约。内的任何时间可以对原告发出包含具体条款的要约;如果要约被原告接受,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书记官提交要约书或者承诺书及其送达证明以此申请作出判决,提前解决纠纷,终结诉讼。(b)款⑤See Rule 68.Offer of Judgment(b) Unaccepted Offer.Anunaccepted offer is considered with drawn,but it does not preclude a later offer.Evidence of an unaccepted offer is not admissible except in a proceeding to determine costs.规定了如果原告拒绝被告发出的要约,则视为要约被撤回,被告仍然可以在开庭审理前14日内再次对原告发出新的要约,但是未被原告接受的要约,除了可以在诉讼费用裁定程序中作为证据使用之外,未被接受的要约不能作为证据被法院采纳。(c)款⑥See Rule 68.Offer of Judgment(c)Offer after Liability is Determined.When one party’s liability to another has been determined but the extent of liability remains to be determined by further proceedings,the party held liable may make an offer of judgment.It must be served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but at least 14 days before the date set for a hearing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of liability.规定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责任确定后,⑦如果一方当事人对于对方当事人应负的责任已被陪审团裁决或者法院命令或者判决确定,但对其负责的金钱数额或者范围尚待以后继续进行的诉讼程序裁决。参见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250页;白绿铉、卞建林:《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证据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106页。责任范围仍有待进一步通过程序确定,承担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在开庭审理前14日内对另一方当事人发出要约。(d)款⑧See Rule 68.Offer of Judgment(d) Paying Costs after an Unaccepted Offer.If the judgment that the offeree finally obtains is not more favorable than the unaccepted o ffer,the offeree must pay the costs incurred after the offer was made.规定了如果要约未被受要约人接受,并且受要约人获得的终局判决并不比要约更好,要约人可以向法院提交要约书及其送达回证,法院裁决作出受要约人应当承担要约人发出要约后所产生的费用。根据文义解释,如果受要约人拒绝要约后,获得的判决赔偿数额等于要约提出的赔偿数额,则受要约人也应当承担要约人发出要约后所产生的费用。简而言之,第68条(a)款规定了发出要约的主体、形式、时间、送达、费用起算点、结案方式以及法律效力,以程序化的方式规范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b)款规定了要约被撤回的情形、发出要约的次数以及未被接受的要约是否具有可采性;(c)款规定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责任确定后,仅有承担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发出要约,这进一步体现了“单边要约”;(d)款规定了受要约人拒绝合理的要约并且终局判决的结果不比要约更好,受要约人承担制裁的方式。
(三)判决要约规则的救济属性
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立法体系,⑨《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共十一章,第一章本规则的适用范围和一种诉讼形式(SCOPE OF RULES;FORM OF ACTION);第二章诉讼开始:传唤令状、诉答文书、申请书以及命令送达(COMMENCING AN ACTION;SERVICE OF PROCESS, PLEADINGS,MOTIONS,AND ORDERS);第三章诉答文书和申请书(PLEADINGS AND MOTIONS);第四章当事人(PARTIES);第五章庭外证言与发现程序(DISCLOSURES AND DISCOVERY);第六章开庭审理(TRIALS);第七章判决(JUDGMENT);第八章临时性和终局性救济措施(PROVISIONAL AND FINAL REMEDIES);第九章特别程序(SPECIAL PROCEEDINGS);第十章地区法院及其书记官:指挥诉讼、发布命令(DISTRICT COURTS AND CLERKS:CONDUCTING BUSINESS;ISSUING ORDERS ;第十一章一般条款(GENERAL PROVISIONS)。判决要约规则被设置在第八章⑩《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八章共九节,第一节(第64条)对人或者财产的扣押(Seizing a Person or Property);第二节(第65条)禁止令(Injunctions and Restraining Orders);第三节(第65条之1)担保:对保证人的诉讼程序(Proceedings Against a Surety);第四节(第66条)财产管理人(Receivers);第五节(第67条)向法院提存(Deposit into Court);第六节(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Offer of Judgment);第七节(第69条)执行(Execution);第八节(第70条)对特定行为的判决执行(Enforcing a Judgment for a Specific Act);第九节(第71条)有利于或者不利于非当事人的执行救济(Enforcing Relief For or Against a Nonparty)。临时性和终局性救济方法(Provisional and Final Remedies)中的第六节,而第七章规定的是判决(Judgment)、第九章规定的是特别程序(Special Proceedings),第八章第五节规定的是向法院提存(Deposit into Court)、第七节规定的是执行(Execution)。这表明判决要约规则注重对当事人的直接救济及其救济措施,而非必须经过陪审员的开庭审理,也就是判决要约规则是通过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而直接救济一方当事人,如果受要约人不接受要约人发出的要约,并且终局判决的金钱数额不比要约提供的金钱数额多时,判决要约规则就发挥它的强制性惩罚作用,即发生费用转移的法律后果。简而言之,根据“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被告有可能通过将财产置于法院控制之外这样的途径来处置其财产,或者实施某些有可能使原告的救济愿望落空的行为,各州已有规定,在特定的场合下,原告可以采取某些保护性措施——一般称之为临时性救济措施——使纠纷实体问题的终局判决先搁置起来”。⑪[美]杰克·H·弗兰德泰尔、玛丽·凯·凯恩、阿瑟·R·米勒:《民事诉讼法》,夏登峻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6页。所以第八章中的对人或者财产的扣押(Seizing a Person or Property)、禁 止 令(Injunctions and Restraining Orders)、担保人的诉讼程序(Proceedings Against a Surety)、财产管理人(Receivers)以及向法院提存(Deposit into Court)均属于临时性救济措施,而判决要约规则、执行(Execution)、对特定行为的判决执行(Enforcing a Judgment for a Specific Act)以及有利于或者不利于非当事人的执行救济(Enforcing Relief For or Against a Nonparty)均属于终局性救济措施。此外,根据“当事人在诉讼中处分民事权利一般是通过处分诉讼权利来实现的。比如,当事人减少或者放弃诉讼请求,一般是通过和解、撤诉或者调解达成协议,对民事权利进行处分”。⑫常怡:《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换言之,判决要约规则属于终局性救济措施,其实质是体现了判决要约规则程序的运作对受要约人诉讼处分权的一种制约。
三、美国判决要约规则的多维功能及评价
(一)美国判决要约规则的多维功能
美国联邦判决要约规则已经有80多年的发展,许多州以此为根据并对其加以修订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一种有特色的未经开庭审理就能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不仅对当事人纠纷的解决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还满足了美国司法实务的需求。
1.判决要约规则促进了当事人达成和解并避免“旷日持久”的诉讼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是唯一一个专门用于鼓励和解的程序规则”,⑬Roy D.Simon,Rule 68 at the Crossroad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fers of Judgment and Statutory Attorney's Fees,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1984,53:889.而且“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旨在为双方当事人通过要约提供对结果的合理预测,尽早地为终结诉讼提供激励”,⑭Jay N.Varon,Promoting Settlements and Limiting Litigation Costs by Means of the Offer of Judgment:Some Suggestions for Using and Revising Rule 68,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1984,33:816.也就是“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可以鼓励当事人达成和解并避免‘旷日持久’的诉讼”,⑮Bult Teresa Rider,Use and Risky Consequences of Rule 68 Offers of Judgment,Process Litigation,2007,33:30.抑或者“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的功能重点在于鼓励和解与防止诉讼拖延”。⑯Andrea M.Alonso,Offer you Can't Refuse-A Proposal for a New State of Judgment Rule,An,New York State Bar Journal,1998, 70:36.不论学理上还是实务界均认为,鼓励和解并避免“旷日持久”的诉讼不仅是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的重要功能之一,还是其根本目的。具体而言,根据判决要约规则的内容,通过具体的程序性规定,有和解意愿的一方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14日内向对方当事人发出要约,要约很有可能被接受,进而纠纷可能无需进入庭审程序而得到解决。所以判决要约规则在于鼓励一方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发出要约,另一方当事人将会谨慎地考虑要约提出的赔偿金额,从而促进了纠纷能够在开庭审理前得到解决,即以要约的方式解决了受要约人的索赔金额,并且避免了“旷日持久”的诉讼。
2.判决要约规则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20世纪70年代后,在美国一个民事诉讼案件的全面庭审平均花费8.1天,就一方当事人而言,传唤专家证人就有2.1人。此外,美国陪审团的巨额费用、高昂的律师费以及专家证人的高报酬等,使得全面庭审的时间和金钱成本非常巨大,并且“在美国每年的诉讼费用已经涨到1000亿美元”。⑰齐树洁:《外国调解制度》,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3页。如果一方当事人根据判决要约规则对另一方当事人发出要约并达成和解,则可以有效地节省当事人的这些诉讼成本,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根据这一规则,当受要约人获得终局判决的赔偿金额低于要约所提供的赔偿金额,要约人的诉讼成本可以节省。虽然该规则只允许被告发出要约,但是合理的要约可能对双方均有利,因为如果要约被原告接受,则可以避免给任何一方当事人带来进一步的诉讼成本,除了对原告提供了较早的赔偿金,甚至有些原告可能还会得到和解补偿金。简而言之,和解符合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反之,对诉讼而言,诉讼成本昂贵并且诉讼效率低下。二,通过惩罚受要约人拒绝合理的要约来增加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动机,也就是通过要约促进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和减少诉讼成本,因为要约人发出要约后的成本通常高于要约人发出要约时产生的成本,而且第68条(d)款“费用”转移目的是惩罚受要约人拒绝合理的要约后继续进行诉讼,但是未能取得更好的结果。⑱Jonathan R.Bumgarner,Rule 68-Should Costs Incurred after the Offer of Judgment Be Included in Calculating the Judgment Finally Obtained-The So-Called Novel Issue in Roberts v.Swain,Campbell Law Review,2002,24:245.
3.判决要约规则减轻了当事人承担“费用”的负担
判决要约规则除了促进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之外,当要约人对受要约人发出比终局判决更有利的要约时,减轻了当事人承担要约发出后所产生费用的负担。假设被告以10,000美元对原告发出要约,原告不接受要约,案件审理后,陪审团对原告作出9,000美元的终局判决。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4条(d)款规定,通常胜诉的原告可以从被告那里收回所有的费用,但是根据第68条(d)款规定,原告必须承担被告发出要约后产生的所有费用,因为要约提供的赔偿金额高于终局判决的赔偿金额。通过第68条(d)款的运作,原告除了承担自己的费用(可能是几千美元)之外,还必须承担被告发出要约所产生的费用,从而导致原告获得的赔偿数额大大减少。这表明,根据第68条(d)款规定的“费用”转移,给原告施加了压力,促进原告接受要约,达成和解以解决纠纷。原告接受要约不仅可以保证获得实质性的救济,而且还避免了在被告发出要约后承担双方发生费用的风险。所以判决要约规则除了促进当事人达成和解之外,还在要约提供的金钱数额比原告的终局判决更有利时,减轻了原告承担要约后双方当事人费用的负担。
4.判决要约规则有助于防止当事人滥诉和“随意反悔”
一方面,在美国判决要约规则与和解要约规则之间有实质性不同,即判决要约规则在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后,书记官可依据任何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要约书或者承诺书及其送达回证作出判决,以判决的方式终结诉讼;而和解要约规则,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并不要求作出判决。另一方面,美国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后要想终结正在系属中的诉讼程序,当事人应当依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41条(a)款第(1)项的规定,向法院提交签署的撤销诉讼的书面协议,以此终结诉讼程序,自愿撤销诉讼通知书与应诉判决具有同等的效力,也就是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即使将其作成法庭笔录,也不具有与应诉判决同等的效力。除了当事人自愿撤销诉讼,和解协议或者和解法庭笔录均不具有与应诉判决同等的效力,可能导致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和解协议,继续进行不必要的全面庭审程序。反观,判决要约规则以判决的方式终结诉讼程序,并且该判决与应诉判决具有同等的效力,这有效地防止了当事人任意的滥用诉讼和“随意反悔”和解协议。
5.判决要约规则提高了法院的诉讼效率和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第一,“美国的和解有较清晰的事实基础,有较为广泛的高额惩罚性赔偿为后盾,所以更可能有利于权利人,并仍有较强的阻吓功能”,⑲严仁群:《“消失中的审判”?——重新认识美国的诉讼和解与诉讼调解》,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5期。而且判决要约规则规定了以判决的方式终结诉讼和拒绝要约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承担高额的惩罚性赔偿,以此保障双方当事人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这实质是减轻了法院审前程序的繁重职责(特别是疑难复杂的案件)和避免了不必要的开庭审理,进而极大地提高了法院的诉讼效率。第二,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也可能成为民事诉讼调解的有效辅助手段,例如如果当事人的调解陷入僵局,一方当事人可以发出要约,根据要约提供的赔偿金额与另一方当事人通过达成和解解决纠纷。此外,“审前程序是美国民事诉讼程序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它不仅发挥着确定争点、发现证据等庭前准备功能,如今它还发挥着无需审判而提前结束案件的功能”。⑳吴如巧:《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新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据统计,“1980-1993年,在联邦法院提出的民事案件中平均仅有4%的案件进入审判,34%的案件不经审判即告终结,55%的案件或者被撤销或者被和解,7%的案件被移送或者发回”21同注⑳,第148~149页。,而且“不经审判而终结的案件数目在近年来甚至更高”。22[美]史蒂文·苏本、玛格丽特·伍:《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从历史、文化、实务的视角》,蔡彦敏、徐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换言之,判决要约规则作为审前程序的一种,其不仅发挥着无需审判提前终结案件的重要功能,而且还具有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
(二)美国判决要约规则的评价
上述美国判决要约规则的多维功能是不可否认的,也是立法者、各级法院、当事人以及学界等对判决要约规则的肯定评价,而否定性的评价主要体现在判决要约规则的内容和和解功能两个方面。
1.对判决要约规则内容的评价
有些法院和当事人认为,由于《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规定得过于简单,该规则的定义不明确和缺乏特殊性规定,导致在司法实务中往往产生不合逻辑和不一致的解释。最常见的主要有四个:第一,原告是否可以发出要约;第二,复杂的多方诉讼中是否可以援引判决要约规则,例如集团诉讼、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第三,原告在终局判决中除了获得金钱赔偿外,是否还可以获得禁令或者其他公平性非货币的救济,23See Jay N.Varon,Promoting Settlements and Limiting Litigation Costs by Means of the Offer of Judgment:Some Suggestions for Using and Revising Rule 68,4Am.U.L.Rev,1984,4:817.例如Reiter v.MTA New York City Transit Authority案件;24See 457 F.3d 224,(2d Cir.2006).第四,第68条(d)款规定的“费用”是否包含律师费。这些不一致的解释阻碍了当事人和律师援引判决要约规则,也是他们不愿意选择使用判决要约规则解决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阐述如下文。
2.对判决要约规则和解功能的评价
“尽管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作为当事人达成和解的工具,但是它仍然经常被当事人忽视作为尽早解决索赔的一种手段”。25Merritt B.Quigley,Tips for Drafting,Accepting,Rejecting,or Simple Understanding a Rule 68 Offer,Business Torts & Unfair Competition,2014,21:20.从当事人的角度,以假设性例子说明判决要约规则可能存在使当事人不通过和解来解决纠纷。例如“在人身伤害案件中,原告对审判结果的估计有三种可能:10%的可能性没有责任,承担10,000美元的几率为50%,承担50,000美元的几率为40%。换句话说,如果原告终局判决的赔偿金额减去开庭审理的费用,超过被告要约提供的赔偿金额,则该诉讼的原告将会拒绝要约”。26Dale A.Oesterle,Proposed Rule 68 on Offers of Settlement,Cornell Law Forum,1984,10:11.从律师的角度,根据判决要约规则在司法实务中的有效性,1994年联邦司法中心对律师使用判决要约规则的调查数据显示,“有31%的原告律师和47%的辩护律师认为,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能够促进当事人达成和解;27%的原告律师和21%的辩护律师不认为,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能够使更多的案件得到解决或者帮助当事人提前解决纠纷;14%的原告律师和10%的辩护律师不确定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是否具有促进当事人达成和解的作用;甚至还有些律师认为,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对61%的和解案件和85%的审判案件没有任何影响”。27William P.Lynch,Rule 68 Offers of Judgment:Lessons from the New Mexico Experience,New Mexico LawReview,2009,39:367.这也是司法实务中,当事人和律师不主动援引判决要约规则解决纠纷的另一个原因。
四、美国判决要约规则的理论争议
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由于该规则规定得过于简单,导致立法机关、学界以及实务界对适用的案件范围、发出要约的主体、“费用”转移的情形以及“费用”的范围等产生了争议。
(一)适用的案件范围之争
根据联邦判决要约规则的规定,该规则适用于所有民事案件,也就是所有民事案件的被告均可以向原告发出要约,其中包括人身伤害案件28See Mincer Richard,Rule 68 Offer of Judgment:Sharpen the Sword for Swift Settlement,U.Mem.L.Rev,1995,4:1402.、版权案件、29See Eric M.Landslide&Henry J.Tashman,Strategic Use of Rule 68 Offers of Judgements in Copyright Litigation,Landslide,2014,4:37.侵权案件30See Maureen Malvern,The Offer of Judgment Rule in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Actions:A Fundamental Incompatibility, Golden Gate U.L.Rev,1980,3:989.等,此外“基于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的重要目的,某种特殊的案件也可以使用判决要约规则,集团诉讼作为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的例外,所以集团诉讼中当事人也可以发出要约”。31Jay N.Varon,Promoting Settlements and Limiting Litigation Costs by Means of the Offer of Judgment:Some Suggestions for Using and Revising Rule 68,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1984,33:813.但是有些州的判决要约规则与联邦判决要约规则适用的案件范围不同,例如“1972年弗罗里达州F.S.§768.585规定,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仅适用于医疗事故案件,1986年弗罗里达州的立法机关将F.S.§768.585替换为F.S.§768.79,将其判决要约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损害赔偿诉讼,无论是侵权还是合同”。32Bruce J.Berman,New Offer of Judgment Rule in Florida:What Does One Do Now,The,Florida Bar Journal,1990,64:38.1990年佛罗里达州的立法机构又提出了F.S.§45.061,F.S.§45.061和F.S.§768.79成为判决要约规则的一般性法令,“该法令规定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不适用于公司解散案件,因为这类诉讼不涉及损害赔偿,但是可以适用于集团诉讼或者股东派生诉讼,而且仅适用于当事人提起诉讼的诉因属于民事诉讼,不能用于任何行政诉讼,也不得用于任何工人赔偿案件”。33James C.Hauser,New Offer of Judgment Statute,The,Florida Bar Journal,1991,65:19.与此同时,“弗罗里达法院认为,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不适用于海事案件,至少第十一巡回法院尚未就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是否适用于海事案件作出一致的答复,因为此类案件具有特殊性,而且对律师费的规定与联邦法规存在实质性冲突,所以佛罗里达州和联邦对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是否适用于海事案件仍然可能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34Mohammad O.Jazil&David C.Miller,An Eerie Erie Question:Does Florida's Offer of Judgment Statute Apply in Maritime Cases, Florid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9,21:357~358.除了弗罗里达州对判决要约规则适用的范围作出明确之外,德克萨斯州的判决要约规则规定,“判决要约规则适用于所有民事案件,但不适用于某些特定案件,包括集团诉讼、股东派生诉讼以及其他类型的案件”。35Elaine Carlson,Offer of Settlement,Advocate State Bar of Texas,2003,24:7.显而易见,联邦和有些州不仅对判决要约规则适用的案件范围,在立法上存在明显的争议,而且对某一种具体案件是否可以适用判决要约规则也存在争议。
(二)发出要约的主体之争
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a)款规定,被告可以在所有的民事案件中发出要约,而不允许原告发出要约,如果被告在诉讼中向原告提起反诉,在这种情形下,原告是否可以发出要约,第68条(a)款未明确规定。学理上认为,发出要约的主体除了被告,如果被告对原告提起反诉,应当允许本诉的原告对反诉的原告发出要约,即本诉的原告可以对反诉的原告援引判决要约规则。36See Roy D.Simon,Rule 68 at the Crossroad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fers of Judgment and Statutory Attorney's Fees,U. Cin.L.Rev,1984,4:890;Lynn Sanders,Offers of Judgment and Rule 68:A Response to the Chief Justice,J.Marshall L.Rev,1985,2:342; William P.Lynch,Rule 68 Offers of Judgment:Lessons from the New Mexico Experience,N.M.L.Rev,2009,2:349.另一方面,由于第68条(a)款仅仅赋予被告享有发出要约的权利,导致原告通常不会选择判决要约规则来解决纠纷,为了保障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公平,许多州的《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明确允许原告发出要约。37See ARIZ.R.CIV.P.68; NEV.R.Civ.P.68;TENN R.Civ.P.68,e.g.例如1970年田纳西州的《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a)款规定,判决要约规则不仅适用于辩护索赔的一方,而且适用于起诉索赔的一方。38See David M.Smythe,Rule 68 Offers of Judgment:A Question of Costs,Tenn.B.J,1987,3:19.又如1971年新泽西州的《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a)款明确规定,任何一方均可以发出要约;1985年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修订了各自的判决要约规则,允许原告发出要约;1990年亚利桑那州修订了其规则,允许所有各方发出要约;1996年俄亥俄州咨询委员会修订其规则,允许所有当事人发出要约。39See William P.Lynch,Rule 68 Offers of Judgment:Lessons from the New Mexico Experience,N.M.L.Rev,2009,2:354.到1997年,尽管加上哥伦比亚有28个州的判决要约规则与联邦判决要约规则相同或基本相似,但有13个州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联邦判决要约规则,从那时起修订《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a)款的趋势已经加快。根据统计,现在有23个州允许所有各方发出要约,虽然现在几乎有50%的州允许原告发出要约,但是也有一些州拒绝赋予原告发出要约的权利。总之,关于发出要约的主体之争,也就是“单边要约”与“双边要约”的不同规定,导致原告承担的风险也不同。就“单边要约”而言,这种要约实质上将风险赋予原告,判决要约规则一旦被当事人、律师或者法院援用,原告要承担费用转移的风险,而被告无需承担任何风险。所以被告通常利用这种独有的优势地位,对原告发出不合理的赔偿金额的要约,目的是让原告承担费用转移的法律后果。为了避免“单边要约”不公平地赋予原告承担被告费用的风险,目前有20个州的《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a)规定了“双面要约”,即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发出要约。40See Edward F.Sherman&Christopher M.Fairman,Interplay between Mediation and Judgment Rule Sanctions,Ohio St.J.on Disp Resol,2011,2:327.
(三)“费用”转移的情形之争
1985年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表示《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d)款既不适用于被告胜诉的情形,也不适用于原告获得终局判决的赔偿数额超过要约提供的赔偿数额的情形。41See Mary A.Hackett&,Susan Anne Texany&Douglas Janacek,Rule 68:An Offer You Can't Afford toRefuse,RutgersL.Rev,1985, 2:373.也就是只有当原告获得终局判决的赔偿数额少于要约提供的赔偿数额时,第68条(d)款才能发挥它的制裁作用,但是有些州与联邦第68条(d)款规定的相反。例如“弗罗里达州的旧规则规定,只要原告获得的终局判决不如要约更有利,就会触发第68条(d)款的制裁。后来,根据弗罗里达州§768.79规定,只有当要约和终局判决之间的金钱数额超过25%的差异时,才会触发第68条(d)款的制裁”。42Bruce J.Berman,New Offer of Judgment Rule in Florida:What Does One Do Now,The,Florida Bar Journal,1990,64:38.又如得克萨斯州法院认为,如果要约未被接受并且终局判决的结果表明要约人获得高于赔偿金额10%的利益,则拒绝要约的一方当事人必须承担要约人发出要约后所产生的费用。另一方面,如果被告胜诉时却只能自己承担要约发出后所产生的费用,此时胜诉的被告被置于不利的诉讼地位。为了避免胜诉的要约人处于不利地位,有些州的判决要约规则采用“双边要约”的,大部分规定了要约人胜诉时,受要约人应当承担要约人发出要约后所产生的费用。据此可知,联邦与有些州的“费用”转移的情形存在明显的争议。
(四)多个被告对多个原告发出单一的要约之争
根据联邦判决要约规则的规定,未明确该规则是否适用于多个被告共同对多个原告提出单一的要约,导致实务中存在争议。例如在Johnston v.Penrod Drilling Co案件43See Nasco,Inc,501 U.S.32(1991).中,两个被告共同提出了要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指出,“虽然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规定得过于简单,但是这并不妨碍多个被告对多个原告共同发出单一的要约,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可以适用于多个原告起诉多个被告的民事案件,只要要约满足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多个被告也可以对多个原告发出要约,这符合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早日解决诉讼的根本和意图”。44Mincer Richard,Rule 68 Offer of Judgment:Sharpen the Sword for Swift Settlement,University of MemphisLawReview,1995,25: 1408.
如果判决要约规则适用于多个被告向多个原告发出要约的情形,将会涉及到赔偿金额是否一次性分摊的问题。这在实务中主要存在两种情形:“第一,多名被告共同对多名原告提出一次性按比例分配赔偿金额的要约。例如原告A、B、C、D共同起诉被告E、F、G、H,被告E、F、G、H对原告A、B发出解决这些当事人之间所有赔偿金额为10万美元的要约,并且该要约对原告C、D有利,这种赔偿金额的分配不以所有的原告接受要约为条件。第二,多名被告共同对多名原告提出一次性未按比例分配赔偿金额的要约。例如被告E、F、G、H对原告A、B、C、D发出解决这些当事人之间所有赔偿金额为10万美元的要约,这种赔偿金额的分配应当以所有的原告接受要约为条件”。45Craig Roecks,A Proposal to Clarify Rule 68 of the Nevada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regarding Offers of Judgment,Nevada Law Journal,2007,7:418.关于这种多个被告对多个原告提出单一的要约,虽然多名被告在没有司法异议的情形下对多名原告发出要约,但是有的法院认为这种做法不当。例如在Fairchild & Co.v.Excavation Construction案件46See 473 U.S.1,21(1985).中法院认为,多名原告因一次车祸主张不同的诉讼请求,而且判决要约规则的目的是鼓励达成和解和节省司法资源,因此如果不能解决所有索赔,被告人应当对每个原告单独发出要约。
(五)“费用”范围之争
“在美国诉讼费和律师费之间有重要的区别。法院一旦做出了判决——一旦有了胜诉的当事人——胜诉方寻求将其诉讼费(可能还有律师费)转嫁给另一方当事人。根据‘美国规则(American Rule)’,该《规则》第54条(d)款规定,胜诉方一般有权从败诉方那里收回诉讼费。然而,一般规则是无权从另一方那里收回其律师费。只有某些例外规定,法律才允许转嫁律师费”。47[美]理查德·D.弗里尔:《美国民事诉讼法》,张利民、孙国平、赵艳敏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35页。《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d)款未对“费用”的范围作出明确规定,导致立法和实务中对其存在很大争议。从起草者的角度,第68条(d)款规定的“费用”是否包含律师费,“最初联邦最高法院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的起草人不承认‘费用’包含律师费,但是美国法规的例外情形,大多数均发生在联邦法规中,起草人被认为完全了解美国法规的例外情形,律师费作为一种例外情形,应当属于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费用’的一部分”。48James S.Stephenson&William W.Kurnik,Rule 68 Offers of Judgment in Actions Arising under 42 U.S.C.Section 1983, Advocate Idaho State Bar,1986,29:22.从立法的角度,“《版权法令》允许律师费作为‘费用’的一部分,胜诉方可以收回律师费,相比之下,《专利法令》和《哈兰姆法令》明确规定律师费不属于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的‘费用’”。49EricM.Landslide&Henry J.Tashman,Strategic Use of Rule 68 Offers of Judgements in Copyright Litigation,Landslide,2014,6:38.
从法院的角度,律师费是否属于第68条(d)款规定的“费用”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在Gamlen Chemical Co.v.Dacar Chemical Products Co案件50See 57 F.Supp.574(W.D.Pen.1944).中法院认为,律师费不属于第68条(d)款规定的“费用”,特别是当原告接受了被告的要约,原告受到要约的约束,无法收回其律师费;在Sanchez v.Prudential Pizza,Inc案件51See 709 F.3d 689,692(7th Cir.2013).中法院认为,律师费被包含在第68条(d)款规定的“费用”范围之内;甚至有的法院认为,法定代理人的费用通常属于第68条(d)款规定的“费用”,例如Honea v.Crescent Ford Truck Sales,Inc案件,52See 394 F.Supp.201 U. S(E.D.Lou.1975).Perkins v.New Orleans Athletic Club案件。53See 429 F.Supp.661 U. S(E.D.Lou.1976).从学理的角度,学者们对律师费是否属于第68条(d)款规定的“费用”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例如特丽莎·瑞德认为,“律师费应当属于第68条(d)款规定的‘费用’范围”;54Teresa Rider Bult,Use and Risky Consequences of Rule 68 Offers of Judgment,Process Litigation,2007,33:28.玛丽·哈克特、苏珊·安妮以及道格拉斯·贾纳切克认为,“律师费自动转移,第68条(d)款的制裁将适用于受要约人不接受要约,并且终局判决对受要约人不比未接受的要约更有利的情形,但是为了保障实现对受要约人的公平性,可以对律师费作出限制”;55Mary A.Hackett&Susan Anne Texany&Douglas Janacek,Rule 68:An Offer You Can't Afford to Refuse,Rutgers LawReview,1985,37:399.林恩·桑德斯认为,“被告的律师费明显不属于原告拒绝要约所承担的金钱风险,将被告的律师费纳入原告拒绝要约的风险中,无疑增加了原告进一步处理诉讼的压力”56Lynn Sanders Branham,Offers of Judgment and Rule 68:A Response to the Chief Justice,John Marshall Law Review,1985, 18:358.;凯文·约翰逊认为,“《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d)款在实现其目的时缺乏有效性,因为它为解决纠纷提供的激励不足以鼓励被告发出要约,这源于第68条(d)款可能只包括最低费用而非实质性费用,例如律师费”。57Kevin,Rule 68 and the High Cost of Litigation:The Best Defense Weapon of Which You've Never Heard and Its Missed Opportunity to Promote Settlement,Charleston Law Review,2016,10:475.
从各州的角度,有些州认为当事人和律师不主动援引判决要约规则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第68条(d)款转移的“费用”太少,不足以成为当事人和律师援引该规则发出或者接受要约的根本动力。为了改变这一现状,20世纪90年代已经有9个州通过转移律师费来增加第68条(d)款的制裁。例如1994年新泽西州修订了《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d)款“费用”的范围,允许无上限的律师费作为“费用”的一部分。新泽西州在明确律师费属于“费用”的范围之后,当事人和律师通过援引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达成和解的案件逐渐增多。正如库珀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转移律师费是‘争议的避雷针’”。58WilliamP.Lynch,Rule 68 Offers of Judgment:Lessons from the New Mexico Experience,New Mexico LawReview,2009,39:369.又如德克萨斯州通过咨询委员会对《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修订,修订后的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规定,受要约人拒绝要约后“费用”的转移,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以及合理的专家费。59See Elaine Carlson,Offer of Settlement,Advocate Texas ,2003,1:7.再如“内华达州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规定,在期限内未被接受的要约被视为拒绝或者撤回,如果受要约人未能获得更有利的终局判决,则要约人可以收回要约发出后产生的诉讼费和律师费,通过支付诉讼费、律师费以及利息来惩罚拒绝要约的一方当事人”。60Shannon John,Offer of Judgement:Can the Party Ever Recover Attorneys' Fees in Federal Court,Nevada Lawyer,2016,24:12.总之,根据上文所述,美国有20个州采用“双面要约”,除了乔治亚州和伊利诺斯州之外,其他州规定了双边费用转移机制(Double sided Fee shifting),允许进行任何形式的诉讼费和律师费的转移,同时也明确了“费用”包括陪审团费、律师费以及专家证人费等。当然,有些正在打算修订判决要约规则的州认为,律师费不属于第68条(d)款规定的“费用”范围,主要原因在于律师费通常占绝大部分的诉讼成本,如果转移律师费则属于过于严厉的惩罚,而且律师费的转移是实体性转移问题,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对其修订,违反了“规则授权法”,以及律师费转移在民事诉讼中很少发挥显著的作用。61See William P.Lynch,Rule 68 Offers of Judgment:Lessons from the New Mexico Experience,J.Kan.B.Ass'n,2009,2:369.例如“密苏里州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规定,如果受要约人拒绝了要约并且终局判决的赔偿数额不比要约更有利,法院拒绝支持收回律师费或者减少此类裁判的情形”。62Jeffrey,The Effective Use of Offers of Judgment and Other Settlement Strategies in Fee-Shifting Cases,Journal of the Missouri Bar,2018,74:17.
五、美国判决要约规则对我国和解制度的启示
当前,我国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规定的过于简单,导致实务中当事人对其利用率极低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本文结合美国判决要约规则的具体内容和多维功能,从审前要约与承诺程序、诉讼费罚则制度两个方面探索解决之道。
(一)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承继
传统上,美国的民事和解制度特别发达,民众大多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而且对既有的司法制度普遍信任和满意。依赖于美国相对较高的诉讼成本,也仰仗于极为发达的高额惩罚性赔偿制度,同时还有对应的判决要约规则作为促进当事人达成和解的有效工具,因而在当事人心中,和解是一种最优的纠纷解决机制,而且很多时候,当事人和律师援引判决要约规则,以和解的方式尽早地解决纠纷。判决要约规则被立法者和各级司法机关认为,基于作为当事人达成和解的有效工具、诉讼成本低、程序简洁、减轻法院负担等优点,有助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不经过开庭审理就能得到解决,应当大力推进判决要约规则。实践证明,近些年,美国联邦和有些州对判决要约规则的修订,使得判决要约规则更向着立法者和各级司法机关希冀的方向发展。
相较于美国而言,我国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也有许多年的发展,然而在当前的法律制度中它没有得到承继和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立法仅以这一个条款规定了诉讼和解制度,而非如同两大法系国家在立法上对诉讼和解制度用较多的条款对其予以具体规定;63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代表的英国,《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36章第1条至第23条共23个条文,对和解制度的程序和法律效力作出了具体规定。参见《英国民事诉讼规则》,徐昕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196页。以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的德国、日本以及法国:《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9条第1款、第323条第1款以及《德国民法典》第779条第1款,分别对和解的辩论时间、和解协议的变更以及和解的效力作出了规定,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丁启明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6、79页;《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07页。《日本民事诉讼法典》第89条、第264条以及第265条,对和解制度的程序和效力作出了规定,参见《日本民事诉讼法典》,曹云吉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82页。《法国民事诉讼法》第829条至第844条共16个条文,对和解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参见《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173页。而且我国相关的民诉法司法解释也未对诉讼和解制度作进一步规定,甚至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案件繁简分流的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也甚少涉及诉讼和解应当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重要方式,仅有2016年《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第26条规定,鼓励当事人先行协商和解。反观,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自1991年民事诉讼法颁布以来历经两次修订,均对诉讼调解制度进行了扩张和完善。64《民事诉讼法》第9条将调解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第93~99条共9个条文,分别对调解原则、组织形式、协商方式、协议内容、调解书、不制作调解书的情形以及调解失败作出了明确规定;第194~195条对调解协议的申请与管辖、裁定与执行作出规定。除此之外,2016年《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和2017年《关于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操作规程(试行)》(法发[2017]14号)均用了较多的条款对调解制度作出具体规定。65《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共40个条文,其中大部分条文是关于健全调解制度建设、完善调解程序安排以及加强调解工作保障等的规定。例如第三部分健全制度建设,共8个条文,其中第17、18、19、20、21、23、24条共7个条文对健全调解制度建设作出规定;第四部分完善程序安排,共8个条文,其中第27~31条共5个条文对完善调解程序作出规定。《关于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操作规程(试行)》共25个条文,其中第7~18条共12个条文对调解作出规定。这表明我国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在民事诉讼立法及其司法文件中,并没有在《民事诉讼法》第50条的基础上得到承继和发展。
笼统地看,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了诉讼和解制度,除了现有的法律制度过多地强调了诉讼调解制度,并且诉讼和解制度规定得过于简单,缺乏法律效力和惩罚性赔偿的立法规定,导致实务中当事人不愿意通过以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进而也就出现了当事人对其利用率极低的问题,66从近几年学者引证的数据看,我国民事诉讼和解案件数量占法院总结案数量的较少比重,最高仅2%,最低仅0.4%,其平均值为每年1.44%。参见张嘉军《诉讼和解观与我国诉讼和解制度之重构》,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5期。而非如同诉讼调解制度的高利用率。672015年之前,在司法实务中不论法院还是当事人均青睐于利用诉讼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例如2013年全国一审民商事案件751.1万件,各级法院以调解方式处理案件479.8万件,调解率为63.9%,参见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4年全国一审民商事案件1103万件,各级法院以调解方式处理案件461.9万件,调解率为41.89%,参见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和一些列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意见,受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的影响,我国调解率略有波动。例如2016年全国一审民商事案件1076.4万件,各级法院以调解方式处理案件532.1万件,调解率为49.43%,参见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不可否认,法院和当事人通过调解结案的数量远远高于和解的结案数量,并且将诉讼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影响着当事人在实务中选择诉讼和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
第一,《民事诉讼法》第50条未规定诉讼和解制度的法律效力,导致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不能直接产生诉讼终结和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具体而言,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如果要终结诉讼,原告须向法院申请撤诉(第二审程序中达成和解以上诉人撤回上诉或者原审原告撤回起诉)或者申请法院制作调解书的方式结案。就原告申请撤诉结案方式而言,这种情形视为原告未起诉,如果被告不履行或者违反和解协议,原告又对该争议重新提起诉讼,导致以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的目的落空,也是当事人不愿意通过以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观,两大法系国家的大部分民事诉讼规则赋予了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与判决具有同等的效力。68在大陆法系国家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日本民事诉讼法典》第267条规定,和解记载于笔录时,该记载与判决具有同等的效力,参见《日本民事诉讼法典》,曹云吉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18条第1款和第492条第3款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应当记入法庭笔录,以及第750条第1款规定,和解内容记入法庭笔录的和解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依据,也就是和解内容记载于法庭笔录,该记载与判决具有同等的效力,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丁启明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110、157页。在英美法系国家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在英国如果当事人能达成和解协议,他们应该决定如何记录协议,应该考虑的是在任何一方不遵守其规定时,怎样强制执行协议。最简单的判决格式为规定立即支付约定的金额,加上往往按标准的基础计算的诉讼费用,凭这样的裁定进行的强制执行程序,能在写成的当天开始,也就是英国的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可以申请法院将和解事项记载在裁定书上,例如一方不遵守和解协议时如何执行等,通常这种裁定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执行力,参见沈达明、冀宗儒:《英国民事诉讼法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323页。在美国,虽然不采纳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那样只要把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记录在法庭笔录里就产生与判决同等效力的做法,当事人可以援引判决要约规则申请以判决的方式终结诉讼,并且该判决与应诉判决具有同等的效力,参见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111页;Michel J.Brady,Robert P.Andris,Kathryn C.Curry,Demise of the Stipulated Judgment as Basis for Bad Faith Action,Def.Counsel J,1993,1:59。
第二,《民事诉讼法》第50条未规定当事人不履行或者违反和解协议的惩罚性赔偿规定,导致当事人“随意反悔”。从民事实体法角度,我国绝大多数的民事责任属于补偿性的,即使有惩罚性赔偿的民事责任,但是因为计算的基数通常不大,导致赔偿人赔偿的数额很小,不足以对赔偿人产生威慑力和促使义务人积极地履行义务;从民事程序法角度,仅在执行程序篇中有两个法律条文规定了被执行人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但是仅以极低的罚款、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及支付迟延履行金作为惩罚性的赔偿金额,同样也不能对被执行人产生威慑力,从而导致执行人的权益仍然难以实现。相形于此,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英国,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或者不配合另一方当事人“诉前和解”(Pre-Action Protocol),法院有权对该方当事人作出支付对方高昂的诉讼费、交付对方的利息或者免除应得利息等惩罚性赔偿的命令;69参见陈杭平:《新时期下“繁简分流”的分析与展望》,载《人民法治》2016年第10期。在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判决要约规则作为当事人达成和解的一种有效工具,当受要约人拒绝要约并且终局判决的结果并不比要约更好时,应当承担对方当事人的费用,这实质是美国惩罚性赔偿的一种体现。
本文认为,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设立,其本身凸显的是一种当事人德性的回归。当事人的德性于内部而言,可以使双方当事人通过彼此之间的利益博弈和平衡,实现双方当事人不通过开庭审理就能解决纠纷的合意;与外部而言,大大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提高诉讼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机制。如果我国再不对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承继和发展,其仍然成为当事人利用极低的法院裁判的取代方式,亦或者司法政策不对其拓展和完善,均将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与2019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法发[2019]8号)的目标渐行渐远。
(二)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拓展
1.审前要约与承诺程序
在当今世界,“诉讼爆炸”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我国也不例外,尤其在2015年实行立案登记制改革以后,传统的审判机制面对日益增长的诉讼,已经超过其承载的负荷。虽然我国民事诉讼和解作为代替审判的一种方式,但是存在当事人对其利用率极低的问题,进而导致整个制度功能的弱化。美国判决要约规则曾受到质疑,也存在上述不完善之处,但是不能否定该规则促进了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节省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以及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等多维功能,并且如今它奠定了在美国促进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普遍适用的基础。所以根据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且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案件繁简分流以及“五五改革纲要”的背景下,非常有必要借鉴美国判决要约规则,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框架中设置审前要约与承诺程序。
要约与承诺程序的具体内容包括:第一,要约与承诺程序发出要约的主体。如上所述,根据美国联邦和州的判决要约规则对发出要约的主体规定不同,以及实务界和学术界对只有被告可以发出要约存在不同的观点,为了避免对原告不公平,被告在和解中占据绝对的主动权,为此应该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发出要约。第二,发出要约与承诺程序的诉讼阶段。为了改变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任何时间被当事人提出,同时防止不必要的纠纷进入审判程序和更好地利用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在审前程序中设置要约和承诺程序,并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20日内的任何时间发出要约。第三,要约与承诺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除了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案件、海事案件、人身案件以及不涉及损害赔偿的案件之外,其他民事案件均可适用要约与承诺程序。第四,要约与承诺程序的结案方式。如果要约被受要约人接受,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向法院提交要约书或者承诺书及其送达回证,法官据此作出判决,并且该判决与应诉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即赋予现行民事诉讼和解的法律效力,防止当事人滥诉和“随意反悔”。第五,要约不被接受。如果受要约人不接受要约、要约人以书面的方式撤回要约以及承诺期限届满要约未被受要约人接受也未被要约人撤回的情形,均应当属于要约被拒绝,视为要约被撤回,但是双方当事人仍然可以在开庭审理前20日内再次发出要约。未被当事人接受的要约,仅在诉讼费用裁定程序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根据“在任何的司法制度中,大多数民事诉讼程序性规则设立的目的都在于促使民事争端得到公正、高效和经济的解决”,并且“接受外国法律制度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性质的问题,而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合目的性和需要的问题(Cine Frage der Zweckmässigkeit,des Bedürfnisses)”,70[德] 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应当借鉴美国判决要约规则的积极意义并去粗取精,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修订民事诉讼法,本文建议在《民事诉讼法》第50条增加第2款和第3款:“在开庭审理前20日,除了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案件、海事案件、人身案件以及不涉及损害赔偿的案件之外,其他案件的当事人均可以向对方当事人发出包含具体条款的要约,并且开始计算诉讼费用。受要约人在要约书送达的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要约人发出接受要约的承诺书,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将要约书或者承诺书连同其送达回证一并向人民法院提交,法官以此作出判决。”“受要约人未接受要约、要约人撤回要约或者承诺期限届满要约未被受要约人接受也未被要约人撤回的情形,应当视为要约被撤回。要约被撤回后,不排除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20日内再次发出要约。未被接受的要约,除了用于诉讼费用裁定程序之外,不被人民法院采纳。”
2.诉讼费罚则制度
美国判决要约规则对当事人具有内部的制约,其源于费用转移机制,如果缺少费用转移机制,该规则可能会失去它的独特价值。虽然判决要约规则的“费用”范围和“费用”转移的情形存在争议,但是费用转移机制是对拒绝要约且获得的终局判决并不比要约更有利的一方当事人的惩罚,以赔偿另一方当事人费用的损失。根据上述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存在利用率极低的问题,缺乏惩罚性赔偿规定是其原因之一,所以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在设置审前要约与承诺程序基础之上,应当设置与之对应的诉讼费罚则制度作为保障。
根据上文所述,无论联邦还是州的判决要约规则对“费用”范围的规定不同,且律师费是否包含在“费用”范围之内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是美国民事案件全面庭审的诉讼成本非常高昂,如果受要约人的终局判决不比要约更好时,拒绝要约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承担要约人发出要约后所产生的费用,所以即便不包含律师费,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也非常高,对受要约人产生制约作用。与之相反,我国的证人、鉴定人以及专家证人等这些诉讼参与人的费用较低或者没有报酬,除了经济类案件的诉讼标的额较大之外,案件的受理费和律师费也不高。为了更好地落实审前要约和承诺程序,我国应当设置诉讼费罚则制度。
诉讼费罚则制度的具体内容包括:第一,“费用”转移的范围。诉讼费罚则制度中的“费用”范围应当包括要约人发出要约后,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法院指定期日出庭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此外还包括案件受理费和律师费。第二,“费用”转移的情形。为了避免要约人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和基于保障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价值理念,诉讼费罚则制度也应当适用于要约人胜诉和受要约人的判决赔偿数额等于要约提供的赔偿数额两种情形。当诉讼中出现这两种情形,要约人也可以追回要约发出后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第三,“费用”转移的惩罚性赔偿。诉讼费罚则制度是针对一方当事人应当通过和解就能解决纠纷而拒绝要约,并且判决的结果不比要约更有利的一种惩罚性赔偿。为了体现该制度的惩罚性,赔偿数额应当是要约人发出要约后所产生的一切费用总和的20倍。
本文建议在《民事诉讼法》第50条第2款和第3款的基础上,增加诉讼费罚则制度,作为第4个条款,即《民事诉讼法》第50条第4款:“受要约人的判决赔偿数额等于或者小于要约的赔偿数额,或者要约人胜诉,受要约人应当承担案件的受理费和律师费,或者要约人发出要约后所支出的诉讼费用、鉴定费以及专家证人费等总合的20倍。”
六、结语
本文认为,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0条诉讼和解制度的基础之上,通过设置审前要约与承诺程序、诉讼费罚则制度,可以有效地激励当事人达成和解,解决当事人对诉讼和解制度利用率极低的问题,最终影响着诉讼和解案件数量占法院总结案数量的比重。研究表明,美国作为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尽管其司法对社会有巨大的承载效应,但其纠纷的解决从来没有完全依赖于全面开庭审理,而是有一系列多元化的解决方式。犹如判决要约规则作为当事人解决纠纷一种终局性的方式,在该规则中,法院只是一个终局判决的制定者,即终局判决的内容完全由双方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通过要约达成各自的合意而决定的。有鉴于此,我国在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框架中设置审前要约与承诺程序、诉讼非罚则制度,不仅能够融于法治原理、制度和实践之中,而且又能为我国依法治国提供创新和发展的理念,实属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