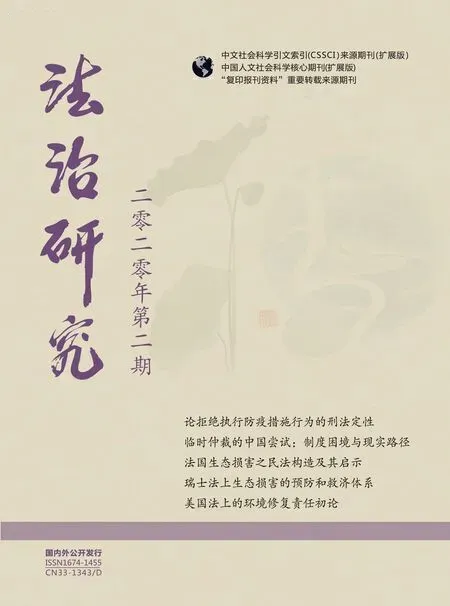临时仲裁的中国尝试:制度困境与现实路径*
——以中国自贸试验区为视角
2020-02-25李建忠
李建忠
一、引言
受我国仲裁法律文化滞后的影响,我国仲裁法对临时仲裁历来持模糊态度,并在实践中采用双重标准:即国内商事仲裁中不认可临时仲裁,但依据相关公约和双边条约有限承认外国临时仲裁裁决和双边投资争端中的临时仲裁。①我国于1986年加入了1958年《纽约公约》,并在司法实践中依据互惠原则承认和执行来自另一缔约国的临时仲裁裁决;另外,在我国与瑞典、德国、荷兰、加拿大等许多国家签署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也约定了通过临时(特设)仲裁庭(ad-hoc arbitral tribunal)解决缔约双方或投资者与缔约一方之间的争议。我国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下文简称“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区内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得临时仲裁在自贸试验区的引入成为重要议题。
为支持自贸试验区争议解决机制的创新,最高院于2016年12月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下文简称《提供司法保障意见》)。该意见第9.3条突破了我国《仲裁法》第16条要求仲裁协议必须选定仲裁委员会的规定,要求各级法院认可自贸试验区企业之间约定在“特定地点”、按照“特定仲裁规则”并由“特定人员”仲裁的仲裁协议,因而在实质上承认了临时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为响应《提供司法保障意见》对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的支持立场,并推动临时仲裁在自贸试验区的有效落实,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新区管委会和珠海仲裁委联合发布了我国的首部临时仲裁规则《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规则》(下文简称《横琴规则》);随后,中国互联网仲裁联盟②中国互联网仲裁联盟于2015年9月成立于广州,是由仲裁机构、高等院校、律师协会、仲裁员协会以及互联网技术企业等共同组成的民间组织。又发布了《中国互联网仲裁联盟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对接规则》(下文简称《联盟对接规则》),以期建立一种临时仲裁程序和裁决向机构仲裁程序和裁决转化的机制。这三份文件的出台反映了我国官方对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立场的松动和民间对自贸试验区引入临时仲裁的积极态度。但从性质和内容来看,它们都不是官方的立法文件,且存在诸多瑕疵,无法形成体系完整且具有普适性的法律制度与规则体系,也不足以支撑临时仲裁在自贸试验区的有效落实。
对于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的制度尝试,国内学者或从文本视野解读《提供司法保障意见》和《横琴规则》,并从多个维度指出了这两份文件存在的缺漏与瑕疵;③参见孙巍:《中国临时仲裁的最新发展及制度完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解读》,载《北京仲裁》2017年第3期。或以肯定的态度评析《提供司法保障意见》和《横琴规则》的现实价值,并展望了临时仲裁在我国自贸试验区发展的可能态势;④参见张建:《中国自贸区临时仲裁规则的法律构建》,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但总体而言,学界对临时仲裁的历史、临时仲裁的核心制度以及我国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引入的制度困境等基础性问题尚未做深入研究,其有关我国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的论断也并非建立在对临时仲裁制度的准确认知之上,因而无法理性回应我国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的制度构建问题。鉴于上述制度现状和理论研究的不足,本文拟从理论视野梳理欧美临时仲裁的历史,观察临时仲裁制度的核心要素,继而分析我国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的制度实践与困境,探寻我国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构建的现实路径。
二、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临时仲裁:欧美仲裁制度的传统基因与结构主体
临时仲裁(Ad-hoc arbitration)即没有仲裁机构管理仲裁程序的仲裁。⑤See Black’s Law Dictionary, 10th ed., 2014, p. 125.由于机构仲裁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且当代欧美各国的仲裁立法在体例设计上并未严格区分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因此,从仲裁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欧美各国的临时仲裁与其仲裁制度有着相同的历史轨迹,并于近代社会分化出机构仲裁,形成了今天欧美各国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交融并存的二元结构。在这个二元结构中,临时仲裁不仅是欧美现代仲裁制度的传统基因,而且在体系结构上构成了其仲裁立法的制度主体与内核,并仍然在现代商事争议解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⑥事实上,从国外学者的相关调查来看,临时仲裁在海事仲裁、网络仲裁以及小额纠纷仲裁等领域,均以其不同于机构仲裁的自主、灵活、高效、经济等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而葡萄牙和希腊甚至曾一度取消机构仲裁,将临时仲裁当作最主要的仲裁形式。参见谭兵: 《中国仲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5 年版,第68页。
(一)历史视野下的临时仲裁:欧美现代商事仲裁制度的传统基因
综观欧美商事仲裁的发展历程,在机构仲裁从传统商事仲裁中分化出来之前,⑦以私人仲裁为形式的临时仲裁向机构仲裁的分化最早出现在英国。据史料记载,1841年成立的英国利物浦棉花公会在1863年第一次草拟了一个包含仲裁条款的格式合同,该仲裁条款要求将可能发生的争议提交公会主持下的机构通过仲裁解决。利物浦棉花公会的这一做法随即得到了伦敦证券交易所、伦敦谷物贸易公会和咖啡贸易公会、德国汉堡的谷物贸易公会(1868年成立)以及德国的不莱梅棉花交易所(1871年成立)等行业组织的仿效。参见李双元、谢石松:《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1页。商事仲裁这一争议解决方式主要以私人仲裁(临时仲裁)的形式持续存在,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出各自的特定形式。
据国外学者的研究,早在古希腊的雅典就出现了在性质和功能上与现代商事仲裁类似的私人仲裁,在这些仲裁中,仲裁者通常由当事人自己选择,其审理案件的权力都受制于当事人的约定,且宣誓要公正地裁决有关案件,而当事人则通过自我约束来遵守裁决且不向法院起诉。⑧See Penny Cyclopaedia p. 252, cited from Sabra A. Jone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INN. L.REV. vol. 12, 1928, pp. 242~243.如在古代希腊辩论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反对美狄亚斯(Meidias)的辩护中,他援引的雅典法律就规定:“如果当事人就私人债务争议选择仲裁者,他们可以合法地自主选择任何人来担任。但一旦他们共同选择了仲裁者,就应当遵守他的裁决,而不得向法庭提起上诉,因为仲裁者的裁决是终局的。”⑨See Demosthenes, Ex recensione Guilielmi Dindorfii, p. 572,cited from Sabra A. Jone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INN. L. REV. vol. 12, 1928, p. 243.
古罗马时期的相关文献中也记载了仲裁员依据当事人的协议审理案件,并根据“善良和公平”标准判定向原告清偿债务的“仲裁诉讼”(arbitrariae)制度,⑩参见[意]毕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2017年校订版),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5页。而古罗马《十二铜表法》和《民法大全》等法律文献中也出现了关于仲裁者⑪古罗马《十二铜表法》第2表规定:“审理之日,如遇承审员、仲裁员或诉讼当事人患重病,或者审判涉及外国人……,则应延期审讯”;第7表规定:“土地疆界发生争执时,由长官委任仲裁员三人解决之”;第9表规定:“经长官委任的承审员或仲裁员,在执行职务中收受贿赂的,处死刑”;第12表规定:“凡以不诚实的方法取得物的占有的,由长官委任仲裁员三人处理之,如占有人败诉,应返还所得的孳息的双倍”。参见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编委会:《十二铜表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57页。和通过仲裁解决争端⑫古罗马的《民法大全》“论告示”第二编提到:“为解决争议,正如可以进行诉讼一样,也可以进行仲裁。执行了仲裁裁决的被告得以免受处罚。”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的叙述。另外,根据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第4章和第8章的记载,以当事人的协议为管辖基础,且以当事人提供的保证金作为裁决履行保障的私人仲裁更是罗马法律实践中解决争端的常用手段。⑬Rainer Luktis, The Inscription of Campomarino - Private Arbitration in Roman Times, Y.B. on Int'l Arb. 2, 2012, pp. 326-328.
中世纪的私人仲裁大约出现在14世纪前期。⑭也有学者主张欧洲11、12世纪出现的“集市法院”“行商法院”“海事法院”“城镇法院”和“领事法院”等不同形式的商事法院是一种仲裁性质的争议解决机构,因为它们具有商人自治的特殊组织形式,且在审理程序上有着迅速、非正式、公平以及不可上诉等特征。但由于这些商事法院对商事争议的管辖权并非基于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而是根据商人自治共同体的强制性要求,且在作出裁决时以商人法而非一般的公平正义原则作为依据,因此,英国学者波洛克和梅特兰(Pollock and Maitland)认为将这种争端解决程序看作商事仲裁尚缺乏充分的依据。See Earl S. Wolav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vol. 83, 1934, pp.133~138;参见[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英格兰在1347年的年鉴中就有了仲裁的记载,而瑞典则在14世纪中叶便确认了仲裁作为契约争议解决的合法形式。⑮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这一论断也可以从英国王室于1353年颁布《贸易中心法》(the Statute of the Staple)中得到印证:该法允许商事争议当事人就商人法庭和私人仲裁的裁决向大法官(chancellor)和皇家法律顾问委员会(King’council)提出上诉,以限制商事法院和私人仲裁对商事案件的垄断。⑯参见[美]布鲁斯·L·本森:《没有政府的正义:中世纪欧洲商人法庭及其现代版本》,徐昕、徐昀译,《经济法学评论》(第三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82~85页;and see Leon E. Trakman, The Law Merchant:The Evolution of Commercial Law, Fred B. Rothman& Co. 1983, pp. 26~27.而在1609年审理的维诺尔案(Vynior case)中,法官柯克勋爵(Lord Coke)也援引了1375年鉴中的案例以证明仲裁协议的可撤销原则。⑰在该案中,柯克勋爵为了阐述私人仲裁的仲裁协议可以被王室法院撤销的原则(the doctrine of revocability),援引了1375年鉴中的仲裁协议被撤销的案例。See Niall Mackay Roberts, Definitional Avoidance: Arbitration’s Common-Law Meaning and the Federal Arbitration Ac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Law Review, vol. 49, 2016, p. 1568。在随后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私人仲裁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逐渐发展成商事争议解决的重要途径。⑱See Earl S. Wolaver,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vol. 83, 1934, pp.132~146.
总体而言,中世纪欧洲的私人仲裁基本上延续和综合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私人仲裁的基本特征,并具体表现为:仲裁管辖权基于当事人的仲裁协议;仲裁者的选定基于当事人的委任;仲裁者裁决的依据是一般的公平正义原则而非法律;裁决的履行依赖于惩罚条款(penalty clauses)和履约保证金(或称违约金,penal bond);裁决具有终局效力且排除当事人向法院上诉。⑲See Niall Mackay Roberts, Definitional Avoidance: Arbitration’s Common-Law Meaning and the Federal Arbitration Ac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Law Review, vol. 49, 2016, pp. 1566~1568.
现代仲裁制度肇始于17世纪英国私人仲裁的法定化。从仲裁法立法的基本历程来看,近代欧美各主要国家的仲裁立法最早可追溯到英国议会1697年通过的仲裁法案,该法案虽然只有两个条文,但一改英国王室长期来对私人仲裁的排斥态度,首次从立法层面肯定了仲裁制度在商事争议解决中的合法地位。⑳在17世纪的英国,受1609年维诺尔案的影响,一个仲裁案件在裁决作出前,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根据“可撤回原则”(the revocability doctrine)要求撤销仲裁协议,继而拒绝接受仲裁庭的管辖。1697年英国仲裁法案不仅承认了仲裁协议的合法性,而且还肯定了仲裁协议对当事人的强制约束力,继而肯定了仲裁庭基于仲裁协议的管辖权。See Niall Mackay Roberts, Definitional Avoidance:Arbitration’s Common-Law Meaning and the Federal Arbitration Ac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Law Review, vol. 49, 2016, pp. 1573~1574;Ernest G. Lorenzen, Commercial Arbitration—International and Interstate Aspect, Yale Law Journal, vol. 43, 1934, p. 717。随后,英国国会又于1889年通过了完全取代1697年仲裁法案的第一部仲裁法(Arbitration Act 1889),该法历经1934年、1950年、1975年、1979年和1996年五次重大修立,最终形成了一个以临时仲裁为传统,兼容机构仲裁的仲裁法体系。
法国近代历史上并未制定专门的仲裁法,其以临时仲裁为主体的仲裁制度主要通过专篇方式存在于《法国民事诉讼法典》中。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1790年,国民议会就将私人仲裁确定为民商事争议解决的重要途径。21参见李乾贵、朱建军:《仲裁法学新论》,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1800年《法院组织法》第3条则规定公民有权选择将其争议交由仲裁员裁判,且仲裁员所作的裁判不受任何审查;1806年颁布《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时,该法典又进一步设立了仲裁专篇。22参见乔欣:《比较商事仲裁》,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仲裁立法在欧洲各国的普及,法国于1925年通过立法,认可仲裁条款的法律效力,同时还修订了《民事诉讼法典》中有关仲裁的法律规定。其后,1980年5月,法国又发布了关于仲裁的第80-354号法令(即《法兰西共和国仲裁法令》)对国内仲裁体系予以重构,该法令于1981年5月并入《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并对国际仲裁作出规定。法国最近一次对仲裁法的修订于2011年完成。23参见郑永南:《法国仲裁制度新发展述评》,载《东南司法评论》(2017年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70~581页。
瑞典虽然在14世纪中叶的地方法典中就将临时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方式之一,但直到1887年才制定了第一个以临时仲裁为传统的仲裁法令。1919年对1887年仲裁法令作了重要的修改,并于1929年颁布了《1929年仲裁法》和《外国仲裁条例》。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实践之后,瑞典于1999年颁布了最新的仲裁法。24同注22,第 23~24页。
德国在历史上并无专门的仲裁法立法,其允许以私人仲裁为形式的仲裁规定最早出现1756年《巴伐利亚法典》和1794年《普鲁士法典》中,但这两部法典均对仲裁施加了严格的限制,继而阻碍了仲裁制度在德意志王国的发展。德国真正将仲裁程序合法化的成文立法是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典》,该法典不仅允许当事人将可能发生的争议提交仲裁,而且还授权法院在当事人无法就仲裁员的委任达成一致时指定仲裁员,体现了立法对仲裁制度的充分支持。25See Ernest G. Lorenzen, Commercial Arbitration—International and Interstate Aspect, Yale Law Journal, vol. 43, 1934, p. 721.该法自1877年生效后,虽经历多次修订,但有关仲裁的规定变化不大,直到东德与西德统一后的1997年,才对其仲裁法作出了重大修订。
美国在整个19世纪及其之前,普通法中的仲裁制度继受了英国仲裁实践中的“可撤回原则”,认为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来排除法院的管辖权是非法的,因此,法院也无意强制当事人履行仲裁协议。法院的这种消极态度制约了仲裁的发展。但随着商业团体的壮大和仲裁案件的大量发生,美国贸易协会、美国仲裁协会和美国律师协会等民间组织于20世纪早期对源自英国普通法的“可撤回原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最终颠覆了仲裁领域的“可撤销原则”,促成了美国仲裁制度的成文化。26See Katherine Van Wezel Stone, Rustic Justice: Community and Coercion under the Federal Arbitration Act,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vol. 1999, pp. 976-984.美国仲裁法的立法主要有两个法律文件:一是美国国会于1925年制定的《联邦仲裁法》(Federal Arbitration Act,简称FAA);二是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和美国律师协会于1955年共同制定的《统一仲裁法案》(Uniform Arbitration Act,简称UAA)。1925年的《联邦仲裁法》属美国联邦法律体系,该法自实施以来至今未作重大修改。1955年《统一仲裁法案》对各州的立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目前有49个州的仲裁法立法不同程度采纳了该法的规定。公元2000年,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通过了《统一仲裁法修订本》(Revised Uniform Arbitration Act,简称RUAA),该法吸收了《联合国贸易委员会仲裁示范法》《纽约公约》和《英国仲裁法》的合理成分,对1955年《统一仲裁法案》作出了重大修订。27参见李叶丹:《美国仲裁法的新发展》,载《东南司法评论》(2010年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1~462页。
(二)比较视野下的临时仲裁:欧美仲裁法体系的主体与内核
1.临时仲裁在欧美仲裁法和相关国际法文件中的根本地位
临时仲裁作为一种商事争议解决机制虽然有着古老的历史,但作为一种法制化的争议解决机制却始于近代主权国家的仲裁立法和相关国际立法。综观近代以来的欧美各国仲裁立法和相关国际法文件,其并未刻意区分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而是在坚持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将临时仲裁作为整个仲裁法体系的主体与根基,并充分考虑立法体系对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的兼容,在特定的立法条文中融入机构仲裁的元素。基于这样的立法体系,在仲裁实践中,机构仲裁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选择,如果当事人未约定将仲裁程序交给特定的常设仲裁机构来管理,则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应归类于临时仲裁。28杨良宜、莫世杰、杨大明:《仲裁法——从1996年英国仲裁法到国际商务仲裁》,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以英国《1996年仲裁法》为例,该法虽然有110个条文,但整个体系却保持了临时仲裁的制度传统,仅在9个条文中考虑到机构仲裁的特殊性,融入了仲裁机构的特殊元素。29这9个条文包括:第4条(强制性和非强制性规定)第3款、第23条(仲裁员权力之废止)第3款(b)项、第24条(法院撤换仲裁员的权力)第2款、第44条(法院支持仲裁程序可行使之权力)第5款和第6款、第56条(仲裁庭在当事人未支付仲裁费用时扣留裁决书之权力)第6款、第59条(仲裁费用)第1款(b)项、第63条(可补偿仲裁费用)第7款、第68条(裁决异议:严重不当行为)第2款(e)项和(i)项、第74条(仲裁机构等的免责)。可见,机构仲裁在英国仲裁法的立法体系中主要体现为一些例外情形,整个立法体系兼顾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并以临时仲裁为主体的特征十分明显。
与英国仲裁法的情形类似,在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德国《民事诉讼法典》、比利时《司法法典》、瑞典《1999年仲裁法》和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等国内仲裁法立法中,以及在1958年《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1961年《国际商事仲裁欧洲公约》、1985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下文简称《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等国际法文件中,临时仲裁均以制度传统得以构成整个仲裁法体系的根基,而机构仲裁在立法表现形式上则体现为传统制度的例外。由此可见,临时仲裁作为商事仲裁制度的原初形态,目前仍然是欧美各国仲裁法和相关国际法文件的根基所在,它与机构仲裁交相融合,共同构成了欧美各国仲裁法和相关国际法文件的完整体系。
2.欧美仲裁法和相关国际法文件中临时仲裁的个性化元素
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在欧美仲裁法和相关国际法文件中并无清晰界限,而是以一种融合渗透的方式,共同构成了仲裁法的完整体系。当然,受仲裁制度历史传统的影响,其立法体例仍然延续了临时仲裁的主体地位,并在若干核心制度上体现了临时仲裁的个性化元素。
(1)仲裁协议对常设仲裁机构的回避。临时仲裁协议区别于机构仲裁协议的根本特征在于当事人无需约定争议解决的常设机构,而仅需约定仲裁员或仲裁员的指定方式。事实上,由于欧美各国将临时仲裁视作仲裁制度应有的原初形态,因此,其有关仲裁协议的规定在体例上兼顾了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这两种形式,不强求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仲裁机构。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443条规定:“仲裁条款应当指明仲裁员,或者规定指定仲裁员的方式,否则,亦无效”;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第809条第2款也规定:“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应写明指定的仲裁员或规定仲裁员的人数及仲裁员的指定方式”。上述立法条文实质上均回避了当事人对仲裁机构的约定,继而使有关仲裁协议的规定可以兼容适用于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
(2)仲裁员资质的宽松标准和协议约定。仲裁员的资质主要指国内法、仲裁规则和仲裁协议对仲裁员的国籍、法律资格和专业知识素养等所提出的必备条件。就临时仲裁而言,其对仲裁员资质的限定主要通过仲裁法设定的基本要求和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所做的特殊约定来实现。
对于仲裁员资质的基本要求,各国仲裁法一般持宽松态度,以便最大限度地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仲裁员。在具体内容的设计上,这种宽松的限定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形:一是仅要求仲裁员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如法国、瑞典、荷兰、葡萄牙、波兰等国的相关规定;二是不直接规定仲裁员的资格条件,在允许当事人约定仲裁员资质的同时要求法院尊重当事人对仲裁员资质所做的约定,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瑞士等国仲裁法的相关规定;三是以禁止少数群体的方式来限定仲裁员的资质,如意大利、韩国、比利时等国仲裁法的有关规定。30这里的少数群体主要指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破产者、被开除公职者、在职法官以及暂时被剥夺选举权者等。
在遵守仲裁法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欧美各国的仲裁法通常还允许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就仲裁员的国籍、语言、法律资格和专业认证资格等做出约定,从而实现对仲裁员资质的特殊限定。31参见[美]加里·博恩:《国际仲裁:法律与实践》,白麟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83~185页。
(3)仲裁庭组成和仲裁员选任的自主性。仲裁庭的组成规则是临时仲裁制度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其内容主要涉及仲裁庭的人数和仲裁员的选任。从欧美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临时仲裁庭的人数和仲裁员的选任或选任方法通常由当事人依法自主约定。
对于仲裁庭的人数,欧美各国的立法普遍遵循奇数原则,要求仲裁庭采用独任仲裁庭或奇数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32法国2006年《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453条和比利时1998年《司法法典》第1681条第1款均规定仲裁庭由独任仲裁员或由人数为奇数的数名仲裁员组成。虽然也有少数国家允许当事人选择偶数的仲裁员来组成仲裁庭,但此种情形下一般会要求当事人再额外委任一名仲裁员作为首席仲裁员或公断人。33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15条第2款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约定仲裁员人数为两名或其它偶数的,应理解为要求委任额外的一名仲裁员作为首席仲裁员”;1998年《比利时司法法典》第1681条第2款和法国2006年《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454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可见,偶数仲裁庭在本质上仍然是奇数仲裁庭。事实上,欧美各国严格采用偶数仲裁员的仲裁庭并不存在。
独任仲裁庭通常由一名仲裁员组成,其仲裁员的选任规则是由当事人双方在仲裁协议中共同约定一名仲裁员。奇数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通常由三名仲裁员组成,实践中,一般要求当事人先各自选任一名仲裁员,然后再由他们选任的仲裁员共同选任第三名仲裁员作为首席仲裁员。34见《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1条,德国2014年《民事诉讼法》第1034条和瑞典1999年《仲裁法》第13条。如果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没有就仲裁员的人数做出约定,各国仲裁法通常会就此做出强制性的规定:如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仲裁法均规定此种情形下仲裁庭的人数为三人,而许多普通法系国家的仲裁法则将独任仲裁庭作为替补方案。35见2014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034条第1款,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15条第3款和美国《联邦仲裁法》第5条。
对于仲裁员的选任或选任方法,《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和欧美各国的仲裁法也允许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自主选任仲裁员或约定仲裁员的指派机构。但在具体实践中,当事人疏于约定仲裁员或仲裁员的指派机构,或虽有约定却无法就仲裁员的选任或选任方法达成一致,或选任的仲裁员无法正常履职等情形十分常见,此种情形将导致仲裁庭的组成陷入僵局。为弥补当事人自主选择权无法有效落实的尴尬局面,《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和欧美各国的仲裁法一般都规定当事人一方可以申请有管辖权的法院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指定仲裁员。36见《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1条,美国《仲裁法》第3条,瑞典1999年《仲裁法》第14~17条,德国2014年《民事诉讼法》第1035条,法国2006年《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454条,日本2004年《仲裁法》第17条。
(4)仲裁庭在仲裁程序推进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在临时仲裁语境下,由于没有机构参与仲裁程序的管理,因此,整个仲裁程序的推进除了需要当事人的全力配合以外,主要依赖于仲裁庭独立自主的工作。仲裁庭在仲裁程序推进过程中的这种独立自主性奠定了它在整个仲裁程序推进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从欧美各国仲裁法和《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的相关规定来看,仲裁庭在整个仲裁程序推进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主要体现于仲裁庭在诸多重大事项上的主导作用,如对仲裁协议效力和仲裁管辖权的裁定、对程序规则的决定、对仲裁地的确定、对仲裁审理过程的控制、对仲裁裁决的作出以及对仲裁费用承担的裁定等。
(5)仲裁程序规则的自主约定。仲裁规则是仲裁机构制定或当事人自己约定的规范仲裁活动的程序规则,也是仲裁机构、仲裁员和仲裁参与人在仲裁活动中应遵守的准则。37参见宋连斌:《仲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在临时仲裁中,仲裁程序规则一般由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协议约定,如《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纽约公约》和大多数国家的仲裁法均有类似的规定。实践中,当事人可以通过自己设定仲裁程序规则或援引现成的仲裁规则(如197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下文简称《UNCITRAL仲裁规则》),来实现约定仲裁程序规则的目的。38参见[英]艾伦·雷德芬、马丁·亨特等:《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践》(第四版),林一飞、宋连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当然,当事人疏于约定仲裁程序规则的情形在实践中也十分常见,在这种情形下,仲裁程序规则的裁量权将只能由仲裁庭和仲裁员来行使。39见《纽约公约》第2条第3款、《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4条第4款d项、《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9条第2款。
(6)司法对仲裁的支持与监督。在临时仲裁中,因没有机构参与仲裁程序的管理,法院的支持与监督往往成为临时仲裁程序得以顺利推进的最后保障。从《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和欧美各国仲裁立法的实践来看,法院对临时仲裁的支持与监督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①在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或管辖权提出异议时优先作出裁定;②在当事人无法依据仲裁协议组成仲裁庭或选任仲裁员时指定仲裁员;③在当事人无法就仲裁地的指定达成协议时裁定仲裁地;④在当事人无法就仲裁员的回避与更替达成协议时作出裁定并指定仲裁员;⑤在当事人申请临时措施时提供司法支持;⑥在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时进行监督等。
除了在上述六个核心制度中体现出临时仲裁的个性化元素外,在仲裁地的约定、40临时仲裁通常由当事人约定仲裁地,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一般由仲裁庭根据案情来确定。参见《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20条、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3条、2014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043条、瑞典《1999年仲裁法》第22条、1986年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37条、2017年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76条的规定。仲裁语言的约定、41临时仲裁通常由当事人约定仲裁语言,在当事人疏于选择或无法达成协议时,一般由仲裁庭来指定,此种情形下支配整个仲裁程序的语言一般就是基础合同的语言。参见[美]加里·博恩:《国际仲裁:法律与实践》,白麟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52页、215页。仲裁员的回避与更换42临时仲裁允许当事人自主约定仲裁员的回避与更换,但在当事人没有达成协议,也没有在仲裁协议中约定仲裁庭的组成方式时,回避与更换一般由仲裁庭来决定,且在当事人对仲裁庭的决定不服时,允许当事人请求有管辖权的法院来决定仲裁员的回避与更换。参见《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3条第3款,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79条和第180条,瑞典《1999年仲裁法》第10条和第11条,比利时《司法法典》第1691条以及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35条的规定。以及仲裁费用的约定43临时仲裁允许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与仲裁庭直接约定仲裁费用事项,或通过援引《UNCITRAL仲裁规则》这类程序规则间接约定,或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形下由仲裁庭依法作出裁定等。参见 [英]艾伦·雷德芬等:《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践》(第四版),林一飞、宋连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页。等事项上均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仲裁庭的主导作用,从而体现了临时仲裁的特殊元素。
三、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尝试的文本解读:有限突破及其规则罅漏
(一)临时仲裁在我国自贸试验区的有限实践
1.《提供司法保障意见》对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协议的支持立场
201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决定,对人民法院的涉自贸试验区审判工作发布了《提供司法保障意见》,该意见第9条要求各级法院“正确认定仲裁协议效力,规范仲裁案件的司法审查”,第3款则进一步要求各级法院认可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下文简称“自贸试验区企业”)之间约定在内地特定地点、按照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有关争议进行仲裁的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且在不认可该仲裁协议效力时报请上一级法院审查,上一级法院在支持下级法院意见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由于该条款的规定并不要求当事人选定仲裁委员会,因而突破了我国《仲裁法》第16条和第18条要求仲裁协议必须选定仲裁委员会的强制性规定,被认为是为我国自贸试验区引入临时仲裁打开了制度缺口,并为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合法化提供了制度依据。
2.《横琴规则》为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的引入提供了规则指引
2017年3月,广东自贸试验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管委会和珠海仲裁委员会联合发布了《横琴规则》。作为我国内地第一部临时仲裁规则,该规则吸收了《UNCITRAL仲裁规则》和其他国家与地区临时仲裁规则的先进经验,在规则设计上体现了国际先进性与本土特色的融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为自贸实验区临时仲裁的落实提供了规则指引。该规则的核心内容包括:(1)借鉴国际国外先进经验,设计了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仲裁员选任和仲裁庭组成的规则;(2)确立了仲裁庭在仲裁程序中的核心地位,赋予了仲裁庭充分的独立自主性,并将这种独立自主性贯彻到仲裁程序的各个重要环节;(3)设计了机构介入模式,并将珠海仲裁委员会作为仲裁程序推进的最终保障;(4)拓展设计了第三方为仲裁庭提供财务管理、秘书服务、场地租赁、案卷保存、代为送达、协助保全等有偿服务的途径;(5)创新设计了临时裁决书和调解书转化为机构仲裁裁决书和调解书的途径——经珠海仲裁委员会同意确认的临时仲裁裁决书或调解书在加盖珠海仲裁委员会公章后即转化为珠海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机构仲裁裁决书或调解书。
3. 《联盟对接规则》为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的对接提供支持
2017年9月,中国互联网仲裁联盟通过了旨在对接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促进临时仲裁在中国发展的《联盟对接规则》。该规则的设计主要针对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的对接,其核心内容包括:(1)将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所有民商事合同或非合同财产纠纷的临时仲裁;(2)设定了简便灵活的仲裁庭组成规则和仲裁审理程序;(3)设计了由联盟提供办案秘书、文书送达、保全措施、庭审服务、翻译服务、调查取证、鉴定服务、专家论证等有偿服务在内的配套服务机制;(4)设计了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的程序对接机制和裁决对接与转化机制。
(二)临时仲裁在我国自贸试验区引入的制度罅漏
1.我国《仲裁法》对临时仲裁的“体系性否定”
尽管我国基于1958年《纽约公约》而承认外国临时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效力,但就我国现行国内立法而言,临时仲裁在我国仲裁法的框架内并不具有合法性,这主要体现于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根据1994年《仲裁法》第16条第2款和第18条的规定,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选定根据我国仲裁法成立的仲裁委员会。从文本上解读,该条款虽未直接否定临时仲裁在我国的合法性,但由于它要求仲裁协议必须选定仲裁机构,因而在实质上否定了无需选定仲裁机构的临时仲裁协议的合法性,继而间接否定了临时仲裁在我国国内仲裁中的合法性。
其次,从我国1994年《仲裁法》的立法体系来看,不仅第16条第2款和第18条要求仲裁协议必须选定仲裁机构,而且在仲裁庭的组成和仲裁员的选任、仲裁庭的自主权、仲裁程序规则的约定、仲裁地的选择以及司法对仲裁的支持与监督等诸多与临时仲裁相关的重要问题上,其法律条文均针对机构仲裁而设,因而体现出对临时仲裁的体系性否定。面对这种体系性的否定,即使废除《仲裁法》要求在仲裁协议中选定仲裁委员会的规定,临时仲裁在制度层面将仍然无法与《仲裁法》的其他条款实现兼容。从这样的意义上看,即使有最高人民法院《提供司法保障意见》第9.3条对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的支持立场,临时仲裁在我国自贸试验区的引入仍将面临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
2.《提供司法保障意见》第9.3条过于简单的设计缺乏可操作性
《提供司法保障意见》第9.3条的目的在于要求各级法院在处理自贸试验区企业之间的仲裁案件时,统一裁判尺度,正确认定仲裁协议的效力,规范仲裁案件的司法审查。为此目的,该条款针对符合“特定当事人”“特定仲裁地点”“特定仲裁规则”和“特定仲裁员”这四个特定要件的仲裁协议确立了肯定其效力的统一裁判尺度,并要求履行上报批复程序。由于这四个特定要件回避了仲裁委员会的选定,因而在实质上肯定了自贸试验区企业之间的临时仲裁协议的合法性。但从该款规定的具体内容来看,它尚存两个方面的重大瑕疵。
首先,该条款的规定过于简单,不足以支持临时仲裁在自贸试验区的引入。如前文所述,临时仲裁在欧美各国仲裁法中的存在是体系性的,需要在立法体系中就仲裁员的资质、仲裁庭的组成方式和仲裁员的选任、仲裁的司法支持与监督等核心问题做出技术性的安排,而《提供司法保障意见》第9.3条的规定显然捉襟见肘,无法回应临时仲裁制度的核心问题,因而也无法为临时仲裁在自贸试验区的引入提供具体的制度依据。
其次,在该条款表述的“四个特定要件”中,除了“特定当事人”和“特定地点”的内涵相对清晰外,44根据《提供司法保障意见》第9条第3款的规定,“特定当事人”即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实践中应当包括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国内企业;而“内地特定地点”的含义则应结合该意见第9条第1款的规定来看(该条针对的是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企业约定在“域外”仲裁的情形),当指相对于“域外”的内地某一个地点,而非局限于自贸试验区内,因为从理论上看,将临时仲裁协议约定的地点局限于自贸试验区的地理界限之内没有实际意义。其有关“特定仲裁规则”和“特定人员”的表述还过于模糊,难以判断其确切内涵。从临时仲裁理论和实践来看,仲裁规则可包含当事人自主约定的仲裁规则和国际社会现成的临时仲裁规则(如《UNCITRAL仲裁规则》《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仲裁规则》等)。那么“特定仲裁规则”所指为何?它是否包含当事人自主约定的仲裁规则呢?另外,该条款还将进行仲裁的人员表述为“特定人员”,但对这些“特定人员”的国籍、专业能力等资质要求却付之阙如,那么是否意味着对仲裁员没有资质要求抑或仍然需要遵守我国仲裁法有关仲裁员的资质要求呢?显然,这种模糊的表述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引发歧义甚至带来认知上的混乱。
3.《横琴规则》的普适性缺失和司法保障机制缺失
《横琴规则》的发布填补了我国临时仲裁程序规则缺失的空白,为我国自贸试验区企业间的临时仲裁提供了备选程序规则。但从《横琴规则》的制定主体和具体内容来看,它仍然存在两个不利于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发展的重要瑕疵:一是机构介入规则的地方化设计导致其普适性缺失;二是对临时仲裁诸多环节的司法支持与监督机制付之阙如。
首先,作为一个地方性的常设仲裁机构,珠海仲裁委员会在制定《横琴规则》时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在“指定仲裁员机构”“仲裁地的确定”“仲裁保全及其他临时措施的申请”“仲裁费用的确定”“仲裁员的选任”“仲裁员名册的提供”“仲裁员的回避与更换”“仲裁程序中止后的恢复”“临时仲裁裁决向机构仲裁裁决的转化”等诸多环节均将珠海仲裁委员会作为仲裁程序推进的最终保障,因而导致整个规则体系都呈现出明显的地方化特征。45见《横琴规则》第2条第3款、第6条第2款、第9条第7款、第13条第4款、第17条第2款和第3款、第20条第3款、第21条第3款和第4款、第25条第8款、第27条第2款和第3款、第40条第4款、第47条。客观地看,这种将临时仲裁规则打上地方烙印的做法很难为各自贸试验区企业所普遍认同和选用,其结果将减损规则本身的现实价值。另外,从我国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地方仲裁机构制定临时仲裁规则的做法本身就不值得提倡,因为这种渗透地方仲裁机构利益考量的规则制定有可能导致其他自贸试验区仲裁机构的仿效,甚至造成临时仲裁规则在我国各自贸试验区林立的混乱局面。46从临时仲裁规则制定的实践来看,由常设仲裁机构制定临时仲裁规则的情形尚不存在。当前国际社会最主要的临时仲裁规则主要有《UNCITRAL仲裁规则》和《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仲裁规则》,前者的制定主体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而后者的制定主体是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
其次,从欧美各国仲裁法和《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的实践来看,临时仲裁由于缺少机构对仲裁程序的管理和监督,因而在部分环节需要得到司法的支持与监督。由于我国现行《仲裁法》体系性地否定了临时仲裁的合法性,因而在现有的立法层面将无法为临时仲裁的司法支持与监督提供法律依据。这种立法上的缺失显然也将《横琴规则》的规则设计置于无法可依的困境。但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提供司法保障意见》的发布,这种困境在司法层面必然得到破解。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横琴规则》中,除了第9条有关仲裁协议和仲裁管辖权异议以及第13条有关仲裁保全和其他临时措施部分引入了司法支持与监督机制外,在仲裁庭的组成和仲裁员的选任、仲裁地的指定、仲裁员的回避与更换等其他事项上,其有关司法支持与监督的机制均付之阙如,而将仲裁程序推进的保障委之于珠海仲裁委员会。47在仲裁程序推进的最终保障规则设计上,《UNCITRAL仲裁规则》基于中立的立场仅在“指定机构的指派”和“仲裁员费用和开支的确定”等为数不多的事项上将最终保障责任交给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秘书长;而《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仲裁规则》也仅在“仲裁员的委任”和“仲裁员的更换”等个别事项上将最终保障责任交给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主席。见《UNCITRAL仲裁规则》(2010年)第6条和第41条,《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仲裁规则》 (2017年)第8条(b)款第2项、第9条(b)款、第11条以及附件五第3条和第4条(b)款第1项。
4.《联盟对接规则》部分对接机制的合法性缺失
如《联盟对接规则》第1条所述,其制定宗旨在于实现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的有效对接,因此,其有关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对接机制的设计显然是该规则的核心所在。但从该规则第五章有关对接机制的具体规定来看,它也存在两个方面的重大缺陷。
首先,根据《联盟对接规则》第21条第2款和第3款的规定,其对接案件的范围不仅包括自贸试验区企业间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提供司法保障意见》第9条规定的“四个特定要件”的案件,而且还包括非自贸试验区企业之间的临时仲裁案件。这一规定显然超越了最高人民法院《提供司法保障意见》第9条对“四个特定要件”的要求,更不符我国《仲裁法》第16条的相关规定,因而在合法性上存在重大瑕疵,并有可能在实践中导致大量非法的临时仲裁程序与裁决最终通过对接程序而获得合法的形式。
其次,根据《联盟对接规则》第21条第4款的规定,境外根据临时仲裁程序作出的裁决文书,为了便于在国内承认和执行,可以通过对接机制与国内仲裁机构对接,并最终将境外的仲裁裁决转化为国内仲裁裁决。但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83条,《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45条、第546条、第548条,《纽约公约》第5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1995)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收费及审查期限问题的规定》(1998)等法律文件的规定,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和执行应遵守我国法律规定的司法审查和报告制度。《联盟对接规则》将外国仲裁裁决转化为国内机构仲裁裁决的机制显然违反了我国的司法审查报告制度,将导致一些外国临时仲裁裁决可能避开我国针对外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报告制度,以国内机构仲裁裁决的形式得到执行。这样的转化机制无疑将扰乱我国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司法秩序,造成消极后果。
四、中国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构建的现实路径
尽管《提供司法保障意见》《横琴规则》和《联盟对接规则》为自贸试验区突破当前的制度瓶颈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面对我国《仲裁法》对临时仲裁的体系性否定,以及《提供司法保障意见》过于简单的规定、《横琴规则》的普适性缺失和《联盟对接规则》的合法性缺失,任何停留在技术层面的、细枝末节的修补都将无济于事。客观面对自贸试验区对临时仲裁的实践需求,理性看待当前我国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的制度罅漏,相关职能部门应当立足长远,借鉴《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UNCITRAL仲裁规则》以及欧美各国仲裁立法的成功经验,分别从暂停《仲裁法》第16条和第18条在自贸试验区的适用、制定普遍适用于各自贸试验区的临时仲裁规则以及全面推进《仲裁法》的改革这三个层面有序推进,最终构建一个理念先进、体系完整、规则精细的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体系。
(一)暂停《仲裁法》第16条和第18条在自贸试验区的适用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提供司法保障意见》第9.3条以“四个特定要件”的要求表明了其对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的变通立场和支持态度,但从该意见的法律性质来看,它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内部的指导性文件而非司法解释,仅对法院系统的审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并不具备普遍效力。48根据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6条规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由此可见,我国自贸试验区的临时仲裁制度要想获得合法地位,还需要得到相关法律的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15年修正)》第8条第10款的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只能通过制定法律的方式来确立,因此,我国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的确立最终还是要得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活动的支持。
从全国人大对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可能采用的立法支持形式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启动《仲裁法》修订程序,系统修改《仲裁法》并直接引入临时仲裁制度,继而为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提供法律依据;二是以我国《立法法》第13条为依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自贸区内暂停适用《仲裁法》第16条、第18条中“仲裁协议应当具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规定,继而采用变通承认的方式认可临时仲裁在自贸试验区的合法性。49也有学者提出第三种途径,即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自贸试验区就临时仲裁进行特别立法。参见曹晓路、王崇敏:《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临时仲裁机制创新研究》,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3期;姜雪梅:《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研究》,载《实事求是》2018年第2期;赖震平:《我国商事仲裁制度的阙如——以临时仲裁在上海自贸区的试构建为视角》,载《河北法学》2015年第2期。但从我国《立法法》第8条和第9条的规定来看,仲裁制度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专属立法权的绝对保留事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能授权其他机关立法。参见张超汉、丁同民:《我国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的意义及路径》,载《中州学刊》2018年第8期。
从我国当前仲裁制度的现状和我国仲裁行业的发展态势来看,系统修改《仲裁法》并植入临时仲裁制度的方式不仅缺乏必要的现实基础,如仲裁员素质整体偏低、法治环境还有待优化等,而且也很难得到仲裁机构的普遍支持,因而在短期内很难推进。与系统修改《仲裁法》相比,采用在自贸试验区暂停适用《仲裁法》第16条和第18条的方式不仅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而且更加符合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局部试点的特殊需求和整体立法特点,因而更具科学性和现实可行性。50参见张超汉、丁同民:《我国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的意义及路径》,载《中州学刊》2018年第8期。
当然,与最高人民法院《提供司法保障意见》第9.3条有关“四个特定要件”的简单规定一样,在自贸试验区暂停适用《仲裁法》第16条和第18条本身并不足以支撑临时仲裁制度在自贸试验区的真正确立,要真正实现临时仲裁在自贸试验区的引入,系统完整且能普遍适用于各自贸试验区的临时仲裁规则亟待构建。
(二)制定理念先进且普遍适用于各自贸试验区的临时仲裁规则
尽管《横琴规则》和《联盟对接规则》的发布给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的引入提供了备选规则和对接机制,但正如上文所述,这两个规则均存在重大瑕疵,对临时仲裁制度在各自贸试验区的引入并不具有全局意义。有鉴于此,为了响应最高人民法院在《提供司法保障意见》对临时仲裁的支持立场,我国应借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UNCITRAL仲裁规则》的机制和模式,充分借鉴《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等仲裁规则的先进经验,由商务部会同并委托中国国际商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51中国国际商会是由中国经济贸易界有代表性的人士、企业和团体组成的全国民间对外经济贸易组织,在中国经济贸易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由其制定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规则更有利于确保该临时仲裁规则的中立性及其在各自贸试验区的普适性。制定立场中立且普遍适用于各自贸试验区的临时仲裁规则,以呼应最高人民法院支持临时仲裁的立场,并遏止各自贸试验区所在地仲裁机构各自为阵,竞相制定临时仲裁规则的可能趋势。
(三)借鉴《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和境外仲裁法的合理经验,系统推进临时仲裁制度的植入
要彻底解决临时仲裁制度在我国自贸试验区的合法性和科学性问题,最理想的路径是全面推进我国《仲裁法》的改革,在《仲裁法》的体系结构中系统植入临时仲裁制度。具言之,应在借鉴《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和境外仲裁法合理经验的基础上,从如下几个方面改革现有的规定,最终建立一个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有机兼容的制度体系。
1.废除《仲裁法》第16条和第18条有关仲裁协议必需选定仲裁委员会的规定,从制度根源上消除妨碍临时仲裁制度植入的障碍;
2.确立仲裁庭独立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将仲裁机构对仲裁程序的支持与监管限定在机构仲裁范围以及当事人委任仲裁机构作为仲裁员指定机构的范围;
3.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从国籍、法律能力、法律资格和专业素养方面限定仲裁员的资质,确立统一适用于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国内仲裁和涉外仲裁的仲裁员资质标准,并增加当事人协议约定仲裁员资格的机制;
4.建立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且兼顾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的仲裁庭组成机制、仲裁员选任机制和仲裁员回避与更换机制;
5.在仲裁程序规则的自主约定、仲裁地的自主选择与依法指定以及仲裁语言的自主约定、仲裁费用的规定等事项上建立统一适用于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的兼容机制;
6.在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员的选任、仲裁员的回避与更替、仲裁地的确定、仲裁临时措施的申请与实施、仲裁裁决的撤销、仲裁裁决的执行和不予承认与执行等环节剔除仅适用于机构仲裁的规定,建立兼顾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且弱化司法干预的有限司法保障机制。52我国《仲裁法》现有的司法支持与监督机制专门针对机构仲裁而设。总体而言,该机制对仲裁的司法干预过多,不利于仲裁的独立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