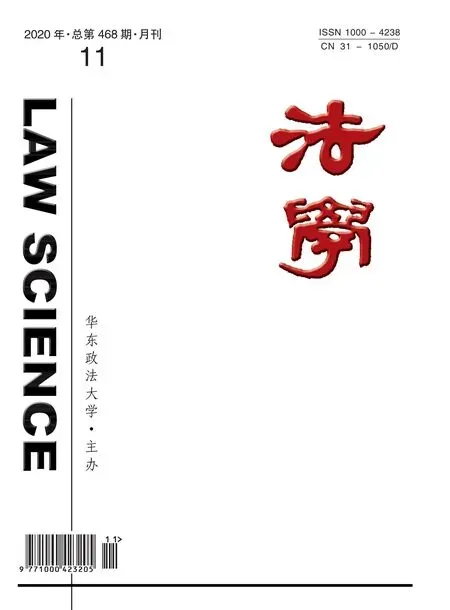秦律:中国“第一”律
2020-02-25闫晓君
闫晓君
秦文化落后于东方六国,东方国家应该先有统一中国的资格,但秦国后来居上,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秦祚虽短,但秦的制度文明影响深远,“百代皆行秦政法”。秦律体现出了巨大的创制精神,它的制定是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大事件,而秦律又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律两千余年,表现出“后有来者”的历史功绩。对于秦律的特点及历史影响,学术界虽有研究,但大多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如刘海年认为秦律除具有一般封建法律的共同特征之外,还有许多特点,如“法的形式多样,条目繁杂”;“在经济领域广泛适用法律”;“刑罚种类多,手段残酷”;“鼓励奴隶解放,又肯定大量奴隶制残余”〔1〕刘海年:《云梦秦简的发现与秦律研究》,载《法学研究》1982 年第1期。。林剑鸣认为秦律“法网严密,条目繁杂”,但法典化程度较低,“较之唐律,在系统、严密和统一方面都有相当距离”;适用“轻罪重刑”和严刑酷罚,“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最为突出、最为野蛮的,表现了封建刑法初期的特点”;在断狱方面,儒家思想影响较小。〔2〕参见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127-129 页。台湾学者吴福助在《嬴秦法律的特质探析》中论列了秦律的十个特点〔3〕参见吴福助:《睡虎地秦简论考》,文津出版社1994 年版,第3-24 页。。除此之外,学界鲜见对秦律特点及基于此对其历史地位或影响的系统性论述。本文将秦律放在中国法律通史的大背景下,将“得古今之平”的《唐律》作为传统成熟律典的标本,通过秦律与《唐律》的比较,从秦律的创制、秦律的立法技术、秦律的司法体系以及秦律的不足之处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重新审视秦律的历史地位,认为秦律为“中国第一律”。〔4〕张金光在《秦制研究》的“自序”中提出“重估秦文化的历史地位”,他说“关于秦,至少可以总结为九个根本方面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具有长期的作用和几乎永久性的意义,也可以说是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造就的九个开创性的‘第一’,以为后世长期效法。”详见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11 页。
一、秦律由秦人的部落习惯风俗发展而来
秦律虽是商鞅变法的产物,但它根植于秦文化,是对秦人早期习惯“移风易俗”的结果,而秦律作为西方后起诸侯国的法律,助推了秦统一,并一跃而成为“大一统”秦帝国的法律。汉朝建立,萧何“捃摭秦律”制定了汉律,而汉以后历代法律都是对前朝法律的继承,并形成了中华法律的“律统”,而真正起奠基作用的秦律是从秦文化中生长起来的“第一律”。
(一)秦律根植于秦人的早期习惯及风俗
《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呑之,生子大业。”〔5〕《史记正义》引《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蒙文通在《秦之社会》中:“《春秋左氏传·文五年》言:‘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使秦系出柏翳,则臧孙辰不应于秦时尚强,而曰庭坚不祀。文四年,楚人灭江,秦伯为之降服出次,曰:‘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江、黄皆雇嬴姓,春秋之时,同姓为重,秦伯于江不曰同姓而曰同盟,是秦非皋陶之胤,左氏有其说也。太史公徒以秦之嬴姓,遂以为伯益、仲衍之后,乃于仲衍至仲滴之世系不能言,又不纪戎胥轩事,于是秦为西戎之说,遂由史迁而泯。”见氏著《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 年版,第215 页。周孝王时,秦人先祖“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6〕《史记》卷5《秦本纪》。秦人早期生活于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又“迫近戎狄”,过着游牧生活,“以射猎为先”,不同于周的农耕生活。孟德斯鸠曾说:“法律和各民族谋生的方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7〕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2002 年版,第284 页。“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8〕同上注。秦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及生活方式,使秦人形成了以游牧、狩猎为主的生活方式,习俗与西戎无异,“民淳法简”。
秦人的早期风俗习惯是自然塑造的“生存法则”,有其内在合理性,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如不遵守,可能给部落带来灭顶之灾。《法律答问》中“者(诸)侯客来者,以火炎其衡厄(轭)。炎之可(何)?当者(诸)侯不治骚马,骚马虫皆丽衡厄(轭)鞅韅辕靷,是以炎之。”〔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 年版,第228 页。长期的游牧生活使他们对养马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们意识到寄生虫对牛马的危害,并通过火燎的办法予以解决,这应该是秦人的生活经验上升成为法律。
《公车司马猎律》:“射虎车二乘为曹。虎未越泛藓,从之,虎环(还),赀一甲。虎失(佚),不得,车赀一甲。虎欲犯,徒出射之,弗得,赀一甲。”“豹旞(遂),不得,赀一盾。”〔10〕同上注,第140 页。参见曹旅宁:《从秦简<公车司马猎律>看秦律的历史渊源》,见《秦律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9-33 页。这显然是秦人狩猎活动中形成的纪律,也是一种生活常识,并一直被遵守。此外,秦人还有一些所谓的“戎翟之教”,如“父子无别,同室而居”等〔11〕《史记》卷68《商君列传》。,这种不同于周人“男女有别”的习俗直到商鞅变法时才被禁革。
秦人在立国前的诉讼习惯则体现了“人定法”的特征,采用公室贵族与其他贵族进行司法分权而共治的原则。《法律答问》抄录了秦人早期的诉讼习惯:“‘公室告’【何】殹(也)?‘非公室告’可(何)殹(也)?贼杀伤、盗它人为‘公室’;子盗父母,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12〕同前注〔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书,第195 页。春秋战国时期,“公室”与“私门”相对应,这里“公室”指秦国的公族,非“公室”的其他贵族家庭中发生的“子盗父母,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则不必劳烦“公室”,所谓“非公室告”就是不必告于公室,“公室”领主也不受理,实际上承认了贵族家庭中家长的权威,家长族长在家族纠纷中享有完全的权力。“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告【者】罪已行,它人有(又)袭其告之,亦不当听。”〔13〕同上注,第196 页。不同家族之间的“贼杀伤、盗它人”则非家长所能处理,故必告于公室,即为“公室告”。秦的这种诉讼传统当是在其部落时代形成的。商鞅变法后,秦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以齐民编户为基础的郡县制逐渐形成,“公室告”与“非公室告”这种部落残余的诉讼传统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擅杀子,黥为城旦舂”〔14〕同上注,第181 页。,已列入罪名加以禁止,诉讼全由“公室”所指代的国家来受理。〔15〕参见[日]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189 页。如正如李斯所谓“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彊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16〕《史记》卷87《李斯列传》。
(二)秦国“改法为律”,首创了律这种成文法律形式
平王东迁,秦襄公领兵护送,遂被赐以岐西之地,并约定:“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17〕《史记》卷5《秦本纪》。“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即营邑之”。〔18〕同上注。秦人开始以农耕为生活方式,但长时间内仍保留其游猎放牧传统。秦人从游牧过渡到农业,法律成了生活所必需。事实上,秦人立国后就开始设立国家的各种典章制度,如“为鄜畤,用三牢”,如“初有史以纪事”〔19〕同上注。,如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20〕同上注。,武公三年依此法“诛三父等而夷三族”〔21〕同上注。。穆公时,对食善马之三百多野人由“吏逐得,欲法之”等,都说明秦国开始明确立法,并以法律御众。
秦国早期法律除了由秦人早期习惯如生活经验、生产纪律等转化而来(如前所述)之外,还有一些就是进入周人故地后承袭了周人的一些礼俗文化,如祭礼、谥法等。〔22〕据传谥法为周公所作。秦国从襄公立国就开始使用谥法,后来被秦始皇废止。《史记·秦始皇本纪》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谧。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秦穆公时居然以中国自居。戎王派遣由余出使秦国,秦穆公以宫室、积聚相夸示,并问由余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23〕同前注〔18〕。
秦公镈铭:“丕显朕皇祖受天命,肇有下国,十又二公,不坠在下”,又说“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睿專(敷)明井(刑),虔敬朕祀”云云,〔24〕王沛认为“从法理角度而言,在春秋时代,秦人对周人的传统不断加以继承和改造。天命、德、布明刑,这三要素都来自周人传统,但其内涵却发生了变化:原本是周文王、武王受天命,但在春秋早期时就已成了秦的先公受天命;原来是周先王作明刑,到春秋后期转变成为秦的现任国君作明刑。对秉持明德的宣扬,则一如周人之旧。诸侯言受天命,实为僭越之举。”《早期秦立法中的周与西戎》,见王沛主编:《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六辑),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毛诗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郑笺》曰:“秦处周之旧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魏源云:“襄公初有岐西之地,以戎俗变周民也。豳、邰皆公刘太王遗民,久习礼教,一旦为秦所有,不以周道变戎俗,反以戎俗变周民,如苍苍之葭,肃杀之政行,忠厚之风尽。盖谓非此无以自强于戎狄。不知自强之道在于求贤,其时故都遗老隐居薮泽,文武之道。未坠在人,特时君尚诈力,则贤人不至,故求治逆而难;尚德怀则贤人来辅,故求洽顺而易,溯洄不如溯游也。襄公急霸西戎,不遑礼教,流至春秋,诸侯终以夷狄摈秦,故诗人兴霜露焉。”〔25〕[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吴格点校,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448 页。
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实质上是秦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移风易俗”,是对秦人旧俗、旧礼、旧法的一次彻底改造。蒙文通认为“古今言者,胥以为商君变秦,为废仁义而即暴戾,若由文而退之野。是岂知商君之为缘饰秦人戎狄之旧俗,而使渐进于华夏之文耶?凡商君之法,多袭秦旧,而非商君之自我作古。”〔26〕蒙文通:《秦之社会》,见氏著《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 年版,第237 页。“秦之文化,为独立之文化,不同中夏,商君固自依其旧制而增饰之耳。是鞅之变秦,非由文而退之野,实由野而进之文。”〔27〕同上注,第238 页。
其主要内容是“耕战”,即“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耕稼”意味着彻底放弃以往的狩猎、游牧等落后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以较先进的农业“耕稼”为主要生活方式。“废井田,开阡陌”就是对旧有土地制度的改造和创新,使秦国的耕稼更具活力。从出土竹简《为田律》《龙岗秦简》上都可以看出来,这些做法非秦之旧俗,亦非周的传统,自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如“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28〕同前注〔18〕。
商鞅变法对家庭结构及家族制度进行了很大的更新和规制,除了“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使个体家族从父家长大家族中脱颖而出以外,也取消了“公室”公族及宗法族长的特权,如“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父亲对子女、奴婢的人身权利进一步受到限制,如《法律答问》:“‘擅杀子,黥为城旦舂。其子新生而有怪物其身及不全而杀之,勿罪。’今生子,子身全殹(也),毋(无)怪物,直以多子故,不欲其生,即弗举而杀之,可(何)论?为杀子。”〔29〕同前注〔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书,第181 页。“士五(伍)甲毋(无)子,其弟子以为后,与同居,而擅杀之,当弃市。”〔30〕同上注,第181-182 页。“擅杀、刑、髡其后子,谳之。”〔31〕同上注,第182 页。自然对于此类诉讼也无所谓“公室告”与“非公室告”的区别和相关限制。
商鞅变法也使急功近利的法家思想成了秦文化的主色调。众所周知,法家人物非秦地出生,其思想及文化亦非秦之本土文化。但从商鞅变法开始,法家对原有秦国法律进行了改造,法家思想成了秦律的主导思想。
《唐律疏议》:“魏文侯师于里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授,改法为律。”〔32〕[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2 页。《晋书·刑法志》也有类似说法:“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於盗贼,故其律始於《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这次变法是一次彻底的社会变革,使秦国法律制度焕然一新,也使秦的国力充分体现了后发优势。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改法为律”。〔33〕祝总斌在《关于我国古代的“改法为律”问题》一文中认为商鞅本人并没有改法为律,因为从商鞅著作、同时期兵家、儒家著作及其他著作中全都找不到法律意上的“律”字,其他各国也没有改法为律,因此商鞅改法为律的说法不可信。但他无可否认四川青川出土的秦武王二年的《为田律》、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魏户律》《奔命律》以及大量的秦律律名,于是祝总斌将法律之“律”字开始使用的上限定为仅比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魏户律、奔命律早几年而已。载《北京大学学报》1992 年第2 期,亦见于氏著《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 年版。实际上,祝总斌用战国文献上出现“律”字进行统计分析,看似严密,实际上并不可靠。笔者倒是赞同张建国的观点,秦武王二年(前309 年)更修《为田律》,说明之前已有《为田律》,而商鞅变法时又“为田开阡陌”,丞相甘茂于武王二年的更修《为田律》距商鞅在世相隔不到30 年,说明商鞅变法时很可能已制定了“为田律”,张建国:《中国律令法体系概论》,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 年第5 期。又见氏著《帝制时代的中国法》,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
综上,秦国法是秦律成长的重要阶段,在秦人习惯法的基础上,继承了西周的礼法文化,商鞅变法又借鉴了魏晋的法家文化,在厉行法治的司法实践中,将秦律焠炼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法律。
(三)秦朝统一,使秦律成为统一帝国的律法
在秦统一之前,秦的政治精英已做了政治思想上的准备,如吕不韦早就主张“必同法令,斦以一心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34〕《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随着不断扩张,秦军铁蹄所踏之处无不纳入帝国版图,秦的法吏和法律也随之而来。沈家本说:“春秋战国之时,诸侯各自为法令,势难统一。秦并天下,改封建为郡县,法令遂由一统,必有统一法令之书”。〔35〕[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2 册,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948 页。《睡虎地秦墓竹简》在楚国故地发现,本身就说明秦吏带来的秦律已然取代了楚国的法律。以南郡守腾和墓主人“喜”为代表的秦国官员法吏正忙于颁布法律令及贯彻执行的文告,改变楚国的故有法律及其顽固的风俗习惯。
秦统一后,需要整齐文化风俗,在推行统一度量衡、文字的“书同文、车同轨”政策的同时,也推行“法令由一统”的法律文化的统一,打破法律文化上的彼此疆界。秦始皇巡视全国留的大量刻石,很能说明问题。《泰山刻石》:“皇帝临位,作制明法。”《琅邪刻石》:“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芝罘刻石》:“大圣作治,建定法度。”《会稽刻石》:“秦圣临国,始定刑名。”〔36〕《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实际上,当时的统治者对在原六国故土推行秦律所遇到的阻力有充分的预估和思想准备,并采取了强有力的对策。如南郡守腾发布的文书说:“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说明他意识到推行秦法政的阻力来源于不同的习俗和文化。面对“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泆)之民不止”及“今法律令已布,闻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37〕同前注〔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书,第15 页。的情形,南郡守腾采用了高压的手段,并加大执行的力度,“今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38〕同前注〔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书,第16 页。,就是不断派人巡查,并追究地方官的法律责任。
随着六国的扫灭,六国的文字文化、度量衡、法律等制度已为历史的陈迹。在秦吏的大力推行下,秦律已然由诸侯国的地域性法律演化为大一统王朝的法律。综上,秦律是中华法系的第一部律,具有原发性。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律实际上都是对前一王朝成型法律的继承,而秦律是则从秦人的本土文化中破土而出,茁壮成长起来的。秦人立国后,秦人的习惯法开始成文化,并先后吸收了周人的礼法文化以及三晋地区的法文化,并改法为律,成为当时最先进的法文化。在一统天下的过程中,由地方性的法律转化为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的法律。
二、秦律首创了系统的律法名词、术语及原则
秦作为新兴民族崛起于西方,其文化虽落后于关东六国,但秦人在东向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和学习先进文化,而又不完全照搬照抄,在其本土文化的基础上,从实用和功利的角度出发,将这些先进文化熔铸成为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律是秦文化的底色和亮点,在秦的立法层面,体现出了极大的创制精神,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秦律创制了较系统的法律名词术语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相当一部分内容通过自设问答的形式,对于法律名词、术语进行解释。名词与术语出现,说明秦的法律语言已不同于一般语言,有些名词术语从字面上已不能识别其精确的义项,故须做出义界的说明。“术语必须有明确的定义来确定它内涵、外延,术语还应当是统一的、固定的、意义单一的。”〔39〕陆宗达:《训诂学的复生、发展字训诂方法的科学化》,见氏著《训诂学方法论》,中华书局2018 年版,第14 页。专业术语的出现,显然是为了法律规定的严谨严密,为了更精准地表达法律条文的意蕴。名词术语具有的特殊性和专业性,也说明了秦律的发育程度。
《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见的名词、专业术语很多,当然不是秦律名词、术语的全部。根据其对后世的影响,也就是流传时间的长短,可细分为三类:第一类随秦律消亡而灭失,仅见于秦律文献,如 “州告”“公室告”“非公室告”等,典籍文献中也难见踪迹,故整理小组的专家在对这些术语进行注解时,很难从传世文献中找到近似的用例,其对后世律的影响微不足道。第二类名词术语被汉律继承,如“城旦舂”“鬼薪白粲”“三环”等,汉以后法律中亦不多见。第三类,有些名词术语传承很久,一直沿用到明清律。通过分析这些名词术语,可以看出秦律对中国传统律的贡献和成就。传承愈久,当然其历史影响就愈大。下面依重要程度来论列:
“同居”一词,最早应见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共有九处之多。整理小组注引《汉书·惠帝纪》:“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颜师古注:“同居,谓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见与同居业者。”〔40〕《汉书》卷2《惠帝纪》。清末沈家本作《同居考》,认为“同居”二字始见于惠帝此诏,为《汉律》之名词,“汉人如何解释,已不可考”〔41〕同前注〔35〕,沈家本书,第1325 页。。可见,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的限制,连沈家本这样的律学大家亦不知“同居”一词为秦律所创。“同居”一词在秦律中自有特定含义,不能任意解读。《法律答问》:“可(何)谓‘同居’?户为‘同居’,坐隶,隶不坐户谓殹(也)。”〔42〕同前注〔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书,第160 页。“可(何)谓‘室人’?可(何)谓‘同居’?‘同居’,独户母之谓殹(也)。‘室人’者,一室,尽当坐罪人之谓殹(也)。”〔43〕同上注,第238 页。
秦律“同居”一词,虽然界定的是人与人的一种法律关系,但往往涉及罪与非罪及是否要负连带法律责任等重要法律问题。如“盗及者(诸)它罪,同居所当坐”,就是说盗犯的同居应连坐,不同居则否。如“父子同居,杀伤父臣妾、畜产及盗之,父已死,或告,勿听,是胃(谓)‘家罪’”,是说在父子同居的情况下,以上行为构成特殊的“家罪”,从轻或免罪。如不同居,则为一般犯罪。“人奴妾盗其主之父母,为盗主,且不为?同居者为盗主,不同居不为盗主”,如与主人父母同居,奴妾盗主人的父母即是盗主,不同居则不构成此罪。
“同居”一词,汉律不仅沿用,由唐宋到明清的法律都在使用这一名词。沈家本曾对颜师古“同居”注颇有微词,认为他身为唐人而不本《唐律》为说:“漫云同籍同财,《疏议》明言同居不限籍之同异,岂得以同籍为同居之限哉?自当以《疏议》之说为断。”〔44〕同前注〔35〕,沈家本书,第1325 页。历代律典虽沿用“同居”一词,但如何界定与如何使用,当微有不同。
(二)秦王朝创制的一些刑罚原则一直为后世所沿袭
《唐律》中有《名例律》,属于定罪量刑的通则,这些原则大都是从唐以前各代法律中继承而来,学界先贤都曾经指出过,如沈家本、徐朝阳等。《睡虎地秦墓竹简》发现后,也有学者指出有些通则是从秦律中沿袭而来,如日本学者堀毅在《唐律溯源考》一文中,认为唐律“二罪从重”的通则在秦律中已经确立〔45〕[日]堀毅:《唐律溯源考—以秦律中“一人有数罪”的规定为中心所作的考察》,见氏著《秦汉法制史论考》,法律出版社1988 年版。。
实际上,关于“犯罪自首”的规定亦当为秦律所确立。《汉书·衡山王赐传》:“闻律先自告,除其罪。”沈家本认为“此《汉律》也,可见此法甚古。汉世必有所承”。〔46〕同前注〔35〕,沈家本书,第1803 页。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可知,汉律之规定当承袭自秦律。《书康诰》:“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蔡传:“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过误,出于不幸,偶尔如此,既自称道,尽输其情,不敢隐匿,罪虽大时,乃不可杀,《舜典》所谓宥过无大也。诸葛孔明治蜀,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其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之意欤?”
“反坐”之法,在《唐律》中主要适用于“诬告”类犯罪。所谓反坐,是一种坐罪方法,即“反坐致罪,准前人入罪法。至死,而前人未决者,听减一等。”〔47〕同前注〔32〕,刘俊文点校书,第428 页。
诬告罪名最早见于秦律,称为“诬人”,汉律称“诬告”,宣帝元康四年规定“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佗皆勿坐。”沈家本认为“诬告为害人之计划,汉法重之,即八十以上之人亦不在勿坐之列”。虽然秦汉律中未见“诬告反坐”的明文,但可以推测“诬告反坐”的法律原则最早见于秦律。
“诬告”罪轻重悬殊,有诬告人死罪乃至灭族重罪者,也有轻罪微不足道者,不能一概而论。其罪名的成立在于告诉事情的虚与实,动机的“端”与“不端”。若所告属实,被告有罪,告人无罪而有赏;若所告事虚,被告无辜,告者故意陷人于罪,不能脱身事外,其罪名诬告成立。原告与被告罪名相互对立,“此有彼无”或“此无彼有”,而犯罪情节随所告之事之轻重而轻重,诬重则罪重,诬轻则罪轻。秦汉律中的“反其罪”也就是《唐律》所谓“反坐”法。诬告死罪,则分别是否论决。《唐律》云“至死,而前人未决者,听减一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译讯人为(诈)伪,以出入罪人,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以其所出入罪反罪之。”〔48〕彭浩、陈伟、[日]工藤元男主:《二年令律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 页。显然一脉相承。
(三)秦王朝的立法体现了高超的立法技术
唐《名例律》是唐律的总则,其中一条规定:“诸称‘反坐’及‘罪之’‘坐之’‘与同罪’者,止坐其罪”,疏议:“止坐其罪者,谓从‘反坐’以下,并止坐其罪,不同真犯。”〔49〕同前注〔32〕,刘俊文点校书,第149 页。唐以后各代律典中皆有此条,并且对“与同罪”的释义变化不大〔50〕如《明律》:“凡称与同罪者,止坐其罪,至死者减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在刺字绞斩之律。若受财故纵与同罪者全科。”《大明律》,怀效锋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 年,第21 页。。研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惊奇地发现“与同罪”条最早见于秦律,《法律答问》:“律曰与盗同法,有(又)曰与同罪,此二物其同居、典、伍当坐之。云与同罪,云反其罪者弗当坐。人奴妾盗其主之父母,为盗主,且不为?同居者为盗主,不同居不为盗主。”〔51〕同前注〔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书,第159 页。
“与同罪”作为古典律中的总则性规定,反映了古人对犯罪现象的深刻认识以及高超的立法技术。首先,“与同罪”虽然涉及两个犯罪主体,前者被称为“正犯”,后者被称为“被累人”,但不是共同犯罪。正犯不须有被累人的协助就构成“此罪”,而被累人“本皆无罪之人,因人连累者也。”〔52〕[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怀效锋、李俊点校,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109 页。实际上,被连累者的“本皆无罪”,法律不必为其另设罪名,仅准正犯之罪而科之,因而产生了“与同罪”规定“被累人”与“正犯”同罪。
其次,正犯为主动犯,被连累者为消极犯,故称“被累人”。清代律学家总结了“与同罪”的三种类型:“有知而不举者,有知而听行者,有知情故纵者。揆之情法,虽应同科其罪,而究其致罪之由,则有差别。”〔53〕同上注。也就是说一般先有“正犯”,后有被累人。无所谓“正犯”,也就无所谓“被累人”。《秦始皇本纪》:“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54〕《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这里涉及“偶语诗书”“以古非今”两个罪名,而官吏并非“偶语诗书”“以古非今”的正犯,仅因“见知不举”的消极行为,或与“以古非今”同罪,或与“偶语诗书”同罪而已。
再次,正犯重而被累人罪轻。明清律中“称‘准’即与同罪之义”。〔55〕同前注〔53〕,第110 页。王明德说:“准者,与真犯有间矣。”〔56〕[清]王明德:《读律佩觿》,何勤华等点校,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第5 页。又说:“准者,用此准彼也。所犯情与事不同,而迹实相涉,算为前项所犯,惟合其罪而不概如其实,故曰准。”〔57〕同上注,第5 页。在法律上设立“与同罪”的条款,是为了量刑上的需要,“与同罪”者与正犯能在量刑上区别对待。“揆之情法,虽应同科其罪,而究其致罪之由,则有差别,故正犯至死者,同罪之人减一等”〔58〕同前注〔53〕,第109-110 页。。“与同罪”在量刑要轻,一般无死刑,亦不刺字。
最后,被累人随正犯罪名之有无、刑罚之轻重而变化。
三、秦律初步构建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司法体系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秦的司法如此评论:“孰谓秦之法密,能胜天下也?项梁有栎阳逮,蕲狱掾曹咎书抵司马欣而事得免。其他请托公行、货贿相属而不见于史者,不知凡几也。项梁,楚大将军之子,秦之所尤忌者,欣一狱掾,驰书而难解。则其他位尊而权重者,抑孰与御之?法愈密,吏权愈重;死刑愈繁,贿赂愈章;涂饰以免罪罟,而天子之权,倒持于掾史。南阳诸刘屡杀人而王莽不能问,皆法密吏重有以蔽之也。”〔59〕[清]王夫之:《读通鉴论》,舒士彦点校,中华书局1996 年版,第7 页。王夫之仅凭个案而发的评论有点扩大其词。秦的司法达到空前的高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具体体现在:一是司法文书化,二是法官法吏制,三是从司法实践中出现传统律学。此外,秦的证据检验制度也是空前的完善,因笔者曾有专论,兹不赘述〔60〕闫晓君:《秦汉对期的法医检验》,载《国学研究》第1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一)秦王朝实现了最早的司法文书化
秦的行政过程已经完全文书化了。下情上达,基层政权对上级官府的信息收集要求文书化,如《田律》:“雨为〈澍〉,及诱(秀)粟,辄以书言〈澍〉稼、诱(秀)粟及豤(垦)田毋(无)稼者顷数。”〔61〕同前注〔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书,第24 页。《厩苑律》:“叚(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62〕同上注,第32 页。《仓律》:“程禾、黍□□□□以书言年,别其数,以禀人。”〔63〕同上注,第40 页。“十月牒书数,上内【史】。”〔64〕同上注,第41 页。这些行政行为,相关法律都明确要求“以书言”“用书”。《内史杂》明确要求下级官府对上级官的行政请示行为也“必以书”,禁止口头请示:“有事请殹(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65〕同上注,第105 页。上级官府对下级官府的行政命令、教戒、文告也是以书面的形式,如秦王政(始皇)二十年四月初二日南郡的郡守腾颁发给本郡各县、道的一篇文告名《语书》,性质也属行政文书,要求“别书弘陵布,以邮行”〔66〕同上注,第16 页。。上下级的行政文书,尤其是朝廷的“命书”还有严格的传递规定和邮驿系统,睡虎地秦简和岳麓秦简中的《行书律》残篇就是有关官文书传递的法律。如规定“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觱(毕),勿敢留。留者以律论之。”〔67〕同上注,第103 页。
秦代的司法应是秦帝国庞大国家机器运行中不可或缺之一环,伴随着秦帝国的行政文书化,秦代的司法过程也文书化。秦帝国的司法文书不同于一般官府行政文书,而是有专门的名称“爰书”〔68〕“爰书”一词,历史文献最早见于《张汤传》。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发现以前,一般学者如陈槃在《汉晋遗简偶述》,日本学者大庭脩在《爰书考》中认为爰书是汉代治狱之司法文书。,睡虎地秦简中有大量“爰书”,它的形成和大量出现本身就是秦代司法文书化的结果和标志。首先,秦代虽仍有口头提起诉讼的情况,但正规的诉讼方式已有了书面的要求。起诉文书称为书状,提起诉讼者必须具名,否则构成“投书罪”。其次,审讯过程包括是否采用刑讯手段却应加以文字记录。“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治(笞)谅(掠)之必书曰:爰书,以某数更言,毋(无)解辞,治(笞)讯某。”〔69〕同前注〔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书,第246 页。。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由25 节组成,实际上是司法文书的制作要求、方法和范式。其中头两节“治狱”“讯狱”是讯问嫌疑人时的理念和方法,“有鞫”“覆”是通过其原籍所在地确认嫌疑人身份之询问文书的文例,其余21 节“爰书”(包括小标题不明的2 节)都是“对案件进行调查、检验、审讯等程序的文书程式,其中包括了各类案例,以供有关官吏学习,并在处理案件时参照执行。”大庭修认为“像是爰书之文例集”〔70〕大庭修:《云梦出土竹书秦律概观》,收入氏著《秦汉法制史研究》,创文社1982 年版。,邢义田认为是文书模板与格式,“从内容看是秦代有关治狱、讯狱、有鞫、封守、覆、盗自告、盗马、争牛、群盗、夺首、告臣、黥妾、迁子、告子、疠、贼死、经死、穴盗、出子、毒言、奸、亡自出等名目的文书程式。”〔71〕邢义田:《从简牍看汉代的行政文书范本—式》,《严耕望先生纪念论文集》,稻乡出版社1998 年版。又收入氏著《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中华书局2011 年版。陈公柔先生讨论封诊式,基本上也认为封诊式是司法公文范本。〔72〕陈公柔:《云梦秦墓出土封诊式简册研究》,载《燕京学报》新3 期(1997),第142 -144 页。
岳麓秦简《为狱等状》由四卷独立的抄本组成,编者们根据四份抄本的内容及简片背面含有“状”字的三种不同的标题达成共识(简139 背“为乞鞫奏状”,简140 背“为覆奏状”,简137 背“为狱□状”),形成目前“为狱等状四种”这样的名字。“状”字是指一种记录刑事案件事实的文书形式。从《为狱等状》可以看出当时对案件记录的基本结构,首先记录收到报告或依职权控告。在受理后询问嫌疑人和目击者时,记录清楚各个陈述之间的对应关系,对嫌疑人的交叉讯问。嫌疑人认罪后,要添加与判决有关的检验结果和跨机构讯问的细节,并与审讯结果进行比对。最后,由确认犯罪事实成立的主管官员对案情的侦办情况进行总结。〔73〕岳麓书院藏秦简整理小组:《岳麓书院藏秦简〈为狱等状四种〉概述》,载《文物》2013 年第5 期。
在秦的各级官府中都有“主典文书”者,负责文书的起草、收发、传递和保管,如在最基层的县一级政权就由令史“掌案文簿”〔74〕参见刘晓满:《秦汉令史考》,载《南都学坛》2011 年第4 期。。秦代形成的司法文书制度对汉代以后的司法文书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如汉初,周勃入狱,“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75〕《史记》卷57《绛侯周勃世家》。所谓牍背,当是狱吏记录周勃口供所用的木牍背面。
孝景时,梁孝王“杀大臣十馀人,文吏穷本之,谋反端颇见。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忧之,问公卿大臣,大臣以为遣经术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吕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经术,知大礼。来还,至霸昌厩,取火悉烧梁之反辞,但空手来对景帝。”〔76〕《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可见,汉代治狱,仍用木牍记录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不仅如此,各级衙门的判决也以文书形式存档。如《后汉书·周嘉传》:“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时为郡决曹掾。太守欲枉杀人,燕谏不听,遂杀囚而黜燕。囚家守阙称冤,诏遣复考。燕见太守曰:‘愿谨定文书,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时病而已。’”〔77〕《后汉书》卷81《独行列传》。
(二)秦王朝产生了完整的法官法吏制
《周礼》:“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师,下大夫四人;乡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司寇系统的法官多称为士,贾疏云:“训士为察者,取察理狱讼,是以刑官多称士。”〔78〕[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中华书局2000 年版,第2711 页。可见西周以前的法官不仅是世袭的,而且是职业化的,虽不知法官的选任须具备哪些条件,但法官须具备法律的知识,《汉书·艺文志》:“法家昔流,盖出于理官”〔79〕《汉书》卷30《艺文志》。。
1.秦奉行法家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治国理念,要求法官断案必依于法,“不推绳之内”,“不缓法之内”。《商君书·说民》:“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80〕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2001 年版,第41 页。所谓“治不听君”,就是赋予官员以法来裁断的权力。“民不从官”而要奉法从法。因此,毫无疑问,秦的官员必须熟知法律。苏轼在《论养士》中指出秦“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王应麟也说“秦贵法吏”〔81〕《玉海》卷117。。有学者指出秦朝实行“通法入仕”,“秦时,通晓法令除可做法官法吏之外,还存在被国君举以为官的可能。”〔82〕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64 页。也可参看黄留珠:《略谈秦的法官法吏制》,载《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 年第1 期。换句话说,秦的一般官员需要通法,更不要说司法系统的法官法吏。
秦在中央设置廷尉,“掌刑辟,有正、左右监,秩皆千石。”廷尉及属官皆取精通法律之士,到汉代亦然。《汉官旧仪》云:“选廷尉正、监、平,案章取明律令。”〔83〕清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周天游点校,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37 页。直到汉武帝时,“张汤为廷尉,廷尉府尽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宽以儒生在其间,见谓不习事,不署曹”。公孙弘“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84〕《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自兒宽、公孙弘之后,大约才有不习文法的儒生进入法官系统。“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85〕《汉书》卷59《张汤传》。
2.秦律针对法官设立了几种罪名,主要是规范鞫狱行为,但客观上也要求司法官员精通法律。如“失刑”虽为“无心而失错也”“本无曲法加罪之意,而误将无罪为有罪,轻罪为重罪者”,或“本无曲法开释之情而误将有罪为无罪,重罪为轻罪者”〔86〕同前注〔53〕,第1015 页。,但也要入刑。与“失刑”不同,“不直”是一种故意犯罪,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论狱何谓‘不直’?可(何)谓‘纵囚’?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87〕同前注〔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书,第191 页。正如栗劲所指出:“如果出于故意,无论是重罪轻判,还是轻罪重判,都属于不直罪。”〔88〕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339 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论狱【何谓】‘不直’?可(何)谓‘纵囚’? 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当论而端弗论,及偒其狱,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89〕同前注〔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书,第191 页。显然两者之间有重合,与秦律“不直”罪包括“故出人”与“故入人”罪不同的,秦律“纵囚”是专指依法应该判刑的故意不判刑,或者故意减轻犯罪事实使其达不到判刑标准,使罪犯逃脱刑罚的制裁,实际上即后世的故出人罪中“全出”。
3.秦从司法实践中产生了最初的律学。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法律在国家管理社会职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保证秦代司法在时间上、空间上和质量上的统一性,一种讲求“法条之所谓”的学说应运而生,这种学说即为律学,沈家本认为律学滥觞于秦。伴随着秦律具体原则或法条的不断确立和完善,律学也随之而出现,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解释具体法律规则和法律名词术语,使律义更加明确,使表达更明精准,不致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歧义。也就是说,历史上出现了秦律,也就随之出现了“律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正是秦代律学成果的表现和律学出现的标志。〔9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在“说明”中讲:《法律答问》“对秦律某些条文、术语以及律文的意图作出明确解释。”同前注〔9〕,第149 页。《法律答问》是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为之加的标题,李学勤先生在《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中认为“这种法律书籍,类似汉世的‘律说’,或可称之为‘秦律说’。”在《简帛与楚文化》中迳称之为《律说》。参见《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104 页、第16 页。
传统律学对法律的解释,依据解释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分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这种传统从秦代律学就开始了。〔91〕张伯元:《法律答问与“秦律说”》,见《律注文献丛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曹旅宁:《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为法律实务题集说》,见《秦汉魏晋法制探微》,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立法解释是指对律文本身的解释以及律文中有关概念的解释。如“‘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者购臣妾二人,系投书者鞫审谳之。’所谓者,见书而投者不得,燔书,勿发;投者【得】,书不燔,鞫审谳之之谓殹(也)。”〔92〕同前注〔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书,第174 页。其中,“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者购臣妾二人,系投书者鞫审谳之”一句为秦律原文,“所谓”以后、“之谓”以前的一段话则是对律文的进一步阐发和解释。
4. 传统律学的解释方法始于秦律。司法解释是指在审判过程中关于如何适用法律的说明和解释,这些内容对各级司法机关及审判官的审判有规范和约束的作用,属预设性的解释。如“害盗别徼而盗,驾(加)罪之。可(何)谓‘驾(加)罪’?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有(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迁之。求盗比此。”〔93〕同上注,第150 页。其中“害盗别徼而盗,驾(加)罪之”一句应是秦律律文,后面“可(何)谓‘驾(加)罪’?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有(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迁之。求盗比此”,应是对“驾(加)罪”的法律适用的举例说明。
以前为大家所熟悉的唐律的解释方式主要采用问答式和举例式,通过与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的比较,才知道《唐律疏议》的问答释义与秦律的解释方式如出一辙,显然传统律学的解释方法也是从秦律开始的。张伯元指出“问答形式的采用有针对性强、与司法实践结合得紧的特点。”〔94〕张伯元:《律注文献丛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第9 页。实际上,此种方式的采用,恰恰说明其法律解释是长期司法审判经验累积的结果,有司法实践的需求作为基础。秦律在解释时也开始采取举例说明的方式,《封诊式》《法律答问》大量使用不定称代名词“某”“某甲”“某乙”“某丙”等来举例。这是由于“律文一般说来都比较概括、原则,给一般读律者乃至司法者理解律意带来困难。为此,《答问》的作者有时采用了假设、举例的方法对律条进行解释,明白晓畅,通俗易懂。”〔95〕同上注,第10 页。
四、秦律已具早期封建法律的地方性、野蛮性特征
因为秦律是“中国第一律”,是帝制形成时代的律,仍处于立法探索的阶段,所以秦律与以秦律为蓝本而形成的后代律尤其是《唐律》比较,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带有中国传统律典早期的特征。
1.秦律有较多原创的内容,但相应地很多名词术语带有明显的秦文化特征。也就是说秦国地域特征明显,在统一兼并过程中,与六国法律及文化有激烈冲突。不少名词术语不见于汉以后律,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如“祠未阕”“盗埱厓”“匧面”“臧(赃)人”“介人”“大误”“羊躯”等皆为秦律中的的专门术语;有些名词虽为汉律继承,但经魏晋社会变革以后,已不见于唐以后律典,如“城旦舂”“鬼薪白粲”等。
2.秦朝没有唐宋律的高度成熟发达,整齐划一。而秦律包括沿袭秦律的汉律具有某种早期法律的不成熟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立法语言的规范严谨不如唐宋律。唐宋律皆以“诸”字起首,明清律以“凡”字起首。明清律中“凡”由唐宋律“诸”字改变而来。诸,《经词衍释》:“诸,犹‘凡’也。”〔96〕[清]吴昌莹:《经词衍释》,中华书局2003 年版,第167 页。杨树达《词诠》:“一切也。总指时用之。”“诸”“凡”可以互训,都有概莫能外的意思。而法律所规定的法律行为具有高度概括性,用“诸”字或“凡”字起首,具有发凡起例的提示作用。检诸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秦律未见用“诸”字者,新出的岳麓秦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以“诸”字起首者己经出现,但不多,并非每条律文或令文皆以“诸”字开始。
其次,唐律是正刑定罪之法,除《名例律》外,其余十一篇律文的律文都“包括罪名、罪状与法定刑三个组成部分。”罪名、罪状与法定刑是刑律(刑法)条文内容的基本结构,同时也是刑律(刑法)法律分类上本质特点的反映。〔97〕钱大群:《唐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67 页。换句话说,《唐律》是纯粹的刑律。以此标准反观秦律,秦律包括汉律则未必是单纯的刑律,如睡虎地秦简《效律》《田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徭律》《司空》《传食律》《行书》等大部分律文都没有罪名,尤其是没有相应刑罚,如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的《复律》《赐律》《田律》《秩律》《军爵律》《史律》也是如此。这些早期律文并非完全都是“正罪名”的,而恰恰是“存事制”的,秦汉律“驳杂不纯”的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值得一提的是,秦汉律与令的关系与区别历来说法不一,难解难分,如《杜周传》:“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中外研究者亦莫衷一是〔98〕如日本学者大庭修:《律令法体系的变迁与秦汉法典》,见氏著《秦汉法制史研究》,林剑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广濑熏雄:《秦汉时代律令辨》,见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七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事实上,秦汉律令的区别含混不清,远不如唐宋的律令关系那样明确清楚,这也是早期律令的特征之一。
再次,《唐律》十二篇之间结构严谨,《名例律》为总则,其余十一篇为分则,《名例律》中规定的原则贯彻于其余十一篇律中,有总有分,收放自如。其余十一篇之间顺序排列别有用心,如《卫禁律》放在第二篇,其理由如疏文所说:“敬上防非,于事尤重,故次《名例》之下,居诸篇之首。”《职制律》排在第三,“宫卫事了,设官为次,故在《卫禁》之下。”《户婚律》排在第四,“既论职司事讫,即户口、婚姻,故次《职制》之下。”《厩库律》排在第五,“户事既终,厩库为次,故在《户婚》之下”等,依统治者对被调整社会关系的评价安排顺序。《杂律》起补充作用,防止罪名遗漏,“此篇拾遗补阕,错综成文,班杂不同,故次《诈伪》之下。”第十一篇《捕亡律》,“此篇以上,质定刑名。若有逃亡,恐其滋蔓,故须捕系,以置疏网,故次《杂律》之下。”第十二篇《断狱律》,“诸篇罪名,各有类例,讯舍出入,各立章程,此篇错综,一部条流,以为决断之法,故承众篇之下。”
《唐律》是一部法典,是由于结构严谨,刘俊文认为“唐律始以总则,终以专则,先列事律,后列罪律,是一部内容丰富、体例整严的综合性法典。始以总则,终以专则的结构反映出唐律在立法技术上已经达到相当高度的水平;先列事律,后列罪律的结构,则表明唐律把调整和强化封建国家的行政管理放在优先的地位。”〔99〕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绪论》,见氏著《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 年版,第35 页。相对照而言,秦律、汉律远未法典化,孟彦弘在《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中认为,“随着令的编集和完善,律由开放性体系变成固定和封闭的体系。”〔100〕孟彦弘:《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载《历史研究》2005 年第3 期。由于学术界对秦律的开放性认识不足,以唐宋法典化来看待秦、汉律,才产生了许多误解。如不适当甚至武断地怀疑《九章律》是否存在,以《二年律令》的二十七篇强行与《九章律》挂钩,当然这些仍不失为学术研究上的有益探讨。
从目前出土文献来看,秦律仍处于初创阶段,很多法律乃因事立法,以单篇行用。由于各篇律之制订非同时制订,先后篇目之间仍缺乏《唐律》各篇之间固定顺序。秦律如此,汉律亦如此,《二年律令》各篇就是如此。大约迟至东汉,汉律篇目方较固定。湖南张家界古人堤出土的汉律律目当是明证。
3.秦律奉行重刑主张,刑罚残酷是其明显的缺陷。《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条注略云:“商鞅传之,改法为律,以相秦。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沫,大辟加凿颠、抽胁、镬烹、车裂之制。”事实上,凿颠、抽胁、镬烹、囊扑等酷刑并未见诸秦律律文,或为秦始皇逞一时雷霆之怒,或为汉儒传闻。但秦律刑罚偏重是不争的事实。
五、结语
秦律是“中国第一律”,主要是说:一,秦律是由秦人的部落习惯发展而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秦国律,进而成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秦朝律。从秦律创制的过程来看,秦律具有原生自发性及地域文化特征,在中国法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汉以后各代的法律都以前朝法律为蓝本。二,秦律创制了较有系统法律名词术语,其法律原则表现出了高超的立法技术,在立法方面体现出了极大的创制精神,对汉以后各代律法的影响深远。三,秦朝的司法体系比较完善,除了法官法吏的法律素养较高,具有专业化倾向以外,司法过程文书化,司法检验的制度和方法也较完善。四,秦律作为中国第一律,还带有与生俱来的早期性、地方性及野蛮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