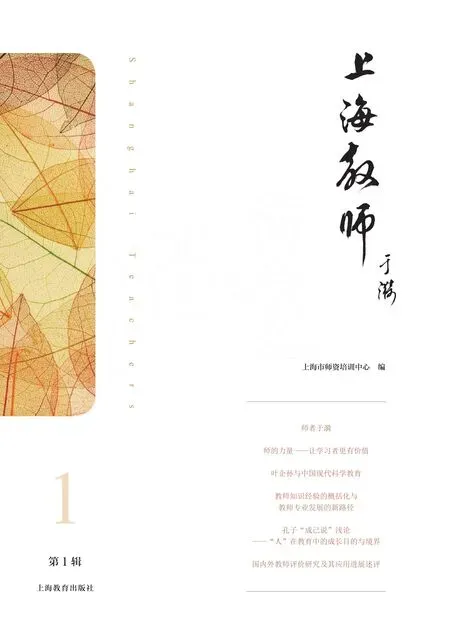面向人类学的教师教育改革:理论透视与实践路径
2020-02-25李云星
李云星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4)
一、引言:作为教师教育基础学科的人类学
教育人类学家拉德森(Ladson-Billings Gloria)曾批评美国教师教育过度依赖心理学而忽视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的现象。他指出,尽管心理学提供了儿童成长心理机制的知识,但它缺乏对学生文化的关注。典型性的职前教师会选修大量关于历史、哲学和教育社会学的基础课程。然而,课程开设存在强烈的心理学集中倾向,相关课程主要涉及儿童或青少年发展、认知与学习、特殊例外(如具有特别需要的学生)。在美国,理解教学就是要理解整个心理领域。[1]
拉德森的批评至少隐含了如下含义:教育与教学不仅仅与心理认知有关,它还涉及文化。人类学作为研究文化的学问,能够为教师培养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人类学能对教师教育有所贡献,在于人类学与教育学的内在关联。不论是教育学还是人类学,成人都是其核心研究对象。略显差异的是,人类学关注的是“何以成人”,即成人是如何发生的。教育学更关心“以何成人”,即如何做才能成人。这一差异也造成了人类学家与教育者在提问方式上的差异:人类学家追问的是“事情是如何的(how things are)”;教育者的提问是“对于这件事,我们能做什么(what can do about the way things are)”。[2]没有对“何以成人”或“事情是如何的”的了解,教育者无法回答“以何成人”或“对于这件事,我们能做什么”。在此意义上,人类学应当是教育学的前提性或基础性学科之一,自然也应当成为教师教育(学)的基础学科。两者的内在关联构成了人类学介入教师教育的可能性前提。本文并不试图“照着讲”教师教育为何需要人类学,而是尝试“接着讲”人类学能够为未来教师贡献什么,以及面向人类学的教师教育改革实践路径。
二、理论透视:人类学对未来教师的可能贡献
(一)认知视角的贡献
人类学对未来教师的贡献首先在于认知视角,包括整全视角、文化视角和他者立场(内部人视角)。
1. 整全视角
詹姆斯·皮科克(James Peacock)曾将整全视角作为人类学的基本特征:
这一宽广的视角——有时会用一个专门术语“整体观”来表示——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人类学特征。不管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类学定义,它都会着重强调,这是一个从整体上去理解人类许多方面的准则。进行整体思考,就是要将部分放到整体中来理解,设法掌握更大的背景和框架——在这一背景与框架内人们会有种种表现和体验。人类学的整体观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人类学总是试图从整体上认知和理解每种体验;二是人类学总是试图描述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而不是从中抽象隔离出部分;三是人类学往往会综合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和视角来理解研究对象。[3]
与其他学科强调由部分认识整体不同,人类学强调对局部或部分的认识必须立足于整体。当且仅当我们对整体有认知的时候,才能发现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联系。人类学的这一认知视角与教育学,尤其是与当代学校教育学不同。教育学通常将对象聚焦到“具体个人”或“群体之人”。因此教师容易陷入就教育谈教育的误区,而忽视具体个人或群体背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文化联系。以人类学观之,学习并不仅仅局限于学校,也不仅仅是知识传递或技能提升,而是涉及师生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的重构。从教育发展史来看,早期教育属于非形式化教育,教育与生活融合在一起。伴随着形式化教育尤其是制度化学校的出现,教育与生活发生了割裂与脱离。尽管学校有其存在价值,但其功能、使命和内在运行逻辑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学校教育不仅要从重构学校教育文化角度统整考虑教育问题,更要从与整体社会文化衔接、融通的角度重构学校与社区的关联。
2. 文化视角
人类学不仅关注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生活及自然生活中人类所处的位置,而且尤为关注人类为了使其生活变得有意义而建构文化框架的方式。[4]人类学尝试以文化为对象和方法,理解、构建关于异域或他者的理论。教育作为文化保存、传递、更新和创造的事业,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类学文化视角对教师的意义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有助于教师从文化视角切入、理解并解决教育问题。以人类学视域观之,教育的问题往往是文化的问题。例如,印第安人学生对教师的提问往往会报以沉默,这并不代表他们不理解或不会,而是与他们的文化相关。研究发现,印第安人学生在课外表现为“吵闹、勇敢、大胆和变化无常的好奇”,但在课堂上总是沉默。这是因为在印第安人的文化里,个人才能的展示会被看作对其他孩子的贬低。这一研究也彰显了印第安人文化与盎格鲁—美国人文化的差异。在美国白人的文化里,个体学生的主动性、竞争力和成就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而在印第安人的文化里,同样的行为是被认为不可接受甚至是不道德的。[5]人类学提醒教师:当遇到教育问题时,首先需要从文化视角重新审视现象或问题本身,透析其原因,并寻找应对方法。文化视角对于理解并解决当代中国乡村教育问题或城市学校中农民工子弟学生的教育问题尤其具有实践意义。
二是有助于教师在教育实践中确立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念与意识。文化相对主义观念由来已久,人类学对不同的文化有着天然的敬畏之心。文化相对主义首先表现为对不同生活方式、文化价值的尊重,其次表现为对不同文化的敏感与意识。当教师学会用文化来看待问题时,会习得文化敏感。
3. 他者立场(内部人视角)
人类学的他者立场,强调从研究对象的视角——内部人视角(insider perspective)而不是研究者的角度理解他们的意义世界。被研究者既是研究对象,又是研究方法。人类学的他者立场致力于理解他者,返回自身。这有助于教师获得关于学生的置身式理解。他者立场强调站在他者的立场或视角看待问题,即“put yourself into other’s shoes”。在人类学视域下,强调要将他者的行为或语言置于他者的文化实践中理解。对教师而言,则强调将学生置于学生的成长环境中理解。这一理解,有助于教师认识到家庭环境对学生发展的形塑与制约。
在教育学史上,学生立场的确立被认为是一场哥白尼式革命。教育学视域的学生立场,强调以学生的发展作为教育的目的和终极评价标准,立足学生的发展需要和发展规律,开展、实施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尽管教育实践界认可学生立场的价值与意义,但囿于“教师中心、课堂中心、教材中心”传统教育实践文化的强大抵制力量,仍需确立学生立场并提升践行学生立场的能力。
他者立场对教师的启示在于: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避免用自己的思维“强牵”学生的思维;避免用个别学生或部分学生的视角、思维与问题代替全体学生的视角、思维与问题;避免轻视学生的思维与经验;避免用习以为常、例行的模式来解读学生,或者用“好学生、坏学生”的二分法来区分学生等。他者立场强调教师应关注学生的日常语言和日常思维,尤其关注学生的叙述、对问题的理解和分析以及学生自己的术语和概念。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声音,哪怕是不成熟的声音不应该被当作需要清除的杂音,而是教育教学实践的起点。
(二)本体论层面的智识启迪
在人类学看来,成人主要是通过学习(文化)机制,而不是神经化学(本能)机制来满足生物学和环境需求。成学(to learn),不是非自愿的回应,是成人(to be human),成人即成学(to be human is to learn)。[6]这表明“成学”(教育)本是“成人之学”的研究对象。
人类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教育。早期人类学家对教育或学习的理解,远远超出学校教育范围。当大多数人将学习看作从教师到学生的科层制组织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通过对萨摩亚人的研究,已经将教育看作与成年人或同伴一起做事的横向联系。金·莱夫(Jean Lave)等人的研究则聚焦日常生活中的学习,通过对裁缝、水手、屠夫等学徒制的研究,强调学习是一种合法性边缘参与的过程。在莱夫看来,学习是学习者在实践共同体中的社会参与,知识是个人与社会情境或物理情境之间互动的产物。人在实践共同体中的互动,会建构出意义与身份,它们与更广泛的情境脉络密切相关。[7]莱夫关于情境学习的研究受到了教师教育界的极大认可和关注,他的研究高居21世纪以来国际顶尖教师教育SSCI期刊论文高频引用文献之首,总计被引269次。[8]人类学的智识启迪还重构了对教育或学习的理解。正如莱夫所揭示的,日常生活中的学习是一项由边缘到中心的合法性参与过程,其中伴随着学习者意义和身份的建构。就此而言,学校教育也应当是学生意义和身份建构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知识接受的过程。教师的职责在于设计相应的做中学项目,让学生主动参与其中,在做的过程当中习得知识、能力、方法和思维。
人类学智识启迪还表现在通过呈现文化的多样性和揭示生活的多样可能性,让教师反思自我文化的刻板性。例如,霍尔通过对西太平洋上特罗布里恩岛上的居民研究发现,他们的时间观并不是基于现代时间观的。现代时间观认为:时间是线性的、进化发展的,是宝贵的资源,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特罗布里恩岛居民则认为,时间并不是一条一个人顺其发展的直线,而是一个人坐在一旁拍溅或在里面打滚的水坑。[9]这一时间观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现代时间观,但它至少彰显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人类社会发展最大的障碍即失去对可能性的想象,而统统归结于一种单向的生活。“可能性”的存在,既需要知道存在多样性可能,也需要对“主流可能”或“唯一可能”进行反思。人类学的诸多研究可以让教师重新反思“现代”“文明”“中心”“城市”等概念,并重新认识“落后”“野蛮”“边缘”“乡村”。迁移到教育,教师也可以借由人类学思维重新思考“成功”“优秀”“进步”等概念,而回到学生对上述概念的自我认知,并基于学生的认知和理解,促进学生的发展。
(三)方法论层面的民族志方法
在人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民族志是关于文化的研究。做民族志的一个原因是让那些通常不可见的生活模式和生活习惯变得可见,以理解那些已经掌握这些模式和习惯知识的人,并确认特定人员知道(或不知道)和理解(或不理解)这些模式的影响。因此,民族志既是在特定社会群体内观看、观察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记录、分析并表达生活的方式。[10]研究表明,民族志方法可以提供影响教育的文化和社会洞见。[11]人类学视域下的反思性实践可以提供一种策略,帮助教育者解决他们实践中的“困扰”,并在文化多元课堂中改进实践。一方面,诸如文化、背景、社会结构、权力等人类学概念提供了理解多元文化课堂的有效方式;另一方面,诸如观察、灵活访谈和人工分析有助于获取有用信息。通过运用人类学概念和信息,教育者可以通过有效的干预以改进教育实践。[12]
例如,民族志观察因本身带有内部视角以及相应的文化关切,因此更能够深度破解教育实践的内在机制。与一般量化观察不同,民族志观察强调聚焦事件、过程、主体感受和意义。教师可以单独观察教学学习过程中的学生,如准备开始学习较慢的学生和迅速开始学习的学生,并提供多样化的学习经验。同样,对于那些温顺的、安静的以及仔细思考问题的学生也给予足够的关注。日本的研究表明,民族志有利于教师加深对学生的认识,并采取相对应的教学策略。在课例研究过程中使用民族志和田野笔记的教师,可以在课堂管理中创造并运用替代性策略。基于民族志的课堂观察更有利于解释学生正在做的事情以及教师在课堂里应该做什么。[13]另有研究通过使用民族志视角帮助候选教师(teacher candidate)成功进入一个发展中的课堂文化,并让一位休学四个月的五年级学生重新融入原来的班级。研究表明,使用民族志的观察和解释技巧,通过重组由课堂互动而已经形成的社交和学术方面的模式化实践,既可以帮助候选教师,也可以帮助返学学生成为具有社交和文化胜任力的成员。[14]
简而言之,作为人类学核心的民族志可以帮助教育者懂得更多的学校文化和学校教育总体背景,让他们处于一个更好的立场以改进教育实践。民族志为教育研究者提供了替代性选择,将教育体系作为整体,并检验其中许多部分的关系;为不同群体、学校和学校社区的多样性提供丰富的民族志描述;民族志研究同样有助于促进家庭和学校的密切联系;它可以形成重要形态的质性评估数据,这是传统学生学业成就测评提供不了的。
三、面向人类学教师教育改革的实践路径
(一)目标更新:培育具有文化回应教育能力的教师
伴随着文化多元时代的到来,国际教师教育呈现出鲜明的文化转向特征。越来越多的国家强调教师的文化意识、文化敏感、跨文化能力和多元文化教育能力。例如,德国教师教育标准规定,未来教师需要了解学生的社会文化生活条件,包括在理论教学阶段、设计教育教学过程时注意跨文化维度,了解性别特征对教育过程的影响及其意义;见习阶段要注意到各个学习小组中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多样性等。[15]西班牙小学教师专业培养目标也要求教师能有效处理多元文化和多种语言环境下的语言学习问题,熟悉和处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校状况,能将教育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并与家庭和社区开展合作,以批判的方式分析和思考影响家庭和学校与现实社会有关的问题,如代际关系的变化、多元文化和跨文化、社会歧视与融合、促进忍让等。[16]
略显遗憾的是,中国教师教育存在文化缺失或忽视问题。以“文化”为关键词检索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发现,仅有四处提到“文化”。其中三处出现在“终身学习”理念中的“优化知识结构,提高文化素养”。仅《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教育知识部分提及“了解中学生群体文化特点与行为方式”。显然,这不符合多元文化时代的发展趋势。
在文化传递、融合和创新进程中,教育承担着重要的使命。面向人类学的教师教育改革,首先在于目标更新,即培育具有文化回应教育能力的教师。文化回应教育(culturally responsive education)旨在立足学生文化差异,利用差异化文化资源,通过发展与学生文化背景和个性特征相适切的课程、教学和管理策略,以实现教育的目标。有研究者提出,文化回应性教师(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er)的典型特征包括:具备社会文化意识;对多样化背景学生的坚信;认为教师有责任并有能力让学校变得更公平;懂得学生如何建构知识并有能力提升知识建构;知道学生的日常生活;在引领学生超越熟悉的时候能够基于学生已经知道的设计教学。[17]事实上,这一界定是文化意识、教育态度、教育过程知识和教育设计能力的综合。面向人类学的教师教育目标需要整合人类学的独特优势并结合教育自身的特点和目的,对未来教师提出新的要求。基于这一要求,文化回应性教师至少应具备四个层面的素养。
一是文化意识与敏感。它包括对学生、家长及其社区文化的尊重与敬畏;能够用文化视角和眼光看待透视教育问题等。
二是文化研究能力。它包括能够通过与学生、家长或其他人士的交流,明晰教育利益相关者的文化理念和教育期待;能够探究、分析学生的知识建构方式及其背后的文化影响等。
三是文化回应教育能力。在尊重文化、敬畏文化、研究文化的基础上,教师需要具备将作为资源的文化转化成课程、教学以及管理的设计和实施能力。它包括营造相互尊重、安全的文化氛围,创造学生实现能力的良好环境;整合学生的地方性知识或本土化概念进行教学设计;针对学生不同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学习方式采取不同但适切的教学策略;发掘地方文化资源,整合开发学生学习课程等。
四是文化反思能力。教师实践不是从已知技术工具箱中选择最佳方案的活动,它面临着复杂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价值冲突。教师需要运用实践智慧,从具体情境中构建出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不断地反思建构自己的专业知识。[18]教师的文化反思是教师反思的一种,但又具有独特的价值和蕴含。它促使教师思考:教育问题的产生是否存在文化差异的因素?如果存在,是哪些因素?教育如何根据这些因素进行调整设计?教育实践中有哪些文化资源可以用于教育的改进?教师自身的文化如何形塑影响教育手段和教育效果?如此等等。
需要指明的是,上述四个层面的能力或素养并不是并列或相互割裂的,而是彼此联系的统一体。
(二)课程引入:作为改革重心的人类学课程
教师教育培养目标的更新必然要求课程的变革。就人类学在教师教育实践中可能扮演的功能作用而言,至少存在以下三种形态的人类学。
1. 作为公共基础课程的人类学
公共基础课程旨在为师范生奠定教育教学的理论基础、知识基础和方法基础。通常它包括“教育学”“心理学”“课程论”“教育研究方法”等所有师范生必选的公共基础课程。人类学作为学科基础课程包含两个目的向度:一是为未来教师提供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框架和基本视角;二是为未来教师提供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基础。前一目的向度的课程改革可以将“教育人类学”作为师范生必选或选修的课程;后一目的向度的课程改革可以与现有的“教育研究方法”进行整合,强调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学习与运用,包括参与性观察、倾听、访谈等技术的扎实学习。作为方法的人类学课程实践在国外早已有之。人类学家兰德斯(Ruth Landes)很早就将人类学田野方法引入教师教育课程,让未来教师通过回溯家族文化遗产来反思个人的文化观念,并挑战、反思关于学生和自己的深层次假设。随后,兰德斯会要求未来教师采取人类学家的立场,在课堂中观察并做田野笔记,以此深化他们关于学生和他们自己行动和理念的理解。
2. 作为学科专业课程的人类学
作为学科专业课程的人类学,强调将人类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方法作为学科教学的内容、资源、手段和策略。换言之,人类学相关知识或理论不再是作为透视教师研究、透视自己或他者的工具,而是作为实现教育目标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或工具。国外教育实践中已有大量的实践案例。例如,有教师将人类学作为一个内容领域或单元,帮助学生学习文化、历史、理论、工具、实践,以及理解人类学主体知识的分类。在此基础上,人类学课程还被用来帮助学生理解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更广泛的社区。也有教师让学生主动实施人类学研究,包括合作参与和自主参与人类学研究。例如,有教授四五年级的教师让学生与当地文化人类学家合作,实施一年的社区研究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让班级学生访问、记录、分析当地农民和社区教堂的福音歌手,以获得文化理解、语言技能、研究经验和分析能力。[19]还有教师让学生用人类学方法研究课堂行为,编制“民族志书(The Ethnography Book)”。学生在此过程中需要学习观察、解释、感知并分析课堂行为。“民族志书”也有助于教师获得学校生活中学生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学生的所思所想。[20]更有教师在课堂中引入人类学方法,如在课堂中引入“民族志思维(Ethnographic Ways of Thinking)”,帮助学生将人类学工作、思维方式和理解复杂情境的愿望转换到学校和生活的情境之中。[21]
除上述实践案例之外,还存在基于人类学民族志与学科深度融合的课程开发与实施案例,如民俗数学(ethnomathematics)。民俗数学强调对传统和日常数学的研究,并将研究发现整合进符合内容标准的课程中。民俗数学承认儿童自身携带知识的价值,并鼓励儿童参与基于日常数学的活动,帮助他们发展有意义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更好的数学能力。[22]关于民俗数学,国内已有研究者开始关注[23],但在教师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方面的实践相对较少。民俗数学仅仅提供了人类学深入学科及其教学的一个案例。类似的实践还包括涉入科学课程、社会研究课程、语言艺术课程等。[24]换言之,上述相关的师范专业都可以将人类学作为学科专业课程,以探讨人类学与学科基础知识及其教学的整合。
3. 作为教师实践课程的人类学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提出,师范生教育应涵盖公共基础课程、学科专业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其中,教育实践课程不少于一个学期。具体到各层次师范生培养课程标准,它们都强调师范生应具有观摩、参与、研究教育实践的经历与体验。在此要求的背景下,各师范专业都设计实施了教育实践课程。但目前教师教育实践课程主要聚焦师范生课堂教学规范习得、学生管理技能学习、学科教学知识运用等方面,缺乏对教育社区的深度关注,更缺乏对学生及其家庭生活方式的置身认知。在教师教育实践课程中,人类学课程及其实践的介入,不仅可以拓展教育实践的内涵,也能丰富教育实践的视角和方法。基于人类学的教育实践强调关注学生及其家庭、社区的文化。以超越认识工程(Beyond Awareness Project)为例,该项目旨在让未来教师从仅仅意识到文化差异转向发展思维习惯,包括理解学生文化并赋予其价值,认可在教学实践中考虑这些文化的需要。项目要求未来教师对所在学校的社区进行跨度为7个月的文化观察,观察点可以是图书馆、课后项目、地方餐馆或宗教机构,观察次数不少于6次。观察的重心不局限于种族问题,而是涵盖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如关注人们的互动方式、行为模式、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运用等。未来教师需要记录这些观察,并就观察对课堂教学的启示写一篇反思笔记。这些观察也会被研究者进行编码,以备后续深度分析。通过人类学方法的运用,未来教师开始与不同于他们观点的人互动,通过这些互动,未来教师可以超越认识,去教课堂中所有的学生——尤其是那些因其文化遗产或差异而被忽视的学生。通过人类学研究,未来教师能够更加批判性地检视他们所观察的情境,并质疑他们关于社区的信念和理解。[25]
四、结语:让教师成为人类学家
利特福德(Littleford Michael S)曾提及教师与人类学家的诸多相似之处:“没有对需要处理的多样化情境的系列描述,教师和人类学家都无法完成他们的任务,因为在卷入之前,无法获知所有的重要问题。他们都必须随着新形态和关系的出现以及新问题的发现随时调整他们的思维。为了操作更为有效,教师和田野人类学家都必须成为敏锐的参与性观察者,这些参与性观察者能够运用必要智力工具以让工作中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变得明确。”[26]利特福德认为,深度卷入、文化敏锐、参与性观察、实践智慧等构成了教师和人类学家的共通点,也蕴含了他对教育的理解:教育是一项需要教师深度了解、置身其中且充满实践智慧的文化实践活动。就此而言,每一位教师都需要成为人类学家。让教师成为人类学家,并不是让教师成为教育实践的旁观者和描述者,而是主张教师运用人类学的视角、眼光、方法和知识,在系统观察、描述和研究实践的基础上系统设计课程、教学和管理方案,从而实现教育目标。让教师成为人类学家的理念对于多元文化激荡的当代中国教育尤其具有实践价值,它需要教师教育机构的理念更新和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