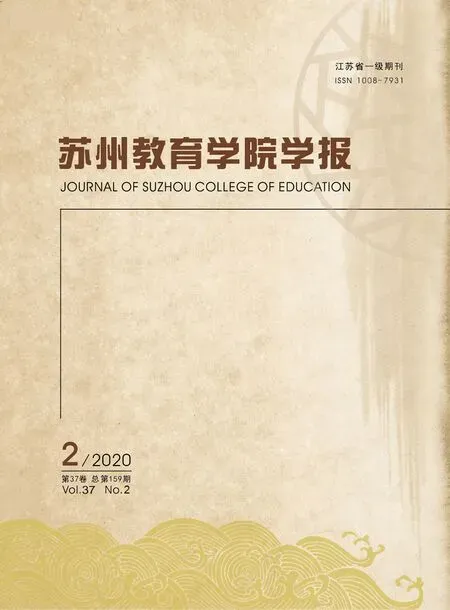缘情入性,由性见道
——论房伟《猎舌师》
2020-02-25邓全明
邓全明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太仓 215400)
自抗日战争伊始,抗战就成为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迄今仍是“文艺重要的关注热点”和“创作突破的难点之一”[1]。“70后”作家房伟在学术界耕耘多年后,转而进入创作领域,第一部小说集就出手不凡,在抗战小说创作方面取得新突破,这与他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对人情、人性、人道的准确“拿捏”和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整体把握分不开。
一
刘再复将人的心灵世界分为三个层次,其中第一个层次就是感性欲望,“它的运动是随机的,不定向的,本能的,无逻辑的”[2],这是感性欲望的基本特征。感性欲望往往随机体状态和外界的刺激而变化,“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感物生情,是对外部世界是否符合主观需要的态度;饿而思食、渴而思饮,则是机体需求产生的欲望。弗洛伊德所言的潜意识也可视为感性欲望。作为人学的文学,不能不表现因时、因地产生的各种情感及感性欲望。
《猎舌师》[4]的成功,首先在于对感性的“人”的细腻表现,把作为个体的人在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场景中的转瞬即逝的各种感性欲望,表现得丝丝入扣,历历在目。在许多抗战文艺作品特别是抗战剧中,只看到日本士兵身上贴着血写的侵略者的标签,却很少展示出作为个体的日本士兵纷繁的内心世界。房伟小说的最大特点在于表现标签下一个个鲜活的灵魂——或罪大恶极,或善恶交织。如《幽灵军》中的长谷川、《地狱变》中的水源清、《副领事》中的领事,都是这样的“圆形”人物。水源清是一个受武士道精神影响、文化水平较高的日本军人,他踏上中国领土时,也有些许不安与惶恐,但更多的是像那些受武士道精神影响的日本军人一样,将“亲历了血与火”视为“壮丽与惨痛”的人生的一部分,将“能在轰轰烈烈的战斗中死去”[4]78,当作军人的荣誉。但当真正走上战场,看到自己的同胞在战争中肆意地强奸妇女、滥杀无辜时,他的内心也有所震动,但这毕竟不是他的同胞,而是敌国的人民,因此他虽“对强奸妇女,杀死老人和孩子不感兴趣,也谈不上反感”[4]82。其实,他内心深处是不喜欢这种残暴行径的,在可能的情况下,他尽量去阻止这种暴行的发生,因为“残暴”有违他的天性,他甚至睁只眼闭只眼地看着远处的八路军在探照灯下“溜走”。面对战争,水源清和许多日本军人一样,未必知道这场战争的实质,他们只是服从国家的安排走上战场。面对残酷、血腥的战争,他们也同样感到个体的渺小、无能,在生与死的挣扎中度日。“我们都是魔鬼,只是在这乱世中挣扎罢了”[4]85,水源清内心真实的想法,其实也是许多侵华日军真实心境的袒露。另外,作者把在满地尸体中饮酒作乐的虚云和尚和凶残、粗俗的土冢的内心世界也刻画得非常鲜活,令人难忘。
《猎舌师》还细腻地刻画了敌占区普通民众内心的痛苦与挣扎。《手肴》中的“表哥”、《猎舌师》中的骆宁安、《地狱变》中的蒋巽,可谓其中的代表。“表哥”的妻子死于南京大屠杀,在亲人尸骨未寒之时,表哥就参加了日本人的自治会,成为汉奸走狗。骆宁安更是悲惨,他的亲人死在日寇的屠刀下,但他没有加入反抗的行列,而是去日本领事馆做了厨师。“表哥”和骆宁安都是性格软弱之人,没有勇气与敌人进行斗争,也没有勇气自杀以保持气节,只好苟且偷生,但他们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他们的良心时时忍受煎熬。《手肴》中的“我”则是另外一种挣扎:“我”遭受了日本士兵的蹂躏,决心复仇,但目睹眼前的日本士兵还有几分稚气,良心有所触动,但最终还是将其刺死。另外“我”还怀着复仇心理“拖着日本军官岩佐一起沉沦。并不是光,而是对于更深刻的黑暗的冲击”[4]274,毒死了对中国“友好”的岩佐。“我”的内心多少受到良知的“拷问”,但杀死仇人,也是情之所然。
战争不是人类生活的常态,而是非常态,战争也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战争中的人无论在哪一方,都会受到战争的伤害——尽管伤害的程度不同。也正因此,人才会渴望回到和平的社会常态。因为战争是非常态,战争中人的情欲也呈现出异态。《猎舌师》的不同之处在于既写出了战争受害者的爱恨情仇,也写出了战争施害者的七情六欲,从而真实地反映了乱世中人的独特而丰富的情感世界。
二
钱穆说:“一切有生物,尤其是人,显然有一个求生、好生、重生、谋生的倾向,有一种生的意志,这即是性。”[5]10确实如此,繁衍生命、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共同天性的重要内容。求生、好生,是人人皆有的天生之性,不过,这一天生之性还有刚烈、平和等之分。感性之心与心性之心的不同在于:前者侧重特殊性,强调的是现场感,主要指在特定生活场景,个体因个人利害关系和在特定生活事件中的角色表现出来的情感、态度;后者侧重普遍性,主要指作为类的人具有的超越时空的本质特征。人情与人性虽有不同,但也不是没有联系,朱熹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6]18,也就是说情从性中发,喜、怒、哀、乐是性的表现形式。故此,文学要揭示人性,就要在聚焦个体独特的情绪世界的基础上洞察带有普遍性的人性。《猎舌师》在这一方面,可圈可点。
抗日战争是中国和日本展开的正义与非正义的现代战争,日本是战争的发动方,是侵略者、施害者,必须受到道义的谴责;中国是战争的被动方,是自卫者、受害者,双方的情感、立场存在巨大的差别,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无论是战争的受害者,还是战争的施害者,既然都是人,就应该还存在共同的人性。《猎舌师》的成功之处在于既从受害者一方的视角揭示施害者的残暴、毫无人性,还试图超越具体角色,揭示共通的“未发”之性。如《幽灵军》中的长谷川信彦,他出生于武士家庭,先祖也曾有过辉煌的战功。此次来到中国,他满怀希望——像他的先祖一样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然而,到达中国后“伟大的战争”已经结束,长谷川信彦所渴望的以惨烈的战斗赢得荣誉的愿望化为泡影,看到的却是卑劣的烧杀抢掠,与他想象的武士道精神相去甚远,长谷川感到十分沮丧,进而感到人生的无意义。长谷川希望建功立业的想法,就是钱穆所言的“好生”——过更好的生活,这是人之所有之性,即性之未发,故无所谓善恶,但“性”发之后的喜怒哀乐,便有了中节与不中节之分,也就有了善与恶。对长谷川也是如此:他希望建功立业的好生之性并无罪恶,罪恶的是“性”发后的实现方式,对此,《猎舌师》的认识是深刻的。超越战争双方的道德立场、透过躁动的人情直指人性的还有《猎舌师》对情爱的描写,其中以《杀胡》最为典型。佐藤与三桥,一个出生于医生家庭,另一个出生于北海道的农民家庭。他们成为战俘暂时被扣押在一个偏远的村子里。小颖和小艾是这个乡村的女孩,两对异国男女却在战场后方产生了男女之情。小颖求爱被拒绝,她竟背叛家族,向佐藤泄密,只为求与佐藤“一夕欢好”。另外,《小太君》《鬼子妮》《地狱变》也都写到这样跨越民族、超越战争,甚至冲破理性栅栏的爱情。男女之情爱,是“人的所有之性”[7]中十分强烈的一种,以致弗洛伊德将其作为人行为最终的动力。弗洛伊德或许夸大了男女之性的强大,但对于其巨大的能量——甚至常常突破人的理性肆意妄为——是毋庸置疑的。房伟的小说将笔触伸到以前抗战小说很少涉及的男欢女爱,体现了他对人性独特的把握和理解。如果说《小太君》《鬼子妮》《杀胡》等以战争方式来书写敌我阵营的爱情,以表现人之大欲,那么,《还乡》则通过同一战壕的战友,为男女之情不惜出卖良心,从另一层面表现同样的主题。棉朵是戴家屯的戴屯长的未婚妻,同村民兵队长觊觎其美貌,企图横刀夺爱。戴屯长以粗暴的方式羞辱了民兵队长,后者为报仇雪耻,竟勾结日寇,引狼入室,致使棉朵等数十人被敌人杀害。《还乡》之所以将那些隐藏在历史角落里的丑恶抖落出来,固然表明历史和人命运的偶然性以及善恶的水乳交融,更是表现出人性的复杂性和人性的痼疾。无论是打破战争的敌我界限、超越民族的情爱,还是与同一阵营因情爱而反目成仇甚至投靠敌人,其表现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根源是人欲的强大。
作者除了描写情爱之外,也对英雄之间的敬慕之情有很好的刻画。《七生莲》写的是勇士对勇士的敬畏之情。鹤田英秋这个日军少尉,“性本爱丘山”,只因日本政府的征召而成为军人——侵略者的一员。上了战场的他对无休止的训练、杀戮感到十分厌倦,对中国军人、农夫“惨烈得令人无法直视”的悲壮产生隐隐的同情。天赐是中国农夫,彪悍而粗俗,是莫言小说中余占鳌式的土匪英雄。天赐的这种气质,赢得了鹤田英秋的敬畏,他下意识地为天赐逃跑创造机会,天赐因此得以逃脱。他们违背敌我原则的私下交流,显然打破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断语,彰显出人性中的“英雄惜英雄”的共同倾向。
当然,人毕竟是人,既有屈服于“求生、好生、重生、谋生”的共同的天赋之人性,还有超越“人的所有之性”的“人之性”:理性和“异于禽兽者希”的德性,即人道。
三
作为社会的人,人还需守人道。朱熹说:“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6]17,守人道、走人的“当行之路”,就是遵守处理利益关系应遵循的原则。钱穆谈到中国文化的特点时说:“中国古人观念,则注重人类内心相互之‘感通’上,认为如把男女化成夫妇般,如此推去,才能把世界人类大群化成一体,成为一个天下。所以他们说文化传播,我们说‘大道之行’。”[5]8“大道”是从整个人类的角度而言的人道,是大写的人道。对于文学来说,缘情索性,固然重要,但作为优秀的文学作品,这还不够——必须由性及道,循道“尽性”,《猎舌师》在这一方面也值得称道。
《猎舌师》中的骆宁安,祖上为书香门弟,到他这一代已破败不堪,他也丢下读书人的面子,混迹庖厨,成为南京有名的厨师。南京大屠杀时,老母、兄长一家皆遭毒手。如此家仇国恨,理应必报,但身为一介草民、生性懦弱的他却选择了苟且偷生。与军统特务老鲁熟识后,他被动地成为抗日队伍中的一员。后来,老鲁命令他利用其南京领事馆厨师职务的便利条件,毒死前来参加宴会的日本军政要人。对此,骆宁安犹豫不决,因为这对于讲究职业操守的厨师来说,在食物中放毒杀人,碰触了职业底线,有违其职业良心,况且与他的天性也不合。但他最终还是全力以赴,圆满地完成了“猎舌”计划,这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饮食杀敌,则义不容辞”[4]300。可以说,胆小怕事、温顺忍让是骆宁安的天性,杀人是不得已而为之,有违他天性。他最后选择“猎舌”计划,是道义使然,是“大道”之凛然正气战胜了骆宁安的天赋之柔弱之性。“宁安叹了口气,就算是地狱之行吧,总要有人下地狱”[4]301,骆宁安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投入到抗战中,正是人性的升华、人道的体现。
“道”既是人必行之路,必有其必然之理,故此,写人道还需进入“必然王国”。描写战争的罪恶,以夸张、戏谑、血腥的方式博人眼球容易,而既能感性地描写战争的各种情态又能理性地反思战争则不容易。《猎舌师》的可贵之处在于克服了从受害者的角度情绪化地描写战争的流弊,对战争进行整体的反思,揭示了人之“大道”。战争固然有正义与否之分,进而有受害者与施害者之分,但要全面反映战争,揭示战争的根源,忽视任何一方都可能有盲人摸象的弊端,这也是《猎舌师》卓尔不凡的地方。事实上,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而且也损害了广大日本民众的利益,最终伤害的是整个人类群体。或基于这样的拷问,《猎舌师》对抗日战争的反思——包括战争对日本人民的伤害,日本最终输掉这场战争,主要是从日本人的视角进行的。长谷川不过是一个出身下层、企图通过战争来实现自己梦想的普通人,他对战争并没有多少深刻的认识,只是怀着个人懵懂的理想踏上战场。不久,他从一个普通军人的良知出发,感受到战争与罪恶相伴,他“讨厌罪行,但崇拜伟大的战争”,并以“谁又分得清战争与罪行呢”为自己开脱,这恐怕是许多侵华日军普遍的心态。随着战争的持续,经历的罪恶与荒唐也就越多,长谷川对战争和自己理想的怀疑及由此而来的幻灭感也就越强。“中尉其实是孤独的英雄,他的敌人,不是川军,也不是数不清的中国军队,而是世界的无意义。当家族荣誉、武士精神这类玩意儿,在这场不义贪婪的侵略面前,被涂抹了太多的脂粉,中尉这样的‘古代英雄’,只能将这种对世界的抵抗,孤独地进行到底”[4]35,这是长谷川的自我反省,也是对这场战争清醒而痛苦的反思。可以说,日本侵华战争的失败,首先是日本自身的失败。最后,长谷川迷失在洞中,在临死前,他眼前出现了中国最终取得战争胜利的幻境,相由心生,这其实就是他内心的声音。认识到战争的邪恶,隐约感觉到战争失败的还有鹤田英秋和水源清。“少尉只是深深地感到厌恶。无穷无尽的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无论如何也杀不完。荣誉、女人、金钱,都能带来刺激,可少尉害怕上级军官的口令声。粗野、威严的声音响起,意味着要走上死亡之路。无数死亡,都在加强和暗示挫折。”[4]191这是鹤田英秋每次战斗前不断重复的心理暗示。鹤田英秋并不想参加战争,也不想通过战争建功立业来改善自身的处境,目睹日本军人在战争中的罪行更是让他厌倦战争。厌恶战争却又被裹挟着不断地进行无情的战斗,这使与鹤田英秋有同样心态的日本军人很受伤:他们已认识到其行为背离了人道——人的必行之路,这不是人应该过的生活,但却无日不在重复着这样的生活。正如昙智法师所说“白莲者,与他有上世纠缠,当避之吉”的偈语,可以说是对中日战争结局的暗示——不义必定决定了日本的失败。鹤田英秋死前似乎是在灵异的引导下,走进村寨,被天赐所杀,可以说是他内心心魔的结果。所谓“心魔”,其实就是入歧路、心智迷失、内心混乱的扭曲状态。心魔占据人心,使其背离人道,作恶多端,在毁灭他人时,最终会毁灭自身,这也是《猎舌师》反思日本侵华战争的独到之处。
《猎舌师》不仅表现了不同人物应物而生、因人而异、瞬息万变的情感世界,也透过个体的情感世界揭示了普遍的人性,还由性及道,从“‘人性’来指示出‘人道’”[5]11,彰显了“文学是人学”这一深刻、丰富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