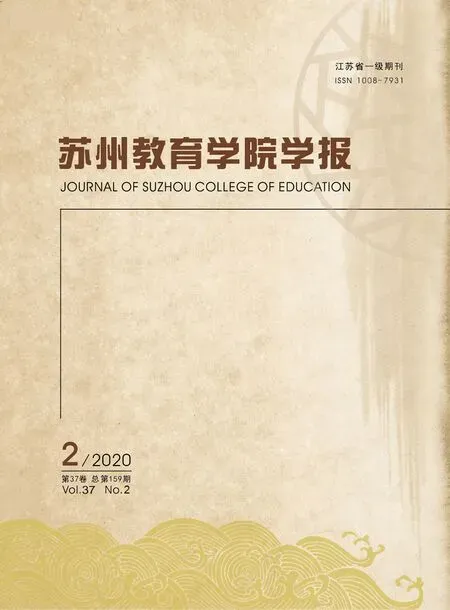梅洛-庞蒂审美深度问题研究
2020-02-25盛颖涵
盛颖涵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莫里斯·梅洛-庞蒂(Moris Merleau-Ponty)是法国现象学哲学家之一,他开创了以身体(corps)为核心的知觉现象学理论,同时也蕴含了一定的存在主义色彩。他早期思想中的“深度”(profondeur)概念主要是关于空间的探讨,后期则主要对绘画进行分析,这使深度回到了视觉的源头,毕竟这个概念的原始意义就是视觉层面的。但梅洛-庞蒂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还揭示了深度的第二层含义,即存在的意义,而这两重含义都建立在回到主客对立、身心二元之前的原始经验世界的基础上。
一、空间中的视觉深度
在传统哲学观念中,无论经验主义还是唯理主义都认为不存在深度,他们把空间当成自在客观的,与之相应的是,主体可以处于空间中的任意角度对事物进行全方位透视,因为主体处于上帝视角,从某一个角度看是深度,换一个角度就变成宽度了,所以,深度是侧面的宽度。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认为,认识主体应该无所不在,物体内部也就变得无所隐藏。在笛卡尔那里,空间是理想化的空间,看也是纯理性地看。与其说一个物体在另一个物体之后,不如说在它之外,事物与事物间没有隐藏的空间,它们都被心灵之光透视穿过。“在我注视着一个画面的时候,我能部分地看见深度,这是一个人人都能接受而其实并不存在的深度,它为我构射出一个幻象的幻象……这个存在物有两个尺度,它让我看见了另外一个尺度,这是一个被穿透了的存在,正如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一扇窗户……然而,窗户最后只能开向‘外在于另一个部分物体的部分物体’,开向高度和宽度(它们只是从另一个侧面看的),开向存在的绝对实证性。”[1]144在笛卡尔看来,透视所造成的三维立体效果即深度感不可能被理性之眼“看见”,因为那是并不存在的空间,换句话说,深度就是宽度而已。为了确保理性之眼的真理性,笛卡尔求助于上帝,通过一个无所不在的绝对者将空间透明化。在从以身体出发的知觉转向以理性为核心的思维,也就是从“眼”到“心”的转换中,深度消失了,即使为感官之眼所见也会被当作错觉否定,因为感官会骗人,但理性不会。梅洛-庞蒂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线性透视(linear perspective)的发明是建立在把空间看成是自在绝对的,可以离开主体独立存在的观念之上,在把知觉空间抽象为几何空间这一点上,与笛卡尔不谋而合。人们追求一种“准确无误”的绘画,他们放弃“天然的透视法”,转而推崇一种“人工的透视法”,前者是指古希腊时期建立在视觉直观基础之上的方法,“由于人眼的结构是球面而非平面的,因此古代透视的结果是:‘直线被视为曲线,曲线被视为直线;柱必须有微微凹进去的曲线,以免出现弯曲。……古老的光学理论比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更符合主观光学印象的实际结构。因为它将视域视为一个球体,古老的光学系统始终无一例外地保持着这样的观点:表面的大小不是由物体与眼睛之间的距离所决定,而仅仅由视角的宽度决定,因此严格地说,物体的大小之间的关系只能以角度或弧度表示,而不能用简单的长度量度表示。’基于人的双眼视觉,它所得到的是一个异质的、不断变动的心理学空间结构”[2]。而文艺复兴时期“人工的透视法”则建立在几何学基础上,它将人眼结构作了平面化处理,将感性直观的空间转变为理性的数学空间,“线性透视的概念忽略了知觉视觉的复杂性,导致它们还原到一个灭点并聚焦于一致性,在空间、光和气氛效果方面,艺术家呈现了一个比任何感性现实更清晰、更有条理的现实”[2]。
笛卡尔认为:“绘画的全部能力都建立在描绘的能力之上,而描绘的能力建立在与自在空间之间的规律化关系之上,就好像透视的投影方式所提供的那样。”[1]142绘画的任务就是将心灵发现的客观空间规律复制到纸上,而这种规律显然不可能通过多变的感官获得,而只能经由心灵,感受是个人的,而理性是普遍的,所以,通过理性的透视原则对空间规律的再现也必定可以得到普遍承认。对绘画而言,无论是再现手法还是再现内容都似乎更接近科学而非艺术,它被一种客观认识所要求,那么,绘画所追求的就不是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和天马行空的各种想象,而是一种唯一的作为真理的完美典范。它描绘了一个符合理性的世界,却与感觉的真实相悖。用潘诺夫斯基的话说,这是“主体的客体化”,不仅事物,连人自身也成为数学空间的一个元素。但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法果真符合笛卡尔的空间观吗?这其实是把现代空间观强加于线性透视法之上,因为绘画所营造的空间不能等同于匀质、无限、纯粹抽象的数学空间,无论如何,绘画需要借助物质媒介,而潘诺夫斯基否认了这一点,他以“窗口理论”来说明绘画的物质表面如同透明的玻璃,吸引人们“穿过”自身投射出三维空间,因此,物质媒介与想象空间被分开了,绘画所表现的空间虽然符合几何规律,但不仅仅是几何规律,它包含了物质媒介与想象空间的双重知觉,而且必须与其他再现方式相结合。潘诺夫斯基想通过世界观的变化来说明线性透视的诞生,但实际上“他首先把线性透视法设想为处理画面空间结构的抽象数学法则和几何投射,然后再把纯形式化的几何投射面直接应用到绘画表面之上”[3]。而阿尔贝蒂在《论绘画》中则表明,数学可以帮助绘画但不能等同于绘画,因为后者无法脱离质料,归根结底,绘画处理的是可见物。潘诺夫斯基是在笛卡尔——牛顿的几何空间框架下来看线性透视法的,但阿尔贝蒂更相信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空间观,前者是纯粹抽象的几何空间,后者是包含感知的物理空间,两者截然不同。
由于梅洛-庞蒂深受潘诺夫斯基的影响而将线性透视法营造的空间等同于笛卡尔式的几何空间,他才会说笛卡尔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透视法的启示,但这显然是对线性透视的曲解,不仅如此,线性透视反驳了笛卡尔的理论,因为它把观看者的眼睛作为中心,以主体视角为出发点建构空间,因此,只能呈现出特定角度和特定时间的事物,事物不是透明的,空间也不是自在的。个体视角的产生源于身体,主体与对象始终处于一定的空间关系中,这种空间不同于几何空间,在客观的几何空间,于观察者而言,正在知觉的身体与知觉的对象一样都是客观空间中的客体,思维的心灵和知觉的身体被分成两部分,后者是需要被超越的对象,因此,客观空间意味着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但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并不是一个被动感知的物体,也不是由各个器官拼凑起来的机器,它具有一种整体性,有自己的空间图式。身体以自身为初始坐标给世界定位,可以说没有身体也就没有空间,它不是在客观空间中产生的一个物体,而是寓居于其中,与空间一同诞生,方位和距离必须以身体为基点来区分和衡量才有意义。因此,身体空间比几何空间更为本源,而线性透视法正是以主体视点为初始坐标来构造空间的。笛卡尔告诉我们深度并不存在,但线性透视法就是要制造视觉深度,取消上帝视角,开启人们对三维空间的想象,用知觉和想象替代纯粹理性地“看”。深度意味着“我”与周围事物的距离已经确定,正因为从“我”而不是上帝的角度出发,世界才向我显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深度不再是第三维,而是第一维,“然而包括其他维的一个首要的维并不是一个维”[1]153。因为“深度之为维度的根本意义并不在这种实际的计量之中,也不仅仅在于以几何的方式把世界看作是刚好三维的,而是在于让我们发现在事物之中存在着一些其自身并不可见,却能够使得事物成为可见者的东西。亦即是说,‘深度’的意义恰恰在于它自身‘什么都不是’,但却能够使得可见者成为可见的。”[4]深度既揭示了一个三维的世界,又揭示了我们带着身体的视角性进入世界的方式。
梅洛-庞蒂说,线性透视法并非一劳永逸的秘诀,线性透视法再现三维空间的能力的确是长久的,他所批评的是把绘画当作精确再现世界的摹本,使之仅仅成为一种投影技巧的观念。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线性透视法一劳永逸地营造出了视觉深度,但由于它把知觉整体性简化为单点的视觉能力,并且对几何规律的相对倚重多少遮蔽了事物的存在深度。当塞尚在寻找深度的时候,他寻找的是对事物存在的体验,因此,绘画不会永远只满足于提供视觉深度,它还要展现存在的深度。
二、存在的深度
自然科学是从前科学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中发展出来的,通过数学化的方法来探索世界的规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世界与经验世界逐渐分开,然而,“理念化了的自然开始不知不觉地取代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5]。并尝试用科学理念来“规训”经验世界,倾向于把我们从自然中发现的诸如因果性一类的素朴观念提升为一种普遍的“先天形式”,认为这些精确的规律必然能够涵盖一切事件。它企图把科学符号和数字当作“真正的存有”,让科学世界凌驾于经验世界之上,前一个世界被打开,而后一个世界被遮蔽,科学主义忽视了经验世界才是并且永远是真正的源头。在后期的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看来,我们早已将这个通过身体知觉到的经验世界遗忘,并且也遗忘了作为能知觉的、会追问存在意义的主体。所谓“存在”是一种先于主客二分和各种抽象思维之前主体与世界的原始亲密关系,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主体寓居、操劳、逗留于世界,“我”与事物打交道的方式不是局部且抽象的认识,而是在知觉场中以整个身体去感知,“这个知觉场不断地纠缠着和围绕着主体性,就像海浪围绕着沙滩上搁浅的船只的残骸”[6]266。因此,主体在世界中存在不是一种现成状态,而是彼此交融、不断生成的状态。而绘画绝不可能如笛卡尔认为的只是镜子般的投影技巧,它要从蛮荒的世界汲取意义,让人们从认识回归知觉,从科学世界返回经验世界,回到主体与客体尚未分离的交织状态。
塞尚认为,古典派大师是“用想象和伴随想象的抽象化来取代真实……古典派是在作一幅画,我们则是要得到一小块自然”[1]49。古典派希望用永恒的理念之真来取代不断变化的眼见之真,他们更依赖定理和公式而不是真实的感受和直觉,要对绘画进行精确布局,对轮廓、结构、光线等要素妥当安排,但在这种人工的完善中,事物丰富的感性特征被大大削弱,因此深度也就消失了。与此对立的是印象派,他们从画室走向自然,重视眼之所见,强调瞬间的感觉,捕捉表象之真,他们虽然“恢复”了刹那间真实的视觉感受,但由于过分重视对氛围的描绘和色调的分离,景象变得模糊而破碎,轮廓被光线和空气晕染得几乎无法识别,在印象派这里,事物自身的分量和深度消失了。塞尚的作品能够让我们回到物体本身,让物体从内部散发光芒而不是像古典画作那样被精心安排的光线从外面照射,也不是像印象派那样让其消失在模糊的色块中。塞尚的作品既呈现出各种瞬间的感官真实,又力图呈现出事物稳固而坚实的结构,这两者在古典派和印象派那里水火不容,而在塞尚的绘画中,这种二分法却难以立足,因为他“从不相信有必要在感觉与思想之间、就像在混乱与秩序之间做出选择”[1]46。塞尚的画作正带领我们回到源头,在一切对立出现之前,在一片混沌中呈现自然的本源,这与梅洛-庞蒂追溯知觉世界的本源性不谋而合。
(一)从线条到色彩
“瓦雷利说画家‘提供他的身体’……正是在把他的身体借用给世界的时候,画家才把世界变成绘画。”[1]128用身体而不是思维,意味着“我”与世界必须要从认识关系返回存在关系。既然如此,那么画家的“看”就不仅仅是视觉的“看”,而是带着整个身体、打开所有知觉域投入其中,因此“每一笔中都应该包含着空气、光线、绘画对象,画面以及绘画的特色与风格。把存在着的表现出来,这是一项永恒的任务”[1]145。而深度正是“物体或物体诸成分得以相互包含的维度”[6]336,事物以其整体性向拥有整体知觉的“我”呈现出来,感官的统一和物体的统一本身相互关联,身体不是各个器官的总和,事物也不是各种性质的黏合物。所以,在欣赏一幅画的时候,我们不是只用眼睛去扫视,而是全身心地沉浸于其中,使知觉场对其开放,在各种感觉的交错中进行体会,感受审美对象各个层次的特质,从而使深度绽开。比如,面对塞尚的《苹果与橘子》,画中的水果拥有沉甸甸的质感,承受着自身存在的重量,它们好像要从画面中落下来,就像从枝头落到土地上一样。每一个水果都满含炙热的阳光、香甜的味道和丰腴的生命,每一笔都显现出肉的多汁与核的坚硬。它们并不是一动不动、死寂般地待在那里,它们活着,并且永远活着,闭上眼睛,仿佛能听见它们的呼吸。正是在主客未分的原初身体体验中,感觉的丰富性与事物本身的多样性相互激发,相互契合,正是在审美中,“我”与事物的原始存在关系展现出来,深度也与之一同诞生。
“如果我们希望世界在它的深度中得到表现,描抹就应该由色彩来完成。”[1]48然而,在传统绘画中,素描是最重要的,事物的线条和轮廓相比于颜色被认为更客观更稳定,前者是可以确定的性质,后者则更依赖于感官而显得变动不居,因此,颜色只能是一种装饰并依附于线条。事实上,在感受事物的时候,物与物之间不可能有极为清晰的界限,每一个事物的边缘都相对模糊,与背景相融,并且彼此之间相互关联,因为观看产生于视觉场,我们的视线不是点状的,它始终围绕着一个晕圈,随着目光移动,事物依次从背景中凸显,周围其他景象隐没在边缘域中,所有东西的形状不可能如几何学一般精确。所以,古典绘画对清晰轮廓和精确线条的追求就会不可避免地使事物丧失深度感,它被剥夺了真实的存在,其丰富而不可穷尽的内在性也被抽象化。因此,物体存在的深度要由颜色来恢复,视觉空间的深度也要由颜色来营造。
古典派作品主要通过对传统透视法的承袭而不是对事物的真实观察来体现空间深度,线条必定在消失点处交汇,物体占据的空间必须严格依据近大远小的比例,桌布两边的桌边线一定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这是由理性法则构成的世界,而塞尚想要打破这种规则以达到“眼见之真”,“力求获得深度感但不牺牲色彩的鲜艳性,力求获得有秩序的布局但不牺牲深度感”[7]。塞尚的画作力图表现体积的实在性和坚固性,用不同颜色的笔触描绘物体的各个面,以色块的倾斜或变形来表示侧面,同时采用反复叠加的轮廓线形成不断后缩的平面来达到立体效果,并通过颜色深浅的过渡暗示空间的后退,形成深度感,这是由于一种“‘中值混合’(middlemixtures)调节法之营造空间的方法:两种离它们‘源色’有着‘等距离’明度、色调差别的颜色的混合,这种混合让塞尚画布上的颜色相互之间的界限得以中和与慢慢消解”[8]。这样就使色彩从线条的束缚、事物从几何学的抽象中走了出来,既保存了瞬间的鲜活知觉,又不让画面陷入平面化,这就是塞尚发明的“活的透视法”。
从存在的角度来看,塞尚认为“大自然并不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它有着深刻的内涵;色彩则是深层内涵的表层表达,它们从地球的根部萌发,是地球的生命,观念的生命”[9]。大自然的深度出于一种原始的混沌,其中既有丰富变幻的表象也有亘古长存的秩序,既有孕育生命的活力也有埋葬死亡的冷峻,它是光明的显现之地,也是阴影的逃遁之所,它有着不可穷尽的神秘,塞尚的《圣维克多山》就展现了这种自然的深度。近处大块的绿色和黄色显示出自然的生机,有一种向上的蓬勃之力和内在动势,通过层次的逐渐过渡,目光聚焦到处于中心顶点的山峰,冷色调与结构相对简单的山体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画面中的景物有一种稳定而坚实的秩序感,但变化并未消失,光线在草木间抖动,空气中弥漫着田野的清香,沉默的土地承载着生命。景物的轮廓“既模糊又实然”,它们彼此相连却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这里有涌现也有寂静,有凝固也有流动,大自然如此这般地显现自身,事物彼此相互应和,观者也同它们一起共鸣,而这共鸣就是存在深度的显现。
(二)从对立到交织
深度不是事物自身所固有的某种性质,必须与主体的深度相关联,之所以在审美活动中两者能够产生共鸣,是因为“我”与对象之间存在着“共通感”(Einfühlung),这个共通感的基础则是“世界之肉”(Chair du monde),这里的“肉”既不是物质性的也不是精神性的,它是一种普遍的“元素”,类似于古希腊人谈论的水、火、土、气。梅洛-庞蒂认为:“我的身体是用与世界(它是被知觉的)同样的肉身做成的,我的肉身也被世界所分享,世界反射我的肉身。世界和我的肉身相互交织(chiasme,感觉同时充满了主观性,充满了物质性)。”[10]317当“我”对对象进行审美的时候,不是站在它之外而是在它之中进行感知的,因为“我”与它同质,“我”感到自己正从事物中涌现出来,它们似乎成了“我”身体的延伸。但这并不是唯我论的,因为另一方面,事物并不是被动地等待我们去发现的,它们召唤我们,向我们诉说,“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我在那里倾听着……”[1]136不同于利普斯将主体的深度单方面投射到对象身上,这里的感知是双向的、可逆的,当“我”不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象之上,而是回到知觉的原始状态,在一种澄澈空明的心境中,不是去看而是等待景象浮现,不是去说而是等待事物在心底激起回音,仿佛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的身体既是可感者也是被感者,因此,“我”与世界始终相互包裹缠绕,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观者在看画,而是审美主体与对象一起萌生。存在的深度之所以能显现,就在于“我”与世界的同质性,以及建立在这之上感知的可逆性。
同时,由于肉身从来就不只是能感觉而已,它是感性与精神性的交织,审美深度也只能在这种交织中产生。梅洛-庞蒂“将精神定义为身体的另一面……身体由于有了这个另一面,它就不是可以用客观的语言和自在的语言来进行描述的——这个另一面漫溢于身体,侵越到身体,隐藏于身体中——同时它又需要身体,并终结于身体之中,停泊于身体之中。存在着精神的身体和身体的精神,以及它们之间的交织”[10]332。塞尚的画里呈现的不只是鲜艳颜色的表面形状而已,它们既有独特的感性外观,也蕴含着通向宇宙深处的精神:万事万物相互关联,彼此应和,有着内在律动和节奏,自然与“我”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融为一体,因此,我们只有通过身体去体会和把握画中蕴含的自然的力量和宇宙精神的形式。
梅洛-庞蒂认为,深度的根源在于“完全还原的不可能性”,只有绝对的精神才能被彻底还原,但我们不是纯粹的精神,事物也不是由意识创造出来的,我们和事物都是肉身。对事物来说,拥有一个肉身意味着不再透明,各个维度在其中镶嵌缠绕,隐藏与显现相互交织,其意义永远取之不尽,我们对它们的感知是一种“流动的逼近”(Aprroximation,胡塞尔)无法达到完全透明。主体也因为肉身而有深度,拥有感觉能力首先必须以预先构成能力为前提,也就是说,感觉必须以能感觉为前提,即与潜在的周围环境相互构成、同时发生的能力。与此同时,“在我的感觉和我之间,始终有阻止我的体验成为自明的一种最初经验的深度”[6]276。这种“最初经验”可能是经由数万年累积下来的“集体无意识”以及在文化中习得的经验方式,它们共同构成了主体的深度。深度始终是潜在的、生成的,只有在审美活动中,有深度的主体与事物之间才能相互开掘,正由于深度无法穷尽,所以,塞尚说他的作品“只是对绘画的不断尝试和不断接近”,创作如此,对作品的解读亦然,深度在显现中总有遮蔽,创作和解释都难免带有些许未完成性。
三、结语
梅洛-庞蒂以肉身为核心要求从主客对立、身心二元的科学世界回到浑然一体的前反思的生活世界,要求绘画从追求理念的真实回到存在的真实,深度概念的转变体现了这种变化。在上帝视角下的视觉空间里,思维宰制感官,因此,深度被宽度取代,梅洛-庞蒂追溯了身体空间的本源性,视看必然从一定视角出发的特性使深度重现。在艺术领域中,画家以传统规则和理念作画,使事物丧失了存在的深度,而塞尚让颜色取代线条、使轮廓让位于深度,每一笔都充分体现了事物中各维度的相互包容性,丰富鲜活的感觉与深邃永恒的精神结合在一起,使审美深度在主体与对象的相互应和中逐渐显现。与此同时,存在的意义也随之产生。主体与世界作为被祛魅的透明物又因为深度而复魅,因此,深度从一个维度生成了一切存在可能发生的原始条件。绘画也从追求精确性和相似性走向了感觉与存在的表现,它不再依附于被模仿物,而是寻求建立一种与自然相平行的“等同体系”,因此,绘画从一面光学镜子变成了一个有深度的不透明物,拥有了独立的价值和表现空间,而这一点似乎开启了杜夫海纳“准主体”的概念,也影响了后者对审美深度的阐释。